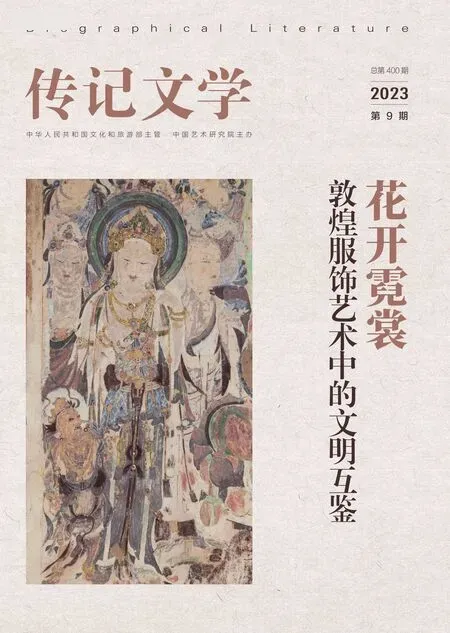花椒:调拌味蕾三千年
2023-11-03白玮
白 玮

在当代川渝火锅的策动下,花椒被今天的味道江湖固化为麻的概念,但这显然是大众对花椒的一次过于草率的误读。花椒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记忆里,一直是个神圣而严肃的存在。从古老的巫司祭祀,到汉朝的椒房乃至后来的屠苏酒,花椒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里一直都扮演着无限尊崇的角色。
掀开历史的灶台,会发现花椒的香气一直缭绕在庙堂和江湖的上空,三千多年来,以它独有的香味调拌着中国人的味蕾。
椒房殿的香气
公元前202 年,夺得天下的汉高祖刘邦,为彰显汉王朝的皇家气派,特命萧何在长安城的西南方位先后营造了两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宫殿,一座是长乐宫,另一座是未央宫。在这两座大型的宫殿里,他都特意给吕后建造有专属的居室,这个专属于皇后的居室就叫作椒房殿。后来班固在修《汉书》之余,还曾经以《西都赋》为题激情澎湃地写了一篇大赋,文中就提到了椒房殿:
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
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后宫则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
之所以把皇后居住的宫殿命名为椒房殿,盖是因为这座宫殿的墙壁都刷着一层花椒泥的专用涂料。据《三辅黄图》卷三记载:“椒房殿,在未央宫,以椒和泥涂,取其温而芬芳也。”李善引《三辅黄图》注曰:“长乐宫有椒房殿。”
以花椒和泥粉刷墙壁,就像我们今天的房屋装修,在刷一遍大白后,还要在外面抹上一层带有清新气息的环保漆。这样的墙壁,不但能给皇后以冬暖夏凉、怜香惜玉般的关爱感,还能使房中荡漾着一种迷离的花椒芬芳。
自从吕后住进椒房殿的那一天起,椒房就成了后宫至尊地位的象征,椒房从此也成了皇后的代称。汉文帝时,椒房的主人是窦皇后,也就是那位在电视剧《汉武大帝》中权倾一时的窦太后。再之后,住进椒房的则是少年刘彻金屋藏娇的陈阿娇,随着汉武帝的继位,她也以皇后之尊住进了椒房殿。在阿娇被打入冷宫后,住进来的则是新任皇后卫子夫,她就是汉代著名战将卫青的姐姐。
以此观之,椒房不仅是皇后的代名词,更是一个后宫女人尊贵身份的标签,因此后宫的佳丽们从进入皇家的那一天起,无不把能住进椒房作为最高梦想。也由此,她们在这个相对密闭的空间内,为了能够获得帝王们的“椒房之宠”,从而上演了一幕幕攻心的大戏,一生的朝华也就此湮灭在宫阙之内缭绕的椒香中。正如唐代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感叹的那样:
西宫南内多秋草,
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
椒房阿监青娥老。
汉家的帝王们为何会如此看重花椒?难道仅仅是因为花椒底层隐隐散发出来的暗香吗?在花椒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皇家心态和社会逻辑?
献给神的祭品
其实,早在汉代之前,花椒的身影就已经广泛出现在周王室和各地诸侯的宏大叙事中了。之所以说关于花椒的叙事宏大,因为它最先不是作为调料的概念而出现在厨房里,而是作为一种神圣的香料出现在祭祀祖先和神灵的祭坛上。
用食物祭祀神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传统。在中国古代,祭祀一直是国家的重大礼仪活动。《左传》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祭祀和战争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
古之祭祀,名目繁多,系统复杂,仪式肃穆,不但要祭天祭地,还要祭日月星辰和山川河流;不但要祭祀祖先,还要祭祀各路神灵。而且,一年四季,基本上每个季节都有重大的祭祀活动,夏至要祭,冬至也要祭;播种时节要祭,收获时节也要祭。直到今天,不管是敬佛、祭灶、敬财神,还是逢年过节、祭奠祖先、婚丧嫁娶,很多人都会部分保留着这种传统,祭拜各路神仙,并向其敬献一碟碟精美的食物。
在周王室的诸多祭品中,花椒是一个重要的祭物。《诗经·周颂》篇里有一首颂诗《载芟》[1],讲述的是秋收后周王室用新谷祭祀宗庙时的情景。在这首诗里,就特别提到了花椒: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
有椒其馨,胡考之宁。
这两句诗表达的意思就是:敬献给神灵的食物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整个国家都会荣光;花椒美酒的馨香溢满四方,家里的老人都会幸福安康。之所以用花椒作为祭品,因为在古老的祭司认知体系中,他们认为花椒的香气可以通达上天,有降神、引神的作用。就像听到舜帝奏响韶乐时,凤凰也会飞来,美妙的馨香和韶乐的原理逻辑是一样的,都能使神灵愉悦,从而为人间降下祥瑞。
这样的认知源于古代的巫祭传统,到周朝时已经形成了成熟固定的模式。这一点,在《诗经》的其他篇章中也能找到佐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陈风·东门之枌》[2]:
东门之枌,宛丘之栩。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
穀旦于逝,越以鬷迈。
视尔如荞,贻我握椒。
这首诗描写的是周朝时陈国的青年男女们聚集在东门的榆树下相互求欢的场景,青年男子们期盼漂亮的姑娘们趁着良辰吉日,送给他们一把花椒以作为定情的信物。陈国,在今天河南的淮阳和安徽的亳州一带。陈国的人民有崇信巫鬼的传统,这和他们的第一代君主夫人太姬的偏好有关。太姬是周武王的长公主,后来嫁给陈国的第一代君主胡公满。这位公主特别喜欢祭祀和巫术。《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有太姬歌舞遗风。”太姬的身份十分尊贵,所以因个人的喜好而把整个国家的好巫风尚带动了起来。
据此,也有人认为,这也许并不是一首完全表达男欢女爱的情诗,说的应是陈国民众祈福求神的祭诗:在东门的榆树下,宛丘高台柞树的林荫里,民众载歌载舞,祈求像锦葵一样漂亮善良的女巫——太姬的代言人,趁着大好时光,赐给他们一把吉祥的花椒,让他们也能享受到神灵的护佑。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因为在屈原的《离骚》里也能找到相通的表述,屈原是这样说的:
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3]缤其并迎。
灵氛和巫咸都是上古时期的神巫。糈是粳米,代表着美好而有香味的食物。椒就是散发着香味的花椒,椒和糈米都有引神的作用。在这里,屈原通过瑰丽的想象,勾画了一幅幻境:他循着巫神灵氛占卜的方向,用散发着香气的花椒和精美的食物向神灵发出诚挚的邀约。闻到花椒香气的巫咸女神,便引领着百神从天空降落在他的身边。与此同时,舜帝还派出九嶷山的众神,缤纷地出来迎接。
可见,在周朝,不管是在政治中心的周王室,还是在诸侯封国的陈国和楚国,都有用花椒祭神请神的传统。同时,在先秦的各类文献中,我们也没发现把花椒作为调味品用在厨房的记载。此时的花椒,更多的是一种祭物,它展现出来的是形而上的神圣性,而非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形而下的调料。
在上古时期,花椒所表达的意象还不仅如此,更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系统。
社会化寓意
通过对先秦时期花椒身影的考察,我们发现:花椒在汉代之前的民间,除了作为一种祭品,有引神降神的功能外,更由此演化出了一个纷繁复杂的隐喻世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古老的花椒几乎构筑了一个独特的花椒社会。
首先,从字形上来说。椒字由木和叔两部分组成,木字无须赘言,重点说“叔”字。“叔”也由两部分组成,左边为“尗”,右边为“又”。“尗”代表豆子的形象,像豆科植物的茎与枝。上部指的是枝茎上结的豆荚,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豆;下部像豆成熟裂开后,指的是散落在地上的豆粒。叔字右边的这个“又”字,是个“手”的形状,表示的意思是用手去拿。
汉魏时期的“叔”字异体,早在秦简中就已经成形,这个写法保存了西周金文的一些特征。“尗”与“又”合起来的意思是:用手将散落在地上的豆粒拾取起来。故此,“叔”的本义为“拾”“拾取”的意思。叔的上面加上“艹”字头,就是代表草本的大豆,在古代,大豆之所以称之为“菽”,即是由此象形而来;叔的左面加上木字,表示的就是花椒。

清代徐鼎纂辑《毛诗名物图说》中的椒
古人之所以用“尗”字来表意豆子,它的寓意是多子多孙,花椒的椒字也是由此寓意演绎而来。花椒果实的外形和豆子有某种相似之处,都是一串串的,籽实繁衍茂盛。中国自古就有子孙满堂的朴素的社会心态,故此由物象而喻人事,就把花椒寓化为多子多孙的象征。
其实,由物象而喻人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创造逻辑,并因此造就了传统中国的一个独特的精神和信仰体系——看见乌龟,就寓意人间的长寿;读到葫芦,就联想到人间的福禄;看到并蒂的莲花和鸳鸯,就用来表达人间的爱情;把大枣和花生放在一起,就寓意早生贵子……这是民间一种朴素的原始崇拜的情感表达。
《诗经》的赋、比、兴修辞手法,接续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所以,在《唐风·椒聊》篇中,此处用到的花椒,采用的就是繁衍子孙的这一意象:
椒聊之实,蕃衍盈升。
彼其之子,硕大无朋。
聊,通常被作为语气词,没有实际意义,但出现在这里,也被当作“莍”,也有说法指代的是茱萸。因为茱萸也是古代的一种天然植物调料,它们的籽实和花椒的形态差不多,也是一嘟噜一嘟噜的,就像一座果实的房子。这几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花椒和茱萸的果实一串串地挂在树上,繁衍不绝,装满一筐又一筐。那位丰腴的妇人儿女众多,高大无双。由此,花椒因其籽实的相貌特征,被人为地完成了第一次意义上的升华。
其次,从气味上考察,花椒的籽实又充满香气。在古代,花椒通常和兰连在一起,称之为椒兰之香。椒和兰,皆芳香之物,故以并称。《荀子·礼论》说:“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
作为史上花椒的第一迷恋者,屈原对花椒的喜爱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在《九歌·湘夫人》中,他说:“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在《九章·悲回风》中,他说:“惟佳人之独怀兮,折若椒以自处。”在《离骚》中,他说:“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屈原之所以多次提及花椒,一方面大抵是因为春秋时期,湘楚之地卑湿,多瘴气,流行巫术。人们除了需要借用花椒之香祭祀和迎神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广泛的生活中用花椒来驱虫、辟邪和祛除湿气。因此,花椒在楚地的价值功用和肃穆性就远比中原地区重要得多。尤其在屈原的多重加持下,花椒更被升华为一种精神层面美好品德的象征;另一方面,屈原把菌桂、木兰、蕙茝、杜若等这些香草花木和花椒一起佩戴在身上,甚至缝制在衣服上,以此来彰显他与那些污浊之物的不同。尤为重要的是,他更借助这些香草来宣示他高洁的品性。随后,椒兰之德便被作为一种品德高洁的意象被固定下来,从而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共同的价值判断。
屠苏酒之源流
说到屠苏酒,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王安石写的《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那么,什么是屠苏酒?古人为什么要喝屠苏酒?这个酒和花椒又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呢?
所谓屠苏酒,其实是一种用各种香料浸泡的酒,类似于药酒,或者说是一种养生酒。这种浸泡酒就跟今天我们用人参、鹿茸、冬虫夏草、枸杞等大补药材泡制出来的二锅头一样。它是古时的劳动人民为了驱避瘟疫而于农历大年初一喝的酒,故此,屠苏酒又名岁酒。也有说法认为屠苏是古代的一种房屋,因为是在这种房子里酿的酒,所以称为屠苏酒。

清代姚文瀚《岁朝欢庆图》中迎接新年共饮屠苏酒的情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按民间的传说认为,屠苏酒是由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而创。按古代尊老之传统,通常饮酒,总是从年长者饮起。但这个屠苏酒的喝法却正好相反。它讲究的是先从年幼者喝起,然后从少及长,依次而饮,最年长者最后饮,逐人饮少许。宋代苏辙在《除日》中所记诗句“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反映的就是这种饮酒习俗。其实苏轼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一诗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
那么,具体到这个屠苏酒中放的都是什么药材呢?根据今人所制屠苏酒的配方,这个健康养生包里的药材大致有大黄、白术、桂枝、防风和花椒等。所谓屠苏酒,其实是一种椒酒。椒酒,也称之为椒柏酒。按《中国药膳大辞典》给出的配方,这种椒柏酒的主要材料是川椒37 粒、侧柏叶7 枝,泡之以白酒500 毫升。具体的做法是:将花椒和柏叶捣碎,置容器中,加入白酒,密封,浸泡7 天后,过滤去渣,即成。主要功用就是解毒和辟瘴气[4]。
根据荆楚之地的民间风俗,此酒主要在大年初一用来祭祖或祝寿拜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依然延续了先秦时期用花椒祭祀、迎神、祈福的古老传统。其实,这种酒的身影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它的前身正是屈原在《楚辞》里重点强调的“椒浆”。
何谓椒浆?就是以椒浸制的酒浆,古代多用以祭神。屈原在《九歌·东皇太一》中说:“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满怀真诚与虔敬之心,把最美味的食物和椒酒献给最尊贵的天神。自此,椒浆作为对天神和尊者的一种敬拜和祭奠的象征物而进入中国的文学叙事系统。后来,也用来表达对屈原的祭奠,最具代表性的有韦庄《题淮阴侯庙》中的诗句:“满把椒浆奠楚祠,碧幢黄钺旧英威。”又如王建《赛神曲》中的诗句:“椒浆湛湛桂座新,一双长箭系红巾。”再如刘长卿《巡去岳阳却归鄂州使院留别郑洵侍御先曾谪居此州》中的诗句:“帝子椒浆奠,骚人木叶愁。”不可胜数,溢满文坛。
由是观之,自汉高祖刘邦始,汉朝的帝王们之所以能给皇后建造一座具有标签属性的椒房殿,在椒房的背后实则蕴含着“播芳椒兮成堂”的传统建殿祖制和厚重的文脉。
融入人间烟火
那么,花椒的本体究竟是何物?竟能铺排出这么一个复杂的文化心态系统,构建出一个如此庞大的花椒大厦?
按今天的植物学给出的百科定义,花椒是芸香科,属落叶小乔木多年生植物,茎高,枝有短刺,因果皮有细小突出的油点呈斑状形似花,故名“花椒”。
花椒原产于中国,在中国各大区域都广为分布。作为一种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调料,花椒以麻和香行走于味觉江湖之上。生食则麻,乡土方在治疗牙疼时,都建议用疼牙咬住一粒花椒,通过麻木神经而起到镇痛的效用。炒熟的花椒有香味,尤其用油焙熟之后,花椒则能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味,所以民间多用花椒来烘制调味料,比较著名的像椒盐、五香粉以及遍布大江南北的十三香,用的主料都有花椒。但比较怪异的是,无论是它的麻,还是香,都不在甘、酸、苦、辛、咸传统的五味之列。麻作用于触觉,香作用于嗅觉。所以,花椒在五味的划分中,以其性辛,散温燥,入脾胃的味性而归类于“辛”。
如此,花椒是在何时从祭神的祭坛上走进灶台,被作为一种调味料被纳入到人间的烟火中的呢?那说来话就长了——
古代中国,药食同源,由祭品而至药食,故此花椒通往人间的生活之旅是从《神农本草经》开始,说花椒能“主风邪气、温中、除寒痹、坚齿、明目”。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补充说花椒可治寒痛和饮食不振,还编写了一首药方歌:
大建中汤建中阳,
蜀椒干姜参饴糖,
阴盛阳虚腹冷痛,
温补中焦止痛强。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椒纯阳之物,乃手足太阴、右肾命门气分之药。其味辛而麻,其气温以热,禀南方之阳,受西方之阴,所以能入肺散寒,治咳嗽;入脾除湿,治风寒湿痹,水肿泻痢。”而真正把花椒作为一种调味料进入食单,则是从魏晋时期开始的。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说:“今成皋诸山间有椒,谓之竹叶椒,其树亦如蜀椒,少毒热,不中合药也,可著饮食中,又用蒸鸡、豚最佳。”南北朝时期,吴均在《饼说》中记载了一些用花椒调制美味的方法,据说用“洞庭负霜之橘,仇池连蒂之椒,调以济北之盐,锉以新丰之鸡”而调制出来的饼食,“既闻香而口闷,亦见色而心迷”。
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也介绍了诸多关于美食烹调的方法,特别提到要用以姜椒等物作为调味料。唐宋时期,花椒作为调味品,已经被广泛使用。南宋林洪在《山家清供》里记载了一道关于“拔霞供”的趣事:有一天,他去武夷山拜访一位故人,遇上大雪天,猎得一只兔子。因为没有厨师烹饪,他的这位朋友就给他介绍了一种新吃法:把兔肉切成薄片,用酒、酱、椒料腌一下,把风炉安到桌上,用少半锅水,等水开了一滚后,每人拿一双筷子,自己夹肉放在开水里,来回摆动涮熟了吃。吃的时候,随个人的口味,蘸调味汁。同时还介绍说猪、羊肉都可以这么吃[5]。这种吃法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火锅。而在那时,蘸着的调料就是花椒,类似今天贵州的蘸水。到了元代,花椒更成了吃食肉类食物之必备调料。
明清以降,随着辣椒的传入,四川人在菜肴中大量放入花椒和辣椒,麻辣味也随之成为新派川渝之美食的标签。普天之下,要说花椒之香,以四川汉源和甘肃陇南武都的花椒为佳。除了拿花椒用来调制菜肴,也有用来品茗的。在唐代,人们还煎茶饮之。采嫩叶蒸过晒干,如炒茶之法做出一种花椒茶,消暑解渴而有余香。煎茶时,倘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以花椒等香料,更是人生难得之体验。
花椒之果实可以用来祭神和调味,殊不知,花椒之嫩叶也是一道美味。初春时节,将花椒之嫩叶采来,用水焯了,沥去水分,拌之以花椒油、香醋和酱油来吃,堪称人间凉拌菜至上品佳肴。另外,还可以把嫩叶裹以面糊,用油炸至焦黄,再蘸着椒盐来吃,一嘴下去,焦脆鲜香,令人沉迷。
一如现在,它被铺陈在百姓厨房的油锅里,正散发着三千年来的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