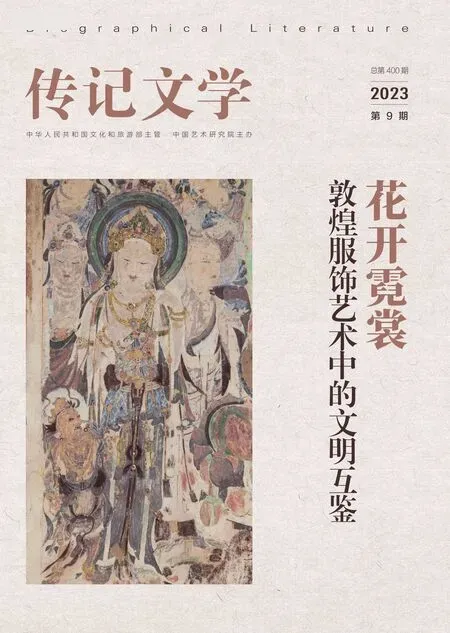八十年代师大校园里的先生们(九)
2023-11-03与之
与 之

北京师范大学西南楼旧影
一
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部分知名高校的学者身上有时带有一些“名流气质”,即便是谦和的态度,有时也难掩不可言说的矜持与距离。这里成因复杂,倒不一定真是有多么的傲慢。距离可能是基于某种认知的巨大差异,矜持也可能是源于人与人之间本能的戒备和自我保护,原本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80 年代我们熟悉的师大老师,却自有一份本真的性情,真率、自然,更多平实的亲切,更少故作的高深。这里,或许有一种师范教育与生俱来的“平民范儿”。
钟敬文先生是中文系最年长的学术大师,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家、诗人、散文家,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名誉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亲手建立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两大学科。我们在校之时,他已经年愈八旬了,但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有“人瑞”之相,据说80 年代初还常常搭乘公交车找诗人朋友如聂绀弩等喝酒聊天。虽然钟先生在中文系首先是学科创立者、大学者,但他自己却更愿意以“诗人”自居。相传先生生前表示,在他去世的时候,希望能够在墓碑上写上“诗人钟敬文”几个字,可见诗人的性情才是他心系神往的所在。诗人的真醇、率性和坦诚是先生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基本方式。我们在校的时候,钟先生以八旬高龄全力推进中文系的民俗学学科建设,常常在早上散步的时候构想一些必须要做的事情,一旦有了想法,就径直迈向学生宿舍,找人商量实施。先生往往起得很早,学生宿舍都还大门紧闭,这突然驾到的老先生不仅让尚在梦乡的弟子手忙脚乱,就连看守大门的老校工也惊诧不已。先生还喜欢郊游、在节庆日聚会。每到春天,就会临时起意:“走,我们春游去!”于是叫上他的十几个学生,自己租车、带饭,一起奔向郊野。散步是先生重要的日常活动,不仅起早散步,有时候伏案工作到下午,感到比较累了,也会在三四点钟找个学生一起去散步。那个时候,先生总是穿戴整洁,或穿大衣或穿中式对襟上衣,手执拐杖,在校园里徐步而行,路遇中文系学生,则停下脚步颔首微笑。
启功先生是国宝级的大师,声名显赫,高山仰止,但有机缘接近他的人,都绝不会产生高不可攀的自卑,因为他会同你打趣、逗乐,一派童真。李军在《乐育教行堪世范,励耘奖学惟吾师》(收录于周星主编的自印班书《岁月静好,情谊悠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78 级3 班40 年记忆》)中回忆说:“启先生在给我的赐字上落款‘启工’。我很诧异,问为何不用‘功’而用‘工’?先生纵怀大笑:‘你是军,我是工,工人对军人嘛!’”为研究生开课时他有一门课,涉及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丰富内容,却不是一般教科书上能够看到的,令人眼界大开,这叫什么课呢?启先生自行命名为“猪跑学”,取义源自俗语:“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1]启功先生的书法求者甚众,以先生的宽厚豁达,大概在那时也应承居多,拒绝偏少,不用说师大校内“字尽其才”,各种大小楼宇、学院系所、商店食堂,全是启功书法,就是京城内外乃至祖国各地,“启功体字”也是四处可见,从国家单位、高级宾馆到理发汽修,应有尽有。有一次,我们还看到一处小巷里的铁匠铺也赫然高挂启功题匾。据说这些市面招贴鱼龙混杂,真迹有限,赝品多多,从文物市场到街头地摊,都有不少专门伪造启功题字的贩子,我们都觉得有些无奈也有些遗憾,觉得这至少会部分损害启先生的社会形象。但是,每当有师大老师对此愤愤不平,严辞劝说先生“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先生总是眯上眼睛,笑嘻嘻地看着他们,不置可否,轻松通脱。有一次,有人从潘家园市场淘得100 元一幅的启功书法,转折呈送先生鉴定,先生端详了一番,居然连连称赞:“写得好啊,写得好啊,其实比我写得更好啊!”
二
师大中青年老师更多适性任情之人,尤其是活跃在教学一线的老师。
研究生毕业留校的老师常常与学生打成一片,赤诚相见,毫无造作。王富仁老师对待他课堂上的学生也是如此。在课下,你可以和他讨论任何问题,除了学术思想,还包括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情感历程,甚至一些敏感的话题。王老师最让人惊讶的是,无论你提出什么样刁钻古怪的问题,他都能够从容应答,条分缕析,仿佛这世界的一切秘密他都了然于心,那些敏感隐秘的部分同样不会遮遮掩掩,环顾左右而言他。但这里没有对思想能力的自夸,没有对广博知识的炫耀,而是一种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毫无保留的敞开和呈现,他愿意与你共同面对意想不到的人生的话题,又以自己的生命体验来承受这一话题,以人生的过程来证实、摸索其中的奥秘。他也不自诩就能一语道破最后的答案,但是却从不拒绝和年轻而大胆的学生分享其中的酸甜苦辣。80 年代后期,王老师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依然以这样的心态对待自己的研究生们。我的大师兄讲述过他毕业的故事:王老师带着一帮研究生在实习餐厅聚餐告别,可能大家都很兴奋,也可能是大家都有点离别的伤感,那一晚喝了不少的啤酒,餐厅服务员却不断催促“下班了”,王老师也有点喝高了,竟像那些青春叛逆的大学生一样拎起酒瓶直奔垃圾桶而去,最后狠狠地将酒瓶砸在垃圾桶里,一时间,满座效仿,一大箱酒瓶噼里啪啦之间全部化成了一堆碎玻璃!大师兄不胜酒力,已经踉踉跄跄,难以自主返回宿舍了。大家都还在商量着谁来搀扶、谁来善后,只听王老师大声说:“这是小事,我身体好,我来背他!”说完就蹲下身子,要把弟子背回宿舍。
古典文学的老师会有多种面相。

赵仁珪先生
唐宋文学的赵仁珪老师是启功先生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他的文学史讲述睿哲圣明,启人深思,时有对历史和经典的妙悟,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则是他的思想、情趣都深得启先生神韵,清通、旷达、自得其乐。最难忘的是学期结束前例行的辅导答疑,赵老师将课堂搬到了室外,在图书馆前的紫藤花架下觅一长廊,脱了鞋子,倚靠在廊座上随意而谈。那一天谈的是苏轼,他讲述着东坡居士的词如何“旷达”而非文学史所谓的“豪放”,又言之何谓“空静”。赵老师徐徐道来,旁边围着十数位备考的学生,或坐或蹲或立。他几乎不看大家,自言自语,目光投向远方的天空,仿佛回到了遥远的北宋,完全沉浸在东坡居士的诗歌境界之中,眉宇之间似乎萦绕着一种令人神往却不可企及的超凡之气。
韩兆琦老师是50 年代末毕业的学术大家,是《史记》研究的权威。他是另外一种激情型的师长,在古代文学学者中尚不多见。学生中传扬着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他为我们讲过汉代文学,慷慨激昂、声情并茂,仿佛司马迁就是他自己。遇到投缘的学生登门请教,常常一聊就是半天,滔滔不绝,恨不得倾其所有。陈仕持在《在师大感受师德的温暖》(收录于周星主编的自印班书《岁月静好,情谊悠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78 级3 班40 年记忆》)中回忆说:“韩兆琦老师住在小红楼,我至今记得他单独为我补课的情形。韩老师就坐在昏暗的书房里,对着我一个人侃侃而谈。他告诉了我朱东润先生的主张:学古代文学,先熟读《资治通鉴》,从熟悉社会历史入手再切入到文学。接着,他谈魏晋时期的社会情势,谈魏晋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谈魏晋士人的傲气与怪癖……越谈越来劲。谈话间,他的公子催他:‘爸爸,吃晚饭了!’‘等一会儿。’过了一会儿,第二次催,他又答:‘你们先吃。’我很是过意不去,老师仍兴致盎然。临走前,他又站起来从书架上找出两本书给我,免去了图书馆借阅手续之繁。有一本书里录有鲁迅的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这是韩老师指出的必读篇目。等我走出小红楼,已经九点半了。韩老师一对一地义务教学,一讲就是三个小时。”
受这些真性情的导师熏陶,80年代走出师大的研究生也多了些率性而为的真实。90 年代后期,我在一次会议上偶遇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杨济东先生,虽然年届中年,却直言快语,无遮无挡,童心毕露,言谈举止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80 年代的师大宿舍,一问之后,方知他就是80 年代的师大古典文学研究生,师从韩兆琦先生。那天,我和济东兄一见如故,有一种“基于师大气质”的认同感。那天晚上,我们聊到了许多80 年代他们研究生宿舍的往事,最“辉煌”的场景叙述是关于他们挑灯夜战,奋笔疾书,如何为中国文学的“重大”问题夜不能寐,据说他永远的记忆是与一位同学同宿舍居住,天天目睹他抨击文学时弊的激昂。一个炎热的夏夜,他一觉醒来,却见室友赤身裸体端坐案前,还在奋力耕耘,狭小闷热的宿舍,激情难抑的论述,竟让这位室友浑身上下大汗淋漓。
三
记得很清楚,我们刚刚跨进师大校门没几天,就有负责思想政治的老师召集全年级开会,强调大学生守则,其中特别意味深长地告诫大家:“大学,是不鼓励谈恋爱的。”在那个年代,青少年的情感生活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师大也不能不有所约束,不过,何谓“不鼓励”?这模棱两可的说辞显然也就是一种例行公事的告示而已。事实上,专业教师出身的班主任老师恰恰十分关心我们的情感生活,尤其是母亲般的侯玉珍老师,她颇为操心这批男生女生的交往友谊,衷心希望他们当中的有情人能够尽快牵手成功。有女生追求某个男生失败了,都会在第一时间向侯老师倾诉,侯老师也可能帮着出谋划策,寻找弥补撮合之道。到了三年级,有几个男生女生还是形单影只,侯老师的焦急程度可能不亚于当事者本人。凡是有热心人牵线搭桥,促成同学间的姻缘,她都乐见其成,鼓励有加。
不过,有一次侯老师却为此而生气了。
那是某一年的四月一日,在西方是愚人节。也不知是谁的恶作剧,班上几个单身男女都同时收到了一个小纸条:“今晚六点,请到主楼背后的小树林一会吧!”没有署名,但是亲昵的语气足以让人陷入美好的遐想。当然,聪明机智的同学暗自思虑之后,都最终放弃了。不过,真的就有那么一两对“实在”的男女按时前往了,而且出发之前都还梳头着装,特意收拾了一番。当然,最终大家都被这场恶作剧弄得很尴尬,也不会有什么意外的喜讯。于是知情不知情的,也就是相互逗乐打趣一阵,这事也算过去了。没有想到,可能有同学向侯老师诉了苦,表达了受人愚弄的委屈。侯老师相当重视这件事,先后好几次找到她有所怀疑的人,严厉批评。当然大家早就了解侯老师的性格,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压力。今天回想起来,可能才略略可以推测其中的含义,侯老师应该是比这些没心没肺的顽皮人更加看重这一份男女之情的真实和可贵,不容许有其他的轻佻和亵渎。
有的老师也不打算回避自己的情感生活,并视作美丽的文学故事向大家讲述,最知名的便是任洪渊老师。任老师天纵英才,但命运坎坷,人到中年才遇到了令他心旌摇曳的爱人,“我一进教室就看见了这双眼睛”[2],四目相对,“就在那相视的一瞬间,在她眼里,我看见了黑陶罐里最早的希望,也看见了自己:一个千年前殉葬多余的活生生的俑。我感到了发自自己生命最深层的巨大震动。当时我觉得,不仅是我,还有那么多美丽过世界的女性,都从时间的暗影下注视着她”[3]。“我的未到二十岁就已经衰老的生命,在快要四十岁的时候,突然开始了第二个二十岁。”[4]这何止是人生的转折、生命的涅槃,简直就是创世般的圣境。他不断在自己的诗歌中深情地书写她的形象,在课堂上重复这个圣洁的名字:FF。她那“梦幻的额角”“蒙娜丽莎的笑”都不断散发出迷人的光彩,让全年级恋爱的、失恋的、憧憬爱情的少男少女永远迷离,长久沉醉,由此生发出关于爱、关于人生,还有生命的奇异的想象。对于80 年代中期的师大中文系学生来说,任老师与FF 的故事就是一个永远的传奇,是自我成长的深刻的记忆。
直到现在,当年毕业于师大的学子还不时谈起任老师,而任老师记忆的重要亮点就是FF,那是现代汉语诗歌中的蒙娜丽莎,是青春永驻、梦境永在的标志,是一代人的性情的底色。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都走过了青春的岁月,在年过半百的时分面对了一批又一批的同样青春的孩子,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今天的学子少了好些我们那个年代的青涩和痴迷,显得更加成熟和理智。有一次,听到我无意间讲起过往的种种,他们甚至有点讶异和不解:“80 年代的你们,怎么会如此的简单和幼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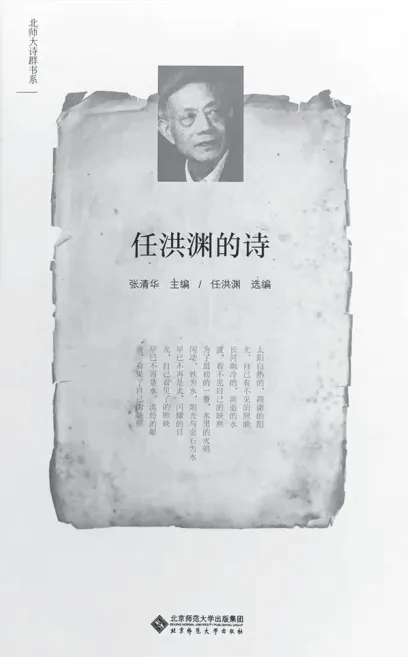
张清华主编,任洪渊选编:《任洪渊的诗》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氛围与风尚,有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风尚,这样的师生?可能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不过想到任洪渊老师和他的FF,我就知道,我们应该是多了些理解,因为就是这些走过历史转折年代的老师们,尽力为年轻的一代保存着他们曾经失落过的最珍贵的理想。因为曾经失去,所以备加珍惜;因为珍惜,所以愈加深情绵邈。而我们,这些在80 年代长大的一代,也因此受益,再不容易那么千人一面,那么老成持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