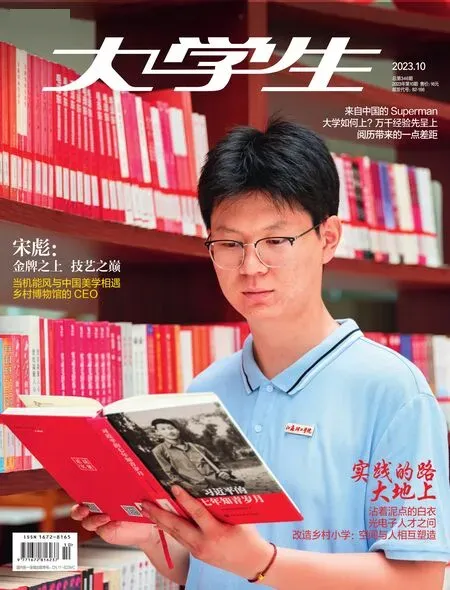托莱多2000年
2023-11-03徐佳怡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徐佳怡(北京外国语大学)
城际巴士盘旋又盘旋,在望见托莱多城门与大教堂尖顶的那一刻,我好像看到了凝固的时间。这里的时间似乎从16世纪开始就不再流动了,但塔霍河在流动——这条河流三面环绕着托莱多,使它与河对岸的土地相隔。有人说,这座依山而建的古城在冬季十分凄凉,但我所见是它夏日的面孔,它是宁静的、神秘的。

光辉基督清真寺

托莱多的兵器商店
今天的托莱多是卡斯蒂利亚-拉曼恰自治区的首府,也是与之同名的托莱多省的首府。走进西班牙的历史,托莱多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这座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早在公元前192年,罗马人就成为了它最初的居民,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也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相继到来。在漫长的历史中,罗马人征服了它,阿拉伯人的铁蹄践踏过它。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托莱多城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走进这座城市,就如同走进了一本活的历史书。当我漫步在城中的街道,望见来自不同时代、源自不同文化的古老建筑时,我仿佛在短暂的凝望中看到了两千年历史长河的痕迹。
托莱多与铁
罗马时代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曾说,西班牙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布满了铅、铁、铜、银和金矿。托莱多位于西班牙的中北部,是伊比利亚半岛重要的铁矿贮藏地。依托自然资源,托莱多发展出了高超的铁器制造工艺,在罗马帝国时期就为整个帝国提供质量上乘、做工精美的铁质刀剑。
托莱多铁器锻造的技术在几个世纪中不断精进,刀匠们能够锻造十分坚硬和灵活的刀刃,并最终通过这种工艺成为了欧洲的“兵器之城”。冷兵器时代已经过去,那时的荣光融进了城中的工艺品——托莱多城中有很多纪念品商店在贩卖兵器工艺品和等比例复刻的中世纪武器,还有一些商店展示着托莱多所铸造的骑士头盔乃至全套甲胄。同时,城中还有一个军事博物馆,那些雕花的铁铸武器——重剑、花剑、短剑目不暇接。战马上的骑士盔甲,还保持着战斗的姿态。这是昔日战场之上西班牙的荣耀。
我拿起一把“迅捷剑”,大概是“三个火枪手”所佩戴的那种。店主十分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当他听到我来自中国时,便十分惊喜地问我是否见过所谓的“龙泉宝剑”,我回答说没有,但是在博物馆见过类似的古代武器。店主是一个年过五旬的男人,他说欧洲和亚洲都有着“剑的文化”,但是我拿起的这种欧式花剑是通过剑尖的击挑来攻击敌人,而中国的宝剑则是通过刀刃进行切割,因此中国和西班牙的“剑的文化”实则是同中存异的。他看着我,又继续说道,无论是在西班牙,还是中国,剑都属于勇士和英雄们。我回应他,的确如此。
离开了商店,我继续在街头漫步,街道两边的橱窗摆放着五光十色的刀具,各国游客蜂拥进店挑选着自己心仪的纪念品。如今,现代世界的战争已经不需要托莱多生产的兵器,因此锻造工坊的产品往往只有两个去向:纪念品商店和影视剧组。毕竟,托莱多最光辉灿烂的时代已经过去。
托莱多与“黄金时代”
西班牙人把天主教双王的统治时期(1479-1516)称为他们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有人认为查理一世及腓力二世的统治时期(1516-1598)才是西班牙历史的巅峰。西班牙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来得更晚一些,持续时间也更长。米盖尔·德·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就是在这个时代横空出世,以一部《堂吉诃德》开启了欧洲文学史的新纪元。
《堂吉诃德》全名应为《拉曼却的机敏堂·吉诃德传》,在这部伟大作品的开篇,作者这样写道:“拉曼却有个地方,地名就不用提了,不久前住着一位贵族。”书中的托莱多是骑士热潮的中心,它有着热闹的市场、技艺高超的铁匠、繁荣的制皮业与熙熙攘攘的客栈,堂吉诃德与他的侍从桑丘正是从托莱多开始了他们的骑士之旅。
当我们沿着山路环城俯瞰,可以看到托莱多城外“堂吉诃德之路”的标志,这是托莱多旅游文化景观的一部分。这里是“堂吉诃德之路”的起点,若从此处出发一直向前,徒步的旅行者即可见到著名的风车、市政广场、城堡和各种具有时代风格的建筑。
托莱多城内就是堂吉诃德的世界,在街道上、在民居的壁画里,乃至在餐厅的装饰中,你都可以见到堂吉诃德主仆二人牵着瘦马的卡通图像;一些店铺还在门前摆放着真人大小的雕塑。几百年以来,堂吉诃德的故事早就成为了托莱多的一部分。城内的主要道路还矗立着塞万提斯的黄铜雕像,他穿着16世纪西班牙式的服装,一手叉腰,一手拿书——他那伟大的疯骑士的故事。这条道路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塞万提斯街。
远处的古城门上镌刻着塞万提斯给托莱多的题词:西班牙之荣,西班牙的城市之光。托莱多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他给了托莱多文学史上永恒的记忆。
托莱多与文化交流
托莱多是“三文化之城”,城市小而美,美而包罗万象,托莱多大教堂、光辉基督清真寺、白色圣母犹太教堂等著名的建筑景观都坐落于此。城内有哥特式、摩尔式、巴罗克式和新古典式各类教堂、寺院、修道院等大型古建筑70多处,外形各异,峥嵘生辉。这些建筑群代表着托莱多的文化共生:阿拉伯文化、犹太文化和基督文化在这里融合、发展,形成了难得一见的多元景观。

托莱多小城
城中的大教堂恢宏壮丽,但我认为光辉基督清真寺才最能代表托莱多的多元气质。这座清真寺十分小巧,它兴建于公元999年,是摩尔人占领时期的遗留物,位于原来的阿拉伯人聚集区。传说,当1085年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征服托莱多时,他的马跪倒在教堂前方。后来人们发现,在穆斯林统治托莱多的三个半世纪里,仍有基督徒在这里偷偷礼拜:一根蜡烛一直在砖石后面燃烧,照亮了一个隐藏的十字架。到了1186 年,阿方索八世国王将清真寺改建为小教堂,并开始在此举行弥撒。因此,走进今天的光辉基督清真寺,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在阿拉伯马蹄形拱门组成的墙壁上,有着褪色的“基督泛神”壁画,在拱形的穹顶之下悬挂着受难的耶稣像,而一些哥特风格的圆柱撑起了整个拱顶。行走在殿堂与花园之中,就好像窥见了不同文明的掠影,见证了一段段征服与被征服的历史。
在文化交流史上,托莱多曾是一个耀眼的名字。托莱多翻译学校由国王阿方索十世兴办,它将数量众多的古希腊、古罗马哲学、科学与文学典籍通过阿拉伯文或希伯来文翻译成拉丁语或卡斯蒂利亚语,为西欧打通了连接阿拉伯文化的重要通道。托莱多的翻译运动沟通了东西方文明,对文艺复兴起到了推动作用。
托莱多的名字在中国与西班牙的关系史中也有迹可循。16-17世纪,一批西班牙传教士来到了中国,成为了明末清初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先驱。比如“西方第一位汉学家”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就曾在托莱多的圣埃斯特万修道院任职。第一次将中国典籍译成西班牙语的传教士高母羡(Juan Cobo)就是在托莱多出生并接受教育。而被称为“西儒”并真正融入了中国社会的西班牙人庞迪我(Diego de Pandoja)就是在托莱多加入了耶稣会,并在此处接受了严格的神学、哲学、伦理学和现代科学的训练。可以说,托莱多作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源源不断地培养和输送了人才。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传教士从托莱多出发,辗转来到了中国,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也向西方塑造了一个繁荣、富庶的东方帝国形象。
离开托莱多的时候,夕阳正在渐渐地沉下去。望着城墙外的塔霍河,我不禁想到,阿方索六世、塞万提斯、庞迪我也许曾和我凝望过同样的河流。大巴车带我们远去,托莱多城堡的美丽弧线、教堂高耸的尖顶最终在视野中消失不见了,耳畔还萦绕着小城中午后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