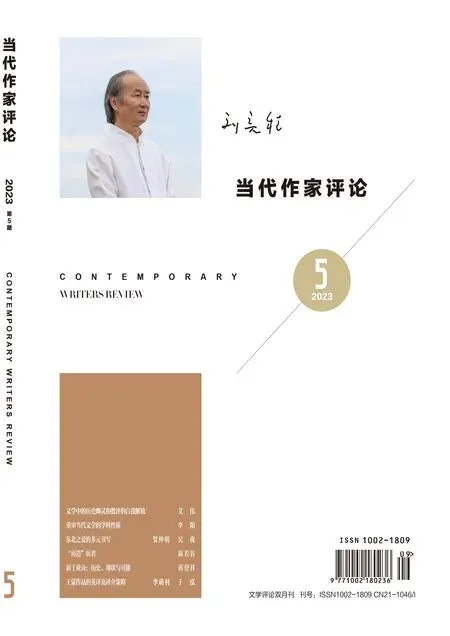《大报》《亦报》视界中的周作人(1949—1952)
2023-11-02巫小黎
巫小黎
《大报》《亦报》是上海解放后,经上海市新政府登记、注册、核准,合规合法出版的两种报纸。
《大报》1949年7月7日创刊,(1)见上海军管会登记证新字第10号。1952年2月15日终刊,历时2年7个月又9天,出版报纸共计935期。(2)笔者曾在上海图书馆龙吴路书库逐日查阅过原报。有研究者误认为《大报》1952年1月31日停刊,应系误记,特此说明。此后,《大报》业务和人员,并入《亦报》。编辑部开始在福州路328弄6号楼,后迁至河南中路368号,直至终刊。社长冯亦代,总编辑陈蝶衣,编辑、记者、美工、校对、经理部、业务部人员均由冯亦代、陈蝶衣二人协商拟定,整个报社总共约30人。(3)祝纪和:《上海解放后第一张小型报——大报》,《新闻记者》1990年第1期。
1949年7月25日,《大报》创刊半个多月后,《亦报》问世,(4)见上海军管会登记证新字第12号,上海邮政管理局执照第40号。社长龚之方、总编辑唐大郎。编辑部开始设在上海黄河路21号,后迁至南京东路353弄4、6、8、10号(慈淑大楼底层),(5)现名东海大楼。直至终刊,历时3年3个月又25天,出版报纸共计1196期,1952年11月20日收官。相关业务与工作人员并入《新民报》(晚刊)。至此,自1897年《游戏报》创刊以来的上海小报真正结束了它的历史。
一、周作人与《大报》《亦报》
1949年1月,周作人既没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后经陶亢德介绍开始给《亦报》做随笔,写回忆文章,随后也给《大报》开设专栏,主要就是换得少许稿费维持生计。按两小报创刊的先后次序,分别概述如下。
周作人为《大报》写专栏的时间实际很短,不过两月有余。起初,他开专栏,大概就是按每两天写一篇几百字的随笔做规划。这从他1950年1月10日在《大报》署名“荣纪”,发表第一篇随笔《双日开市》的题目即可知道。不言而明,这是作者和编者一开始就共同商定好的专栏计划,跟1949年11月《亦报》先行开设《隔日谈》专栏的思路相仿佛。不料,开张仅两个多月,“荣纪”卖文店便在1950年3月27日关门大吉。周作人在这里发表随笔共计仅有42篇。(6)周作人发表在《大报》的文章,手稿自订目录时题名为《大报寄稿》。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862页注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另,荣纪的《关于〈章氏丛书〉》(《大报》1950年1月28日)一文编入时,因内容关系附录在《周作人散文全集·随笔外编》(十六)之后。见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0卷,第680页。为方便行文,《周作人散文全集》后面简称《全集》。
《亦报》空间的周作人,比《大报》灵动、活泼不少。小报作者群与周的互动积极踊跃,品评回应率真、随性,言辞睿智机警,偶尔还擦出些微思想的亮光。饶有意思的是,年近古稀的“十山公”竟然和风华正茂的张爱玲不期而遇,于是有“周作人与张爱玲《亦报》空间的互动”。(7)巫小黎:《周作人与张爱玲:〈亦报〉空间的“互动”》,《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6期。
细究起来,周作人首次进入《亦报》是1949年11月22日。是日,该报第3版新辟《隔日谈》专栏,第一篇文章题为《说书人》,署名“申寿”。栏目题名《隔日谈》,即明示每两天发表笔谈一篇,作者、编者的策划意图一目了然。“周作人与《大报》”前面已经做了交代,对比可知,周氏和两小报商定的方案大体一致。然而,日历翻到这年公历的最末一天,《隔日谈》发文合计21篇,《亦报》第3版登出短文《岁除的话》,三四百字。最末一段云:
鹤生先生的著作,明年起也大量发刊,而申寿先生更写出劲来,他认为“隔日谈”不够过瘾,所以改用“饭后随笔”,日刊一文。这是《亦报》文艺作品中的极选,为以前的小报所从未有过的。(8)记者:《岁除的话》,《亦报》1949年12月31日。
文中的“鹤生先生”其实并非另外的什么名作家,正是“申寿先生”周作人。1949年末敲定的“隔日谈”,才一个多月,便感“不够过瘾”,就想在新年改成“日日谈”了。然则,专栏题名不是依据见报的频次改“隔日谈”为“日日谈”,而名之曰《饭后随笔》。
为方便后面的分析和讨论,首先将周作人在小报上发表的文章做一个简明扼要的列表。仍旧按《大报》在先、《亦报》随后排序。
表1清晰显示,周作人《亦报》使用的笔名包括“东郭生”在内共有12个。倘若将完成于1947—1948年间,刊载《亦报》的《儿童杂事诗》也一并计入,《亦报》上周氏发文共1025篇次。多的时候,一天用三个笔名发文三篇。毫无疑问,《亦报》上发文最多、最勤的作者,非周作人莫属。

表1 表1中01—04的4个专栏里随笔小品共有
《亦报》空间里,众多“知堂粉”追着,捧着“老作家”,一如“记者”之捧“申寿先生”。唐大郎则公开打油一首,自我表扬一番:“自从邀得申公写,人谓高唐未白编。”(9)高唐:《寄齐甘北京》,《亦报》1950年1月9日。“申公”指周作人,因其笔名“申寿”故。高唐,唐大郎《亦报》上使用的笔名。原诗全文如下:“昔梦春明淡若烟,多劳吹到眼门前。裹中絮履夫人托,肚内篆章居士镌(注一)。已爱寻声来市侧,最怜觅静坐茗边(注二)。自从邀得申公写,人谓高唐未白编(注三)。”作者原注:“注一:前二日,齐甘夫人托寄棉鞋一双,我把山人居士刻的图章放在鞋肚里,一同付邮。注二:近来我欢喜两篇《亦文章》,一为《闹市寻声记》,一为《有茶可吃记》。注三:有人说,《亦报》得申寿先生文章,终大郎之世,算他不曾白做编辑也。以告齐甘当为颔首。”齐甘即徐淦,绍兴人。《亦报》专栏《亦文章》作者。再譬如传奇《梁京何人?》(10)申寿:《梁京何人?》,《亦报》1950年4月6日。一文评说署名“梁京”的小说《十八春》,文末,却径直来一句奉承周作人的话:“《亦报》有十山之文,子恺之画,梁京之小说,可拿得到任何文评画展大会去矣。”(11)传奇即胡梯维,梁京即张爱玲。
然则“申公”也好,“十山先生”也罢,编/读者的喜好、偏爱,改变不了其身份背景,尽管隐秘得很,且频繁更换笔名,以遮人耳目,编者还是只能忍痛割爱,舍弃“小报所从未有过的”“极选”。1952年3月9日,《亦报》发表周作人最后一篇随笔《羊角与蚌壳》,署名“祝由”,(12)祝由:《羊角与蚌壳》,《亦报》1952年3月9日。从此再不登周氏随笔。大约一周后,即3月15日,“纪事实”为主要目的,署名“十山”的连载《呐喊演义》第29节《九斤老太》(13)十山:《九斤老太》,《亦报》1952年3月15日。发表后,连载也戛然而止。实际上,《呐喊演义》至此已公开发表的部分不到三分之一。此时,距离《亦报》终刊归并《新民报》(晚刊)还有8个多月。据周作人1952年3月18日的日记显示,唐大郎曾致函向其禀明“演义已停止刊登”事宜,舆论日渐收紧,即此可见。
综上,周作人1949年11月到1952年3月,应上海《大报》《小报》之约,发文1067篇次(含1947—1948年间所作《儿童杂事诗》72首),先后使用过12个笔名。若不受制于舆情管控和时局,(14)《关于小型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编号Q431-1-74,成文时间为1949年。致其先遭《大报》拒发、退稿,后又为《亦报》“腰斩”。他的小报文章肯定远不止现有这个数量。
二、缄口不提摆“文摊”
1949年11月至1952年3月,约两年半,周作人在《大报》《亦报》上发文1067篇次。尽管早有研究者搜集、辑佚编成书出版,有的甚至反复修订、增补,重版重印多次,譬如《儿童杂事诗》。再有,表1中05—09合计5个专栏的文章,以及回忆鲁迅和记述故人、旧事的短文,加上《亦报》未刊稿及后来续写的《彷徨衍义》(含《朝华夕拾》)等,都由作者编订结集题名为《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分别出了单行本。1997年,止庵编《关于鲁迅》一书,收录上述两书外还包括《鲁迅的青少年时代》及周氏所写回忆鲁迅的其他文章。这些为研究鲁迅提供了一份系统而难得的珍贵史料。回忆鲁迅的内容本文不论,在此聚焦周作人小报空间的个人言论和自我表达。
文章790篇(节)。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含《大报》随笔)收录712篇,由湖南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钟叔河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悉数收录《大报》《亦报》的随笔、小品,研究者有幸得窥全豹。
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生前对这790篇文章却秘而不宣,甚至《知堂回想录》50多万言,竟没有一字提起。“纪事实”的关于回忆鲁迅的那些文字则公开出版行世。
周作人是认同“古人所谓竹头木屑,也可以有相当用处”(15)周作人:《木片集·小引》,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木片集》,第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这个说法的,但790篇文章竟没有收入自编文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彼时,编成文集在大陆出版,由于周作人大节上有亏欠,思想、文化、文学界阴晴不定,出版个人文集、别集的可能性不大。《木片集》出版受挫,就是很好的证明。20世纪60年代初,他自行编订《木片集》(开始题为《草叶集》),拼力争取公开出版,经过许多周折,费了很多心思,最终还是没能面世。该书开始拟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校都出样了,结果正式付梓之前化为了镜花水月,后又谋划在广州出版,结果也是落空。《木片集》作为周作人自编文集的最后一种,直到他去世,都没能公开出版。
假如说公开出版自编文集,并非作者没有意愿,而是客观上不允许,那么再看另一件事。20世纪60年代初,曹聚仁代表香港《新晚报》约周作人撰写个人回忆,即后来行世的《知堂回想录》。此书“明确体现了作者的‘自我视点’”,(16)止庵:《关于〈知堂回想录〉》,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随想录》,第1、681、684、68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即内容和写法由叙述者自主设定、自由选择。全书50多万字,内容丰富、翔实,是研究周作人的重要文献。然而,周氏既缄口不提上海《大报》《亦报》编者殷勤约稿的美意,也不叙唐大郎等专程上门访候的高谊,至于频频更换笔名,开店、设专栏卖文更不涉及。饶有趣味的是,另一方面,又单独写了“迎接上海解放”(17)止庵:《关于〈知堂回想录〉》,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随想录》,第1、681、684、68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一节,叙写被迫困厄住在上海的门生尤炳圻屋里,白吃白住半年多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甚至有哪些师友到访等,周作人反倒不回避、不隐瞒,而是娓娓道来详细记录。1949年,出版译著《希腊女诗人萨波》一书,也都一一写下了。其次,郑重其事说:“我回到北京以后,所做的第二件事乃是重译英国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18)止庵:《关于〈知堂回想录〉》,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随想录》,第1、681、684、68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三,郑振铎、叶圣陶等人暗中授意并安排,请他翻译古希腊文学、日本古典文学的事实及大致经过,都有所交代。
《大报》《亦报》写专栏、摆文摊的事默然不表,似乎完全没有发生过一般。不仅如此,更煞有介事地宣称:“对于文学什么早已关了门。”(19)止庵:《关于〈知堂回想录〉》,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知堂随想录》,第1、681、684、68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可以认为,周作人《大报》《亦报》随笔没有出版文集不仅客观上不允许,或许作者根本就没有出版文集的主观意愿。
那么,叙述者藏着、掖着小报写专栏混饭糊口的“委屈”,既是有意为之,显然就暗含某种思虑。莫非真如作者自己所言,“写文章”是并不要紧、随性而为的“副业”,(20)周作人:《写文章的副业》,《亦报》1950年1月15日。没有写入个人生命史的价值,而翻译才是正当的志业?
有意思的是,《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出版时,周作人又都明确交待这些文章是“陆续写了在《亦报》上发表的”,(21)止庵编:《鲁迅的故家》,第3、197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或报告《亦报》上“只发表了极小的一部分”。(22)止庵编:《鲁迅的故家》,第3、197页,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亦报》和他生命有过交集,此时,因为所写的内容和鲁迅有关,他又还是公开承认了。
应该看到,周作人所写关于鲁迅的书,是有意利用鲁迅,近乎回到同住一个屋檐下,兄弟怡怡的早年,兄长独立支撑、遮风挡雨,小弟安步当车、乐享其成。某一意义维度说,周作人此时又重返靠鲁迅吃饭的旧时光——譬如东京留学后期,周作人基本是靠鲁迅寄钱生活在异国,悠游逍遥读自己的书。
如是说来,周作人小报上发表的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790篇随笔,尽管芜杂细碎,缺少组织,没有主旨,写作者又本不愿其流传后世,研究界再不重视,一批很好的学术资源,可能就浪费了。另一方面,明明卖文将近3年,又说“文学什么早已关了门”,因由何在?
三、个人认知与自我建构
前清士大夫破落户子弟周作人,从19世纪末一路走来,深深浸淫传统中国文化,又广泛接受异域文化与文明的洗礼。他著述宏富中外闻名,学问识力亦非等闲,“落水”之前是文学圈受青年膜拜的先驱。基于此,对他那些豆腐块文章,尽管在他只是为了一时填饱肚子而写,并且大都是鸡毛蒜皮细碎锁事,指东说西欲言又止,有些篇什甚至还颇为晦涩难懂,但是仍然有其特殊意义和研究价值。
周作人的小报随笔,是大作家写的小文章,文本品质好,信息密度大,蕴藏着丰富密集的文学、文化、时政、历史信息。20世纪中国,政局动荡波谲云诡,世事多变莫测难料。政权交替的历史“拐点”,知识人如何自处,怎样安置个体的肉身和灵魂,这是一个颇费心神的难题。“老作家”在小报上发表的这批随笔,为探讨作为现代知识生产者周作人精神思想图景,提供了一份极有研究价值的珍贵文献。研究界可以据此探测一个渺小的生命个体,别无选择地被时代洪流卷入全然陌生的制度环境和思想文化场域后,自我认知和生命形式可能出现的变异,也为考究其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时间交汇处的生存境遇、生存进路提供了某种契机。易言之,研究《大报》《亦报》周氏随笔,对还原周作人1949—1952年间生存境况、精神思想图景,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华北沦陷后,周作人没有跟着流亡大军离开北平到南方,而是继续留在北京大学执教。苦口婆心劝他南下的友人很多,一律被婉拒、谢辞,还自信满满说:“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23)唐弢:《关于周作人》,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第47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他对各方解释说自己“苦住”北平,意在为抵抗奴化教育做点实际工作。不俗的自我期许,满有担当的个人定位令人感佩。
真实状态呢?后来的事实,确证周作人的自我期许其实不大靠谱。《古今》编者周黎庵与他书信往来长达9年之久,却一直未曾谋面。1944年,某次,周作人南下已经走到苏州,周黎庵以为他会到上海,便想应尽地主之谊,安排一次宴请,打算替周氏接风洗尘,便去信商量具体行程。意想不到周氏竟然不领情,回复:“绝不足履上海一步”。(24)周黎庵:《周作人与〈秋燈琐纪〉》,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第88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架子、派头大姑且不说,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傲慢,睥睨俗子轻蔑凡夫的矫情,令人一时语塞。
不过才隔几年,周作人当年风光不再,未来玄妙莫测。学富五车的老教授衣食不保,犹如丧家之犬,凄凄惶惶不可终日。昔日的友人、门生何炳贤、朱肇洛、杨克南、李小峰、龙榆生、废名都先后赠物送钱为其纾困解忧。
《大报》《亦报》邀他写专栏,的确给他打开一条生路。表1已经显示,上海两小报周作人用过的笔名共有12个之多,大概圈子中人也忌讳得很。那么,此时他个人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期许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一)自比“说书人”
《大报》上周作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双日开市》。文章说,“我们摊开纸笔来写文章,觉得仿佛也是在市集中占一席地,摆列点什么东西,等候普天下的主顾”,而读书人写文章则“可自比于摆小人书摊的吧”。(25)周作人:《又日开市》,《大报》1950年1月10日。
而在《亦报》平台上,周氏推送的第一篇小品是《说书人》。据他的意思,“说书人”就是“技术专家”。技术高妙的坊间说书人,比大学里的博士、教授还更能够“得到民众的喜爱”。因而,他“羡慕说书人的本领”,对“说书人的技术”心怀敬意。然则,说书人技术不论如何了得,说得再动听都是“说了就完,耳边只是一阵风似的过去,不曾留下一点儿痕迹,可以给没有能够听到的人随喜瞻仰”。(26)申寿:《说书人》,《亦报》1949年11月22日。前面说,《大报》《小报》发表790篇随笔无一收入周作人自编文集。据此看来,其实他早想明白了“说书人”的把戏,无非娱乐大众,逗着听书人乐一乐而已,不必太当回事。
上述两篇文章,合在一起约一千字。细读深思,不能不佩服周作人文笔的老辣精到、辞约意丰。他的深文周纳、微言大义,确非一般等闲之辈可比。回眸20世纪初《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熠熠生辉的檄文,彼时周作人的名字曾令无数文学青年为之心旌摇荡。30多年风风雨雨过去,前后比对,他的自我定位,犹如天壤。如今的周氏,堪比十字街头“说书人”——不外乎凭借雕虫小技,悦乐市民大众的“技术工”罢了。通古今、贯中西的学界名流,知名大学的教授,现在却以摆地摊的贩夫走卒自况,类乎集市上供“游手好闲的人消遣时光”的“星卜杂技之流”。
《拿手戏》有代表性。此文周氏把著作人、写文章的人与“写字的人”简单画上等号,偷换概念却显出一副懵懂幼稚、天真无邪的样子,结尾处再来一声感叹:“著作等身不如拿手戏三五只”。(27)持光:《拿手戏》,《亦报》1950年9月7日。平和冲淡中蕴藏着无限酸辛与凄楚。《文章与陶器》从写文章难,说到自己本领不够写不好文章,接着又说自己“常要懊悔择术不慎,不该写文章”,要是“当初学了手艺岂不很好”。(28)十山:《文章与陶器》,《亦报》1951年6月19日。
报纸写专栏,随时要应付编辑催稿。写篇《作文难》叹一下苦经,唠叨几句“做文章到底是苦事”。(29)申寿:《作文难》,《亦报》1949年12月20日。说完才几天,又有《续作文难》推送出来,这回感觉自己像极了旧时读书不多却又要写应考作文的秀才,咬笔头、搜枯肠,沉吟不已的模样,即便“别人不来笑我,我自己也觉得好笑”。(30)申寿:《续作文难》,《亦报》1949年12月28日。
小报卖文的周作人,一如给身边的孙男孙女讲故事,某些事明明已经讲过,不多久就忘了,或者确实找不到可讲的事,就只好拿出以前讲过的再讲。譬如“赵世杰半夜起来打差别”的故事。(31)荣纪:《打差别的笑话》,《大报》1950年1月24日。秀才和老婆争论读书人写文章与女人生孩子到底那个更难的笑话,(32)《续作文难》有一段文字:“秀才苦吟,妻笑他说,你们做文章的艰难好比女人的生产,秀才说,我们还要难,因为你们肚里是有的,我们是没有的。”《瓜熟蒂落》(《亦报》1950年9月30日)“这本来说生产只要顺其自然,便自顺遂,产婆妄加催逼,乃多难产,我这里拿来说明作文,也有同样情形,老笑话里说,生产原是肚里有的,秀才做文章乃是肚里没有的,所以,更为困难。”上述的老笑话,出处相同。他就重复过好多遍。论岁数,年过花甲两鬓斑白;论身份,大学教授社会名流。为糊口为养家,每天硬着头皮埋下脑袋,写着这类格调品位并不高的笑话,能不叹这差事真的是苦吗?
(二)寓言化的自我问疑
周作人写了大半辈子文章,或许从没有现在这么难,忽然想起《写文章是哪一行?》,看似莫名其妙、漫不经心的随口一问,却意味深长。
写文章算是做什么的,这问题在旁人看来觉得毫无道理,但在我们写着文章的人却是很切要的。这算是艺术、工艺、技术么?都不是的。我们从艺术里挑出画家,工艺里挑出陶工,技术里挑出说书的来做代表,他们都要在出手以前经过相当时期的训练学习,这是与写文章相同的,至于其他事情便不是一样了。(33)十山:《写文章是哪一行?》,《亦报》1951年4月9日。
读者应该不难由上面一段文字联想到不伦不类、不人不鬼这类刻薄人的老话吧?写文章是哪一行的俏皮话,有打趣,有调侃,有感慨。
我们写短文章的,在现今提倡文章愈短愈好的时候,本来应该加倍努力,可是也实在不容易。俗语说,吃一行,怨一行,既如上边所说写文章到底不知道算是什么,不成其为行,那么也就无所用其怨了吧。
“写文章到底不知道算是什么”,表面上是在怨,其实,又含有自我质疑的意思。说到底,周作人真心想弄明白的问题,并不是纸面上的“写文章是哪一行?”周作人爱写文不对题的文章,有时,信手拈来一个题目,不过是他即兴作文的由头,照他的话说,“题目只是幌子”,(34)持光:《语体的古文》,《亦报》1950年10月2日。意在有个包装或标签,便于吸引受众眼球而已。
所以说小报空间的周作人,频频重复一个意思,即本人虽然出身士大夫阶级,是读旧书、受“封建文化”熏陶的读书人,现今走进社会主义新中国,告别阶级出身,回到“人民”中来,是时候了。《拿手戏》《师爷笔法》《目连戏的情景》《文人与吹鼓手》(35)持光:《拿手戏》,《亦报》1950年9月7日。持光:《师爷笔法》,《亦报》1956年9月12日。持光:《目连戏的情景》,《亦报》1950年9月13日。十山:《文人与吹鼓手》,《亦报》1951年3月26日。等篇章,能清晰感受到周作人紧跟时政,趋新求变的良苦用心,阶级论、出身论等时髦的语词闪闪烁烁,出现在个人言说与表达中的频次非常高,但生搬硬套的概念化痕迹颇为刺眼,“老学究”味道挥之不去。
要之,小报上的随笔,可以理解为是他自我质疑、估摸个人身份归属的文学化、寓言化表达。
(三)“学做点心”的隐喻
倘或说《写文章是哪一行?》暗含周作人的不满,但并不完整。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既是探测公众反应,又有意博取同道中人的同情和怜悯,委婉表达自认为学富五车的名学者,却不受待见的凄凉境况。
那么,《写文章的副业》则直接吐露英雄末路的困顿与尴尬,原本是博古通今的学界名流,如今却找不到用武之地,被无助与无望的焦虑情绪所笼罩。创深痛巨、备受冷落的灵魂之苦,剥皮剔骨、椎心泣血的精神之痛,需要领悟,作者微妙细密的心曲和暗藏深埋的用意值得体味。
沦落到卖文为生的周氏,自我认知和价值定位一下子仿佛低到尘埃里去了。等次、品级都在小说家、职业报人之下,显露出一副卑微苟且、摇尾乞怜的窘相。苦撑难熬的日子,免不了异想天开,说自己愿意“改而做工,参加生产工作”,譬如去工厂做螺丝钉之类,甚至再理想化一点,做工之余“留下一点功夫来写文章,称为半工半文如不合适,可以说是以做工为本业,写文章为副业吧”。(36)十山:《写文章的副业》,《亦报》1950年1月15日。
这些奇思妙想,超出一般人想象。读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学做点心》(37)持光:《学做点心》,《亦报》1950年10月17日。再一起讨论吧。
从前在大街上走,时常替别人担忧,看见店头的水果,或是点心糕饼,到晚快边还是满满的,觉得今日不见得能卖去多少,剩下来到明天会不会要坏了,长了白毛,怕要赔本吧?实际上这样事情似乎很少,因为这些店一直开着,并无亏累停歇的模样。近来我不再这样想了,倒是很羡慕他们,特别是点心店,那种生意虽然不算是理想的,也总比耍笔杆要好得多。第一,货色香甜好吃,卖出去不无主顾,肚饥时自己吃一个也实惠上算。第二,制造虽然要点手段,材料很容易找,就是剥点核桃,做点枣泥,也都不很费事,若是鲜花藤萝饼之类更是同艾叶一样,府拾即是了。或如街头杂写所记,月饼标明自制,当场烘焙,生意特佳,那更是景气十足,不会留下隔天陈货,是可想象得来的。我们写文章的就算是也有一点点手段,可是材料都要自办,而且每天不能老做这一样,比起烘月饼来真是事倍而功半,现在想起来,真有悔不该起初不曾学了做点心的手段之叹也。
读着这样幽默风趣的文字,简直就像“说书人”逗着听书人开心,街头玩杂耍的逗着游手之徒找乐。不难看出《学做点心》就是顺着《拿手戏》《文章与陶器》各篇思维惯性而来的神异之思,且进一步将朦胧、空幻的职业意识清晰化、具体化。
将《写文章的副业》《学做点心》和前面若干篇什并置,或许可以解读为,周氏意在回应知识阶级普罗大众化、劳工劳农化的时代召唤。然而,周作人写的是随笔,不是论说,他曾旗帜鲜明主张“不写说理文”,认为:“还是写些有人有事文章好”。(38)十山:《不写说理文》,《亦报》1950年5月30日。这些没有确切题旨的文章,读者可从不同路径进入文本,做出合理解读,但“悔不该起初不曾学了做点心的手段之叹”,后来却为种种历史事实证明周氏之感喟自有深意。
四、卖惨、邀宠的复杂绞缠
卖惨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的传统,且不说屈原、杜甫等古代文人,就说20世纪废了科举之后,读书人上升的通道被截断,文人卖惨之风更炽更盛。现代社会卖文的书生普遍暗自滋生低人一等的自卑,因而卖惨便轻易搭上卖文的顺风车——即卖文搭卖惨,卖惨卖文难解难分。
周氏卖惨,首先是哭穷。周没有工作,生活日用都靠昔日学生、旧好、友朋接济。卖文为生的艰辛,落魄潦倒的苦况,唯有独自咽下。其次,周之卖惨,又带着矜持和傲气,稍稍还有点邀宠、讨喜的意味。上面列举、摘引的那些篇什,只从文本粗粗看仿佛意在倡扬知识精英普罗大众化,知识人劳工劳农化,其实真正的意思并非这么清浅易见。可以解读为他已经有意提醒、暗示读者要用读寓言的思维和技法,才能有效抵达文本的内部,发现他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易言之,“古文的小题大做,或指东话西,说得莫名其妙的做法”(39)持光:《语体的古文》,《亦报》1950年10月2日。正是他随笔小品有意为之的一种美学旨趣。
周作人的学问、文章在同时代人中堪称一流,然而,公开邀宠恣意炫技,更不被允许,个性矜持傲骄,即便是“讨喜”也只能指东话西,拐弯抹角吞吞吐吐。《亦报》杂讯《周作人走访沈尹默》(40)鹤谿:《周作人走访沈尹默》,《亦报》1949年7月31日。是佐证,该文字里行间散发着他敏感自尊的气息,彰显其表面谦和内心强硬、倨傲的秉性。
另一件事同样印证周作人并非谦和、能轻易俯就他人的性格。1952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委托他替一位日籍女翻译家萧萧校订一部书稿。工作当然做完了,并且还做得很认真。事后,周作人却感慨地对他人说:“没有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41)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第221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自视甚高,可见一斑。
有话绕着弯儿说是周作人的风格,卖惨、邀宠都少不了一番讲究,一如牛山和尚的“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类似这样,顾及社会的公序良俗、个人的体面尊严,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非猫论”,写法上“跑野马”,是周作人偏爱的文风。他有意公开表彰牛山的诗,(42)荣纪:《牛山猫儿诗》,《大报》1950年3月2日。实际上刚好与牛山发生了共情。
周黎庵说他“书读得多了,名声大了起来,我觉得他似乎有些矫情,像东晋谢安那么的矫情镇物”。(43)周黎庵:《周作人与〈秋镫琐纪〉》,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第88、88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这话的确说到点子上了,直击周作人的要害。说他“矫情”,不妨再看《我的手艺》。他说:“我有一种手艺,并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内,也并不由师傅传授,但总之可以这样说,这便是补破钞票的手艺。”(44)周作人:《我的手艺》,《亦报》1951年7月22日。这口气和腔调,听着似乎还有点小得意。周黎庵对此看得分明,想得仔细,他说周作人“有些作为,表面现象与内心世界并不一致”,(45)周黎庵:《周作人与〈秋镫琐纪〉》,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第88、88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一语中的,令人深思。刻薄点说,表面看这位知名老作家藏着虚虚实实似真却假的情绪、真假莫辨的神秘,实则真心不足,油滑有余。
由是观之,“写文章是哪一行”的问疑,当初没有“学做点心”的懊悔,提议“写文章的副业”之外,以做工为主业,诸如此类的言说,就当不得真了。倘若根据那些小品随笔,认为栽了跟斗的周作人,进入新中国后能立意改过自新,完成历史性跨越,受时代气氛熏染,萌生知识阶级普罗大众化、劳工劳农化的思想新芽,那很可能会误读。
在《大报》《亦报》空间里,周作人为文为人颇有点戏剧性和表演性,即周黎庵所说“表里不一”,普通读者或许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即便是谈话聊天也不例外,譬如《三个绍兴人》一文的作者说,持光(周作人)、齐甘和他是同在《亦报》写专栏的三个绍兴人,由于都住北京,不时相邀鼎谈,都说“文章实在不容易写,和持光先生谈起,他说不容易,和齐公谈到,他也说不容易”,而作者则“愿取谈话而舍作文”。(46)雪窗(陶亢德):《三个绍兴人》,《亦报》1950年10月21日。看似平平常常一句话实则语涉多义,一是作文烧脑劳心劳力,不容易;二是时世易变,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吃不准、摸不透,不容易;三是政治上跌跤后,继续保有公开表达的机会,不容易。
无论如何,高朋满座众星捧月的日子一去不返,精神上的痛苦和孤独,感情上的无聊与落寞,可想而知。小报上指冬瓜画葫芦,细细碎碎欲言又止的小品随笔,是周作人的精神寄托,也是他与外部世界建立关联的渠道。卖惨、邀宠、讨喜或自新,多重意义向度交缠混杂真假莫辨,但可以认定为真的是其寻求精神慰藉和心理支持的情感诉求。要之,《大报》《亦报》空间周作人矫情、忸怩的形象实在是个人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