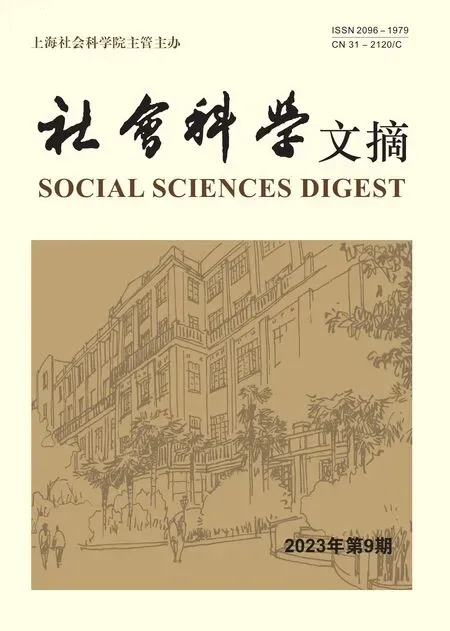数字媒介时代的交流悖论
2023-11-01冯建华
文/冯建华
我们正处于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人类社会的交流与互动,愈加离不开媒介变革开启的现代性进程。从媒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媒介化与人类社会交流互动是否呈现正相关呢?也就是说,是不是媒介化程度越高,人类社会的交流与互动就会愈加改善呢?美国当代传播学者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其代表性著作《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中对此有过深入剖析。他从人类传播历史的角度提出,“交流”犹如硬币的两面,一面是“现代人诸多渴望的记录簿”,呼唤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另一面也存在着诸多难以逾越的“不可交流性”,其不仅“存在于人的世界中,而且存在于人如何与动物、外星人和智能机交流等令人头痛的问题中”。这种内含于交流之中的悖论,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特别是大众媒介引起的,或者说是后者的存在使得这种交流悖论更加凸显。
20世纪电子媒介带来的交流“困境”和“焦虑”,到了当下“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数字媒介时代,这种“困境”和“焦虑”为何非但没有消减,在社会心理感知上往往反而觉得更加扩大了?在人类传播历史上,媒介化交流都会形成一定的悖论,只是基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与媒介属性差异,其带来的交流悖论所呈现的特质及其影响有所不同。我们该如何审视交流形态演变的历史文化现象?数字媒介化交流形态呈现何种特质?又将如何应对数字媒介时代的交流悖论?
交流形态的历史演变
交流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社会出现,从本源上讲是得益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交流维系和联结社会,失去了活性而有效的交流,人类社会发展便会停滞乃至枯萎。在不同的媒介时空环境下,交流的规模和效率有所不同,交流之目的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早在原始社会,为了共同抵御来自周边环境的威胁,提高相互协作水平,人与人之间借助物质和象征符号,如身体语言、信号、记号等,实现了简单而实用的交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受制于有限的自然资源,族群部落为了生存发展而不得不移迁徙移动。社会流动增加了不确定性,对交流便产生了更深层次需求。于是,交流的媒介不断扩展,其中最具变革意义的就是语言和文字的产生,人类文明也由此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语言使交流变得更加便捷,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语言也具有地域性和多义性,不时成为交流的障碍;文字让交流能够跨越时空界限,传之久远,其虽可破除口头语言造成的交流障碍,但文字亦可作为身份的象征,成为阶级和文化区隔的符码(如果将语言和文字视为媒介,上述情况也可视为两者带来的交流悖论)。因文字交流面临诸多制约因素,面对面口头交流通常被认为是理想的交流形态。中西方都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口语交流文化,但两者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旨趣却有较大差异。中西方口语交流文化的历史传统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数字媒介时代交流形态的特质。
15世纪,印刷媒介革命使文字阅读和知识传播不断走向大众化,打破了权力阶层的身份区隔和知识垄断。现代报刊出现后,进一步提升和扩展了交流的效能与范围。大众媒体形成的公共舆论,不仅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而且培育了广泛的“阅读公众”,使得民族和国家成为“想象的共同体”。但单向传播带来的“对空言说”也会产生一种遮蔽效应,因为在大众媒体上呈现的并非社会全景,而只是某些被选择的内容。彼得斯认为,这种交流“与其说是一个语义和心理问题,不如说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哈贝马斯提出,19世纪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出现结构转型,也正是出于现代报刊对咖啡馆、酒吧等传统公共领域的交流模式进行了扭曲或者说“封闭化”。
进入20世纪,电报的日常使用终结了传播和运输合一的历史,大大提高了交流的速度和效率。广播和电视的继而兴起,更是进一步拉近了远距离的交流,在电子革命的神话中,“地球村”由想象变成了现实。美国当代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提出,“传播的任何一个进步,因其结束孤立,因其将各地人民结为一体而被宣告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理想的实现”。可他也不无清醒地认识到,电子媒介虽然大大扩大了接收的范围,却也同时缩小了发布的范围,而且受众“不能直接做出反应或参与激烈的讨论”(这可视为传—受或主—客体二元化大众传播带来的交流悖论)。因而,现代技术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未来”,而是让公众参与某种控制仪式,这场仪式在迷人的技术面罩下掩盖了政治和权力的事实。
从“看/听”到“说”的转变
互联网的快速崛起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交流形态和场景。从传播历史来看,数字媒介对于人类社会交流带来的深刻改变,是以新技术手段实现了广大个体之间的直接连接,交流形态出现了从“看/听”到“说”的转变,交流场景由悬置化的“对空言说”走向了实时化的“人人都在说”。本文以“看/听”和“说”分别概括传统大众媒介和新兴数字媒介环境下的交流形态,主要是一种形象隐喻,重在凸显主体参与交流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种新媒介的流行,主要源于激发了潜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欲望。互联网打破了传统媒介资源的稀缺性,充分释放了个体公众的表达和交流欲望。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数字时代“人人都在说”交流形态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其背后潜隐的是对于认同的需求或渴望。如今,碰到热点流量话题,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空间的超高人气,即可感受到热闹非凡的“交流”盛况。然而,这种看似异常“热闹”的交流场景,却往往与现实生活中的相对“沉寂”形成鲜明对比,网上网下犹如“冰火两重天”。
网络时代参与文化的发展,构织了数字空间“人人都在说”的交流场景。网络粉丝文化研究先驱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在其发起的对谈式著作《参与的胜利——网络时代的参与文化》中分析认为,人们在网络时代参与沟通交流的能力,虽然与之前相比大大加强了,但“对于什么是有意义的参与以及如何实现有意义的参与却缺乏共识”。我们不禁反思:数字空间出现的“热闹”交流场面,是否或如何构成一种有意义的参与行为?为何不时出现网上网下交流的冷热反差现象?
从现实情况来看,这应与中国口语交流历史文化传统不无关系,如偏于感性、委婉、从众的口头交流文化,体现在网络空间即表现为“情绪化”“群体围观”“表情包”“贴图”等交流方式。此外,与我国社会环境和媒介体制导致的线上线下表达能量客观上存在较大势差也有一定关系,由于制度化表达渠道相对受限,网络空间成为民意表达和舆情聚散的主要阵地。但从传播和文化共性角度而言,媒介化社会进程带来的交流形态演变则是其根本性的内在原因。
在传统媒介环境下,“看/听”(报纸、电视、广播)作为一种文化仪式,体现的是客体身份,基本属于静态的意会性交流;而在数字媒介环境下,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或参与行动,交流形态由“看/听”转向“说”,彰显的是主体性姿态,更多属于动态的展演性交流。相较而言,“看/听”主要在于求“同”,“说”更多在于存“异”。这种标新立异之“说”,是数字媒介空间的源头活水,也是推动其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这种“说”如果变成几无约束的“人人都在说”,则可能走向交流的反面。为了追求所谓独异,很多网民便走向以“自我”为中心,罔顾“对方”而“自说自话”,真实的情感和理性的认知很可能淹没在碎片化的信息海洋之中。
在某种层面上,数字空间涌现之“说”是对长期被动“看/听”的反叛或宣泄。这种肆意之“说”通常重在“表达”而不在于“交流”,其虽可作为社会情绪或社会压力的缓释地带,但如果失去了交流所应具有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网络表达匿名化和“去中心化”消除了传统大众媒介的内在价值约束机制),彰显的可能不仅仅是个性和自由,而且会释放人性中的丑与恶。我们要防止的是,这种隐藏于网络空间的“丑”与“恶”,在“说”之赋能和赋权之下,从所谓的网络“亚文化”或“草根文化”,演变为一种社会文化惯习。
从长远来看,数字空间个体表达的单向性和肆意狂欢(以随意化、戏谑化、解构化为特征),带来的可能是交流的落寞和异变。数字泛在连接技术加快了生活和工作的节奏,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和亲情,有时更多只能在媒介化的多屏交流中,依靠象征性的“只言片语”或碎片化信息得以维系和联结。但长期沉浸于以自我言“说”为中心的数字交流环境,特别是当数字空间“人人都在说”演变为对“看/听”的对冲扬弃,人与人之间的近在“咫尺”,在数字屏幕横隔下将可能演变为心与心之间的远在“天涯”。彼得斯所言的“心灵交流”难题,到了数字媒介时代不仅难以化解,而且可能进一步加深和扩大。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无可否认也难以回避的两难困境。
摆脱数字媒介时代的交流悖论
通常而言,人们愈发感觉交流的无奈,在内心深处实则更加寄托了对交流的渴望。“我们渴望交流,这说明我们痛感社会关系的缺失。”从上文分析可知,数字媒介时代的传播和交往环境,似乎让我们更感陷于交流的悖论之中:交流易得,而其心灵沟通的价值却在流失。数字媒介环境下,很多人交流的圈子虽然越来越大,交流的频率也越来越快,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难以同步拉近或加深,有时反而感觉似乎被冲淡或拉远了;在“广种薄收”的数字交往心态下,感情交流的长度和浓度却可能相应缩小变淡了,心与心之间的情感共鸣则更是愈显稀缺珍贵。
数字媒介时代的交流悖论表现在多个维度,如传播的“时间与空间”“广度与深度”“开放与隐匿”“个体与社会”“理性与欲望”等层面。由于多重结构因素相互交织,数字媒介带来的不仅仅是“交流的无奈”,而且可能导致诸多新的现实问题。如2023年湖南省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发生的年轻人集体跳崖自杀悲剧事件,其背后驱动力正是源自隐匿于数字空间、面向自杀倾向者的各种“交流群”。在“人人都在说”的传播环境下,这类“交流群”不仅是悲观厌世情绪的渲染者,而且是自杀行动指南的提供者。这虽是极端的少数案例,但对于社会集体心态以及由传统道德和主流价值观构筑的人类心灵秩序(被认为是个体开启安宁幸福生活的“智慧之光”),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确实是深远而巨大的。
麦克卢汉早就断言,媒介不是传输信息或传播思想的消极管道,一种媒介特别是新媒介的产生,都是“活生生的力的漩涡,造就隐蔽的环境(和影响),对旧文化产生腐蚀和破坏作用”。在数字传播和交往环境下,每个人被置于重新塑造和呈现自我的非确定性“巨空间”。在这个“前台”与“后台”、现实与虚拟相互转换和融通的“隐蔽”环境下,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将可能被卷进“活生生的力的漩涡”,面临不同程度的调整和重塑。可以说,对于选择网约集体跳崖自杀的年轻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并非作为媒介平台的互联网,而是透过互联网交流话语传递出来的价值观对于他们固有心灵或道德秩序的颠覆与碾压,从而导致他们失去了“生”之希望与信心。由此而言,数字媒介时代出现的交流悖论,严格说来并不是交流的倒退,更不是时代的逆流,而是技术冲击带来的世态变更和人心沉浮。我们只有正视这种思潮和现实,才能更好适应数字媒介化交流的现代性悖论。
如何摆脱数字媒介时代的交流悖论,首先需要思考何谓真正的交流。数字空间呈现为一个矛盾体。个体主义是数字空间的鲜明表征。然而,个体主义并非无原则主义,更非放纵主义。数字空间的交流应树立广义的个体观,树立“对他人和自我两方的关爱”,而不是过度宣扬狭义“自我”无穷无尽的欲望。但是,这并不是说数字空间的交流要消灭个体性的“自我”,而是强调个体在“用主观的方式构建自我”的同时,亦应考虑并尊重“他人”的感应度和接受度,即中国传统文化所言的“推己及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要摆脱数字媒介时代“人人都在说”带来的交流悖论,一方面应最大程度保障“说”之自由和空间,另一方面也要适当规范和优化“说”之秩序与环境。从更深层次来分析,是需要深究和把握“人人都在说”背后潜隐的社会心理动机或社会集体诉求,并对之加以科学合理地回应和导引。数字空间交流场景构成了我们共同栖息的“集体性的生存环境”。每个交流主体唯有以真诚、友善、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其中,正确处理“自我”和“他人”的关系,彰显广义的个体观,摈弃狭义的自我意识,数字媒介化交流空间才能如詹姆斯·凯瑞所言,达至“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而不至于成为横亘在人与人之间的“咫尺天涯”。
数字媒介化交流形态和场景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症候。数字媒介化交流形态从“看/听”走向“说”,交流场景从“对空言说”走向“人人都在说”,不仅仅是传播技术带来的结果,其中还有深层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摆脱数字媒介时代的交流悖论,或许还没有成为急迫的社会问题,但其显现出来的传播文化现象和社会集体心态值得深思和体悟。从长远来看,为了顺应和化解数字媒介时代的交流悖论,除了需要理性认识交流的本质意义,回归交流的本真状态(双向沟通而非单向表达),关键要在以数字媒介为驱动力的加速度社会中,不断强化数字空间制度规则意识,培植个体交往的公共伦理,重塑新技术时代的心灵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