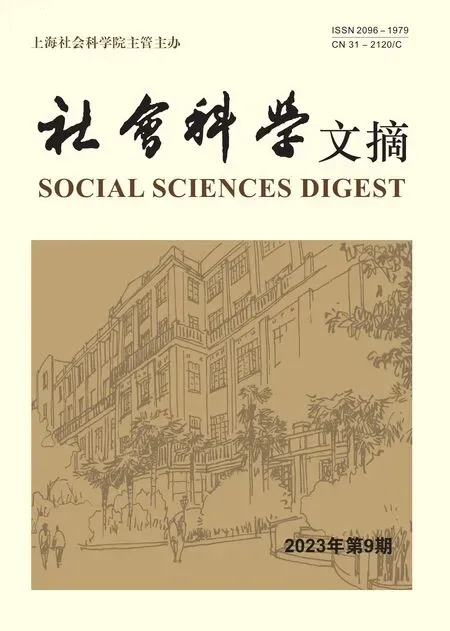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
2023-11-01吴承学
文/吴承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通常是以批评家、批评专著与批评理论的个案研究为基础的综合论述,现有的研究领域是基于传统的研究眼光而形成的。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集体性的文学观念极为重要,但尚未得到相应的重视,很少被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中。笔者希望通过开拓“集体认同”的不同面向,在传统文学批评史之外寻找另一种阐释中国文学思想观念的路径。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是中国文化认同的一部分内容,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一个民族基本价值和精神的认同。研究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意在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寻找中国文学之基因、传统和独特性。
“集体”的认同
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着眼于考察集体性的文学观念,这一命题有两个关键词:“集体”与“认同”。所谓“集体”,既有国家、民族、文化这样大的集体,也有地域、朝代、阶层等小一些的集体。集体认同并不代表没有个人的观点,而是许多个人的观点都融合到其中,成为一个整体。“集体”意味着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而“认同”则意味着它可能不具备明晰、系统的理论形态,往往代表一种集体的文学观念、理想与信仰。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是基于文化传统而形成的深层且相当稳定的观念,也包括当时的普遍知识、常识。这些观念与知识成为大多数人理解问题的框架、判断问题的依据、推断事理的逻辑。集体认同与个人的文学理论相比,往往是跨时代的,有些较为根本的文学集体认同观念早在上古时期就建构和积淀下来,成为人们的集体意识或者集体记忆。这些观念在后来的历史中,有些成为显性的认同,有些成为隐性的认同;有些集体认同观念是贯穿整个历史的,有些观念是某一历史时期所特有的;有些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中不断推移、变化的,有些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被遗忘或中断,后来又重新被唤起和激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解构和建构。研究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有多方面意义,既探索中国人普遍的文学观念,也探索中国人相对恒久或变化推移的文学信仰。
中国文学集体认同的发生,主要渊源于早期的经典,尤其是诸子百家之说。从先秦至汉代,中国古代知识的基本框架与基础已形成,包含了中国早期文学最核心、最重要的术语、概念、命题,这也是中国文学集体认同的基础和框架。早期的集体意识后来有些成为显性的认同,有些成为隐性的认同。像比兴、文本于经、文以载道、诗骚传统等范畴、观念、关键词都是较显性的集体认同。有些集体认同隐蔽在文献渊薮之中,或在诗文里反复出现,或成为人们习焉不察的规则、常识与熟语。这类是隐性的集体认同。
集体认同与个人思想,可能互相纠缠,难以理清。在历时性的集体认同中,有些观念是由某些人命名的,但是观念的发生则是多源性的。像“江山之助”这一命题,表面上看是刘勰提出的,但这种认为地域自然与人文环境对于文学创作产生影响的观念,其实是对古已有之的集体观念的沿用、发挥与概括。刘勰把这种观念引入文学批评,并加以明确命名,使之更为集中显豁。这种情况可称之为个人对集体认同的推进与确立,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文学批评史往往将之归为个人的理论,但是从其发生的角度看,这些观念应该属于中国文学集体认同的一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集体化的倾向非常普遍,很多个体提出的理论,最后都被集体接受、采用和传播。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从古代到现代都被普遍接受,“兴观群怨”是一种由孔子个人明确且系统地提出,又作为经典在历代传播,得到广泛认同的观念。
关乎信仰的“认同”
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并不以系统理论形态出现,一些不同时代、不同人物在不同场合不断重复的话题、习语或片言只语,所反映的并不是个人或某一时段的观点,而是一种历代积淀的集体意识。认同往往是一种话题,表达的是或清晰、或含混的感觉或观念。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要表达的并不是事实,不是逻辑推理,也可能没有体系性、理论性,它表达的是中国人所宗奉和追求的文学信仰与理想,是中国古人大致相同的认识与评价,是集体的文化记忆。
认同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集体认同,更重要的是把它们放到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去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判断其真假与对错。“诗能穷人”与“诗能达人”,“穷而后工”与“达而后工”,在中国古代是同时存在、各有事实依据的诗学论题,但在长期的诗学接受史上,多数人还是选择“诗能穷人”“穷而后工”“诗人薄命”之说,而“诗能达人”“达而后工”之类表述则渐渐被人们遗忘或被遮蔽。这种选择与接受,是一种基于传统诗学观念与价值判断之上的集体认同。它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诗歌与诗人的集体理想,对诗人的想象与期待及对诗歌的价值判断:诗是一种承载苦难、超越功利的神圣信仰,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寄托。“诗人”是一个被赋予悲剧色彩的崇高名称,它必须面对苦难和命运的挑战,承受生活与心灵的双重痛苦,必须有所担当,有所牺牲。
集体认同包括某种“反向认同”,即在批评某事物背后,寄寓其正面理想。对于“文人”的贬责是中国文学集体反向认同的典型个案。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诗人”往往带有悲剧性,受到同情和尊重,而“文人”则普遍受到贬责和卑视。诸如“耻作文士”“文人无行”“号为文人便无足观”等代代相传的集体话语。在“文人”话题中所表现出来的焦虑,潜藏了古人的社会价值观与文学价值观。古人以士人为理想人格,用士人的标准来衡量文人和自我期许,文人之不足与缺陷显得更为突出与明显。古人对于文人批评还包含对文人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人格的期待,对文人积极用世、对文章经世致用的期待。这是一种特殊的“反向认同”。
思想框架与公共知识
文学的集体认同,往往受制于当时人们普遍的思想框架与公共知识。中国文体学作为中国古人普遍接受的文学思想框架,与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关系非常密切。文体是在集体运用中产生的,文体体制也是被集体认定和选择的。文体理论本身就是集体所认同的文体规定,比如,文体运用的场合、写作对象、语言形式的规定和风格的约定等。
文体学为我们打开考察集体认同的特殊视角。在魏晋南北朝文坛上,出现诗歌创作的个性化与抒情化倾向,对传统政教观念有一定的解构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当时流行的像唱和诗、公宴诗、联句诗这些文体,以及赋韵、赋得、同题共作、分题、分韵等诗歌创作形态,都明确地反映出整个文坛注重文学的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的风气,也体现出儒学“诗可以群”的文学观念。这揭示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另一种颇受忽视的倾向,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复杂性。
中国古代文体品类复杂,成员众多。各种文体在整个文体家族中的地位尊卑、价值高下各有不同。在传统的文体价值谱系中,那些纯粹或偏重审美与娱乐的文体地位就不如源于政治、礼乐制度的文体尊贵。比如词、曲、戏剧、小说等文体的地位,就远不如诏、令、章、表、奏、移、檄等行政公文,以及诗、赋、颂、赞、祝、盟、碑、铭、诔、哀吊、墓志等直接产生于礼乐制度的文体。这种文体的尊卑高下与现代的文学观念差异很大。究其原因,中国古代的文体谱系与早期礼乐制度关系相当密切,两者颇有异质而同构之处。这种复杂情况,可以称之为文体王国中的“政治”。从先秦到清代,这种“文体政治”一直在变化中延续。到了晚清民国,受西方文化冲击和影响,新的文学文体谱系得以建立,传统的文章文体谱系才告结束。
古代有许多知识并非高深理论,却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普遍接受和运用的常识,故可能对集体认同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在儿童时代所接受的启蒙教育、童谣、儿歌、读本等,都成为一段时期内的“公共知识”。这种教育给我们以文学的观念,经典的观念,诗歌、古文的观念,它们甚至可能积淀成为集体性的深层审美心理和文学理想。
和一般文学批评的个性化、私人化不同,类书尤其是官修类书罗列的主要是公共的常识,代表着当时的主流意识。类书收录了当时百科全书式的内容,是公共与普遍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阶层的集体意识。知识分类的背后是一个整体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有传统与固有的框架,但在对知识类目的设置和具体文献的选择上,多少又反映出某个时代的观念。类书对文献加以分类和排列的过程也反映出当时人们普遍的文学与文体观念。类书中“文学”部类的设立不仅能够反映出“文学”在古代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与“文学”观念相关部类如“杂文”“文章”等内容,也反映出古人对“文学”内涵的理解,以及与现代的“文学”内涵的差异。类书既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典范。每类文体下所选的例文,应该是编选者心目中的代表性作品,体现那个时代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标准。类书对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和传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考察中国文学集体认同的独特路径。
隐藏深处的集体认知
在中国古代,有许多隐性的集体认同,它们往往散落在零碎的文献记载中,或者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常谈里。中国古人喜欢通过用各种比喻来表达对文学艺术的认知,并揭示其特征。这些比喻的运用具有普泛性,也属于中国文学集体认同的一部分。中国古人最常见、最普遍的是把文学艺术作品比喻为人体。中国古代的许多审美概念如:风骨、形神、筋骨、主脑、诗眼、气骨、格力、肌理、血脉、精神、血肉、眉目、皮毛等,律诗学中的首联、颔联、颈联、韵脚等,评论中所用肥、瘦、病、健、壮、弱等术语,都是一种把文学艺术拟人化的隐喻。这些比喻反映了中国古人一种深刻的文学观念,即把文学艺术形式与人体形式都看成是有生命的结构。
如果说“生命之喻”重在艺术的生命整体结构,那么“兵法即文法”则重在艺术法度的形成与超越的思想观念。古人明确提出过“文章一道,通于兵法”,或者干脆说“兵法即文法”。文人喜用兵法批评文章,某种意义也是文人在知兵、谈兵方面的想象与言说的一种延伸和惯习。喜好知兵、谈兵既出于古代文人期待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是一种自我身份塑造,故而在评文之际,会自觉不自觉将知兵谈兵的身份认同和知识积累带入其中。可见,“兵法即文法”这种文学的集体认同具有超越文学之外的文化学与社会学意义。
除了以人体结构隐喻文学艺术结构,中国古代还有以身体象征人格与艺术品格的,最典型的就是以身体残疾来隐喻不俗的道德人格或艺术品格。如庄子在形的“支离”基础上,提出德的“支离”命题。这种超越性的思维方式不仅属于老庄思想,也是古人比较普遍的观念。基于这个认同,有些在庸常社会看来有缺陷的人格,反而往往受到古人激赏。除了支离疏式的人物之外,还有作为狂与畸象征的接舆与畸人。在中国文学艺术中,那些疯癫怪异、狂人疯子,往往代表蔑视礼法,超越人生惯常,其实是一种回归本真、清高不凡、冲虚寂寞的智者、悟者形象。在中国古代,“愚”的品性或形象,往往也是一种超越于“智”的象征。这种观念延伸到艺术境界上,便是对于技巧的摈弃,对原始、古朴的回归。
官方思想与民间想象
集体认同也包含了官方认同与民间认同。官方思想对民间观念肯定起决定性的作用,而民间的思想观念也往往是对官方思想的延伸与反响。
统治阶级的文学思想观念未必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在当时对社会各个阶层却可能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只有了解统治阶级的文学思想、政策,最高统治者与统治集团主要成员的好恶,才能对各时代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趣味有比较根本的认识。官方思想对中国文学的集体认同产生重大的影响。如“二十四史”的艺文志、经籍志以及官修大型丛书等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是《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官方文学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集体认同。《四库全书总目》必须经过皇帝“钦定”。四库馆臣不可能完全依照自己的好恶来撰写,而是应该体会、揣摩并贯彻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趣味。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并非代表个别学者的观念,而是代表以乾隆为首的整个统治阶级集体的思想和学术观念。
关于民间对于文学的集体认同,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阙如,有较大的拓展空间。从文学批评角度看,谣谚给我们提供了文学批评的重要背景。比如,众所熟知的宋代流行的谣谚“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反映出苏轼文章对宋代科举考试评价标准与宋代举子科考训练的重要影响。而从明代流行“唐有李杜,明有李何”的俗语中,也可见明代人眼中的当代足与李杜并称的诗歌大家是李梦阳与何景明。
民间文学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文学集体认同。作为民间文学的民谣,看似浅俗,其实大有意趣,比如有一首熊岳民谣:“瞎话瞎话,无根无把。一个传俩,两个传仨。我嘴生叶,他嘴开花。传到末尾,忘了老家。”以民谣论民谣,寥寥数句,就把民谣的集体性、虚构性、传播性、变异性等特征生动地描述出来。民间的文学集体认同有多种形式,如神话、谣谶、谣谚、笑话、民间故事乃至一些无名氏的创作,都有反映集体认同的意义。
在民间文学作品中,不同时期的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历史印迹累积而成,文化叠加与文化层积在跨代无名氏的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顾颉刚运用这种方法展开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不仅在民俗学领域具有示范意义,在整个人文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中国文学集体认同的角度看,这种跨代的“无名氏”之作也具有集体认同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