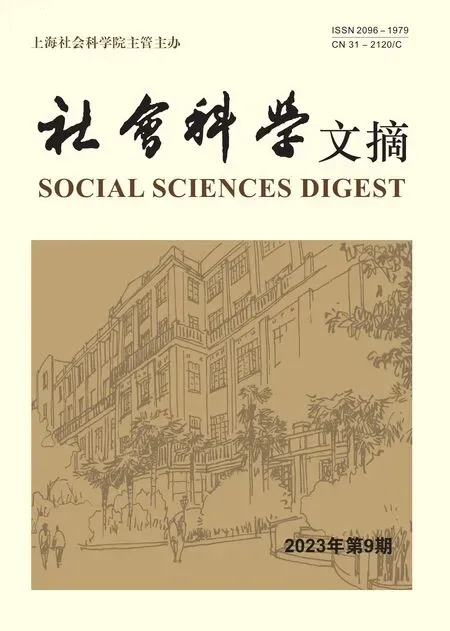翦伯赞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建立
2023-11-01李长银
文/李长银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从未轻视史料,还积极致力于史料学的建设。不过稍显遗憾的是,这些史学家都没有撰写专门的、系统的史料学论著。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翦伯赞相继撰写《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文章,并结集出版《史料与史学》一书。这些文章率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对史料的范围、史料的分类、不同史料的相对价值,以及史料搜集与整理的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而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建设史料学的缘由及历程
20世纪4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家逐渐由偏重方法转移到方法与材料并重。翦伯赞引领了这一风气。1945年5月18日,翦伯赞应复旦大学文学院周谷城的邀请,作了一次题为《史料与历史科学》的学术演讲。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讲演由顾颉刚主持。翦伯赞在这位实证主义史学领军人物面前畅谈史料学,这无疑显示了其建设史料学的自信。演讲结束之后,即有书店请翦伯赞以演讲稿为基础,“写一本关于史料学方面的小册子”。翦伯赞欣然应允,预计整理出三篇,分别是《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和《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至8月2日,翦伯赞即整理出第一篇《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对史料的范围、史料的分类以及不同史料的相对价值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但由于时局的变动,翦伯赞不得不暂停整理工作。最后,翦伯赞与书店方面达成协议,收录整理好的第一篇,外加《论司马迁的历史学》和《论刘知幾的历史学》两文。1946年4月,该书以《史料与史学》为题,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
此后,翦伯赞并没有放弃整理工作。虽然他迟迟未能整理改写第二篇,但是《中国史纲》第一卷序言已条举推至中国古史上限的考古材料。1946年3月,翦伯赞又发表《〈中国史纲〉第二卷序言》。可以说,这两篇序是翦伯赞对第二篇《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的全面深入的归纳与总结。1946年10月,翦伯赞发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依次论述了“史料与方法”“史料探源与目录学”“史料择别与辨伪学”“史料辨证与考据学”“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等问题,着重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地位。此文实际上正是他要整理的第三篇《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可以认为,《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以及《中国史纲》第一、二卷的两篇《序》基本构成了翦伯赞原计划中的著作《史料与史学》。而这些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初步形成。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就学术渊源的角度而言,翦伯赞之所以能够初步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不仅远承刘知幾的传统史学认识,而且有效地择取了梁启超的实证主义史学观点。但是,翦伯赞并没有囿于刘知幾的传统史学认识,更非仅仅“重述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料观念”,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传统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一)贯彻这一建设路径的首先是《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史料范围上,拓展一切文字记录皆史料的范围。翦伯赞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的导言部分指出,一切文字记录都是史料。这一认识直接导源于梁启超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不过翦伯赞并没有囿于梁启超的看法,他在该文结尾强调说:“又岂仅如梁氏所云账簿,家谱可以当作史料,即杂志,报纸,传单,亦无一不是史料。”而且,翦伯赞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他在演讲中强调:“在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的眼里,任何类的创造都是史料;因为人类之任何创造,却表征着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之生产力的高度,从而表现出由这种生产力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内容。”由此而言,翦伯赞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提出了一切文字记录皆史料的观点。
第二,在史料价值上,对不同种类的史料价值进行了明确的估定。翦伯赞认为,“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诚如有学者指出的,翦伯赞对正史的评价之低,“是前所未有”。与此相对应的是他对“正史以外之诸史”的评价。翦伯赞在正文部分对“正史以外之诸史”与正史进行了系统比较,论证了“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而刘知幾即重视杂史,梁启超更认为杂史“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但问题在于,刘知幾一方面认为杂史不乏“最为实录”,另一方面却认为其弊繁多,而梁启超只是说“时复过之”。与二人相比较,翦伯赞只是略提及杂史的体裁、行文问题,而详述其正面价值。可以说,正是“由于对上层社会和群体所拥有的话语权的批判意识,导致了翦伯赞对正史的深切怀疑和对正史以外著述的肯定”。
第三,在“正史”的具体分析上,揭示了其背后的阶级属性。翦伯赞认为正史不可靠的原因有四:一是循环论的观点,二是正统主义的立场,三是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四是主观主义的思想。这些认识受到了刘知幾、梁启超的启发,但翦伯赞的认识并没有囿于二人的看法。他在《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一文中做出了进一步阐述,认为“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扼要地说来,就是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问题”。首先是立场问题。翦伯赞指出,我们“应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建立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新的历史观点”。我们“要重新写著包括中国境内各族人民的历史在内的真正的中国历史”。其次是观点问题。翦伯赞指出,我们“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此外,我们“应该从千头万绪的复杂史实中,去揭示那条通过曲折歪斜的过程但始终是向前发展的道路”。
第四,在“正史”之外的群书的具体考察上,重点强调这些群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翦伯赞认为“正史以外之诸史”“史部以外之群书”等皆是史料,基本源于梁启超的认识。但较之梁启超的观点,翦伯赞重点强调了它们的社会属性。关于“正史以外之诸史”,翦伯赞指出“中国史部杂著之丰富,其中自记事、记言、记人,以至记山川物产,风俗习惯,宫阙陵庙,街廛郭邑,神仙鬼怪,无所不有”。关于“史部以外的群书”,翦伯赞则指出“古文经中,还是含有真实的史料”。而“当作史料看,诸子之书,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最主要的史料。而且其中亦有纪述前代史实及反映或暗示当时社会内容的纪录,故又为研究先秦社会史最好的资料”。作为史料,集部之书“正是各时代的社会缩写,正是各时代的人民呼声,正是千真万确的历史纪录”。关于“四部以外的各种文字纪录”,翦伯赞指出,清代档案、碑铭墓志、私人函札、宗教经典等都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史料。总之,“读正史的时候,必须要读‘野史’,读当时的文集、诗集、小说,乃至研究当时遗留下来的雕刻、绘画,从这些东西中去找到一些现实的反映”。
(二)翦伯赞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同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刘知幾的传统史学认识、梁启超的实证主义史学观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史料与方法”中,翦伯赞强调了“史料与方法”的统一。他认为,对于历史研究来讲,史料与方法都非常重要。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过类似的看法,但梁启超仅指出史料的重要性,要用“精密明敏的方法”去搜集史料。翦伯赞则进一步提出:“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较之梁启超对“史料与方法”的强调,翦伯赞“合而为一”的认识更为深刻。此外,较之傅斯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与部分机械唯物论者的“重理论、轻史料”,翦伯赞的认识无疑真正踏上了“科学的阶梯”。
在第三部分“史料择别与辨伪学”中,翦伯赞进一步估定“伪书”的价值。他受梁启超的启发,认为只要“确知了伪书的作伪时代,则伪书还是可以用作作伪时代的史料”,并进一步指出:“即研究史前时代的历史,伪书上的史料,也可以引用。”因为“要从文字的纪录中,找出没有文字时代的人类之自己的纪录,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要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实,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以为断”,“只要有考古学的资料做根据,不但伪《古文尚书》上的史料可以引用,即更荒唐的纬书上的史料乃至现在流行的关于远古之传说神话,也可以引用”。他的估定突破了梁启超对“伪书”的认识,提升了“伪书”的利用价值。
在第四部分“史料辨证与考据学”中,翦伯赞主张“利用考古学的资料去辨证文献上的史料”。他认为,“史料辨证”有待于考据学。其中,清代学者对中国文献上的史料进行了“一度精密的考证”,但还只是拘束在文献的部门之中。仅对诸史之书志考证来看,大半侧重于地理和艺文文献上的史料。这一认识有别于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翦伯赞进一步指出,清代学者“还不认识地下出土的史料之价值”。现在对史料考证的任务要“用现在既存的考古学的资料,去衡量清代学者考证过的史料,使考古学的资料与文献上的资料结合为一,然后史料的考证,才算达到最后的完成”。翦伯赞的上述认识无疑超越了梁启超对清代考据学的批评。而较之王国维、傅斯年等人的考古,虽考证方法有相通之处,但其目的之一却是要寻求“生动的整然的历史”。
在第五部分“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中,翦伯赞列出了“史料的搜集整理”的三种方法,分别是统计学、逻辑学和唯物辩证法。翦伯赞关于统计学、逻辑学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在梁启超的《历史统计学》《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找到相应的学术资源,但他要重点强调的是唯物辩证法。翦伯赞认为,史料经过初步整理之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史料中抽出历史原理”。而进行这种工作,则需要唯物辩证法的帮助。“最初是把各组史料,加以提炼,由一千条史料中抽出一百条,一百条中抽出十条,十条中抽出一条,这一条,就是一千条史料中提炼出来的精髓”,“再把这一条史料的精髓,放在科学高温之下,加以蒸发,于是这条史料,便汽化而为历史原理”。“对某一类史料如此,对其他各类史料也是如此,于是以前的一些史料小组,现在遂升华而为若干条历史原理了”,“再把这些原理加以辨证的综合,使之在更高的抽象之上,化合为一,这就是历史的法则”。最后,“有了这种历史法则,我们又倒回来用这种法则去贯串史料,于是这种体化于法则中的史料,再不是陈死的片断的史料,而是生动的整然的历史了”。总之,“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他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他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他的发展法则”。翦伯赞的上述“识断”,不仅在傅斯年的“史学本是史料学”之上,“更非并时之史的唯物论者所能企及”。
史料学建设的影响与意义
翦伯赞的史料学建设不仅是其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与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上也有着特殊的学术地位与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是逐渐建立的,翦伯赞的史料学建设则是其中重要一环。1927年到1937年,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形成。其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启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吕振羽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首次科学地认识中国史前社会”。1937年到1945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形成。其间,范文澜出版《中国通史简编》,“最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中国通史框架”;侯外庐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系统而深入地梳理了中国思想史”。与上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相比,翦伯赞的特殊贡献在于出版《历史哲学教程》,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而如本文所述,翦伯赞于1945年之后相继发表《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等文章,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这一史料学的建立无疑进一步完善了已经基本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
与此同时,翦伯赞的史料学建设还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发展。史料学是史学的重要分支。民国之后,以胡适、梁启超、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史料考订派学者,一方面继承乾嘉考据学的遗产,一方面汲取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从而在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与辨伪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比较系统的史料学原则与方法,取得了前不让乾嘉并能够与域外汉学一较高下的成绩。然而,这一学派基本止步于史料整理与考证,而未能对史料进行应有的理论分析与综合研究。翦伯赞则进一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不仅主张用正确的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来整理史料,还主张以史料来验证方法的真确性。这一史料学见识无疑超越了史料考订派的史料学原则与方法。由此而言,翦伯赞不仅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还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料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