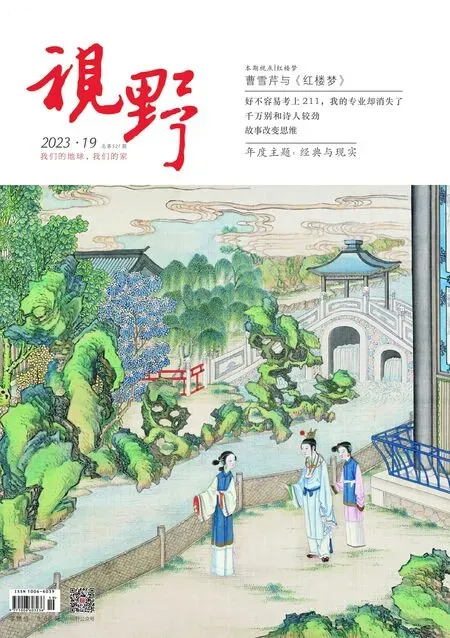进哥
2023-10-29苏南
苏南
一路都在下雨,车子缓慢行驶在路上。
饶是晴天,这辆车也看上去跑不快,行驶在平地上面,整辆车也发出不规则的振动,好像随时都会散架一样。
那是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国庆节,临到要回学校,我才到客运站里买票,然而天不遂人愿,所有去宁波的车票都已售罄。我焦急地在售票窗口问售票员怎么办,好心的阿姨给我出了个主意,先买去奉化的票,到了奉化,去宁波就方便了。我得以踏上这趟未知的旅程,坐上那辆破破烂烂的车。
后来雨越下越大,坐在最后排的乘客忽然大叫起来:车顶漏雨了。我转过头去看,车顶的雨如瀑布一般倾泻下来,落在车厢里,神奇的是车厢并没有因此积上很多雨水,最后排乘客的脚上有好几个大的洞,我坐在前面,只是回头瞄了一眼,就看到了地面,潮湿的地面正被汽车甩在后面。
跟车的女人也是售票员,这种私人承包的车总是会有这样一个岗位,以在国道上随时停车揽客。
售票员原来坐在驾驶座旁边靠车门的位置,她站起来走过来,只好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最后排那个乘客。乘客收拾好行李往前走,一路骂骂咧咧,说这种车就应该立刻报废,而不是带着一车人冒险。售票员笑着说是的,这是最后一趟了,这辆车明天就要开去报废了。
我心里骂了一句脏话,暗想最好一路平安不要出事。整车人目送那个倒霉的乘客坐到前排去了,我跟邻座的大哥搭上了话:你也去宁波吗?
他并不回答我,而是轻微点点头。
我自讨没趣,就打开书包,拿出一袋粽子,正要剥开其中一个的时候,我又扭过头问邻座的大哥你吃吗?然后把还带着温热的粽子递到他手上,他只好接下,然后也打开他的行李包,掏出两听王老吉,分给我一瓶。我们就这样一路聊着,我于是大概了解了他,这个大哥是在宁波做工程的,具体的项目是水电消防。我纳闷地问他:消防?十几岁的我不知道所有的消防栓、灭火器、喷淋系统都是需要工程队去施工的,还天真地以为那些都是消防队做的事。
后来我们在奉化一座立交桥下下车,这样可以少淋点雨,售票员也说那里搭车去宁波方便一些。
那个倒霉的乘客也跟我们一起下车,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邻座大哥的三哥。我们很快拦到了一辆去宁波东站的客车,然后坐上去,颠簸了很久,我们才到达东站。
临告别前,邻座的大哥给我留了他的电话号码,让我有空找他玩。他指着附近一座搭满架子的大厦,说他就在这里,很好找。又给我指了对面的公交站,你回学校可以去那里坐车。
这就是我跟进哥相识的经过。
我们再次见面已经是快两个月后了。有一次我去镇海找同学玩,回程路上,我坐在公交车上又看到了那栋搭满架子的大厦,鬼使神差地,我就下了车,走到那个大工地旁边,拨通了进哥的电话。
他带我去他办公室,是在一个活动板房里面,里面有人正在画图,还有人正在聊天,间或还有工人跑来要材料和吵架的。后来他递给我一个安全帽,说带我去看一下工地。我们搭乘建筑电梯来到大厦里面——那是我第一次坐建筑电梯,一部电梯被安装在建筑的外面,外面能看到各种架子,还有专门的人坐在里面负责开关电梯。新奇胜过了对危险的判断。
我跟着进哥巡视完工地,他又带我到了顶楼,我们站在露天平台上面,远眺宁波全城,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意味油然而生。后来他带我去吃晚饭,我在吃饭的时候问他,我可以过来跟他学一下水电吗?
他同意了。
那以后的几乎每个周末,我都搭乘公交车来到这个工地,给一个王姓的师哥打下手。每次出工前,我们都会在仓库领好物料,然后听进哥宣讲安全规范。我们这帮人有二三十个人,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两到三个人,分到整个工地的各个位置,埋管、穿线、安装。
在这些人里,进哥家的大哥负责看管仓库,里面堆了很多诸如电线、插座、消防管之类的材料,还有一些水电工需要的工具;三哥是其中一个小组的小组长。我后来才知道进哥家里人丁兴旺,兄弟姐妹一共八个,他排行老四,除了最小的弟弟在开叉车,其他兄弟全部都是做水电的,管理能力好一点的就在各地承包工程,一般点的就在工地一线做事。
在工地上,我们都没有自己的名字,统一叫做“吊毛”,唯独有一个除外,这个人天生一头卷发,我们都叫他“卷毛”。卷毛比我还小一岁,是1990 年生的。
2008 年的工地上,逐渐开始有90 后出现。彼时的网络上大家都把这一代人唤作“脑残”,90 后被贴上自私、个性的标签,但在现实里,每个人都在努力赚钱养家,不分年龄和时代。
我去工地的第一天,进哥就带我去附近的店里买了草席和被子,并在活动板房里给我分了一个床位。
板房里除了几张上下铺,还有一张桌子,上面乱七八糟摆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电磁炉和一个电饭煲。
我记得那个板房的后面正好就是一条河,我们在用电磁炉烧菜的时候,一打开窗户,油烟就飘到河上去了。
有很多个周六的晚上,我就睡在板房里,白天我们在工地干活,晚上就三五个师兄弟相约一起去附近的网吧上网。他们在打游戏、网恋,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看电影。偶尔我们也走上一段路去宁波体育馆打篮球,有一次,我的手感奇好,大概有过半的命中率,临到结束,有一个宁波本地的大哥还给我留了电话,让我下次过去打球叫他。其实我的打球水平很一般,那次只是意外,我怕穿帮,后来就没有再联系过那个大哥。
有一段时间,进哥让王姓师哥带我在大厦的次顶楼穿线,建筑里预埋了镀锌管,我只要把电线穿管而过,从这头穿到那头,再把两边的线头打个结就可以了。后来有一天,我怎么也穿不过去电线,找到王姓师哥,他上去试了一下,忍不住骂了一句:钢筋工这些吊毛。
我这才知道工地还有一个工种是钢筋工,而且最容易跟我们水电工发生矛盾的就是钢筋工,因为他们抡起锤子砸向地面的时候,经常会把预埋的镀锌管砸瘪,镀锌管瘪掉以后,穿线就变得异常困难。
后来王姓师哥找了一根粗铁丝,把电线头绕在铁丝上面,用力穿过管道,这才解决问题。那个时候我年轻气盛,问师哥我们怎么不去找钢筋工讨个说法。他指着不远处一个正在抡锤子的钢筋工,说他有锤子。我顿时不作声了,那个钢筋工的手臂比我的粗了一倍还不止,跟他吵上一架,他怕是会拎小鸡一样把我拎起来扔出去。
后来我们还是跟钢筋工爆发了矛盾,我们的梯子被一个钢筋工拿走,我们过去讨要的时候,该无赖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梯子本来就是他的。
我指着梯子上红色油漆的记号问他那怎么解释这里写着我们水电班的字。
钢筋工冷笑一声,那你叫它会答应吗?王姓师哥马上掏出电话叫我们其他的工友一起上来,钢筋工见势不妙,也掏出电话叫人。后来是进哥和钢筋工的工头一起过来,他们互相沟通之后,以钢筋工把梯子还给我们了事。
工地上其实很少为了工作的事情打架,一来危险,四周一圈全是架子,稍一不慎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二来有项目部管着工头,下面的人打架,项目部罚工头的钱,工头也会罚工人的钱。大多数工人出门都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拼命。
但有一次,进哥带了很多人去杭州,因为他们家老五在杭州包工程,被钢筋工打了。那个时候我正在学校里,后来去工地,听三哥讲他们几十个人坐火车去杭州,再去工地,人刚到不久,警察就来了。三哥说:“要不是警察来了,非要放倒他们一些人。”
等到12 月份的时候,天气已经有点冷了,有时候我爬在梯子上穿线,远眺外面,风景很好,风也很大。我在想以后这里是不是就成了写字楼,各种光鲜亮丽的人在这里上班,我会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呢?
后来我跟朋友讲起这段经历,说以前宁波江东区那个综合体顶楼两层的电线几乎都是我穿的。朋友说那个地方着了两次火,是不是就是你的电线没接好啊?我就不再说了。
那个综合体好像命里犯火。大厦结顶以后,有一年过完寒假我回学校,进哥给我打电话,说你过来玩吧,晚上可以放烟花。我跑过去一看,都是大纸箱的烟花,奇大无比,摞在大厦边上,烟花垒起来一面墙,比我个头还要高了。
进哥说这些烟花本来是除夕夜放的,结果放了几个,打到大厦上面,着火了,来了好几辆消防车过来救火,只好先收起来,等到元宵节再放。
我从来没有放过那么大的烟花,我们把烟花搬到地上,几个几个分开点燃,后来还是出了意外。可能是因为搬运次数太多,烟花又大,底座不稳,有一个烟花倒在地上,到处乱射,我们四下逃窜,躲进建筑里,祈祷那个倒霉的烟花不要打翻旁边堆着的烟花。还好没事。
算起来我在工地拢共并没有多少天,因为不久以后那个综合体就验收了。但是进哥在那边呆了好几年,后续进场的商铺,很多都找进哥做了水电。
做工程结款很难,反而是这些商铺,做完就可以收钱了,相对来说稳定又靠谱,进哥也乐得做这些小单子。
我再去综合体的时候,活动板房已经拆掉了。进哥在工地一楼一根大柱子旁围了一些建筑模板,大概有四米多高,里面放一张简易床,再用模板做了个门,用挂锁锁住。然而综合体一楼的层高有七八米高,上面都是空的。有一次晚上我跟他睡在这个地方,被蚊子咬得睡不着,凌晨起来,两个人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末了,进哥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给我数了一些,说这是我在工地干活的工资。我连忙推辞,说我过来是跟他学手艺的,他不收我的钱都算好了。后来推辞不过,我收了钱,回头给他买了两条“大红鹰”香烟。
等到我快毕业的时候,进哥又接了另外的工地,一个是潘火的红星美凯龙,另一个在镇海骆驼街道那边。有一次,进哥开玩笑地问我,毕业后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做工程。我连说不了,做工程钱难结,工地又脏。没想到后来去做装修和门,还是天天在工地上。
这些年我和进哥始终保持联系,每年过年我都会去他家拜年。虽然我叫他哥,但在我心里,他是我的师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他永远是我敬爱的长辈。他也每年都会邀请我去他乡下老家,打麻糍、烤烧饼,跟他们一大家子人一起,热闹极了。我总是很羡慕他,能有那么多其乐融融的家人。
前几天进哥过来找我,他正好要去接小孩放学,时间还早,就过来跟我见个面。我们聊着近况,我忽然想到当年我认识进哥的时候,差不多就是我现在的年纪,一转眼过去十五年了。
岁月如梭,连他当年抱在怀里的小女儿,也快上大学了。后来他站起来,说要去接孩子了,然后说过几天村里搭戏台做戏,邀请我带上家人过去玩。我说好啊,哥,我肯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