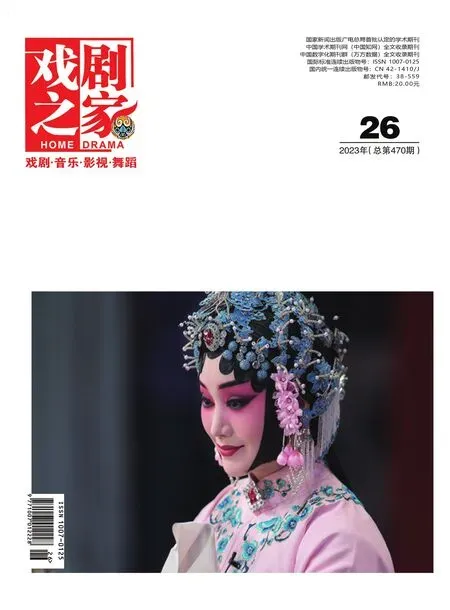浅析伍慧明《骨》中的“逃离”主题
2023-10-24王璐
王 璐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00)
著名美国华裔作家伍慧明于1956 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一个普通的中国移民家庭,父母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她的母亲在一家制衣厂上班,父亲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学生食堂当厨师。伍慧明在28岁那年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文学院毕业,之后她一边在餐厅做服务员,一边利用闲暇时间在1993 年创作出第一部小说《骨》。这部作品一经出版便畅销全美,得到评论界的广泛好评,该小说还被收录到“手推车奖文选”中,并入选1994 年福克纳笔会决选书单。
《骨》是伍慧明根据个人和家庭生活为蓝本而创作的,讲述的是生活在旧金山唐人街上一个平凡华裔家庭的故事。父亲利昂当年凭借“契纸儿子”的身份进入美国。然而,他一生都没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作为美国社会的边缘性人物,他只能靠打零工养家糊口。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和复杂的家庭矛盾,利昂只能通过长期出海来逃避这一切。母亲在华人的成衣厂做工,勤劳能干,任劳任怨。平时,除了繁重的工作以外,在丈夫出海后,她还要照顾三个子女,她是一个典型的旧式中国女性。大女儿莱拉是母亲与前夫所生,在培养华裔子女的小学工作。二女儿安娜和利昂生意伙伴翁家的儿子奥斯瓦尔多相爱。但后因两家合作失败而反目成仇,父母坚决反对安娜与男友在一起,绝望的安娜最后选择跳楼自杀。三女儿尼娜离家远走东部的纽约,以此摆脱家里挥之不去的愁云苦雨。莱拉选择留在家中,照顾父母,帮助他们度过丧女后最艰难的那段日子。在经历了这场家庭灾难后,莱拉最终决定与男友结婚并搬出唐人街,开启新的生活。
故事中的利昂一家人是众多华裔移民家庭的缩影。作品以内视角向读者揭示了华裔一代和二代的生活与情感体验,通过微观的个人生活经历反映宏大的历史现实,真实地还原第一代华裔辛酸、沉重、压抑的情感和第二代华裔不解、误解、理解的情感历程。这个故事中的人物都面对众多压力和创伤,企图通过逃离痛苦之源来寻求心灵上的慰藉。
一、里昂的逃离:失败的“美国梦”、破碎的家庭
“契纸儿子”现象最早可追溯到19 世纪80 年代,其是1882 年美国颁布《排华法案》后中国人进入美国的“快速通道”。伍慧明根据这段真实历史生动塑造了《骨》中的男主人公—利昂。利昂一生最大的成就便是花费重金、抛弃自己的真实身份,以梁爷爷“契纸儿子”的身份进入美国,目的就是实现“美国梦”,开始新的美好生活。但现实是残酷的,作为美国的“他者”,里昂处处受排挤,他只能做一些不体面的、靠体力的廉价工作。作为父亲和丈夫,他无法跟自己的家人坦白在工作上的失败,只能偷偷地把拒绝信藏起来;他也不能随便找人诉苦,因为“契纸儿子”的身份使里昂“不能讲”“不敢讲”。讽刺的是,利昂以抛弃自我身份为代价换来的美国身份不仅是假的,连“美国梦”都是虚幻的。他的一生都建立在谎言上,“契纸儿子”给他带来了身份上的焦虑,里昂只有在海洋上才能逃避身边的一切。
安娜是利昂和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和利昂感情最深、深受他喜爱的女儿。但由于和翁家在生意上合作失败,利昂禁止安娜和奥斯瓦尔相爱,安娜最终以自杀的形式终结生命。安娜的死给利昂一家沉重的打击。安娜虽然死了,但她的“幽灵”一直游荡在梁家。“就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被分裂开来了。对于我来说,时间就像断裂开来了一样,分成了安娜跳楼之前和跳楼之后。”(伍慧明,2011:15)对于安娜的死,利昂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说,“美国梦”的破灭只是让利昂感到悲伤的话,那安娜的死和对她的愧疚让里昂感到悲哀。“悲伤是人的一种正常的情感反应,它是对所爱之人、国家、自由、理想缺失的正常伤痛,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替代物的出现而逐渐消失的;而悲哀则是一种病态的情绪,它无法摆脱缺失,拒绝替代物,是一种无止境的哀恸。”(Freud,1963:164)“悲伤”可以因时间的推移而治愈,而“悲哀”会因为缺失而一直存在,并进而产生愤怒、自我憎恨和自我排斥。失败的美国梦、破碎的家庭、身份的焦虑和安娜的死亡让利昂想要逃避这些“痛苦源”,因此,他离开家,搬到破旧的三藩公寓,以出海为借口来切断与外界的联系。
利昂把一切不幸的根源归结于他没能完成对梁爷爷的承诺,将他的遗骨送回中国,以落叶归根。但最根本的原因正在于利昂被虚假的“美国梦”迷惑,以切断血缘关系、放弃自我身份为代价换来的“契约儿子”身份。利昂为此收集所有文件来证明他在美国存在的合法性。因为“对于一个契纸儿子而言,纸就是血统”(伍慧明,2011:61)。但这一切都是谎言,他的身份在隐喻层面上就是被否定的。尽管利昂也梦想过有一天能够衣锦还乡,可悲的是,为实现梦想,被谎言围绕的利昂最终陷入了自己的谎话中,被困在异国他乡,成为一个主流社会里“沉默”的他者。
二、安娜的逃离:逃离矛盾冲突
安娜虽然是小说中缺席的人物,但她的影子却贯穿了整个故事。安娜是利昂和母亲的第一个女儿,也是他们最宠爱的女儿。她从小生长在唐人街,接受父母的传统文化教育。她会和利昂在过年时摆上一桌宴席敬奉神仙,为了缓解父母之间紧张的关系,她每天早上去找利昂,陪他处理事情。“安娜有着像利昂一样的耐力,她任他像火山一样地爆发,当他骂完的时候,她就开始劝他回家”(188)因此,她从小就是传统意义上听话、孝顺的女儿。但随着安娜的长大,她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主流文化提倡的自由、独立、个性思想的影响。因为利昂和翁家合作失败,她与奥斯瓦尔的相爱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这时的“家庭—自我”“孝顺—自由”仿佛成了二元对立。如果选择听从父母,意味着她要放弃爱情,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如果选择爱情,她就要背叛父母,和奥斯瓦尔离开唐人街,但她又感觉无法融入“新世界”。“她总是觉得自己像被卡住了,动弹不得。”(165)此刻的她处在众多矛盾的夹缝中:无法缓解的父母矛盾、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主流文化的冲突、追求爱情和承担家庭责任之间的失衡等,安娜开始变得对家人“沉默”。由于对自我身份认知不确定,夹在两种文化价值观中的安娜无法在服从父母和勇敢追求自我中做出选择,只能通过死亡来逃离这种困境。
三、尼娜的逃离:离开唐人街,逃离中国身份
在众多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生活在唐人街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华裔在种族、家庭、身份的压力下总是渴望逃出唐人街,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尼娜便是其中的一个,比起中国式子女在面对“权威”父母时选择“沉默”式服从,她的选择是针锋相对。尼娜喜欢在和父母争吵、顶嘴后扬长而去。“在尼娜的脑子里,家是她想的最后一件事。”(伍慧明,2011:36)她吃饭喜欢用叉子,筷子反而成为插头发的装饰品;明知道会让母亲不高兴,尼娜还是选择穿着一身红衣去参加安娜的葬礼,她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当安娜的死亡使全家笼罩着一层阴影,生活得小心翼翼时,她不愿像父母、莱拉那般靠内疚过日子。“我知道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得不……可是我学会的是这个:我做不到”。(39)特别是目睹了安娜渴望父母的理解却遭到了他们的背叛因而强迫自己放弃爱情和自由时,莱拉被锁在了利昂和母亲的生活里,受到美国文化中强调自我的价值观影响后,尼娜不愿违背自己意愿,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唐人街,搬到纽约,当上了空姐。在伍慧明的作品中,曾多次出现过空乘员这个职业,当被问及原因时,伍慧明回答:“逃离。我出生于一个逃离的年代,每个人都想要离开。”(Kwong,2006:327)空乘人员的工作给了尼娜逃离“中国身份”的机会。但是,尼娜的决定却让她和亲人的联系变得更少,她成了“不过问的女儿。”“一个人在外面,而且还是在那么远的地方,这对尼娜来讲并不容易。”(伍慧明,2011:29)作为华裔后代,她刻意疏远自己的“中国性”,割裂与家庭和过往的关系,努力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她却并不被美国社会完全接受,“尼娜仍然在受煎熬。”(16)
四、莱拉的逃离:逃离后的回归
安娜的死让家里四分五裂。照顾母亲和利昂的工作就落在了莱拉的身上。莱拉不得不来回在利昂和母亲之间缓解两人的矛盾。为安慰母亲,莱拉甚至不顾丈夫梅森的反对,从他那里搬出来回到鲑鱼巷。但安娜的死让母亲过于沉浸在痛苦中,忘了还有莱拉陪伴在身边。莱拉似乎是个隐形人,“我觉得自己被夹在了他过分的孤独和她无尽的悔恨之间。”(27)夹在女儿和妻子这两个角色中的莱拉十分痛苦。“我无法承受再去回想这一切。回到家里以后我没有一分钟的时间属于自己,我需要时间。”(18)莱拉在扮演这两种角色时不断拉扯。这也意味着在面对父母和丈夫时,她需要不断切换生活方式。在父母面前,莱拉要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方式表达对家人的关心和照顾;但在丈夫面前,她要以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沟通。处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莱拉需要频繁地面临选择并被迫做出改变。这让她十分羡慕尼娜的选择,她想要逃离充满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家庭,逃离唐人街。当莱拉和尼娜去餐厅吃饭时,她们会故意选择气氛轻松的美国餐厅而不是压抑沉重的唐人街餐厅。特别是当被问到她和尼娜是否是中国人时,莱拉也不高兴地表示两人是亲姐妹。
故事中的莱拉一直在“逃离”和“留守”之间犹豫不定,尽管她渴望像尼娜那般离开唐人街,追求自由。但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莱拉在父母发生不和时总会回去调解矛盾,也正是在与父母不断的沟通中,她有机会了解了上一代人的过去,最后明确自我身份,做出最终选择。莱娜发现了利昂锁在箱子里的过去:一些往日的证件和一封封的拒绝信。看到这些,她瞬间明白了利昂作为“契纸儿子”背后的辛酸与不易,懂得了保存这些旧文件是利昂收集过去的一种方式,了解了这个不承认他的身份却又困住他的国家给他带来的伤痛。通过这些过去,她治愈了自己。追忆过去是直面并摆脱困境的最佳方法。“我是个契纸儿子的女儿,我继承了这一箱子的谎言,所有这些都是我的。我所拥有的就是这些记忆,所以我想把它们全都保留下来。”(伍慧明,2011:75)莱拉虽有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痛苦,但她再也不是先前那个对中国文化一味排斥、偏向美国主流文化的女孩。她有着对这两种文化更加成熟的认识和处理方式。正如莱拉的职业:使用中、英文,负责华裔家长和当地的学校之间的沟通,她树立了一个中西方文化之间的译者形象,成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中介。
尽管最后莱拉搬离了鲑鱼巷,但她的内心平静且坚定,她明白自己的身份是华裔移民的女儿。她不会因两种文化的碰撞而在内心撕扯,也不再因不同族裔身份的对立而苦恼,反而在确定自己的社会文化属性后,创造性地构造了一个多重文化并存的杂糅式身份,这不但不影响她继续前行,还让她开启了新的生活。因为莱拉在拥抱新生活的同时也时刻铭记着过去。
通过对梁家一家人的塑造,伍慧明再现了华裔移民史上一段真实的经历。通过塑造作品中的莱拉这一形象,她表达了自己心目中跨文化生存的理想形象,证明了华裔移民只有尊重和接受多元文化融合,才能构建新的自我身份,才能在美国社会中独立健康发展,真正融入美国的多元文化,因为记住过去就会让现在充满力量(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