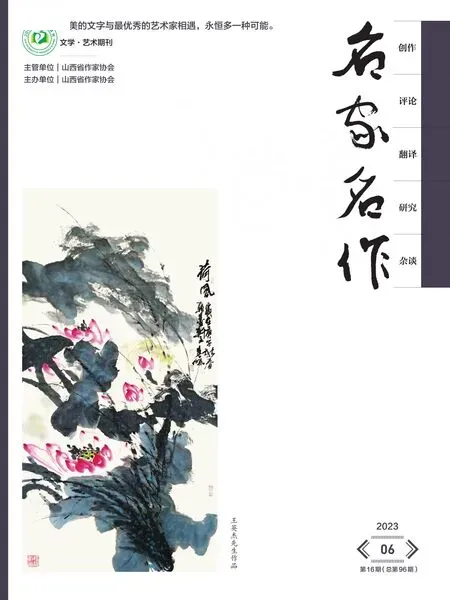探析《庄子》中的深层生态学思想
2023-10-23李梦想
李梦想
深层生态学作为当代西方激进环境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流派,其概念的提出建立在20 世纪以来包括水土流失、空气污染、土地荒漠化、森林资源锐减、物种灭绝等各种生态危机的基础之上。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的发表,标志着深层生态学的基本概念首次进入公众视野。阿伦·奈斯在文中把深层生态学和浅层生态学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态思想进行了区分和对比,并将自己的思想概括为“生态智慧T”。以此为基础,他和其他学者共同构建了深层生态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结构,其中第一层是自我实现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两条最高准则。这两条最高准则不仅是深层生态学立论的基础,也是整个理论体系的中心。
道家思想为深层生态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被称为“传统的东亚深层生态学”。《庄子》作为道家流传至今的经典著作,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无论在文学、美学还是伦理学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其所蕴含的深层生态学思想,更被西方看作是构成深层生态学的基础之一。“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其泉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进一步挖掘、整合《庄子》中的生态哲学资源,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大有裨益。
一、自我实现准则
深层生态学理论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结构:第一层是自我实现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两条最高准则;第二层是阿伦·奈斯和乔治·塞欣斯共同起草的八条行动纲领;第三层是在第一、二层次演绎基础上得到的规范性结论;第四层则是依据第三层的规范结论而演变得到的行动准则。奈斯将自我实现准则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准则作为深层生态学立论的基础和最高准则。[1]
自我实现准则中的“自我”不是西方传统文化中狭义的本我主义的自我,而是形而上学的“自我”,是一种超越性的对世界的整体认同。这种“自我”的实现建立在人的自我认同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人对自然的认同逐步加深的基础之上。奈斯用了四个词来表达这一最高准则——“最大化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2]奈斯认为只有通过实现人与自然的认同,才能使人站在其他存在物的立场之上,实现真正的同情,自觉维护其他存在物的权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过程不仅需要人不断地向自己内心发问、思考,从狭隘的自我中逐渐脱离,还要看到自然存在物之间的各种联系,从而形成一种与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的认同和相互渗透的自我意识。[2]
这种整体主义生态思想在《庄子》中也有许多体现。“道者,万物之所由也”[3],《庄子》将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3]尽管对于万物有各种不同的称呼,但根本上“物无非彼,物无非是”[3],宇宙万物是“通为一”的。过分执着于彼此的分离和对立,只会使“成心”愈大,离道日远。古之人,处于混沌蒙昧之中,淡漠无为,没有“物”的观念,也不执着于是非的争论,那时候阴阳调和,鬼神不侵,万物不伤,是最高的合一状态。直到“燧人、伏羲始为天下”,“顺而不一”;“神农、黄帝始为天下”,“安而不顺”;“唐、虞始为天下”,“去性而从于心”。[4]从合一状态到顺应自然,从顺应自然到安定天下,从安定天下到大兴教化之风,德的三次下衰,是人与万物为一的天赋本性的不断堕落,是狭隘自我的不断上升,是世间与道的互相失去。
《齐物论》中提及“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3]这是建立在对彼此的讨论之后一种超然的态度,世间万物没有不是彼的,也没有不是此的。彼与此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万物之间彻底没有任何差别,而是从物的世界中摆脱出来,以一种更高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庄周梦为蝴蝶,翩翩飞舞,悠游自在,醒来后发现“蘧蘧然周也”。[3]那么究竟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呢?蝴蝶和庄周各有自然之分,但是在梦中这种分别却被打破了,梦境所代表的就是“物化”。“物化”即“化于物”,通过对“我执”的放弃,使人从狭隘的“我”的角色中脱离出来,使“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3]这与深层生态学的将自我认同对象的范围扩大到万物,建立一种形而上的“生态自我”相类似。
这种最大化的自我实现发掘了人内心的善——对其他存在物的一种同情。马的本性是蹄践霜雪,毛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3],欢喜时彼此交颈相靡,生气时背对背相互踢踏,却被善治马者“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3],用绳索串联,关进木棚做的马槽之中,“烧之,剔之,刻之,雒之”、“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3]鸟的本性是“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随群鸟而居,以泥鳅小鱼为食,却被鲁侯之类“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最终“眩视忧悲”,不敢吃一口肉,不敢喝一杯酒,“三日而死”。[3]混沌是中央之帝,待儵与忽十分和善,却因儵与忽的报答之意,而“日凿一窍”,最终七日而死。对于马、鸟和混沌的痛苦和死亡,处于“本我”和“社会自我”阶段的人无法生发出一种感同身受的痛苦,只有处于“生态自我”阶段的人才会“在所有存在物中看到自我,并在自我中看到所有的存在物”[3],从而产生对其他存在物的真正同情。
“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3]《庄子》中描绘了一种人和万物和谐相处、相伴而居的至德时代。在至德的时代,万物生长在一起,草木茂盛,禽兽成群。山中没有路径信道,水上没有船只桥梁,人们结绳记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3],素朴无欲,因而可系羁禽兽而游,可攀援鸟巢而窥。这种至德之世与深层生态学所希望建立的生态社区式的生活一样,不仅是生态环境的美好,还是人与万物关系的和谐,是自然与社会的有机统一。
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准则
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不是动物权利意义上的平等,也不是其他非人类中心主义狭隘意义上的平等。以汤姆·雷根为例,他所说的平等是非人类动物个体意义上的平等,是基于个体自身的固有价值而平等地享有个体权利。[5]而深层生态学的平等虽然同样以固有价值为基础,但是更多强调生物圈中的所有生物和实体,作为与整体相关的部分,都具有平等的固有价值。深层生态学一方面肯定了物种多样性的积极影响,物种愈多,生态系统愈丰富,愈有利于其稳定健康地发展;另一方面则否定了生态系统中的物种等级差别,人作为众多物种中的一种,和其他自然存在物一样平等地享有生态系统所赋予的权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种权利的实现正是“自我实现”的前提。因此,生态中心主义平等指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在大写的“自我实现”中实现自我的权利。[2]
《庄子》也从整体出发探讨存在物的固有价值。东郭子请教庄子:“道在哪里”,庄子回答:“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3]庄子将道作为整体,道内存于万物之中,哪怕是卑微的地方都有它的存在,所以“以道观之,物无贵贱”[6],无论是大鲲、学鸠,还是镆干、飘瓦,都“固有所然”“固有所可”,[3]各有其固有价值。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3]自然本就有运行规律,人依照天理行事就足以让天下不失去养育。若是鲁莽地对自然进行干涉,就会像耕种粗疏、除地草率的长梧封人一样,只能得到同样马虎草率的收成。“性者,生之质也。”[3]“性”是万物最本质的特征,是其存在和内在价值统一的基础。正是因为“性”之不同,所以夔一足而行,蚿多足而行,蛇无足而行,稻谷需深耕熟耰才能繁荣生长。把人对有用、无用的认知强加于它物之上,从功利主义角度出发,将万物的使用价值作为其存在的价值,是非常狭隘的。某物不具有满足人的某种具体需要的性质,被称为“无用”。实五石的大瓠因装水则“坚不能自举”,为瓢“则瓠落无所容”,被“无用而掊之”;[3]能弊数千牛、百尺粗,“临山十仞而后有枝”的社树因“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最终被视为“不材之木”。[3]而能够满足人的实际需要的如桂、漆、橘柚果蓏之属,虽被称为“有用”,但是因其可食、可用、可剥而被伐之、割之、辱之,无法保全自身。肯定某物的实用价值,赋予其“有用”的称号,又利用、伤害它。[3]世间万物都来源于道,因“性”之不同而各有参差,所谓的“有用”“无用”仅是一种狭隘的人为价值的划分,是对万物自然本性的损害。
“号物之数谓之万,人一处焉。”世间物种的数目以万来计算,人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北海“万川归之”“尾闾泄之”,无论春天、秋天亦或水灾、旱灾都没有任何影响,不知何时停止,不会干涸也不会满溢。它如此广大,却“未尝以此为多者”。而人和天地万物相比较,就像一根毫毛在马身上一样,若“自以为多”,就如同井底之蛙。[3]“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7]《庄子》中不仅提及了物种的多样性,肯定了其多样性对于自然的丰富作用,“有万不同之谓富”[7],还形成了初步的演化观念和生态循环意识。万物一直都在变化,由微小的机而来,遇水长成继草,遇到水土交界之处长成青苔,遇到丘陵就长成陵舄。从机到植物,然后到乌足、蛴螬、蝴蝶、斯弥、青宁等昆虫,再到程、马等动物,最后到人,“人又反入机”。[7]这种连续的演变,一方面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随环境而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表明,万物各有种类,人和陵舄、斯弥一样,出于机,入于机,都是物之一类,是相互传接中的一环。“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7]庄子将死亡看作是气聚散过程的一个阶段,就像是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因此,他不会为妻子的死亡而哭泣,也拒绝临终时弟子为自己准备的厚葬,“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7]庄子面对死亡豁达的态度,正是基于他对于“天均”的理解。
三、结语
《庄子》将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原,以此为基础阐发了“天地与我为一”的整体主义生态思想,并通过“物化”,在打破庄周与蝴蝶之间分界的同时,也取消了彼与此之间的区别,在面对马、鸟和混沌时,都因万物“复通为一”而生发出真正的同情。因为此时,“我”即善治马者手中 “死者十二三矣”“死者已过半矣”的马,“我”即鲁侯手中“三日而死”的鸟,“我”即“日凿一窍”,七日而死的混沌。
《庄子》一方面从道作为本原的整体性出发探讨了存在物的固有价值。道内存于万物之中,而万物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则是因为“性”之不同,因此“物无贵贱”。以能否满足人的某种具体需要作为标准,将自然界中的各种存在物进行“有用”“无用”的划分,不仅忽视了“性”这个最本质的特征,也违背了自然运行的规律。另一方面又以“天均”为中心,在肯定物种多样性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将人和其他万物都置于平等地位,形成“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6]的演化观念和生态循环意识。
《庄子》中的这些思想总是或多或少地与深层生态学自我实现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两条最高准则相通。在新的历史时期,探析《庄子》中的深层生态思想,不仅有利于为生态文明建设蓝图增添新的内容和色彩,还有利于突破以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为核心的现代社会传统范式,实现深层生态学的新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