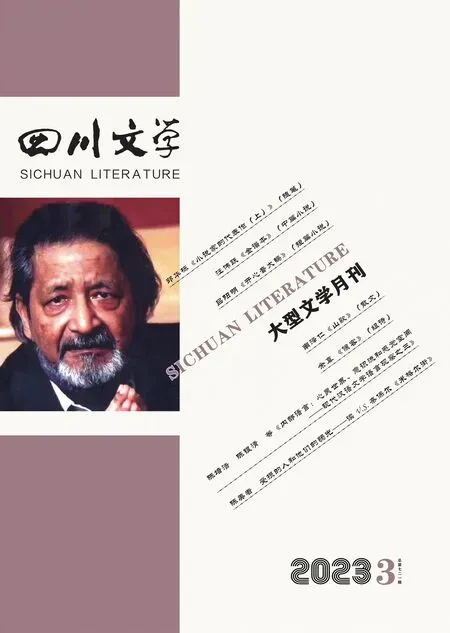仙人仙语
2023-10-22林宕
□文/林宕
一
刚走近家门口,小英就听到了客堂里传出的说话声。
她妈说:“她怎么会推他到河里?”
随即,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阿戆说的。阿戆你说是不是?”
小英的心“噗噗噗”地跳快了。心跳一加快,她的脚步也加快了,她几乎是一步跨进了她家的客堂里。
她妈美娟、阿戆妈红桃、阿戆站在客堂的北窗前。透过敞开着的北窗,可以看到屋后美娟搭的那个丝瓜棚已经一片葱绿,一些高处的藤蔓即便寻不到东西可以攀援了,却还在向上生长,梢头倔强地伸向了空中;部分藤蔓的躯干却已经从架子上长长地耷拉下来。
小英的目光从窗外的丝瓜棚上收回,看着她面前的三个人,说:“是我推他的,推他落水的。”
小英回忆了前天上午的情景。她把阿戆这个戆大推到河里后,这个阿戆竟然“憨人有憨福”——在岸上福气不好,生了个木瓜脑袋,在水中,他的福气却来了,他沉不下去,身体在河水里转了几个圈后,缓慢地爬上了岸,然后,浑身水淋淋地重新站在了小英的面前,还嘿嘿地对着小英笑。
小英想不到这个戆大竟然会把这件事说给他妈听。说了也就说了,说了或许更好,小英就重复了一遍自己刚才说的话。
美娟的眼睛里掠过惊惧的神色,她的眼睛对着小英的眼睛。她发觉小英的目光特别明亮,似乎不能经受这份明亮,美娟快速转过脸去,然后举手撩一下额头上的头发,眼神安定下来,又转回脸来,对小英说:“你瞎讲啥?发烧把脑子烧坏了?”
美娟知道,是自己在瞎讲了,小英的脑子不会坏。可她不瞎讲又能怎么样?她跟红桃家的亲家是好几年前就攀好了的。刚攀时,阿戆刚从娘肚皮里出来,谁知道他是个戆大呢?知道他是个戆大后,美娟觉得也不能反悔,她不想让村里人戳背脊骨。
阿戆一步跨近小英,喉咙口发着“嘶嘶”的气流声,脸上露着欢喜神情。当他的身体差不多要贴上小英时,他妈一把拉住了他,把他拉开了。
这一拉,让小英的眼睛里有啥东西闪了一下。她的目光更明亮了。
小英说:“我没有发烧,是我把阿戆推到河里的。”
小英注视着阿戆妈红桃,红桃也注视着她。两道目光绞在了一道,它们像是在角力,在角力的过程中谁也不愿意服输。片刻间,时间像是凝固了,很快,时间又突然化开了——红桃的眼睛首先移开了,脸上居然还露出了笑。她似乎醒过来了,说:“随你哪能说,你都是阿戆没有过门的媳妇。你再惹毛我,你也不要想变了这个身份。”
红桃笑嘻嘻地把脸转向美娟,说:“你说呢,美娟?”
美娟点头说:“对的,这小货色是在瞎嚼舌头呢。”
美娟又对小英说:“你肚皮里几条蛔虫,红桃婶娘一清二楚呢。”
小英涨红了脸,好像自己心里的啥秘密一下子暴露在了她妈和红桃面前。她微微张嘴,吁出一股悠长的气息。小英像大人了,有话不脱口而出,有话会把它们变成一股悠长的气。她确实是大人了,她不是大人的话,怎么会主动惹毛红桃呢?惹毛红桃是一个心机呢——红桃和美娟几乎同时在这么认为了。
阿戆是戆大,他的好多话是没头没脑的啊,他的话好多是颠三倒四的啊。说不定他那样对红桃说,还是小英教的呢,小英如果真想下毒手,阿戆现在还能立在这里吗——红桃和美娟也同时这样认为了。
红桃和美娟的脸上都露出笑了。
红桃对阿戆说:“你以后不能再瞎三话四了。”
阿戆呵呵笑。他这样笑,看上去是在承认自己之前的瞎三话四了。
其实,阿戆瞎三话四是正常的,可以原谅,他本来就叫阿戆啊。可小英瞎三话四就不正常,不能原谅了——红桃和美娟又一次同时这样认为了。
这样认为后,红桃和美娟都收住了脸上的笑,她们对小英板起了面孔。美娟还跨前一步,伸手捩了捩小英的臂膀,说:“以后再瞎讲,看我不撕破你的嘴。”
小英的嘴巴扯动了一下,像是真被她妈用手撕了一下。
二
小英在路上碰到了红桃。红桃一副走亲眷的样子,左胳膊里挎着一只篮头,篮头上遮着一条羽襟。恍惚间,小英以为红桃是要来她家,可旋即,小英看出不是的,红桃并不是往她家的方向走的。
小英想躲开红桃,可已来不及了,红桃叫住了她,随后把她往一旁的杂木林里拉。红桃的手感到了小英的不情愿,就说:“又不是要强奸你,怕啥?”
红桃又说:“以前,你爸泉荣倒想在这林子里强奸我呢。”
红桃脸上露出笑。小英也笑了,然后她的胳膊和身体柔软下来,跟着红桃往林子里走。
这时候,红桃的脑子里则浮现出这样的一些情景。这些情景发生在她刚出嫁到这里时。
刚嫁到横泾村时,红桃以为自己会与别的刚嫁到这里的新娘子一样,被男人们“吃豆腐”——这是这里的一个风俗。可吃新娘子“豆腐”大家也是遵守着一个度的。过度了,这里的老人们是不同意的。因为有着这么一个风俗,嫁过来时,红桃的内心有些惶恐,不过,令她想不到的是,她嫁过来后没人吃她“豆腐”。就在她暗自庆幸时,她得知:有一类新娘子,男人们是不去吃她们的“豆腐”的,那就是坏脚坏手们和戆大们讨进的新娘子,而在村里人的眼中,红桃的男人阿伟是一个戆大。其实,阿伟也就是哑子一样不愿开口说话,可他并不是真正的哑子。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哑子,却连着一周不说一句话,这不是脑子坏了的戆大,还是什么?村里人的这个判断后来被证实了,被红桃后来生出的儿子阿戆证实了,阿戆这个真正的戆大证明了自己的父亲确实是一名戆大。当红桃明白别人不吃她这名新娘子“豆腐”的原因时,尽管她内心的惶恐没有了,可她心里不爽了,她心里憋屈了。她后来在路上碰到泉荣时,就问泉荣,你也不吃我“豆腐”吗?
红桃娘家所在的村庄和泉荣所在的横泾村,也是夫家所在的横泾村就隔着一条河,所以,红桃与泉荣从小就认得的。当泉荣听到了红桃的这句问话后,他搔了搔头皮,似乎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才好。红桃看着泉荣那张英气的脸,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说不清的感受。当时的泉荣还没有处对象,看年轻女性的眼睛里,就难免有一种特别的神色,这特别的神色就是一种既胆怯又勇敢的神色,这神色像是一种年轻而又生猛的火焰,点燃了新娘子红桃的血液。她又向泉荣开口了,说,你吃我“豆腐”吧?说着,她挺着胸脯朝泉荣跨近了一步。
他们的身边是一片杂木林。泉荣朝杂木林瞥一眼,说,现在又不是在公众场合,单独碰着,不能吃的。
泉荣说的是一个当地人吃新娘子“豆腐”的规矩。可红桃的血液已经被泉荣眼睛里的火焰点燃了,她似乎不理会这个规矩了,说,那我们就不要让人看到,不要让人看到你吃我“豆腐”时不在公众场合。
红桃的脚步朝杂木林里移动了。泉荣在迟疑,可很快他跟进了杂木林里。他们在杂木林惊动了一群麻鸟,麻鸟们飞走后,他们就在两棵榆树间站住了。泉荣的双眼里尽管像着火了,可他不知道该干什么。红桃就把自己的胸脯挺到了泉荣的胸脯上——这哪像是男人在吃新娘子“豆腐”,分明是新娘子在吃别人豆腐了啊。这似乎让泉荣感到不好意思了,感到自己对不住男人这个称谓了。他一把抱住了红桃,很快又放倒了红桃。在地上,他要进一步动作时,红桃挣扎起来。红桃一挣扎,泉荣的动作变大了,他的动作一变大,红桃就叫起来,还一口咬在了泉荣的肩膀上。泉荣叫了一声,然后慌忙从地上爬起。片刻后,两人面对面站着了,都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泉荣说,是你让我进来的,要我这样的。红桃说,你这样不是“吃豆腐”。泉荣说,我说过“吃豆腐”要在公众场合,可你偏要领我进来。红桃似乎吃瘪了,说不出话了。她转过身来,快速走出了杂木林。
杂木林还是以前那个杂木林。可进入杂木林的两个人已经不同了。
红桃继续想着以前的那段时光,她和泉荣进杂木林的时光。
红桃想彻底离开夫家、回娘家——她的这一企图后来没有实现,在夫家的家族势力以及强大的某种村俗前,她的这种企图最后被粉碎了。在她的这个企图刚成形时,她悄悄地把泉荣再次约到了杂木林里。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泉荣起先是不答应的,可红桃用坚决的口吻告诉泉荣,她是有“要紧事”跟他说。泉荣说,有“要紧事”说也用不着进杂木林。红桃说,没人规定杂木林里不能说“要紧事”。歇一口气,红桃又说,放心吧,我不会在那里吃了你。看着红桃像刚摘的鲜桃一样粉嫩的脸,又觉得她都那么说了,泉荣的脚步就动了,就跟着红桃进了杂木林。
红桃还是在两棵榆树间立停了,一立停,她就坐了下来。她扯一下泉荣的裤管,要泉荣也坐下,泉荣的屁股也就落到了地上厚厚的枯叶上。红桃把手放到泉荣的膝盖上,泉荣一动不动。红桃的手开始抚动,泉荣还是一动不动。泉荣觉得自己变了,觉得自己已不是上次来这里时的泉荣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啦,好像肚皮里正涌动着一股委屈。见泉荣一动不动,红桃真的开始跟泉荣说“要紧事”了,她的话让泉荣吃惊。她说,我要离开这里,我要离开阿伟。泉荣瞪大眼睛看着红桃。红桃问泉荣,你说阿伟是戆大吗?泉荣摇摇头。红桃说,你认为不是?泉荣又点头。红桃说,所以,我离开他,不是因为他是戆大,他不是戆大。他不是戆大,可他让我变成戆大,变成脑子有病的人了。红桃转脸四顾,似乎在担忧有人突然闯到他们身边。她又说,我说的事,你千万不能说出去的。泉荣点头。她接着说,我为什么想离开,还有……她咽一口唾沫,似在犹豫,就在她重新抿上嘴巴的时候,树林里响起了几声明丽的鸟叫,像是在替代红桃说话。不过它讲的是啥,泉荣听不懂。
泉荣抬头,头顶上是浓密的枝叶,不见鸟的踪影。它一定是隐藏在哪片宽大树叶的背后,在窥视着密林中的两个人。当红桃欲言又止时,它终于忍不住,替她讲了几句。
泉荣想起身,红桃一把拉住他。她把他的手往自己身上拉。她又说,我不能白来这里一次,我不能白做一次新娘子……她对泉荣继续嗫嚅道,你晓得吗?出嫁后,再带着囫囵的身体回娘家,后半生过不太平的……泉荣心里惊叹一声,再次瞪大眼睛。
红桃的另一只手在自己身上动了。泉荣的手立刻缩回,他想站起来。可他站不起来。红桃又伸手拉泉荣,泉荣的身体终于倒在了红桃的身体上。
三
十多年后的一天上昼,小英在路上碰到了红桃,红桃一副走亲眷的样子,左胳膊里挎着一只篮头。红桃让小英跟着她进了杂木林。
进了杂木林后,红桃打量起身周的树木。杂木林确实还是原来的杂木林,里头的树木仍旧是有的挺拔有的弯曲,它们的枝叶仍旧是葱葱绿绿的,它们分泌出的树脂的气味仍旧是那个味道,有点清香有点甜。红桃还觉得,即使与不同的人进去,在里头围绕着他们的那股诡秘气氛还在。没办法,进这个杂木林,好像就是要做一些诡秘事情的。
红桃立停在一棵厚壳树边。这里,地上的落叶不多,还都是些新鲜落叶,所以地上显得还干净。红桃把篮头放在地上,一屁股坐下。见小英还立着,她伸手拉小英,小英几乎是跌坐到了地上。
红桃拿掉篮头上的羽襟,抓出一只酱煨蛋。酱煨蛋的味道让小英的舌根处一酸。可她不接红桃递过来的酱煨蛋,别过头去,把舌根处的酸水咽了下去。
红桃放回酱煨蛋,又从篮头摸出一块葱饼,递给小英——红桃拉小英进杂木林好像就是为要了给她吃东西。吃东西又不是件需要遮人耳目的事,用得着把她拉进杂木林?小英感到有点好笑,又有点可气,就想从地上立起来,可红桃还是拉住了小英,另一只拿着葱饼的手缩回到了篮口边。
红桃说:“我本来想回娘家去的。”
“那你去吧。”
“等一等吧。”
“那你早点去吧。”
小英说着又要立起来,红桃也再次拉住了她。
小英说:“你领我进树林里,就是想让我吃东西?”
“不是。你不吃就不吃吧。”
“那是为了强奸我?”
小英说着“噗嗤”一声笑出声来,红桃也笑了。小英想不到自己能够在红桃面前说出这样的话来。两人这样笑,当然是把这句话当成笑料了。这样笑,还说明了一点:两人其实把红桃先前说的那句话也是当做笑料的,那句话就是:以前,你爸泉荣倒想在这里强奸我呢。
既然拉小英进树林不是为了给她吃东西,也不是要强奸她,那么还坐在这里做啥呢?小英就说:“那么好吧,既然没有别的事,我们就出去吧。”
红桃却再次一把拉住小英的臂膀。
红桃说:“不,我有事,我有事要问你。”
“那也用不着进树林问啊。”
“进树林就是因为有事要问你。”
“你就问吧。”
红桃的嘴唇皮掀动了一下,却没有一下子出声。片刻后,她终于嗫嚅道:“那天阿戆落水,是你推的,是吗?”
小英不接嘴。有了上次她家客堂里的经历,小英觉得自己没必要像上次那样说了。说了,也会从红桃的嘴里得到同样的应答。
红桃又说:“上次在你家里,我那样说了后,你怎么不吱声了呢?你应该反驳我,反驳你妈。是你推的,你就要咬牢。”
和上次一样,小英的脸又涨红了。好像她做的错事被红桃发现了。不过她还是没有吱声。
“你应该咬牢啊。”红桃舔一下嘴唇,“是你做的事,你为啥不咬牢呢?”
红桃伸出手来。这一次,她伸手不是为了递吃的东西给小英了,她的手直接放在了小英的臂膀上,两根手指捩了一下小英。小英没有反应。红桃的两根手指在小英臂膀上再次用力捩起来。
小英尖叫一声,晃动臂膀,晃掉了红桃的手指。然后,她的身体没有了进一步的行动,她没有试图从地上立起来,一动不动地坐着。红桃的声音则再次响起来:“小货色,我当时是盼着你咬牢的啊。你怎么说了一声就不再说下去了啊。”
小英脸上的红色已彻底褪去,不但如此,她的面孔还泛白了。她没有看红桃,苍白的面孔正对着前面的一棵鸡爪槭。
接下来的片刻,两人都没有声音,一片寂静包围了她俩。在小英的感觉中,这片寂静是重的,压在了她的身上,她的身子更加立不起来了。而在红桃看来,被她捩了几下,外加说了几句后,小英是服帖了,不再犟头捩脑了。
既然小英不再犟头捩脑了,红桃就又开口:“你以为我一定想把你讨进我家吗?我家阿戆一定要你吗?不,把你讨进家里派啥用场?不派用场,只是讨进一张吃饭的嘴巴罢了。我家可没那么多口粮。我只是要你讲,阿戆落水是你推的;当然,你是这样讲了,不过你要在你妈和我面前咬牢啊,我以为你要咬牢的。”
红桃的两根手指又放在了小英臂膀上。小英的臂膀抖动了一下,可红桃却不再捩小英。
小英说:“你不是在说我瞎三话四吗?”
“你是在瞎三话四吗?不,你说的是事实,是事实,你就要咬牢,要多说几遍。”
“不,我没有推他落水,是他自己落水的。”
红桃的两根指头又在小英臂膀上用力捩起来。小英没有发声,也没有抗争,不,她抗争了,她的抗争集中在了自己的脸上,她脸上的皮肉在扭动,嘴角也扯到了一边。不过,她的身体不动,僵硬着。红桃似乎很不满这僵硬,用力推了她一把,又扑到了她的身上,随后双手同时在她身上掐起来。
小英居然还是不出声,只是身体在扭动,想从红桃的身下挣脱出来。可她越是挣得厉害,红桃的双手掐得越是厉害。于是,她不再动弹。
红桃继续掐小英。她不想在小英身上留下看得出的掐痕,所以她不再掐小英露着的臂膀。她现在只掐小英被衣裳遮着的胸脯。她边掐边在嘴巴里咕,你非但不咬牢,还否认是你推的!你这样说,不担心被雷打吗?
红桃不再掐小英,猛地直起上身,从小英身上下来,坐定。喘着气,她又说:“其实,现在你否认也没用了,横泾人都晓得是你推阿戆落水的,都晓得了你不愿来我家。”
小英还是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见小英对她的话没啥反应,红桃就一把抓住小英的手臂,把她从地上拉起来,还把一口唾沫吐到了小英面孔上,接着,她对小英说了这次见面中的最后一句话:“告诉你,你来我家的话,除了给我家白白增加一个人的口粮,没其他用场。现在,我家可以不要你了,不过,因为你推阿戆落水了,村里的人会认为是你家不要阿戆的。”
红桃拎起篮头,拍了一下屁股,一篷尘烟从她屁股后头悠悠飘下,飘到了小英的面孔上。小英打了一个喷嚏,也从地上爬起来,尾随着红桃,往树林外走。
四
红桃又来到了美娟家。她进门时,正在客堂里的小英想转身往灶头间走,红桃叫住她:“做啥要逃?怕我吃你吗?”
在客堂的一角,美娟正在一只青缸里发豆芽。她把脸从缸口抬起来,直起身,沾满汗渍的面孔上堆出笑。她甩甩湿漉漉的双手,向红桃迎上去。
红桃还是挎着一只篮头,上面遮着一块羽襟。
小英立停在了灶头和客堂之间的门槛上。恍惚间,她以为红桃是刚从那个树林里出来的,她身上被红桃捩过的地方也立刻疼痛起来。她一步跨进了灶头间里,走到灶肚后面,在木凳上坐下。她闻着灶肚里草木灰的淡淡香气,支起耳朵,听客堂里传来的声音。
美娟说:“红桃,你这是做啥呢?”
红桃已拿掉篮头上的羽襟,里头是方糕和赤豆粽等一些糯食。
红桃说:“做的时候,多做了几个。看到我,你家小英做啥逃呢?”
美娟就朝灶头间里喊小英,没有回应。
美娟说:“这小货色,真不识相。”
她又朝灶头间里喊。小英在灶肚后立起来,不过她没走进客堂里,而是一步跨出灶头间连着后院的木门。她感到她身上的疼还在,她像是要逃避这疼似的逃向后院,绕过丝瓜棚,走过一块小小的菜地,然后来到了隔壁人家的滩涂石上,坐下。她听不到她家客堂里的声音了,只听到面前的河水的细小流动声,甚至听到了水草里小鲤鱼的唼喋声。河水的流动声和小鲤鱼的唼喋声衬得周围特别宁静。一歇后,小英似乎有点忍受不了这种静了,朝她家客堂的方向侧转头来,支起耳朵。然后,她家客堂里的声音也真传来了。这声音居然也像她面前的河水声一样清晰起来。她听着美娟和红桃的对话,感觉到自己的命运也像小河河水一样在向前流动,在流动中被不断挤压。她感到美娟和红桃的声音就是两道扭曲的河岸,不断挤压着她的命运之河,而她的命运之河在挣扎着往前流动,流向不可知的明天。
红桃说:“我看算了。”
美娟说:“啥意思?”
“阿戆配不上小英。”
“你不要试探我,我们不会变。”
“还用试探吗?你看,我一来,小英就躲开。”
“她那是难为情,你也不要再开玩笑了。”
“我这不是试探,也不是开玩笑,我这是实话。我实话对你讲吧,其实小英来我家,我家就是多支了一份口粮。”
“红桃,你越说越豁边了。你说这个口粮不口粮的豁边话,说明你就是在试探。我不能上当。”
“不是试探。”
“我如果把你的试探当真了,上你当了,村里的人最后戳的还是我的背脊骨,而不是你的背脊骨。”
“美娟,谢谢你这样讲。”
“红桃,我只能这样讲。你不要落眼泪,你伤心啥?你不要落眼泪。”
“好,我不落。我不伤心,我开心。你怎么也落泪了?”
“跟你一样,我这也是开心的眼泪。”
这些话,像是一缕轻风,穿过小英家的后窗,越过屋后院子里的那个丝瓜棚,又经过那块小小的菜地,然后吹到了隔壁人家的滩涂石的上方,和小河的流动声、鱼儿的唼喋声汇聚在一起。汇聚在一起后,这缕轻风似乎变强大了,开始撞击小英。小英的上身微微摇晃起来,这撞击似乎也让小英感到疼痛了,也或许感到开心了,她流泪了,和客堂里的那两个女人一样流泪了。她也和那两个女人一样,说不清自己的眼泪是伤心的眼泪还是开心的眼泪。她低头,看到河中的水草边有几尾鲫鱼,嬉戏中的它们显然是开心的。开心的鲫鱼却让她脸上的眼泪水流得更多了。
她继续泪眼朦胧地看着河中的鲫鱼,它们还在左右追逐,上下嬉戏。它们的追逐和嬉戏在河面上激起了一道一道波纹,这波纹是它们开心的笑,无声,可持久。
她也笑了,流着眼泪笑,泪眼里也有一圈一圈闪亮的波纹。她在滩涂石上立起来,也想做一条鱼了,也想让自己的笑化作河面上一圈一圈的波纹。她跨前一步,立在了最后一个台阶上。这个台阶是一块狭长的黄石,河水的长期浸润,使它变黑了。不过它还是那么阴凉,阴凉透过她的鞋脚底传到了她的脚底心,然后又传遍了她的全身。这是黑的阴凉、水的阴凉、鱼的阴凉,也是快乐的阴凉。她站在最后这个潮湿的台阶上,已感受到鱼的快乐了。鱼的快乐是左右追逐、上下嬉戏的快乐,她也要去追逐它们了,和它们一道嬉戏了。
横泾河里产生了一声水响,像有一条大鲤鱼跃起后重新扑入了水中。
五
正走在河北岸的春林把小英救了起来。他看到有人在河里挣扎,都忘记了惊呼,立刻跳入河中。
春林第一时间认出了小英。小英已经窒息,脸色像白纸。春林向四周发出几声救援般的唤叫声,可没有谁应答他,周围一片寂静。
把小英抱到河北岸的玉米地里后,春林稍稍镇定下来。他看到过好几次别人抢救落水者的情景,现在,他也要这样做。他在小英的脸上拧了一下,看到被拧过的地方立刻凹下去,又迅速弹回来,他心里就有底了,马上跪下左腿,弓起右腿,然后把小英背朝上、面朝下地横搁在自己弓起的右腿上。
午后的阳光洒下来,春林的头顶感到了阳光的热辣。他开始不住地颠动弓着的右腿,随着颠动,小英横着的身体也在上下颠动。他的右腿感受着小英肚腹的柔软,眼睛盯着小英的嘴巴,终于,他看到小英的嘴巴里开始挂下一线水流。
在阳光的蒸烤下,玉米叶散发着干涩的气息,地上的泥土蒸腾起干燥的气味。春林翕动着鼻翼,继续颠动右腿。小英嘴角那里流下的水线变粗了,她的喉咙口发出了一记轻微的声响,垂向地面的右手似乎还抓摸了一下。
这声响和抓摸让春林大腿的颠动舒缓下来,他的目光落在了小英身上,小英湿漉漉的上衣和单裤紧紧贴在身上,身上的曲线就显现出来。很快,春林又抬头四顾,目光中带上了一丝警觉神色。
周围没有人。不过春林眼中还是有些许担忧神色,他又转脸四顾,然后右腿完全停止颠动,左手向前伸去,像要去半空中抓摸啥。他的左手停在半空,仍带着一缕担忧神色的眼睛又朝小英看去。小英嘴角处的那条水线还挂着,不过变细小了;她的脸色在泛红,身体上的温度也在上升,春林的大腿已感受到了这体温。
春林的左手迅速落下,落在了小英圆滚滚的臀部。左手摩挲了几下后,他放下了小英,把她放到地上,两只手同时在她身上抓摸起来。可很快,小英的眼睛睁开了。
春林的眼睛第一时间和小英的眼睛对上了,他迅速移开目光,也迅速地把手移开。他单膝跪下,左手重新伸进了小英的胳膊间。
春林说:“你醒转来了。”
小英却重新闭上眼睛。
看着小英闭着的眼睛,春林觉得她已经没有问题。春林注视着小英右眼皮上一粒细小的黑痣,希望她躺在他臂弯里的时间长一点。可小英很快又睁开了眼睛,挣扎着要从春林的臂弯里立起来。春林搀扶着她,让她立起来,自己也立了起来。刚立停,小英的腿弯打晃了,身体就歪靠在了春林身上。
春林说:“怎么会跌到河里的呢?”
小英不出声,身体从春林身上移开去,也终于立稳,立稳在了离春林半步远的地方。
小英说:“春林哥,谢谢你。”
“怎么会跌到河里的呢?”
“在滩涂石上汏脚,滑了。”
春林不再细问。
好了,小英已经完全没有事了。春林瞥一眼靠在北岸边的一条鸭头船,又瞥一眼对岸,说:“上船吧,我送你过去。”
两人就跨到了鸭头船上。揽在一棵小树上的缆绳被春林轻轻一扯,就断了,也在这时,春林发觉船上没有撑篙和摇橹。这是一条弃船。春林让小英立在舱里不动,自己则立在船艄上,双脚使一下劲,稳住了鸭头船,然后向岸上伸出左脚,用力一点,鸭头船就快速地滑向河心。刚过河心,船的滑速就慢了下来。小英担忧的目光落在春林的背影上。她看到春林的双腿似乎又在使劲了,鸭头船就继续缓慢地向河的南岸移动。小英目光里的担忧消失了,她放心了。
看着春林的后背,小英心里突然产生了一股异常的感觉。她觉得自己刚才心里的那份担忧是冲着他的,现在心里的那份放心也是冲着他的。她进而觉得,自己心目中的真正男人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男人:既让她担忧又让她放心、安心。
她想到了阿戆。阿戆只会让她担忧,不会让她放心、安心,甚至连担忧都没有。她低头想了一下,发觉自己心里确实不曾对他有过啥担忧。
鸭头船靠近了南岸那个滩涂石的东侧,船头轻轻吻上泥岸。春林的一只脚放在船艄,一只脚放在岸上,两只脚让鸭头船定稳在了岸边。
他对小英说:“上岸吧。”
小英待在船舱里不动,似乎还不想上岸。可当春林伸出手时,她的手立刻迎了上去。春林把她一把拉到了船头上,然后轻轻托住她的腰,把她推送到了岸上。他自己也上岸了,在跨上岸的一刹那,用脚蹬了一下鸭头船,鸭头船在他的身后迅速滑开去,晃晃悠悠地在河心打起转来。
“缆绳坏了。”
春林好像在为自己的蹬船动作寻借口。而小英并不认为春林把鸭头船蹬到河心去有啥不好,她觉得就应该让它自由自在地在河中晃悠,想飘到哪里就飘到哪里。不要用一根绳子去拴住它,不要去当小船的主宰,不给它自由。为什么现在的人都喜欢当主宰?既想当物件的主宰,还想当别人的主宰?
小英回头看着在朝东漂移的鸭头船,嘴里小声嘀咕,你飘吧,随便飘到哪里,你想飘到哪里就飘到哪里,你是自由的,别人管不着你。
“你怎么像老人,对东西讲话了?”春林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小英,随后他笑了,“我救你的事你也只好对死东西讲,不好对活人讲啊。”
春林想到自己刚才那双不老实的手,舔舔嘴唇,又说:“你回家吧。”
小英抬脚后,春林朝另一个方向走了。没有走出几步,他回头看,目光与小英的目光相遇了。
六
还是有人晓得了春林救小英的事,小英跌进河的事还是传到她爸妈耳朵里了。美娟想问小英是怎么跌到河里的,可看到小英对她不理不睬的一副样子,就没有开口。美娟跟泉荣说起,泉荣就瞪她一眼,说你是阿木林?自己跳的!
美娟一听,身体当场软下来,瘫坐在了一只竹椅子里,然后放声哭起来。
泉荣又瞪她一眼,走开了。屋里,就只有美娟一个人了,她就尽情哭。后来,她的哭声变小了,可哭声还是显得委屈、绵长。好多人都听到了她的哭声。
对于美娟的哭声,路过她家门前的大部分人是见怪不怪的,因为经常有女人的哭声从哪个家门口传出,夫妻吵架、娘家有难、男人轧姘头、家里丢东西等等,都是发出哭声的原因。在横泾村,女人的哭声,有时就是这户人家的一种对外宣示,告诉外人,这家人家或者这个哭着的女人碰到不幸啦,可这不幸是外头人没法帮忙的,所以女人的哭声不是求援,只是一种告知、宣示。这种告知或宣示看上去与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相抵触,其实不,这种哭里没有具体内容,只有悲伤。这种哭是在把心里的悲伤往外放呢,往外放了,心里的悲伤才会减少,直到消失。站在外头人的角度看这哭,这哭其实也是平常的,见怪不怪的,哪一户人家没有难处、一直能避得开不幸呢?避不开的,横泾有那么多户人家,总有不幸降临其中一户人家。于是,在横泾,经常会有哪户人家屋里传出女人的哭声,外头人一般不去打听这哭声背后的故事,就像看到哪户人家屋顶传出炊烟后,他们一般不去打听这户人家到底烧了啥饭菜一样。外头人晓得,家家户户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碰到不幸的时候。一旦家遇不幸,男人承受力强,女人往往会承受不住,就要哭,她们会哭得委屈绵长、抑扬顿挫。她们中,会哭出好听和不好听两种味道——有些外头人路过发出哭声的人家,有时会立停脚步,听一歇,像听歌一样。这时,在屋里哭的人好像晓得有人在外头听,哭得更加抑扬顿挫了,甚至会哭出一股特别的韵味。外头听哭的人如果不认得这哭着的人,这时会开始在哭声里想象哭者的长相、年龄等,他不会揣摩这哭声所产生的原因,只会揣摩哭者的容貌、年龄等。
现在,美娟的哭声也是抑扬顿挫的,已经有一股糯糯的韵味在里头了。她不晓得外头有没有人在听她哭,可她晓得,她的哭既是给外头人听的,更像是给她家的不幸举办的一种仪式,这仪式是在“超度”她家的不幸呢。
可她家的不幸是啥呢?她的哭似乎是由小英的跳河引发的,不过小英不是由春林救起来了吗?救起来就是由“不幸”变成了“万幸”,美娟该高兴啊,她怎么哭了呢?——当然,没有啥人这样问。不,也许美娟的家人在心里这样问了,泉荣、小英,甚至红岗,都这样问了,尽管他们现在都已离开了家,可美娟的哭声早已进入了他们的耳朵。他们不是外头人,他们一定是在心里这么问了,只是没有问出口。到了夜里,泉荣的一句话终于证实,他确实在心里那样问了,他还自己回答了自己。
泉荣的这句话是对美娟说的,他说:“我看算了,还是到红桃家去回掉吧。”
美娟瞪着红肿的眼睛,说:“啥意思?”
“去回掉,回掉这门亲事。”
周围静下来,这种静好像是有重量的,压在了美娟和泉荣身上,让他俩的喘气粗重起来。美娟停了手上的生活——她正在叠衣裳。昏黄的灯光下,她手中已褪色的土布衣裳也泛着一层黄色,像是没有洗去的尘土。美娟把衣裳放在身左的竹椅上。
美娟说:“我不想让人戳背脊骨。”
她又说:“憨人有憨福。”
之前,美娟对泉荣说过这两句话,现在她是在重复,不过这次她说的语气好像不同了。哭过之后,在说这两句话时,她语气坚决,这让泉荣感到奇怪,也让泉荣感到灰心。
与美娟相反,泉荣刚才说话的语气倒比平时轻柔多了,好像不久前放声大哭的倒是他,倒是他把身上的力气哭完了,于是他说话的声气变软了。这声气其实与他说的那两句话的内容不符的,所以,就如他惊奇于美娟的话,一开始,他的话也是让美娟惊奇的——美娟惊奇于他说话的语气,也惊奇于他所说的话——他还是第一次对美娟说这种话。
泉荣说得比平时轻柔,不等于他是在随口说,他是一本正经的,他又轻声而态度坚决地说:
“去跟红桃说吧,回掉吧。”
“不回。”
“你不回,我去回。”
泉荣转身,跨出家门。他像是听到了美娟在背后发出的叫唤声,可他不管了,继续朝前走,走上了通向那幢走马楼的村道。走马楼是村里的老地主遗留下的一幢老宅,老地主新中国成立前逃到台湾后,村里的几户贫农搬了进去,红桃的公公家也搬了进去。
村道两边,乳白色的雾气在两侧的田野里升起,带着一股在白天积聚起的温热,飘荡到了他的身边。不一会儿,泉荣走到了走马楼前的场地上,在两棵青枫树中间蹲下——此时,他像怀揣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很怕碰到熟人,他甚至想把脑袋埋到两腿间了。
终于,泉荣还是从两棵青枫树间立起来,摇摇晃晃朝前面的黄岗岩门框走去。年轻时,即使在夜里,他也能看清门框上方“高家府邸”那几个字,此刻,他努力朝门框上方看去,却已看不清那几个字了。看不清,要么是风雨已把那几个字侵蚀得不像样子,要么就是他的眼睛已经退化,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太多的日脚已经从他身上、从他周边的东西上碾过,现在的日脚已经不是过去的日脚。
泉荣跨进门厅,闻到了鸢尾花的淡淡香味。他低头,目光落到门厅墙脚跟的几丛鸢尾上。门厅里尽管幽暗,可他还是看到了一朵朵的鸢尾花像一只只蓝色的蝴蝶,停留在鸢尾叶间,随时要飞起来的样子。他立停,走不动了,再次蹲了下来,就如刚才蹲在两棵青枫树间一样。
一歇后,泉荣终究还是立起来了,转身走离门厅。他明白,他是没法敲响阿伟家的门的,他是根本无法实现来这里的目标的——实际上,现在来这里的目标到底有没有,他也不清楚,这个目标或许只是嘴巴上的目标,只是他与美娟争吵声里的目标,并没有存在于他的心里。
泉荣在村道上往回走了,这表明,他和美娟的争吵已经结束。
争吵结束了,可泉荣的思绪还不能一下子平复下来,快到家门时,他没有继续朝前走,而是在场角上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然后,他又想了一遍自己与美娟的那几句争吵,笑了。他认为美娟的话是对的,美娟的话其实倒代表了他的意思,而他的话倒没有代表自己的意思,不,他的话只是代表他当时的意思,没代表他平时的意思。平时——讲到平时,他心头漫过一股水一样的东西,既暖又酸,说不清让他好受还是难受——对阿戆,他心头一直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感觉让他在阿戆和小英这门亲事上,感到自己像是男方一边的人。这让他自责,也让他自醒:在小英和阿戆这两个孩子的事情上,应该这样做,必须这样做(他心头有了一个偏向)。很难说,阿戆和小英的这门亲事,是不是这种“自醒”的结果,尽管看上去这门亲事是阿戆家的人主动攀上来的,可这种“自醒”是否无意中促成了对方的主动呢?在对方主动后,这种“自醒”是否加固了双方的那份约定?
回想起来,当泉荣心头发出了“应该这样做,必须这样做”的声音后,再看到小英时,他心里真切地感受到了一股柔情,一股父亲对女儿特有的柔情。他不晓得以前面对小英时,心里是否有过这种柔情,不管怎么样,他现在有了。他感谢这门亲事,让小英“成为”了他的女儿。当然,有时候他也自责,自责时,他会有一些“反常”的言辞和举动,比如和美娟的这次争吵,比如向阿伟家的这次进发。
好了,现在又回到了平时,他的内心也终于平复。他从石头上立起来,吸一口凉凉的空气,向屋门走去。
七
对于横泾村的人来说,时间就像横泾河里的河水,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河段,它看上去是不动的;也像中午时分挂在头顶心上的太阳,看上去是静止的。可实际上河水和太阳在一刻不停地动,时间也在看似不动地“动”,泉荣家就在这种“动”中迎来了一件大事。
在这件大事到来前,泉荣和美娟先是发现小英话更少了,不过变温顺了——她不主动跟泉荣和美娟说话,可当泉荣和美娟让她做啥,她都二话不说地去做,甚至泉荣和美娟没让她做啥,只要她觉得他们需要帮手时,她也会默默地上前,做他们的帮手——这完全是一个就要出嫁的姑娘的行派了啊。不是吗?好多即将出嫁的姑娘都是这样的,突然间话语变少了,可也突然间变勤快了。她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突然觉得自己说不出话了,她们只能用手、用一份勤快和体贴来表达心里的依依惜别之情,也表达对父母多年养育的感恩。大恩无言,她们怎么能用话来表达自己的感恩心情呢?不能的,说出来,这感恩之情就轻就薄了。所以她们不说,只行动。她们中,有人甚至会在半夜里悄悄地爬到她爸妈的床上,蜷缩到她妈的脚跟头、身体边或怀里,睡上一夜。她想回到童年,甚至想重新钻进她妈肚皮里呢。现在,小英尽管没有在半夜里睡到她爸妈的床上,可毫无疑问,她已经成为她们当中的一个。
不过,小英与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是不同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惜别和感恩时,一定还有一份憧憬。而小英心里只有恐惧和厌恶。不过,她把心里的恐惧和厌恶压制住了,不让它们流露出来。所以,她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无数即将出嫁的横泾姑娘所表现出来的样子。
这样子让泉荣和美娟心里难过,真正难过了。尤其是美娟,有一天夜里,落了半夜眼泪。后来,她用枕巾揩干面孔,起身走过间壁墙,躺到了小英床上——倒过来了,美娟倒成了一名就要出嫁的横泾姑娘,而小英则变成了她妈。其时,小英和红岗已分开睡了,美娟在原来的那张木床边给红岗搭了一张小床。当美娟睡到小英身边时,睡在小床上的红岗似乎听到了动静,翻了一下身子,嘴巴里叽咕一声,又磨了几下牙,就不再有动静,重新发出细微的鼾声。他没有被惊醒,真正被惊醒的是小英,可她假装没有醒转,假装还在梦头里。当她妈的手臂绕到她身上时,她一动不动;当她妈把脸颊贴上她的脸颊时,她还是一动不动。可她妈已经感觉到她醒转了,小英也晓得了她妈的这感觉。晓得了,她还是装作没有醒转来,装作还在梦头里。
美娟也不动了,手臂仍旧绕在小英身上,脸颊仍旧贴着小英的脸颊,好像她也睡着了。美娟侧躺着,小英仰躺着,两人就这样“睡着”了。这样的“睡着”能把两人真正带进梦乡吗?肯定不能,对美娟来说,抱着孩子睡觉已是陈年旧事;对小英来说同样如此,躺在她妈怀里睡觉不知是哪一年的事了。现在,她们已经不能回到过去,可她们这样做一定是想回到过去,这样,她们其实是在与自己过不去了。与自己过不去,只能让自己难受——两人不能再装作睡着了,再装作睡着,身上的皮肉就一定会酸疼,皮肉一酸疼,两人只能动。小英先动,她的身体一拱一拱的,既像在撞击美娟,更像要钻进美娟的身体里。美娟身上的酸疼感被拱轻了,可还有,她的右手就在小英的后背上轻轻抚摸,抚摸的动作牵动了她浑身的皮肉,她身上的酸疼感就基本消失了。小英身上的酸疼也消失了,不过朝她妈身上拱的动作似乎给她带来了另一种感觉,她想留住这感觉,甚至想让这感觉再强一些,就不仅继续拱,双手也开始在她妈身上抚摸,不,其实是抓摸。她妈身上像有着啥滑脱脱的东西,需要她一次次抓摸。她的抓摸是轻柔的,这轻柔地抓摸也像落在了她自己身上,让她心里那股暖暖的酥软感觉更强了。她把脸贴到了她妈的脸上,就跟她妈刚才做的那样。她的脸一贴上她妈的脸,她妈的脸就在她的脸上摩挲起来,她感到自己终于在那股暖暖的、酥软的感觉里融化了,融化进了她妈的身子里。她也就真正进入了梦乡。
可美娟还是睡不着,她就开始回忆,回忆自己嫁到横泾后发生的桩桩件件事体,也回忆嫁到横泾以前发生的桩桩件件事体。这些事体都是她经历过的,也是让她难忘的。把这些事体串起来,就是她的一条命运的曲线——在她还是姑娘时,有一次,一位算命先生曾指着她手掌上的一条纹路,说它是她的婚姻线。女人的婚姻线就是她的命运线。因为美娟家穷,给不起“卦金”,这位走村串户的算命先生不愿意再说下去了,拄着拐杖要走。美娟妈立刻把两个鸡蛋塞到算命先生的口袋里。算命先生就重新开口,对美娟说,你的婚姻大事一定要由你爸妈做主,我只能多说这一句话,不能再说别的了。算命先生多说的这句话是用两个鸡蛋调来的。现在看来,就是当时的两个鸡蛋把美娟最终引到了横泾——红桃当时来做介绍时,美娟其实与本村的一个小伙子好上了,可她爸妈是极力反对她嫁给这个小伙子的,而对红桃提起的这门亲事倒是极力支持的。后来,在大人们为小英和阿戆确定那种关系的前后,美娟也曾拿着“卦金”去给小英和阿戆算过命。算命先生的家在十几公里外,那里有一棵千年白果树,被人称做“仙树”,“仙人”就在“仙树”下为小英掐算。第一次掐算时,“仙人”居然说:你女儿的婚姻大事一定要让她爸妈,也就是你与你男人做主。这不由得让美娟感到惊奇,立刻想到了以前那个拿了她家两个鸡蛋的算命先生。更让美娟感到惊奇的是,“仙人”又加了一句:这样,你女儿的婚姻才能顺当。美娟就睁大了眼睛,看着“仙人”那张枯瘦的脸,又把目光转向一旁的白果树,看着这棵需几个人合围才抱得过来的大树,她很想给它烧根香,她也很想给“仙人”增加点“卦金”。可最后她啥也没有做,只是怀着一份敬惧回家了。后来,她又去寻“仙树”下的“仙人”了,这次,她报上了阿戆的生辰八字。“仙人”沉默一歇,然后说,没人说聪明不好,可实际上,聪明总被聪明误;没人对憨人道好,可往往是,憨人总有憨福气。美娟又一次睁大眼睛,又一次把目光从“仙人”脸上转到了“仙树”上。“仙树”粗粝的树皮上有一道弯弯的疤痕,它像一只含笑的眼睛,看着美娟。
现在,床上的美娟觉得那只“眼睛”仍含笑看着她。美娟的嘴角处也露出了笑意。她一笑,身体就放松了,身体一放松,一股暖暖的、酥软的感觉就上身了,这感觉和小英刚才的感觉是一样的,既是一种酥心的感觉,也是一种瞌睡的感觉。在意识到自己快要睡着时,美娟使劲睁一下眼睛,抬起放在小英脖子上的右手,在半空中抓摸着,像是一只溺水者挣扎在水面上的手。很快,她的右手重新落下,落在了小英的肚腹上。
美娟的右手感觉到了一份异样,她凝神想了一下,睡意顿时跑掉了一半。她的右手在小英的肚腹上抚摸了几下,心头的睡意彻底消失了。
美娟在床上坐起来,侧身拉了一下灯绳,然后掀开薄被,借着晕黄的灯光察看起小英的肚皮。
小英睁开了眼睛。
美娟连忙说:“困吧困吧。”
然后,她又侧身拉了一下灯绳,周围重新一片漆黑。
八
美娟后悔告诉泉荣了。泉荣在屋后拦住小英的一刹那,美娟就后悔了,她看到泉荣一把抓住小英的肩膀,低吼:“我还以为你是胖了!”
小英想挣,泉荣把她按在瓜棚边的石凳上,又低吼:“不要动。”
泉荣还从来没有这么粗暴地对待过小英,美娟很吃惊。接着发生的事让她更吃惊了,她见泉荣拿起地上一根细竹竿,开始往小英身上抽打,边抽打边说:“说,谁的?”
泉荣把自己的说话声压得很低,可在美娟听来,这声音还是那么响亮。
和压低嗓音一样,泉荣也控制着抽打小英的动作,他似乎没有狠命抽打,手臂没完全抡开,只用手腕用力。他眉头皱紧,嘴角歪斜,脸上显出了痛苦的表情,好像被他抽打的是自己。
每挨一下抽打,小英的身子就抖动一下,可她不挡不逃,也不叫。
美娟也像受到了挨打,她身体发软,腿弯打战,一下子跌坐到了地上。可她立刻又挣扎着立起来,往前走几步,把身体挡在了小英的面前。
这时候,如果老天爷的目光投向人间的这个场景,他会看到泉荣拿着竹竿的手迟疑了一下,眼睛里似有亮光一闪,然后,泉荣的手臂再次抡开了,他手中的竹竿落到了美娟身上。美娟的身体震动了一下,还发出了声响,人,也又一次跌坐下去。这一次,她跌坐在了石凳上。
老天爷听到了美娟身上发出的声响,它比刚才小英身上发出的声响要大。老天爷还看到泉荣的眉头展开了,嘴角也不再歪斜。
挨了竹竿后,美娟的嘴巴里没有发出声响。这一点,她是与小英一样的。她的嘴巴紧紧抿住,她似乎变成了电影里受到逼供的英雄。她又挨了一竹竿,身体再次震动了一下,双手的十指紧紧抠住身下的凳沿。
泉荣手中的竹竿落下的频率密起来,美娟的嘴巴里终于发出声响了,可她在压抑这声响,所以显得粗粝、喑哑,她试图把这粗粝、喑哑的声音压回到喉咙口,可失败了,失败后,这声响像是被撕裂了,带着“嘶嘶”的尾音。这种撕裂感就是她的疼痛。她的疼痛粗粝、喑哑、破裂,可这疼痛让泉荣眼睛里的光亮更亮了。老天爷看到这光亮一闪一闪的,老天爷认为这一闪一闪的光亮就是快乐。快乐大部分情况下会变成笑,甚至会变成手舞足蹈。如果快乐没有变成笑,变成手舞足蹈,就会变成快乐者眼睛里一闪一闪的光亮。这样的情况,老天爷看到的多了。就是在泉荣身上,老天爷以前也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他从红桃那里回来,眼睛里就有一闪一闪的光亮,这种光亮往往要持续大半天或大半夜。老天爷当然晓得每个凡人的快乐是从哪里来的,世间万事万物都掌握在他的手里,他哪能不晓得呢?他现在就晓得泉荣的快乐是从哪里来的。他看到泉荣发亮的眼睛里映现的美娟不是现在的美娟。好多年前,泉荣没有用竹竿抽打美娟,现在美娟送上来让他抽打了,他的手臂就抡过了十六年的时光,让竹竿落在美娟身上。
红岗的到来中断了泉荣的抽打。红岗冲上来,抱住泉荣,还朝石凳上的两个人哭喊,你们跑开啊!
泉荣扔掉了手里的竹竿。
尽管受了皮肉之苦,可美娟不恨泉荣。到了晚上,两人躺在床上时,美娟的身体悄悄贴到泉荣身上,泉荣动一下,微微移开身子。美娟又贴上去,泉荣就不再移开。美娟把手放到泉荣胸膛上,她想抚摸,可手臂和腰身上的疼痛最终没有让她做出抚摸的动作。她就贴着泉荣躺着,一动不动,泉荣也一动不动。后来,泉荣终于开口,说:“我要废了那小子。”
美娟像是没有听见,她没有立刻接嘴。
“不能便宜他。”泉荣又说。
美娟终于说:“他是谁?”
泉荣说:“对,他是谁?”
“我问你呢。”
“这死货色不肯说,我现在再去问她。”
泉荣要起身,美娟想拉他,可抬手的动作把她浑身的疼痛又都牵出来了,她嘴里呻唤一声。
泉荣转脸问:“怎么啦?”
美娟说:“不要去问了,是春林。你没有觉得?”
“我怎么没有觉得?打她时,我问管问,肚皮里还是清爽的。我就是想让她亲口说出来。”
“她已经亲口对我说了。”美娟声气绵软地说,“她不说,我其实也晓得是谁,我撞到过他们几次……”
泉荣重新躺到床上。
“我也看到过,可我没有往那方面想。”
“现在也不要多想了,领着她,悄悄打掉吧。”
“不,不能便宜了春林。”
“对,不能便宜了他家,应该找上门去。”
“你怎么顺我了?”
片刻后,一股警觉掠上泉荣心头。他重新抬起上身,他这次不是为起床,是为了看美娟。他和老天爷一道,在美娟的眼睛里看到了亮光。这亮光曾经在他自己的眼睛里闪过,在自己眼睛里闪时,他没有看到,只有老天爷看到,现在闪在美娟的眼睛里时,他与老天爷一道看到了。
“黄花闺女能让人随随便便困了?”美娟说。
美娟看着泉荣。泉荣注视着她眼睛里的亮光。
泉荣说:“这事不能声张,悄悄地领她去打掉。”
“悄悄地领她去打掉也有人会晓得。”
“这不管,这总比闹腾后让人晓得好。这事不能闹腾、不能声张。”
泉荣又说:“这事不能让红桃家晓得。”
美娟说:“要是晓得呢?”
“晓得我们也不承认。”
“晓得,他们也会当做不晓得。”
说罢这话,美娟眼睛里的光亮熄灭了。
九
看到红桃,泉荣想绕开,可红桃喊住了他。
红桃说:“怎么开始躲我了?”
泉荣舔舔干裂的嘴唇,说:“我躲你做啥?我又没有做啥亏心事。”
后来,他们走进了村道边上一个废弃的茶棚,红桃说:“美娟来寻过我了。”
泉荣呆了呆,随后,他听到自己的牙骨发出了响声。立在他面前的好像是美娟,而不是红桃,他的眼睛里都有火焰了。他朝地上看去,地上没有竹竿。不过,他的右手都在不由自主地抖动了。
红桃说:“我都没有激动,你激动啥?”
“我怎么激动啦?我有啥好激动的?”
“好,你不激动就好。我告诉你,随便发生啥,我家都不会变。”
泉荣的右手不再抖动,他看着红桃,又舔舔嘴唇,说:“我家也不会变。我家怎么会变呢?”
“可美娟好像要变。”
“笑话,她怎么会变呢!”
“不变就好。”
红桃转脸四顾,见周围没有啥动静,就压低声音说:“早点作日脚吧。”
“你家作吧,快点作好。”
泉荣再次舔舔嘴唇,想说啥,终于又没有说,转身走开了。
三天后,两人再次碰到,红桃就把作好的日脚告诉泉荣,说是一家人翻了老皇历的。日脚作在两个月后。泉荣抬头,看到天空像是一块巨大的蓝布,一朵朵白云是钉在上面的一块块补丁——他知道自己是高兴了,自己一高兴,脑子里就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
红桃说:“你朝天上看做啥?天上会落下好东西来?”
“不是落下好东西了?”
红桃举手揩一下眼睛,突然哭了,还男人一样蹲了下来。
泉荣说:“做啥做啥?”
泉荣想不到自己的话会让红桃哇的一下哭出了声来。他去拉她,说:“做啥做啥?”
红桃扬起脸来,涕泪纵横的脸上居然露出笑来,她说:“我是高兴呢,我高兴了就要哭,你又不是不晓得。”
泉荣的喉头有点发热,他也想蹲下来,然后抱住红桃。可他刚想这样,红桃就直起身来了,说:“走吧?万一被人看到。”
“我们又不做啥,怕啥?”
“不怕啥我也要走了。你还有啥话要对我说?”
“看你样子,倒像还有啥话要对我讲。”
“你看出来了。我还有一句话要对你说。”
“你说吧。”
这时,红桃反倒迟疑起来,目光里闪着一丝担忧神色,似在担忧自己要说的话会让泉荣不开心,甚至会让泉荣光火。不过,迟疑片刻,她还是说了:“你让小英带着身子来。”
说罢,红桃眼睛里担忧的神色没有了,她静静地看着泉荣。泉荣没有接嘴,与听到任何一句极其普通的话一样,他脸上的表情很平静。从这表情看,看不出他是不是会照红桃的意思办,不过即使他想这么办的话,小英本人和她妈不一定愿意这么办——红桃好像正在这么想了,她在转身前又说:“你也对美娟和小英说一声。以前美娟不是也这样,带着身子嫁到横泾村的。”
说罢,红桃走离了泉荣。
回家后,泉荣没有对美娟和小英说啥。实际上,他自己也不愿意听红桃的话,怎么可能想让美娟和小英听她的话呢?他只是一声不吭地牵住了小英的手,往外走。
小英想犟,他的手就捏紧。小英只得乖乖地跟着他走。后来,泉荣不再牵着小英的手,她也乖乖地跟着泉荣走了,她跟她阿爸上了队里的拖拉机。拖拉机到了香花集镇后,他们下来,转乘上一辆像要散架的公交车。
这是一辆开往江苏木渎的公交车,因为一天就两个班次,所以车厢里很拥挤,根本占不到座位。一歇后,泉荣和小英被陌生乘客隔开了。在车厢的晃动、乘客的挤压中,泉荣不时通过人体间的缝隙,朝小英看上一眼,有时看到她的半张脸,有时看到她的后脑勺。一路上,车子要停靠好几个车站,司机是个好心人,逢站都停了。可车里实在挤不进人了,在中途的某个车站上,有人就吊门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举动,可车子又不能不开,否则车子里的乘客要闹。司机就尽量往马路当中开,以免路旁的树木碰到吊在车门外面的人。后来,吊门的这个小青年终于到站了,还未等车子停稳,就跳下去,拔腿跑了。车厢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泉荣有个表弟是江苏木渎人民医院的医生。他带着小英要去找的人就是他。那时候,乡下人碰到这样的事都是这样的,都去远方寻找熟人或亲戚的,越远越好,最好出省。这个熟人或亲戚是医生的话最好了。
车子终于到终点站了,停靠在路边的一块木牌子边,木牌子上是五个蒙尘的字:木渎汽车站。
车门“嘎吱”一声,车厢里的人都像要扑向那块木牌子。泉荣是被人撞下车的,差点儿掼倒,好在他在木牌边及时收住了跌势,立停,双脚就一下子感受到了脚下土地的坚实。他又迅速往一旁跨开去,避开人流,目光开始寻找小英。车门口还在挤出乘客,这车门此刻就是一只水壶的窄口,在往外倒的却不是茶水,而是饺子,这些饺子争着从壶口出来,显得既拥挤又急促。在这种拥挤和急促中突然发出了一声叫唤,有人在车门下掼到了。
泉荣心头一紧,连忙跨步上前。泉荣的第六感觉是正确的,还没有等他走近,倒地的小英已经被人从地上搀了起来。泉荣对搀小英的那位老人笑笑,老人也笑笑。老人自己都有点走不稳路了,可那么多人中搀起小英的就是他。泉荣犹豫着自己要不要也去搀扶一下老人,然后陪他走上一段路。最后,他打消了心里的这个念头,只是走在老人身边,像是随时准备着去搀扶要倒下的老人,而小英则跟在他的后面。
乘客们已经四散,泉荣身边的行人越来越少,最后,那个搀扶过小英的老人也拐进了右边的岔道。
通往表弟家的泥道上只有泉荣和小英了。泉荣停住脚步,让走得过于缓慢的小英跟上来。待小英走近时,泉荣在尘土气息中闻到了一丝腥味,他疑惑的目光落在了小英苍白的脸上。他的目光开始下移,然后看到小英的裤管在滴水。泉荣的目光像是一只手,推搡了小英几下,小英终于支持不住,身体一歪,又掼在了地上。
直到这时,泉荣的脑幕上才像是划过了一道亮光,他醒悟过来:他看到的是血,不是水。他走上前去,在小英的身边蹲下来。
小英的裤管湿溻溻的,一股腥甜的气味再次钻进泉荣的鼻孔里。他想张口说啥,这时一辆拖拉机正巧在他们身边“突突突”地开过,迎面扑来的尘土让他呛了起来。就在他发出咳嗽声时,小英歪歪扭扭地从地上立了起来。
泉荣也立刻从地上立起来,他一步跨到了小英的面前,转个身,蹲下来,说:“上来吧。”
泉荣感觉到了小英的迟疑,双手就向后伸去,反抱住了小英的腿弯,然后身体前倾一下,迅速直起。他驮起了小英,开始往回走了。他晓得已经用不着去寻自己的木渎表弟了。
泉荣的脸上都是泪水。他心里,也涌动起一股水流,他不晓得是高兴的水流还是伤心的水流。
十
这次,美娟是拉着泉荣一道去十几公里外的那棵千年白果树边的,可是,“仙树”还在,“仙人”却已不在。白果树西侧的一幢砖木平房里走出一位老妇人,告诉美娟和泉荣,说他走了,半年前走的。
美娟把目光转向一旁的白果树,在这棵需几个人合围才抱得过来的大树上,她再次看到了一道弯弯的疤痕,它还是像一只含笑的眼睛,看着美娟。片刻间,这眼睛变成了那位“仙人”的眼睛,仍旧含着笑意。与此同时,似乎有和缓、低沉的声音也在美娟的耳边响起。
美娟侧脸,问泉荣:“你听到了吗?”
泉荣说:“听到了。”
“听到他说了什么吗?”
“听到了。”
“我也听到了。”
回家后,泉荣去了田里。美娟没有去,在客堂里腌起菜来。一会儿后,小英进门。美娟把她叫到身边,迟疑一下,然后用亲切的语气对她说:“春林是个聪明的小伙子,阿戆呢,也是一个憨人有憨福的人。”
小英不明白她妈说这话的用意,脸上露出茫然神情,不过只一歇,她似乎明白了她妈这句话的用意,脸上换了一种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