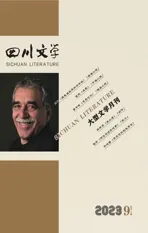马尔克斯教我写作
2023-10-15林为攀
□文/林为攀
文学对我的影响并非细水长流式,而是像一颗超新星大爆炸。这颗超新星爆炸的时候,我还在上高中,举目望去皆是打了鸡血的同学和老师,我无法跟上这种连呼吸都马不停蹄的生活节奏,便私自决定让我的生活慢下来。
我为自己的慢生活找到了三种方式:一是去学画画;二是去学唱歌;三是到校外租房。后来我回顾这段岁月的时候,才发现前两种举动差点让我与文学擦肩而过。好在我并没有绘画天赋,我不懂造型和光影的作用,也无法理解把一个实物画在纸上的实际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不喜欢灰扑扑的画室,不管是纸上的素描,还是大理石雕像和满地的铅笔灰。
离开画室后,我徘徊在县城的十字路口,一时竟忘了自己该何去何从。在随后的一节音乐课上,留着长发的音乐老师向班上一些高考无望的差生发出了招生邀请。当晚我和另一个在班上有“五中谢霆锋”之称的同学赶到了音乐老师的家里,向音乐老师表达了我们想学音乐的强烈渴望。音乐老师让我俩每人唱一首歌,最后表示我们都很适合唱歌,假如稍加训练的话,将来在乐坛一定会有我们的一席之地。说完让我们填写报名表,我的同学多嘴问了一句,上课要多少钱?音乐老师说每周末上一节课,一个月四节课,总共是两百块。我们当时囊中羞涩,又不愿找家长出这笔钱,只好遗憾地告别了乐坛。
眼看学画和唱歌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当时只有十七八岁的我似乎提前看到了自己将来必将被社会淘汰的惨状,有一段时间强行振作,把心思都花在学习上,可惜我依然对数学一窍不通,那些数字就像一枚又一枚锈迹,成功让我大脑的齿轮停止了运转。可以说,我的高中生活简直一败涂地,不过好在也有一抹亮色,那就是写作,当然不是写小说,而是写作文。我当时很擅长写作文,不管是应试作文,还是参赛作文,我都能准确摸到出题人的脉搏,为此让我的作文和比赛次次都能取得好成绩。此时我还不认识那个在《读者》杂志上熟睡的马尔克斯,他也不在我每周都会去一趟的学校图书馆。我认识他是我从学校搬出去以后。我搬出学校的原因是嫌宿舍吵,当时我不擅长与同学相处。当班主任知道我要到校外租房时,表示只要我父亲同意,她没任何意见。班主任以为我的父亲肯定不会同意,抱着胳膊戏谑地看我在她的办公室拨通我父亲的手机。我让班主任过来接听这通电话,胜券在握的班主任还开了免提:喂,你好,是林为攀家长吗?
我是。老师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你的儿子林为攀想去校外租房,我来征求你的建议。
老师,在校外租房贵吗?
好像只比住宿贵五十块。
既然这么便宜,那就去校外住吧。
“啪”,班主任果断挂断了电话,脸上满是来不及掩饰的尴尬。可以说,我从班主任当时的表现让我学到了珍贵的一课,即没有人会愿意当众跌股(客家话丢脸之意),他们会极力寻找借口找回自己的尊严,即便这些借口在旁人看来会增加跌股的成分。后来,当我走上写作之路时,每次要写一个逞强的角色时,我都会想起我的班主任。
我就这样从校内搬到了校外,比其他有此想法的同学顺利多了。其他同学要想在校外租房,找摩托车司机冒充家长去学校签字的有之,一人分饰两角在电话里既当爹又当儿子的有之,站在高处表示不遂他意就要往下跳的亦有之。后来我揣测我能如此顺利住在校外的原因并不单单是我父亲开明,而是他当时已经彻底对我的学业不抱指望了,因此才对我采取放养的姿态。我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后来当我弟读高中也想在校外租房时,却被我父亲强势拒绝了。
从此我就开启了一段家庭和学校两不管的“飞地生活”。出租屋是一栋刚建造起来的八层楼房,我租住在七层,每天开窗都能看到不远处的宿舍。我的同学们住在宿舍的四层,我因为住到了校外,一时之间竟比他们住得足足高了三层。我每天俯瞰在宿舍走廊忙忙碌碌的同学们,他们有的在一边刷牙一边在走廊上收衣服,还有的早上不愿早起,就躲在宿舍睡回笼觉,被班主任杀回马枪抓了现行。还有的早早起来在走廊上背诵英语单词……总之,宿舍走廊就像一个培养皿,我以此获得了写作的第一笔素材,就像创业之初收获的第一桶金。
我不愿有人在我的生活中指指点点,因此“独居”生活非常适合我。我当时留着爆炸头,穿着人字拖和故意剪了破洞的牛仔裤。现在重看高中时代的照片,我都会觉得那时的自己虽然很幼稚,可一点都不傻。你会穿过重重迷雾,从他特立独行的发型和衣着上看到一双明亮的眼睛,在这双左眼角有一颗痣的眼睛里,你会看到他已经找到了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那就是写作。在此之前,他已经独自在宿舍与文学交上了手,体验确实非同以往,其势能比他的老对手应试作文高了好几个量级。在如此强大的对手面前,他必须也要拿出百分之百的精力才能与之周旋。
虽然如此,我初登文学宝地却一头雾水,不入其门,难窥其奥。我只好等着灵感主动找上门,可是一连等了数天,灵感依旧没来,不知道是压根儿没来,还是半道迷路了。我不愿再被动等待,每天在课堂上,在出租屋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我在出租屋里阅读时,四周很静,只有蚊子被蚊香熏死后掉在地上的声音。可当我在教室里阅读时,四周马上就变得喧闹起来。后桌在桌上竖起了一本数学课文,看似在读书,实则在偷偷啃瓜子;左边的同桌在用镜子挤青春痘,嘶嘶声就像在抱啃一块滚烫的马铃薯。班主任在贴了报纸的窗外窥视,我这才发现报纸上的那个破洞刚好与班主任的眼睛同等高度。不过我还是在自习课后看到了残留在走廊上的红砖屑,也许班主任在报纸上抠的窟窿太高了,因此她只能在脚下加垫一块砖头才能看清教室里的众生相。
我生性敏感,不愿放过生活和学习中的诸多细节,但我那时不懂得这些细节的可贵之处,反而还为了证明自己不食人间烟火极力远离这些。我的文学之路极不顺遂,不是因为我缺少写作天赋,而是我还没找到符合自己的叙述方式。那时我相信只要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叙述方式,就能像能工巧匠鲁班一样在纸上建造出任何器物。好在我并没有花费多长时间的寻找,在我搬到校外三个月后,我在一本《读者》上无意间看到了一篇吹捧《百年孤独》的文章。
可是学校图书馆并没有这本《百年孤独》,我只好骑着单车去县城找。找了一圈,我在新华书店和博文书店都没有找到这本书,就在我以为这本书并不存在时,最后居然在一家专卖文具的书店找到了此书。它就躺在一众文具的最下面,封面蒙尘,内页发黄。
这就是我初识马尔克斯的情形,过程一点都不美好,就像网友线下见面,刚开始甚至还有点嫌弃对方。我把这本书放到书包里,书包被我背在身上,我骑着那辆买来的二手单车回到出租屋。那几天我都没有去上课,一直待在出租屋里翻看《百年孤独》。后来当我在史书上看到大部分帝王出生时都会天有异象,我瞬间就相信了这种看似荒谬的说法,因为多年前当我第一次翻阅《百年孤独》时,我的内心也突然电闪雷鸣起来,当然窗外还是和往常一样,并没有刮风下雨。
我看到第一句话时就被折服了,并在后来的写作中养成了一个坏毛病:认为开头是一篇小说最重要的地方。并不惜为了写好开头次次推翻要写的故事。这个包含三个时空的开头简直太迷人了,让我刹那间就窥见了小说所能达到的纵深。我从此不再一叶障目,并在每次写作之前,都会把自己当作孙悟空那样缩小和放大:先用缩小版回到过去检视这篇小说的历史脉络,再用放大版去到将来俯瞰这篇小说最远能抵达何处,最后再用正常版站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一手捏起过去那根线条,一手抓起将来这根线条,再把这两根线条放进嘴里抿一抿,看看我笔下的文字能否把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写出一篇具有万千气象又不缺内心幽深的杰作。
然而我在写作中始终缺少这种进退有序的从容与气度,经常迷失于脑海中密集的碎片。我没有办法把这些碎片有效组织起来,每一块碎片几乎都能另立山头,导致笔下的文字臃肿,不堪入目。每当这时,我都会重温《百年孤独》,看看马尔克斯到底是如何解决繁复的素材并把它们有机统一起来的。我不再像第一次阅读时,久久停留在开头,而是根据开头判断下文究竟如何具体呈现这三个时空。当然,从人物性格入手是个好办法,毕竟布恩迪亚家族在马孔多繁衍了七代人之多,几乎每一代都有两个相同的人名,看似一头雾水,不过好在不同的性格能让读者成功做出区分。
我探究文本的办法并非从人名入手,而是从动物入手,其中的黄蝴蝶、小金鱼和猪尾巴我认为是《百年孤独》中非常重要的密码与线索,你能通过这些动物解读出马孔多从建造到兴盛再到被一场龙卷风覆灭的全过程。我后来的写作之所以也写了许多动物,譬如水牛、秋田犬和鸡鸭,想必也是受该书这种风格的影响。
黄蝴蝶在《百年孤独》中非常显眼,因为这种弥漫死亡气息的蝴蝶即便在梅梅的爱情遭到毁灭后,依旧若隐若现地浮现在读者眼前。与中国一样,拉丁美洲的蝴蝶也象征着爱情,但黄色在拉丁美洲又象征死亡,于是黄蝴蝶的出现在带来爱情的同时,也带来了死亡。《百年孤独》这本书写的是持续一百年的孤独,但却经常用斑斓的色彩来烘托这种孤独,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认为孤独一定是冷色调。马尔克斯偏偏用暖色来形容孤独,这无疑让这种孤独更加立体,更加深入骨髓。我在后来的写作中也照猫画虎喜欢用黄颜色,比如金黄的稻谷,涂了黄颜色以示区分的鸭子等等。我知道所有故事终将在时间面前过时,但故事中堪比胎记的颜色却能永远留存在人们心中。
除了黄蝴蝶,小金鱼也是《百年孤独》中一个重要的道具。最开始,小金鱼只有一条,那就是奥雷里亚诺上校送给小蕾梅黛丝的那条。后来上校把拥有的十七条小金鱼分别送给了十七个儿子。最后小金鱼彻底沦为上校的收藏品,他停止制造新的小金鱼,而是一遍又一遍地融化掉旧的小金鱼。我不想从小金鱼的增多和融化等方面分析拉丁美洲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我更愿意从生活中来分析这些金鱼的作用。我认为小金鱼的出现并非政治隐喻,或别的什么,而是爱情。起初的那条小金鱼代表每个人的初恋,由于稀少而变得弥足珍贵,后来的十七条金鱼则代表历经千帆后的破罐子破摔,最后不再制造新金鱼而把旧金鱼融化则代表初恋是每个人永远戒不掉的瘾。当然马尔克斯为初恋找了两个结果,一个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当那份持续半个世纪的初恋少了中间的柴米油盐时,最后再次见面时依然会像最初那样甜蜜——每个人都只想享受爱情的甜,而不愿忍受爱情的苦;另一个就是在《百年孤独》这些融化又重新制造的小金鱼身上,它象征着在日常生活中爱情的模样:爱情在日复一日的吃喝拉撒中早已面目全非,所以要不断地通过融化小金鱼重温最初的爱情。上校融化又重新制造金鱼这个举动,在现实中处处能找到对照,也为后来的许多影视作品找到了灵感,比如《月光宝盒》《恐怖游轮》等这种用时空重复回溯叙事的电影。
猪尾巴是一种不洁的象征,我小时候经常听人说近亲繁殖就会生出带有猪尾巴的后代。当这种畸人越来越多时,就说明世界末日为时不晚了。《百年孤独》以猪尾巴收尾,可见马尔克斯对人类的命运并不乐观,当然这些都是小说家言。真实的情形是,就像人类偶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一样,猪尾巴出现的概率也微乎其微,即便已成事实,也会被大自然强大的调解能力掰回正轨。这也是我对《百年独孤》略有微词的地方,我觉得马尔克斯写到最后也难免落入窠臼,走到了谶纬算卦的老生常谈里去了。假如结尾不让马孔多毁于飓风,而是把前一百年的孤独无限循环下去,我认为此书会更上一层楼,虽然现在已经足够好了。因为死亡太简单了,并非人类的归宿,百年囚等于一日囚才是人类真实的写照。
遗忘和孤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本讲述孤独的鸿篇巨制中,遗忘也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甚至关于遗忘的篇章让我印象更加深刻。当丽贝卡这个远道而来的女孩开始吮吸手指、用指甲抠着墙上的石灰吃时,就给马孔多带来了失眠症,而失眠症又是遗忘的罪魁祸首。还有就是戎马一生的上校最后也罹患上了遗忘症,他战胜遗忘症的方式是在每个物品上写上名字,就像马孔多草创之初许多东西叫不上名字时需要用手指指点点。通过小女孩丽贝卡和老上校的遗忘症,我突然发现遗忘并非老年人的专利,孩童或者青壮年也有可能患上这种失忆症。我之所以对该书中的遗忘症记忆深刻,源于我的祖母。
我的祖母在晚年就饱受遗忘症的折磨,她会在饭点忘了厨房的位置,即使记得厨房在哪儿,也会忘了点火的火柴。反正一到要做饭的时候,她的记忆就开始丢三落四。但只要家人提前把饭做好了,她又会准时出现在饭桌上,而且舌尖还能成功品尝出哪个菜放了味精、哪个菜没放味精。还有就是,她对于好听的话耳聪目明,对于不好的话则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后来我才发现,祖母这种有选择性的遗忘症也有其缘由,那就是她需要靠这种方式尽力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假如她不装聋作哑,那么她的晚年仍无法停歇,依然要干许多活,如果她完全老得不能动弹,又可能会彻底遭到家人的嫌弃。因此她艰难地坐到了一个跷跷板上,巧妙地在干活与不干活之中找到了平衡点。
不过祖母的记忆可以任由自己打扮,但她身体的各个器官却都很诚实,当她的身体开始疼痛时,她终于承认自己败给了岁月。在此之前,她始终不服老,以为自己还能像从前一样徒步赶集。记忆可以杜撰或者修改,但疼痛却骗不了人,她开始逢人就兜售自己的疼痛,见到同龄人就说自己的心脏像蜂窝煤一样破了无数的窟窿,见到年轻人就说自己的肺管子像是损坏的扇叶,见到小孩子就说自己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她的疼痛视不同的人而定,而且心脏、肺管和眼睛正是她身上三大疼痛的源头,只不过并非同时疼,而是有个先来后到。有时是眼睛开始疼,眼睛疼的标志是爱流眼泪,她需要用手帕勤拭眼泪,她这副尊容被家人看到后,家人就会误以为她又在别人面前数落他们,然后就会在饭桌上指桑骂槐,但祖母仍旧装作听不见。心脏疼的标志是呼吸困难,好像空气里掺了沙子,每呼吸一次都像用嘴嘬断水的水龙头。至于肺管子疼,其外在特征就更明显了,只要走到离她三步远的地方,你就会听到她的肺部像堵塞的发动机,导致她再也走不了远路。
我后来重温《百年孤独》时,经常会把我的祖母代替里面的老上校,然后我的故乡就这样在我的记忆中变成了马孔多。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震撼并非源自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而是近在身边的感同身受。我能在里面找到许多现实的依托,我的故乡与拉丁美洲的直线距离足有16010公里,可是我呼吸的却和马尔克斯同样的空气。后来随着四季嬗变,我也早已从学校步入社会,对这本书的感受将会愈发深刻。因为人生就是一座马孔多,从选址开始就困难重重,好不容易建造成功,又要为维护它的荣誉而呕心沥血,可是最后仍然避免不了被红蚂蚁蛀空,导致毁于一场史无前例的飓风。
多年以前,我的足迹开始从南方漫无目的地移动,这双暂时还没找到心安之地的双脚在春天曾徘徊于漫长的海岸线上,也曾困在路比房屋高的西南地区,经历过初乘地铁与电梯的窘迫,也在几十米高空的餐厅掉落过刀叉。最后在北京一间潮湿的地下室里停止了漂泊,开始拿起纸笔,把自己多年来的惶恐与焦虑写在纸上。起初我并不会处理现实与小说的关系,认为写作应该与现实不能捅穿那层窗户纸,哪怕在小说中出现一个真实的地名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耻辱。因为我的恩师马尔克斯曾经利用自己的如椽大笔把整个拉丁美洲虚拟化了,然后任由在这片虚拟的陆地汲取所有用得上的元素。我要达到和他一样的效果,即看似虚构,却处处有现实的影子。可是我失败了,在我笔下的文字到处透露着矫饰与浮夸,我根本没有仔细考虑每一篇小说的纵深以及人物。我小说里的背景无一例外全像聚沙成塔,我小说里的人物全部都像行走在脆弱的纸上,好像走快一点,就会戳破这张纸似的。
因此我比多年前还没下定决心写作时更加恐惧,当初我还可以用自己不适合应试教育开脱,但面对自己选择的这条写作之路,我却不能再寻找借口,因为任何借口都是对我自身的彻底否定。而且写作又不能追求速成,越着急越不行,写作需要适当的压力,更需要一颗清醒的头脑,否则就会像我曾经无数次目睹过的牛被绳索缠蹄自缚一样。
我强迫自己慢下来,即使地下室外面的马路上和地铁里每时每刻都有无数步履匆匆的上班族,即使房租过几天就要交了,即使耳边频繁响起家人的问候电话。我开始更多地了解马尔克斯,了解他的喜怒哀乐,了解他在写作上的困惑。我把他的生平仔细看了几遍,最后得出结论,即使是马尔克斯,也不是一出手就是《百年孤独》。他也需要有《第三次辞世》《枯枝败叶》和《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才能写出后来令整个世界着魔的《百年孤独》。更重要的是,他也需要有师傅传授手艺,由开始的卡夫卡,再到令他倒背如流的《佩德罗·巴拉莫》。
马尔克斯用《百年孤独》给我树立了一个标杆,让我一开始就窥见了文学上的奥林匹克,也因此给写作之初的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为只要没达到本书水平的小说都不值得写,却忘了要到达这座文学圣殿,需要前期数十年的筚路蓝缕——写作不能只看结果,过程更加重要,而且很多时候恰恰是过程决定了结果。曾有无数作家受过马尔克斯的影响,这股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席卷自拉丁美洲的“文学大爆炸”,经过多年的发酵终于在二十年后抵达了东方。然后让大部分作家找到了毕生赖以攀登的高峰,从马尔克斯这棵大树上成功长出许多分枝,然后这些分枝又分别长成参天大树,供树下所有希望长成大树的嫩芽吸收水分与沐浴阳光。文学的谱系并非稻子和稗草那种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双木成林乃至万木成林的关系。
所有受惠于马尔克斯的作家即使口头上不愿承认,也会在自己的作品里若隐若现地呈现出与他的寄生关系。马尔克斯是一座高峰,既然是一座高峰,那么带来的阴影也会像黑夜那样深邃与坚不可摧。这也是大部分作家的可悲之处,一方面既要学习他的手艺,另一方面又要摆脱他的影响,在这座高不可攀的山峰中开辟出另一条路。我也曾为极力摆脱他的影响尝试过无数回,可是就像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游子仍然改变不了乡音一样,马尔克斯带给我在文学上的乡音我也始终无法完全抹去。后来我就坦然接受了这股来自文学浪潮的洗礼,我把重心放到了如何利用他的影响写出自己的故事上面。
直到写作十多年后,我才停下来仔细回顾我的少年时期。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口井,尤其对写作之人来说更是如此。我们手中的笔就是一把铲子,至于能把这口井掘得有多深,就看这把铲子有多锋利。在这口记忆之井里,深埋着无数层来自不同时期的化石。出生在城市里的作家能在里面挖掘出尘封上千年的胡同与巷弄的家长里短;出生在边疆的作家能在里面挖掘出遥远的驼铃声;出生在农村的作家能在里面挖掘出祖先曾用坏过的一把锄头……反正不管是都市,还是乡村,只要手头这把铲子没有生锈,总能在这口井里挖出自己想要的东西。文学是兼收并蓄的,并没有城乡之别,没有雅俗之分,更没有高低之分。文学只格外强调一点:是否发自内心。
十多年前,一个少年曾在校外的出租屋里津津有味地阅读《百年孤独》,在他嚼过许多其他晦涩难懂的小说后,终于在这本书里品尝到了小说的滋味,并立志也写出这种越嚼越香的小说。不过当初他未免把写作想得过于简单了,认为只要有条凳子能让他坐下来就行,没想到却会遇到这么多困难。他一方面既要和环境战斗,又要和自己的内心抗争,在他身边充满了太多的杂音,这些杂音全都是他写作之路上的绊脚石。从那时开始,他就知道,人们评判一个人从来不看过程,向来都是结果论。假如这个人缴械投降了,那么这些人就会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善事,提早让对方迷途知返了,假如这人最后有幸成功了,那么这些人又会把功劳揽在自己头上,认为自己当初的掣肘是一种激励,而且还会认为成功的程度与当初使绊子的力度密不可分。
不过即便如此,我依然对人类充满乐观,并愿意把这种乐观带到小说里。因为我深信,人类不会真正遭遇马孔多里那场毁灭万物的飓风,孤独与遗忘终将会像疾病一样被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