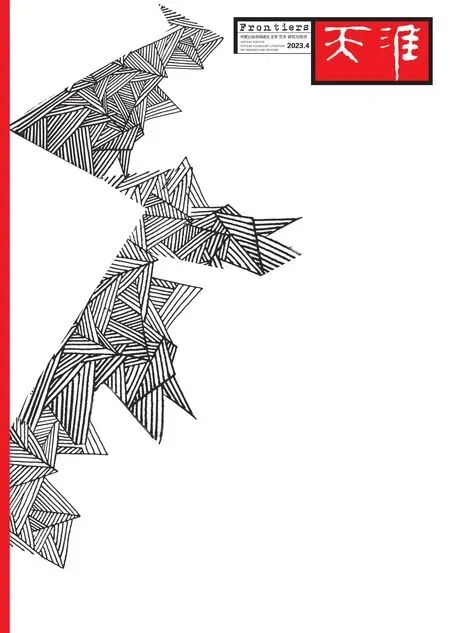疾病、艺术与互助
——李博、唐浩多对谈
2023-10-14李博唐浩多蒋浩
李博 唐浩多 蒋浩
源起
李博从十九岁患尿毒症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与这种绝症伴随、忍受和抗争一生。他在患病之初,碰见了当代艺术,特别是受他偏爱的装置,并以此作为他人生的一部分。即使他一直处于中国艺术圈的最边缘,作品也不曾被更多的人看见和认可,但是他仍然在坚持对艺术的实践和思考。李博在去年11月份被诊断为肝癌晚期,但是他并没有打算进行治疗,反而是觉得心里踏实。“万物皆有病”是李博确定的展览主题,他说万物并不是完美的,我们要接纳这种不完美。李博的本次个展,不仅是他个人艺术之路的回顾,同时也是一场人生的告别。这场展览并没有艺术机构的支持,而是由他的艺术伙伴和朋友们合力相助筹办起来的。这完全是一场自发性的展览,它由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串联起来,所以这也是一场“互助行动”。本次展览将展出李博自2006 年以来的手稿、绘画、方案效果图、行为和装置等近60件(组)作品(其中有5件装置作品是第一次呈现)。观众可以通过这些作品,了解李博的经历、生活、情感、病痛、婚姻、艺术和思想。此外,李博还有一个正读初中的还未成年的孩子,因此我们也希望本次展览既是为了完成李博的心愿,也是对他儿子的关注和支持行动的开始。
(唐浩多)
前言
疾病无异于受难。很难想象,李博从十九岁到现在,二十年始终饱受病痛折磨的同时,还在孤寂地从事自己喜爱的当代艺术实践。在他自己看来,艺术不是治疗,不是自恋,不是审美,不是雅趣,不是拯救,而是“批判”(李博访谈)。这意味着他至少在同时进行着两种孤绝的战斗:与自己身体所居的病魔,与自己身体所处的时代。也许,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病人对他认为的“万物皆有病”的时代的发自本能的身体性理解、诊断和对话,但这孤绝的“一个人的运动”(德·库宁语)无异于双重的受难。真可谓:博者,搏也。因此,对于李博来说,每况愈下的“沉船上的生活”(杜尚语)就像《生,活》(2008)中那倒扣在大地上的青花瓷碗,简直就是在心里隆起的一座巨坟。而在高速物化、动荡不安的当代同质—拟真生活造就的《旋转的人》(2012)中,具体有别的个性细节被抽象成柱体上凹凸起伏的曲线构成的共性轮廓,展现的正是一个失去个性或“没有个性的人”(穆齐尔语)的“脸之悼亡”(里尔克语)的同时代悲剧。如果把这个作品理解为是对德勒兹意义上的“无器官身体”的某种重构和致敬,那么李博显然不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光明柱》(2012)中蜡烛燃烧熔化形成的人形蜡烛和烟熏形成的人形黑影之间毕竟是有一道光,照耀和指引着他的“坚持”、“方向”和“正直”品格,像那枚经过他艺术分解的《螺丝钉》(2012)深深地楔入到他的整个艺术思考中,因此,他手稿中那只理想主义的《气球》(2019)利用挣脱地心引力的艰难飞升来拉满弓弦。《凝视》(2017)显然是对深渊哲学(尼采)的又一次积极改写:你凝视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眼睛。与其说这种自我凝视是对自我的“精神空间”的追问式概括,不如说是我们对待生命的他者态度,不管是因为疾病,还是因为艺术,或如李博这样,不管是二者兼而有之,还是兼而因之,正如尼采所说:“不妨大胆一点,因为我们终究要失去它。”善哉!
(蒋浩)
唐浩多(以下简称唐):李博,你好!我第一个想了解的是,你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请你概括一下。
李博(以下简称李):童年就是在农村度过的,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十几岁初中毕业。小学的时候比较听话,那时候读书成绩还是算比较好的,初中就开始跟着(别人)玩,学着抽烟。那时,我家里的生活条件在农村还算可以的。
唐:你当时读小学的时候是在农村上的学吗?
李:一直都是在农村,从我出生起,读小学和初中基本上都在农村,很少去别的地方。初中的话就在镇上,一个很小的镇,哪也没去过。
唐:那当时在农村上学的时候是跟谁在一起生活?
李:在农村的时候,父亲在外面做生意,基本上每半年回来一两个月。我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跟我母亲和我姐姐在一起生活,没有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唐:当时你也算是一个农村的留守儿童,因为父亲常年在外面做生意,这一段经历,对你有没有影响?爸爸不在身边的话,你当时心里面会怎么样?
李:当时农村的小孩子基本上都这样,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一段时期,每个家庭都是三四个小孩,父母基本都在种地。我家里面也没怎么种地,毕竟父亲在外面做生意。母亲没上过学,也没有文化,所以说小时候在学习方面也没人管,我过的是比较普通的农村小孩的生活,对比现在来说也不算是留守儿童。因为最起码母亲一直在家里面照顾我们,父亲有一些文化,但是常年不在家,在学习方面也没有管我们什么。那个年代基本上每家小孩都多,大多数农村人都没什么文化,基本上也没怎么去管小孩,儿童的心理和学习方面,他们也不懂。感觉也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基本上都是那样的,每家每户基本上都是那样。
唐:就是说其实没有跟别人有家境上的不同,其实可能也不是说没有影响,但是因为大家都一样,没有差别,是这样吗?

油画《十月怀胎》 60×80cm 2007年 李博
李:对,基本上就是这样。自己跟其他小孩子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说有些父母是一天到晚在种地,而我父亲在外面做小生意,我母亲有时候也种地,但是种得比较少,然后就打打麻将什么的。
唐:那你是什么时候才跟父亲长期生活在一起?
李:大概是从2015 年开始长期生活在一起,之前他基本上都是每年回来两次,每次回来待半个月或一个月。
唐:当时你已经结婚了,是吗?
李:2015 年那时候,我差不多三十一岁了,我儿子都八岁了。
唐:那就是说,你从童年到青年的大部分时间是没有跟父亲生活在一起,那么当时对父亲有过一些不解或者不满吗?
李:小的时候是有的,一直到十几岁都有这种想法,感觉父亲经常不在身边,好像没什么依靠和安全感,后来逐渐习惯了。习惯以后,后来经常跟他生活在一起,反而感觉还不如以前那么的舒服了。
唐:因为经常不在一块,所以人的情感的联接是减少的,就有点变得陌生。二十多年以后,又生活在一起,就变得有点像是跟一个陌生人生活,情感上还是有点疏离的。以前,我也不算是留守儿童,我是流动的,我跟我家人也是有一种疏离感。
李:对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就是总感觉观念或者是什么话题都聊不到一块去,或者说各有各的想法,经常产生一些争执。
唐:那你年少的时候有过叛逆吗?
李:我很小的时候特别听话,到初中时,十五六岁开始产生叛逆心理。
唐:你能描述一下当时的这种叛逆的状态吗?比如说对某物某人某事有一些怎样的一种质疑,或者是一种抵抗?
李:那是上初中以后,因为离家远了一点,学校在小镇上,骑自行车十来分钟。那时,开始偷偷地旷课,或者是在外面打游戏,学着抽烟,跟着一些外面的人玩。这样子就基本上不爱学习了,就变成了班里面最差的那一批中的一员,经常坐在最后面睡觉。
唐:但是它有个过渡,你当时作为一个比较好学的,班里面学科成绩不错的一个学生,转变成为一个翘课、不学习、爱睡觉(的学生),这样的一个变化。我特别好奇的是那种转变是怎么来的,或者是当时你的心理是怎样变化的,当时是怎么想的,有没有过一个难忘的一瞬间?是什么能够让你放弃过去小学生的那种状态,转变成为初中生这样的一种状态?
李:那个时候主要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父亲生意的失败,刚好我是在读初中,那段时间,我父亲有两年没回过家,过年也没回。然后,初中二年级开始,家里没钱,上学经常被老师赶回家,因为我交不起学杂费。平常这费那费,一交就是一两百,那时算很多了。这样,我渐渐地不爱学习了,也趁着被老师赶回家的这个“机会”跑去玩。主要是父亲生意的失败,家庭条件的急转直下,再加上离家里比较远,那时候也没有电话,老师也没办法马上去找家长,所以说那时候就转变挺大的。
唐:家境的变化,父亲的创业的失败,带来了生活的变化,包括你的学习和身份的转变。那你觉得这样一段儿时的经历,包括后面叛逆期的一个转变,对于你后面的生活,比如说现在选择当一名艺术家,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吗?
李:应该说多少会有一点,如果那时候学习成绩一直很好的话,可能来到海南之后,学习应该也挺好的,再怎么说也应该不太会去学习绘画,即使生病以后也不太可能去选择绘画。学习绘画毕竟比较轻松一点,对我个人来说,对我的身体来说。生病以后,学习成绩也不好,即使重新读高三,再重新考试,也考不上大学,所以那时候干脆就读了成教班,想去学点书法,画点什么行画,给人家画画装饰画之类的。刚开始就是这种想法,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后来,才慢慢喜欢上艺术,开始接下来的学习生涯。
唐: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如果不是后面的转变,有可能你就不会接触到艺术,像你说的学习好的话就不会学画画了。那现在来看,成为一个艺术创作者,你觉得当时的那种转变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油画《我和儿子》 60×80cm 2012年 李博
李: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说是好还是不好,毕竟你走到哪一步,是无法预测的。也许当初我一直好好学习下去,考个好学校,或者是上个名校什么的,过得也挺知足挺好的,但是这个东西没办法说。只能说是走到哪里算哪里,最好的结果就是我毕竟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我还能够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就觉得挺好了。有很多事情并不是按照你想象的那样发展,只是说走到哪里再看,再一步步往前走,只要是你能够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好坏,或者说规定你一定得做什么,毕竟做什么还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唐:就是说人的生活,人的生活的转变,选择做什么样的人,或者做什么样的事,过什么样的生活,它并不是由人的一个意志来预定好的,就像你说的那样:我们还是随着各种人生的转变,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也是对命运的一种接纳。
李:是的,接受生活,再去发现生活,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坚持做下去,这就是后来的我!
唐: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当代艺术的?
李:最早接触是在2006 年。2006 年的时候去大学里学习绘画,因为身体的原因就想学一下绘画。在学绘画的时候接触到一些同学,他们比较了解当代艺术嘛,我当时是一点都不了解。所以,经常跟着他们了解到一些当代艺术的信息。那时候当代艺术也比较火嘛,我慢慢地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当代艺术,包括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等。了解到以后,我就特别喜欢装置,特别钟情于装置,就从2006年开始,去查一些资料,买一些书,开始去了解它。

装置效果图《螺丝钉》 2012 年 李博
唐:刚才你说到比较钟情、偏爱于装置艺术,那你觉得做装置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李:最吸引我的是做装置艺术时对材料和空间的利用,这两种东西比较吸引我。像行为艺术,以我的性格,我不太适合做。所以我就把自己缩小在装置艺术这一块。当代艺术有很多类别、很多形式,我就特别喜欢利用一些材料,采用一些不同的手法,结合一些空间,去表达自己的一种感想或者是一种体验,所以就一直在坚持做装置。
唐:我看到你有很多作品方案的手稿,其中很多做成了效果图。因为我也是做当代艺术创作的,也会面临经费的问题。当时你是否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会想着用效果图来呈现,它能够起到一个替代的作用吗?还是出于什么考虑?
李:有时候想知道作品的具体效果是怎样的。当自己有个大概的想法时也会画一些草图,但是真正想知道最后呈现的效果,你就必须要做出效果图来,看看是否能够达到你想要的那种效果。我以前也想去做一些简单的装置,也想去把它做出来,所以就做这个效果图。另外也想去报名参加一些评选,别人要看效果图,我没有实物图,也不敢轻易去把一件装置做出来,因为经济条件太差了。做成效果图的话,就便宜一点。如果有展览,需要我去展览某件作品的话,我就可以先把作品效果图发给他,再去做出来,这样的话也不会浪费经费。我自己这么多作品,如果只是给别人看草稿的话,别人有时候也不知道你具体想表达什么。因为装置本身就很注重空间感的那种效果。有些装置作品,如果我不在旁边写上一些阐释性的文字,有些人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就做了很多的效果图。
唐:你觉得艺术和你的关系是什么?
李:反正我自己觉得从我生病以后,也干不了其他很累的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接触了装置艺术。从感兴趣到创作,那时候就觉得我这辈子即使一事无成,我也离不开装置艺术这种表达形式。我本身就不是很擅长用语言表达的人,但是装置它会让我感觉像是一个人写日记一样,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呀,一些经历呀,融入到装置里面去,用装置来诉说一些自己的经历、经验,自己想说的话、想表达的东西。它就像是我的一种语言、一种私人的日记本一样,最能表达我内心真实的东西。它在我生命中,就像一个人和他的语言一样,合为一体了,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到现在,可能在我死之前,我都会一直做下去,即使一件作品也卖不出去,哪怕自己的作品从来得不到那种所谓的高端成功艺术家的认可,但我觉得总会有人去理解它,所以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唐:我觉得无论做艺术也好,还是做其他形式的事情也好,对一个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它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一种精神方面的组成部分。其实你刚才说到了一点,不管在这个系统里面、在这个圈子里面,能否获得知名度或者所谓的成功,我们仍然会继续做。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包括以前有一些艺术家,也是这种情况,他们好像是带着某一种目的性或者某一种功利性去进行艺术创作,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有一些人最后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就停止或者转向了。但是你仍然还在坚持着,特别是你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之下,还是坚持在做,不管是做方案还是对这方面的思考,我觉得都是挺可贵的。你是一个真正热爱艺术和做艺术的人,这一点很打动人。接下来,我想请你来聊一下,你是如何看待当代艺术在中国的现状的?
李:现状的话,我觉得大部分做当代艺术的艺术家,比较倾向于市场。他们可能也是受市场的影响,受生活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为了让作品好卖一点,有些做得很花里胡哨,或者是景观式的那种,能吸引大众眼球。但真正纯粹的,去关注当下一些事件,关注当下社会的某种现象,去做出一些真实的、批判性的东西,我就比较喜欢。只有思考当下,这个社会才会更加进步、更加美好。
唐:你刚说到一点就是当代艺术需要批判性,在我看来也是如此。当代艺术之所以成为这时代所谓的一个先锋(过去我们也会把它称为先锋艺术),是因为它具有这种批判性。我觉得这是当代艺术的本质之一吧,我也是非常认可你的看法。
李:不仅是对社会的批判,还有对当代艺术自身的一种批判。
唐:对!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组织或者是固定的某个流派。当代艺术不是一个流派,当代艺术讲的是思想价值的问题,它永远都站在一个批判者的角度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李:当代艺术也是非常多元化的。
唐:对!多元化是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思想理论。刚才你说到自己的病痛的问题,那么能不能谈一下这一场病?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对你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李:发病的时候是2004 年,我在高三上学期,之后做了移植手术,五年之后又发病,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个社会,生病的人很多,比我更惨的也有很多,所以说生病对于我来说,是我必须接受的一种现实吧,就像做装置作品一样,你必须去感受那种真实,去接受它,接受之后顺其自然地去生活吧。
唐:当初在高三的时候,你年龄应该也是十八九岁。
李:那时候是十九岁。
唐:十九岁,当时你对这种病有了解吗?
李:一点都不了解!我当时身体很不舒服,去医院,有经验的医生一看全身浮肿啊、心率快啊、血压很高啊,就直接让我去抽血化验。因为是急诊,结果很快就出来,半天时间吧,各种指标出来以后就诊断为尿毒症晚期。
唐:当时,你知道尿毒症晚期这个诊断结果之后是什么心情?
李:高中的时候还不是特别成熟,我也不知道会一直透析,那时候不懂,我以为半个月、一个月这样子出院以后就会好了,从来没有想过透析这么多年。那时候父母也一直陪在身边,都是安慰说,没事的。

李博手稿
唐:没告诉你实话。
李:对。我也没意识到这个病的严重性,也不懂。
唐:什么时候才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
李:大概做了半年透析以后,就知道这个病没办法医治,只能做肾脏移植。透析一年以后就做了肾脏移植手术,后来才了解到即使做了肾脏移植,也是有年限的,后面基本上就比较了解了。做完肾脏移植以后,就看靠自己保养的情况了。
唐:可以谈婚姻的问题吗?
李:可以。
唐:你结婚是在什么时间?
李:我在2007 年结婚,大学没有毕业,上一年大学,出来就结婚了。2006年,上了一年的成教班。
唐:是在省内还是省外读?
李:海南大学的成教班,混了一年,2007年结婚。
唐:当时跟你老婆,现在算是前妻了,当时你和她在一起是怎样的一个机缘?
李:是家里人介绍的嘛,她和我是同一个地方的人。结婚之前我也把我的这个病告诉她了,她也能接受。以为(肾脏移植)可以用很长时间嘛,起码用个十年八年,没想到五年就坏了,我又发病了。从我又发病以后,家里面经济条件又开始下滑了。
唐:我记得以前你做过一个行为作品叫《求生之路》。你当时在写关于征集器官捐献的一封公开的求助信。如果有人遇到意外后,当他意识还清醒的时候——我不一定记得清楚,你可以纠正一下——就是说希望有这样的一些人可以把肾脏捐赠给你,是这样吗?
李:对。但是这个行为艺术作品的初衷并不是说真正为了去寻找一颗肾源。我当时做的背景是,那个时候在中国愿意去捐献身体器官的人很少,包括什么肝移植、心脏移植,这些都非常非常稀缺。很多人都等着这个救命,需要别人捐献。但是在国外很多,包括国外很多健康的人,他们都会有个生前遗嘱,有遗体和器官捐赠的协议书。所以,我的目的就是想从身边的朋友开始,一点点去影响大家对这种器官捐献的理解。这样的话,以后捐献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就像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捐献了。一个人脑死亡以后,他的身体器官可以救活好几个人、好几条性命。现在的人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了,也是因为社会的进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现象。
唐:当时,我记得是你的前妻愿意跟你签了这个协议。
李:对。她愿意签。
唐:当时已经离婚了?
李:嗯,离婚了。她愿意捐献,但并不一定是捐献给我,因为这个是要配型和排队。我如果跟她是夫妻关系的话,她是直接可以捐献给我的,但是我们已经离婚了,即使她要捐献也不一定轮到我。她跟我签这个协议,是我想让她参与进来,因为她也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假如出了事故啊什么的,如果她愿意捐献器官的话,也能救活很多人,但不一定是我,我只不过是想要通过这个行为艺术,让身边的人去了解器官捐献。
唐:对。我当时在康学儒策划的“海的距离”那个群展的时候看到你这个作品,印象很深刻,尤其深刻的是你的前妻愿意签了这样的一个协议。虽然说她不一定把这个器官捐给你,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但她是在你身边的人中第一个去响应你的人。在我看来这是挺能打动人的一个行为。其实她和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是普通人,不过她是一个非艺术家的身份,而且她也不是很喜欢写作或者做其他艺术创作的人,我们只是比她多了一个(做艺术的)嗜好而已,但是她却能够支持或者理解你的这个行为和作品,并且作为第一个参与的人。
李:因为她跟我毕竟生活了这么多年嘛,对这个病情也比较了解,所以她可能比一般人要更加地知道器官捐献的重要性。只是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但是她对我这个行为艺术还是很支持,而且很理解。因为她毕竟接触我的这个病情有很长时间,她比一般人要理解,所以她就第一个签了。
唐:对。而且我感知到你也挺接受这段婚姻的离舍的,也能够理解她。
李:我能够理解。
唐:嗯。是你提出来离婚,还是她提出来?
李:她提出来的,那时候小孩还小。她之前就有提过,我当时没答应,是因为小孩子才几岁。我就跟她说,你可以去外面打工,但是先不要正式离婚,先不要影响到小孩。但是后来小孩长大几岁,她觉得小孩可以接受了,然后我说,你既然觉得小孩可以接受,那么我也没有办法去阻碍你的。毕竟两个人可能三观方面不太一样,虽然她也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而且我的身体状况、经济情况也不好,自己没有经济来源,对于她来说都是一种束缚。所以说与其这样子,还不如让她自由。我觉得要互相理解,就像她愿意第一个跟我签那个协议一样,互相理解嘛!
唐:当时结婚的时候,是父母有这种欲望,还是你有这种欲望?
李:我们结婚,是比较草率的那种,她那时候年龄也不小,她比我大半岁。我家里也是急着让我结婚,就是让我传宗接代,带着一个目的性。她家里也是带着目的性的。那个时候,她也是为了快点结婚,再加上我家里那时候条件还可以,我们就很草率地结婚了。在我们农村,很多人都是这样,都是经人介绍之后,半个月一个月就结婚了,然后又出去打工。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八后离婚率很高,是有原因的。
唐:就是说她开始结婚的时候,是在一个比较草率、懵懂,或者不是在自己全然的意志之下结了婚的。所以到最后她还是会觉得自己隔了一层,当大家都可以坦率地去面对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婚姻的变化,其实都可以理解。
李:互相都可以理解,没有什么怨恨之类的。
唐:其实都是一代人,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好像都是父母左右了很多。
李:特别是八后这一代。
唐:很多人的婚姻都会有父母的一个想法在里面。当他们在度过婚姻的时候,就知道婚姻的这种尴尬存在着某种不可调和。然后各自都想再追求一下自己的生活,这个时候就会提出离婚的想法。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接下来我想请问你,你是如何去面对这种病痛呢?你方便说你现在还有其他的什么病吗?
李:我现在是尿毒症晚期已经十九年,最近又查出肝癌晚期。反正经历了这么多吧,我觉得受的苦我也熬过来了,对于生死这个问题或者说得了两种重病,我已经可以非常平静地接受了。我确诊肝癌的那一天,我心里就挺踏实的。真的!因为我感觉不管是尿毒症十多年也好,还是得了肝癌晚期也好,就是说我的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而且这么多年面对生死,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死掉,这是很焦虑的。就像一个杀人犯在外面逃,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但是突然被抓到以后,反而踏实了。
唐:这种踏实是来自于什么?
李:来自于有了一个确切的结果,就是知道我的时间还有多长。然后,心里的那种焦虑感就减少了很多,就不会再担心我什么时候死呀,我还要活多长时间呀!因为这个病一般都是,快的话两三个月,慢的话半年。而且,现在我家里也没有钱去治疗呀,吃什么药呀,就是已经完全放弃治疗,只是在做透析而已。
唐:就是还在做针对尿毒症的这个透析。
李:肝癌的话,就是放弃治疗了,就这样了。所以说自己过一天少一天嘛,好好地开心地去过吧。
唐:对于我来说,可能不会存在这种焦虑,因为我没有病痛。我其实有点害怕和恐惧发生那种不知所措的意外。你面临长期的十九年的病痛,当时诊断就已经是尿毒症晚期了,这十九年来,你觉得比较痛苦的是什么?
李:十九年来最痛苦的就是没有自由。因为离不开医院,不管去到哪里,首先要找医院,而且隔一天去一次,完全没有自由。得尿毒症的话,不能乱喝水,吃东西也要小心,睡觉也睡不好,身上也痒,还要面临一些并发症,面临透析中的高血压、低血压等等各种问题。很麻烦。这十几年,真的是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再加上事业上,可以说是一事无成吧,三十多岁还是啃老。十几年来,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在困扰着我的。所以,当我得知又得了肝癌晚期以后,我觉得以后不用再面对这些了。我觉得这就是命运的一种安排吧!如果不是肝癌晚期,是我自己跳楼或者什么样的话,可能别人会觉得我多少有点不负责任,对家庭呀,对小孩呀,是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对于我来说,我可以接受。而且我能够非常平静地去接受,非常坦然。我确诊以后谁都没告诉,父母都没告诉。
唐:到现在也没说吗?
李:现在他们知道了,因为还有一些后事需要我去交代嘛!我交代给我姐了,后来我姐告诉我父母。父母也理解,他们知道家里条件也就这样,不可能再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他们也慢慢地接受现实,毕竟我也生病十九年了嘛。他们也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唐:说到父母的话,作为父母的角色,面对自己的孩子十九年的病痛,这样的一种折磨(是十分巨大的)。对于你父母来说,我想他们也不轻松。
李:对!父母也过得比较辛苦,这些年。
唐:父母也是过得比较辛苦的,因为自己的孩子。但我们也没法知道他们当时的想法,但是这么多年来,他们应该跟你差不多,(现在)也是有一种解脱感。现在反而好了,像你说的,都很坦然了。对于自己的生命,面对这十九年来的病痛,在挣扎和抗争中度过。当然,这个也是需要意志的,我觉得如果意志薄弱的人,可能会像你说的那样,会用其他的方式来结束生命。另外,谈谈我们最近要筹办你的这个个展吧。你觉得这个个展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李:这是我第一次个展,也应该是最后一次个展了吧!对于我来说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做艺术,一边学习,一边创作。从2007 年开始吧,一直到现在2022年,有差不多十五年了吧。这是对我自己的生命的一次总结吧。回过头来,从开始接触艺术,画画,创作装置,一路走到今天。这个展览可能包含了我这十几年的一些创作的过程,还有一些对于这个社会的体验和思考,等等。这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回顾吧。
唐:就是个人的艺术史的一个回顾。可以这么理解吗?
李:可以。
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绘画,接触美术,后面还读了成教班?
李:就是2005 年做完手术以后嘛。2006 年,过完年,我本来是打算学书法的,因为书法比较轻松,以后可能写写对联呀,去靠这个养家糊口,想得很简单的。
唐:当时还是很功利化的,就希望学个小技术,学个手艺。
李:2006年就去了海大的成教班,跟着同学画画,老师也不管,也不教,靠同学教我。2006年学了一整年,2007年结婚,就再没有去过学校。
唐:高中之前你是没有接触过艺术,也没有想过要学这个?
李:根本就没有想过,我连看都没看过。我那时候从农村过来的,根本就没见过那种绘画呀、石膏像呀,没见过!完全是一无所知的状态,包括我2006 年去学习,我都是很惊讶的。进去一看,唉,怎么能够用铅笔画出大卫这种这么立体的石膏像?这直接把我给震撼到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李博个展现场的自画像 小曹 摄
唐:刚才我们说到一点,你是2006 年接触到当代艺术嘛,当时你是从什么渠道接触到的?
李:对,2006年,当时就是通过同学了解到的。
唐:同学也是在讨论当代艺术和艺术家的作品。
李:那时候很火嘛!当代艺术。所以说经常听他们讲一些当代艺术的事情,包括看一些绘画。
唐:跟老师有关系吗?
李:跟老师一点关系都没有。
唐:纯粹就是这种信息在社会上传播以后,学生自己获得了这样的一种信息。
李:可以说是同学让我了解到了有当代艺术。然后,学习全是靠自己自学,自己创作。
唐:其实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还真的没有所谓当代艺术课程,可能你学得更多的是当代艺术史、美术史这样的东西,甚至没有固定的所谓课程。下面这个问题也许我不该问,但是我也想更敞开一点说,刚才说到你会在家里面有交代一些后事,我不知道你对我们有没有这种交代。我们认识有八九年了,是好朋友的关系了。你对我们这些朋友有没有一些想要说的?
李:2014 年,是我最焦虑的一年,也是我鼓起勇气走出来的一年。之前一直都是不跟任何人联系,不跟外界联系,然后我就走出来找到以前海大的一些同学,就知道了江萍,还有他们当时做的海口当代艺术馆(王小飞创办的)。我就去找江萍了,她就把你们介绍给我,我就在这个圈子里面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很多一直在帮助我的人,让我从焦虑里面慢慢走出来。一直到今天,即使很长时间不联系,你们这些老朋友、艺术圈朋友,一直都是很关心我的,一直在尽全力帮助我。真的,我是很感谢你们的,很多人。
唐:不用客气。那还有一个问题,你觉得做艺术创作的话,最要紧的是什么?一个人要做艺术创作的话,他应该持怎样的一个态度?
李:要真实地表达自己,要非常理性地去看待这个现实的社会。也许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我只能用自己那种可能跟别人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去尽量真实地表达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感触,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客观、理性。要一直保持这种初心,然后要坚持下去。这就是我做当代艺术的理念。
唐:今天我们刚好是用了一个小时,谈了一些话题,当然有可能我问的也不一定很全面啊,不过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访谈或者是一个记录。我觉得是挺重要的、挺珍贵的。
李:你们以后可能还会想起我这个朋友吧。
唐:那肯定的。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这种记忆,这种经历,这种生活,都会有。谢谢,那我希望尽快在一月十号左右,我们张罗起来,一起来把你这个展览做起来。
李:非常感谢你们!你们替我完成这次展览,完成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心愿。非常感谢!
唐:不客气,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们在海南真诚地做当代艺术的,是特别少的,而且很多人做着做着也没办法持续,但是你即使在很困难的时候,也还在持续地去思考和关注,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真诚地去做艺术的人,我认为做艺术很需要这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