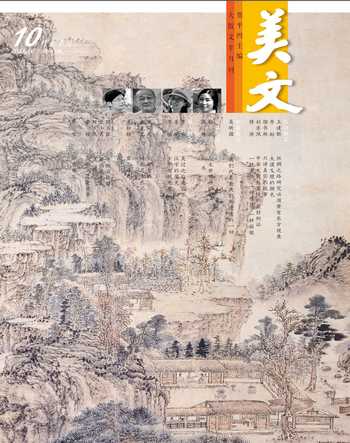美过之后是寂寥
2023-10-13管乐
管乐
每一个“此刻”,请款待自己
疫情期间,养成了拍摄落日的习惯。大概是办公室临海、朝西的缘故,每到夕阳之时,我都守在窗边,视野极其开阔——浑圆的红日渐渐没入海平面,或橙红或淡粉色的晚霞,把天空晕染得绚烂无比,有时还能见到海鸟的身影,那句流传千年的“落霞与孤鹜齐飞”大抵也是如此吧。
拍下美景的时刻,总觉得暮色四合,夕阳无限美好,然而待到某天重温那些曾经拍过的相片,一股“时间正在流逝”的伤感竟悄然涌上心头。我一度以为是自己过于“伤春悲秋”,没想,近来在刘思伽的最新散文集《若非此刻,更待何时》找到了共鸣。“时间在不断流逝,而你眼中稳定的世界其实每时每刻都不一样。正因为如此,快乐不会持久,悲伤也不会永恒。下一刻,一切都会改变。”如此不加掩饰的“真相”,读来真让人心下一凛。
《若非此刻,更待何时》乍看书名,以为是要传递“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忠告,但事实却是作者通过遛狗、写作、练瑜伽、赏日落等稀松日常,带我们不断反思:在人生这个“尘世游乐场”里,什么是幸福?你清楚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吗?你真的肯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吗?
“对自己诚实”,我以为,是贯穿这本书的核心理念。就像练瑜伽,要尊重自己的身体感受一样,“诚实是了解自己的唯一方法”。“不要轻易隔绝感受。当情绪袭来,不要忙着关闭闸门,而是要找一个安全的环境,沉浸在其中,试着体会它想要传达的信息。假若能够多倾听自己的身体,然后随时进行调整,让自己始终处于轻松又饱满的状态,生活就不再只是例行公事,而是真正欢欣地展开每一天了。”没有浓重的“鸡汤味”,带出的却是真挚、自省又积极的人生态度。
王鼎钧曾说“以有情之眼,看无情世界”,《若非此刻,更待何时》告诉我们,要细察和尊重源于内心的感受,以丰富细腻的精神,“看”到你所拥有的,随喜你所将有的,因为“真正的爱是对生命和世界的一种甜蜜感情,将这种感情注入自己的内心,你自然会带着爱意看待世间的所有,所有接触到你的人,必然会感知到这种发自内心的甜蜜和温暖。”
“每一个‘此刻,爱上世界,款待自己”,是刘思伽赠我的题签。在纷扰喧嚣的当下,这样的勉励尤为珍贵。不必强求自己成为什么或放弃什么,当明白了最重要的东西属于内在之后,自然不会想再去抓住那些于成长毫无意义的东西,学会享受一切,才能容纳更多的真正的喜悦。这便是我读完此书最深的体验,不啻为另一种治愈。
林风眠:美过之后是寂寥
疫情平息,出行全面放开,蓬勃的艺术活动再次回到日常。上周前往苏富比香港春拍现场,一来是感受疫后复甦的艺术品交易市场氛围,更多的则是可以近距离观赏大师作品,比如林风眠。尽管林风眠早已是各大拍场上的“常客”,然而每当驻足凝视、于我而言是他的“新”作品时,总有一个问题萦绕脑海:一位杰出的艺术家究竟特别在哪里,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
喜欢林风眠的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他的画很容易入眼:浓浓淡淡、几近铺天盖地的滩涂中,穿插着些许透亮的水塘,成排的芦苇,还有接踵而飞的鹜群;闪光的花瓶里盛开着怒放的菖兰;娴静淡雅的仕女,或坐或立,或梳妆或奏乐,静态中蕴含着动态美,恍若旧日相识在梦中相会,要想与她们促膝长谈一番。但是,在这祥和宁静、“绘画世界美”的背后,卻是画家颠沛流离、历经坎坷的悲苦人生。他的内心是有多强大?对艺术的坚持是有多执着?
一九○○年出生的林风眠,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令人啧舌的绘画天赋,未到二十岁赴法国以半工半读的形式留学,二十一岁就被推荐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柯罗蒙工作室学习(徐悲鸿此前也在这个工作室学习),毕业之后在欧洲游学期间受到蔡元培赏识,受邀回国。这位留法“海归”,二十六岁就当上了北平艺专(今中央美院)的校长,成为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年轻的高等艺术学府校长。如同那张著名的林风眠年轻时摄于法国的照片:眼神中流露出十足的自信,一派意气风发。
上任后,他开始施展自己的艺术抱负。改革中,他顶着艺专学院派的抗议——“齐白石这个木匠前门进来,我们就从后门出去”——摈弃画派之嫌,邀请“草根画师”齐白石“出山”任教。尽管就连齐白石本人都自嘲是“乡巴佬”出身,不肯到洋学堂教习,林风眠仍一次次登门邀请,最终感动了对方。二人惺惺相惜,成为忘年挚交。记得几年前在北京画院举办的“清寂鹜影——林风眠艺术精品展”上,见到一幅林风眠于一九三一年赠给齐白石的《鸡图》。绢底画布上,虽寥寥数笔勾勒、轮廓看似粗放,却是将三只白羽红冠的肥美公鸡奔走啄食的神态展现得淋漓尽致。画面左上方是林风眠的题赠:“齐白石先生正画,后学林风眠,西湖一九三一春”。才华、眼界、修养,在这位而立之年的画家身上展露无遗。
似乎年轻时太过顺遂得意的人生,到了后来大多都要遭遇波折与考验。就好比被誉为“雕塑天才”的意大利建筑家贝尔尼尼,中年时期因为判断失误,事业跌入谷底,饱受负评。回望林风眠的一生,多舛的个人命运始终被跌宕起伏的大历史裹挟。抗战爆发,时局动荡,在逃难的洪流中,他前半生所积累的大部分作品,毁于一旦。重庆嘉陵江畔,他过起隐居的生活,潜心作画七年。没有画布就将宣纸裁成方形,买不到油画颜料,就改用彩墨。也是在那里,他的画艺达到纯熟,中西合璧——不同于中国水墨画的留白,他的风景画几乎被色彩沾满;视觉上又不及西方油画的浓烈,依然散发着中国画的意境与深远。不过,于他看来,“绘画是很个人的东西,个人里面创造出来就是流派,我主张还是个人发展”,“绘画本质是绘画,无所谓派别,无所谓中西”。
一九七九年,林风眠重回巴黎母校,相片中的他,表情依然慈祥,还透露出一丝天真,如同与落霞齐飞的秋鹜,逆风疾行,留下的是孤寂与倔傲。
在岁月的跌宕和命途的多舛中,画家没有借笔控诉,没有表达愤怒或宽恕,而是将现实中的苦难化为了绘画里的诗意。或许,唯有对艺术的坚持,对真善美的执着,才能化解挣扎和悲哀,换来平和与温情。
一个人的旅行
即将开启一段长途旅行。三年的原地未动,不免让我对这趟一个人的旅行期待又忐忑。
说实话,在疫情之前,我常常选择独自旅行。面对周围人的疑问:一个人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我往往会借用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里的话:“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
所谓“希望”,因人而异。最普遍的,我想,大概是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地与自己相处。友人常说,人是群居动物,的确,在这个每时每刻都需要跟人发生联系的社会,我们要想在日常中独处并不容易,而一个人的旅行,似乎为“独处”提供了条件:原来我可以脱离日常。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人的旅行,是否真的可以脱离日常呢?旅程中,我们可以忍住不查看短信或电邮吗?若是突然到了一个没有网络支持的地方,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不安全感吗?从准备一个人旅行时的兴奋,到真正出发时的欣喜,再到旅途中的所见所闻,经历意料之外的惊喜,会否又生发出一种如果有他/她在身边一起欣赏就好了的感慨呢?
若此,我们是否还真的喜欢独处?
《伊豆的舞女》开头写道:“那年我二十岁,头戴高等学校的学生帽,身穿藏青色碎白花纹的上衣,围着裙子,肩上挂着书包。我独自旅行到伊豆来,已经是第四天了。在修缮寺温泉住了一夜,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然后穿着高齿的木屐登上了天城山。一路上我虽然出神地远眺着重叠群山,原始森林和深邃幽谷的秋色,胸中却紧张地悸动着,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
为什么他要选择一个人旅行呢?“我已经二十岁了,再三严格自省,自己的性格被孤儿的气质给扭曲。我忍受不了那种令人窒息的忧郁,才到伊豆旅行。”带着要摆脱“令人窒息的忧郁”的希望,他开始了这趟旅行,而无论最终希望是否实现,起码他有了在路上的理由。
一个人的旅行,快乐吗?不尽然。有时答案甚至是相反的:是为了在极痛中寻找疗愈与希望,一如《伊豆的舞女》里的主角。
漫游古都的“对话”
前几天做了一个很奇妙的梦:萧瑟冬日里,京都的鸭川边,川端康成在一排枯枝樱花树下,与我讲“物哀之美”。或许正应了那句“梦是现实的反映”,尽管从京都回来已有三个多月,但我一直对这趟旅行念念不忘,尤其是疫情之后的重新启程,行走在这座于我并不算很陌生的城市,川端康成以及他的《古都》总会时不时地穿越时空,与身为“旅人”的我产生“对话”。
《古都》的故事情节一如作家的其他作品,没有激烈的人物冲突,讲述一对自小失散的孪生姐妹千重子和苗子的命运遭遇——千重子被绸缎批发店老板夫妇收养,苗子则生长在一个农户家庭,原本无交集的姐妹二人在街头偶然相遇相认,千重子劝苗子过来和她一起住,但苗子自知两人的生活已是两个世界,便婉言拒绝,最后苗子在千重子家住了一晚便悄悄离开了。故事也到此戛然而止。
在描写这一对孪生姐妹际遇的同时,川端康成加入了大段大段对日本传统节庆、城市自然风光的描述。如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没有很华丽的词藻,都是看似轻描淡写的细腻景色描写,就好像在看Discovery频道,从春天绽放的紫花地丁的小花到冬天飘落的雪花,京都的风景和节气习俗被一一涵盖。
比如,千重子到平安神宫赏樱花,“如今的确称得上除了这儿的花朵,再没有什么可以代表京都之春的了”,再循着南禅寺的方向,“穿越知恩院后面,通过圆山公园,踏着幽雅的小路”,前往清水寺观落日,“城里华灯初上,而天边还残留着一抹淡淡的霞光”。小说还带读者经历葵祭、祇园祭和时代祭这京都三大祭。难怪有人会把《古都》当作介绍地方风物的旅游小说,认为京都才是真正的主角。据说,川端康成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对风光美景、京都民俗的描写,勾起人们对古都过往的怀念,呼吁日本在战后大力发展工业、经济腾飞时仍要注意保护民族传统。
小说在一个下着霏霏小雪的寒冷早晨结束:“千重子抓住红格子门,目送苗子远去。苗子始终没有回头。在千重子的前发上飘落了少许细雪,很快就消融了。整个市街也还在沉睡着。”相比春、夏、秋,京都的冬天基本没有大型的户外活动,记得在与当地人聊天时,他们会不无惋惜地告诉我:“你应该选择其他季节来,那时都是多彩缤纷的。我们冬天都是窝在温暖的家里。”的确,唯有身处其中,才能清晰地感受到四时的交替、日常的更迭。
回港的前一天,顶着凛冽的寒风,我走在冷冷清清的鸭川边,没有一个人旅行的孤寂感和冬日里的季节性忧郁,相反,这种自由的独行漫游,倒可以让自然和风物直接进入内心,也突然间明白了川端康成当年在诺贝尔获奖词里所说的:“美的感动,强烈地诱发出对人的怀念之情。”
谈食知味
吃,很简单,也很复杂。一日三餐,寻常不过;而一饮一食间,人情世故、世间百态又皆在其中。手头这部《香港谈食录》,关乎食物,关乎味觉,还有饮食文化背后的历史掌故以及折射出的风土人情,颇值得一读再读。
香港被誉为美食之都,饮食类书籍更是比比皆是,踏入书店,摆在显眼处的也总以此为主。然而,底蕴深厚的,往往凤毛麟角。我以为,《香港谈食录》当列其中。
正如该书作者徐成在序言中所写的,“这是一本关于香港餐厅和美食的散文集,我无意将其写成觅食指南。这些文字是用餐体验带来的思考,也探讨了餐厅对本地文化和历史的影响,更讲述了餐厅背后的人和故事”,《香港谈食录》始于“吃”却又不止于“吃”——在探索美食、满怀逸趣的同时,也有对逝水流年的追忆,那些带着记忆的吃食和乡愁的味道,最是引人动心。徐成是浙江人,定居香港之后,为解鄉愁,自然会寻觅浙菜餐馆。杭州酒家曾是他一度“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去处。即便一人独自点份莼菜鱼圆汤、一道酱烧茄子、四个小笼包、一碗葱油面,再加上桂花酒酿圆子,也有种“暂时回到家的错觉”。至于宁波菜餐厅甬府的大肉包,则尤得他钟爱,“老面配上多汁足料的肉馅,蒸好后鼓鼓囊囊,透着淡淡肉汁色泽……一咬下去面皮蓬松,馅料多汁,唤起了关于家乡早餐店大肉包的遥远记忆。”的确,真正会吃的人,吃的何止是味道?往往还有这道食物传递出的情愫以及人间百态的美妙。
徐成写食物,感情上十分坦率,“坚持自费品尝和不写鳝稿是我的基本原则,不然写出些虚情假意的文章,自己不爱,怎么相爱?”比如,对于坐拥中环海景、曾长时间蝉联米芝莲三星的中餐厅龙景轩,“定价自然不便宜,但有些食材高出市场平均水平太多,而出品却未必有那些传统高级食肆来得到位”。对不喜欢的食物,他毫不客气,不好吃就是不好吃,名气再大也徒然。
事实上,早在去年六月,我便已收到刚刚出版的《香港谈食录》。于我而言,这是一部值得反复拾起、可堪细味的美食散文集。从作者的这些饮食探索和书写中,我们得以窥见社会发展史的一个面向:天南海北的人们移居此地,带来风格迥异的饮食习惯,各地菜系也随之生根发芽。在书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纷繁多样的中餐格局,也跟着作者的妙笔体验到色香味俱全的生活百味。同为在外打拼的游子,这一道道或庄重或休闲的食物,也使得凝结在我心里的缕缕乡愁有了具体去处。
近乡情怯之后
惠风和畅,终于要回到因为疫情阻隔而阔别三年半之久的故乡。启程前,竟有些“近乡情怯”的忐忑。友人借用《围城》里方鸿渐回江苏老家时的内心独白安慰我:“这两天近乡情怯,心事重重。他觉得回家并不像理想那样的简单。远别虽非等于暂死,至少变得陌生。回家只像半生的东西回锅,要煮一会才会熟。”
的确,近乡情怯乃人之常情,这样的情绪之所以会产生,多半源于对物是人非、情谊生疏的担忧。就好像面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贺知章,在《回乡偶书·其二》再次感慨:“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然而,当我真正踏上故土时,先前的顾虑全都抛诸脑后,没有了伤感与悲凉,取而代之的是内心的充盈和喜悦。漫步在护城河水岸,清风徐来,波光潋滟,碧树葱茏,目之所及,还有那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塔,穿过岁月的风雨,几经修复,保留至今。驻足在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九一四年的钟楼前,想到的是儿时每天准点听到的那浑厚悠远的钟声,成了彼时日常起居的报时器。沿着钟楼墻根向西转,就进了如同迷宫般的巷道,同时也把市中心车水马龙的繁华喧闹隔绝在了外头。粉墻黛瓦早已斑驳,蜘蛛网般的电线管道杂乱横陈,岁月的颓垣在这里暴露无遗,如同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只不过这样的落寞与苍凉,很快被不知从哪里蹿出来打闹的孩童打破了,满富活力的笑声回荡在阡陌纵横的小巷里。
若是走累了,打开美食点评app,去试试排在推荐榜首的附近一间咖啡馆。经过老民房改造过的小馆,焕发出别具一格的生命力,清新质朴,又不失文艺的气场,天井没有刻意雕琢,基本还保留着老院子的形态,白墻灰瓦,还有冲天生长的绿植,在这里点一杯咖啡,伴随着轻淡的背景乐,即便只坐上个把钟头,心里也已有“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知足。
不可否认,时光总会带走旧时记忆里的印痕,也会改变昔日的风物人事,然而总有些情愫是永恒的,岁月的流转并不会褪去它的底色,相反,在荏苒中历久弥新。可幸,故乡的风雅秀丽,以及水、桥、钟楼、古塔等等共同构建的那份深邃还在。
离乡情更怯
“细雨春灯夜欲分,白头闲坐话艰辛。出门便是天涯路,明日思亲梦里人。”清代汪中这首《别母》可谓道尽了一个即将远行的游子对于母亲的依恋与牵挂。这种不舍、复杂、难以平静的离愁别绪,自然地,在我这趟返乡休假结束时也真真切切地涌上心头,反反复复,愈结愈浓,化不开。特别是与亲人道别之时,纵有千言万语,往往也只能是无语凝噎,仿佛所有的话语在当下都是苍白无力的。儿行千里母担忧,自踏上远程的那刻开始,漂泊在外的游子也就多了一份沉重的乡愁。
“披星戴月地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很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小小的门口/还有她的温柔/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曾有一度,歌手李健的《异乡人》旋律一起就让我忍不住潸然。干净清澈的声线,看似随意的清唱,却将异乡人的无奈与感伤娓娓道来,每每听到,总有种直击心灵的震撼。
不可否认,科技的进步令物理距离不再是游子们排解思乡的最大障碍,实时的视讯相见,“咫尺天涯”可以秒变“天涯咫尺”。然而,长年只身在外,再坚强的心灵也容易受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侵蚀,那种不知要走向何处的惧怕,常常在夜阑人静时变得尤为强烈。难道,这就是离乡的代价吗?
然而,当面对诸如“有回去的打算吗”这类问题,我又会倔强地回以“我在他鄉挺好的”。人生没有如果,踏出去的每一步,既是自己的选择,也是一段未知的流年。该继续在此地坚持下去,还是心下决定回乡发展,我们无法预判哪一个是最好的方向,也不可能准备万全的计划来应对。既然做出了选择,就照此勇敢地心无旁骛地走下去,因为这趟踽踽独行的旅程,其中的悲与喜、平淡与激荡,唯有自己才能真实体会。
宁取格格不入
时光荏苒,今年已是在香港生活的第十五年,人生的将近一半时间给了这座城市。只不过,很惭愧地说,我依然未觉自己真正地融入到其中。每当想仔细打量这座城市,占据视野的总是汹涌的车流和人潮,这种过于喧嚣的感觉,很难让人的心灵深入地贴近她、真切地感受她的温度。我,始终是一个异乡人。
或许源于相似的背景,香港话剧团几年前有一出名为《骄傲》的舞台剧,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男主角是一名从深圳移居到香港的“新香港人”,无论是粤语发音,还是着装举止,甚至能熟练唱出《狮子山下》,种种外在表象几乎无异于土生土长的港人,然而他内心想与香港建立落地生根情感联系的渴求,往往因为用力过猛,令自己常常处于过度的敏感与不安中。比如,面对阿伯污蔑自己假结婚骗身份的过激反应,对入境处遗失申请材料的动机怀疑等等。
剧目取名“骄傲”,表面上说的是男主角骄傲自大,不愿妥协,事实上则通过大段的剖白呈现一个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物形象。演出中还特地安排“登月航天员”不时穿插于写实场景中,也正是男主角“飘无定所、无法着地”的内心映照。
于我而言,最受触动的则来自于剧中异乡人的纠结与苦恼——拼力融入圈子,却难被理解,从始至终都是自我的撕扯与缠斗。对漂泊的人来说,可能要穷尽一生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也因此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努力寻找“家园”,然而时时困扰的身份认同,又在提醒着“不知乡关何处是”。
如今,回看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回忆录《格格不入》(Out of Place,又译:乡关何处),疏离、难以被接纳、身份认同的困惑,是作者在喋喋不休一再述及的话题。生于耶路撒冷,在开罗度过童年,接受的却是西方教育;身為巴勒斯坦人,持有美国护照;母语是阿拉伯语,但一口流利的英语让人怎么都觉得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就连萨义德这个名字,也是在阿拉伯的姓氏前加上一个美国名。如此矛盾的存在,身份的割裂,令他走到哪里都不被认同,显得格格不入。
可是,这些“冲突”又如何呢?他在回忆录结尾淡淡地写道:“我生命里有这么多不和谐音,我已经学会不必处处人地皆宜,宁取格格不入。”
书海编舟
友人推荐了一套名为《但是还有书籍》的纪录片,刚看第一集便被吸引住了。这集聚焦几位常年坐冷板凳的编辑译者,于细微琐碎中找寻生活的意义。取名《书海编舟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数年前的一部日本电影《编舟记》。这部根据三浦紫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讲的也是一班出版社编辑的故事。
或许是同为编辑的缘故,我时不时地会重温《编舟记》,每每依然能从中感受到热血。电影没有我们惯性思维里的冲突与跌宕,故事在缓慢的节奏中铺陈开来,主角马缔光也,标准的宅男,不善于和人交往,却对文字有极高的敏锐度,做事也极为认真投入,他被即将退休的前辈相中,加入辞书编辑部。自此,马缔光和同事们十五年如一日,埋首故纸堆,一个词一个词,整理出一本厚厚的辞海。电影高度还原了小说里描绘的编辑工作,比如如何取舍词汇,作者根据什么标准撰稿,编辑如何选定词条。
大概编辑都是有完美主义倾向的。而马缔光也对完美的追求,在选纸这个细节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造纸厂为辞海研发了专用纸,轻巧、薄纸、不会透墨,而且色泽雅致考究,然而他却认为“触感不对,应该是那种手抚在纸上有粘连感,一页一页想要翻下去的感觉”。
房东竹婆在马缔光初入辞书编辑部时对他说:“你这么年轻,就找到了这辈子想干的工作,真是太幸福了。之后只要一路走到底就行了。”十五年时间,他从不善辞令的“怪咖”,成长为一名团队领袖,带领大家完成辞海的编纂工作。在出版的祝捷酒会上,当其他人都松一口气的时候,马缔光和前辈不约而同地拿出各自采集的例句卡,于他们而言,“辞典的编纂工作没有尽头。承载着希望,航行在词汇海洋上的小舟,航程永无止境。”
无论是《编舟记》里的辞海,还是《书海编舟记》展示的厚厚书本,凝聚的皆是我们常常谈起的匠人之心——长期专注地做着看上去艰苦枯燥的事情,背后却蕴藏着“无法与外人道也”的喜悦与满足。
别忘记为什么出发
前些天见到来港出差的大学同学,谈起当年同读新闻专业的三四十人班级,如今只有包括我与她在内的屈指可数的几个仍待在传媒圈。顿时,一股五味杂陈的情绪涌上心头:坦白说,毕业十多年,谁在其中没有动摇过?尤其是不时听到传媒翘楚猝逝的消息,内心更是掀起不小的波澜。
比如,四年前在办公室突发心梗的新华社知名记者、国际部专稿中心主任徐勇,去世时五十六岁,尚处于事业的“黄金期”。犹记得,当时消息一出,不少人为之痛心和惋惜。怀念文章中提及的徐勇对年轻人的耳提面命,比如,写稿子少用形容词,少用“的地得”,不要用“被”字;要用短句,能短则短,多用直接引语,其实在我唸书时,就已经间接地透过国际新闻翻译老师、徐勇的新华社前同事周轶君有所熟知。虽然并未直接受教于徐勇,但他对新闻的严谨认真,甚至是近乎苛刻的规矩,都深深地影响到了身处千里之外的我,并一直将之奉为圭臬。
再比如,另一位英年早逝的媒体人、被誉为“中国电视纪录片里程碑性的人物之一”的央视评论部前副主任陈虻。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那句“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经陈虻演绎成“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早已成了业界名言。
陈虻常说:“我不是在改片子,是在改人。”审片时,他往往重视如何与编导实现有效的沟通,因为他更在意的是对方的思维方法,包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以及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他爱用这样一个比喻:“我希望我的说法不是铁锹,是馒头。给你一把铁锹你就只能挖坑。我给的应该是馒头,你吃下去浑身是劲,愿意干啥就干啥。”这是陈虻二十多年前的话语,不但没有过时,相反经历了岁月的推敲更显其价值。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陈虻、徐勇等佼佼者的离去,对传媒界而言,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损失。也正因此,他们的逝世,总能在现实或者网络上掀起讨论潮,无论是媒体公号,还是媒体个人,都会自发地写文缅怀。而在这些汹涌悼念的背后,更加汹涌的,其实是“对自己的反思”。
于我而言,十五年的传媒生涯,与陈虻、徐勇们相比,或许不足挂齿。然而,他们却如我踽踽前行路上的启明星,告诉我:纵使前路迷茫,依旧要保持激情,因为正如陈虻所言“现在,就是小时候想过无数次要为之奋斗的未来”。
既然想起了当初为什么出发,就别忘记继续前行。
(责任编辑:庞洁)
管 乐 笔名:陆小淑。江苏人,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现为中国香港《大公报》副刊部主任。曾获“2018香港报业公会最佳新闻奖”最佳文化艺术报道奖。文章发表于海内外报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