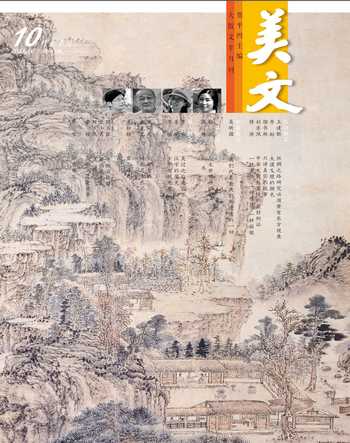人生世相争供眼
2023-10-13韩羽
华君武有一漫画《老死小有往来》:两座楼房的阳台紧紧相对,阳台上各挂一鸟笼,笼中鸟“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可笼中鸟的两位主人,彼此侧目,作“老死不相往来”之状。
我边看边笑。
按说鸟儿吱喳乱叫,同声相应,司空见惯。没见有谁大惊小怪,更谈不上“笑”了;街坊顶嘴,邻居吵架,“老死不相往来”,也司空见惯,没见有谁大惊小怪,更谈不上“笑”了。可是一到华君武的画里,你能不笑?
思摸来思摸去。想起了一句成语:互文见义。意即把两种不同的概念合并在一起,可以生发出新的概念。以绘画颜料为喻。红色颜料的色相是“红”,蓝色颜料的色相是“蓝”。如把红色颜料与蓝色颜料糅合到一起,其色相既不是“红”,也不是“蓝”,而是“紫”了。这“糅合”,用在艺术创作上就是“想象”了。也就是朱光潜说的“平常的材料之不平常的新综合”。
两只吱喳乱叫以示亲切的笼中鸟,不是“平常的材料”么,一对“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不是“平常的材料”么,谁曾为之动心而正眼相看过,当华君武把这两个“平常的材料”凑集一起,做了个“不平常的新综合”。不由你不正眼相看了,而且很快地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得出结论:“哇哈,不会说话的鸟,还吱喳乱叫以示亲切哩,可会说话的人,反而横眉冷对,无话可说。”你能不为之慨然而苦笑。
漫画所画,皆俗人俗事,所以通俗。然而“俗”未必不“雅”,甚或大俗也可大雅,也可出经入史。试把这幅漫画放在《孟子·离娄章》里,与“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摆在一起,能不谓为是一幅绝妙的讽喻插图。
《羊毛出在羊身上》(见《华君武集》):新婚洞房合卺之夜的婚床,简直成了阳羡鹅笼。“阳羡鹅笼,幻中生幻”,鹅笼之幻,是笼中书生口里吐出一个女子,而这婚床之幻,是新郎新娘变而为羊,尤奇于鹅笼。
画中的羊说话了:“亲爱的,你的毛呢?”一羊答:“电气化了。”果然,婚床的四周,电灯、电炉、电视机、电冰箱,“四大件”无一不备,全有了。一提起“四大件”,人们全明白了,是男婚女嫁哩。试想,哪家哪户没有过儿子娶妻、女儿出嫁,哪家哪户又少过“四大件”,为了大讲排场,弄得个倾其所有。
反映这一题材的漫画,数十年来屡见不鲜,唯独此幅,最为入木三分。它以新颖的比喻——从羊身上的羊毛作文章,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婚嫁陋俗之害。
这个比喻之所以新颖,且看钱钟书关于比喻的一段话:“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
新郎与羊,一为衣冠尊严的“人”,一为腥臊的“畜”,可谓“两者全不合”。为了“四大件”电器,把浑身的毛都剪掉卖了的“羊”,和为了排场铺张而砸锅卖铁的“人”,不都是同样的倾其所有?又可谓“两者全不分”了。凡喻必以非类,凡比必于其伦,正是“两者全不合”而又“两者全不分”,才“合得愈出人意表”,从而更加强了对婚嫁陋俗的嘲讽冲击力。
华君武为池北偶《多刺的玫瑰》作插图,图中一男士叼着香烟,悠闲地躺着在泡澡,可又不是躺在澡堂子的池子里,而是躺在茶杯里。
每见此画,注目有顷,似乎闻到了茶的香气。
别人如何,不得而知。以我的生活体会,茶欲喝得痛快,莫过于在澡堂子里泡澡之后了。热气蒸腾、汗流浃背,端起茶杯,牛饮鲸吸,馥郁茶香,遍布周身。
画中男士,异想天开,不只泡澡,更妙在茶杯里泡澡,真真个善解人意也。逗得我“对屠门两大嚼”,隐隐然得一丝茶香,这大概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通感”了。
华君武有一漫画,无标题。且妄拟一题:“摆积木。”这画儿把中国的或诗或文给形象化得惟妙惟肖。
或诗或文,无非男女衣食,善恶美丑,有如积木。任人摆来摆去,所以作者在画上写了两句:“笔笔有来路,句句有出处。”从古代擺到如今,虽万变不离其宗,或曰不离其宗而万变,却也大有说道,摆得巧者,绝俊之笔,运以绝圆之机,谓之“化”。等而下者,八哥学舌,水獭祭鱼,谓之“抄”。
所以张岱说话了:“盖诗文只此数字,出高人之手,遂现空灵,一落凡夫俗子,便成腐臭。”
《华君武集》里有一“生活拾趣”的漫画,画中的男子举起儿子:“乖儿子,叫我一声。”于是儿子应声而叫:“发发。”“发发”者,爸爸也。又“发财而又发财”也。一语双关,尚在牙牙学语,就如是之聪慧,有儿如此,能不乐乎。
无独有偶,还有另一个爸爸与儿子的相类故事。那位男子也同样地举着儿子:“叫爸爸,叫爸爸。”日复一日,儿子终于学会了,一见他就:“叫爸爸,叫爸爸。”人们哄堂大笑。有一朋友给他出主意:“你以后见了儿子,就冲他‘爸爸,爸爸。”
和小友共赏《鞠躬尽瘁》。
小友:“哇哈,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跳猴皮筋儿,真开心,小女孩都乐疯了。”
“小女孩开心,所以爸爸妈妈也开心。”
“难道爸爸妈妈不喜欢跳猴皮筋儿?”
“起码,不会像小女孩那么喜欢。”
“你怎地知道?”
“是画里的爸爸妈妈告诉我的。”
“你瞎说,画里的爸爸妈妈不会说话。”
“还告诉我,他们更喜欢打羽毛球。因了孩子喜欢跳猴皮筋儿,只好不去打羽毛球,一起陪孩子跳猴皮筋儿了。”
“你更瞎说了,画里的人没说过这话。”
“他们没说,是他们手里的球拍子替他们说的。”
画中一老者,指着玻璃柜台里的商品作询问状,被问者是柜台旁边的展示时装的蜡人模型。粗心欤?眼花欤?老者成了笑料。
我的确笑了,不是笑老者,是笑我自己,我又瞅了瞅画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八八年六月。
为何笑自己,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隆福寺百货公司的五层楼上(专售卖高档衣服的那层),远远瞅见玻璃柜台旁坐着一洋女人,不由惊叹:“哇哈,简直可以乱真了!”急步凑了过去,打算仔细瞅瞅,刚欲细审,那眼珠忽地一眨,吓我一跳,忽而憬悟,洋女人竟是活的。真真个刘姥姥进入怡红院也。
畫上的老人把假的当成了真的,我则把真的当成了假的,又真真个“假作真时真亦假”也。
华君武的一幅漫画,在我这儿成了两幅漫画。
这是一幅批评铺张浪费的漫画。一桌食用过后的盘子摞盘子、碟子摞碟子、盆碗摞盆碗的丰盛筵席,与之相对的是两只愁眉苦脸的猪。按说桌上的剩肉剩菜作为“泔水”,对猪来说,犹如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求之不得,可两猪为何反而若此?欲知端的,且看标题:肥猪也怕泔水“肥”。点出了一个“怕”字。
为何怕?请听另一个猪的故事。
养猪的主人和邻居在猪圈旁闲说话。
邻居说:“你这猪,挺长膘儿,快有二百斤了。”
猪的主人说:“到了年底,若能长到二百五十斤,就宰了它。”
这话被猪圈里的猪听见了,从那以后,那猪光喝水,不吃食。
漫画《食不下咽》,画中有两人是坐而用餐者,其背后四人是立而候餐者。一看便知是某一阶段的时代景观。是以画笔记录的世相百态的一态。
一天,去华老家串门,到了饭时,华老说:“离家不远有家烤肉店,吃烤肉去。”还有华端端、张子康,一起去了。是意料中事。熙熙攘攘,座无虚席。躬逢其盛,成了如画幅中的立而候餐者,此画谓为“夫子自道”亦无不可。
曾是画中人,看画吓一跳,从来不去想,一想方知道:一个饭店里的小小的座位,竟然能把仪表堂堂的“人”折腾得个六神无主,能不谓之大奇?我仍依稀记得立而候餐时的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是什么滋味。我瞅到对面的几位立而候餐者,其眼神是:看桌上的饭菜不是,看天花板不是,看地板不是,看人不是,不看人不是,看远不是,看近也不是,不知看什么地方才好。他们简直像镜子一样照出了我:是不好意思,是自感多余,本来比那些坐着吃饭的高出两头,然而却觉着比他们矮了半截。
且再换位思考一下,想想那些坐而用餐者,未必就比立而候餐者更少些尴尬。试想,正在吃饭,一个黑影儿紧贴身后,呼哧呼哧冲着后脖颈直喘气,能无动于衷,无扰于我?能有食欲?更有甚者,无名火起,既难以下咽,干脆不咽了。且抽支烟,耗上了。你敢撵我站起来么。哇哈,想着想着,走火入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当然,大多数是:快吃快吃,快给人家腾座位。
就画说话,本想试为一笑,却又欲笑还休。
画的标题是“又骂又买”,画中一穿西装戴眼镜的人提着一条鱼给人看,说:“这物价涨得真邪乎,你瞧……”瞧到的是“……”。这表明他刚要骂了,又把“骂”咽回到了肚里。试想,如若真地骂了出来,岂不污人耳目。实者,以虚出之,借标题点到为止。
“又骂又买”,源远流长。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侯宝林就曾说过一段相声。过年的集市上,老太太拿着一张“灶王爷”,一青年人问:“多少钱买的?”老太太说:“不能说‘买的,要说‘请的。”青年问:“多少钱‘请的?”老太太:“就这么个玩意儿,两毛!”
这又使我想起了家乡的集市,集市就在我家北屋窗外的街上,人声鼎沸,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多少钱?”
“六块钱。”
“三块,行不行?”
“少五块不卖。”
间或也有不傍人口吻别具一格者。
“这袜子怎值十块线,八块行不?”叽叽咕咕,终于成交,钱货两讫。可是话还没完,再往下听。
“八块钱就买这双袜子,说实话,你就是言不二价,硬要十块钱,我也买。”
“我也说实话,只要你抬腿一转身,六块钱我也照样卖给你。”
既争金钱胜,又争口舌胜。
华君武在1961年画过一幅《杜甫检讨》,我当时在报上曾看到过,深深有感于大师的画笔涉及领域之广。
画《杜甫检讨》,是因了北京某大学忽然发起批判杜甫长诗《兵车行》。
华君武在《关于〈杜甫检讨〉》一文中说:“在当时,人的思想也很复杂的。像我有盲从的一面,但也有怀疑的一面。比如对待法国的两位大画家毕如索和马蒂斯就不同。有一时期甚至要批判马老。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不能称马蒂斯是法国的齐白石呢?也可以说齐白石是中国的马蒂斯。北京某大学忽然发起批判杜老的长诗《兵车行》,据说是分不清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犯了和平主义思想的错误。怎么办呢,当时的批判是不容争辩的,只有检讨。因此杜甫必然检讨,画了《杜甫检讨》,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心境。画儿在《光明日报》发表后,有同志皱眉,有人悄悄对我说,你画这干啥?”“是多年之后的某日,我碰到总理办公室负责处室的孔原同志,他告诉我《杜甫检讨》在报上发表,周总理看后哈哈大笑。”
《华君武漫画》一书的序,也是漫画。是作者自己画的一幅漫画。正应了那一句老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己拉弦自己唱,乐在其中,趣在其中。
画上有一锅粥(喻漫画作品),众多和尚围锅而立,等待喝粥(喻漫画读者),一干部模样的人(喻漫画作者),拧开水笼头正往粥里掺水。作者借成语“僧多粥少”在作自我批评。
后来作者曾写文章提到过这幅漫画:“1980年为了给自己造成一种压力,凡报刊来索稿者大多不拒,现在来看有的作品就显得粗糙。今后当力戒之,这也算自序罢。”
《华君武集》中五本漫画的封面,也是作者自画的漫画像,两手捂脸,作“不好意思”之状,谦逊之态可掬,就这一捂,人品画品。尽在其中矣。
自画序,自画像,是兴之所至信手拈来的些微小事,别看事小,却小中见大,因为在这类小事的背后,往往是由随缘而化、触景生情,不拘成法、不落方隅的大智慧给垫着底儿的。
一看标题“林和靖寻子”,扑哧一笑。张三寻子,不好笑。李四寻子,不好笑。任谁寻子,都不好笑。独独林和靖寻子,才好笑。笑他千不该万不该说了“梅妻鹤子”那句话,既说了那话,就是监护人了,所以漫画家就找上他了。责有攸归,他不寻,谁寻?
接下来的对话,却笑不起来了。
林和靖问:“请问,见到我儿了么?”
酒家坦然而答:“十分抱歉,昨夜已吃了。”
你听,“昨夜已吃了”这不成了“焚琴煮鹤”的现代版了。面对此情此状,可又奈何,叹则气短。“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只有苦笑。
能够把人逗得“苦笑”,表明了典故用得恰到好处。
华君武曾说:“我在漫画上寻求‘民族化,并不想有国画的形式,并不想漫画被国画化了过去,那就成了老话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了。”以此画为例来看,华君武所寻求的漫画“民族化”,并不仅仅是国画用笔的“书法入画”。中国画既然“画中有诗”,漫画又何尝不可画中有“文”,从而把幽默更提高一个档次:有巴人之趣又兼以阳春之雅。
华君武为方成画的漫画像,堪称惟妙惟肖。说其惟肖,如对镜取影,一看便知;说其惟妙,不见五官,只是一个苹果,一个盘子。能不令人一惊一乍。我曾对一从事中国画理论研究的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中国画讲究的是‘得鱼忘筌,是‘舍形取神。现有華君武画的方成漫画,就是个好标样。你试为之理论理论如何。”彼笑而不答,实是难以言答。真真个“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也。
解铃还须系铃人,听听作者的言说:“我想讲一个形和神的问题,它是一个内涵的问题,被画的人的个性特点的问题。你对要画的人熟悉了以后,你画出来不但形上像而且更多的内在东西也能表现出来。我举个例子,有个很有学问的作家叫黄裳,他面如重枣,颜色颇似关公,他的戏剧论文集要出版,嘱我为他画书的封面,我就画一个关公夜读。脸,当然还是黄裳的脸。”“还有方成那张画,你要真让我画方成我也未必能画出来。那天正好有个苹果放在一只瓷盘子上。我稍加夸张画出来颇似方成,我问我老伴像不像,她说不像,我就不服气,我画下来寄给方成,他看了回信说觉得非常神似。”(《华君武集》)
华君武提到两幅漫画像的形和神时,说黄裳“面如重枣”(关公也面如重枣)“颜色似关公”,黄裳写了一本《戏剧论文集》,关公也恰是家喻户晓的戏曲剧目中的重量级角色。这就是说,他从两者的“不同”里看出了“同”,将其糅合一起。“就画了一个关公夜读。”典出关云长夜读《春秋》。“脸,当然还是黄裳的脸。”关公欤?黄裳欤?你中有我也,我中有了你。“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了。
可是苹果与盘子和方成“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共同之处,却又像极了方成,这又怎么说。作者说:“此为无意中得之。”似是出之偶然。可是偶然的背后常常隐藏着必然,这个“必然”又是怎样个所以然?我们的古人干脆,只四个字:神来之笔。
(责任编辑:马倩)
韩 羽 1931年生,山东聊城人。原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现为河北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版有《韩羽画集》《韩羽文集》。漫画、国画、书法、插图分别编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获中国漫画金猴奖成就奖、首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