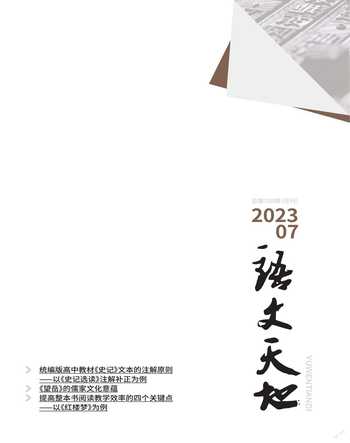统编版高中教材《史记》文本的注释原则
2023-10-12张干许云劼
张干 许云劼

一、《史记选读》注解补正对统编本相关篇目的意义
苏教版《史记选读》作为“一纲多本”时期的经典教材,在篇目选择与字词注解方面均具有典型性,表现出与统编版教材相统合的共性特征。
在篇目选择方面,其所择取篇目均为《史记》的典范之作,其中部分记叙名篇仍作为西汉文学的代表作品而被收录于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而部分篇目所选内容虽不相同,但仍可与统编版教材选文形成呼应关系。在字词注解方面,与《史记选读》本《屈原列传》相比,统编本《屈原列传》在注释形式上表现出进步性,以尊重《史记》原貌为基准进行了更多细部处理,不仅对删减部分用省略号进行标示,亦将衍文在文本中还原并以注解进行注明。由于篇目选择与字词注释的近似性,苏教版《史记选读》注解疏失体现出与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相类似的共性问题,对其进行补正能够为统编版相关篇目的完善提供相应借鉴。
二、《史记选读》注解补正六例
(一)避仇从之客
《高祖本纪》记吕后之父吕公迁家至沛地之事为:“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注释解“避仇从之客”为“吕公因躲避仇人到沛县县令家里作客”(丁帆、杨九俊主编,《〈史记〉选读》,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4275页)。将“从”解作介词“到”,把“客”释为动词“作客”,两处注解失确。
句中“客”当为“客居、旅居”之义。《说文解字·宀》:“客,寄也。”段玉裁注:“自此托彼曰客。”王筠句读:“偶寄于是,非久居也。”(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中华书局2014年,第7474页)可见,“客”字本义为离开故里,到别处短暂地居住。《史记》中亦见“客”为“客居”之用例,如《扁鹊仓公列传》记:“风癉客脬”,张守节正义曰:“言风癉之病客居在膀胱”(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801页),即将“客”释作“客居”。从该句之出现语境来看,吕公最开始是在单父(今山东单县)居住,后因为在当地招惹仇家而外出躲避。吕公因与沛县县令交好,便跟随沛令到能够为其提供庇护沛县客居,一段时间之后,便把家从单父迁往沛县,由客居变为常居。所以,“避仇从之客”句义应为:吕公因躲避仇人跟从沛县县令客居。“从”的词性是动词,为“跟从”之义。
(二)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
《李将军列传》录司马迁评价李广之语曰:“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在句读文句方面,选读课本延续了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的点校方式,将“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之句标点为疑问语气。为了使文义符合此语气,故注解此句云:“他那忠实的品格确实得到了士大夫的信任吗?”(丁帆、杨九俊主编,《〈史记〉选读》,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57页)此句句读与释义均存在疏失。
除《史记·李将军列传》外,在纪传体史书中,李广生平事迹亦见于《汉书·李广苏建传》。此传中对李广的评述部分主要承继自《史记》,其评价李将军之句曰:“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流涕,彼其中心诚信于士大夫也。”(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469页)在《汉书》中,“彼其中心诚信于士大夫也”之句被句读为句号,表陈述语气。从文本语境来看,李广为汉朝名将,与匈奴交战七十余次,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其虽有赫赫战功,但却终生未能封侯。李广在其最后一次对匈作战中因迷道失期而被大将军卫青问罪。当李广被质询之时,一言不发,后卫青下令追责其帐下幕僚,李广为护部下,慨然自刭赴死。司马迁在史传结尾部分表现出对李广悲剧人生的哀悼与痛惜,其言称,李广自身不善言辞,在临终之时并未替自己辩白,但在其去世之时,天下人皆自发为之哀悼。所以,李广内心的忠诚虽并没有用言语表述,但早已表现在一生的行动之中。《汉书》中点此句为陈述语气的句读方式更符合原文语境,在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的《史记》修订本中,即采取《汉书·李广苏建传》的句读方式,将此句标点为陈述语气(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478页)。
同《汉书》文本对校,“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与“彼其中心诚信于士大夫也”两句义同。“忠实心诚”与“其中心诚”皆指李广内怀忠诚之心,“信”同“伸”,词性是动词,义为“伸张、申述”。考察源流,《史记·管晏列传》载“君子诎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135頁),“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即源出此句。为李广哀悼的众人皆为其知己,李将军的磊落内心与忠义操守已经在他们之中得以伸张。以读音言之,“信”为心母真部,“伸”是书母真部,两字属同一韵部,音近。在传世典籍中,多见有“信”读如“伸”之例,如:《礼记·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曰,“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陆德明亦赞成郑说,指出“信,依注为伸,音申”(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0页)。左思《魏都赋》有句为“信其果毅”,李善亦采用郑康成此注解其中之信字(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第136页)。《史记》《汉书》中皆存有此用例,前文所引《管晏列传》“君子诎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司马贞索隐即言:“信”读曰“申”(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135页)。此句中“诎”之义为“屈”,“信”与“屈”文义相对,读音是“申”,故其义当为“伸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威信敌国”,司马贞索隐:“信”音“伸”(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452页)。《汉书》中《杜钦传》《赵充国传》有句为“唯将军信臣子之愿”(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671页),“信威千里”(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2989页),颜师古注曰信,读曰申。此两例之“信”义与“伸”同,句中“信愿”“信威”为“伸张愿望”“伸张威信”之义。
(三)贵轻重,慎权衡
《管仲列传》载太史公评价管仲为政举措之语曰:“贵轻重,慎权衡”。对于“贵轻重”之解释,在《史记》三家注中即存在分歧。司马贞索隐“轻重谓钱也,《管子》有《轻重篇》”,张守节正义“轻重谓耻辱也,权衡谓得失也。有耻辱甚贵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133页)。司马贞把“轻重”解作钱,并与《管子·轻重篇》相联系,而张守节则将“轻重”释为耻辱。《史记》选读课本之注释采取司马贞之说,解“贵轻重”为:“《管子》有《轻重篇》,论述物资的聚散,盐铁山泽的开发,货币和物價的高低等。‘贵轻重’实指重视经济的发展。”(丁帆、杨九俊主编,《〈史记〉选读》,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69页)此种注释虽依循古注,但仍有疏失之处。
“贵轻重,慎权衡”之句所用修辞手法为单句互文,前后两部分文义相互补充,其义是“重视权衡利弊得失”。其中,“贵”与“慎”义同,均训为“重”。典籍文本中多见此例,如:《老子》第十三章“何谓贵”,陆德明释文“贵,重也”(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356页)。《国语·晋语七》“贵货而易土”,韦昭注“贵,重也”(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412页)。《文选》录有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一文,其中有句“《周易》所贵”,刘良注“贵,重也”(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第804页)。传世文献亦常见将“慎”解为“重”者,《吕氏春秋·节丧》“慈亲孝子之所慎也。”高诱注“慎,重也”(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220页)。孔融《荐祢衡表》“陛下笃慎取士。”刘良注亦为“慎,重也”(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第685页)。句中“轻重”词性与“权衡”同,为动词,可释作“权衡”,为斟酌比较之义,其用例可见于王安石《众人》诗。其诗云,“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8页),只有圣人能对人的能力进行权衡,不会把很轻的当作很重的。从《管晏列传》文本语境来看,该文段赞扬管仲政治眼光长远,其为政善于对利弊得失进行权衡,不会拘泥于眼前小利,亦避免因仇恨而造成国家损失。在“贵轻重,慎权衡”之句后,依次举“责楚不入贡包茅于周室”“令燕修召公之政”“遵曹沫之约”三事为例证。三事均与政治活动有关,而同经济活动无涉。若将“轻重”释为“重视经济发展”,则与其语境相悖。
(四)韩信说汉王
秦朝灭亡之后,项羽分封天下,先进入咸阳的刘邦受到刻意打压,被封为汉王,封地是远离中原的汉中巴蜀。刘邦到汉中之后,烧绝栈道以使项羽安心,然士兵以为归乡无望,纷纷逃离汉军。此时,韩信面见汉王,建议刘邦及时出兵,成语“及锋而试”即出于此。《高祖本纪》记其言语。
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67页)。
此事亦见于《韩信卢绾列传》,记为:沛公立为汉王,韩信从入汉中,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近地,而王独远居此,此左迁也。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乡,可以争天下。”汉王还定三秦,乃许信为韩王,先拜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632页)。
《韩信卢绾列传》为韩王信、卢绾、陈豨三人的合传。传中的韩信为韩王信,是韩襄王的庶出之孙,属韩国王室,与同萧何、张良并称为“汉初三杰”的韩信并非一人。西汉著名军事家韩信因在汉朝建立之后爵位为淮阴侯,故其人物生平见于《淮阴侯列传》。在刘邦出兵之后,历史便进入楚汉相争的时期。在楚汉双方的战争中,韩信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成为帮助刘邦击败项羽、建立汉朝的重要力量。在《〈史记〉选读》课文中,此段下文有“于是韩信、彭越皆往”之句,此句“韩信”即为淮阴侯韩信,而非韩王信。前后相接之两段均有“韩信”出现,但并非一人。“韩信说汉王”段中“韩信”若不以注释明确其为韩王信,极易被误读为淮阴侯韩信。
(五)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管仲列传》“太史公曰”部分有句为:“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注释解“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为“鼓励并顺从好的,纠正并制止不好的。将,扶持”(丁帆、杨九俊主编,《〈史记〉选读》,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70页)。此处释义失确。
“将顺其美”之句“将”与“顺”义同,为“顺应、顺从”之义。经典文献中多见此例,如《庄子·庚桑楚》“备物以将形”,王弼注为“因其自备而顺其成形”,解“将”作“顺应”(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793页)。成玄英之疏与陆德明释文同,皆言“将,顺也”(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793页)。《汉书·礼乐志》所载《郊祀歌》第七章《惟泰元》有句云:“招摇灵旗,九夷宾将”,颜师古注曰:“将犹从也”(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057页)。王力亦把“将顺其美”之句作为例句,归于“将”字“顺从”义之条目下(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第230页)。
“匡救其恶”之“匡”当训“救”,如:《左传·成公十八年》“匡乏困”,杜预注:“匡,救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923页)。玄应《众经音义》卷十九“匡领”注引《周礼·匡人》,郑玄曰:“匡,救也”(玄应,《一切经音义》,影印清道光二十五年海山仙馆丛书本,第340页)。《逸周书·糴匡》“分助有匡”,朱右曾集训校释“匡”字为“救”(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清光绪三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第214页) 。“匡救”之“救”为“阻止、禁止”之义。《说文解字·攴部》:“救,止也”(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中华书局2014年,第3662页)。《周礼·地官·司徒序》:“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郑康成注“司救”为:“救,犹禁也。以礼防禁人之过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698页)。《集韵·虞韵》亦记:“救,禁也。周官有司救”(丁度等编,《集韵》,中华书局1988年,第22页)。
所以,“将”“顺”与“匡”“救”均为同义复现,“将顺”是“顺应”之义,“匡救”义为“阻止”。考察源流,“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之句语出《孝经·事君章》,其言: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560页)
该句同“进思尽忠,退思补过”骈列成文,“进”“退”互为反义,“将顺”“匡救”当与此相同。解“将顺”为“顺应”,释“匡救”作“阻止”,亦符合其文本的原始语境。
(六)爽然自失
《屈原贾生列传》载司马迁读贾谊《服鸟赋》之句云:“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汉语大词典》收“爽然自失”条,释其义为“形容茫无主见、无所适从”(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第1552页),并以《屈原贾生列传》此句为例证。苏教版《史记选读》采取《汉语大词典》之说,解“爽然”一词作“茫然”(丁帆、杨九俊主编,《〈史记〉选读》,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75页)。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亦取用此释义。
此处“爽然”当作“奭然”,义为消解、消散。《屈原贾生列传》“又爽然自失矣”之句,徐广音义曰:“一本作‘奭’”(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504页)。可见,《史记》文本有作“奭然”者。“奭然”一词,语出《庄子·秋水》“且彼方跐黄泉登大皇,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沦于不测;无东无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66页)此句形容庄子所论之道极其宏大,其与黄泉上天相沟通,超越了南北西东的空间界限,同幽深难测的大道相际合。陈鼓应注“奭然”为“释然”(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504页),为消解之貌。“奭然四解”指道无界限,不受限制,充布于四方。
《服鸟赋》为贾谊被贬于长沙时所作。《屈原贾生列传》记其事曰:“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長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496页)司马贞索隐引姚氏云:“广犹宽也。”(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497页)句中“广”为宽慰之义。贾谊时为长沙王太傅,一日有服鸟飞入舍中,霎时引发其伤感之情,感觉自身难以适应长沙卑湿的环境,很可能寿数不长,于是作《服鸟赋》来宽慰自己。在《服鸟赋》中,贾生用庄子思想来进行自我开导。《服鸟赋》援引《庄子》之句计有8处,其中直引3处,化用5处(具体如表1所示)。
贾谊认为生死祸福本无界限,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应顺其自然大道,不该过度担忧。这种思想直接来源于庄子。在庄子思想中,万事万物皆为齐一,生与死、福和祸、得与失本没有绝对的界限。其《齐物论》即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508页)。“爽然自失”指自身与外物界限消失,彼此对立的二者融成一个整体,其与“同生死”“轻去就”均为庄子齐物思想之体现。
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传文本,《史记》的篇章叙述与文字语言均具有典型性,对其进行准确化注释,不仅有助于把握历史本真、体味文本之美,亦能够在实际语文教学过程中强化受教育者对文言释读的认知。苏教版《史记选读》的注解疏失代表了高中语文教材《史记》类文本注释中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对其进行补正能够为统编本教材相关篇目的完善提供借鉴。参合《史记选读》的六例补正,高中《史记》文本注解应遵循下列原则:其一,在文本选择方面,应以中华书局最新修订本为基础,同时与《汉书》等其它书引文中相关段落的句读与注解进行参照,以底本与对校相结合的方式保证其文本准确性。其二,在字词疏解方面,依托文本语境与《史记》它篇用例对词义进行确定,在词义确定过程中注重单句互文、同义复现等特殊文言用法。其三,在异文确定方面,充分重视《史记》三家注与校勘记所提及的文本异文,参核《史记》原文意旨与它本相应秦汉典籍之思想内涵对其进行厘清确定,并按照古籍整理规范进行相应处理,即不在原文之上直接修改,而于注解当中予以说明。其四,在其他方面,以追求文本理解的准确化与完备化为原则,对文中同名异人等特殊之处进行疏解。
本文系江苏省“十四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世界遗产视野下中学生人文素养涵育研究”(项目编号:C-c/2021/02/06)阶段性成果。
单位:江苏省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