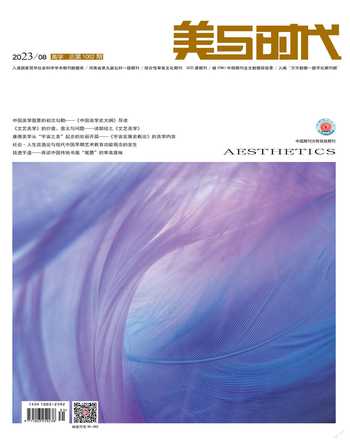文本与视觉的互动:李沧东电影与文学的互文性探析
2023-10-10邬宏玺

摘 要:韓国电影近年来备受关注,尤其是以作家身份浮出韩国电影历史地表的李沧东导演,2020年出版的小说集《烧纸》主要收录了李沧东1983—1987年间的文学作品,作为前文本的文学与后文本中的电影形成了较为紧密的互文关系,在从小说到电影的沿袭脉络基础之上,实现了文本与视觉层面的互动。由此,通过“人物形象的建构”“作为修辞的身体”“叙事空间的生产”三个维度的比较,探讨李沧东电影与李沧东文学之间的互文关系,从而形成一条可追溯的李沧东创作考古路径。
关键词:李沧东;电影与文学;烧纸;文本互涉
苏珊·海沃德曾在《电影研究关键词》一书中将“互文性”定义为“文本指涉文本,或文本引述前文本”,互文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影响的文本之间的关联性。大多数电影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互文——一个文本指涉其他文本,文本之间相互交织[1]。
李沧东电影与文学是李沧东的一体两面,文字与影像的多样性使得李沧东自身就成为了一个多声部的主体。无论是文字的书写,还是影像的创作,李沧东都直面韩国的社会现实,将叙事视角向下扎根于底层民众,多次质询韩国现代工业社会在狂飙猛进之时,人的社会地位与生存价值的消亡。而当我们再次将游移的目光置于李沧东一系列的影像作品后,诸如“绿色三部曲”、《密阳》《燃烧》等,得以窥见李沧东电影作为后文本,其实是对前文本文学小说的一次历史性的回望,也是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之间的一次隔空对话,小说的光彩不仅没有被影像视听元素的多元化遮蔽,反而是后文本电影创作的炼金石,更因为两者之间的沿袭与互动而鲜明呈现出了李沧东电影中的文学思想的本源和哲学思考。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电影文本内部的情节生成早已在小说之中得到某种诠释,而小说中的情节设置业已体现出李沧东电影的现实质感。
一、痛楚·反抗——人物形象的建构
李沧东的电影大多描写社会边缘人、底层人的生存处境,以小说式的叙事方式、冷峻的客观视角,从时代进程、生存苦难、追寻意义等多个维度展开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他所书写的人物角色总是深陷于满布荆棘的丛林与泥泞不堪的沼泽之中,间或表达着在韩国工业化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社会属性丧失,他们在如此阴沉与幽暗的地带进行无奈的挣扎与反抗,苦痛与哀怨,尽管他们身陷囹圄,但仍对人生无常的荒诞与戏谑投以希冀,而现实再次给予他们的却是更沉重的伤痕与失衡。可以说,正是李沧东对文学与电影中角色的无限关注和悲观现实主义的表达,才定义了他作为作家和导演的双重身份。
2020年出版的李沧东小说集《烧纸》收录了《火与灰》(1987)、《大雪纷飞的日子》(1987)、《战利品》(1983)、《舞》(1985)、《烧纸》(1985)、《为了大家安全》(1987)等作品,而其中一则短篇小说《火与灰》(1987)所建构的故事世界及人物形象的塑造,都与电影《密阳》(2007)呈现出某种互文关系。
小说《火与灰》讲述一名父亲面临着逝子之痛,他曾和妻子把孩子的骨灰洒向汉江,在孩子忌日这一天,他决定独身前往江边祭奠,而妻子则希望在这一天通过对宗教的信仰来治愈逝子的心理创伤。李沧东通过小说中父母对早逝孩子的追忆,由此拷问死亡与人生意义:
一个孩子死了,而这个世界里却找不到任何痕迹。四季依旧更迭,又一个春天开始了,阳光又开始发烧一样温暖起来,从教室的窗户外看,花粉像是从弹棉机里筛出来的棉尘一样,白花花地弥漫在运动场上……[2]31
李沧东以冷静而克制、细腻而温柔的文字书写,向读者以及自身进行严肃的拷问——存在的意义。孩子因一次意外被卡车倾轧,此时的他们忍受着内心无尽的伤痛,却又苦于找不到发泄的出口,仿佛承受着西西弗斯般的惩罚。而在这样循环而吊诡的惩罚之中,他们或许试图用赞美诗歌和祈祷来战胜苦痛(母亲对宗教的信任),或许是对宗教的怀疑与质询(父亲对宗教的困惑),又或许产生通过记忆的追溯与内心愤怒达成和解的意图(前往汉江祭奠),但他们终究不过是无法停止忙碌状态的芸芸众生,在如此动荡不安又瞬息万变的社会境况下,他们的内心情感再次被放逐于群体之外,成为一名“孤独的城市流浪者”。与此同时,他/她们所拖曳着的孱弱躯体作为一种身体物质外壳再次被伤害得体无完肤,对世界荒诞与虚无的反抗意识,从肉体到灵魂都消弭殆尽。
电影《密阳》中人物的反抗姿态相对于小说《火与灰》更为明显。失去丈夫的李信爱带着儿子重返丈夫故地——密阳,她做好一切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但儿子却遭到绑架谋杀,万念俱灰的李信爱内心被愤恨填满,逐渐在她抱以希冀的城市空间中迷失自我,从而转向基督教以求得内心的宽慰。可是,当她准备原谅牢狱中的杀人凶手时,凶手却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告诉她,我的罪孽已经获得了上帝的赦免与宽恕,这让她彻底对生活及宗教信仰感到绝望,由此人物开始产生强烈的自觉反抗意识,破坏基督教活动,质疑上帝的存在,撕开宗教伪善的面具。但李沧东曾在采访中说道:“我通过《密阳》这部电影来谈的不是宗教信仰,也不是要谈上帝,我要说的是人和他的生命、人生。”[3]由此看来,李沧东并没有刻意反对基督教,而是对宗教教义所延伸出的形而上的虚伪意识压抑人类本真欲望的诘问与对人类生命原相的追寻。影片结尾,李信爱剪掉了自己的头发,镜头缓缓地跟随飘落的碎发,摄影机摇移到一缕阳光照射的荒芜空地上而结束。通过固定镜头的静态构图以及开放式的结尾,从而使影像营造出了一种李沧东电影中独有的文学诗意之感。
由此,无论是李沧东电影还是李沧东文学中的人物,都被作者赋予了某种反抗特质,尽管他们都深陷迷惘与痛楚之中。他们是社会底层人物,是城市空间中“孤独的流浪者”,是被时代发展进程所抛弃的奋斗者,是对生命虚无的思考者,也是对命运荒诞的反抗者,他们没有被刻意塑造,而是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本中的角色。因此,可以说作为后文本的影像是前文本文字的转化、阐述或者延伸,如果没有文学作为前文本,那么很难有作为后文本的电影创作,两者之间的沿袭与互动,为我们了解李沧东电影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明确而清晰的路径,由此可找到李沧东影像书写的意义所在。
二、疾病·欲望——作为修辞的身体
当我们对前文本小说进行分析与研讨时,就可以发现那些曾经频繁出现在影像中的身体意象也同样在前文本小说中浮现,并且在电影与文学的互文之中,身体通常作为修辞的形态连接二者。由此可见,文学与电影作为前后文本紧密契合。
(一)身体与疾病
“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借疾病之名,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4]虽然苏珊·桑塔格反对赋予疾病各种阐释,但就艺术创作而言,仍然揭开了身体疾病所隐含的社会文化、政治、历史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李沧东的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疾病图景,我们往往能看见他所描绘的是一种“残缺”的身体,通常与生理疾病相联系,它不仅仅是身体肌理平衡的破坏,更是通过身体的疾病来隐喻文化与政治压迫下的人际疏离以及个体生命的呐喊。例如,《祭奠》(1985)中经历过韩国南北战争的父亲晚年瘫痪在床,行动力丧失,日常生活的琐事都要依靠主人公“我”——正宇以及母亲的扶持,亦如书中写道:“虽然父亲的身体瘫痪,连大小便都要人伺候,时刻散发着死亡的味道,脸上却是一派恬不知耻的祥和。”[2]53父亲每天都要忍受巨大的身体疼痛,这种疼痛如鬼魅般萦绕在每一个家庭成员之中,父亲显形的“残缺身体”所忍受的苦痛业已蔓延至文本中的“我”、哥哥、母亲、姐姐,甚至是文本外的读者内心,这样的身体意象同样也出现在另一篇处女作《战利品》:“病人忽然间安静了下来,我们围站病床两旁,犹如围绕什么千古景观一样屏住呼吸,注视着这片慢慢扩大的洇湿的面积。护士叹了口气,小声说:‘小便了。”[2]275作品讲述的是主人公具本守、吴美子以及金长寿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因为金长寿的辞世而再次连接多年未见的“我”对金长寿前女友吴美子的缱绻之情,从而追溯过往。由于金长寿患有肝硬化,他的身体与意识都无法控制最基本的身体排泄功能,身体内部的生理系统开始紊乱,但他终于在临终之前,释放了被疾病所压抑已久的排泄欲望,对金长寿而言是灵魂与肉体的解脱,也是对身患疾病的无奈反抗。所以,在李沧东小说中个体的创伤疼痛已演变为特定时期群体的伤痕记忆,尽管李沧东尝试在书写中表达对个体创伤的抚慰与疗愈,但是在韩国南北战争爆发、军事独裁政治以及韓国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历史语境下,民族的分裂、民主的反抗都切实地具象为身体与疾病,是韩国社会文化症候的一种镜像反应。同时,身体的“在场”所指涉的是另一半“缺席”的历史图景,在包裹着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社会发展的外壳下显影的是在韩国历史中那些错综复杂而又束手无策的各方矛盾,亦如70年代汉江奇迹,80年代光州事件,再到90年代的金融危机,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成为集体梦魇而深植于民众内心。
“电影正是通过躯体(而不再是通过躯体的中介)完成它同精神、思维的联姻。”[5]在李沧东电影中,依然能够捕捉到关于身体疾病的影像。例如,《绿洲》主人公洪忠都思维与身体反应的迟钝,韩恭洙则是脑瘫患者,他们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畸零人形象。当忠都第一次推开门看见脑瘫疾病所导致恭洙面部极度扭曲的形象时,他没有选择回避。恭洙手里攥着一面镜子,从窗外折射进来的阳光透过镜子形成了一道道光斑,随着恭洙手不自主地晃动,那些光斑在之后的影像中幻化成蝴蝶,在苍白的墙上跳跃浮动。这个光斑意象的生成与其说是恭洙大脑意识在外部世界的一种延伸,不如理解为她对完整身体的一种极度渴望。《诗》的开场就寓示着肉身的死亡与生命的终结——一具中学女孩的浮尸顺流而下,身体的死亡意味着人类的感知系统遁入未知的黑洞之中,而主人公杨美子所遭遇的是身体记忆的丧失——阿尔兹海默症,在家庭和社会双重剥削与规训下,杨美子记忆的丢失反而使她内心对诗的爱意苏醒,让她开始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诗歌的美感从眼睛观察到的现实中来,又与肉身死亡的恐惧接洽,不避讳的性爱场面宛如一把利剑,刺穿一切虚妄的生死。
(二)身体与欲望
“身体作为知觉、情感和欲望的转喻,与象征精神和理性世界的心灵之间产生张力和冲突,这种二元关系往往是作品的主题寄托。当人物被建构为充满欲望的身体主体时,混杂着窥视欲和认知欲的身体便会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内驱力,亦即叙事动机。”[6]在《为了大家安全》(1987)这则短篇中,来自乡下的老太太不顾车上乘客的反对,执意在座位的过道上纾解尿意。“老太婆正蹲在座位之间的过道上,撸下大裤衩在小便,脸上一副无比畅快满足的表情”[2]20。人的身体机制本能的欲望在此刻得到释放。此时的身体又演变为一种符号化的过程和阶级话语同时存在,不仅推动着叙事的发展,而且也指涉着农村与现代城市、底层民众与上流社会的二元对立冲突,当落后的乡村文明与现代文明高速冲撞之时,老太太只有以一种癫狂的行径且充斥着民族之“恨”的情绪幻想来打破彼此的阶级壁垒。尿意是身体本能的欲望,但是受到现代文明的惩罚与规训,人们不得不压抑个体的本真状态,所以老太太如此疯狂的言行举止不过是以可见的姿态而作出的反抗的身体态度。
短篇《舞》(1985)中的尚哲与妻子出门远行,妻子的省钱癖导致他们的旅程常常陷入窘境,结尾返家时发现家中被盗,妻子却因损失较小,兴而舞之。结尾写道:“他的脑中瞬间画出了一副图画。就像原始人在漫长坚信的战斗之后庆祝胜利一样,他和妻子一起,在小偷们劫掠过的这片触目惊心的残骸之上兴致勃勃地舞蹈。”[2]170妻子有两次舞蹈被提及,第一次是在尚哲幻想中妻子的舞蹈,第二次是结尾悲极生乐的舞蹈,这两支舞蹈通过对身体的描写,指涉负重家庭开销的当代青年群体的生存状态,是经济文明的压迫,是社会转型的压抑。“换个角度看,则意味着无法认同支撑着工业化社会原理的另一个原理——排泄原理,即无法融入工业化的社会生活。她的生活仅仅偏向一侧的原理,却彻底压抑着支撑这个原理的基础——享受欲望的原理。”[2]305
两次舞蹈所延展出的身体意象就如同李沧东电影《燃烧》中惠美的夕阳之舞。在李钟秀家门口的院子场景段落中,伴随着悠扬的萨克斯音乐响起,惠美缓慢地走向前方的围栏,面对着日落的余晖,镜头从中景伴随着人物的运动方向改变了背景,通过内部蒙太奇的场面调度,将惠美映衬着霞光的娇媚的身体姿势呈现出一种慵懒的感觉。梦幻般的身体剪影赋予了流动的影像一种模糊感与幻灭感,身体由此也成为独立于叙事情节之外的元素,它摆脱了经典电影中叙事对角色的桎梏,实现了人物身体内潜藏的欲望的自我表达。
事实上,李沧东小说与电影中的身体景观并不指向一种大众文化消费的庸俗模式,相反,它以巧妙的表达形式绕过身体消费生产的陷阱,从而转向一种独特的审美表达与哲学思考,通过身体的表达对影像与文字再次升华,又延展出了其对生命、世界把握的诗学方式。但笔者认为,从身体理论范式进入李沧东电影与文学的互文关系探析,仅仅是通往李沧东文字与影像世界的一扇窗口,并不能代表其全部的风景。
三、边缘·底层——叙事空间的生产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与自然场所的鲜明差异表现在它们并不是简单的并置:它们更可能是互相介入、互相结合、互相叠加——有时甚至互相抵触与冲撞。”[7]由此,空间以主动的方式容纳各种社会关系,且总是处于不断被建构和变化之中。
韩国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各阶层的断裂,尤其指向农民、工人等边缘群体与上层阶级、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激化。李沧东的电影与文学都致力于对底层叙事空间的建构,以社会知识分子话语为底层民众发声,并为他们争取本该属于边缘群体的话语权利。《祭奠》(1985)中的底层空间生产表现为小时候的“我”与母亲、姐姐居住于“潮湿的房间,以及长满霉斑的天花板和因鼠尿而软塌塌的墙壁”[2]58。他们一直生活在阴暗而逼仄的密闭空间内,不仅因为父亲的党派之争要如同蝼蚁般苟且偷生,还要背负着与某种“现实”不符的骂名。小说所描写的底层空间就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以蒙太奇手法浮现。底层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此时成为了韩国历史进程中的牺牲品或马戏团的小丑,用生命和苦难祭奠着当下韩国战争的历史。《为了大家安全》(1987)中的底层空间构建在于闷热而又散发着汗味的车厢,将不同阶层的个体同时纳入同一密闭空间中,呈现出各个阶层的话语对立及民众群像,语言成为了相互竞争的话语之间斗争的场所,它表征着韩国社会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以及小市民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
电影以其流动的影像媒介形式,更直观地触摸着韩国社会当下,以其独特的影像生产完成与当下的对话,形成对韩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审视与思考。《绿洲》里的主人公洪忠都一家四口人蜗居在韩国小县城的公寓里,狭窄的空间里充斥着腐败、沉闷、乏味的生活气息,他们的生活态度是消极悲观的,出狱后的忠都于他们而言,是想抛弃却囿于亲情无法说出口的累赘。《密阳》里李信爱失去孩子之后,导演通过摄影构图经常把人物置于封闭的空间之中,例如监狱、卧室、轿车、钢琴教育机构等场景空间,以门框式的构图来隐喻人物内心的闭塞。《燃烧》中的空间二元对立设置在李钟秀破败的村屋与Ben的豪华公寓,甚至是双方交通工具(货车与跑车)的比较,此时影像内部底层空间的建构(村屋)打破了“底层话语”在韩国当下的隐匿形态,冲破了资本主义消费生产下的人们逃避生活的美梦幻象,将底层人们在当下韩国的生存状态呈现于银幕,展现着阶级壁垒与断裂中的双重边缘化。另一方面,李钟秀与Ben之间的主体差异是通过空间的差异显现的,从而探讨阶级断层问题。因此,不管是李沧东电影还是李沧东文学,都致力于对底层空间的建构,它不仅作为一种客观物质而存在,也是各类社会关系的“容器”。
四、结语
“所有的文本皆会与其他的文本进行对话,‘互文本指涉关系实为‘文本的相互关系,如果这种相互关系没有在某个作品产生回应,就不可能理解这部作品本身。”[8]李沧东的电影与文学之间的互文关系不仅仅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建构、身体修辞以及叙事空间的生产三个维度,还可以透过文学中的符号意象进行细节上的比较,它是一条非常复杂的创作考古路径,也是一次庞大的信息整合。由于篇幅所限,笔者无法全面而精准地对李沧东电影与李沧东文学进行多维度的分析,但以李沧东的文学作品为切入點,通过前后文本的互文,从小说到电影,从文本到视觉,从文字书写到影像实践之间的对话,为我们解读李沧东电影的作家身份提供了更丰富的面向。
参考文献:
[1]海沃德.电影研究关键词[M].邹赞,孙柏,李玥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李沧东.烧纸[M].金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
[3]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07级影视文化与传播班全体同学.韩国社会与情感的影像描摹 李沧东电影交流对话录[J].2008(2):69-72.
[4]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5]德勒兹.电影2:时间-影像[M].谢强,等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
[6]徐蕾.当代西方文学研究中的身体视角:回顾与反思[J].外国文学评论,2012(1):224-237.
[7]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8]克里斯蒂娃.主体·互文·精神分析 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M].祝克懿,黄蓓,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作者简介:邬宏玺,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美学。
编辑:雷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