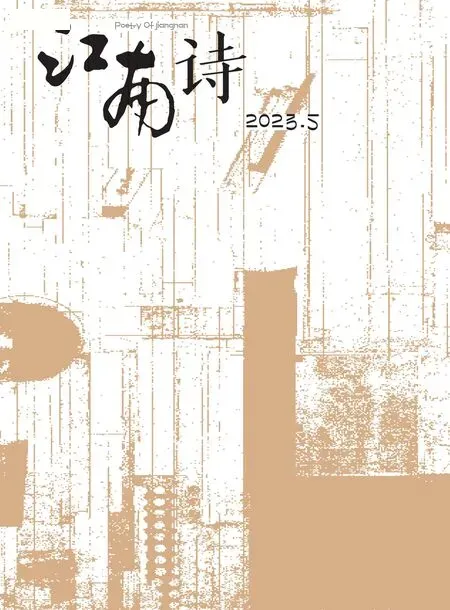天命似水,引舟如叶
2023-10-09严英秀
◎严英秀
七月流火。今夏,尤甚往年。
叶舟刚从南京回来,他说走出中川机场,脚一踏在兰州的地上,感觉自己就像一条鱼游回了水里,我的天,太舒服了!
我理解这种感受,因为我也多次在盛夏时节去往南方城市,遭受高温、濡湿和冷气交互的折磨。电话里我看不到他的表情,但还是被他一连串的感慨逗笑了。我仿佛看到了一幅画面,叶舟化身为一条焦渴的鱼,一个猛子“扑通”扎进了“姓黄的河流”(这是他的一部中篇小说题目),那绝地逢生的姿势溅起了欢天喜地的水花。
他是去领奖的,《凉州十八拍》以排名第一的票数获得了第四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三年前,他上一部曾提名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敦煌本纪》获得过第四届“施耐庵文学奖”。总之,从2008年的“《人民文学》年度小说奖”开始,十多年来,他马不停蹄地领着种种这样那样的大奖小奖。大家总是羡慕嫉妒恨地开玩笑说,叶舟同志不是在领奖现场,就是正奔波在领奖的往返路上。
看惯了叶舟行色匆匆。生活在同一座不大的城市里,我们其实很少见得着他。但他一直在,这个城市始终有他。无论他出发得多么频繁,无论他走了多远,他总会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大口地呼吸这片天空下清冽的空气。他是一叶扁舟,他的江河湖海已经铺展到了无穷远的地方,但他只愿意停驻在兰州的码头上,以及兰州背后连接着的那些更浩荡广袤的地名:凉州,敦煌,河西走廊,被月光照耀着的甘肃省(叶舟的诗集《月光照耀甘肃省》)。这是他命定的水,唯一的州。

2023年5月,叶舟在武威文庙《凉州十八拍》分享会上
叶舟联系我,是要我写一篇关于他的印象记。著名诗人沈苇约的稿。他说他和沈苇从二十几岁时互称“小叶”“小沈”,现在都快“老”了,还这么叫。他说我已经答应小沈了,所以,小严,你就写一下。
这就是叶舟,许多人印象中“天生当大哥的那种人”。他的请求更像是命令,不容辩驳。他说“写一下”,那口气好像写一篇人物印象记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好像我和他一样笔力丰沛,心到便会文成。然后,他像是安抚似的加了一句,不用写得太拘谨,好玩就行。这时候,我才弱弱地发问:可是,你好玩吗?我见过你好玩的样子吗?谁知叶舟毫不谦虚地接口:当然!我还不好玩吗?
也许,确实,他可能是好玩的。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深刻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得出了最终答案:之所以不曾见识过叶舟好玩的那一面,是因为我自己不好玩。我蜗居校园一隅,生性疏懒,不擅交际,那些作家诗人们漫长的活色生香的酒场饭局,那些“从一只酒杯到另一只酒杯的流动盛宴”,于我都是传说。透过现象看本质,可以说写作近20年来,我始终没有进入文坛另一个“现场”。不喝酒,就没有朋友!这是多么粗暴而简单的生活道理。叶舟也曾写过,在酒场上几近阵亡,在兰州,这也许就是掏出一颗真心的表达方式。而我是一个烟酒不沾、言辞寡淡、吃饭吃到肚子饱就想离席回家清静的人。所以,我从来都只是在文代会、作代会、研讨会这样的场合里能见到叶舟,见到他严肃的、严重的、煞有其事的表情,听到他正襟危坐的、奇峰突起的讲话。我甚至还见过他摘掉棒球帽、西装革履打领带的样子,我得说实话,那绝对没有他一贯的形象好看。认识这么久了,在叶舟恣意挥洒“好玩”的地方,几乎很少有人见到过我的身影。除了校园,能让我精力不怠的事情只有两个,一是看风景,二是去KTV唱歌。可是,我和叶舟竟然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共同的采风活动,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至于唱歌,明明许多人都说叶舟擅唱,可我竟然也是从未能一睹风采。好像什么时候不知怎地提起过一次,他顾左右而言他:阳了以后,嗓子还能唱歌吗?想来,我的唱歌和他的唱歌本质上是两种事情,我的唱歌是字面意义上的唱歌,大白天提着一条嗓子认认真真唱曲、清清醒醒记词,而他的“大声唱歌”多半是发生在“大口喝酒”之后的动作,那是一种更即兴、更激情的衍生物。
所以,或许,这也不排除我自己可能也是一个好玩的人,只是我们各自的“好玩”没有交集过。事情就是这样:十多年了,我们有机会不时碰头,但我不曾见过叶舟只身匹马、斗酒高原的胆气和酒量,不曾见过他醉酒至极的慨然而歌,包括那像旷野之风呼啸而过的气场;不曾见过他以瘦弱之躯“劈面一拳”应对威权的迅猛与血性;不曾见过他那些可能的爆发和嚎叫,那些突降的软弱及柔情;我不曾在午夜时分看见他把小石子投向远远的黄河水,然后抱着一棵大树放声哭泣。是的,他那些离地三尺的狂狷,他那些凝水成冰的忧思,我都不曾见过。太多的属于叶舟的传说,我都无缘成为见证者。
可是,我真的需要见到那样的一个叶舟,才能觉得是懂他的吗?一个写作者,他用了30多年时间一笔一笔写出来的诗集、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这些满满当当铺在我眼前的一部部厚重大书,难道还不足以构成他的生命秘语、他的心灵史、他的精神自传吗?
好像已经是一辈子的事情了。在叶舟的《大敦煌》时代,我就成了他忠实的粉丝。我曾那样地被那些滚烫奇崛的诗句震撼过,被那些葱茏幻美的意象缠绕过。落花流水,青春成昨,但那样的文字,遇见了便是生生世世。后来,当我站到了他的面前,我没敢套用那句貌似很流行的话:我是看着你的诗长大的。事实上,叶舟还这么年轻——仿佛,一个时代遽然被大风刮走,一群人不由分说地抛下了他,他一个人站在老地方,他一个人慢慢回首,望向了来时的路。再不会被大风吹老,再不会被时光揉捏。一些仓惶,更多笃定;一些破绽,更多睥睨。是的,叶舟的年轻是“好吧,那就这样吧”的决绝了断,是刀锋在暗夜里兀自寒光四射,是野花斑斓一地的戛然而止。这样的年轻,比老去更有着绕梁不绝的来历、欲说还休的沧桑。
但现在是八月。一些地方地震,一些地方泥石流,一些地方的庄稼和树木都旱着,另一些地方却大雨不断,频闹水患。不堪回首的三年时间一步步熬到头后,世界依旧难以太平,我们的身心依然不能安妥。一场众所瞩目的文学评奖,也在八月里尘埃落定。叶舟,曾经那么幸运地被鲁迅先生“摸了顶”,却再度与这一文学奖擦肩而过。一枚钉子,钉死了甘肃预设的大欢喜。远方,众声喧哗,嘈嘈切切。身边,一些笑容,突然变脸。多么让人鄙视啊,这人世的可笑和势利!获奖当然是鲜花和掌声,是无上的荣誉,但本质上也只是一件华丽的外衣,外衣袖口绚丽的花边。获奖者们在发表感言:写作从来不是为了获奖,但获奖是对写作的总结、肯定和激励。多么正确的话!是的,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他的价值永远只体现在写作本身。有何胜利可言,何谈失败!
人事如旋涡。叶舟,当他在这个八月,在兰州市白银路的一间寂静小屋里听着世界的喧嚣,他是否会想起遥远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月亮女神阿赫玛托娃?那个一生磨难悲辛的女诗人曾说:荣誉“不可能给诗人添加什么东西,同时也不可能剥夺诗人什么东西”。没错,对于今天的叶舟,不可能添加什么,也不可能剥夺什么了。他曾经那样地对峙过孤独和荒凉,却依旧戒不掉他的狂放。他不止一次地被众目聚焦所灼伤,但依旧孤勇着他的骄傲。他也省思过去,“因为赶路、因为奔波,也因为生活,我们往往躬身于日常的琐屑当中,我们时常屈膝于一地鸡毛的尘烟里,忘了直起腰板,忘了举首问天,忘了扪心自问”。如今,他只愿意倾听自己心底的风声。
而延宕成性的我,终于提起笔写这篇关于叶舟的印象记。我不知道我能否写出“小沈”口里的“小叶”,我不知道我的文字会在多大程度上贴合大家的叶舟印象,我只知道应该写出自己读到的、认知的那个叶舟,为了稿约,更为了向一个一直走在前面的同道,一个曾以诗歌之光照亮过我的青春的诗人,一个已然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王国的优秀小说家,来表达一种纯粹的致敬。
这才发现,其实有太多的人写过叶舟了,说名满天下绝不为过。且不说作品评论,就连他本人的印象记之类,也是林林总总一大堆。著名的有李敬泽的《鸡鸣前,大海边》,他评价叶舟的创作已走进了黄金时代,是“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大胆狂徒、醉鬼和侠客的时代。另外,徐坤也有激赏之辞:“刀子中的刀子/你是男人中的男人/王中之王。”语不惊人死不休,她以“写完这部诗集《大敦煌》的人,我想,应该气绝身亡了”,表达了叶舟诗歌对人心的强烈震荡,以及她对叶舟才情的无比惊叹。徐坤文章的题目“在地为马,在天如鹰”之后被广为引用,几成经典之语。还有沈佳音富有场面感的描述:“在兰州,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酒酣耳热。叶舟好酒,一晚上可以赶四五个酒场,马不停蹄,激情四溢。”
我最喜欢的则是诗人张海龙写叶舟。一是因为他不光写人,也写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兰州城,他认定一个诗人的血脉与气质,必定与生息于斯的城市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写了叶舟的史前史,叶舟在成为著名的“叶舟”之前的许多美好场景。叶舟应该庆幸,这世界上有另一个男人在时隔20年后,还在如此深情地回忆与他的初遇:“一九九二年春天,在西北师大校园,我们一伙文学兄弟初识叶舟。触目所及,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能具备叶舟那种独有的魅力:他身材瘦小但气质近乎专断,他目光凌厉说话仿佛藏着刀锋,他衣着干净站姿挺拔,整个人就像一张绷紧的弓。他出现在我们这群浑浑噩噩的年轻人面前,好像西北荒野里放牧群羊的一个羊倌……”
一生锋利。这是张海龙对叶舟的概括。也许还能想出很多属于叶舟的形容词,但若只能用一个,却似乎再没有比“锋利”更准确的了。是的,叶舟是一个锋利的人。他也许不会“爱海只爱海的惊涛骇浪,爱青草仅仅爱青草遍生于废墟之间”,但更多的时候,他选择了决绝、鲜明、铿锵、燃烧的色彩,他选择了淬心沥骨、九死一生的事物。
也是在张海龙的文章里,我看到了叶舟的这段文字:“在逼仄的河流之畔,他们朗诵过我的诗歌,目睹过我的失败,见证了我的青春是怎样一寸寸嚎叫与湮没的。同样,我也欣赏过他们美妙的少年,认出了他们文字中的跌仆,并且目送他们一骑绝尘,笑傲远方。在斑驳的旧日时光里,我们共存着一个旧日的地址,一捆旧日书信,一支老歌,以及一桩桩缠绕的回忆。”
多么好。一个旧地址,一捆旧书信,一支老歌,一桩桩回忆。若能共同怀抱这一切,便可称得上是天长地久了吧?我们的人生不就是在对这些美好事物的拥有、流逝、缅怀中慢慢老去的吗?
所以,很羡慕张海龙,他是陪伴者、见证者,甚至,是互相的塑形者。而我,只能在酷热不退的立秋时节之后,在键盘上力不从心地敲打一个已经完成的“叶舟”。我知道,当他穿过这个季节走向将要接踵而至的薄凉秋冬时,他的目光一如春夏般丰盈。他已经写出来的那些文字,和注定还会写出来的文字,已经垒出了高高一堆雪天的炭。走了这么久了,从逼仄的河流之畔开始起步,在一片又一片洼地上盘旋,如今他已经走到了高处,走到了山峰,成为方向。
当夜色漫洇,漫步于黄河苇荡中,我看见大游轮慢慢驶来,小汽艇飞一样飚过。这实在是今年夏天的一件好事吧:兰州的旅游几乎没有预兆地随着天气热了起来,火爆出圈,黄河风情线上游人如织,中山桥夜夜不眠,大小号上一片喜悦的调侃:“牛肉面,根本拉不完!羊皮筏子,根本漂不完!羊,根本活不了!”
听到最后这一句,思绪里突然就蹦出了“午夜入城的羊群/迎着刀子/走向肉铺”。你看,事情就是这样,生活在兰州,许多时候不经意间就会和叶舟狭路相逢。他的诗,他的小说,他广阔的隐喻世界。“一只船”街道上的那家牛肉面,吃凌晨六点钟头汤的仿佛总是一些似曾相识的面孔,如今却挤满了天南地北的口音。当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不知叶舟可否还有精力加入到狂欢的人群中,去夜市里找那一碗白胡子大爷的牛奶醪糟?羊群,以更汹涌的阵势在夜色中穿过广场,他只能沉默地目送它们卷起的沙尘。他曾掷笔放言:在这样的热闹时代,在这样的喧嚣时间,写作不啻于一种疯狂!时间如黄河穿城而过,不舍昼夜,热闹和喧嚣一天天地变本加厉了起来,一年年地更漫无边际了,他却依然困守在自己的写作里,以不变的疯狂应对世界的热闹和喧嚣。他不再试图挣脱了,他说“天命如水,只能顺水推舟”。
是的,没有比写作更深刻的宿命了。就像午夜入城的羊群走向肉铺,叶舟只能在兰州、敦煌、凉州、大西北和广袤的北方,在这些精神的星空下和词语的丛林中,找见他自己此生此世的庇护。
我是从《羊群入城》这部作品才开始了解叶舟的小说的。之前,我心目中的“叶舟”这个名字确乎是属于诗歌的。但不经意间,诗人叶舟悄然成为了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优秀的著名的小说家,成为了我的城市一个地标般的存在。每一个与文学有一定关联的外地人,说起兰州,便会提起叶舟,就像他们提起黄河和牛肉面一样自然。
从诗人到小说家,叶舟到底走了多久?洋溢的才情,极致的创造力,使得他的小说创作似乎根本没经过人们常说的转型、蜕变,一转身便是华丽出场,便预示着“最高一跳”。2008年,《羊群入城》获得了迄今为止甘肃省唯一的“《人民文学》年度小说奖”。六年后,2014年,《我的帐篷里有平安》荣获了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填补了甘肃省在这一奖项中的空白,这是甘肃文学的标志性事件。记得那一年,甘肃的诸多同仁在叶舟获奖后发表了庆贺文章,简直是一派普天同庆,欢欣鼓舞。
我当然有理由比别人更喜欢《我的帐篷里有平安》,因为那是来自我“故乡”的故事,那些祈求平安喜乐的众生也是我亘古的父老乡亲。那真是一篇让人沉静、让人欢喜、让人飞飏的小说,充满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深长意味。授奖词如是说:“叶舟举重若轻,在惊愕中写安详,在喧嚣中写静谧,在帐篷中写无边人间,在尘世中写令人肃然的恩典,对高原风物的细致描摹和对人物心灵的精妙刻画相得益彰。小说的叙述灵动机敏,智趣盎然,诗意丰沛,同时又庄严热烈,盛大广阔,洋溢着赤子般的情怀和奔马雄鹰般的气概。”
这就是叶舟的小说之路,层峦叠嶂,柳暗花明。无穷远的远方,等着他去造访,去探问,去书写。然而,最终他还是回到了最初的诗歌版图——“大敦煌”。敦煌,敦煌。它到底是什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怎样的一种魔力,召唤着一代代艺术家朝着它义无反顾地奔去,从此让生命改写?叶舟在19岁时写下了第一首关于敦煌的诗,从此它便成了他的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这一路走来,他当过教师、记者、编辑和职业作家,唯一不变的是他一直在写敦煌。2000年,在跨过千禧年的门槛时,叶舟完成了诗文集《大敦煌》。也就是在那一年,在敦煌的冬日暖阳下,聆听着西北风吹过佛窟发出的天籁之声,他发愿将来一定要为莫高窟写一本厚重之书。
此后,叶舟酝酿了整整16年,实地勘察也有足足十余次。终于,他如愿捧出了一个大部头,捧出了敦煌的威仪与不朽,让它凌空独尊,卓立天际——这就是迄今仍然畅销的“现象级”的《敦煌本纪》。“如果说,敦煌以及河西走廊,包括那些沉痛的历史,它们曾经是一片绵远而斑驳的‘锈带’的话,那么现在的重述,今日的辩护,将是一份除锈的天课,一切才刚刚开始。”叶舟说,“我的答案就在《敦煌本纪》中。”

叶舟在鲁迅文学院
为敦煌立传,为河西走廊正名,为被蒙尘的西北历史除锈,叶舟兑现了他自己在天地之间的诺言。
而这还不是全部。在400多页篇幅的诗集《大敦煌》与皇皇百万言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之间,叶舟还创作了大量不同体裁的敦煌文本,像是过去的一位莫高窟画匠那样,揉捏着手中颜色各异的石料。他以小说的深广,诗歌的热烈,散文的赤诚,剧本的清奇,一以贯之地表达着对敦煌刻骨铭心的热爱。那一条由佛窟、草原、戈壁、沙漠、雪山、马匹和不可尽数的遗址构成的温带地域,成了他倾身而去的文字空间。他在这里聆听到了千年乡愁的声音,他在这里叩天问地,生死悲欢。他说:“这是我个人一命所悬的天空。与其说我是迷恋,不如说这是一种皈依;与其说我在供养,不如说此乃一块福田。”他在敦煌赐予他的无边的光明和忧伤中,寻索着生命的净化与救赎之路。他行走,他沉吟,他一刻也不能停止歌唱:
没有你,我要这歌声做什么?
没有你,这一场今生今世,对谁诉说?
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疑惑,那个许多人口耳相传的“好玩”的叶舟,“从一个酒桌直接奔赴下一个酒桌,一晚上可以赶四五个酒场”的叶舟,和出版了《大敦煌》后立即发愿写《敦煌本纪》、写完了《敦煌本纪》紧接着又着手《敦煌本纪》续集的这个叶舟,真的是同一个人吗?是怎样的笃定和狂野,使他在这座“酒精里泡大的城市”中过五关斩六将,成为别人活色生香的深刻记忆?又是怎样的使命和雄心,在断喝他,命令他赶紧,让他一次次“心里起了一场火灾”,让他“急成了一堆火”,去奔赴下一个写作任务?谁能想象没有强大、刻板的纪律约束的写作?听听,叶舟是这样说的:我必须抓紧时间,我有一种跟生命赛跑的感觉,在接下来写作《凉州十八拍》的47个月中,我几乎马不停蹄,甚至没能歇息过哪怕一天。
事实上,这才是打开劳动模范叶舟的正确方式:在全体中国人最看重的农历春节,在本应和父母家人团聚的时刻,在最有理由和朋友们醉酒的夜晚,他放弃了一切去写作。张海龙这样描述大年初二的叶舟: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把自己包在一套军用绒衣裤里。窗外市声喧嚣,烟火璀璨,他写了一张稿纸然后一把揉碎,又拿起第二张……
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这是朴素的常识,颠扑不破的真理。
历时47个月,用“赛跑的感觉”写下的就是《凉州十八拍》,这部上中下三卷、计134万字的长篇小说——它之于叶舟,分明是一场命定的夙愿,却又像是一个意外的邂逅。
2018年写完《敦煌本纪》之后,叶舟开始准备《敦煌本纪》的续集,这被称之为“丝绸之路三部曲”系列,就连故事架构都已构思妥定,只等动笔。然而,事情起了变化。后来,我们从众多的报道中了解到了原委:叶舟的父亲是甘肃武威人,二十几岁只身来到兰州安家落户,终生乡音未改。他酷爱读书,总是期盼着儿子能写出一部有关故乡的小说。《敦煌本纪》出来后,他问儿子,怎么写的又是敦煌呢,河西走廊的第一站不是凉州吗?
和所有的父亲一样,这个心系故土的老人终于无可抗拒地衰老了。在看着父亲插上了氧气管的那一天,叶舟突然间决定要把敦煌题材的写作计划束之高阁。之后的四年,他只想做好一件事——为父亲写一部以河西走廊为背景,以古凉州为原点的长篇小说。他祈愿在将来成书时,专门腾出一页雪白的纸,写上:献给父亲大人。
然而,父亲没有等到《凉州十八拍》出版,便驾鹤西去了。但叶舟再一次兑现了诺言:在父亲的墓前敬献了三本沉甸甸的大书,完成了一个儿子对父亲别样的孝报。这部关于父亲的故乡凉州城的故事,以古典悲剧《赵氏孤儿》为引子,以十大名曲《胡笳十八拍》为结构,讲述了父辈们义薄云天的生死历史,以及河西走廊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它一经问世,便引起了比《敦煌本纪》更为广泛的关注。太多太多的人给了《凉州十八拍》深刻的剖析和高度的评价:“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一个传奇”;“一部关于伟大地理与伟大文明的史诗”;“是一部致敬传统、面向未来的联通之作;是一部黄钟大吕、余音绕梁的阳刚之作;更是一部沉郁顿挫、抑扬跌宕的厚重之作”;“凝聚中国筋骨、突出展现中国恢宏气象的深情之作”;“为当代文学补充了古典深情和义气的崭新的、有气魄的、能够立得住的厚重文本”;“‘少年中国’的诗史重构”……等等,等等。
珠玉在前,关于这部作品我不再赘言。我只想说,《凉州十八拍》值得这样被肯定,被赞誉,恰如这本书的题记:“天凭日月,人凭心,/秤杆凭的定盘星;/佛凭香火,官凭印,/江山凭的是忠义。”
让我为之潸然泪下的还是叶舟的自述:“《凉州十八拍》故事的时间背景相当契合了父亲的童年与少年,待成书之后,我宁愿相信奔跑在当年凉州天空下的那一帮儿子娃娃当中,有一位就是我的父亲。”如此这般的眷念,《凉州十八拍》怎么可能不成为一种深情主义的写作?
评论家施战军说:“叶舟是60后中一个代表性作家,在中国文坛已经长成了庞然大物,一部部扎实而自觉更新的力作使他稳定地走在被持续经典化的路上。”如此的赞许!路上,这又是一个多么契合了叶舟精神的词语。多少年来,他从没有停止过在路上的奔跑与追逐。现在,所有的功课,包括颂赞、致敬、供奉,都一一完成了,他再一次走到了路上,再一次寻索远方:“究竟,走过多少北方/才能在内心,攒下/一座虔敬的/教堂?”

叶舟在敦煌《敦煌本纪》诵读会上
下一个出口,又在哪里呢?
他不再奢求答案。他只是走出了书房,走出了人群,河西走廊、青藏高原、甘南大地、天山脚下、青海湖畔、蒙古高原……北方的山河依次绽开,永无止境的“目击、感恩、引领和呼喊”再次开始。他唯有对着大地深深地躬下身去,像一个隐忍而悲伤的行者。天空盛大,阳光雪白,他张开双臂,再一次成为了那个前路辽阔的勇猛少年,恰如他的诗歌所云:
我体谅自己,这一生都在路上
寸步不离自己,也没有丢失一点一滴
我体谅这一条路,始终扶住我
用飞鸟的心,蚕的速度,慢慢抵近
我体谅天空,不弃不离地照彻我
在夜晚仓皇不已,在白天有一份伟岸
2023年8月20于兰州黄河雁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