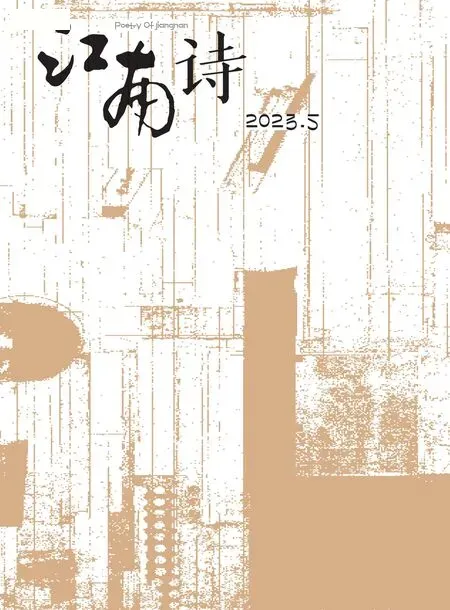无缰野马的冲决与涤荡
——评南疆诗人作品辑
2023-12-11◎董赴
◎董 赴
犹如“无缰野马”之称的塔里木河一样,南疆诗歌群体出发,以蓬勃之姿,强劲之势,在荒漠、戈壁、绿洲、城镇组成的开阔里冲决涤荡,迅速形成一方面目清晰的诗歌版图,这种集体呈现,不禁令人刮目相看。
卢山的《将雪推回天山》,老点的《尘土之上》,二伟的《固执西行》,沐沐的《大写零字》,沙海驼的《胡杨记》等,成型的文字和更为稔熟的笔力,探究着地理诗性赋予的偏远气质和雪峰、胡杨、浊流见证的物种多元。由于静心和滞重,他们的诗句沉淀着专注,传达着个体的缺憾和饱满,也不掩饰不住对于当代人文精神的质询和诠释。
“发梢四起的时候 / 不去阻止心尖上的陈年旧事/ 学着日光添置一条斑驳的影”(《一个人的苹果地》)。沐沐对女性情感瞬间捕捉的扎心片断,明晰中饱含迷惘,失落中掺杂了见血的剖析。架构上的天然浑成,空灵意象和信手拈来的数学用语,呈现着立体交叉的截面组合。“我把我全部的热能都给你 / 快要冬天了,我习惯了在冰雪地里哆嗦 / 在黑夜中吸烟,把一张泛黄的照片藏在枕头下 / 你知道吗?我在红里取暖隐居,甚至把泪流到一张木桌子”(《无所果》)。情感激流闪烁的迅捷和细致多棱折射着的过渡地带,在诗境的隐含和幻化上达到了极致。
老点的精神触角,波及事物内在的恒定。“渺小的尘土,阔大的嘴巴 / 它吞没万物 / 又催促春天一再出发 / 尘土知晓所有的秘密 / 却从来都沉默不语”(《黄昏,穿过麻扎》)。朴素记录的时间片断、物我相通的回还往复,无可抗拒的角力与对峙,孩童般地执着与温热,延展出乡土苍茫、家园老去的情愫。“我喜欢这朝阳加热了的城市 / 喜欢一个人在人群中漫步 / 我满怀忧伤和爱意 / 把匆忙的众生注视 / 喜欢在一株青杨下默默沉思”(《醉了》)。
二伟审美格局抒写的气场,空间延展着多维的边界,其艺术解构呈现的色彩,与心理累积的沉浮息息相关。“呼吸贴着时间被织进车窗 / 我如卵石胸藏淤青和翅膀 / 你怪心照不宣 / 怪瞬息与得失”(《端午》)。从“四壁流沙”的破茧而出到地域激荡的命运征象;精神独立和灵魂束缚,让他手中的诗歌介质洐化为散文式的张力和磅礴。“人群低过草木 / 逆着光把欲望的骨头倾泻给塔里木的胡杨”(《塔里木诗章》)。
由故乡甘肃初入新疆的耳南,醇厚生动、寓意丰满的诗融汇了古典音韵和哲思之美。“有这只鸟作为凭证 / 丛林极准确地放下防备 / 以绝对感性敞开多数洞穴 / 然后邀风直入”(《慈悲》)。在篇幅的极端克制之下,他擅长以现代视角的简约集粹,不断变量的词语错位或连缀,经年古意的沧桑之感和大隐隐于市的洒脱认证,钻啄着市俗浮白的硬壳,更新着麻木的视若无睹的时间节点:“对镜无言,而镜以火焰应答 / 照此来推论,太阳便有机会平视一把椅子 / 它那炽热的一面将受到谅解”(《镜》)。
“当我在阳台浓密的树下 / 拧出浸湿衣裳的雨水/ 并在回首中望见了 / 灯光晦暗处那个漫步的身影 /仿若我的前世 / ”(《前世》)。高高在冗余生活之外的凝视,平和、散淡而从容。“你 / 白堤上大雨中奔走时的回眸一笑 / 一如身后的孤山 / 那千年中的沉默自若”(《羞于欢喜》)。栖伏于空间的景深,细雨笼罩的心境,北方的干燥在白堤、苏堤、孤山所蕴藉的千年晕染中,回眸前世的约定。
“似无轻重的叶子被风碰掉了 / 落到与书等宽的桌子上 / 另一些叶子,正在泛黄 / 这里的天空除开云,没有其他 / ”(《吹口琴的树下》)。田奕枫惯用白描式的人生寄寓,切近时空的静态和受众自行堆垒的势能。漂泊无定地归来与出走,幻象的坚定与不甘。“银河路南,春天的一树枯枝 / 是去冬的目击证物,十一点零分 / 晚班车停在他最后的站台”(《空站台里的最后一列晚班车》)。夜晚沉郁的风,机械读秒的红绿灯——个人生命际遇的方向疏离和镜头闪回之下的重复等待,无尽又无奈。
范小军——昆仑山巅的冰雪和戍守,给予的标高和险峻,造就诗人精神的挺拔和心理空间的爆发力。盆地、高原的落差,肌质与棱角的被消解、抵抗,诗行的硬朗和情感的韧度构成诗群的一个异数。“这些游荡了千年 / 战马嘶鸣的印象 / 在他的身体里,如同一场末日地震 / 沉默,孤独,祭奠…… / 绽放着——光芒 / ”(《饮水的人》)。干涸与丰沛纠结千年的塔河流域,日益加固的堤岸和跨越的一座座长桥,见证了屯垦戍边、359旅理想主义砌筑的绿洲模式和审美清样。“旧日”与“现实”的回旋冲荡,昆仑文化的共识,生态文明开掘呈现的远古余韵——“流水的神经抓住河岸的沙粒 / 河道中,小石头宽恕着波涛 / 一片绿洲渴望被带走 / 芦苇摇曳着苍茫”(《夕阳下的河流》)。
“阿拉尔是诸神频繁降临的地方 / 沙漠河流都是水的子孙 / 胡杨红柳都是神的使者 / 我们都是虔诚的众生 / ”(《阿拉尔》)。胡昌平头枕塔河的波涛,四季物候孵化了的千年古道上;抚胸致意地迎送,故纸堆里的兀兀穷年,学子们的潮来潮去——涂染了华发,殷殷嘱望的中年质朴、纯粹。“偶然瞥见河边的红柳 / 洪水消退之后依旧扎根沙滩 / 泥色纠缠绿枝和小红花 /河床足够宽阔,都留下来吧”(《偶然》)。
“山中之城的泛舟 / 我看不到仰望的远方 / 在酒水与泪水的涟漪中 / 我选择了随波逐流”(《流河》)。刘亚博的负笈西行,浸透了泪水、酒水掺杂的滋味。中原、西域苦涩辛辣的切换辗转,难舍难分。
“风沙是他命里析出的汗泽 / 羊群在他命里奔跑/ 像被风沙凝固的血液 / 他祈愿——羊群穿过河西咽喉”(《嘉峪关》)。沙蝎与荒凉为伍,蔚头州、唐王城,湮灭与新生的更迭往复,驿路驼铃裹挟的传奇,游牧惯常的飘忽无定,使“毡包随暮色一路散开、匐下 / 像一群带发修行的苦行僧 / 雪自鹰翅融化而来 / 是大漠人不朽的经文”(《云上天上》)。
“灵魂凭借文字相识 / 肉身总是羞怯 / 我们都是球茎植物 / 把稚嫩的欢喜一层一层包裹”(《神秘的引力》)。雨青的细腻,用沉默的根茎和茁壮的花蕾传递。在低徊的情感困局里,涓涓细流的潜藏在风沙的磨砺下,终将汇聚成脉象如昔的奔淌千里的内陆河:“我将与自我重逢 / 邂逅鲜花 / 冷漠无动于衷的雪山 / 以巨大的冰川 / 孕育万马奔腾的河”(《五月》)。
“风里有些什么呢 / 它们拼命地摇晃每一棵树 /从黑色的槐树到白色的杨树 / 再到滴滴答答的果树/ 问得那么急切”(《大风》)。沙海驼平实的笔触,从不急于剖白什么。他倾听万物的絮语,俯身人间的温情和悲悯。他缄默地顶破土层,在多碱的荒旱里,焕发一株株新叶:“逛巴扎,我喜欢带点土的蔬菜 / 它们令我安心 / 此外,我还喜欢带土的河流 / 比如黄河、塔里木河 / 它们都是劳动的河 / 带点土的文字,我格外喜欢”(《带土的事物》)。
“晚风吹不干手心的汗水 / 那些闪烁的灯火 / 在华北平原的大地上 / 总有一盏必定是留给我的”(《天地间铺着无数金光大道》)。卢山一以贯之的诗学地理,源自亲身的切入,中年的迫近和混血文化的双向冲撞,使他远离了空洞的惯性。从江南到疆南,近乎宿命的延伸与锻造,荒野大漠的边塞与江浙沿海千年不绝的血脉,穿透阻隔,以鲜活的物象贯通册页。坚实的质地,晾晒出乡野的倔强。“头顶的烈日像一个永不厌倦的时钟 / 命令着我的母亲率领她的晚年 / 艰难前进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母亲节》)。
“诗人是不妥协的异化生存 / 生命的敞开、洞察者,是诗歌伟大精神共时体和求真意志的发展者,是另一种火焰或升阶之书的铭写者”(陈超)。在一个语境苍白,精神自娱、血性隔绝,甚至全民同质化狂欢的时代。诗人何为?南疆诗群如破冰的河流,在天山、昆仑山的夹峙中,汇集众水,携带枯木乱石,一路向前,浩浩奔赴。愿他们的写作会与这里的塔里木河一样,成为另一种动人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