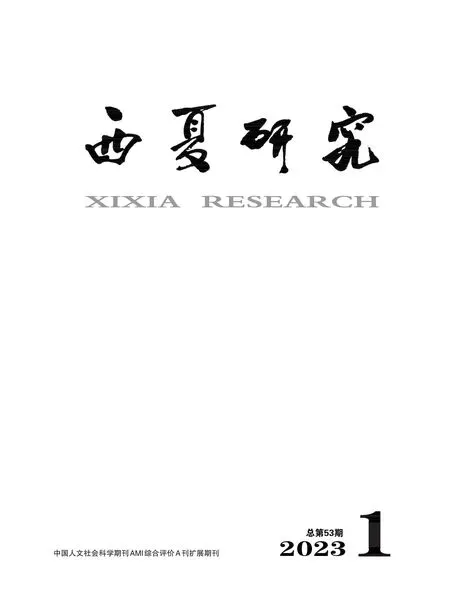从“文化异域”到“中国奥区”
——“河西”文化地理想象在中古时期的转变
2023-10-07郝凤凤
□郝凤凤
一、作为中原(华夏)民族文化想象的“河西”
自中原(华夏)文明诞生之日起,便有着自身的一套文化符号观念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处于基础地位并对人们思维和想象起到支配作用的便是“中央”与“四方”相对的符号区分——用哲学语言来说,即时空观乃是世界观的基础,而人是生活于时空观念之中的。[1]96
作为常识,“河”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特指黄河,故而与“河”相关的表示空间方位概念的“河西”“河东”“河南”“河北”“河内”“河外”“河右”等等充斥史乘的概念无不体现着以黄河为生命轴线的中原(华夏)民族的文化地理想象。时移世易,随着生产技术的逐渐进步和民族的交往与融合,“中原”“中国”乃至“华夏”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就导致像“河右”“河西”这些词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变化映射着不同的“华夷观”和“正统观”。
在“中原中心观”的视域下,以黄河为坐标的命名区域大致是围绕着仰韶文化以降,夏、商、周三代核心族群活动的中心区域,亦即黄河中下游特别是黄河中下游的拐弯处。地理“中心”观念的形成和三代核心族群活动的中心区域,也就是夏、商、周三代都城的位置有极大关联。
“河西”地区现今一般指甘肃省境内,在自然地理上指祁连山脉与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之间的呈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地带。其南与青藏高原毗连,北与蒙古高原接壤,东与黄土高原相邻,西同塔里木盆地交界,东西长千余公里,南北宽数十至百余公里不等,以“河西走廊”的名称名世。而“河西”在古代语义主要有两种。一是指黄河秦晋段之西,这个意义上的“河西”是中原地区的黄河以西。如《左传·文公十三年》:“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2]4021,《史记·秦本纪》:“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3]1648。二是指甘肃、青海段以西,亦即河西走廊乃至湟水流域。如《史记·河渠书》:“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3]1414,《汉书·霍去病传》:“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4]2492
在后一种意义上,“河西”往往伴随着族群文化方面的联想,言“河西”不但意指远在边鄙,而且常与“西戎”“氐羌”“戎狄”交互形成意向群。韩愈(768—824)在《论捕贼行赏表》中说:“两河之地,太半未收;陇右、河西,皆没戎狄。”[5]1461清朝的孙诒让也说:“然雍州西北二边,世有戎翟之患。”[6]3234这里的雍州指的就是“河西”——这来源于《尚书·禹贡》,而“河西”这一名称的边地意味其实最早亦可溯源至《尚书·禹贡》和《尔雅·释地》。
《禹贡》中说:“黑水、西河惟雍州。”《尔雅·释地》中有:“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杨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7]620之语,按“雝州”即“雍州”。李巡进一步解释说:“(雝州)其气蔽壅,受性急凶,故曰雝。雝,壅塞也。”[7]620由此,“雍州”也就是“河西”的荒凉肃杀之气便成为中原历代写书者的共同心理意象了。清人胡渭在《禹贡锥指》更进一步指出历史上“雍州(河西)”与“戎狄”的天然联系:“雍州西北二边,世有戎翟之患。自夏桀时,畎夷入居邠、岐之间……然,自雍州以正西,其西北西南两隅皆缺焉。然则梁地为羁縻之国,固不待言。而雍之西境如西倾、积石、猪野、流沙、三危、黑水之区,皆没于戎翟。”[8]299
尽管随着“中原”区域在一步步扩大,“河西”一词也由多指关陕一带逐渐演变为多指涉河西走廊这一广阔区域,但是“河西”这一中原人的地理想象与异文化的黏合一直到13世纪都没有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河西”也被称之为“河右”。如《三国志·魏志·阎温传》:“河右扰乱,隔绝不通,敦煌太守马艾卒官,府又无丞”[9]550;《魏书·列传第二十四》:“蒙逊称蕃,款著河右,若俾遐域流通,殊荒毕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诏褒慰,尚书李顺即其人也。”[10]830
西汉中期以降,随着汉武开边,中原农耕本位政权的势力全面介入河西,使得原有的文化疆界逐渐西移,河西地区也就开启了在各种政权的你来我往中逐渐但反复地“中原化”进程。由于河西地处要冲,一度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加之其地可耕可牧,适于不同生产方式的族群聚居,故各政权各族群在河西地区你方唱罢我登场。
唐及唐之前,整个“河西”即“雍州”的沿革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交代得比较清楚:
《禹贡》雍州之西界。自六国至秦,戎狄及月氏居焉。后匈奴破月氏,杀其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匈奴使休屠王及浑邪王居其地。汉武帝之讨北边,休屠、浑邪数见侵掠,单于怒,遣使责让之,二王恐见诛,乃降汉。汉得其地,遂置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昭帝又置金城一郡,谓之河西五郡,改州之雍州为凉州,五郡皆属焉。地势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间,隔绝西羌、西域,于时号为断匈奴右臂。献帝时,凉州数有乱,河西五郡去州隔远,自求别立州,于是以五郡立为雍州。魏又分雍州置凉州,领河西五郡。晋惠帝永宁元年,以张轨为刺史,持节领护羌校尉,会永嘉之乱,因保据凉州,是为前凉,至张天锡,为苻坚所灭。后十余年,又为吕光所据,是为后凉,至吕隆,为姚兴所灭。及沮渠蒙逊起兵据张掖,是为北凉,至沮渠茂虔,为后魏所灭,及太武帝,改州镇,置四军戍,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复为凉州,领武威等十郡二十县。周置总管府,隋大业三年改为武威郡,废总管。隋末丧乱,陷于寇贼,武德二年讨平李李轨,改为凉州,置河西节度使,都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八千八百匹。备羌胡。[11]1017-1018
两《唐书》则明确揭示,“河西”在唐代成为正式行政区域和军镇辖地名称。《旧唐书·地理志》:“景云二年……自以黄河以西,分为河西道。”[12]1639《新唐书·方镇表》:“(景云元年)置河西诸军州节度……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13]1861-1862
这些出自中原人士的措辞表明,从先秦至宋代,活跃在河西地方的人口多有非汉人(华夏)族群,即中原人所谓的“戎”“羌”“夷”“狄”之属。既然表示方位的“河西”一词总是和表示非汉族群的蔑称“戎”“羌”“夷”“狄”联系在一起,这大概就表明在当时习惯上沿袭着中原中心的文化地理想象模式。
直至宋代,河西在完全落入西夏后,沈括还在诗作中昂扬地表示:“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莫堰横山倒流水,从教西去作恩波!”[14]43因为当时西夏已经基本领有整个河西地区,而这一地域上遍布羌人族群,沈括不经意间将历世关于“河西”作为“文化异域”“华夏边缘”的地理想象描绘成了王朝国家之间的“民族边疆”——东则宋地多汉人,西则夏土皆羌人。
二、代指西夏或是西夏故地的“河西”
大约在同时,以“河西”代称西夏便出现了。而这比较多地体现在诗歌中。如:
仇侯能骑矍铄马,席上亦赋竞病诗。玄冬未雷苍蛇卧,玉山无年天马饥。三天荷戈对摇落,十倍乞弟亦可缚。何如万骑出河西,捕取弄兵黄口儿。
——黄庭坚《戏答仇梦得承制》[15]1310①
家声远继河西守,游宦多便岭外官。南海无波闲斗舸,北堂多暇得羞兰。忽闻常棣歌离索,应寄寒梅报好安。它日扁舟定归计,仍将犀玉付江湍。
——苏辙《送钱承制赴广东都监》[16]290
西城橐驰来驾兰,入贡美玉天可汗。萧关夜开月团团,弹筝古峡鸣哀湍。前将军,不擐甲,取大官。今将军,能抚士,尚盘桓。河西五郡兵气完,骏马跃栈无箭瘢。我嗟乘劣不受鞍,焉得乞与都人看。
——梅尧臣《寄渭州经略王龙图》[17]655
漠漠河西尘几重,年年画马亦难逢。题诗记着今朝事,同看联翩五匹龙。
——陈与义《题伯时画温溪心等贡五马》[18]455
新淬鱼肠玉似泥,将军唾手取河西。偏裨万户封龙额,部曲千金赐袅蹄。
——秦观《次韵出省马上有怀蒋颖叔》[19]474
逮至蒙元时期,以“河西”代称西夏或西夏故地便多有出现了。其中代指西夏(党项)或西夏人(党项人)的,如《黑鞑事略》中的“茶合角得之兵在回回,拔都驸马之兵在河西”[20]184,《元史·世祖本纪》“罢诸路女直、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21]118,《元史·文宗本纪》:“凡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各一人”[21]712。或以“河西”代指西夏故地,如元人马祖常(1279—1338)《河西歌效长吉体》:“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草染衣光如霞,却招瞿昙做夫婿。”[22]716《元史·王诏传》:“时方讨西夏,迓者耶律诚欲尝我,言曰:‘河西无礼,大国能容之乎?’”[21]9189
明清,乃至现今,“河西”一词的出现就更为频繁了。所不同的是,“河西”不再具有边地想象和民族边疆的意味了,从而真正成为“中国”之“奥区”。值得一提的是,成吉思汗(1162—1227)进攻西夏的时候,窝阔台(1186—1241)恰有一子出生,为志武功,取名为“河西”,转音为“合失”。后合失酗酒早亡,自此蒙古人讳言“河西”,惟称之“唐古忒”。[23]6928②
当时及后世之所以频频以“河西”代指西夏以及西夏故地,实在是由于河西地区对于西夏太过重要。
首先,元昊夺取“河西”之后,西夏才有了一定规模的人口和地理空间基础。西夏故地曾经“临广泽而带清流”[24],但是11世纪,中国北方逐渐变冷[25],夏州周边开始出现了沙漠化。[21]9129③夏州以东,是西夏与辽、宋紧张对峙的山西地区。要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只有向西发展一途,亦即先灵州,后河西,唯如此才能拥有农业生产的条件。加之,河西乃四战之地,为东西交通之要道,其可耕可牧的自然生产条件,可以承载西夏更多的人口。
其次,元昊夺取“河西”之后,曾一度垄断丝路贸易,与西域诸国、诸部族的商业往来使得西夏有了敢于同宋分庭抗礼的经济基础。西夏占据河西后,可扼要道与辽(金)、吐蕃诸部、回鹘等西域诸国进行贸易,从而摆脱对宋的贸易依赖,并且可以征收商业税。《西夏书校补》载:“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永宝’钱,与金‘正隆元宝’钱并用。金主禁之,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26]1432
再次,元昊夺取“河西”之后,农耕区和游牧区的交错在本质上支配和型塑了西夏前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策略。儒学是一整套的社会运行机制。儒家思想以及依托于儒家学说的社会运行体制必须根植于一定规模的农耕区和由此形成的农业文化。佛教在一定程度可不必一定依托于一定的经济形态。河西长期蕃汉混居,其地半耕半牧,由此形成的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长期碰撞交融。其表现形式即是游牧贵族集团和汉人贵族集团共同执政。在这一过程中,党项诸部族不断整合,蕃汉也出现交融的局面,两位梁太后的执政实质上是皇权、外戚(舅权)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表面是路线和宗教信仰的斗争,实际是农耕本位和游牧本位的互相竞争,其根源即是灵夏和河西的经济形态。
进一步说,元昊夺取“河西”之后,使得西夏成为“文化掮客”进而成为“文明的创新者”。黑水城文献的发现使得西夏时代诸多谜团的解开成为可能,诸多文献表明,西夏后期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西夏文化,特别是汉藏显密圆融的佛教文化。[27][28][29]
三、作为西域文化互动的“河西”和中国奥区的“河西”
首先,河西由于地理形态和地理位置,历来是各族群(汉、吐蕃诸部、回鹘、诸党项等)、各宗教或思想(儒、释、道、景、摩尼等)混集之地。西夏之前的河西地区或处于汉文化本位政权的边缘之地,或民族政权倏忽代换,于是造成上述状况。河西是西夏重地,由河西深入西域,进而参与了整个11—13 世纪内地文化互动。[30]金朝取代辽朝后,宋和西夏直接的交通被阻断,故西夏后期,对西夏持续进行文化输出的变成了吐蕃人(僧)和回鹘人(僧)。黑水城出土的《译经图》中绘有汉人、党项人和回鹘僧,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从西夏后期翻译和刻印佛经的规模来看,其耗资巨万,绝非仅仅依靠农业税所可以完成。而河西地区作为天然的商路,西夏依此对商业税的征收无疑为西夏后期的印经事业助力不少。而商路又天然与僧团相联系,故而河西商路的畅通又为僧团的进入和佛教思想的传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河西地区的可耕可牧是儒学、佛教在西夏交相辉映的根本原因。由于材料奇缺,要在数量上准确估计西夏或者西夏时期河西地区的人口都是不可能的,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也无法确知西夏或者西夏时期河西地区族群分布的详细信息,更遑论属于文化、信仰层面的这种模糊性概念了。但是通过黑水城文献和其他西夏时期的文献我们对有些问题还是可以管窥一二的。
再次,杰弗里·萨缪尔(Geoffrey Samuel)认为藏传佛教中萨满型修习的极为精密的体系大概是藏地对人类最重要的一种贡献”[31]8,并形象地将藏传佛教和社会的典型特征称为“文明的萨满”(Civilized Shamans)。此说是否准确暂不评论,但西夏故地的地理环境和西夏后期藏传密教的流行也确实存在一种紧密联系,即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与藏传密教的萨满性质的互动催生了藏传佛教在西夏的流行[32]61-68。吐蕃僧人恰适于填补原为传统的萨满巫师所占领的文化位置[33]5-11。西夏百姓“选择藏传佛教作为他们主要的宗教信仰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人文兴趣是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的”[34]326。河西的地理位置对于佛教传播来说,要完全优于灵夏地区,而与之相辉映的是,河西地区农耕经济的发展,使得以定居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统摄下的民间信仰在西夏也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最后,作为统治民族在人口上不占据绝对优势的“王朝”的政治文化实践,西夏统治阶层多语文并行开元明清“同文之治”的先声。随着近年来西夏语文研究的进步,学界发现西夏文记录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笼统的“西夏语”,而是至少两种语言——番语和勒尼语,“番语”为河湟一带党项人传统的通行语,“勒尼语”则是外来统治部族带入的。而西夏文的创制使得“一文记双语”,以语文来弥合族群认同问题无疑是西夏带给我们的启示。[35][36]另外,“所谓多语文的政治文化”,指在以多语文为表征的多元族群与文化的政治环境中所形成的“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以及“政治现实与文化理想”之间的相互作用。换言之,这其中包括治理思路、制度设计、具体的政策决断,以及为之提供正统性论说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同时,多语文政治文化最明显的表征便是行政语言的多元。[37]西夏时期,无论是钱币铸文[38][39]④,还是经济文书[40],乃至敕文[41][42]⑤,都有西夏文、汉文乃至藏文等多种样态,更遑论数量庞大的汉文、西夏文和藏文的佛经了。为了满足民众沟通交流的需求,甚至编写了一部通俗实用的夏汉双语字典《蕃汉合时掌中珠》。[43][44][45]夏仁宗(仁孝,1124—1193)时,西夏开设汉学、蕃学学校以教育贵族子弟,并行科举以选拔人才,甚至破天荒地尊孔子为文宣帝[46]14024-14025;[47]153-173。元人虞集在为西夏蕃汉教授斡道冲书写画像赞时追述:“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48]诚如《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序言中所说:“兼番汉文字者,论末则殊,考本则同。何则?先圣后圣,其揆未尝不一故也。然则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43]5-6
可以说,西夏不据有河西,则无法成为一个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王朝”。相比于沙陀贵族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王朝,西夏的政治整合难度要大得多,而西夏在整合境内多文化多族群的政治实践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
正是由于西夏时期对河西地区的文化整合和政治整合,元朝之后,河西再也不具有“文化异域”的想象和“民族边疆”的现实基础了,从而最终成为华夏之根蒂和中国之奥区。
注释:
①《黄庭坚诗集注》曰:“西夏自陷永乐城后,为边患。及秉常卒,子乾顺立。元祐二年,遣使册乾顺,夏人以地届为词,不入谢。且犯泾原镇,戎军又侵德靖砦,又犯塞门砦。‘黄口儿’谓乾顺也。”[15]
②洪钧《元史译文征补·海都补传》:“海都,太祖诸孙,合失子。太祖征西夏,合失生。西夏为河西地,蒙古称河西音似‘合失’,转音为‘合申’。名以合失,志武功也。合失嗜酒早卒,太宗痛之。自此蒙古人讳言河西,惟称唐古忒(亦作‘唐兀惕’‘唐兀’)。”(洪钧《元史译文征补》,转引自田虎《元史译文征补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页)。
③《宋史·宋琪传》:“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从银、夏至青、白两池,地唯沙碛,俗谓平夏。”[46]9129
④面文为西夏文的钱币已经发现有五种,分别是“福圣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以及“天庆宝钱”。这五种钱币正面为西夏文,背面为光背,形制都为小平铜钱,非常少见,属于珍稀的古钱币。汉字体的西夏钱币按照年号分已经发现有八种,这些钱币的书体均为楷书,分别为“大安”“大德”“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以及“光定”。
⑤比如刻于“黑水河桥敕碑”的《告黑水河诸神敕》便是夏仁宗仁孝为纪念黑水河桥的建成和祈求神灵保佑民众而撰写的敕文,此碑便是一侧为汉文,一侧为藏文[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