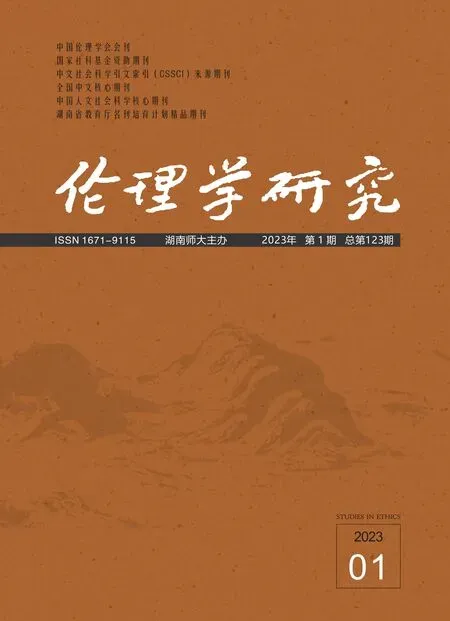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价值与事实观
2023-10-07龚群
龚 群
价值与事实问题是现代哲学提出的一个哲学基本问题,然而,这一问题有着久远的思想史的渊源。价值与事实二分,在这两者之间首次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人是柏拉图。价值世界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事实世界或客观现象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样一个二分法对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把握有着深远影响,而且对于人类的价值思维同样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不仅建构了一个与现象界相区分的理念价值世界,同时也以更大的篇幅建构了一个理想的社会价值世界,这就是他的乌托邦。乌托邦与现实的政治社会相分离,同时也是价值与事实的二分。这样一种对于整体世界和人类世界的价值与事实二分性思考,十分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思维。这两者都是人类对于价值世界与客观事实世界认知把握的理论方法,对于价值哲学的研究来说有着重要意义。
一、理念世界
柏拉图在《理想国》(又译为“国家篇”)里首次提出理念(idea、eidos,或译为形式、相等)①idea、edios 这两个词在柏拉图那里经常混用,也往往可以被不加区别地对待,但却难以用一个中文词来准确地翻译,理念、形式或相都是目前中文界通行的译法,不过,还有一些其他译法,如王太庆就译为“通式”。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分,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早于《国家篇》的《斐多篇》中,柏拉图对于理念这一概念给予了诸多探讨,但他并没有就此提出对于整个世界或宇宙图景整体意义的观点。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二分,是柏拉图在“理念”(或形式、相)这一概念思考基础上对把握这个世界整体的本体论思考。这一本体论思考,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价值本体的思考,即柏拉图把“理念”提升到世界价值本体的高度来重新观照整个世界。在柏拉图看来,这个世界是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截然二分的二重世界:理念世界在上,而现象世界在下。人类不可能用感官来感知理念世界,而只能凭感官来感知现象世界。一个我们的感觉经验无法感知的世界是否真正存在?柏拉图通过影像说、模仿(汪子嵩等人编著的《希腊哲学史》用的概念是“摹仿”)说等说法来证明这样一个世界不仅存在,而且是我们的感觉世界存在的依据。同时,柏拉图认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感觉世界,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价值世界,真实的价值世界超越于这个感觉世界,在此之上的理念世界才是真实存在的世界。就人类经验而言,只有感性现象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柏拉图在这个现象世界之外再造一个超验的价值世界,将一个无处存在的世界说成是真实的价值世界,而将一个真实的客观世界说成是一个不真实的虚假的世界。这一唯心世界观反映了人类对于完善理想世界追求的人类精神和心灵状态。因而柏拉图实际是在构想一个人类理想的价值世界。
在柏拉图看来,我们感官所感知的世界是变动不居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夏天所看到的枝叶茂盛的大树,到了冬天,则成了一幅光秃秃在寒风中哀号的残败景象。因而我们所见的都不是真实的。柏拉图继承巴门尼德的存在是永恒不变的存在的理念,把赫拉克利特的一切都在流变中的观念视为对于存在的虚假描述。在《斐多篇》中,柏拉图提出,“等”本身、美本身、是本身,理念或形式是灵魂要力图把握的,它们是单一的、同一的,不是组合而成的,而具体事物是组合而成的。理念或形式是不变的,具体事物是经常变化的。理念或形式是不可以用感官来感知的,具体事物是可以用感官来感知的。理念或形式是纯粹的、不变的,而具体事物是不纯粹的,是要毁灭的[1](236-239)。人们以感官所认知把握的是“意见”,只有摆脱感性而以理性把握的理念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这也就是巴门尼德所说的认识把握存在的两条道路,即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对立[2](90-96)。
《斐多篇》中的理念或形式,没有超出巴门尼德的存在。《国家篇》则把理念或形式(相)与现象界进行区分,提出两个世界的概念。这个理念或形式世界并不是单一的存在形式,而是多重样式的形式或理念。理念世界为数学理念以及其他理念构成了这个理念世界。与以往对理念的讨论不同,柏拉图将伦理学的“善”理念置于所有理念(形式、相)的最高地位上。在所有的理念中,善的理念是最高的理念。不过,如果结合柏拉图在《会饮篇》中的讨论,还有一个理念是在最高位置上,这就是“美”的理念或美本身。柏拉图在《国家篇》的讨论中,也提到了美本身和善本身的问题。他认为这与美的具体事物或善的东西都不同,是另一类认知对象。善与美和其他理念或形式、相的差别不仅是价值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是空间上的差别。在柏拉图看来,世界是二分性的,善与美的理念在理念世界,而作为善与美的摹仿或影像的具体事物在现象世界。然而,我们知道,“善”首先是希腊哲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其次才是柏拉图的理念论中最高的理念。这一最高理念的地位,也就决定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说是一价值学说,是关于世界的价值学说,即把善价值置于最高地位,从而也就使得柏拉图的世界本体论成了在世界本体意义上的价值论。对善是什么,柏拉图确实没有讨论,但在柏拉图的伦理学中,它的地位高于其他所有的伦理学概念,高于正义、勇敢、理智(智慧)这些在他的伦理学体系中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在本体论和价值论意义上,这些伦理学概念所关涉的是人世间的伦理问题,而善本身则是关涉到理念世界的本体存在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专门有一段话讲到柏拉图的理念(形式、相)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关系,他说:“柏拉图接受苏格拉底的教义,但是认为不应将它应用在感性事物上,而是只能应用于另一类事物。理由是:可感觉的事物总是在变动中,所以共同的普遍定义不能是任何感性事物的定义。这另一类事物他就叫做理念(idea,形式或相),他说感性事物是依靠它们并以它们为名,众多的事物是由分有和他们同名的‘理念’而存在的。”[3](987b)亚里士多德说,柏拉图提出了现象世界对理念世界的“分有”说,并在其前期的《美诺篇》和《斐多篇》中主张具体事物分有理念。不过,在《国家篇》第10 卷中,柏拉图则明确提出了“模仿”说,并且,在讨论哲学家的第七卷中,也提出了“影像”说。这三种说法都是柏拉图对于理念价值世界与感性现象世界关系的说法。“分有”说则提出现象世界中有理念世界的理念,只是它是分有而已,而模仿说和影像说则完全否认了这样一种内在关系,只是认为两者之间一个是真(是)有,另一个是假(是)有。柏拉图完全改变了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们从物质世界本身来寻找物质自然世界构成的基质的努力,转向考虑存在着一个超自然的存有或超验的价值本体世界,我们感官所感知的这个自然世界则是由于模仿了理念世界的理念或仅仅是它的影像而存在。
柏拉图以“洞穴寓言”来说明我们所处的世界与真实的价值世界的区别。他叙述了一个这样的寓言:有群人一出生就住在一个洞穴里,从来没有到过这个洞穴之外,而且这些人被锁链锁着,背对着洞口,因而不可能转过身来看望洞口。在他们身后有一堵高墙,高墙外有堆火在燃烧着,有人举着木偶在晃动,于是这些洞穴人看到墙上木偶的影像晃动,以为是外面有人在走动,他们并不知道那是影像在晃动。多少年后,洞穴里有个人挣脱了锁链,走到了洞穴之外,他发现他们在洞穴里所见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影像。然而,当他走出洞口,外面的阳光他并不适应,等他适应之后,他才发现太阳的光辉照耀着大地,然而,当他试着仰望太阳,他的眼睛则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太阳光会把他的眼睛灼伤。他来到外面真实的世界,感觉最大的冲击是对他长期以来所形成的观念的冲击,即以往在洞穴里所形成的关于世界的观念是虚假的,真实的世界不是那样的世界。柏拉图提出,如果这个人要回到洞穴里,告诉其他人,你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虚假的,都是谎言,他会是怎样的结果?洞穴里的人会认为他发疯了,会把他处死。柏拉图的这个寓言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真理之光来自超验的天上,而人是不可能以自己的感觉感官来感知的,同时,我们处在感觉世界,就如同处于洞穴中的那些人,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真实的世界是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真实的价值世界,这就是要走出洞穴,但走出洞穴,并非意味着用自己的感官去感知,而是要用理性来把握。并且,人并不会永远满足自己生活于洞穴之中、生活于谎言之中,而是要追求对这个价值世界的真理的把握。
二、与现象世界的关系及其认知
柏拉图认为,将以善为最高理念的理念世界看成一个价值世界,并不是一个虚构,而是一个实在,并且真理与实在同在。与我们把感觉世界看成唯一真实的世界相反,柏拉图认为这只是一个由于模仿了理念价值世界而才存在的变动不居的世界,模仿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并且远没有真实世界那么完美。柏拉图说它只是真实的理念价值世界的影像,如同阳光下物体在水中的倒影一样。因而我们对于感觉世界的感觉所获得的只是意见,而只有对理念价值世界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有理智或智慧表明人的视域从感觉世界转向理念世界,并把握到理念世界的真理,从而有了理智或智慧。人的眼睛只能注视可感知的现象世界的事物,而只有人的灵魂才能关注理念世界的事物。柏拉图说:“人的灵魂就好像眼睛一样。当他注视被真理与实在所照耀的对象时,它便能知道它们了解它们,显然是有了理智。但是,当它转而去看那暗淡的生灭世界时,它便只有意见了,模糊起来了,只有变动不定的意见了,又显得好像是没有理智了。”[4](266-267)柏拉图通过知识论来论证善的价值本体界与感觉世界的二分,在他看来,感觉世界只是因为分有或模仿了理念世界而才存在,柏拉图提出又一个概念“天上的床”,天上的床只有一张,而所有地下无数张各式各样的床都可被称为床,在于所有这些床在能够被我们说成床之前,在我们的心目中都有了一个“天上的床”的概念,从而能够将各种各样并不完美的床说成是“床”。然而,任何模仿物与真正原本的事物相比,都不可能是十分完美的,因此,我们通过感觉现象界的事物所得到的认知,都并不是真正的知识,而只是意见。意见不等于真知,真知在于对价值本体世界的认知。善的理念、知识与真理,就这三者的关系而言,善的理念给知识的对象以真理,同时又给知识的主体以知识的能力。善的理念作为本体存在,是真理与知识的原因,在这二者之上,真理与知识是关于善的理念的真理与知识,但并不能认为真理与知识和善的价值本体同等重要。在价值意义上,善的理念具有根本的意义,是真理与知识之源。善的理念从存在论意义上看,是所有存在物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同时也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可认知世界的根源。
柏拉图的立论起点是现象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暂在性的、易变和易朽的,但人并不满足于现象世界没有永恒和完美价值的一切,而价值追求即追求那永恒不变的存在和完美(完善)是人类精神最深的动因。在《会饮篇》中,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女祭司狄奥提玛(Diotima)说法给我们提供了人类精神一步步地从具体的、暂在性美的追求到永恒的美本身追求的上升过程。《会饮篇》是一部讨论爱情的可读性很强的短篇著作。在众多智者大量讨论了什么是爱情之后,苏格拉底以狄奥提玛的说法指出,大家都同意人类对爱的追求是对美的追求,任何一个坠入爱河中的人,都会爱上某个具体的美的身体,而“他必须思考身体之美如何与其他方面的美相联系,他会明白,如果他过分沉醉于形体之美,就会荒谬地否认一切形体的美都是同一种美。到了这一步,他就会设定自己应当爱一切美的形体,而把自己对某个对象的爱限制在恰当的分寸上,视为渺小的、不重要的”[5](253)。不过,就我们关于爱情的一般观点而言,狄奥提玛的这一观点可被视为泛爱论,而不是爱情的专一。但这仅是柏拉图的爱情论的第一步。第二步,“他应该学会把心灵美看得比形体美更为珍贵,如果遇见一个美的心灵,纵然他在形体上不美,也会爱上他,并且珍视这种爱情……经过心灵之美,他会被进一步导向思考法律和体制之美”[5](253)。第三步,“他的注意力应当从体制被导向各种知识,使他能看到各种知识之美”[5](253)。当我们的爱达到这样的境界时,柏拉图认为,我们就不会把爱专注于某一个美的对象,如某个少年,某个男人①古希腊盛行同性恋。——笔者注或某个体制。此时他会用自己的双眼来观照整个美的汪洋大海,而获得最崇高的思想,即哲学上的丰收,也就是关于美的知识或对美本身是什么的知识。柏拉图说:“就这样,当原先那种对美少年的爱引导着我们的候选人通过内心的观照到达那种普世之爱时,他就已经接近终极启示了。这是他被引导或接近和进入爱的圣地的唯一道路。从个别的美开始探求一般的美,他一定能找到登天之梯,一步步上升——也就是说,从一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形体,从两个美的形体到所有美的形体,从形体之美到体制之美,从体制之美到知识之美,最后再从知识之美进到仅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最终明白什么是美。”[5](254)人类的爱情是对美的追求,而对美的追求只有上升到对于美本身的认知把握才可说达到了对于美的认知把握。在柏拉图看来,这是最高的爱的境界,即上升到抽象的美本身的真理性知识层次,我们人类的爱才真正进入理念世界的领域,从而认识到,现象世界的一切美的事物,都是暂在性的,而只有美的理念才是永恒存在的。依柏拉图的模仿说,天上的美本身是地上所有具体的美的事物的摹本,它是地上所有美的事物的模型,而地上所有具体的美的事物与真正的美本身比较都具有某种不完美性。科尔斯戈德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相信,价值比经验事实更加实在,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实在界正是价值自身。他们认为这个经验世界中的事物,就其本性而言,都试图成为比现状更加完美的东西。”[6](3)然而,正是因为有完美的价值世界才有这个不完美的现象世界,人居住在这个不完美的现象世界,但人的灵魂则是要不断向上攀升,直到那美与善的理念本体价值世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则设置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的心灵或灵魂的训练过程,即数学的训练,从而使得哲学家能够有真正的理智,有了这样的理智才可能达到理解和领悟美与善的理念的智慧。人栖居于感性世界,但柏拉图认为人的理性能力以及理智训练使人能够领悟到那个价值世界的存在,使人类最有哲学智慧的心灵在理念世界的高空来鸟瞰和统治这个世界。因此,柏拉图不仅预设了一个与现实事实的现象世界相分离并高于现象世界的价值理念世界,同时,也设置了一个关键性因素——可以从现象界上升到价值理念界的特殊人物:哲学家王。在柏拉图看来,如果现象界的人类王国能够有这样的人物来统治,则就有可能以天上的理念来统治,从而实现地上的价值理念王国。然而,他认为这样的机会是十分稀少的。那么,地上的理想王国是怎样的状况呢?
三、正义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
柏拉图的《理想国》本身,所建构的就是一个社会乌托邦或政治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在柏拉图看来,是真正具有正义价值的人类理想之地。
《理想国》对人类理想城邦或正义理想价值所系之地的设想,是通过以伦理学的基本要素为核心,同时以他所理解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成功的要素为辅助来进行的。他所建构的这个正义之邦,就其核心要素而言,就是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基本德性。换言之,柏拉图以其理想伦理价值为核心,建构一个理想的城邦。它是一个以智慧、勇敢和节制德性为主导的城邦,智慧德性体现为以哲学家为王,勇敢德性体现为护卫者都具有这一品德,节制为这个城邦所有成员都需要具备,但主要是下层普遍劳动者应当具有的德性。当所有这三种德性都在不同的社会阶层起作用时,这样的国家就是正义的。
在这三种德性中,智慧的德性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个城邦的统治者如何才能具有智慧的德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两卷的篇幅详细地进行了讨论。首先,要在这个城邦中选拔那些具有哲学家天赋的天才儿童进行培养[4](244)。在柏拉图看来,“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是哲学家的天赋”[4](244)。真正具有哲学家天赋同时又能坚守哲学的人少之又少。其次,是要对具有哲学家天赋的人进行算术、几何等数学方面的严格思维训练。哲学家的认知就是要脱离可变世界而使自己的思维上升到抽象层次即理念世界,从而能够把握善的理念这样的永恒真知。以柏拉图的话来说,也就是“这样地看见了善本身的时候,他们得用它作为原型,管理好国家”[4](309)。哲学家的智慧也就是能够获得理念世界的最高善的理念知识的智慧,并且,他能够以这样的知识来治理国家。然而,柏拉图认为,现行的政治制度没有一个适合于哲学家来进行统治。他说:“一个也没有,现行的政治制度我所以怨它们,正是因为其中没有一种是适合哲学本性的。哲学的本性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而堕落变质的……哲学如果能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那时可以看得明白,哲学确实是神物,而其他一切,无论天赋还是学习和工作,都不过是人事。”[4](248)柏拉图这样一种悲观的说法表明了他对现实政治的深深失望。
那么,这样理想的伦理价值是怎么来的?首先,我们看看柏拉图关于统治者与护卫者的德性问题。他并不认为理想人是天生有德性的人,但他也许像中国的孟子那样,认可人有先天的德性基础,这在关于统治者的智慧德性的讨论中表明得很清楚,他认为具有哲学智慧的天才是有的,但十分稀少。而且,他认为,一旦发现这样的天才,就需要进一步培养,要不,社会环境的腐化可能会使他的天才智慧退化。然而,护卫者的主要德性勇敢,在柏拉图的文本中则没有看到,柏拉图不认为他们的勇敢是天生的(但他认为哲学家可能会有这种天赋)。柏拉图以大量篇幅讨论了对护卫者勇敢德性的培养与训练,以及如何确保国家内部(主要是护卫者)的纯洁问题。就勇敢的德性培育而言,柏拉图强调的是从小进行的体育训练,柏拉图意识到,军人勇敢的德性与身体健康或体魄健壮有着内在关系。与此同时,对于护卫者或城邦国家的保卫者来说,柏拉图讨论更多的,是有一定权势的人(如护卫者)如何才能不腐败的问题。在柏拉图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个人的私人利益有可能过分膨胀,从而攫取非分的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从而与国家利益或国家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分为穷人和富人两个相互敌对的部分,那么,这个国家就内部分裂了,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什么比闹分裂化一为多更恶的吗?”[4](197)在柏拉图看来,如果“一个国家最大多数的人,对同样的东西,能够同样地说‘我的’‘非我的’,这个国家就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4](197)。同样说“我的”,柏拉图的意思是所有这些社会财物都是公共的,在公共的意义上,又都是所有人共同所有的。那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其次,柏拉图提出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设想,这个设想就是:消灭家庭。其做法是:首先,所有成年男女可以与任何异性同居,除了自己所出或自己的父母之外①不过,柏拉图在行文中有时也用到对男子与某一女子结婚的叙述,表明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还不彻底。;任何婴儿一出生就会被社会抱养(公共抚养),而不是留在父母身边。柏拉图说:“这就是我们城邦里护卫者中间妇女儿童公有的做法。这个做法和我们政治制度的其余部分是一致的,而且是最好最好的做法。”[4](196)这还不够,柏拉图认为,这还不足以解决私人财产问题,最后就是建立公共财产制度,即所有人都在公共食堂就餐以及在公共仓库领取自己的所需物。柏拉图说:“我们的护卫者不应该有私人的房屋、土地以及其他私人财产。”[4](200)他还说:“这些女人应归这些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同样地,儿童也都公有,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4](190)在他看来,如果“各人把他能从公家弄到的东西拖到自己家里去,把妇女儿童看作私产”[4](201),这样的国家必然是四分五裂的。柏拉图正确地认识到了,私有制实际上就是家庭所有制,消灭了家庭同时实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公有或公共所有,也就消灭了私有制的最后藏身之地。这样一个原始共产主义式的财产制度,不仅没有腐败,同时也没有了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从而也就是所有公民没有利益冲突的利益共同体,这也是最纯洁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也就最能实现社会正义。这是柏拉图在思考何为正义的国家的问题上对于社会结构以及财产结构的考量。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他在设计城邦三阶层构成上的意义。
最后,对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商人、陶工、农民等的德性问题,柏拉图也给予了关注。在柏拉图看来,一个理想正义的国家在社会秩序上,最重要的是使不同阶层的人能够处于自己的地位而安分守己。在柏拉图看来,最不容易安分守己的阶层就是劳动者阶层。柏拉图提出了心理服从的问题,其方法之一就是宣传“高贵的谎言”。然后是道德服从,即强调节制的德性。节制的德性也就是抵制自己的非分的欲望,而最大的非分欲望就是不安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安于自己的职分。有了节制的德性,人们就不会去想非分的事,从而也就会自觉抵制蛊惑或怂恿而不犯上作乱。由于普通劳动者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的欲望实现得最少或最不容易得到满足,因而最需要节制的德性来约束和规范自己。柏拉图说:“当城邦里的三种自然的人各做各的事时,城邦被认为是正义的。并且,城邦也由于这三种人的其他某些情感和性格而被认为是有节制的、勇敢的和智慧的。”[4](157)实际上不仅仅是“各做各的事”,而且是自觉自愿地去做,才是柏拉图的本意。
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城邦为上述三种主要职业和三种主要德性的构想,提出不同职业上的人应有不同的德性。当这些德性都发挥作用时,这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因此,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价值意义上的理想城邦,他希望通过德性在不同的阶层和不同职位上的人们发挥其尽有功能,在城邦共同体中实现其价值理想。这类似于中国以德治国的理念。不过,以德治国理念仅仅是一种理念,而柏拉图则是将其具体化为一种制度设计。为此,柏拉图还设计了一些关键性的价值要件,如提出哲学家王的理想、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家庭,以及他的“高贵谎言”下的普遍劳动者的普遍节制德性,都并不是真实的价值存在,从而表明这样一种在城邦共同体意义上的价值理想不过是一种价值想象。对于这样一种价值想象或价值理想,无疑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提出许多批评,但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他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理想价值城邦并不是在现实中存在着的。柏拉图以德性为中心,以城邦制度设计为路径,类似于理念世界,为人类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试验。可以说,柏拉图整个城邦设计实际上是他心中的人类理念世界,即一个完善的乌托邦价值世界。在柏拉图看来,这一人类社会或人类存在的价值理想世界,与他所提出的知识论意义上的本体理念世界的存在一样,都是在人类的心灵之中而可以把握的。
这样一个完善的价值世界实际上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既然这样一个理想的价值城邦是在现实中不存在的,那么,它具有什么作用与意义呢?柏拉图认为,它可以作为价值标准和价值尺度来衡量现实的国家政体。这再一次使我们认识到,柏拉图再一次运用了价值与事实的二分法来构建其社会理论。类似于理念世界是这个世界的真知或真理的来源,理想城邦同样也是现实世界中的那些城邦的真理标准和价值尺度。类似于从天上的理念世界下降到现象世界,柏拉图也从理想的价值城邦下降到现实城邦。他把希腊的主要政体分为四类,或四种政治制度。这四种政体的排序是从最接近理想价值政体(理想城邦)再一一下降到离理想政体最远的政体。离正义理想政体最近的是斯巴达式的荣誉政体,其次是寡头政体,再次是民主政体,最后是僭主政体。在僭主政体中,僭主有着专断的权力,有着永远无法满足的无穷无尽的欲望,而所有其他人都落入僭主的最严酷、最痛苦的奴役之中。从对这四种现实政体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柏拉图认为现实政治并不体现真正的政治价值或理想正义的价值。但柏拉图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从现实的不理想的事实状态走向理想的价值状态。或者说,柏拉图建构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价值理想。
柏拉图具有认知意义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以及政治社会意义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当看到,这两者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的。前一个二分法为后一个二分法提供了认识论上的依据,而后一个二分法则再次强化了前一个二分法。不过,就认知意义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而言,要等到18 世纪的休谟才继续推进了这一二分法。对于休谟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问题可能需专文讨论,我们重点说一下在政治领域中的长远影响。价值理想与经验事实二分的方法对于人类政治思想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1516 年,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就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蓝本,为人类重新设计了一个理想的价值乌托邦,莫尔这本书的书名就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乌托邦》的第一部分,就是对莫尔当时的社会真实现状的写照,而第二部分就是他所提出的“理想盛世”的乌托邦。他将这两者对照起来,表现出了一个鲜明的柏拉图式的理想价值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同。莫尔又是近代以来第一个系统地提出消灭私有制、财产公有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尔后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如康帕内拉、安德里亚、马布利、傅立叶、巴贝夫、欧文等人也都体现了柏拉图的这种乌托邦精神。不过,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与柏拉图不同的是,在这些理想价值与经验事实二分的思想家看来,人类的终极目的就是实现那真正美好的价值乌托邦,人类本身是带着真与善的美好理想前行的。这一过程可能有无数的艰难险阻,但永远不可能让人类失去对价值之地的期待。换言之,他们并不仅仅是把理想价值和理想价值目标看作一个批判现实事实的尺度,而是同时也把它作为人类心灵所期盼之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承认这些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宝贵贡献,也指出他们的空想性,正是在他们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将空想变为科学,从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价值与事实的意义上,柏拉图为我们提供了认知经验现象世界和客观人类政治社会的一种二分性思维方法。人类的理性能力总是能够超越现实,或从不完美或不完满的现实中提升出价值理想,并把这样一种价值理想作为对现实的观照。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人类自由之谜或人类存在之谜。但柏拉图的问题在于把人类理性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颠倒过来,他认为理念世界是真正存在的客观实在,而我们认为只有经验现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实在。实际上,亚里士多德就将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的“理念”或“形式”,下降到现象的客观世界,而将柏拉图的理念或形式改变为客观现象世界或物质世界的本质要素,与物质的质料结合,形成不同种类和无限个体存在的客观世界。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可知,把形式(理念)作为客观现实世界中所有事物存在的本质要素,体现了柏拉图将理念作为根本价值的精粹。但我们认为,我们也不需要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理念世界的价值下降到现实中,而是从现实中提升价值理想,把现实中的潜能变为更美好的现实,从而实现人类更美好的未来。把人类政治社会领域里的理想追求作为一种乌托邦建构,应当看到的是人类思想中有着长久生命力的追求方向。不过,人类价值乌托邦的方案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变化。柏拉图的价值乌托邦的粗陋性由前述内容我们已知,但柏拉图所思考的问题是深刻的。他所提出的消灭私有制的构思得到了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回应,并成为社会运动的伟大而具体的方案,优秀的人类子孙为此前赴后继。
总的来看,现代人生活在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的价值乌托邦精神之下,不过具体形态有所改变。哈贝马斯认为,自18 世纪兴起而直至20 世纪中叶的人类乌托邦精神是以“劳动乌托邦”为代表的,20 世纪后期,劳动乌托邦在历史变动中呈现消退景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告别了乌托邦。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如同生活在一片沙漠之中,而乌托邦就是人类精神的绿洲。如果乌托邦这块绿洲在沙漠中干枯,展现出的就是一片平庸不堪和绝望无计的荒漠。萨特也曾谈到,人总是带着希望生活的,如没有希望也就只有绝望。不单个人如此,人类整体也如此。哈贝马斯说:“时代精神从两种相反的,但也互相渗透和彼此相需的思想运动获得推动力,或者说,时代精神因历史的思想和乌托邦的思想两者碰击而得到火种。”[7](88)哈贝马斯认为,乌托邦力量向历史意识进行渗透,造就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近代以来的那种时代精神的特征。现代精神正是从乌托邦之火中得到火种。乌托邦体现了人类的精神之火,承载着人类的希望。不过,以体现人类价值追求希望而出现的种种乌托邦,也可能有冒充为真正价值的那种伪品,当年希特勒就蛊惑德国人为他的法西斯卖命。沉痛的历史教训给我们以警醒,如波普就从柏拉图所建构的乌托邦中看到了专制主义。任何一个人的乌托邦只能依据那个时代以及他本人的思想背景来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否定乌托邦本身。不论如何,人类精神需要价值乌托邦。当柏拉图认为所有的现存希腊政体都远离正义价值时,他并没有因为对现实的判断而放弃人类的希望。哈贝马斯所说的18 世纪以来的劳动乌托邦之火还在燃烧,这个世纪人类是否还有新的价值寄托?历史在前行中,价值乌托邦总是具有引领经验世界的意义与功能。因此,价值与事实的相对区分,也许是人类永恒精神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