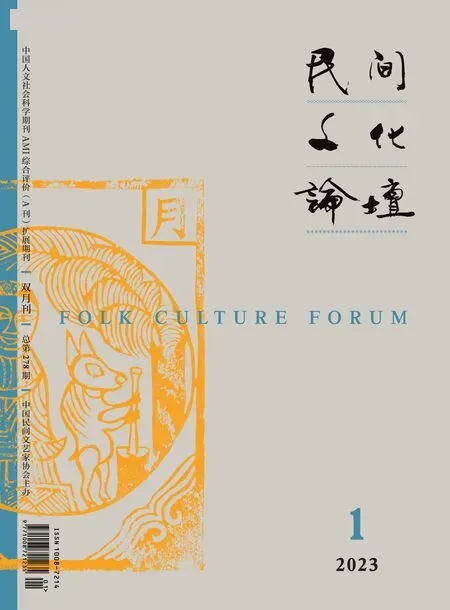交错的自我形象与刻写的身体
—— 以Coser的身体实践为个案
2023-10-06张淇源
张淇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民俗学界出现了“朝向当下”的学术转向,学者们不仅仅重视文献考据,他们还关注到了实践主体的主观感受。描摹日常生活的民族志,以及口述史、个人叙事等强调个体鲜活生命的书写形式纷纷涌现出来。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演进,民俗之“俗”逐渐从人们熟识的村落社会移植到了个体联系更加弥散的城市当中,从可感的现实世界挪移到了虚拟社区内部。“俗”的内核和形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者们也开始重新思考并修正“民”的基本定义。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指出,民俗学界关于“民”这一学科元问题,可以从四个维度思考:“第一,‘民’在当下意味着什么?第二,当下之‘民’生活在哪里?第三,‘民’又是如何生活的?第四,民俗之‘民’指向的是个人而非集体,又意味着什么?”①[德]沃尔夫冈•卡舒巴:《民俗学在今天应该意味着什么?——欧洲经验与视角》,彭牧译,《民俗研究》, 2011年第2期。在“重视语境”“关注日常生活世界”等学术取向的影响下,学者们也不遗余力地对青年亚文化群体进行了“深描”与“热描”,将他们从鲜为人知的角落推向了公众的视野当中,这恰恰是民俗学一以贯之的旨趣。刘绍华对凉山利姆乡的吸食海洛因青年群体的观照,发现了盗窃、吸毒和坐牢是这些青年们动荡的都市生活经验,这些经验见证着他们的青春悸动。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些“青春经验”也成为标识他们成年与否的重要标志。②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覃奕则聚焦于青年迷群中较为显著的角色扮演现象,他们因“爱”入圈,因“趣缘”联结,在身体的模仿实践中为自恋提供了排遣的路径,也通过社团活动拼凑出集体记忆的图谱。他们看似桀骜不羁,却又极度渴望自我的价值得到肯定与认可。③覃奕:《民俗志写作方法的新尝试——以书写漫迷群体的cosplay实践为例》,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4年。
在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内部,青年亚文化凝聚成一套独特的内部语汇体系。“梗”构成了“玩梗者”共同的身份符码,他们有着与外界截然不同的“共享知识、交流习惯与群体认同方式”④张倩怡:《“梗”与“玩梗”——亚文化群体的交流实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8年。,同时玩梗者们又保持着高度的自反性。祝鹏程注意到,“梗”并非陌生的网络代码,它可以将严肃的神话人物作为叙事主干,消解了神话的神圣性。这时候的“神话”成为了个体调侃的重要资源,这一过程也重构了神话传统。⑤祝鹏程:《“神话段子”:互联网中的传统重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0世纪末期,美国民俗学界兴起了将身体视为研究取径的热潮。据彭牧在《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一文的梳理,身体民俗大致存在着两条研究路径,第一条路径受到了福柯的话语分析、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关注身体象征与社会的影响,探寻社会文化、权力话语如何刻写在身体这一媒介之上,身体的背后交织着复杂的权力博弈网络,也折射出社会主流审美话语的阴翳;第二条取径则“沿着马歇尔•莫斯(Marcel Mauss)‘身体技术’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这一脉络,关注身体的经验、能力和知识。”①彭牧:《民俗与身体——美国民俗学的身体研究》,《民俗研究》,2010年第3期。自我形象(self-image)是身体民俗学中的关键术语,它根植于西方哲学关于灵肉关系的讨论,强调作为主体的“民”并不是机械化的存在,个体对自我存在着复杂的认知状态。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个体会在这些交叠的自我形象中有意识地呈现或隐匿。尤其是在当下,虚拟与现实的边界互相浑融,个体往往会将虚拟世界中扮演的角色等同于现实,进而在现实空间中再现这一虚拟形象。对他们而言,复原虚拟形象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形象呈现、抉择的文化苦旅。
“角色扮演”是指对动漫、游戏、影视以及轻小说等作品中的角色、人物进行扮演的一种次文化衍生活动。从事这一扮演活动的主体,通常被称为Coser。
角色扮演对玩家的吸引力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满足了玩家对另类人生体验的猎奇感、新鲜感。通过角色扮演,玩家可以体验另一个人的人生,角色本身蕴含着希望、奋斗等特质。通过扮演,玩家觉得自己似乎拥有了这些特质,并获得了角色身上附着的希望。其次,Coser圈为玩家们筑造了一座可以逃避现实的城堡,他们在圈内与圈外呈现出巨大差异。在Coser圈外,在社交方面屡屡碰壁,在家长看来,子婴是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内敛幼稚的女孩,与他人正常交流时都结结巴巴。但在Coser圈内,她却能井井有条地处理好与其他Coser的人际关系,Coser圈给予了她安全感——二次元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标签化的世界,Coser只要循着特定标签,按照它对应的行动逻辑处事即可。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你所接触的人,甚至是自己本身都是复杂的。在现实中游荡的我们,扮演着社会交托给我们的角色,切换着不同的身份,久而久之,我们都遗忘了“我们是谁”:
二次元这种标签化世界给了我一种轻松感,我只要按照这个标签的人设行动就一定不会出错,甚至大家还会认可你。但是三次元世界太复杂了,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每次到一个陌生场合面对一个陌生人,我都要纠结到底要展示哪一面的性格,我要如何说话,如何跟人相处,但只有在Cosplay时,我才觉得不必去想这些复杂的问题。②访谈对象:乌拉拉(化名),女,2018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1月25日,访谈地点:北师大新乐群四楼。
一、身体知识的习得与内化
从空怀热爱之心的二次元爱好者,到一名资深的Coser其实需要历经漫长的蜕变。而要想实现这种蜕变,唯有重复。“重复”是资深Coser引以为傲的经验。通过单调的实践和操演,他们实现了从二次元爱好者到Coser的身份转换。而对Coser身份的认同,来源于圈子内部的化妆、眼神训练以及平面拍摄、舞台表演等一系列复杂的身体知识的习得与内化。
(一)还原:Cosplay的评价标准
评价Coser水平高低的标准在于角色的还原度。在平面党①平面党:通过平面图像的形式来展现角色。看来,现实中Coser所出的片子和虚拟游戏角色之间贴合度越高,这组片子的质量与Coser的水平都会得到赞许。这便涉及中国本土语境内一对看似对立的传统概念——神似与形似,也即判定Coser是否还原时,究竟是还原出角色的气韵更重要,还是角色外观的逼真更重要。
在欧美与日韩的Coser看来,“形似”是优先的。但是,在中国本土的审美传统中,关于“形”“神”何者优先的讨论层出不穷。无论是民间曲艺,或是民间艺术,“形神兼备”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评判标准,也是许多表演者、创作者竞逐的目标。在先秦时期,《庄子•知北游》中写道,“精神生于道,形体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②庄子:《庄子》,方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537页。他强调作为宇宙万物本质的“道”,孕生了主体的“精神”和气韵,但是,主体的精神又需要借助外在的形体加以展现,这一时期的形神之辩存在着重神而轻形的倾向,这也奠定了后世从文人书写到民间艺术基本的“形神观”。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指出,“若拘之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③潘运告:《汉魏六朝书画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宣和画谱•墨竹叙论》中也写道,“以泼墨挥扫,整整斜斜,不专于形似而独得象外者。”④赵佶、蔡京等:《宣和画谱》,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396页。清代画家石涛也写道,“画必似之山必怪,变幻莫测懵懂间,不似之似当下拜。”⑤石涛:《苦瓜和尚语录清瘦阁读画十八种》,光绪二十六年刻本。在他们看来,突破外在形态的限制而追求内在神韵,才能把握住对象的精髓,外在的形态固然重要,但对于神似的直觉把握,更能使主体从形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们的主观感受、情感体验的波动,都能透过外在形态的框架展现出来。
国内一直存在着偏重神韵的传统,而Coser圈又重视外形的逼真与细节的真实,这体现出:积淀深厚的民间传统和现代社会崭新的文化实践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张力。一成不变的传统是不存在的,传统的活力在于它始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长期接受神似传统熏陶的Coser们在形似/神似之间如何做出文化抉择,存在着两种声音。第一类Coser认为神似更为重要。他们认为Coser圈最忌讳模式化,每一个角色都有自身的特质,关键是要在自我和角色之间找到契合点。真实的人体生理构造和虚拟的纸片人是不能直接对等的。所以,还原不等同于复制粘贴,它要求玩家反复观看、熟识游戏剧情,将自我的身体、情感乃至对角色丰沛的热爱投射到角色身上。这可以说是一次自我体会、感知的二次创作过程。第二种声音主要以刹那等舞台党⑥舞台党:指通过舞台表演再现传统角色的Coser群体。人为主。他们认为,舞台表演更侧重视觉呈现,Coser复杂的眼神与神情难以突破舞台空间的局限,难以被观众直截了当地捕捉到。Coser外在的形态和身体构造其实限制了他们角色扮演的选择。
虽然,以还原度为传统旨趣的角色扮演,在中国经历了“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中国的Coser们并不全然接受欧美、日韩的Coser圈中奉行的形似这一评价准则。在本土的圈内,他们替换成国内更熟识的“神似”和“气韵”,这一次传统的本土化再造的过程,衡量了中国悠久的审美传统,并被内部群体所接纳,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二)化妆技术的习得、实践与传承
“化妆”是一个玩家在现实身份和游戏身份之间,建立联结的中介。Coser熟练的技术来自反复的模式化实践——“这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画三次和画三十次,最后你的熟练程度和手感完全是不一样的”①访谈对象:Lili(化名),女,夜校研究生在读,现任北京朝阳市场销售,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8日晚,访谈方式:微信电话,访谈地点:北师大兰惠公寓二楼咖啡厅。。Lili谈及,自己平日里会拿着人像图反复描绘。在大学中,Lili还代表社团,给其他同学开设了化妆课程,她在科普完Cos妆及需要准备的道具后,便让座下的人两两一组互相化妆。在这种往复的过程中,Coser的手指和笔刷之间达到了一种驯化的状态——用力轻重、何处着力、何处轻放等经验知识如同代码一般被嵌套进自己的身体中,平日里这些身体经验是缄默不语的,在Coser被实体上妆等真实情境触发后,便会驱动着身体机械本能地做出反应。
数字媒介的出现,扩充了习得内部经验知识的路径,将诸多小众的经验知识公开化。防风②访谈对象:防风(化名),女,N大图书馆学2020级研究生,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4日早9点46分许,访谈方式:微信电话,访谈地点:北师大邱季端体育馆二楼看台。观看了大量的B站教程视频,学习如何贴眼睫毛,为了克服手抖的坏毛病,她一只手按着眼睛,另一手贴睫毛,在一次次的重复操演中,自己的眼线慢慢可以画得夸张、精准了。新媒介开辟了新的知识习得与传递的场域,知识表面原本覆盖着的神秘纱幕,被交织着的光纤网线、数据代码尽皆掀起,个体的经验与知识不再被少数群体操控着,知识也愈发开放,散落在不同地理空间的个体只要拥有一部手机,便能通过各种社交软件接触、习得这些经验。如果说之前知识经验的传承主要通过口传身授/心授的方式,那么,在融媒体的时代,知识与经验的权威逐渐从一元走向了多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精英群体对知识的垄断——原本以单一知识权威为核心的格局,逐渐演变为多个知识权威并置的局面。
(三)平面党的身体实践
平面党指穿着Coser服,以静态写真的形式,呈现扮演的虚拟角色的Coser。舞台党指“把游戏背景、故事构架、人物形象等通过真人cos在舞台上的走秀,吸引眼球。”③cosplay爱好者如何成为职业coser.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50830.舞台党既包括与游戏产商签约的团队,也包括以社团为组织进行排练、比赛的群体。摄像机、摄影师、自我身份与游戏角色之间复杂交错的关系,始终萦绕在每一个平面党身体实践的过程中。如何代入游戏角色,如何让精妙的光影与构图建构出一个“完美”的自我形象,这两个问题凝聚着Coser群体丰富的身体体验。
在自我身份与游戏角色之间,Coser主要借助镜子、衣服等外在物进行身体练习。“镜子”是Coser窥探自我身体是否安放准确的重要媒介,也陪伴着每一个Coser从一个不谙世事的新人,到慢慢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表情和四肢。防风谈到,对平面党而言,眼神传递是否准确,关系到出片质量的高低,所以眼神训练在Coser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她一般会在脑海中悬想着游戏剧情中的相关场景,让同理心引领自己代入到角色情绪之中,对着镜子反复调整自己的表情、神态。最重要的是,不断提高情绪投入的浓度,使得眼神可以体现更复杂的情感,最终找到一个可以视为模板的眼神,她以自己扮演改编自圣杯传奇的莫德雷德经历为例:
淡淡的忧伤(这种情绪),对我来说,就是眼中是悲伤,但嘴角微微翘起,眼睛不要睁太大,稍微有一点迷茫……我会想这个角色,他经历过什么故事或剧情,说过什么话,说话语气是什么样的,猜想他说话的心情,他想到了什么,就是一种投射与同理心,将他的情绪投入到我身上,将我的心境代入到角色的身体里面,会造成什么状态,这是掌握这个角色最好的方法。①访谈对象:Lili(化名),女,夜校研究生在读,现任北京朝阳市场销售,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8日20时11分许,访谈方式:微信电话,访谈地点:北师大兰惠公寓二楼咖啡厅。
在镜子前,自己还要不断调整身体姿势、位置和角度,找到“最美的角度”。对身体有疤痕的Coser来说,这个过程至关重要,接下来便是在练习中不断地复刻这一特定情境。随着智能手机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Coser每一次的练习,都可以通过摄像功能被存储、记录,玩家可以按下暂停键,分析、比对每一次定格的表情、身体安放方式。但是,“角度”“代入”的方式和结果难以被标准化,也很难被准确复制,有时可能只是灵感乍现,或是神来之笔使然。所以,这种融于身体(incorporated)的知识与体验是模糊的,也是流动不拘的,它依靠的是“意会”,是Coser对于练习情境的重新唤起,是Coser将自我放置到先前循环往复的身体调适实践过程之中。
除了在镜子前反复地操演,Coser还需要借助Cos服弥合自己和虚拟角色之间的裂隙。Coser服不仅仅是一个视觉符号,而且是文化象征的符号——它铭刻着Coser们的记忆,激荡着他们鲜活的情感。穿上Coser服后,自己逐渐地远离现实身份,也慢慢产生了对虚拟游戏身份的认同感。当自己穿上Cos服后以角色口吻说话,放大了“我就是他”的感觉,也强化了身份认同感。
这种认同不仅是精神认同,而且还对他们细微的日常身体实践产生影响。比如,Lili出过一个男性角色,这个男性角色戴着眼镜。在反复地揣摩、还原和亲身体验下,最终该角色推眼镜这一个标志性动作,成功地嵌入了自己的身体。即便现在脱离了表演的语境,自己仍然会不自觉地推着眼镜。该角色喜欢穿白衬衣、西装、牛仔裤,这一看似怪异的搭配方式,通过反复“出装”,也默默地形塑着自己的审美风格:一开始Lili会觉得这种穿衣搭配过于怪异,十分排斥,觉得丢人,但因为要找到自我与角色的契合点,所以需要不停地跳进跳出,通过穿Cos服找感觉。慢慢地,自己也内化了这种审美风格,白衬衣也成为了现在自己日常穿搭的重要部分,自己的衣柜中也积压了不下四五十件白衬衣。
来自摄影师、摄像机对于Coser身体的“凝视”,也影响着平面党的身体实践。这里的“凝视”指女性的身体受到来自男性目光以及机器的影响,在心理及身体层面产生了不适感,从而影响到她们身体的姿态。
当Coser经历了“后台”的化妆、神态表情与眼神的反复训练后,接下来便是与摄影师、摄像机打交道了。在摄影过程中,男摄影师与女Coser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话语和地位的不均等,男摄影师将来自外界的优越感,带入到摄影的过程之中,通过较为强硬的命令语词,操纵着、控制着女性Coser的身体姿态,女性Coser的主体性在该场域中慢慢地被消解、驱逐,逐渐成为男摄影师欣赏的符号,这种来自男性的“凝视”,能被一部分女性Coser敏锐地察觉出来。防风抱怨道,在和男摄影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的命令往往是强硬直接的。一句“头往右摆”可能令人猝不及防,甚至有些言语可能带有对女性身体羞辱(body shaming)的意味——“把你肚子上的赘肉遮一下”。他们对女性Coser的脸部轮廓不甚关注,关注的大多是构图、灯光以及女性性征,但对于女Coser假发开了,或者疤痕没遮住等小细节,一向置若罔闻:
上次在漫展,有个男生直接跟我说——“你手拿开一点,不要挡到胸,不然就拍不到胸了”,这样的话让我觉得非常反感,可能他们出于个人的想法,愿意去捕捉曲线,但是他们的做法和动机让我觉得不适。①访谈对象:防风(化名),女,N大图书馆学2020级研究生,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4日早9点46分许,访谈方式:微信电话,访谈地点:北师大邱季端体育馆二楼看台。
乌拉拉②访谈对象:乌拉拉(化名),女,2018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1月25日晚,访谈地点:北师大新乐群四楼。在影楼出片的经历,深深地给了自己被“商品化”“客体化”的感觉。她说道,影楼是属于摄影师的空间,所以,当男摄影师要求自己做一个自己不情愿做的动作时,出于腼腆,因而不好意思拒绝。每每遭遇这种情况,那种“像商品一样被摆弄”“精神被绑架”的感觉便会涌上心头,就“好像他天然地具有一种支配权”。虽然自己花了钱,是摄影师的雇主,但现实中自己和摄影师的关系却恰恰相反、倒置,就感觉“女性似乎注定了弱势”。
所以,当要Cos暴露程度比较多的传统角色,比如改编自日本妖怪传说的玉藻猫等,出于自我保护,她们往往会选择女摄影师。她们觉得自己和女摄影之间的交流更自然,也更频繁。这种平等的交流,往往会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女性之间也更熟悉彼此的身体构造,更了解如何精妙地捕捉身体曲线,男摄影对女Coser的身体有时会存在误读现象——将曲线等同于女性性征的凸显。
无论是乌拉拉,还是防风,所幸她们都意识到了来自男摄影“凝视”的目光,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出Cos单纯是来自对角色的喜爱,是希望自己的青春、美好的记忆以及蓬勃的活力,能通过照片被定格、凝结,而不是为了满足男摄影师的要求,所以要拒绝他们的眼光约束。她们有着一定的女性自觉、警醒的意识,但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始终没有缺席与退场,在行为上,她们暂时还无法从父权制的阴影下突围。在另一方面,像仓鼠等女Coser则驯顺地接受了、内化了这种凝视的目光。当男摄影师调侃起自己肚子上的赘肉,让她遮挡一下,她并未感觉到这种调侃的失礼,只是单纯觉得是“为了构图和效果更好”。
(四)舞台党的身体实践
刹那最早接触Coser圈是在2007年。当时,漫展上刚好有社团在招募成员,那阵子自己对动漫十分痴迷,为了找到更多同好,就加入了社团。但这份快乐十分短暂,正当自己准备出Cos时,因为响应国家应征入伍的政策,他背上行囊,离开了老家哈尔滨,来到了天津,这也宣告了自己暂时脱离Coser圈。退伍后,他留在了天津,成为一名朝九晚五的行政助理。两年的军队生活,让他深深地体会到与社会的脱节,社交空间极其有限。从2012年下半年起,刹那和朋友们闲暇时经常约着去桌游吧玩,一来二去,便和老板混了个脸熟,交谈后才发现老板是一个Coser剧团的团长。借此,刹那加入了剧团,重新回到了Coser圈。谈到Cos,谈到舞台,刹那总是异常亢奋:
Cos对我来说是梦想,是毕生想要追求的光。舞台是我喜欢这个(圈子)的一个方面。我第一次上剧还没有太大感觉,主要还是紧张。转年第二次上大剧时,有那么一瞬间是我站在舞台的c位,我在表现我自己所坚持的东西,这一套动作打下来后,我明显能感觉到台下观众的掌声和注目,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非常棒,我特别享受这一瞬间的感觉。③访谈对象:刹那(化名),男,大专学历,黑龙江哈尔滨人,现任天津某政府行政部门助理,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5日下午15:20分许,访谈方式:微信电话,访谈地点:北师大邱季端体育馆二楼看台。
舞台党的身体实践大致可以细分为观察、言传、身授、表演的创编四个阶段。首先是观察,Coser要学会观察、模仿同类型角色的存在,当内化了这一类型的身体姿态、动作后,再从肢体感受角色的内在特质。当自己出阳刚的角色时,比如改编自希腊神话的赫拉克勒斯时,可以尝试大开大合地走路,当出阴柔的角色时,可以通过细小的步伐,带动身体节奏放缓。
言传与身授往往是彼此交融的,所有的表演框架、知识的制定、传递与习得都由社团前辈手把手带着新人完成。一般而言,前辈们会花15—30分钟左右详细地讲解表演的框架、演绎、姿势与上下台的细节,在前辈反复演示后,每位成员开始认领动作,私下揣摩动作的力度、高度,以及背后暗含的情绪变化。社团前辈大多通过身授,矫正Coser们的动作,他们认为这种表演技术很难通过语言精妙地表达出来,也很难被提炼成标准化、格式化的身体知识,它更多地依靠“悟”“照着前辈的示范练”和“反复”。最后,无论是表演传统框架的要素,抑或是前辈个人表演习惯的痕迹,都通过演示、动作的反复操演,以及练习沉淀到新Coser的身体之上,这便如波兰尼所说——“通过示范学习就是投靠权威。你照师傅的样子做是因为你信任师傅的办事方式,尽管你无法详细分析和解释其效力来自何处……一个人要想吸收这些隐含的规则,就只能那样毫无批判地委身另一个人进行模仿,一个社会要想把这个人知识的资产保存下来就得屈从传统。”①[英]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的哲学》,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80页。
cos里面很多动作没办法纯靠说来表达,更多的是把这套动作放慢速度,然后一点点把它再做一遍,如果还是学不会的话,我可能去帮他摆一下动作,比如翻肘、甩剑花这种比较难的动作。②访谈对象:刹那(化名),男,大专学历,黑龙江哈尔滨人,职业:现任天津某政府行政部门助理,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5日15:20分许,访谈方式:微信电话,访谈地点:北师大邱季端体育馆二楼看台。
刹那所说的“放慢速度”式的身体练习,也被Lili、歪头反复提及,这是舞台党练习动作一致性、整齐度的法门:先按照八拍拆分、熟记动作,再从频率、速度极慢的八拍节奏中重复每一个动作,接着,逐渐提升喊八拍的速度,以此训练Coser在快节奏中调适、转换身体姿态的能力。慢慢地,社团前辈减弱了喊八拍的声音或是只喊重要八拍,逐步减少动作的提示,最后,使得Coser在不喊八拍的情况下也能娴熟地做动作,正是通过反复地实践与模仿,这些看似繁复的动作内化成了Coser身体行为的模式与能力,他们能控制好自己的肢体与表演,达成日本能剧大师世阿弥在《花镜》中对表演者的希冀——“序、破、急的有序条理”③J.T.Rimer and Y.Masakazu(trans.), On the Art and NO Drama: The Major Treaises of zeami.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79.。
Coser们强调对模式化表演框架的突围,主张表演者基于个人能力的动态创编。Lili在剧团排练时,团长一般会对每个队员的动作量身打造1—3个“粗胚架子”,剩下的功课便是Coser们立足于对角色的咀嚼与理解,融入匠心。比如,特种兵出身的Coser在出少林大师时,手持50斤重的禅杖,并展示了转棍、甩棍、金鸡独立等高难度动作,Lili曾在东北赛区看过同样有武术背景的Coser从两层楼高的高度空翻落地。
歪头所在的剧团也推崇这种放养式表演,他们强调表演是个体与角色的融合,是表演者主体性的洋溢与彰显。舞台表演中的身体虽然面对着来自观众、自我期待的规制,难免会显得局促、约束,但主体性与个人特质的在场,会为角色灌注鲜活、丰沛的灵魂,他们的身体不再是被约束、框定的,反而带上了几分自由、洒脱的色彩。这种自由有赖于“抢戏”,因为“抢戏”,Coser的舞台表演在既定框架与动态创编之间达成了一种和谐、平衡:
刚入圈时,团长选择的政策是放养,简单地说一些框架、要点,自己去练。比如一段剧情是配角需要凸显主角时,别的社团大都要求后面的人定点做固定动作。我们团是配角们自由地想一些动作,这养成了我们抢戏的习惯。主角表演他的戏份,作为配角在不打扰他的情况下,我去抢自己的戏份。①访谈对象:刹那(化名),男,大专学历,黑龙江哈尔滨人,现任天津某政府行政部门助理,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5日15:20分许,访谈方式:微信电话,访谈地点:北师大邱季端体育馆二楼看台。
二、身体的管理与塑造
在复原游戏世界中传统角色的过程中,身形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受到日本纤细、美形的审美规范的影响,游戏世界中的传统角色都呈现出纤细、富有曲线美的外形。玩家为了更好地还原出角色本身,便不得不对自己的身形进行严格地管理和塑造。自古,我国便存在着许多规训女性身体的手段,如盛极一时的束胸、裹脚风尚,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对身体的建构,而且最后还演变为女性对自我身体的规训。迈入现代文明社会后,社会渐渐地生产出一套所谓的“科学”标准,通过数值设定、量化的标准来界定民众的身体是否“健康”。伴随着这套标准中数值的浮动,玩家的情绪也随之变化,其中以“身体焦虑”这一情绪最为明显。与“身体焦虑”相伴随的是玩家对身体的管理和塑造。
(一)节食与健身
Coser们为了能出自己热衷的虚拟角色,为了让自己的体态更贴合原作形象,纷纷采取相应的身体管理、塑造的策略。防风本来想出②出+角色:Cos圈术语,指的通过穿着相应的Cos服,化妆等,还原该角色。伊什塔尔这个角色,但受限于身体曲线与卡面上的伊什塔尔相距甚远,只能放弃。最终,她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出孔明③FGO中孔明为女性角色。。但出孔明也并非易事,她还是费了一番周章去改善体态。因为她出的孔明形象要裸露腰部,这对腰上线条提出了要求。为了去掉“赘肉”,她一天只吃一餐,每天坚持跳宅舞,希望“甩掉腰间的赘肉”。
不光是女Coser,男Coser们也深深地被卷入了这场塑身的浪潮中。刹那每天坚持跑3—5公里,这一习惯已经坚持了半年多。他训练时还为了挑战高难度动作,导致不轻的脚踝伤势。即便如此,他还是一天不落地跑3公里。我和刹那的访谈在下午三点半,不一会儿,手机那边便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在我纳闷之余,刹那说,这是他今天的第一餐,刚刚的声响是外卖小哥将外卖放在了敞开的门口。他的外卖只有蔬菜沙拉和糙米饭,我十分讶异,毕竟这个饭量实在难以支撑一个中年男人的能量所需。
正是通过刹那,笔者才了解到Coser们为了让自己有“胶原蛋白的质感”,为了永远洋溢青春的气息,他们的化妆台上堆满了形形色色的进口化妆品,用于补水、美白,他们还定期服用燕窝等补品,更有甚者,他们还每年斥巨资打瘦脸针、抗衰针等。
那么在当下,哪些动因影响着玩家对于自我身体的管理与塑造?所谓的“健康的”“美的”标准是谁生产出来的?他们是被动地接受这种规训,还是主动直面它?
首先,社会主流话语形塑着玩家乃至民众的身体,不同的身体形态有着不同的隐喻。在传统社会中,身体往往被附加了生殖崇拜、巫术信仰的象征意味。比如,在福建某些偏远的农村,仍流行着一套评价女性生育能力的标准——女性屁股的“宽、大、翘”与其生育能力有着莫大的关联;又比如,通灵者的身体被视为是神灵在现实世界的载体,是民众沟通神灵的媒介。
在现代社会中,身体形态的背后则隐匿着一套科学的话语体系,身体形态往往和财富、生活方式、阶级相关联。在一个以“瘦”为美的时代中,“胖”被视作是懒惰的、糜烂的生活刻写在身体的表征。“瘦”则联系着健康自律的、勤勉向上的生活状态。这种隐喻的出现,与健康评测标准的产生有着莫大关联。在重视科学数据、强调效率量化的社会中,健康与美并不是来自个体对自我身体的感知和觉察,而是随着数据的浮动而变化:个体自然地将自我纳入到了标准当中,他们通过量表中的数值来定义健康与美。换言之,主体对健康的体认、对美的判断被这套标准整合起来,不符合社会主流审美规范的身体受到了来自外界他者的羞辱、贬斥与压制,这种羞辱可能表现为来自家庭的唠叨与规训,来自同辈的指点与嘲讽,甚至是路人轻蔑的讥笑。王尹东谈到了来自家庭的规训对自己产生的莫大的影响,“在家里我穿个吊带开衩裙,我妈绝对会狠狠地打我”,这就是她为什么无比热爱Coser圈的原因:
自己不会表达感情,原生家庭畸形的表达方式难辞其咎。他们缺少夸奖的词语,只能看到我哪里不够完美。即使我的外形遗传于他们,他们也不止一次嫌我不高。他们心里只有一个美丽的模板,要一米六五,要高挑纤瘦。他们觉得青春期的女生胖了是天大的罪恶,穿裙子是在暴露自己的丑陋。当我咨询一条价格合理的裙子,他们的第一反应必然是不好看、不适合,即使穿上后确实好看,他们总喜欢将期待和喜悦扼杀在摇篮里。他们不止一次认为肌肉会显得太壮,像个“汉子”,认为我的性格不像所谓“女生该有的可爱”,却完全没意识到正是这样的气力和勇气才能空手夺下可以剪断筋肉的剪刀,阻止他们伤害对方。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语。我不会再咨询哪件衣服好看,因为他们只会给我批评和贬低。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缺失数十年的,应得的认可和安慰。为什么要逃离原生家庭。我觉得我逃离的不是家庭。我逃离的是异化的人和畸形的感情。①访谈对象:王尹东(化名),女,北京师范大学2019级法学院本科生,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1年4月4日,访谈方式:微信电话,访谈地点:学四楼。
在社会他者炽热的“凝视”下,个体似乎丧失了掌控、支配身体的权力,“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督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都是由他们自我加以实现的。”②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即便是提倡“异装”的个体,他们看似张扬着个性,但当你深入到这个圈子后,会发现他们对于“瘦”“健康”的憧憬与普通人别无二致。
其次,影视传媒图像规训着玩家的身体审美。摄像机凹凸的镜头会横向地拉长了被拍摄对象的体态,使他看起来比实际更“胖”。所以,我们在镜头前看到的体态匀称的主体,实际都比视觉图像看着更瘦削。因此,Coser们要想在镜头前展现出“完美”的体态,只能内化“以瘦为美”这一主流的审美规范。生产者出于盈利目的,反复邀请“貌美的”“瘦”的主体作为广告、影视剧的主角,借助现代传媒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大的特点,不断地传阅着,型构着一种理想化的状态。包括Coser在内的民众通过反复地接触和观看,其实内化了这种审美风格。这种完美形象、审美风格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传媒工作者有意生产的。以往,我们认为图像是现实的映射,但其实不然,影视图像中人物视角的选取,生活截面的呈现与消隐,其实都操控在传媒生产者的手中,他们通过镜头的移动,出镜者的选择其实传递着一种虚幻的事实,也向接受者灌输着他们奉行的审美观念。
在某些情境下,Coser无法轻易改变自我的身体构造,但为了身体能和游戏角色有着更高的相似度,有时候需要在化妆方面花点心思——用妆面去修饰身体“缺陷”。虽然Coser有时会为了发胖的身材而忧虑不已,但在重复的实践中,他们的内部也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规避身体“缺陷”的策略:丰满的体态可以通过道具和化妆来掩盖,为了使脸颊变小,Coser往往会贴一下两边的鬓角,将头顶垫高,同时也让发量变多,在拍摄时还需要侧一下脸。此外,Coser还可以借助轻纱,或是打光、姿势与角度获得“体态的完美”——多拍摄半身照,减少坐姿拍摄,因为坐姿让脖子以及下颚的赘肉过于明显;打光时可以多打一些蝴蝶光,另一面则打一些暗光与阴影,使得脸部轮廓更为立体显瘦。这也体现出了Coser们能动地在不伤害身体的情况下,迎合着社会的规训与审美的规范。
(二)跨性别扮演中的身体反叛
在Coser圈内,Coser会扮演和自己生理性别不符的角色,这更能获得他人的关注,这种现象被称为“跨性别扮演”。在传统的戏曲艺术中,“男(女)扮女(男)”并不稀奇。在戏曲艺术中,跨性别扮演彰显着表演者个人能力的高低,但在Coser圈内,这种跨性别扮演多少带有了猎奇、反叛的格调。
Coser圈内男性Cos女性往往更能受到圈内人的追捧,但这不阻挡女Coser热衷于出男性角色,本部分的主人公——防风便是其中一员。因为一次痛苦的爱情破灭,防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因此,她厌恶周遭所有的男生,并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取向发生了转变。她剪去了自己蓄了多年的长发,痴迷于男性装扮,开始疯狂地Cos男性角色。先前,防风没法克服以女性身份代入男性角色的问题,似乎迎刃而解了,反倒是在出女性角色时,会感到深深的违和感:
当我觉得自己是铁T的时候,那时候留着短发,会去Cos某些女性角色,会感受到一种违和感,但这种违和感又慢慢地被对于新身份的新奇感给冲淡了。①访谈对象:防风(化名),女,N大图书馆学2020级研究生,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4日早9点46分许,访谈方式:微信电话,访谈地点:北师大邱季端体育馆二楼看台。
在那段阴暗的日子里,她尽量穿着宽松,特别排斥凸显女性曲线的紧身衣物,她无时无刻不穿着增高鞋,“感觉身高变高了之后,自己更像个男生了,也更有安全感了。”她的所作所为只是想挣脱、逃离生理上女性的身份符号。当其他玩家夸赞她身上流露出的男性气质时,她就倍感兴奋。但是,当他人用女性化的标准称赞自己时,她感受到的是愤怒。她想逃离女性这个身份符号,但是“我身上的身体特征,却时刻提醒我是个女的,这太令我沮丧了”②同上。,她感觉自己丧失了支配自我身体的权力,为了弥补这种无力感,她纷繁地通过文身、打耳钉、舌钉和脐钉来重新获取对身体的操控权。
防风这种身体刻写的行为,带有两方面的意味。第一,身体被作为了联结自我与角色的重要媒介。只要喜欢一个角色,都会将与该虚拟角色相关的符号(图像、标志物)等刻写在身体上,就好像和角色建立一个“类似于永恒的、信念的、契约式”的关系。这些符号凝结着防风青春的回忆,也见证着她日常生活的美好与动荡,在她看来,人的身体会衰老。但是,这些符号却能永久保存。通过它们,自己似乎能在某种意义上“逃离衰老”,也逃离“时间对容颜的侵蚀”:
我身上的各种符号、文身都是有意义的,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一些对我有意义的人、事、物都留下来。①访谈对象:防风(化名),女,N大图书馆学2020级研究生,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4日早9点46分许,访谈方式:微信电话,访谈地点:北师大邱季端体育馆二楼看台。
第二,在防风看来,这种身体刻写的行为构成了自我与众不同的身份标识,是反叛独立,甚至张扬个性的标志,“与众不同、独一无二”是她从小的追求;但同时,她看似与世俗格格不入,其实无形中也内化了社会的规训。她会考虑到自己的学生身份,不能在身上留下太明显的符号,比如唇钉,“耳钉在大家的认知中比较正常,我打耳钉也不会太奇怪,舌钉和脐钉的话,如果我不刻意显露,别人也看不到。”②同上。从她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她一直想要逃离他人目光、主流审美对身体的规制与约束,但其实她似乎从来没有从他人的凝视中突围,也没有从主流审美给自己造的“茧蛹”中破茧而出。
(三)作为权力话语的“头模”
Cosplay这一过程中带给女性的身体体验,永远绕不开一个“痛”字。比如乌拉拉、防风不止一次地提到自己无比希望能摆脱女性的身体,因为成为男性,就不用再承受出男性角色时束胸带来的痛楚。乌拉拉说,裹胸带来的痛楚,令自己难以无视这种痛感,这大大地影响到了自己代入角色——“男Coser出女性角色就比我们容易,可以全身心投入,他们出女装时那么多人追捧、尖叫就可以理解了。”③访谈对象:王尹东(化名),女,北京师范大学2019级法学院本科生,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1年4月4日,访谈方式:微信电话,访谈地点:学四楼。乌拉拉说每次自己卸彩妆时,就感觉“像蛇蜕了一层皮一样”,假发又重又热,发网每次“都把头勒得嗡嗡响”④访谈对象:乌拉拉(化名),女,2018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1月25日中午11点半,访谈地点:北师大新乐群四楼。;仓鼠为了出角色,即便来了例假,也依然穿着小短裙,在北师大的银杏大道上拍写真,“那天刮了4—5级大风,全凭一口仙气吊着,拍完直接在床上瘫了一天。”⑤访谈对象:仓鼠(化名),女,2018级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本科生,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0月24日下午4点半,访谈地点:北师大新乐群四楼。
此外,还有Coser沉迷于“3D打印头模”,这些头模Coser所忍受的痛感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但是,如果仅仅是简单地把头模Coser的痛感理解为对角色的热爱,其实只看到了这种身体实践的表层,这种痛感的体验更被他们作为了一种建构新的身体话语体系的工具。
3D打印头模指将游戏角色的外观打印成塑纸,Coser套进去后只留下一个微小的气孔,他们声称,这才是最正宗、最极致,也是最传统的“还原”——因为外观完全是角色在视觉图像上的复刻。他们会频繁、生动地讲述自己24小时内如何忍耐着饥饿,“闷”在塑纸中,也会极力渲染自己皮肤、颈椎因此而饱受各种“病痛”的困扰。通过这种讲述,他们希望利用这种极致的“还原”、剧烈的“痛感”与“自我牺牲”来彰显自己对角色的热爱之深,更是为了确立自己在Coser圈内的话语地位:在Coser圈内,你对角色的热爱程度越高,还原的效果越好,你的文化等级越高,相应地,你也会获得更多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往往体现在其他Coser对你的羡慕、夸赞,你的作品也会因此获得更多的关注度与点赞量。
除了痛感的渲染外,这种地位的确立还和经济资本投入有关。头模的价值远远高于普通的Coser服。一套质量尚佳的Coser服大致在4000—5000元。但是,一套头模最少要2—3万,质量好的可以达到十多万。作为小众文化的Cosplay,涌入的人群越来越多,现在出现了一种从融合到分离的趋势——早期的老Coser们为了维持自己在该趣缘社区中的地位,便利用自己过剩的资本去生产出新的审美趣味,通过“炫耀性消费”的方式,凸显自己“高人一等”①肖索未:《欲望与尊严: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5页。的地位,从而赢取他人的重视与羡慕,也通过“求异”的方式圈定新的“领地”,将自己和新Coser们区隔开来,在这个意义上,消费构成了界分人群的重要形式:
在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间,其实越来越多的老Coser们想要生产出2.5次元,他们想求异,想把自己化成少数,但是在化成少数的过程中,他们又想附属一个群体,因为一个人玩太孤单了,这个时候就会不断地出现融合、分离,再融合、再分离这样的趋势。我的生活应该跟别人不一样,但这也太标新立异了,当众人不理解你在干什么时,你会觉得很孤独,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在个性和分享之间达到平衡。②访谈对象:吴茗,女,2018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生,访谈人:张淇源,访谈时间:2020年11月29日上午10点半,访谈地点:北师大新乐群四楼。
三、Coser圈复杂的身体生态
作为小众的Coser圈有着复杂的生态,这些生态和Coser的身体紧密地缠绕着、交织着。首先,“福利姬”指某些女性Coser并非出于还原的需要,而是想通过身体的暴露,获得更多的关注度,甚至不惜将自我的身体商品化,以获取经济收益。福利姬将身体视为盈利的筹码,这也使得刚刚剥离了小众标签的Cosplay文化,又陷入了污名化的泥淖。福利姬们内化了男性的凝视,在自己的身体刻下了色情、欲望和挑逗的印记,这些印记体现为带有性暗示的身体表演与姿态,或者是暴露的穿着。对其他只想纯粹地出角色的Coser群体来说,这种将身体资本化的行为是一种对情怀的亵渎与背叛。
其次,滤镜技术的出现与引进,有利于为Coser群体生产出理想化的图像。但是,这种技术也在制造着一种虚幻的真实,正如加仑•拉尼斯所言,“社交网络给了人们一个可以塑造‘虚拟模范’的机会……人们可以精致地修饰每一张图片,扮演和展现一个完美的自我,但正是这种对于塑造完美自我的渴求,使人们将自我‘囚禁’在自我表现的监牢中。”③[英]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第二版),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页。某些Coser对这一技术产生了强烈的依赖,他们寄希望于后期修图能弥补身体的缺陷,呈现出完美的自我,但这其实偏离了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玩家的身体逐渐成为技术的附庸。他们开始疏于眼神、体态与动作的训练,但这恰恰是每一个老Coser们引以为傲的立身之本,其中蕴藏着许多珍贵的记忆:在乌拉拉看来,“那些依赖滤镜的Coser们是可悲的,除了拥有一套衣服、一张皮外,但是却没有内在的灵魂。”对容颜姣好的Coser而言,滤镜、后期等技术可能是一个福音;但是,对于外表平庸、精于挖掘角色神韵的Coser而言,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四、结语
作为边缘、小众的群体,知识的习得、他者的凝视在Coser的身体上铭刻了烙印。他们的实践既包括后台中身体反复的操演、前台中表演的创编,也包括在多重的自我形象中,游移地建构自我的认同。此外,他们的身体还从肉身性的维度超逸出去,成为建构趣缘群体边界、争夺话语权的符号表征。最后,在滤镜技术的阴翳下,“何为真实的自我”始终萦绕在Coser的认知之中。在真实的肉身与技术修正过的“身体”之间,他们对自我形象的认同呈现出抉择的分岔。
在趣缘社区林立的当下,Coser的个案呈现了青年亚文化群体孤独地获取自我认同、建构自我形象的“摆渡”与“游移”。这种踯躅的“精神摆渡”,恰恰是当下青年人精神风貌的缩影——在“千面”中寻求一种人际的谐和、自洽。当民俗学的镁光灯投射到都市青年群体,他们细微的絮语、丰沛的情感进入学术的视域,我们看到了社区边界复杂的建构与流动过程,也彰显了民俗学在深耕亚文化群体巨大的阐释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