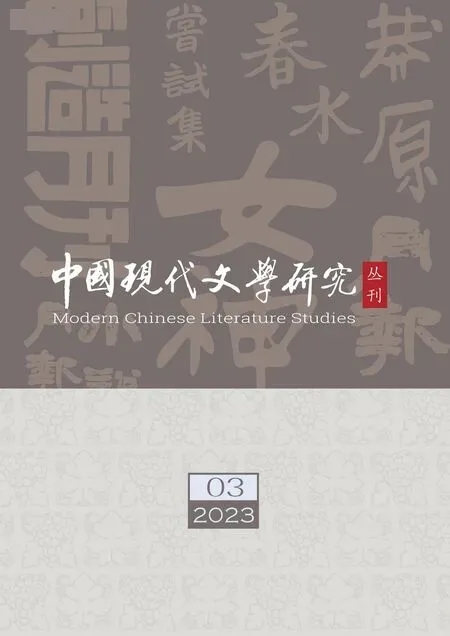随笔与政论:《西滢闲话》之后的陈西滢
2023-10-06杨勇
杨 勇
内容提要:学界一般认为,陈西滢自从与鲁迅论战之后即从文坛隐退。然而通过搜集整理陈西滢佚文,可知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仍写作了六十余篇随笔、政论文,并非隐退无为。借助这些新发现文献,可以再次回顾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领略陈西滢知止知退的批评论辩风度;《读书与环境》《谈声誉》《行政效率的趣剧》等篇堪称中国现代散文精品,带有鲜明的知性特点,由此追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滢闲话》,则无疑可说是现代知性散文的源头;至于抗战时期的政论,则是陈西滢专业特长的发挥,展现出精准的政治判断和独到的历史洞察力。
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陈西滢因与鲁迅论战以及闲话创作而名噪一时,但一般认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陈西滢即退出文坛。及至1943年赴伦敦工作,陈西滢更彻底远离中国文坛,淡出学界视野,以至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甚至有学者认为他因与鲁迅论战战败而隐退。其实,鲁、陈论战之后,陈西滢于1928年前往武汉大学任教,乃是有意远离、淡化论战是非。在武汉,他一方面忙于教学,另一方面也间或写一些随笔、政论文。2015年以来笔者和导师合作,搜集到陈西滢1920—1940年代的随笔、政论文数十篇,证明陈西滢后期不但未从文坛隐退,而且还创作出了若干散文精品,以及极具历史洞察力的政论文。这些随笔和政论文,无不透露出陈西滢爱国忧民的情怀。
一 《西滢闲话》外的闲话:学生运动的证言及其他
鲁迅“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战士精神着实令人叹佩,直到临去世前,他依然决定,让自己的怨敌怨恨去吧,他“也一个都不宽恕”1《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2页。。这不宽恕的对象想必有陈西滢。1925年前后,以陈西滢为首的《现代评论》派与以鲁迅为首的《语丝》派围绕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展开了激烈论战,然而论战远远超出学理讨论。
鲁迅当然能做到一个都不宽恕,但陈西滢却未必一直怨恨他。陈西滢后来毫无偏见、极其公允地认可评价了鲁迅其人其文的伟大。鲁迅去世后不久,陈西滢就在一篇文章里提到1936年去世的中国文化名人——其中也包括鲁迅——并表达了敬意:
学术界名人,国学方面有章太炎先生,科学方面有丁在均先生,文学方面有鲁迅先生。“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一时失去这许多人,真是国家之不幸。他们中大部分受到国葬或公葬的哀荣,也可以表示国家对于他们事业学问的一点敬意,一点答谢。2陈西滢:《公葬与公墓》,《武汉日报》1937年3月28日。
此外,陈西滢还曾经借机替鲁迅说过公道话。那是1940年,施蛰存发表《鲁迅的〈明天〉》,该文旨在通过分析小说《明天》来指导青年学生写作技巧,但却生搬硬套地运用性心理学方法,以至于附会穿凿,认为鲁迅的很多话语都是有意为之,背后隐藏着性心理暗示。针对施蛰存的过度阐释,多年远离文坛的陈西滢特意撰写了《〈明天〉解说的商榷》,有理有据地纠正了施蛰存的过度阐释,中肯地评价了《明天》的写实艺术。应该说,陈西滢写这样一篇文章,出发点肯定不止于还原一个真实的《明天》,正如施蛰存所说:“陈西滢先生好久不写那么长的文章了,这回竟被我那篇金圣叹式的文章‘引出’这么长的大文来,亦是荣幸而又惶恐的事。”3施蜇存:《关于“明天”》,《国文月刊》第11期,1941年12月16日。应该说,陈西滢其实有意借此表达对鲁迅的歉意和敬意。
事实上,陈西滢不只大方肯认鲁迅各方面的成绩,他还有意避而不谈早期的论战,比如在重印《西滢闲话》时删除和鲁迅论战的部分,“据说六十年代在台湾重印该书,侨居英国的陈西滢将其中与鲁迅论争的部分删去了”1吴福辉编:《西滢闲话》,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第9页。,这正显示了他的忠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后来从未再提及周氏兄弟曾经炮制的关于他的谣言。因为鲁迅的文章收录完整,所以关于鲁迅和陈西滢的论战,后来的研究者往往顺着鲁迅提供的材料和观点,难免先入为主地揪住陈西滢攻击鲁迅“某籍某系”、误责鲁迅抄袭等事件——当然,无须否认,这些也都确有其事,是陈西滢眼中的“木屑”——但鲁迅眼中的“大梁”却被有意无意忽视了。这“大梁”便是周氏兄弟参与制造的关于陈西滢的谣言。按,1926年1月20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周作人寄给他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其中就有影射陈西滢的谣言:
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颇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2岂明:《闲话的闲话之闲话》,《晨报副刊》1926年1月20日。
虽然周作人并没有点出两位“新文化新文学名人名教授”的姓名,但通览该文,内容大都是在与陈西滢辩驳,所以剑指何方昭然若揭。这封信极大刺激了陈西滢,因为这牵涉自身的清白声誉,“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样的谣言足以让一个人身败名裂。于是,陈西滢逐个致信周作人、张凤举等相关人士3相关来往信件题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质问他们是不是亲耳听到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不是亲耳听到,那么又是从何人听来?针对这样郑重的质问,周作人先是回信表示要调查,然后过了一天,他毫无歉意、轻描淡写地答复道:
通伯先生:
前日所说声言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两个人,现经查考,并无先生在内,特此奉复。
一月二十二日,周作人4岂明(周作人)致西滢的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
至于张凤举,则显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打算通过自己承担责任来化解此事。他在给陈西滢的回信中写道:“不过我要向你道歉,因为这次事完全是我误传的结果,与别人绝不相干。”1凤举(张凤举)致西滢的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然而这样模棱两可的道歉明显不能解决到底谁才是“陈西滢说女学生可以叫局”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说,这些信件虽然证明了陈西滢的清白,但谣言源自何方仍未查清。既然周作人第一封回信里说:“那句话我是间接听来的,如要发表说话的名字,必要先得那位中间的见证的允许”2岂明(周作人)致西滢的信,《晨报副刊》1926年1月30日。,可见谣言必有源头,只是周作人、张凤举等都在给始作俑者打掩护。
由此重审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恐怕不像鲁迅所说那样是非分明。首先,就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而言,不能单纯因为鲁迅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就把鲁迅捧上“道德正确”的高地,乃至以鲁迅的是非为标准,上纲上线地把鲁迅和陈西滢对置在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胜利与失败这样的关系中。实际上,鲁迅和陈西滢远非敌对关系,他俩都致力于启蒙大众、改造社会,只是方式方法不一样,鲁迅及《语丝》派是疾声唤醒式,富于战斗性、革命性,而陈西滢及《现代评论》派则相对温和,希望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陈西滢和《现代评论》派也同情支持学生运动,但是他们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比较慎重,不是无条件支持的。《现代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周鲠生在《青年学生的政治运动》一文中有精到论述,他认为在政治不进步、民众难以组织起来的国度,学生作为“比较有组织的团体,容易号召起来”3周鲠生:《青年学生的政治运动》,《现代评论》第1卷第22期,1925年5月9日。,也能发挥积极作用。但学生的能力是有限的,他提醒学生“对于他们自己的地位也应当有个觉悟。要知道不是一切形式或意义的政治活动,都是学生应做的”4周鲠生:《青年学生的政治运动》,《现代评论》第1卷第22期,1925年5月9日。,并提醒学生不要借助政治运动的名义来达到满足私人利益的目的,同时,更有力的政治运动必须与民众势力相结合。陈西滢也持类似意见,他同情学生运动,但他希望学生有能力时、想清楚时再去请愿,尤其是弱小的孩子,更要避免参加。在“三一八”惨案后,陈西滢“遇见好些人,里面也有率领小学生的中学教员”5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1926年3月27日。,可见很小的孩子也被组织去参加群众运动了,当陈西滢听说死者中多为妇女小孩时,他在一篇闲话中沉痛地检讨说:
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虽然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你们目下还算不上“匹夫”,这责任也不妨诿一诿,等你们成了“匹夫”,再来担当吧。这话自然特别对他们的父兄,尤其是他们的师长说的。对理性没有充分发展的幼童,勉强灌输种种的武断的政治或宗教的信条,在我看来,已经当得起虐待的名字,何况叫他们去参加种种他们还莫名其妙的运动,甚而至于像这次一样,叫他们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做父兄,尤其是做师长的,也不能因为他们自己愿意去,便不加劝阻禁止,不能因为他们愿意去,便脱卸自己的责任。他们还没有审判力,他们还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意志。父兄师长们对于孩童们乱吃东西,尚且恐怕他们生病,加以劝阻禁止,何况参加关系重大的国事呢?
我遇见好些人,里面也有率领小学生的中学教员,他们都说,那天在天安门开会后,他们本不打算再到执政府。因为他们听见主席宣布执政府的卫队已经解除了武装,又宣读了李鸣钟1李鸣钟(1887—1949),河南沈丘人,西北军将领,时任京师警察总监。的来信,说对于这一天的运动,军警当妥加保护,所以又到执政府门前去瞧热闹。谁知道执政府门前立了五排执枪背大刀的纠纠武夫!又谁知道李督办事后说当日并没有军警在场!我们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句话。要是主席明明知道卫队没有解除武装,他故意那样说,他的罪孽当然不下于开枪杀人者;要是他误听流言,不思索调查,便信以为真,公然宣布,也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要是李鸣钟真有信去,答应保护,事实上却并没有派军警去保护,那么李氏百口也不能辩他无罪;要是李氏并没有信去,那么宣读的信,出于捏造,那捏造的人,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2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68期,1926年3月27日。
陈西滢认为: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父兄师长不能因为他们愿意参加运动便不加劝阻禁止,更别说父兄师长鼓励支持他们参加了。这本是对学生运动的诤谏,目的是减少不必要的流血牺牲。
有别于学生运动,当群众运动遭遇到执政残酷镇压时,陈西滢丝毫不含糊,在五卅惨案之后,他仗义执言道:
在国外的时候,事事处于旁观的地位,所以自己觉得是理智的动物,不易受感情支配的。现在知道自负的理智也不过这样。
当初我们立在执政府门前的时候,看看出出进进的执事人们,不禁得到一种奇异的印象。中国人本是一个丑陋的民族,可是像那些其貌不扬的人们,一时也不容易找出这许多来。难道物以类聚,不那样便不会进那个门了呢?还是进了那个门便连相貌都变了呢?1陈源:《西滢闲话》,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3~74页。
虽然不是狂风暴雨式的怒斥,但对于执政残暴的愤怒和讽刺同样力透纸背。
其次,如果说陈西滢和鲁迅因教育和文化背景不同而在学生运动方面持有异见尚有情可原,那么其后的相互谩骂、相互指责抄袭等一系列意气之争则远远溢出学理讨论,带给双方极大伤害。而更需警惕的是由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演变为帮派论战,乃至不择手段。学界往往关注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的“攻周专号”,但1926年1月26日《语丝》第63期对陈西滢的攻击远比“攻周专号”令人触目惊心。该期所载刘复(刘半农)《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署名“爱管闲事”制作的《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以及林语堂《写在刘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极尽对陈西滢的挖苦讽刺和人身攻讦。
最后,当鲁迅因韧性的战斗精神而彪炳史册时,更不应该忽略陈西滢知止知退的气魄。陈西滢论战之后不再提及叫局流言、撰写关于《明天》的文章、再版《西滢闲话》时删去与鲁迅的论战,等等,这一系列文学行为,都可以表明:他为自己曾带给鲁迅的伤害和不敬表示歉意,同时尽弃前嫌完全放下了鲁迅对自己的伤害,并肯认鲁迅的伟大。这种风度难道不应该更令人钦佩吗?!
二 随笔两篇及其他:陈西滢与现代知性散文
解志熙在《气豪笔健文自雄——漫说文坛健将杨振声兼谈京派问题》一文中曾经指出,1940年前后曾出现一股知性散文创作高潮:
“随谈录”式的知性散文则直到40年代才成规模地崛起于南渡的学院文坛,却长期被学界所忽视。毫无疑问,“随谈录”式的知性散文之崛起乃是一个很重要的现代散文运动。2解志熙:《气豪笔健文自雄——漫说文坛健将杨振声兼谈京派问题》,《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
陈西滢其实也是这一散文运动参与者之一。1928年之后,陈西滢前往武汉大学任教,在忙碌的教学之余,也写一些随笔,其中不少是关于学习读书的,如《读书与环境》,载于1934年12月出刊的《珞珈月刊》第2卷第4期文艺专号,该文编者在《编辑后记》里说:“《读书与环境》是陈西滢先生一篇在本校纪念周讲演的稿子,我们却是拿来当作很好的随笔读的。”诚哉斯言,《读书与环境》旁征博引,内容饱满亲切而又富于趣味,确是引人入胜的好随笔。作为教师,陈西滢十分关注教育教学和学生身心健康,此类的随笔还有《怎样做笔记》《谈谈学习外国文》《哈提》《一部英文学的参考书》,指导学生学习方法,向学生推介英国的文学家和英语文学学习资料;《关于考试》《大学入学问题》写大学入学考试等制度不合理,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烦难,并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改革建议;《为下一代人的身体着急》《为下一代人的心智着急》从题目便可看出陈西滢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关心忧切。此外,陈西滢还写有一些关于社会时事、文化风俗等方面的随笔。如关于文化风俗的随笔《过年》,虽然批评中国人过年赌钱、吵闹等陋习,但针对政府禁止过年的做法,陈西滢却表示异议,他认为百姓一年到头辛苦操劳,难得有过年几天可以热闹庆祝一下,实在是不应该废止。
显而易见,陈西滢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随笔里充满了对青年一代的关爱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怀。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随笔并不刻意渲染抒情,也不刻意求深说教,相反,这些随笔有意节制感情,质朴亲切,同时兼具就事论事、文化批评、旁征博引、行文幽默等特点,透露出知性的思考,是很好的知性散文。解志熙在《别有文章出心裁——中国现代“知性散文”叙论》中“定性”地解释了“知性散文”的内涵:
有人注意到此类散文中的智慧、学问和书卷气,并追索到其作者从而称之为“学者散文”,也有“文化散文”以至“哲理散文”之称。这诚然于此类散文的独特品性有所感知,但距离准确的定性似乎尚有一间未达。揆诸实际,称之为“知性散文”或许更为切当些。所谓“知性”,当然有相对于理性和感性而言之意,但无须特别强调它的哲学意义如老黑格尔所言。其实这类散文的“知性”品格,乃指融会其中的一种不离经验而又深化了经验的感受力、理解力,因为它既不同于理论论述的理性化、抒情叙事的感性化,也与激情意气有余而常常欠缺理性的节制及“有同情的理解”的论战性杂文也迥然有别,所以不妨借用现代诗学中的知性概念而称这类散文为“知性散文”。1解志熙:《别有文章出心裁——中国现代“知性散文”叙论》,《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40页。
陈西滢的随笔中最能体现知性散文特点的当属《谈声誉》和《行政效率的趣剧》两篇。
《谈声誉》发表在1942年2月14日《星期评论》第42期。该文看似随意趣谈自己的经验,但却引人深思自省,很是耐人寻味,可说是陈西滢散文最高水平的代表,更是中国现代知性散文的精品。文章结合陈西滢自己的切身体验,笑谈声誉名利的虚假可笑,而又丝毫无“名利过眼烟云”的说教味。比如,作者讲述自己进校门时的一幕趣剧:
可是在一个学校教了十几年书,老是有一个信念,以为学生总不至于不认识这样的老教员。可是有一天却忽然的打开了眼。在走去学校的路上,遇到了戒严。那位站岗的兵士倒是十分的客气,他说无论什么东西只要证明我与学校有关,便可以让我过去。不幸我身上什么也没有。他又说,只要别人有证件,而又认识我,也可以让我过去。我想这不成问题,走过那条路的学生多的是。一会儿一个学生来了,我问他带了校徽没有,他说带了,兵士问他认识我不认识,他说不认识。没有办法,只好眼望他过去。问一问他是属于那一院的,他说是理学院的。我想,这也难怪,理学院的人当然不大会认识,一会儿有文学院的人来,便不同了。不久又来了一个学生,身上也有证件,而且告诉兵,我是学校的先生,于是让我通过了。一问,这位学生果然是文学院的!我正在欣幸自己想得不错,却听到他在回问“先生是不是工学院的?”从此以后,我再不敢相信一个老教员构成什么资格。以前在路上遇见学生,看他们不打招呼,还多少觉得不够礼貌,现在也不这样想了。
这段文字读来多么亲切,陈西滢就像读者的老朋友一样娓娓讲述了自己的一幕尴尬经历,尤其是讲到“先生是不是工学院的”这一发问时,真是令读者忍俊不禁,自嘲式的幽默之余,也能引起读者反思这种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的声誉的可笑。讲完自己的经验,陈西滢又转入更宏大认真的思考:
同时候的巴斯德发现了微菌,他为法国酿酒业所减少的损失,即十倍此数目,救活的人命更不用说了。一个是祸害国家的罪人,另一个是造福民族的功臣,可是当时一百个知道拿破仑第三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知道巴斯德?声誉就是这样的不合理。横尸百万、血流成河的人受了重赏不说,还享了极大的声名,在试验室中发现了救世活人的方法的科学家却往往只有少数的人知道。茶余酒后写几首诗、一本戏、两篇小说的人成了群众所景仰崇拜的大师,在图书馆里消磨了半世,耗了全副心血所著成的作品却往往卖不出几本。这也不仅是古时如此,后世还不是一样?现在知道拿破仑的人,不一定听见过巴斯德或康德,知道秦始皇的人,不一定听见过荀卿。几首小诗,永远有人们的口缘,许多高文典册,却在图书馆中堆满了灰尘。声誉是一个不容易伺候的女神。她很像恋爱,往往你去追求她,她老是溜出你的掌握;你没有希望遇到她,她却从对面来了。所以有的人,“一觉睡醒,已经成了大名”,有的人,辛辛苦到头童齿豁,也没有几个人知道。
哦,声誉原来如此不合理:广济众人者淹没无名,横尸百万的人却万世知晓。陈西滢谈声誉,既有幽默的经验自述,又有严肃的议论思考,藉此,就无须再饶舌什么大道理,而超然智慧已汩汩而出。该随笔诚可谓小大结合、收放自如,在文字内容、艺术水准、洞见智慧等方面都炉火纯青。
陈西滢发表于《星期评论》的随笔还有《行政效率的趣剧》,该文则寓沉痛于幽默,借几个人的闲谈,述说某甲君要从四川给在内地沦陷区的家属寄钱,没想到填了无数的申请书表格后,用了一年多的工夫也没能把钱寄出去,遗留在家乡的三个孩子相继饿死,太太也生了病、快不行了。可是事情还没有完——
袁问:“现在甲君怎样办呢?”
张说:“他太太还没有死啊。还不是重填申请书,把钱先汇给上海的熟人。只是说不定甲君下一次接到信,便是报告他的太太也已经去世了!这件事,从去年十一月直闹到今年十一月,还没有超过填写申请书的阶段。这样的行政效率,就是在我们贵国,也不能不说是相当高了吧?”
袁说:“你说的明明是行政效率所产生的一个悲剧,怎样偏说是趣剧呢?”
张说:“这戏还没有完场啊!大约在甲太太死了葬在义冢里以后的几个月中,甲君也许会收到准许他汇款给他太太的通知,不就成了趣剧了么?”
赵说:“也许准汇的通知到时,甲太太虽然还没有死,可是甲君因这里物价飞涨的结果,他自顾不暇,也没有钱汇给太太了!”
李说:“不,我看甲太太死后三个月或一个月,甲君又接到了通知,但非准他汇款,只是又要他去另填两张申请书!”1陈西滢:《行政效率的趣剧》,《星期评论》第3期,1940年11月29日。
这其实是一出悲剧,但陈西滢以趣剧为题,用戏谑的语调讲述一个悲哀的故事,极大讽刺了行政效率的低下。可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陈西滢的创作已臻佳境,如《谈声誉》《行政效率的趣剧》等已达到了很成熟的境界。伴随着同期的知性散文运动,陈西滢极有可能写出更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但可惜的是,随着好友刘英士主编的《星期评论》停刊,陈西滢也就停笔不作了,再加上1943年赴英国任职,更是远离了中国文坛。然而,总体而言,陈西滢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创作了数十篇随笔和政论,林林总总汇集起来,也有二十余万字,由此,那种“陈西滢因与鲁迅论战失败而隐退”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更何况,像《谈声誉》这样以一当十的散文,更是需要珍视的中国现代散文宝贵收获。
再回过头考察一下陈西滢1920年代写作的《西滢闲话》。不难发现,陈西滢散文中的知性特点一直贯穿他的创作始终。1922年,时年26岁的陈西滢结束十年在英求学之旅,回国到北大任教。面对中国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态,学成归来的他难免书生意气,满腔抱负要启蒙大众、改造中国社会,而途径之一就是借助当时方兴未艾的报刊。陈西滢1920年代的闲话写作有意借鉴英国报刊散文的写法,尤其是1709年斯梯尔创办的《闲谈家》——后因艾迪生的加入更名为《旁观者》。《旁观者》有意主动担负启蒙大众的任务,这也正好迎合了当时英国新兴阶级求知的需求。1711年3月12日,艾迪生在《旁观者报》第十期发表《〈旁观者报〉的宗旨》,开宗明义指出该报创办的初衷便是要帮助读者把自己从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竭力让道德带上机智的光芒,让机智受到道德的制约”1刘炳善译:《伦敦的叫卖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19页。,也就是说,让读者在道德和机智两方面都能得到教益。该报预设的目标读者是“空想的商人、挂名的医生、皇家学会的会员、不爱辩论的律师以及丢了差事的政治家”2刘炳善译:《伦敦的叫卖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19页。等,针对这样的读者群体,就要求朴实平易的文风,力戒刻意高深,正如斯梯尔在《闲谈家》第一期里就明确提出的:“本报之宗旨为揭露生活之伪技,撕掉奸诈虚荣、娇柔造作之伪装,推崇衣饰、言语、行为之简朴。”3陈新:《英国散文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旁观者》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这些报刊散文多采取温和宽容的态度,鼓励读者克服弱点,反对迷信、虚伪、做作、酗酒等,崇尚修生养性、节制慈善等。
正是在英国报刊散文的影响下,陈西滢开始了一系列闲话创作。他的闲话范围同样十分之广,涉及道德、迷信、事实、戏剧、电影等,针对具体问题,陈西滢取绅士态度,富于幽默、力求公允地品评时事,颇有英国《旁观者》启蒙的风范。如《捏住鼻子说话》,该文批评迷信、提倡理性,写一个河南美少年装狐仙,竟然骗得全城官员和百姓崇拜。因此,陈西滢说“中国的智识阶级和老百姓非但隔了一道河,简直隔了一重洋”4陈源:《西滢闲话》,第138、139、58、141、143页。,“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官绅本来只有拜在妖狐坛前的程度”5陈源:《西滢闲话》,第138、139、58、141、143页。。再如《东西文化及冲突》,针对梁漱溟“替社会做事,享受总要薄一点才对。我从未走进真光电影场,从未看过梅兰芳的戏,总觉得那些地方是甚可耻”6陈源:《西滢闲话》,第138、139、58、141、143页。的观点,有感而发,举董仲舒“十年不窥园”的态度,与泰谷尔(泰戈尔)“亲近自然,不必读书”的观点相对照,认为适度的休息娱乐是极其必要的。又如《共产》一文,针砭中国官员富人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世界各国所说的共产,现在无非是劳动者去共资本家的产,平民去共贵族的产,穷人去共富人的产。中国的共产就不大相同了。中国是富人去共穷人的产,官僚去共平民的产”7陈源:《西滢闲话》,第138、139、58、141、143页。,然后陈西滢举委员进公园不收门票、阔人点灯不用花钱、中西税收差异等例佐证,最后批评制度:“这样的制度不扫除,怎样能叫中国人不想做官?”8陈源:《西滢闲话》,第138、139、58、141、143页。当然,比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随笔,陈西滢二十年代的闲话显然不够成熟,时常露出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批评姿态,存在刻意公允等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毕竟年岁尚轻,人生阅历相对欠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刚刚回国就开始与鲁迅热战,这无异于对本就年轻气盛的陈西滢火上浇油,势必会影响他的创作心态。但瑕不掩瑜,《西滢闲话》1920年代仍红极一时,成为新月书店最畅销的书。
英国随笔是中国现代散文的一个重要源头,影响了不少中国作家,如梁遇春的散文集《春醪集》和《泪与笑》就明显受到英国随笔的影响。但梁遇春的随笔仍留有刻意模仿的痕迹,相比之下,陈西滢谙熟英伦文化,他本人的气质也与英国绅士相通,因此,《西滢闲话》则显得更加自然。陈西滢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实践宽容、理性,针对具体时事、观点展开讨论,注重论事析理,态度理性、议论犀利而语言泼俏,最得英国“报刊随笔”之真传。解志熙在梳理中国散文谱系时认为,“中国现代的散文其实都导源于西方的随笔,进而分别与中国固有的杂文、小品和论议文章相结合,于是分流为三”1解志熙:《气豪笔健文自雄——漫说文坛健将杨振声兼谈京派问题》,《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即:“随感录”式的战斗性杂文、“随想录”式的情调美文和“随谈录”式的知性散文。由此可见,《西滢闲话》的知性特色实开“随谈录”式的创作风格,可视为中国现代知性散文的源头,陈西滢在中国现代散文史的重要性也可见一斑。
三 战时政论:精准独到的政治洞察
陈西滢在英国所学专业是政治学,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云诡波谲的国内国际局势,他发挥专业优势,在《中央日报》《中央周刊》《星期评论》《日本评论》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有洞见的政论文。这些政论展示了他对国内国际局势精准的洞察预判,同时,一片忧国忧民之心灼然可感。
比如关于中日战争的洞察和判断。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陈西滢就在一次题为《实力的准备》的演讲中指出日军侵略中华的野心,他清楚地看到,日军在侵略之前做了很充足的准备,而中国却在各方面都无丝毫准备,既没有兵工厂,也没有发展空军。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陈西滢于8月1日发表《华北时局的解剖》一文,带着很清醒的历史意识来看待这一事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卢沟桥事件不是一件地方性局部事件,而是国家事件:
可是比较眼明的人却没有舒那口气。他们看得到,卢沟桥事件决不是局部的地方冲突。一件真正的地方的事件是不难由地方迅速解决的。何必数百列车的军士与军火,陆续的入关?何必日本国内几十个师团,或星夜出动,或整装待发?果然,三十七师后退了,日兵却没有同时后退。而华北日驻屯军司令香月,反向宋哲元提出通牒,限三十七师于两天以内,退出卢沟桥及北平,而且必须撤至保定以南。同时我赵登禹师去接防,日方又藉口人数不符,提出抗议。二十六日日兵又在廊坊挑衅,与我三十八师发生激战,我方军民伤亡至千余人。笔者草此文时,还不知廊坊战争的结果。但是一部分人的迷梦,也必定完全被飞机大炮所轰破了罢?1陈西滢:《华北时局的解剖》,《武汉日报》1937年8月1日。
陈西滢在该文中指出:日军处心积虑早就“想把华北特殊化,使华北成第二个冀东,逐渐成第二个‘满洲国’”,“不幸前年的华北自治运动,很拙劣的失败了”,加之近几年中央政府励精图治,使得华北越来越成为“中国人的华北”“华北人的华北”,所以日军分化离间华北是难以实现了,因此不得不武力豪夺。接着,陈西滢站在国际视野的高度分析了为什么卢沟桥事件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他认为此时的欧洲正自顾不暇——西班牙内战,英法美的绥靖政策唯恐战事上门,苏俄连续清党,而德意又是暗中认可支持日本的战争。在这样混乱的国际局势下,日本才敢肆无忌惮侵略中国,所以陈西滢说,这个时候“卢沟桥事件如不发生,别一事件此时必然发生”。最终,他得出结论:“大战局面已经形成。我国退无可退,和平已经到了‘根本绝望的时期’,除了焦土抗战,牺牲到底,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
陈西滢热切关注抗日战争,当听到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喜讯时,他写下《光芒万丈的台儿庄》,从地理条件、战术战略等方面分析了台儿庄胜利的原因,盛赞我军的英勇,并且指出台儿庄胜利的历史意义:
台儿庄自有它历史上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在台儿庄,中国第一次得到了大胜利:在台儿庄,日本第一次遇到了大失败。这意义还不限于这次中日战争。中国自有近代的外侮以来,在台儿庄得到了第一次的大胜利。日本自有史以来,在国外作战,在台儿庄遭遇到了第一次的大失败。所以台儿庄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台儿庄象征了日本帝国的没落。光芒万丈的台儿庄,在历史上开了一个新记录。1陈西滢:《光芒万丈的台儿庄》,《武汉日报》1938年4月10日。
台儿庄胜利带给陈西滢的喜悦激动溢于言表。面对外侮,陈西滢的民族气概溢于言表:“中国民族有了新的自信心,可以‘忍劳耐苦,奋斗到底,以完成抗战之使命,求得最后之胜利’。光芒万丈的台儿庄已经响了民族复兴的钟声。”
陈西滢精准的洞察还体现在他常常把中国抗战与国际局势相联系之分析。1939年7月,他在《中国青年》创刊号发表《抗战两年后中国在国际间的地位》,指出虽然抗战两年来中国损失巨大,但是中国在国际间的地位却大大提高了。两年来举国上下精诚团结一致抗日,英勇的战斗赢得了国际的同情。而战争也使西方人看清了事实,长期以来,日本借反共之名,行野蛮粗暴的侵略之实。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因此,英法苏应该与中国成为盟友,并且提供援助。《德义日同盟与中国》(1940)一文则反驳了走德意路线的荒谬,因为德、意与日本的目的都是通过战争统治世界。该文指出虽然英美的外交是自私的,常常因躲避战事而有负中国。但是随着德意日结成同盟,英美法等国必将会更大力地支持中国抗击日本,因此,德意日同盟将会深化英美法苏与中国的盟友关系。
陈西滢进而把观察分析的视野指向整个世界的格局。如《东方西方两个战争的分析和预测》(1940)一文就有理有据地论证了德国和日本都将不免失败的结局。德日两国都想凭借闪电战快速取得胜利,但英法美中等国后劲实力足,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在各方面都超过德日,并取得压倒性优势。德苏战争关系到整个欧洲的局面,陈西滢专门写过两篇文章来讨论德苏战争。写于1941年7月的《论德苏战争》一开始便指出德苏之前的友好协定只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德苏迟早一战。德国深知侵英将会成为一场持久战,所以便将矛头指向苏联,确信能在短时期内解决苏联,获取苏联丰富的石油资源。但陈西滢早已预测到,苏联将因地大、物博、人众抵挡住德军的入侵。一年后,陈西滢又写《苏德战争一年以后》一文,指出德军入侵苏联是希特勒发动战争以来战略上第二个大的错误,第一个是两年前未能在英国远征军敦刻尔克大撤退时乘胜追击。苏德战争将德国陷入深深的泥淖之中,因此,陈西滢乐观预测,“也许在苏德战争的两周年,我们便可以看到和平的曙光了”1陈西滢:《苏德战争一年以后》,《中央日报》1942年7月3日。。值得一提的是,陈西滢对于苏联的态度公允平正,不像当时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样反苏反共。他高度评价苏联在二战当中的作用,并且还关注介绍苏联的情况,如《苏俄的青年》介绍苏联青年成长中的收获与问题,《苏俄的思想自由》介绍苏俄的思想自由正在逐渐增长。
陈西滢关于国际局势的文章还有《太平洋战局的检讨》《对印度政治家的期望》《北非之战》等。此外,他还写有一些介绍政治制度、政治人物的政论文,如1942年11月,陈西滢在《中央日报》上先后连载了八篇对于英国文化制度的演讲文章,系统介绍了英国的政党、议会、内阁、皇室、文化背景、民族性、人才教育、报纸。这些文章足见他对英国了解的深入。还有一些讨论战略战术的政论文,如《海军与空军》(1936)指出,随着空军的不断强大,海军的重要性已经远不如往昔,并且建造一艘大型舰艇的成本也远远高于制造飞机的成本。陈西滢站在战争战略的高度,建议应该组建独立的空军管理部门,大力发展空军。再如,《关于游击战》(1938)探讨战术战略。陈西滢反对那种忽视游击战而一心焦土抗战的主张,也反对过分夸大游击战的作用。游击战虽然起不到大规模打击敌人的效果,但可以成为正规战的有效辅助战术。该文对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和中国国情的分析是很客观到位的。
综上所述,陈西滢对于国际局势的分析,能够站在“多边主义”的角度,把各国之间的策略放在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中,条理清楚地梳理呈现这些复杂的关系,进而得出结论,足见他在国际局势方面的洞察和远见。他的政论文对时局的剖析和预测大都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在当时曾引起日本论敌的敬畏。遗憾的是,1943年调任英伦后,陈西滢就此搁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