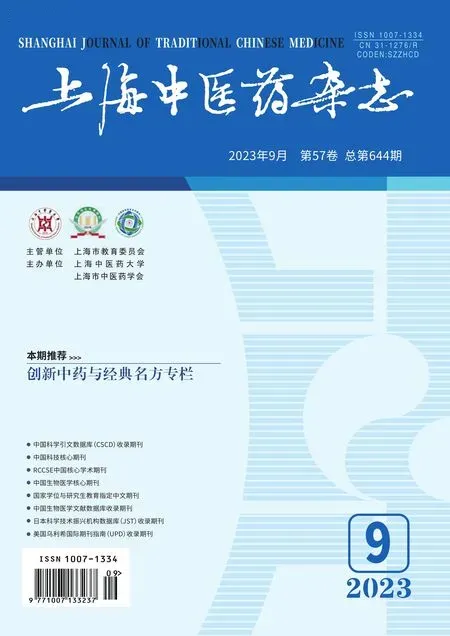基于“宣可去壅”探讨辛味药在抑郁症治疗中的应用
2023-10-03冯秋涧陈颖君
冯秋涧,赵 捷,赵 明,张 震,陈颖君,曹 宇,裴 卉
1.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2.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老年科(北京 100091)
抑郁症作为临床常见疾病,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以心境低落为主的精神疾病,其发病率高达10%[1]。中医对于抑郁症的认识和研究由来已久,且不断发展完善。基于各医家的论述和见解,抑郁症可归属于中医学“郁证”“癫证”“脏躁”等范畴。情志因素是抑郁症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随着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加,抑郁症的患病率也呈现上升趋势,预计到2030年,抑郁症将成为全球致残率最高的疾病[2-3]。中医学认为,抑郁症以“气机郁滞”为首要病机,与肝、肺密切相关。实际上,临床中气滞、血瘀、痰凝、火热、本虚等病机均可导致气机不畅进而壅滞,诱发抑郁[4]。气机郁滞不仅会加重上述病理变化,还可与上述致病因素相互搏结,阻碍气机,壅滞难化。正因如此,抑郁症患者多存在病情迁延反复、治疗周期较长等特点。“宣可去壅”理论源于《本草拾遗》,指应用宣散疏通、开达郁结的药物治疗以壅滞为主的内伤杂病。我们结合抑郁症以“壅滞”为主的特点,将特性宣散的辛味药进行组合,辨证运用,临床疗效显著,现分析如下。
1 “宣可去壅”理论渊源
“宣可去壅”首见于《本草拾遗》,书中将其归为“十剂”之一,并明确其用药思路为“宣可去壅,即姜、橘之属是也”。姜即生姜,味辛微温,因其辛温可发表散寒、宣肺温脾,故谓之“宣”;橘即橘皮,味苦辛温,借其辛温可理气化湿、调中化痰,亦谓之“宣”。由此可见,“宣”者可升可降,既可外达腠理,又可调和中焦,尤以“理气机”为要。赵佶《圣济经》中对于“宣可去壅”理论进行了详细解析:“郁而不散为壅,必宣剂以散之。”由此可知,郁滞不散皆为壅。
后世医家秉古推新,对“宣可去壅”理论进一步丰富并扩大其临床应用范围。金元时期,刘完素、张子和均认为宣散郁火的栀子豉汤可列入宣剂[5]。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宣者,布也,散也……不独涌越为宣也。”即凡可使气机布散的方法均属于“宣”法,不应将其局限于涌吐、发越之法。清代陈士铎在《本草新编》明确“宣”法之旨为:“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皆宣之谓也。”因此,凡具有“宣通”性质,可使“邪去正安”的治法都属其范畴,如行气、活血、化痰、散火、滋阴、温阳。
辛味药禀“宣可去壅”的特性,如香附、川芎、陈皮、藿香等,善于畅达一身之气机,且常兼理气、活血、化湿、醒脾等功效。我们认为,尽管有些辛味药存在寒、热等偏性,但适量应用并加以配伍,对于治疗抑郁症这类病机以本虚标实为主的疾病,恰到好处。
2 基于“宣可去壅”辨治抑郁症的病机基础
《灵枢·本神》曰:“愁忧者,气闭塞而不行。”即气机阻滞则生愁忧。后世医家以此为基础,对于郁证病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述。张景岳曾言:“郁则结聚不行,乃致当升不升,当降不降,当化不化,而郁病作矣。”因此,抑郁症以气机郁滞为首要病机,痰、瘀、火为重要环节,以正气虚损为结局。
2.1 气机郁滞为首要病机 《素问·生气通天论》载:“阳气者,精则养神。”气机郁滞、清阳不升,可使神失所养、精神不振;其次,气在体内具有温煦、推动等重要作用,气机郁滞则温煦无权、推动无力,各脏腑机能随之下降,精神萎靡、肢体怠惰。因此,抑郁症的形成以气机郁滞为肇端,肝、肺郁滞为其始动因素。
肝主疏泄,喜条达而恶抑郁。肝木调达则气机升降出入有所主,诸病不生;肝失疏泄则气血津液运行失常,变生诸郁。因此,肝失条达最易成郁,即《丹溪心法·六郁》所言“诸郁皆属于肝”,气郁之生亦不外乎此。
除肝失疏泄外,肺失宣降也可导致气机郁滞的发生或加重。肺主一身之气,其宣发肃降功能主宰一身之气的正常运行;宣降平衡失调,气机运行失常,无法周流全身,闭塞于体内,则肺气郁结,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诸气愤郁,皆属于肺”。
2.2 痰、瘀、火为重要环节 本病始于肝、肺,以气机郁滞为先。因此,气机运行受阻、推动无力则可见痰、瘀、火等邪,而这些病机又会停滞体内阻碍气的循行。如此交互作用,成为抑郁症患者病情迁延难愈、不断反复的重要病因。
首先,气机郁滞可生湿化痰,亦碍于食。由于气郁多成于肝,而肝木克伐脾土,故抑郁症患者多兼脾胃功能的失常。脾主运化水液,脾失健运,运化失常则津液输布不利,可聚湿生痰,痰蒙清窍,发为抑郁。另外,脾胃为气机升降之枢,痰湿阻滞则枢机不利,又可加重气机壅滞。
其次,气机郁滞多导致血瘀的发生。《丹溪心法·六郁》言:“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人身之气血相伴相随,气机失常可使血的运行不畅,日久可致血瘀,即《临证指南医案》所云:“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瘀血易阻气机,因此瘀血的形成可导致血瘀气滞、气滞血瘀的恶性循环,从而加重抑郁症。研究[6]发现,血瘀是中医证候要素中反映郁病轻重程度的一个因素。
《丹溪心法》载:“气有余便是火。”气郁日久,阳气郁遏不疏则化火热。火为阳邪,易耗气伤津、扰神动血,即《临证指南医案》所载:“因情志不遂,郁而成病,郁则气滞,气滞久则必化火热,热郁则津液耗而不流,升降之机失度,初伤气分,久延血分,延及郁劳沉疴。”因此,随着疾病的不断发展,气郁日久而火热渐生,既可以扰动神明而见失眠焦虑、急躁易怒等情志异常,又可炼液为痰、血结为瘀而加重其郁,还可耗损气血津液成虚,继而形成虚实夹杂之抑郁症。
2.3 正气虚损为结局 抑郁症初起多为实,进一步发展则由实转虚,最终形成虚实夹杂、迁延难愈之疾。气机郁滞可导致气血郁于局部、运行不利,日久气血虚少可转虚;其次,气机郁滞日久化火可损耗正气,气血津液因之耗竭亦可转虚;最后,痰湿可困阻中焦,后天之本因之失权,气血津液无以化生亦可致虚。因此,正虚为郁证久病不愈的继发之证,而正虚形成后又可因虚致实,加重各种病理产物的郁滞,它既是疾病发展转归的最终结局,又是疾病进一步发生发展的加重因素,临床不可不察。
3 基于“宣可去壅”探究辛味药辨治抑郁症
辛为五味之一,清代汪昂《本草备要·药性总义》将其特性描述为“辛者,能散、能润、能横行”。现代《中药学》基于此将其能化、能补、能润、能通、能升等作为引申功效[7]。辛味属阳,五行属金而归于肺,走于气分而主动。因此,辛味药能以“动于气分”解“壅滞”之疾,符合“宣可去壅”之旨,也契合抑郁症的基本病机及治疗原则,分而言之则能行、能化、能散、能通、能补、能润,辨证施治,巧妙配伍可增强疗效。
3.1 辛能行,行气以宣 《灵枢·五味论》云“辛走气”,畅达气机为辛味药的核心作用,理气药大都具有辛味。在诸理气药中,治郁首重柴胡。柴胡味辛入肝胆经,有疏肝解郁、升举阳气之功,《滇南本草》谓其“行肝经逆结之气,止左胁肝气疼痛”,最能舒达肝木,调畅周身气机。枳实作为调气机之品在郁证治疗中同样重要。《名医别录》载枳实能“破结实,消胀满、心下急痞痛、逆气”,由此可知此物药性较猛,不可久用以免耗气,合理应用可除气郁。香附作为“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实属解郁之佳品,《滇南本草》谓之能“调血中之气,开郁,宽中”。香附气血同调、肝脾并治,对于抑郁患者气机郁滞继而血行不畅者尤宜。除上述经典用药外,后世医家尊古推新,进一步丰富辛味药在抑郁症中的应用。如王彦刚教授常用香橼、佛手,通过其辛香之性可疏肝理气,顺应肝升发之性,进而透达肝胆之郁[8]。
治郁不调肺,非其治也。肺气升降有常,可使一身之气运行不怠。清代《续名医类案》载一郁证医案,用“紫菀、干葛宣肺之气,枳实、桔梗散胸中之结,杏仁、苏子导肺中之痰,一剂而神清”。方中紫菀苦辛温,能下气消痰,治胸胁逆气。因其辛而能宣、苦而能降,宣降相合最宜调肺。桔梗作为舟楫之药能升能降,李杲谓其能“利胸膈,破滞气及积块,除肺部风热”,实为宣气机、开肺闭之要药。杏仁、紫苏子为味苦降气之品,临床用之多配味辛之麻黄。麻黄轻清宣透,入肺经而善走窜,邹澍谓其能“彻上彻下,彻内彻外”,为开肺气郁闭之要药;与杏仁相伍则辛苦相合,升降相因,可复肺气周转之常。
3.2 辛能化,化痰散瘀以宣 痰瘀作为抑郁症常见的病理产物,以辛味药治疗不仅可化痰散瘀以治其标,更可调畅气机以疗其本,为标本兼治之法。
3.2.1 辛能化痰 痰湿由津液停滞不化而成,治疗时常以行散之辛味药化痰祛湿。化痰之方多以二陈为宗,以味辛之半夏、陈皮为君药。半夏辛温而入脾胃,辛以开泄走窜,可荡涤痰浊,又善燥湿,可绝生痰之源,即脾不留湿则无以生痰。陈皮为调气以化痰之品,临床治痰常与半夏配伍。陈皮兼备苦味,故调气之功散中有降,且陈皮入肺脾二经,为上中二焦同调之品,《药性论》谓其“治胸膈间气,开胃”。因此,二者配伍既可增强畅气化痰之功,还能使其治疗范围由中及上、肺脾同调,更能寓降于宣,防止过于辛散而致气逆。
3.2.2 辛能散瘀 气行则血行,气机郁滞、推动无权可致血瘀,治疗时可以辛味药之行散,畅气机、开瘀结。川芎味辛而善动,为血中气药,因其辛温走窜故行气于血,因其行气故周身可达,正如《丹溪心法》所言可“解诸郁”。郁金味辛苦而性寒,功善活血解郁,可通畅一身之气血,散一身之郁滞,《本草汇言》谓其“性轻扬,能散郁滞,顺逆气,上达高巅,善行下焦,心肺肝胃、气血火痰郁遏不行者最验”。
3.3 辛能散,郁火以宣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言“火郁发之”,又曰“辛以散之”,因此辛散为散郁火常用之法,在郁证兼见火邪的治疗中有独到作用。淡豆豉作为治郁火名方栀子豉汤中的重要药物,为发散郁火之主将。淡豆豉辛散宣通,《本草汇言》曰“此药乃宣郁之上剂也。凡病一切有形无形、壅胀满闷、停结不化、不能发越致疾者,无不宣之”。与栀子等寒凉之品配伍,合理应用,更可收清解郁热之功。除淡豆豉外,薄荷也为散郁火、畅情志之佳品。薄荷味辛性凉可散郁火,质地轻清可去停滞,“尤善解忧郁……入肝胆之经,善解半表半里之邪,较柴胡更为轻清”(《本草新编》)。
3.4 辛能补,“阴中求阳” 辛味作为五味之阳,其性最动。所谓“动则生阳”,辛味药可助阳气振奋化生。补益之药性多滋腻,易滞气机,补虚效果往往不佳。因此,若性缓凝滞之阴药配以辛散善动之阳药,补益因此而效,即“阴中求阳”也。
辛味药用以补益虚损常与补气养血、滋阴助阳之甘味药合用,正所谓“辛甘化阳”是也。临床应用时,两种药物之间的比例及剂量的使用,应根据患者病程长短、病情轻重综合考量。“辛甘化阳”的代表药对为桂枝配甘草,临床观察证明,在治疗中加入桂枝和甘草可有效改善抑郁症患者的一些症状[9]。桂枝味辛甘且性温,纯阳无阴,专入心肺二经而上行,振奋心阳。其与甘草相配,能缓急以平不安,能调节以解纷争,能化阳以补不足,能培土以抑木侮,适用于抑郁日久、由实转虚者。附子性大热,味辛甘为纯阳之品。其能入肾以补真火,温真阳;又能走诸经、达周身,使十二经脉通利、脏腑官窍无阻。附子温元阳之力强,凡抑郁而致阳虚者无论损及何脏皆可用之。且附子能补火暖土,助先天而资后天,因此抑郁而见脾脏虚寒、气血不足者亦可酌情应用。
3.5 辛能润,“阳中求阴” 《素问·藏气法时论》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气也。”由此可见,辛能润并非以补增液,而是以通布津。津液属阴而宁静,唯有借气之推动方可布达周身。气机壅滞则津液不布,津液不布则机体失养,机体失养则诸燥变生,表现出急躁易怒、紧张焦虑、躁扰不宁等异常症状。此时,虚为其标、壅滞为其本,仅以养阴生津之品无法使津液直达病所。唯有“阳中求阴”,以辛味开其郁闭,布达津液方能使诸燥得解。因此,“辛能润”是从另一种角度对其舒畅宣发之性的阐述。例如,李跃华临证治疗心肾阴虚型抑郁症,常用仙茅、淫羊藿、巴戟天等辛温之药温补阳气,阳中求阴、辛温发散以布达其阴,从而阴阳和化,平和解郁[10]。
4 验案举隅
刘某,女,39岁。初诊日期:2022年12月1日。
主诉:持续性情绪低落6个月余。
现病史:患者1 年前因母亲去世悲伤欲绝,出现情绪低落,默默不语,曾于当地医院就诊,给予疏肝解郁中药治疗,效果不佳,遂来就诊。刻下症见:情绪低落,悲伤易哭;胸部满闷,气短,倦怠乏力,咽部不适;时有怕冷,呼吸急促,不思饮食,入睡困难;小便可,大便二三日一行;舌淡红、苔白腻,脉弦紧。
西医诊断:抑郁症;中医诊断:郁证(肺郁痰扰);治法:宣肺解郁,行气化痰;方予泄郁汤加减。
处方:蜜紫菀15 g,桔梗10 g,炒苦杏仁10 g,紫苏叶10 g,醋香附10 g,炒蒺藜6 g,麻黄6 g,砂仁6 g,半夏10 g,黄芪15 g,生甘草6 g。每日1剂,水煎,早晚分服。
二诊(2022 年12 月15 日):患者诉情绪稍好转,胸闷、咽部不适减轻,食欲增强,未见呼吸急促,仍气短、乏力、失眠;舌淡红、苔白腻,脉弦紧。前方加合欢皮10 g、夜交藤10 g。服法同前。
三诊(2023 年1 月3 日):患者精神状态改善,时有笑容;胸闷明显减轻,未再出现气短,乏力、睡眠好转,大便可;舌黯红、苔白腻,脉弦。前方继进。
患者继续服中药治疗1 个月后,未再出现心情低落、悲伤易哭,而是面带笑容,其余症状亦均不明显。纳、眠可,二便调;舌淡红、苔薄白,脉弦。
按本例患者发病起于情志因素,因悲伤过度、情志不舒,导致肺气郁滞,故见情绪低落、胸部满闷、气短、呼吸不畅、倦怠乏力等表现;肺气郁滞,水液运行不畅,聚湿成痰,痰扰清窍,故失眠;痰气阻于咽喉,故见咽部不适,痰湿碍于脾胃,故不思饮食。综合其症状及舌脉,为肺郁痰扰之象,故治疗采用“宣法”宣肺解郁、行气化痰以“宣其壅滞”。桔梗、紫苏叶、麻黄开宣肺气,紫菀润肺下气,杏仁降气,香附、蒺藜散肝郁、开肺气、宽胸利膈,用以治疗肺气郁滞之症最为恰当。半夏是一药而兼二职,一是化痰,二与桔梗相合,具有解郁利咽之效。黄芪补气以助开肺郁,砂仁行气开胃,甘草调和诸药。诸药合用,使肺气得宣。二诊时失眠仍重,故加以合欢皮、夜交藤解郁安神宁志,以助睡眠。其后,患者邪去病愈。
5 小结
抑郁症作为以情绪低落为主要症状的精神疾病,以“壅”为病机关键,以宣散为治疗要点。“宣可去壅”首见于《本草拾遗》,为治疗壅塞不通类疾病的有效方法。而辛味药因其行散之力,最能秉“宣可去壅”之旨以行气、化痰、祛瘀、散火、温阳、润燥散其壅滞,临床中根据具体情况辨证应用能畅达周身、疏通气机,使壅滞得去,郁证自除。因此,本文将“辛以宣壅”作为着眼点,对于辛味药在抑郁症中的辨证配伍进行探究,以期为抑郁症的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