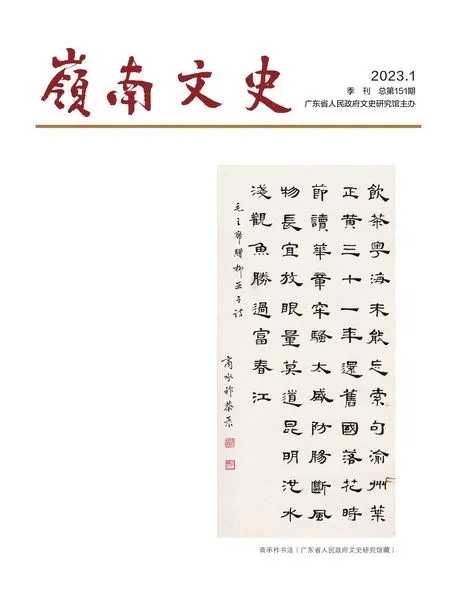唐代休咎禅师与广东灵化寺、海光寺的关系辨析
2023-10-03杨宪钊
杨宪钊
扶胥港是唐宋时代广州海上丝路的重要港口,除南海神庙外,尚有佛教寺宇落户于此,灵化寺与海光寺即为其中著名寺庙。在海运史上,民间流传休咎禅师度化南海神,而使其性情温顺,船毁人亡现象得以缓解的历史故事,史书与佛教典籍也记录此事。在这则故事的宗教语境下,神庙与佛寺并行不悖,扶胥港成为人们修佛拜神的停泊之地,在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因此,扶胥港不仅是本土宗教祭祀海神的圣地,而且是外来宗教佛教的重要道场。从宋代起,扶胥港海光寺即灵化寺的观点早已出现。然而,两寺是否为一寺?建立在何时?又与东莞海光寺有何关系?三寺分别与唐代著名高僧休咎禅师有何关联?休咎禅师的道场究竟是哪所寺庙?对于这些问题,明清方志记载也有错漏,亦有不少穿凿附会,学界对此并无专文加以探讨。笔者试图考察其真伪,以益于晋唐佛教传入期岭南佛教的研究,并进一步深化对岭南方志的认识。
一、三寺之文本记录
目前流传下来最早记载三寺的是广州海光寺。《太平广记》卷34《神仙》言:
“贞元中,有崔炜者,故监察御史向之子也。向有诗名于人间,终于南海从事。炜居南海,意豁然也,不事家产,多尚豪侠,不数年财业殚尽,多栖止佛舍。……后数日,因游海光寺,遇老僧赘于耳,炜因出艾,试灸之。”[2]
这段讲主人公崔炜离奇曲折故事的论述,提到崔炜游览海光寺一事,从中可知唐贞元年间(785—805)已有海光寺,且有一定知名度。
对灵化寺的记载,北宋广州刺史蒋之奇作《灵化寺记》,全文收录在明成化《广州志》中,其中言:
广州扶胥口灵化寺者,休咎大师之道场也。大师姓梁氏,新兴郡人,卯岁出家,寻师慕道,遂游东都,圣善寺则天坛受戒,巡礼天下名山祖塔。还游罗浮山延祥寺,传三乘行业,广度群迷。至天宝十二年,本道节度使李复响师道德,遣兵马使李玉往罗浮迎师还番禺供养。……师比明出庙至其地,遂开基址,建草庵,即今寺也。自是僧众相继,住持不绝,号花果院。[3]
蒋《记》不仅提到灵化寺是休咎大师的道场,且言明休咎禅师最初是在罗浮山修悟,唐天宝十二年(753)被节度使李复迎至番禺,后建灵化寺。灵化寺最初为草庵,号花果院。而明成化《广州府志》的撰者王文风在记载灵化寺时,却与蒋《记》有明显出入:
灵化寺,在郡东扶胥口,休咎禅师道场也。师,梁氏,新兴人。唐武后时游罗浮山。元和间节度使李复即罗浮,迎师至扶胥镇。[4]
王氏言休咎禅师武后时在罗浮山,到唐元和年间(806—820)被李复迎至番禺扶胥镇,中间相隔近百年,似不可信。显然王氏在全文摘录蒋《记》时是明晓此记所言休咎禅师到达扶胥的时间,然王氏并未苟同其说法,而是另言时间,王氏的论点根据应是源于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89:“休咎大师,姓梁氏,新兴人,武后时游罗浮山,元和间至番禺县扶胥镇。”[5]明清记载休咎禅师传记的方志,多沿袭王象之的表述,其他尚有记载南汉乾和年间(943—957)的,以明万历《广东通志》为最早:“乾和中节度使李复初迎师至扶胥镇”[6]。他志多因循于此,从蒋《记》中休咎禅师事迹去思考,则更为错误。那么,究竟是唐天宝十二年(753)还是唐元和年间休咎禅师抵达扶胥?蒋之奇与王象之说法谁更为确切?两者皆为宋人,由此可见,宋人的某些模糊观点完全在于明清方志书写中,而明清方志书作者并未对这两种说法有任何的考析辨证。
不仅休咎禅师抵达扶胥建寺的时间有错漏,且在宋代广州海光寺与灵化寺的关系上更为笼统化。《舆地纪胜》卷89言休咎禅师“至广州,住海光寺,卒赐谥休咎大师,寺今为灵化寺”[7]。海光寺即灵化寺的这一说法,先后被清道光《广东通志》卷229《古迹略十四·寺观一》和光绪《广州府志》卷88《古迹略六·寺观一》收录,其他方志并未采用王象之的说辞。明清两代方志书作者对王象之这一说法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出这一说法的真实可靠性存疑。
最晚被记载的是东莞的海光寺。明万历元年(1573)设新安县,即今深圳市。海光寺又归新安所管辖,是深圳历史上最早的寺庙。将东莞海光寺与休咎禅师联系上的最早文献是明天顺(1457—1464)《东莞县志》。该志卷三《寺观》言:“海光寺,在县南二百五十里东莞场正,与南山相对,乃休咎禅师道场也。”[8]而《东莞县志》和《新安县志》也在《仙释》中为休咎禅师立传,清雍正《东莞县志》在休咎禅师传记后明言:“海光寺在东莞所,南汉时铁佛犹存,今属新安。”[9]显然是将广州海光寺与东莞海光寺混淆。
二、三寺关系之考证
方志记述中对唐代广州灵化寺、海光寺与东莞海光寺存在着讹错失真现象,笔者试加以考证厘清原委。
关于灵化寺建立的时间,笔者认为应是唐贞元年间(785—805)。前文文献记载只是不确定休咎禅师到达扶胥镇的具体时间,但无一例外肯定迎接休咎禅师的主要人物是节度使李复。检阅《旧唐书》卷112《李暠附复传》可知李复是李唐宗室,活跃于唐代宗与德宗两朝,唐贞元十三年(797)去世,年59。[10]有研究表明,李复任职岭南东道节度使是在唐贞元三年至八年(787—792)。[11]依此,可以推断休咎禅师到达扶胥镇的时间是唐贞元三年至八年。据此,笔者认为:灵化寺建立的时间是唐贞元年间,且在贞元前期。那么,海光寺和灵渡寺都在唐贞元年间出现,且都位于扶胥镇,是否说明两者为一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两者具体地理位置不同。海光寺“在波罗庙左侧”[12],也就是说海光寺与南海神庙的位置紧邻,民间有言“东佛西玄,护卫一官庙”,玄指凝真观,官庙指南海神庙,而佛即海光寺。灵化寺,蒋之奇在撰写南海王与休咎禅师的故事时,言休咎禅师欲乞南海神庙为伽蓝,南海王当然不许,但却为师别择他地:“已于扶胥北得一处,去此五里,以纸钱定四隅是已。”[13]宋人方信孺据此认为灵化寺“在扶胥之北五里”[14]。后世方志也多借用方信孺的言辞。从中可知,灵化寺与南海神庙相隔五里之远,南海神庙位于扶胥镇西南,故海光寺也当位于扶胥之西南,而灵化寺位于扶胥之北,显然不可能是同一所寺庙。
其次,在休咎禅师的传记中,大多都言明休咎禅师修建灵化寺居住,后到海光寺住持,并最终于唐元和年间(806—820)圆寂于海光寺。尽管传记记述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但两寺与休咎禅师的关联确是有先后之分,不易混杂。考其泉源文献,则为蒋《记》言:
“师复至庙语王曰:‘贫道受请入城,故来告辞。窃闻大王为性严急,往来舟楫遭风波溺死者甚多,王慎毋为此,贫道今为大王摩顶受戒,自兹已往,勿害生灵,保扶社稷。’即为授三皈五戒而行。时节度使司遣巡海将何仿往东莞取海光寺额归,改城中西□院为海光寺,请师主持终焉。实元和二年七月五日也,寿六十二。是年冬十月,敕赐谥号为休咎大师,普通之塔。”[15]
此段记述阐明休咎禅师初至南海神庙后,曾有再次莅临。这次的目的是为南海神摩顶受戒,以保扶社稷。故事实际上是佛家借助人神对话,宣传佛法无边,藉此抬高身价。[16]正是源于此,灵化寺一直兴盛至元代:“自元季以来,寺亦隳毁,惟存佛堂以奉香火而已。”[17]而海光寺则是休咎禅师第二次光临南海神庙时才建立,也就是说灵化寺在先,海光寺位后。且海光寺的建立是由城中西□院改建而成,与灵化寺由休咎禅师建造截然不同。海光寺也不同于灵化寺至元季已经倾颓,清乾隆《番禺县志》卷5依然记载“海光寺在今波罗庙旁”[18]。至此,基本可以断定两座寺庙是不同的寺庙。
扼珠江口内要塞的扶胥镇,是广州城东歇息和中转之地,而南海神庙是人们出海和归航的祭祀场所,便利的交通和官方的神庙,扶胥港成为南海县乃至岭南的一方名镇。[19]这样的名镇,对于崇尚风水之说的僧侣而言,无疑是俱佳的吉地所在,寺观庙宇纷纷落户于此,不足为奇。著名史学大家罗香林认为,海光寺的建立与佛教东传有关,海光寺是梵僧沿海上丝绸之路东来的停居地:“南海神庙为唐宋时海舶入粤所必经行祷祀之大庙。海光寺建于其侧,殆亦兼为梵僧居停也。”[20]直接道出了扶胥港海光寺与海上贸易的关系。因此,扶胥有灵化寺与海光寺两座著名寺庙,也是经济社会各元素推动的结果,属合理现象。
明白海光寺即灵化寺这一错误的问题后,再探讨广州海光寺与东莞海光寺的关系。两者皆名海光寺,前文蒋《记》已经提及是巡海将何仿往东莞取海光寺额归,改城中西□院为海光寺,也就是说东莞海光寺在唐贞元年间(785—805)以前即已经存在。也就是说,今深圳历史上最早的寺庙就是这座海光寺。当时的海光寺有一定的知名度,可能由于破败等缘由,寺额被广州海光寺所占用,而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官府,所以这一行为是有其合法性的。广州海光寺是在官府支持下建立的,隐然有“官寺”的身份,延请休咎禅师住持后,名僧、官寺、地理位置的因素,显然广州海光寺已成为唐代重要的寺庙。而东莞海光寺至南汉时期才又重新兴起:“海光寺,旧在县西观音堂后,徙于南门外。传南汉时有铁佛在海中,夜有光,因祀之于寺。又有石鱼,亦南汉时物,今废。”[21]广州海光寺与休咎禅师有密切的关联,并未与东莞海光寺有任何关系,也未有任何文献记述休咎禅师到过东莞境内。笔者认为,方志将休咎禅师列入东莞志与新安志,是不妥之举。但也并非所有东莞、新安的方志皆将两者混淆,如清嘉庆《新安县志》卷21即对此怀疑,并删去了休咎禅师传记:
按旧志载有唐休咎禅师、大鉴禅师二则。但云休咎,乾和中,节度使李复初迎至扶胥镇,憩南海王庙,谒王,因留住海光寺。查郡志及番禺志,俱称海光寺在波罗庙侧,则休咎住锡处,乃番禺扶胥镇之海光寺,非安邑南门外之海光寺,明矣。大鉴虽有像塑于今海光寺,然当年实未到此,与邑无涉,故郡志已将列入南海,今皆从删,以昭传信。[22]
三、结论
历史上,由于文献缺乏的关系,对宋以前的记述颇多错漏疏忽之处。明清时期的方志书写者多秉承宋人对唐代历史的观点,更易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甚至同一本书出现自相矛盾的说法。宋明时期,珠三角地区不断推广礼教,扶持了一群以保障“礼教”为己任的士人,通过这些礼仪,珠三角得以归入国家“礼教”的秩序之中。[23]而这种规范的礼教,是以书院和社学作为士大夫教化的据点,日益世俗化的寺观无疑成为其重点打击对象,明嘉靖初魏校毁淫祠就此诞生。在这种背景下,方志书写者也就不可能对寺观着墨过多,多将其列入《外志》《杂志》等篇章中。如戴璟所修的明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广州府就只记录了十二所寺庙。[24]更多的做法是将前人的记述不加考辨,全盘端用,给今人研究岭南佛教史带来诸多困难,其中唐代广州灵化寺、海光寺与东莞海光寺即是鲜明的案例。
通过梳理三寺的文本记述,考察其三者的关系,笔者推论出以下结论:灵化寺建立的时间是唐贞元年间(785—805)。灵化寺与广州海光寺为同一时期两座不同的寺庙,灵化寺建立在前,广州海光寺建立在后;广州海光寺的寺额取自东莞(新安)海光寺,东莞海光寺在唐贞元年间以前即已存在,是今深圳历史上最早的寺庙,两寺并非同一所寺庙,而广州海光寺是休咎禅师的道场,休咎禅师与东莞海光寺并无任何关系,也无文献记载休咎禅师本人到过东莞境内。故笔者认为东莞、新安等各版本县志将休咎禅师书写在《仙释》中,存在讹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