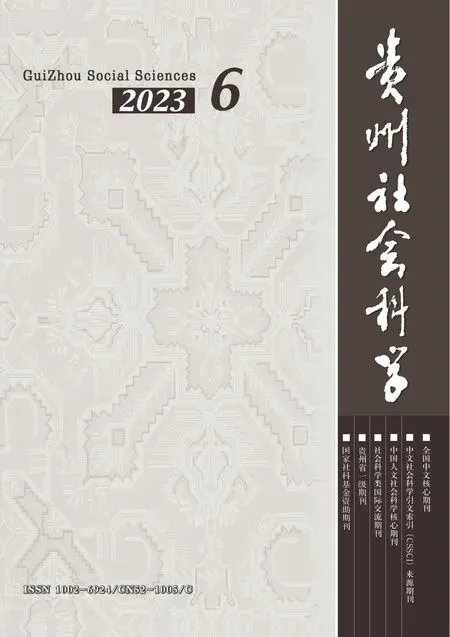20世纪30年代苏联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构建
2023-09-28吕卉
吕 卉
(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570228)
苏联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构建于20世纪30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颠覆了俄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村社会关系和农民日常生活,尽管至今评述纷纭,但是农业集体化运动有力推动了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形成和发展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有了集体农庄,广大农村才能历史上第一次覆盖了医疗卫生体系。集体农庄巨大的动员能力能够高效集中物质资源,其中一部分用来维持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集体农庄是保持农村社会日常生活条件健康运行的保障,在意识形态、财政和组织方面均能为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支持。农村医疗卫生面貌的改善也被视为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积极成果,吸引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最终促进农业集体化运动全面完成,同时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关心农民福利的有力佐证。
苏联史学主要以社会政治经济的宏观进程为研究对象,较少反映重大历史进程中的日常生活问题,农村医疗卫生未能成为关注重点。1930—1940年代的研究多阐述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积极变化,强调集体农庄制度的优越性和对农村医疗的推动作用,如巴特吉斯的《苏联卫生20年》。①1950年代后期研究范围开始扩大,科纽斯②和列维③论述了妇幼保健政策,维诺格拉托夫分析了1930—1934年④和1935—1940年⑤两个阶段农村医疗的优势和特色。相关研究还散见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全景论述中,如维尔灿的《伟大的卫国战争前夕的苏维埃农村1938—1941》⑥和泽列宁主编的《苏联农民史》第二卷《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变革时期的苏维埃农村:1927年末—1939年》,⑦二著阐述苏维埃国家在卫生运动、消除传染病和降低死亡率方面的成就,但对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困境和不足缺乏关注。1990年代后,史学界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发生了根本变化,从一元变多元,研究的优先项也从社会发展变化向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转变,作为社会成分的个体进入研究视野。斯克里科⑧从宏大的社会实验视角解读农村医疗卫生政策。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形成交叉学科,拓展微观史学新领域,格拉茨科娃⑨探讨了苏维埃卫生观视域下的农村女性医疗。列宾娜⑩认为苏联医疗卫生体系兼具“关怀”和“监控”两种职能。这些研究力图客观反映历史事件,肯定农业集体化对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帝俄与苏维埃政权初期的农村医疗卫生状况
(一)被排除在正规医疗外的帝俄农民
俄国国家医学发端于伊凡四世治下,1581年建立了俄国史上第一个国立医疗机构,1594年戈杜诺夫将其改造为医务衙门。医务衙门的主要职能是为王室、贵族和特种常备军提供医疗服务,供应草药,预防流行病,邀请外国医生和培训本国医务人员。医务衙门无暇顾及农村,农民普遍采用民间医疗手段,巫医盛行。
彼得一世时期,俄国医学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1721年取缔医务衙门成立卫生厅,1763年将卫生厅改组为医学委员会,开设了第一家医院。1720年圣彼得堡成立了第一家国家医疗采购工厂,用国内原材料制造药品。1755年创立了第一所医科大学。177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颁布法令,开始向平民提供药品。1864年之后,34个省和地区的农民获得了正规医疗服务。
20世纪初,俄国传染病发病率位列欧洲第一,天花、霍乱、鼠疫和疟疾等疾病肆虐。农村没有下水道,卫生条件恶劣,因病致贫非常普遍。直到1917年俄国也未能建立统一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内务部、国防部、红十字会和地方机关都履行医疗卫生职能,国家、社会、私人和慈善机构均参与其中。医疗服务基本是有偿的,农民因贫困无力购买药品。由于国家医疗支出严重不足,慈善机构在医疗筹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统一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就不能统筹解决国家医疗问题、控制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改善卫生条件。临时政府尝试建立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未及成功。
(二)1920年代“公共免费”医疗原则下的城乡差距
列宁充分意识到建立医疗卫生体系对于新生政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在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监督下成立卫生部,由巴尔苏科夫领导,为士兵和工人提供医疗援助,筹建国家医疗卫生体系。1918年6月,谢马什科在全俄医疗卫生大会上提出“公共”和“免费”的医疗原则。7月11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组建卫生人民委员部法令》,这是苏联医疗卫生体系创建的起点。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卫生人民委员部管理条例》规定,卫生部是领导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最高机构,明确了卫生部的权利和义务,合并包括军事医学部门在内的全国医疗部门。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国家卫生法案,目的是推动卫生立法、广泛开展卫生运动、科学卫生饮食和预防流行病。这一年,列宁的很多工作都涉及到医疗卫生:谈话强调流行病防治的头等重要意义,签署法令征召医助服兵役,讨论战场流行病防治措施等问题。年底,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宣布将医疗卫生事业列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认为斑疹和伤寒是“俄国不文明、贫困和愚昧无知的恶果”,是威胁社会主义存亡的“第三种灾难”。列宁亲自发动了抗虱战役,提出“或者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的宣战口号。
1924年,苏联开始创立社会化医疗卫生系统,即著名的谢马什科模式:国家统筹、封闭预算、统一救助、免费共享。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惠及大众的免费医疗模式一直运行到1989年。谢马什科模式医疗卫生体系在应急事件中具有快速、专业的动员能力。
20世纪20年代的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在城市范围开展,受益人群为被布尔什维克视为社会基础的工人阶级。干部医疗享有特权,由于国内医疗薄弱,官员都在亲属陪同下出国治病。城乡医疗卫生之间存在鸿沟,市民有医疗保险,可以免费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和度假疗养。农民没有医疗保险,休病假和产假没有工资,新生儿没有补贴。农村严重缺医少药,城市医生宁愿失业也不愿去农村工作,农村医生比例仅占10%。
二、农业集体化运动推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
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内容广泛,包括疾病防治、卫生监督、健康教育和妇幼保健等,涉及医疗资金筹措、医疗设施供应和医护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联共(布)中央首先确立了医疗卫生面向生产的总体方针,主要任务是维护劳动力健康,保障工人和农民全力开展劳动生产。
农业集体化运动是一场彻底的农村社会经济变革,国家控制农业生产,可以集中调动农村所有物质资源用于国家工业化和建设农村公共设施。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后,农村医疗卫生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1929年末,谢马什科在卫生人民委员部会议上指出,农村医疗卫生资源极度匮乏,正在组建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应该直接参与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建造维护。卫生部随后颁布命令,要求村委会与集体农庄密切合作,坚决解决农业生产进步和农民生活水平落后之间的主要矛盾,提升农民福利待遇,从集体农庄预算中拨款建造护理站、急救站、妇幼保健院和产房等医疗机构。
农业集体化运动初期,农村医疗卫生体系迅速铺开。1932年,农村医疗机构数量增加到5千个,农村病床数量突破10万张。1934年,在顿河流域等农业集体化运动发动最早的地区,农村医疗机构的绝对数量和比例都超过了城市。但是,农村医院的容量明显落后,亚速黑海边疆区的城市医院平均床位数151张,农村医院则只有24张。
1930年代中期,国家农业政策转向宽松,特别是减轻了庄员的税收和粮食收购任务,随着集体农庄制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获得了新的发展,但也面临着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1937年10月,卫生人民委员部编写的《苏联农村医疗体系现状报告》指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满足农村人口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共有1.15万个门诊,1.45万个助产士站,5529所医院,1444个妇幼保健所,1.65万张产床,千人平均病床数1.11张,不足城市的五分之一。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密度低,诊所平均覆盖半径24公里,服务1万人,医院平均覆盖半径35公里,服务2万人。土库曼、哈萨克、吉尔吉斯和亚美尼亚等地广人稀的共和国医疗卫生机构的密度更低。1930年代后期,苏联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发展加速,1940年农村诊所达到3.45万个。从中央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进步巨大但城乡差距依旧明显。全苏共有病床77万张(农村21万张,是1928年的3.5倍),千人平均病床数4.36张(农村2.55张,是1913年的5倍),结核病防治所1048个(农村207个,是1932年的5倍),性病防治所1498个(农村544个,是1932年的2.3倍),产床14万张(农村6.6万张,是1928年的7倍);托儿所85万个(农村20万个,是1928年的24倍);医务人员13万人(农村不足2万,是1932年的2倍,是1913年的4倍)。
初步建成的苏联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城乡差距明显。农村诊所的数量和医疗水平仍然无法满足需求,全科医院更是奢望,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严重短缺,只有少数大型集体农庄才有胸透机;其次,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对集体农庄财政的依赖度高,富裕农庄和贫困农庄之间的医疗条件存在较大差距,医疗卫生发展不均衡;第三,集体农庄的核心任务是粮食生产和收购,管理层对医疗卫生工作重视不足,管理中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第四,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是稀缺资源,医务人员假公济私以及腐败行为并不罕见。
(一)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资金保障
中央、地方和集体农庄是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三个资金来源,中央地方两级预算和集体农庄投资各占50%。农村医疗机构也发挥自身作用解决部分资金来源,集体农庄为医疗机构专门划拨土地并帮助耕种,医务人员和病人也自力更生参加劳动,生产的粮食、蔬菜和肉品用来改善病人伙食。个别医院的附属农场规模大土地多,自给自足外还能创造额外收入。
集体农庄投资包括农庄资金和互助储金。互助储金会(КОВК)是集体农庄中独立的社会组织,庄员自愿加入,按照规定数额缴费。因此必须指出,农民自有资金也参与了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此外,农庄也给互助储金会支持部分资金。政府命令明确规定,互助储金会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建设新型集体农庄社会生活。1934年末,俄联邦互助储金会被责成拨款2876万卢布用于下一年度社会福利机构运营。
互助储金会资金的用途多元,除医疗卫生领域外,还用于抚养孤儿,援助军属,修建阅览室、理发店和食堂等公共设施,多点建设的后果是医疗卫生投资常常捉襟见肘。1935年10月14日,俄联邦社会保障部颁布《关于制定1936年集体农庄互助储金会工作计划》,规定互助储金会总资金的3%用于医疗卫生领域,首要任务是建设药房,保证庄员可以“连续、不间断地参加生产”。互助储金会不再负责产房的建设和维护,移交给区卫生局管理。失去互助储金会支持后,产房受到了消极影响。由此可见,互助储金会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运营具有重要作用。
(二)农村群众卫生运动
农村生活环境恶劣,卫生条件差,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数量严重不足,严重的食品困难造成农民营养不良,身体抵抗力差,以上都是传染病肆虐的主要原因。因此,防治传染病是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机构的首要任务。
农村医务工作者对抗的传染病种类繁多,包括疟疾、流感、肺结核、鼠疫和天花等。国家的传染病防治方针是预防为主,1930年代初开始广泛进行疫苗接种。此外,还加大力度增加传染科的病床数量和专家人数。党、政、军、医四方力量协同集体农庄统筹行动,开展抗疟战役。在人与自然的战役中,也未能避免部分农庄管理者的僵化操作,例如,集体农庄中患疟疾的农民病休,不工作就没有没工分,没工分就没有口粮,没口粮就没有营养,最终导致病人死亡。
为了改善农村恶劣的卫生状况,国家发动了群众卫生运动。集体农庄组建卫生委员会,在住宅、食堂和学校等场所宣传卫生观念和防病知识,以村妇为主要力量的积极分子组成卫生检查小组,走家串户检查卫生,督促改进,进行“社会主义竞赛”。群众卫生运动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培养了农民自觉讲卫生的文化习惯,打造了农村整洁的生活环境。农民最初的抗拒心理也转变了,起初把卫生检查小组赶出家门的农民也树立了卫生观念,卫生小组再次进门检查时被要求蹭干净鞋底再进屋。1930年代末,疟疾等传染病防治取得了显著成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都没有再爆发大规模传染病。
(三)以人口增长为宗旨的农村妇幼保健
人口问题一直备受苏联最高领导层关注。1896—1900年,俄国女性平均活产5.23个新生儿,1926—1930年降低到2.2个新生儿。农业集体化运动期间人口减少明显,1930年代中期政府多策并举,目的是增加人口、提高生育率、降低婴儿死亡率、防治性病和保护妇幼健康。
1936年2月初,俄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苏利莫夫在第十六届全俄中央执委会会议报告中提出,农村建设集体农庄产房意义重大,地方执委会应提供长期援助。3月26日,俄联邦颁布《关于集体农庄产房》命令,在集体农庄广泛开展产房建设。此后,农村产房数量明显增长,1936年底达到4369个,产床1.26万张,是1935年的4倍。产房数量增加,改善了农村女性的生育条件,保护了女性身体健康,促进人口数量增长。
农村女性的堕胎现象比较普遍,一方面受制于政治经济因素,生活环境不稳定,粮食收购导致食品困难,无力养育子女;另一方面母亲出于心理因素,认为孩子是拖累。由于交通不便和生活贫困,农村女性多选择自行堕胎,严重影响身体健康。1936年6月,苏联颁布了著名的《反堕胎法》,规定除特殊情况外禁止堕胎,无论是在医疗机构还是在医生和孕妇的家中都不能帮助女性终止妊娠,如有违反,医生将判处1至2年徒刑,在不卫生环境或经未受医学教育者堕胎将判处3年以下徒刑,堕胎孕妇也要受到刑事处罚和公众谴责,再次违法将处以最高300卢布的罚款。《反堕胎法》还提高了国家对孕妇和多子女家庭的物质援助,加速建设产院、托儿所和幼儿园,修改离婚法案,对逃避赡养费行为加大刑事处罚力度。1936年,全苏妇幼健康设施建设拨款总计21亿卢布。农村的儿童病床数量也有所增加,儿童的营养、医疗和娱乐也得到关注。农忙季节母亲无暇照顾孩子时,农村儿童也有机会被送去夏令营和疗养院。
集体农庄内部也采取了诸多保护妇幼健康的社会政策。1936年宪法明确规定,农村妇女可以休两周产假。这是农村女性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产假权,具有巨大的政治宣传意义,彰显了加入集体农庄的优势,因为个体农民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女性在田地里生育屡见不鲜。
(四)农村医疗机构监督集体农庄生产纪律
农村医疗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监督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全力保障农业生产顺利开展。尤其是1930年代前期,加入集体农庄后,为求自保,农民多利用医疗卫生体系的管理漏洞维护个人利益,试图寻找合法理由逃避集体劳动。佯装生病成为逃避劳动的最佳借口,农民擅长利用植物让自己发烧,伪装出疟疾症状。
医生开具的病假条是庄员可以合法休息的有效证明。为了获得病假条,庄员千方百计和医生疏通关系,医生的徇私行为十分常见。称病请假者多为女性,即使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和军属也是如此,有的农庄的所有女性都持有医生开具的妇科病证明,一边逃避农庄劳动,一边在家经营副业经济。
为了监督集体农庄的劳动纪律,政府加强了对农村医疗机构的管理,增加了医疗卫生机构的数量,保证每个集体农庄大队都有医务人员,能辨别真假病患,避免因医生短缺造成诊断缺失,导致农庄缺少劳动力。同时加强了对医务人员的监督,加大对医生开具虚假病假条的责罚。
(五)农民疗养的确权与运行
苏联时期,疗养是国家改善人口健康的综合措施之一。作为社会生产链条的重要环节,劳动者修生养息,降低疾病率,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精力投入生产。1920年12月21日,列宁签署了《关于利用克里米亚治疗劳动人民》的法令,将“克里米亚以前大资产阶级的疗养院和度假村、大地主和资本家的美丽别墅和豪宅、以及沙皇和公爵的宫殿用作工人和农民的医疗保健之用”。法令打破了帝俄时期社会阶层中的等级意义,除权贵外,普通劳动者也享有了度假疗养的权力。
虽然法令规定,疗养的受益对象是“工人和农民”,但事实上农民疗养受到了严格限制,并未真正享受到旧日权贵的美好生活。在索契疗养的人群中党政干部占40%,工人阶级(多为工厂干部)占43%,农民仅有1.7%。与此同时,新权贵及其家属长期使用公款住在疗养院,疗养特权非常普遍,以至于捷尔任斯基公开批评“苏维埃的太太们”和“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在疗养院一住半年,“工人们却体弱多病”。显然,捷尔任斯基未提及健康更差医疗条件更糟的农民。1925年,俄共(布)四月大会提出提高农民福利,增加农民疗养人数。但是,整个1920年代农民疗养权都未有明显改善。除了政策原因外,农村缺少度假疗养习惯、疗养价格昂贵、农民预算有限和农闲时间不足也是主要原因。
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后,疗养权作为集体农庄福利对农民具有巨大吸引力。卫生部、社会保障部和集体农庄组建了联合工作体系,确保农民疗养权得到切实落实。疗养的程序是:有疗养需求的农民经过集体农庄同意向最近的医院提出申请,由医生根据其身体情况决定疗养地区和疗养时间,批准后将疗养证提交当地疗养办公室,疗养办公室核算旅费后告知集体农庄转账数额和方式,在收到集体农庄的旅费后寄还疗养证。疗养费和往返旅费由互助储金会支付。根据1935年10月俄联邦社会保障部规定,互助储金会此项支出比例为10%。
1930年代初,全苏范围开始兴建疗养院,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具有得天独厚医疗资源的地方被纳入疗养院选址。疗养院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促进,为疗养院提供农产品也成为集体农庄尤其是个体农民发展经济的良机,农民收入增加,在疗养院就业成为不少农民的工作选择。1930年代前期,由于集体农庄经济并不巩固,大多数互助储金会囊中羞涩,疗养农民数量未有明显增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33年全苏所有集体农庄都未能发放疗养证。1930年代中期,情况开始好转,由于集体农庄经济逐渐巩固,互助储金会增加了对农民疗养的资助,更多的农民得到了疗养券,享受到了度假疗养的福利。1935年,农民的疗养权被写进《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1936年写进苏联新宪法。
然而,农民的疗养权落实并非毫无限制。首先,疗养权不是普惠政策,仅是一种奖励措施,只有集体农庄中政治可靠的劳动模范才能获得公费疗养的机会;其次,疗养证发放并不完全公正,集体农庄管理漏洞滋生腐败,管理者滥用职权,疗养证成为利益交换的工具。
尽管有种种不足,农业集体化运动仍然促进了农民疗养权的整体改善。虽然农民疗养人数和比例仍然低于党政干部和工人,受益人群有限,但农民疗养彰显出的社会价值不容忽视。毕竟,苏联农民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公费疗养权,旧时高不可攀的滨海度假和休闲治疗也成为农民可以企及的福利待遇。
三、结 语
俄国史上长期缺乏广泛的医疗服务,国家仅提供有限的防疫措施。现代意义上的医疗服务体系起步于18世纪初,但发展缓慢,规模和影响甚微,受益人群仅为几个主要城市的贵胄富贾,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排除在医疗服务之外。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内战、饥荒和流行病肆虐的极端条件下开始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体系,试图以公共免费原则惠及大众,但农村的医疗卫生未能明显改善。农业集体化运动推动了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集体农庄成为农村医疗的财政和组织保障,1940年代初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形成,农民健康水平提高,农村人口增加。尽管农业集体化运动严重影响苏联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也不可否认农业集体化运动对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形成的决定性推动作用。
注 释:
①Г.А.Баткис.Двадцать ле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во медици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44。
② Э.М.Конюс.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охраны материнства и младенчества (1917-1940). 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во медици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4。
③ М.Ф.Леви.История родовспоможения в СССР.М.:Госиздат.1950。
④ Н.А.Виноградов.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в период борьбы за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ю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1930-1934).М.:Соцэкгиз.1955。
⑤ Н.А.Виноградов.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в предвоенный период (1935-1940).М.:Соцэкгиз.1955。
⑥ М.А.Вылцан.Совет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накануне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38-1941 гг.)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0。
⑦ И.Е.Зелнини.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в 5 т. Т3.Совет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период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конец 1927-1937.М:Наука.1986。
⑧ А.П.Скорик. Проблемы экспериментов и ошибок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Ростов н/Д.2001。
⑨ Ю.Градскова.Культурность.гигиена и гендер: советизация 《материн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в 1920-1930-е годы.М.:ООО 《Вариант》, ЦСПГИ.2007。
⑩ Н.Лебина,П.Романов, Е.Ярская-Смирнова.Забота и контроль:соц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1917-1930-е годы. М.:ООО 《Вариант》, ЦСПГИ.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