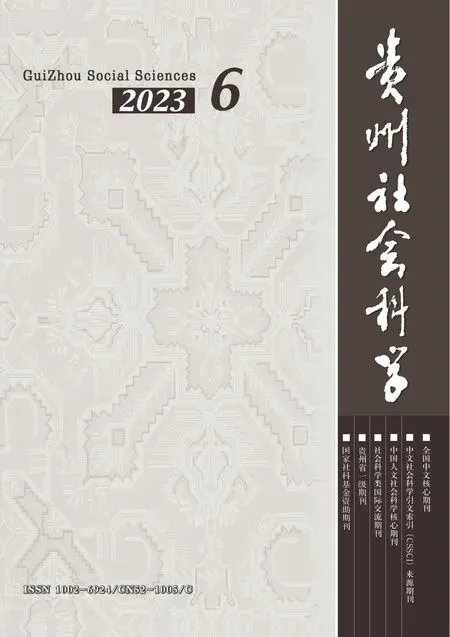《百年一觉》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
2023-09-28姚达兑
姚达兑
(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570228)
一、引言
1888年,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出版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小说《回顾:2000—1887》(下简称“《回顾》”)。这是一部典型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此书作为一种“想象的历史”,乃是受启于一些前辈的乌托邦巨著——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和培根的《新大西岛》等作品,当然也杂糅进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为当时资本主义危机频发的时代和读者提供了一幅完整而美满的未来社会图景。[1]小说出版后,因其主题涉及思想、社会、制度和民生各个方面,其影响超越了文学领域,在政治和思想等方面也有长久的回应。据克里山·库玛统计,在1889年至1900年间受《回顾》影响而出版的乌托邦小说至少有62部,有的是《回顾》一书的续集、有的模仿其写作的模式、有的则是借这种小说体裁提出种种反驳的意见。[2]然而,贝拉米清楚地知道,他所想像的未来理想社会与现实之间仍有不小的距离,要百余年后方有可能实现——在小说中是113年后,即2000年。这部小说中的未来社会是一种乌托邦,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批判。人类需要创造一个当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乌托邦,其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对现实有某种程度上的不满。换言之,乌托邦是对未来的憧憬,也是对现实的批判,包含了推动改革的动力。或许正因为这样,1891年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作将《回顾》译为汉语在杂志上连载。
李提摩太等译出此书,可看作是借助文学的乌托邦想像带给晚清中国改革的动力。《百年一觉》在晚清对改良派知识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目前主要有刘树森、何绍斌、吴国坤、武春野等人的重要研究。(1)刘树森:《李提摩太与〈回头看记略〉──中译美国小说的起源》,《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武春野:《政治小说的语言策略:以Looking Backward的四个汉译文本为中心》,《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何绍斌认为,“新教传教士的译介目的与结果之间的错位为晚清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何绍斌:《从〈百年一觉〉看晚清传教士的文学译介活动》,《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4期。吴国坤指出,“中国译者以其传统的叙事形式,有意将贝拉米原创的宗教预言转化为符合中国语境的进化论式的历史想像。”Kenny K. K. NG, Ending as Beginning: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Edward Bellamy’s Utopian Novel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Frontier of Literary Study in China, 2016, 10(1), pp.9-35.然而,这些研究,皆未曾深入分析《百年一觉》译文对哪些改良派知识人在哪些具体方面产生过影响。近期,笔者对《百年一觉》一书进行整理和校注,在校注过程中有新的发现,故撰此文,试作一解。
二、《百年一觉》中的大同思想
《回顾》一书原著出版于1888年的美国,出版后很快在欧美世界引起很大的反响,重印多次,也产生了不少其他语言的译本。1891年,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作将其译为《回头看纪略》,分5期连载于《万国公报》之上,后于1894年在广学会出单行本,更名为《百年一觉》。比对连载本和单行本可以发现,除开篇介绍稍有改动外,其余内容完全相同。《百年一觉》以简要文言译成,原著二十八章,译作也一样为二十八章,但仅有1.4万字,汉文仅是粗陈概要,大量细节未译出,故而汉译本原题有“纪略”两字。此后,提倡推广白话文的裘维锷(即裘廷梁,1857—1943)依据此单行本,用“白话演义”(白话改写)。裘氏改写的《百年一觉》连载在1898年《中国官音白话报》第七、第八期合刊(现仅存4页),仅有前面数回。1904年,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的《绣像小说》连载了另一个白话章回体译本,题为政治小说《回头看》,误署作者名为“美国威士原著”(下简称“绣像本”)。该本未能确知译者是谁。“绣像本”也并非全译,而是缩译,原著二十八章,被合并调整为十四回,计约6万余字。1905年,绣像本收入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中单行出版。这一译本,在1913年、1914年等还有几次再版。196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林天斗、张自谋合译的《回顾:公元2000—1887年》 ,即现今的通行版。
19世纪末,接触到西学的晚清知识分子,深知他们身处大变局之中,未来必定会有新的变化,故而当他们接触到西方知识谱系中产生的乌托邦思想时,自然会寻找中国传统资源与其格义、对话。这种跨文化对话的过程,蕴含了文明的创造性转化的可能。蔡尔康用“大同”一词,来对译《回顾》中的未来社会,便是一例。大同思想,源于中国《礼记·礼运篇》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蔡尔康将这种传统思想援接到了他和李提摩太合译的西学著作上,比如《百年一觉》和《大同学》这两部译作中的西学内容皆能明显看出中国传统话语的深入渗透。
遍查《百年一觉》全书便可发现,书中仅有两次提及“大同”两字,分别处于书中的第一章和第十九章。此两处内容,前后相互响应,关联起了作者论及的种种议题。汉语译者在此两处对中西思想文化观念作了直接的嫁接,在这种跨语际的转换过程中,旧的词汇被赋予了新的思想内容。开篇第一章中,主人公伟斯德说道,“岂知上帝生人,本为一体,贫者富者,皆胞与也,至富者自高位置,而于贫者毫无顾惜,岂所谓大同之世哉。”(2)《百年一觉》有多个重印本,本文所引为第一个单行本即1894年上海广学会编印版,下文涉及此一引用时均出于此,不再一一标注。贝拉米在对比贫富两阶层之后,批评富闲阶层的人们(乘车者)对被剥削和压迫的低层人民(推车者)没有丝毫怜悯之心。汉译本这里的内容,与并不原著对应。原著中,此处伟斯德说道,“当他们把自己的奢侈生活和他们兄弟姊妹们的牛马生活相比,而且明了自己的重量增加了他们的负担,难道不感到自己的奢侈生活难以容忍吗?难道他们对于那些仅仅由于命运的拨弄而与他们处境不同的人们,没有一点同情心吗?”[4]15作者直接指出,这样的社会不公现象“极不人道”。伟斯德的评论当中,提及了富闲阶层的人们和“他们兄弟姊妹们”。在这里,伟斯德(或作者)在基督教思想观念影响下,像牧师布道一般举例解释种种社会不公的现象,并加以评论,在评论的话中可见出他以基督教思想作为参照标准来观察,将世人——无论贫富智愚,都同等看作是兄弟姊妹。《百年一觉》这一章译文的末段这样总结道,“盖上帝生人,原属一例。虽工匠与富户,亦兄弟也。而今乃以贫富悬殊之故,致视贫贱如奴仆,无怪常有争端也。”本来此处在原文中仅是一带而过,但是在李提摩太与蔡尔康合译的过程中,却被译者大加发挥解释了一番。
在译文第二十四章《昔日争端》中,伟斯德与理德医生讨论到了19世纪的阶级矛盾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由此引出了旧时代的工人罢工事件,以及社会组织应当如何维持,进而讨论到国家治理等方面的问题。理德医生指出,“缘从前贫富相争,贤愚相争,老幼相争,强弱相争,男女相争,如此似与禽兽无异。必须将一切事尽听国家办理,使各等人皆如弟兄,不再相欺相争,永远相助相爱,方称治理。”在以前的旧时代,社会各行各业、万事万物皆都于“相欺相争”的状态,故而社会矛盾丛生,人则如同禽兽——注意,这里借用的是《孟子》的论述,即“人禽之别”在于有无“仁义”。(3)《孟子 离娄章句下》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298-299页。但是,在译文中这里则被换用成“兄弟姐妹相助相爱”“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的基督教精神。小说中,在2000年新时代里,人人都能各尽其才,整个社会不是竞争而是相互合作的状态。新时代有一个全能的大政府,会协调各类合作事宜。贝拉米寄希望于一个全能的大政府的存在,未免太过于天真。在贝拉米的宗教观念里,宗教的救世作用和未来世界的大政府几乎是同时存在,同等重要,起到了同等的功能。
针对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贝拉米在原著第十四章提供了一个“雨伞之喻”予以解答,即由政府为全社会各阶层所有人民提供平等而公平的服务。[4]14伟斯德来到2000年的波士顿后,与理德医生父女走在街上,时逢大雨,人行道一下子就全被防雨顶篷遮盖住了,“变成了一个灯光明亮、地面干燥的走廊”。理德医生解释道,在19世纪,当波士顿人遇到下雨天,30万人的头上撑起了30万把雨伞,而到了20世纪,只打开一把大雨伞,便可使他们免于淋雨。过去时代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个人主义时代,新时代则是人人利他、集体协作的时代。医生的女儿仪狄(Edith)有这样的解释:“爸爸最喜欢拿个人撑伞的例子来比喻从前个人只顾自己和自己家庭的生活方式,在艺术馆里有一幅19世纪的画,画中许多人站在雨里,个人撑着一把雨伞遮住自己和他的妻子……”[4]113这里的“艺术馆”,其实是特指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这幅画,就是收藏于该博物馆的一幅作品——法国印象派画家古斯塔夫·卡里伯特(Gustave Caillebotte,1848—1894)在1877年所作巨幅油画《巴黎的街道·雨天》。卡里伯特在这幅画里敏感地捕捉到当时经过改造后的新巴黎街景的特征。巴黎,作为19世纪资本主义和人文世界的首都,当然也就代表了当时的西方人对现代世界的感知图景。在理德医生父女看来,这幅画就是那个旧时代的映像。从仪狄的话中可知,在理德医生眼中这幅画就是对那个时代的讽刺。换言之,新时代的新人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社会不公等状况,有着非常清晰的批判意识,而“雨伞之喻”便包含了贝拉米对社会不公的解决方案。
“雨伞之喻”的情节,在李提摩太和蔡尔康的汉译本《百年一觉》中对应的是“天下为公”的未来景象。汉译本第十四章“新机蔽雨”里这样写道:“从前每下雨,必支伞,穿雨衣、雨靴。今则出门,见看街卒手按一机,恍若橡皮布,支起若仓。人行其中,并有电光照耀,不黑暗。”在汉译本中,这个隐喻对应了全能的大政府对个体的保护,但是其字面的意义可能会让蔡尔康等中国文人联想到中国传统典籍中的“天下为公”观念。
《回顾》一书中,前后两个时代的对比和反思,往往会引申至宗教说教,这一点在保儿屯(Barton)牧师的无线电演讲中达到了高潮。第二十六章章名为“今胜于古”。在这一章,保儿屯总结道,“盖遍国人皆如弟兄,所出之力,全系公出。所生之利,亦全系公分。不必劝人施舍,亦无有望人施舍者。从前皆言人心坏,岂人心坏哉,法不善也。不然,何以今日法一改,人心皆善耶?又前世彼此相争,如恶鬼然,现今彼此相爱,如兄弟然。”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是因为新时代的政府更懂“养民各法”,人们的道德水平更远胜于过去,所以人们“不为自己计,全为众人计”(利他精神)“人心皆善”“国人皆如兄弟”“现今彼此相爱,如兄弟然”。这种对利他精神、友爱之情的强调,也正是本于基督教的相关理念。
以上所举几例论及贫富矛盾,以及以新型的友爱观念来引导人们,虽然借用的是中国古典传统中的词汇,最终导向却是基督教信仰。译文有不少添加的地方,比如讨论延伸至“民胞物与”“天下大同”等概念。“民胞物与”一词,出自宋代理学家张载的著作《西铭》中的名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源自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观念,皆可再追溯至超越性的“理”。也即是说,这背后隐含着宋明理学的思想。这里所写的“世人皆如兄弟姐妹”“上帝生人,本为一体”等内容,指向的是基督宗教的神学,尤其是自然神学的观念,然而译者运用中国传统词汇而将其巧妙地嫁接到了理学思想上面。在李提摩太的其它译本如《大同学》《天伦诗》等,也能见到将自然神学与理学思想嫁接在一起的现象。所谓“大同之世”的感慨,则是蔡尔康进一步地阐发。前文论及的“非大同之世”,在第二次提及“大同”时译者有所呼应。
《百年一觉》第二处提及“大同”是在第十九章,这一章的标题为“牢狱空虚”。在原著中,贝拉米让理德医生为伟斯德解释前后新旧两个时代的不同。理德医生通过一系列的对比,突显出了新时代的优越性。原著中仅是例举对比,章末并无总结之语。汉译《百年一觉》仅是略译,所以原著中理德医生提及的新时代没有犯罪、不需要律师、没人会说谎,法庭和法官的审理方式、州政府和市政府的功能有新变化等内容,大多被略过不提。原著中本是理德医生长篇大论般地平铺直叙,译文则改置为伟斯德提问、理德医生应答。伟斯德问道:如何保证当官的人没有滥用权力(得毋有任性暴虐者)?原著对应的段落是理德医生这样解释道:“长官发布命令,每个士兵都得服从,但是,不论一个长官的职位怎么高,他也不敢对最低一级的工人傲慢无礼。如果任何一个长官在和公众接触中有什么蛮横粗暴的行为,那么,就一些次要的过错来说,这种行为必然会首先而又迅速地得到惩处。我们的法官坚持主张,待人不仅要公正,而且很有礼貌。不论一个人对工作的贡献有多么大,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宽容他的粗野无礼的态度。”[4]150-151这一段被译者处理为,“叟曰:‘此事绝无有也,盖均以相亲相爱之意待之,即有暴虐,立即撤任换去,缘向日为民主之俗也。’伟叹曰:‘若是,则真所谓大同之世也,与前百年霄壤之别矣。前尝有人谓我曰:百年后世界必要大变,如今日景象。我犹以为过言,乃今而目睹矣。安得均起百年前之人而皆目睹乎?’”这一段中,所谓任事者一旦有滥用职权、暴虐之举,便会被撤掉,因为他们任人的制度是按照约定的社会惯例,即民主选举。因而,伟斯德大为感慨,前后百年,两个世界,便如霄壤天地之别,而现在这个新时代就是“大同之世”。这里的“大同之世”,正好呼应了第一章的“非大同之世”。也即是说,小说开头设置的疑问,在这里得到了合适的解答。
原著这一节中还有一处值得注意,理德医生和伟斯德讨论到新时代的人们无人犯罪,犯罪就是过去旧时代的“隔世遗传症”[4]16-17,在这个平等、公正的新时代,人们不需要、也不愿意撒谎。这时伟斯德评论道,“如果大家都不再说谎,那就真像先知者预言的那样,‘正义充满于新的宇宙天地之间’了。”这是一个新天新地。接下来,医生便直接揭示了作者的观点。“事实上,这就是今天某些人的信仰,’医生回答,‘他们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千年至福的时代了。’”[4]147在作者的观念里,这个黄金时代就近似于基督教的千禧年。汉译文中的“千年至福”,即为原著中英语单词“Millennium”,其典出自《新约·启示录》(20:1—5)。在基督教神学里,这是指耶稣基督复临世间,建立一个和平、公义的王国,并统治一千年,所以称为“千年至福”的新时代。贝拉米在社会进化论和千禧年观念的指引下,完成了对未来的塑造,并相信其终将会实现。《回顾》一书的后记(也即全书最后一句)中写道,“我写《回顾》一书持有这样的信念:黄金时代不是已经过去,而是在我们前头,并且也不遥远了。我们的孩子们无疑将会亲眼看见;而我们这些已经成年的男女,如果能以我们的信念和工作来作保证,也是可以看到的。”[4]242这也是原著第五章中作者提出的观点:社会的发展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最终必定合理地完成进化,为人类开启一个光明的未来。
翻译是两种文化相互协商和整合的过程,这种情况在晚清合作翻译中最为明显,但也因为合作译者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使得研究者很难判断翻译过程中谁起的作用更大。如若对比贝拉米的原文和汉译本《百年一觉》,便可看到,李、蔡的译文加入原文所无的“民主”和“大同”等关键词汇。既然是原著所无,那么政治理念可能是来自李提摩太,而大同理念则来自蔡尔康。蔡尔康在《百年一觉》中,通过与李提摩太的合作,将千禧年主义的理念,嫁接到中国的“大同”理论,而在其后两人合译的《大同学》(1899)中也有进一步的阐发。在《大同学》中,译者认为社会会不断进化,其进化的最终目的是抵达一个完美的、理想的社会,也即大同,故而将颉德的《社会进化》一书易名译为《大同学》出版。[5]要之,两人前后合作数十种著作,借助中国传统语汇,译介西方西学,功不可没。至于将大同思想接入西学资源,起最大作用当属笔受者蔡尔康。
三、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
《百年一觉》对晚清知识分子、政治小说或乌托邦小说产生了一些影响。以该书对康有为及其《大同书》、梁启超及其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为例。康梁这两部作品都可看作是“乌托邦小说”,因为对未来各有其乌托邦想像。(4)董启章将康有为的《大同书》看作是“乌托邦小说”,参见《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David Der-wei Wang ed., 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7, pp.237-241.康有为在写作《人类公理》(即后来的《大同书》)时曾参考过《百年一觉》。他提到“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的影子。”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也特别提到:“若西书《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梁启超也将《百年一觉》列入《西学书目表》中。梁氏在《读西学书法》中评论《百年一觉》“亦小说家言,悬揣地球百年以后情形,中颇有与礼运大同之义相合者,可谓奇文矣!”[6]这两位影响巨大的近代知识分子,都曾提及《百年一觉》中的大同思想。
《百年一觉》对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知识人的影响,笔者在此前研究中曾有简要论及,也曾指出“有多处的文本相似性表明,康有为的《大同书》受到了《百年一觉》的影响。”近年又有一些新的发现,下文将从三个方面对此前的论述作进一步的补充。
第一,关于未来世界中人类的一生规划。《百年一觉》第六章里提及政府为新时代的人们规划了一生应如何度过。“自幼至二十一岁,皆在学读书日。自二十一岁至四十五岁,皆作官作工之日,二十四年之久,凡作官及作工者,正出力办事之时。过四十五岁以后,苟非极有事之秋,皆安开养老之日也”以及该书第十二章还写道,“叟曰:君总须牢记人自幼至二十一岁是在塾读书之日,初出塾学事,是各样粗工,三年外,又有一年学专门技术,再后个人因其长进有升等因之出力任事,至四十五岁,除此之外,又各有所司之人,共有五等,凡升等者,皆因其艺精进也。至四十五岁以后,即可以安闲,国家俱有赐养,虽其家子孙不能无养,而国家视人如一家,凡有老病,俱与以养给。”[1]42康有为的《大同书》所设置的未来世界里,人生在世已经被“公政府”规划妥当,前二十年接受教育,此后为国家和社会工作二十年,每个个体都按其个人才能被分派到需要他的岗位,此后个人才能得到自由,去追求精神事业,也即是:四十之后,乃许辞工专学道,去修炼成为神仙,追求灵魂之乐。康有为这样写道,“惟人受公政府之教养二十年,报之作工亦须二十年,如乱世人之当报父母也。其有入山屏处者,必须四十岁之后,乃许辞工专学道也。……以人为公政府所教养二十年,非己所得私有,须作工二十年报之,乃听自由。……”[7]康有为为未来的人类所作的人生规划,正是来自于《百年一觉》的相似描述,那是贝拉米对新时代人类的一生所做的规划。
第二,《百年一觉》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思想观念:未来将会出现世界和平,并产生一个世界政府一样的庞大机构来协调和分配社会资源。关于世界和平以及此后的世界政府的观念,在《回顾》一书原文中已有出现。在小说的第十三章里,伟斯德独自在理德医生的图书室内感慨新时代竟然这样就产生了,在这个时代里有一个世界政府帮助维持世界的和平,一切都那么令他满意,稍有遗憾的是他自己未曾为其实现而付出一些努力。[4]此时此刻,理德医生心中不断地回响着一首诗,那是丁尼生的诗《洛克斯利田庄》。该诗寓含了一种希望有一个世界政府以维持世界和平的观念。这一点,笔者此前已有总结:“《大同书》中乙部‘去国界合大地’第二章《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一节,设想了一个所有民族国家完全消失了的和平世界,此时全球仅剩一个‘公政府’,以帮助维持秩序。这种世界和平和世界政府的设想,也是源自《百年一觉》。”[4]13-14
第三,《回顾》原著宗教色彩浓厚,其书末的拯救主题在汉译本中得到保留,最终影响到了康有为的《大同书》。
《回顾》原著中,字里行间还有很多基督教的思想内容。在小说的结尾,伟斯德进入一个花园,跪倒在其爱人的面前,当场忏悔,表达了对上帝的感恩之情。《百年一觉》的最后一章名为“诸苦必救”,伟斯德从一个富闲阶级的不事劳动者(这是有罪的、不配活在新时代),变成了一个利他的新人。“于是又跪祷于上帝前认罪,又矢愿曰:若使我活在此好世界,自此以后,不敢仍似从前,但为自己计,总欲为众人计。……仪狄曰:上帝是最慈悲者,既已悔过前罪。谅必赦也。”这里“为众人计”,即是放弃自私自利,要具备利他的奉献精神,也即“天下大公”之意。花园忏悔这一段,这个花园就是一个新的伊甸,而他们就是千禧年的两位新人。最后,伟斯德大发感慨,认为他自己完全不配呼吸这个黄金世纪的新鲜空气,像他这样绝望的人“获得的最终审判竟然是如此的仁慈。”《百年一觉》简化了这一段,也去除了一些关键情节,但仍保留了主题,即只要归信基督教,忏悔过往,改过自新,那也就能得到救赎。故而,主要的内容和主题仍是得到了保留。
《百年一觉》的末章“诸苦必救”的观念,以及支撑这种观念的千禧年主义,影响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大同书》的各章节,自甲部(首章)“入世界观众苦”开始,列举各种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等等,进而设想未来世界里“去国界”“去级界”“去种界”“去形界”“去家界”“去产界”“去乱界”“去类界”,最终至癸部(末章)“去苦界至极乐”终结。康有为在全书中强调了世间各界有“诸苦”,最终因为各种困厄界限被破除而人类得到了拯救。这其实也正是《百年一觉》的“诸苦必救”的模式,当然细节上略有不同。因而,《百年一觉》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其理论模型脱胎自基督教的千禧年主义,更具体的影响源头来自于《百年一觉》。
《百年一觉》对梁启超的小说也有直接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叙述方式、情节设置和时间观念等方面。刘树森曾指出,“李提摩太的《百年一觉》不仅是‘翻译为中文的第一部西方现代小说’,也开创了晚清一个重要的小说类型——政治小说。 ”[8]晚清第一部政治小说,当属梁启超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仅有五回,未完稿)。《回顾》原著的情节是以未来完成的叙述方式展开。故事开始于2000年的12月26日,时间是圣诞次日——这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主人公伟斯德来到波士顿市某学院历史学部,开始了他的演讲。伟斯德作为历史学部教员的身份,显示出他作为新人的大转变——自19世纪的富闲阶层不事劳动的青年变成了新时代的劳动者。在作者设想的新时代里,每个个体都需要劳动,所谓“人尽其才”——所以仍很年轻的伟斯德,其工作任务就是作为一名历史学者,讲述他此前所生活的19世纪波士顿的历史。在《回顾》中处处可见过去时代(1887年)和现在时代(2000年)的各种对比。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同样使用了未来完成时的叙述方式,也隐含了各种现在世界和未来世界的比较,这些无疑是受到《百年一觉》的影响。《新中国未来记》开篇即写1960年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之史学部,遍邀名家演讲历史。此时,孔觉民作为符合国民德行的最佳代表出来演讲,面对着众多国际友人,讲述中国人民克服帝国主义强敌、独立自强,最终和平崛起变成世界超级强国的“历史”。这与伟斯德在波士顿某学院开讲,回顾过去历史,在情节设置上非常相似。孔觉民做演讲的这个时间,设置在1962年,距离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正好两个甲子——即中国传统时间观念中的两个周期。在这种时间设定中,1902年是梁启超发表这部小说的时间,距离1842年正好60年。孔觉民所讲的是“中国近六十年史”,“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起,到今年壬寅”,刚好六十年一个甲子。(5)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13页。在这一章首段一句,梁启超在转换孔子纪年和耶稣纪年时,有前后不一致的错误。此处正文论述为标准来作讨论。这六十年里,想像中的“未来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从一个“存亡绝续”的危机时刻,到富足强大、“万国来朝”(派使节来参加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贝拉米在《回顾》中设置的“未来”是在2000年,即新的千禧年的开始。在基督教时间观念中,一个千年为一个周期,所以小说的未来设定在第二个周期。这两部小说都否定“过去”这个时间节点,都把“未来”这个时间节点设置在第二个周期时间作为新的开始,故而可说,两位作者在小说中展现出了非常相似关于“进步的”时间观念。
综上讨论,《百年一觉》对康梁的著作,在内容、情节设置、叙述方式和时间观念等方面,有直接的影响。
四、总结
贝拉米生长在一个有浓厚宗教背景的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都非常热衷于讨论社会变革的议题,希望借用基督教思想观念来改造社会。贝拉米所处的时代是19世纪末,将迎来新的千禧年,其时的北美宗教运动愈演愈烈,在此大背景下贝拉米的小说呈现出强烈的宗教色彩。《回顾》一书被译介进晚清中国之后,曾产生不少讨论,引起强烈的回应。
《百年一觉》仅是缩译,原著中许多细节并没能得到保留,仅保留的宗教内容有的被替换成大同思想,寄寓了深刻的意涵。李提摩太善于引申发挥书中的基督教思想,比如强调基督徒的友爱观念,而笔述润色者蔡尔康则惯用带有儒家理学色彩的词汇。两人的合译的本意是引进西学,其实做的是文化交流和再创造的工作,有其独特的时代意义。
学界此前并未具体指出《百年一觉》一书在哪些方面对康梁产生了影响。本文通过几种文本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大同思想、小说内容、情节、叙述方式和时间观念上都有明显的承继关系。李提摩太对康有为、梁启超其它方面的影响,还有一系列的证据。在维新时期,李提摩太甚至可以说是康、梁等维新党人的精神导师。1895年3月,李提摩太曾在《万国公报》上征文,而康有为投来稿件,最终还榜上有名,获得了奖金。1895年10月17日,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时,两人曾一道去拜访李提摩太。据李提摩太的记录,康有为在交谈中曾表明相信“上帝的慈爱”、愿意与传教士合作改造中国。[9]这一年,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合力创办“强学会”时,李提摩太也是创会成员之一。在这一年的年底至次年年初,梁启超曾有几个月任李提摩太的私人秘书。梁启超阅读了李提摩太出版的书刊,后来还选编出一批书籍,作为维新党人阅读的资料,其中包括了广学会版的《万国公报》《泰西新史揽要》和许多晚清西学著作。这一类的西学作品,康梁曾列出了一个书目,呈交给了光绪皇帝,作为推动维新运动的思想资源。要之,李提摩太和《百年一觉》对康有为、梁启超,甚至是同时期的维新知识分子,都产生了关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