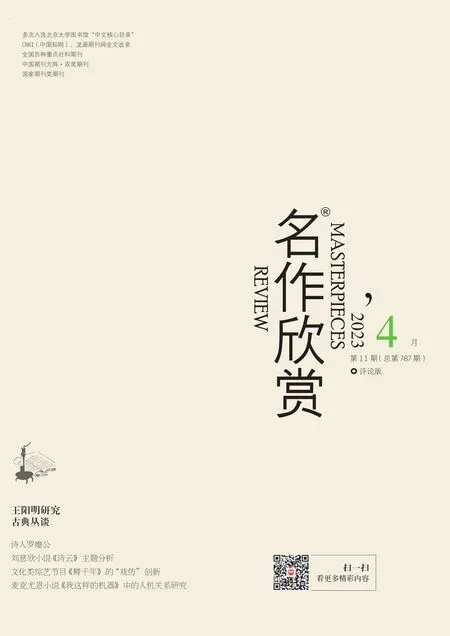诗人罗瘿公
2023-09-28董昕中国戏曲学院北京100073
⊙董昕 [中国戏曲学院,北京 100073]
罗瘿公(1872—1924),广东顺德人,名惇融,字掞东,号瘿公。其父罗家劭,同治四年(1865)乙丑科二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同治十一年(1872),罗瘿公生于北京,取名“惇融”,寓勉励终生始洞彻明察之意。他幼承家学,聪慧过人,很小便有“顺德神童”的美誉,先后就读于康有为创办的广雅书院和万木草堂,与陈千秋、梁启超同列高弟;光绪二十九年(1903),得中副贡;1905 年,时值废科举,于是报捐主事,在京供职,官至邮传部郎中。辛亥革命(1911)后,历任总统府秘书、参议、顾问、礼制馆编撰等职。1915 年,因不满袁世凯复辟帝制,不念与袁曾有旧交,弃政辞官,自此纵情诗酒,留恋戏园。1917 年得遇程砚秋,至此倾其所有,尽心栽培,为其编写《鸳鸯冢》《青霜剑》等十二个剧本。另为梅兰芳编写了《西施》一剧,成为梅派代表剧目之一。1924 年春,肺病发作,入德国医院,同年9 月16 日病逝,终年五十二岁。
罗瘿公一生著述颇丰,今存有《太平天国战记》《中英滇案交涉本末》《中俄伊犁交涉本末》《中法兵事本末》《中日兵事本末》《威海卫潜师记》《割台记》《德宗继统私记》《戊戌德宗之密诏》《拳变余闻》《庚子国变记》《藏事记略》《张文襄之自述》《鞠部丛谭》《赤雅吟》以及京剧剧本《梨花记》《龙马姻缘》《花舫缘》《红拂传》《玉镜台》《鸳鸯冢》《风流榜》《孔雀屏》《赚文娟》《金锁记》《玉狮坠》《青霜剑》《西施》十三种。他的诗作三百多首,经友人曾刚甫删定后,选录其中二百余篇,题作《瘿庵诗集》。
罗瘿公一生最得意自己的诗作,他病重前在讣告中写道:
平生文词皆不足示人,惟诗略有一日之长,可请刚甫定正印选以为纪念,亦不亟之,以精择为主。哀也不必附送,无可足言也。前诗及此数纸可印送。①
品读罗瘿公的诗作,从内容上大致可归结为以下方面:政治篇、隐逸篇、梨园篇。
一、政治篇
罗瘿公出生于仕宦之家,幼承家学,聪慧过人,一心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1899 年,二十七岁的罗瘿公获选优贡,入国子监深造;三十一岁时考中副贡;三十三岁应考经济特科(清末朝廷用以选拔“洞达中外事务”人才的特设科目),成绩优异,获授邮传部郎中之职。但是,在京为官,并不能如他所愿。1908 年(戊申)除夕,罗瘿公在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三十七年随例去,光阴留得一分残;
莽惊急鼓凋英气,尚借幽花殿岁寒。
毷氉一官孤注尽,艰难入口腐儒酸;
余生幸托风波外,莫怨仙山路折盘。②
官场的乌烟瘴气,纷繁动荡的时局,令罗瘿公当年的豪气也在无奈中渐渐消解了。他在画家罗两峰的鬼趣图上题下这样一首诗:
子非鬼,安知鬼之乐,忽然开图令人愕?
偶从非想非非想,青天白日鬼剧作。
群鬼作事自谓秘,逢迎万态胡不至。
岂虞鬼后不生眼,一一丹青穷败类。
中有数鬼飘峨冠,自矜鬼术攫美官。
果能变鬼如官好,余欲从鬼得奥援。
问鬼不语鬼狞笑,鬼似摈我非同调。
吁嗟鬼趣今何多?两峰其如新鬼何!③
这幅画我们虽然不得而见,但从诗中可以看出,罗瘿公以鬼喻人,以戏谑的口吻,表达了对官场黑暗、宵小得意的丑恶现象的鄙视、厌恶,也表达了自己不肯同流合污的内心意绪。
晚清时期,社会动荡,腥风血雨,愁云惨雾,官场亦是阿谀逢迎,贿赂成风,政治环境十分恶劣。罗瘿公曾在他的诸篇历史笔记中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的一幕幕情景,如《庚子国变记》中,他记述了义和团的种种行为。当时的情形极为复杂,慈禧太后想借义和团之力与洋人决一死战,于是下诏褒“拳匪”为“义民”,致使双方交战,京城大乱,出现了下述的惨状:
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毙之,惨无人理。京官纷纷携眷逃,道梗则走匿僻乡,往往遇劫,屡濒于险,或遇坛而拜求保护,则亦脱险也。④
面对这样的形势,朝廷的文臣武将皆是“谄谀干进者,争以拳匪为奇货”⑤。罗瘿公虽力求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客观记述,但依然流露出他对当权者的不满,也表达出对行凶者滥杀无辜的愤慨。
1911 年,辛亥革命的风潮很快席卷了全国。辛亥秋,梁启超自日归国,罗瘿公赋四首律诗:
海东风急怒涛喧,马角看君入国门;
握手不知成涕笑,剖心宁暇说寒暄。
头颅十戴江湖剩,烽火神州天地昏;
急劫危棋空袖手,只应还卧旧邸园。
须磨海畔千帆过,漆室忧天日万言;
泪尽精灵从化石,狂来诗酒与招魂。
众雏踞地时亲母,万卷撑肠独闭门;
颦鼓声中惊起坐,残山一角是中原。
党碑元祐新除籍,头白东坡海外归;
威凤羽毛宜自惜,屠龙赤手欲何之。
苍茫帝所钧天梦,零落华年故国衣;
黑水白山王气尽,人民城郭是耶非?
相期四印斋头坐,翻踞双涛阁上层;
山鬼女萝松下月,敦煌经卷佛前灯。
百年此日并哀乐,一姓何当问废兴;
归去傥携三岛月,海山云气梦飞腾。
戊戌政变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被迫远走异国,在海外他们宣传君主立宪及保皇主张,又受到主张民主共和的革命派的猛烈攻击,他们的改良主义陷入了顽固派与革命派两方的夹击之中。辛亥革命爆发,政治局势有了新的转机,梁启超踏着革命风潮回到了祖国。罗瘿公深感局势动荡,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他也预感到几千年的封建帝国气数将尽,但又没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变革社会的热望,于是怀着忧国忧民的种种忧虑,力劝梁启超暂惜羽翼,情绪极为沉郁。
诗中可以看出罗瘿公对清朝的覆亡有着清醒的认识,政治的腐败令他无所留恋,所以他才有“一姓何当问废兴”的感慨。他劝说梁启超,其实也是在劝慰自己,“山鬼女萝松下月,敦煌经卷佛前灯”,可见此时罗瘿公已经开始流露出对隐逸生活的憧憬。
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民国初年,罗瘿公先后担任了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参议、顾问等职,并且教授袁世凯之子袁寒云诗文。任职期间,罗瘿公觉察出袁世凯称帝的企图,曾在《鞠部丛谈》中写道:“项城有称帝之意,而尚伪辞谢。张季直入谒讽止之。项城曰:‘若民意趋向帝制,吾必退位,以帝位还诸清室或朱明之后人。’”⑥罗瘿公以史家的笔法勾画了袁世凯急于称帝的面目与心态。
1913 年3 月20 日,宋教仁在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获胜,而选举刚结束,袁世凯便指使暴徒杀害了宋教仁。宋案的发生,更加暴露了袁世凯的野心。之后不久,洪宪帝制之议便已呈春云渐展之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1914 年初,袁世凯废临时约法,解散各省议会,解除熊希龄之职,名流内阁遂倒台,继之以撤销国务院、废各省都督、设政事堂和将军府。袁世凯还身穿古装祭孔祀天,妄图独揽大权任终身大总统。1915 年5 月,袁世凯正式承认日本政府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8 月,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鼓吹帝制。11 月,御用国民代表大会赞成君主立宪。12 月12 日,袁世凯宣布为中华帝国皇帝,改国号为洪宪元年。
罗瘿公原本就和那班想攀龙附凤的人物枘凿不合,于是每日流连戏园,寄情歌场。当他目睹了袁世凯的种种作为之后,不念与袁曾有旧交,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公府秘书之职,为一时称重。
罗瘿公生于1872 年,卒于1924 年,这52 年间正是历史上极为动荡的一个时期,“甲午”“戊戌”“庚子”“辛亥”“五四”,大事迭出。罗瘿公虽然都没有参加,却也难以彻底地置身世外。他目睹北京城头不断更换的旗帜,眼见国家衰败破灭、战乱纷争所带来的艰难,心情异常沉痛和抑郁。他在战乱时期仍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留下了数十万字的历史笔记,为后人研究晚清、民国历史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
罗瘿公临终前,立下遗嘱:
显考罗瘿公惇于中华民国某年月日疾终某处。不著科名官职,前清已取消述之无谓也。民国未入仕,未受荣典,但为民而已。如公府秘书、国务院参议上门走及顾问咨询之类,但为拿钱机关,提之汗颜,不可涉及。
碑文式。诗人罗瘿公之墓。最好请陈伯严先生书之。不得称清诗人,盖久已为民国之民矣。⑦
罗瘿公耻称大清遗老,死后也不愿别人称他“清诗人”,是因为他耳濡目染了清末太多的战乱,亲身经历了清末官场的腐败,感到心灰意冷。然而这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王贵忱先生藏黄晦闻壬寅乡试落第卷,后有罗瘿公一跋,说:“吾生平知己惟文达公一人,自公薨后,遂以疏狂自放,逆知今世断无真知吾若文达公者,故宁颓废以没齿也。”⑧文达公即张百熙,在广雅书院时非常赏识罗瘿公的才华。因举荐康有为获罪,薨于1907 年。文达公的死,使罗瘿公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后来官场的种种经历更加剧了这种情绪。他对清廷无所眷恋,对民国政治亦很难认同,最终选择隐逸,驰情菊部。
二、隐逸篇
对官场的远离,使罗瘿公将目光转向了自然。宣统元年(1909),罗瘿公与当时的文豪樊樊山(增祥)、林畏庐(纾)诸人,集为诗社。每次集会,必选胜地,林畏庐作画,众人和之以诗,他们在大自然的山光物态中寻求心灵的宁静:
小坐春风啜茗谭,长安花事数精蓝。
眼前景物丁香占,劫后风光老衲谙。
似水年华过浴佛,故乡桑柘正眠蚕。
时危那更知来日,且可勤来共一龛。⑨
乱栽花竹公归处,舍宅千秋剩此堂。
髡柳尚僛含雨翠,万荷齐迸远风香。
争墩轻益林泉趣,补屋宁知草树荒。
更策疲驴冲潦云,钟山一角坐招凉。⑩
不同朝代的文人们都曾将隐逸山林作为安顿生命的一种方式,它能使人暂时忘记人世的庸碌烦恼,摆脱滚滚红尘的纷扰。六朝人出于对大自然的眷恋,对人格操守的自持而隐逸山林。而罗瘿公则是为了回避官场的是非纷争隐迹山林,在行云流水间感受大自然的清新壮丽:“我昨盘山访红叶,蹋遍千峰万峰雪。归来煮酒话瘿庵,雪色吟声两奇绝”(《和尧老江亭大雪用东坡聚星堂韵》);“一筇身出万松颠,脚底诸峰气藐然。张袂平收东海水,翦门散作蓟门烟”(《上盘顶云罩寺暮不达而返》);“万峰高下影窗前,星斗依微接曙天……霞光动海诸天豁,日气蒸山众态妍”(《万松寺待晓》)。他以诗人的情怀、超逸的姿态,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表现出一种闲适悠然的生命状态。
历来文人对自然都情有独钟,这与他们都信奉儒家学说密不可分。儒家思想中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说法:仕途顺利时,就可以朝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努力;不顺,则可以退回来,自我修炼。孔子一方面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的理论,另一方面对其弟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逸情非常欣赏。罗瘿公也是在山水自然中寻求解脱,颐养性情,荡涤心灵的尘垢。看得出诗人对大自然中的雪有着独特的感受。他在《辛亥岁朝大雪得尧生侍御除夕雪诗成此当和》一诗中表明了不愿南归故里的原因:“我归无田又无雪,贪醉长安看雪飞。” 罗瘿公的很多首诗作中都有雪的意象,如“惊心明日是中年,腊尽长安雪满天”(《庚戌岁除小病见雪》);“雪中唤起西山睡,心拟花时看耦耕”(《正月初二雪晴作》);“一庐天地佛香外,满眼公卿春雪中”(《吾生》)。
平生快意几回雪,风车晓过泰岱前。
千山皆成缟素色,百里尽是琼瑶天。
天为玉海挟地转,山作银涛随毂翻。
中有白龙来蜿蜒,瞥入几案俄渺然。
我时凭窗衣薄绵,一榻暖如春日妍。
龙沙毛幕裘拥毡,拔刀割炙轰杯盘。
灞桥驴背剡溪船,羊羔酌与雪水煎。
较量风味谁最贤,王城闭置竟何作。
未辧青鞋悔尘缚,冬山祗合蒙毂练。
深雪尤宜贮林壑,挂眼西山白到城。
想象远梅红破萼,客冬大雪玉泉山。
提挈稚弱浮图攀,俯睇离宫烂银阙。
叠嶂不敢开苍颜,明知奇景追火速。
定有腰脚如吾顽,正当犯寒直上千。
崖顶收取幽燕雪,雪色寘之怀袖间。⑪
诗中充满了对雪的喜爱以及诗人欢愉、闲适的心情。他从自然中体会到宇宙的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自然和人生,达到一种超越尘世、天人合一的境界。
烟峦林杪出云扃,欲挈江流赴石城,
袖底三山收紫翠,尊前六代入空冥。
一流向尽伤颓照,千劫苍茫剩此亭,
收拾湖光从倦鸟,疏杨归路带寒星。⑫
千峰绝顶支床处,梦里松涛杂梵声,
高月转霄回夜气,空阶鸣叶迸凉酲。
万缘灭后余禅味,一枕颓然接太清,
袱被尚思从老衲,稍怜寒拾不同盟。⑬
细品罗瘿公的诗作皆含有一丝禅意,并且他的多首咏景抒怀之作都与佛教、寺庙相关联,如《万松寺待晓》《游天童因呈寄禅上人》《慈仁寺访松谒顾先生祠同诸公作》《崇效寺呈蛰公》《天宁寺赋呈石遗叟》《极乐寺看海棠作》《卧佛寺》《宿潭柘寺》等。他京城的居所名为瘿庵,亦可知其有向佛之心。
其实,禅宗原本就崇尚自然,让人们从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中体会到宇宙、生命的真意。它和道家一样,以气韵生动的自然向失意之人昭示着一种新的人生观,使失意之人抚平伤痛,它们共同形成了儒家理想的互补结构。罗瘿公正是在经历了政治的失意后,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禅宗的世界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将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融和起来,形成了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存态度。正是这样一种人生态度使他在后来遭遇的困顿中保持了不失格调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三、梨园篇
罗瘿公退出官场之后,整日投身歌场,流连戏园,与梨园艺人结下了友好情谊。他的才华,深得艺人们的敬重,每逢年节或特殊日子,罗瘿公都很乐于题赠一些诗篇给艺人:
名伶三世梅余耳,英秀而还汝最贤。侪辈卯时俱习熟,而翁在日屡周旋。
更能将母承先志,难得称觞值闰年。真舞斑衣学莱子,听歌吾亦忘华颠。⑭
余叔言是京剧老生行余派创始人,被京剧界和学术界公认为是继谭鑫培之后的京剧老生泰斗。这首诗是罗瘿公为余叔言母亲六十大寿所题,诗中对余叔言的孝行大加赞扬:
相逢喜未减容光,旧话重温意倍长。新岁仆人齐下拜,七年儿女渐成行。重来京国添春色,莫要扬州念故乡。满目兵尘犹未洗,又烦歌舞日登场。⑮
此诗是罗瘿公为迎接贾璧云自沪返京而作。贾璧云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旦角演员,时有评论称:“与十三旦(侯俊山)全盛时埒,都人靡不道贾郎。”⑯
贾璧云性情耿直,不畏强权,受到很多文人的钦佩。罗瘿公与之相交多年,此诗是二人分别七年后再次相聚所作,表达了诗人的喜悦之情。
驿路花飞送玉郎,练裙雕珮总生光。长安士女愁眉坐,徐福童男拍手狂。
日预离筵共酒杯,争看渡海不凡才。出门郑重无多语,入手声名及早回。⑰
1919 年,梅兰芳首次受邀赴日本演出,罗瘿公前来送行,赠此诗,以表对其艺术的赞扬和依依惜别之情。
除上述诗作外,罗瘿公另有《玉芙乞书箑赋此示之》《畹华令祖母八十寿诗》《贾郎为之汉口为诗送之》《题诸伶画册》等数首诗,说明他与当时的一些名角交谊颇深。他也多次在诗中提到纵情鞠部带给他的无尽快乐:“性本难禁酒,缘何不听歌”(《追春六韵》);“一月竟连阴,几日青天破……但恨阻听歌,未免惜此座”(《苦雨》);“差幸听歌无间阻,不知来岁定何如”(《丁已除夕》);“终年听曲行吟处,尽是先生快活时”(《扰扰》)……
然而,他投身梨园的行为却遭到很多人的不理解。好友黄晦闻在《瘿庵诗集序》中这样写道:
瘿庵驰情鞠部,世有疑而议之者。余尝举以相规。则答于,书曰:吾欲以无聊疏脱,自暴于时,故借一途以自托。使世共讪笑之,则无暇批评。其余非真有所痴恋也。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纵情歌场的生活方式对于文人传统的人格理想无疑是一种挑战,一种摒弃。罗瘿公退出政坛,远离官场,“自暴于时”而自托于梨园,对这种生活的选择,的确意味着一种人生态度的自我调适,自我转变,这样做需要勇气,需要胆量,更有不为外人所知的原因。罗瘿公选择梨园一方面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一种“避祸”的心理,“终忧闭门有危阱,且讬疏狂散愁疾”⑱,罗瘿公以此作为托词而躲避迫害,但是在梨园“避祸”期间,他越来越深入其中,进而痴迷忘返。罗瘿公在一次拜访好友黄晦闻时说道:“吾度日之资今日只余一金耳,以易铜币百数十枚,实囊中不复听歌钱也。”⑲年关难度,尤不忘听歌。罗瘿公京城居所名为瘿庵,庵内所供都是佛像,而以名伶小影悬于佛像之上,瘿公同时代诗人赵熙谓此“古佛无言守玉郎”。由此可见,罗瘿公对歌场、名伶的由衷喜爱。
远离尘嚣,寄情梨园,寻获一种自得自适的生活,使罗瘿公的诗中蕴含了一种闲适散淡的逸情:
午枕醒余残暑消,蠹书罢理更长谣。洒然已觉风捎竹,静极惟闻雨打蕉。一室扫除吾事了,万缘灭后篆香销。王城自有宪中味,丛桂何劳苦见招。⑳
廊庙山林两不收,绳床高卧更何求。好官岂待思玄保,生子宁须似仲谋。
本未识途非老马,尽饶闲地著沙鸥。腹中空洞原无物,日足黄齑饱即休。㉑
奇气中年病埽除,日高乱拥半床书。了无兴废关渠事,或寄声歌纵所如……㉒
1917 年,罗瘿公见到了程砚秋,这一见便结下了二人的不解之缘。罗瘿公在《赠程郎》诗中道出他对程砚秋的喜爱和欣赏,题记曰:
程砚秋,京旗人,父荣某,国变后冠汉姓。父殁,寄养伶人荣蝶仙家,延师教艺,习青衫三年始出奏技,今十六岁矣。(按:程砚秋实际年龄应为13 岁)余屡闻人誉艳秋,未之奇也。一日观梅郎剧罢,杨子穆生盛道艳秋声色之美,遂偕听曲,一见惊其慧丽,聆其音宛转妥帖,有先正之风。异日见于伶官钱家,温婉绰约,容光四照;与之语,温雅有度。朅来菊部颓靡,有乏才之叹,方恐他日无继梅郎者;今艳秋晚出,风华相映,他时继轨,舍艳秋其谁?来轸方遒,当仁不让,勖力以诗。
诗曰:
日下新声渐寂寥,梅郎才调本天骄。谁知后辈风华甚,听彻清歌意也消。
除却梅郎无此才,城东车马为君来。笑余计日忙何事,看罢秋花又看梅。
协律陈郎(彦衡)最自豪,鹍弦矜绝不轻操。肯陪日暮歌台侧,珍重延年一语褒。
小李将军(李释戡)意气横,《散花》《奔月》制新声。平生难得垂青眼,许尔他年继老成。
风雅何人作总持,老夫无日不开眉。纷纷子弟皆相视,只觉程郎是可儿。
紫稼当年绝代人,梅村蒙叟足相亲。而今合待樊山老,评尔筵前一曲新。㉓
用罗瘿公的话说,程砚秋其貌慧丽,其音宛转妥帖,其人温婉绰约,其语温雅有度,其声来轸方遒。难怪罗瘿公会在“纷纷子弟”中“只觉程郎是可儿”。正是程砚秋的才华和气质,博得了罗瘿公的偏爱;也正是出于爱才之心,罗瘿公才会在程砚秋艺术生涯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
当时,13 岁的程砚秋正处于倒仓期。倒仓对于戏曲演员来说非常危险,如果不注意休息、保养,嗓子很难恢复。而荣蝶仙为了几百两包银,硬是在程砚秋变嗓的时候与上海签订了协议。罗瘿公爱才心切,得知此消息后发动自己所有的关系,一方面四处筹钱,一方面调动各方面关系给荣蝶仙施加压力,终于将程砚秋从荣家接出来,当时还即兴赋诗一首:“金绦初解鸟高飞,谁道轻抛旧舞衣,柳絮作团春烂熳,随风直送玉郎归。”㉔此后不久,罗瘿公便将程砚秋一家从天桥搬到了北芦草园9 号,开始精心地培养。
七年中,罗瘿公为程砚秋延请名师,学习文武昆乱各门技艺,并且亲自教程砚秋识字、读诗文、作诗、练习书法、研习音韵,对程砚秋进行全面培养。还为他编写剧目,组织班社,筹划演出,创立新腔。因积劳成疾,身体几好几坏,始终不得痊愈。1923 年,罗瘿公痛失幼女,其妻哀痛之极,得了狂疾,终日疯疯癫癫。他的两个儿子年纪尚轻,还在读书。罗瘿公遭此变故,既伤女逝,又悯妻狂,心力交瘁。1924 年5月27 日,终于支撑不住,住进了德国医院,始知他所患是肺结核,并且到了难以治愈的程度。
为了治病,医院为他注射针药,月余日间,注射达三百余针,这使得罗瘿公不胜苦楚,他在诗中这样记述:
世人欲杀李太白,天意终存铁汉楼;
万楚千辛都历尽,又撑病骨入新秋。
故人每恚音书绝,忽讶讹言已九原;
一客相存报奇事,又求遗墨海王村。
吞针一钵同罗刹,袒背瘢痕似鄂公;
今岁再蒙天所赦,自标新号属甡翁。
注射针剂使他体无完肤,念及好友,音书已断,想要写信、题诗却又力不从心,其间的痛苦之状,可想而知。
是年9 月16 日晚,罗瘿公溘然长逝,终年52 岁。
罗瘿公逝后,老友黄晦闻为《瘿庵诗集》作序,其中论及罗瘿公为人,这样写道:
瘿公与世可深,而不求深于世;学书可深,而不求深于书;为诗可深,而不求深于诗。至其驰情鞠部,宜若深矣,然自谓非有所痴恋,则亦未尝求深。其绝笔诗,尚致叹于嗔痴损道。夫唯不求深,故万缘之空,犹得在未死之日,否则其怀早乱矣。乱则无所不至而义失,义失则诗虽存,存其字句声律耳,诗云乎哉?抑瘿公游不择人,言不迕物,读其诗者,随处而可见,盖其度大也。然使瘿公而不穷,则其志没矣;然虽穷而无瘿公之义之怀,则其志亦没矣。若非深知瘿公者,何能作此语。罗瘿公临终时,留下这样一首绝笔诗:
平生自诩安心法,每为嗔痴损道功;
今日病中才悟彻,万缘灭尽一心空。
诗后注道:“病中楚酷,凡人生痛苦,靡不尽历,惟灭尽思想,则痛苦渐减。今则痛苦渐尽,思想渐起,仍当力破嗔痴耳。”㉕病痛之余,还自省自身缺点,仍担心“嗔痴损道”,可见诗人的内心是怎样的纯然、虔诚。
①程永江编撰:《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卷),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②罗瘿公:《戊申除夕》,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③罗瘿公:《题罗两峰鬼趣图》,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④⑤《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罗瘿公笔记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⑥罗瘿公:《鞠部丛谈》,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
⑦程永江编撰:《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卷),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⑧《听曲看花亦绝伦》,转引自博客:往事(http://eluncun.bokee.com)
⑨罗瘿公:《尧公招集法源寺》,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⑩罗瘿公:《半山亭荆公舍宅》,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⑪罗瘿公:《对雪》,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⑫罗瘿公:《登清凉山》,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⑬罗瘿公:《宿万松寺》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⑭罗瘿公:《余叔言为其母六十寿》,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⑮罗瘿公:《贾郎璧云自沪上归相见赋赠》,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⑯胡冬生、苏移、韩希白、侯硕平主编:《中国京剧史》(中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版。
⑰罗瘿公:《送畹华之日本》,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⑱罗瘿公:《岁暮吟次晦闻韵》,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⑲黄晦闻作《瘿庵诗集序》,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⑳罗瘿公:《午枕》,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㉑㉒罗瘿公:《偶成》,见《民国诗集丛刊·瘿庵诗集》,国家图书馆馆藏。
㉓程永江编撰:《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卷),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㉔陈培仲、胡世均:《程砚秋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㉕程永江编撰:《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卷),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