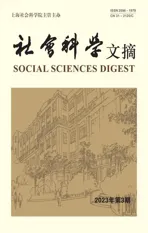口头诗学当代意义的再认识
2023-09-23意娜
文/意娜
社会进入电子时代以后,才真正区分了口头与书面文学。数字语音时代的来临,使基于口头的相关文艺样态得以复兴。语音—口传文艺,在视觉—音频传输中彰显了强大的能量,突破了书面文学独霸的局面。这种后现代式的颠覆,让我们返回对口头传统的研究,在理论领域引出对口头诗学当代意义的重新思考。书面语是同一性普遍影响的结果,而口语则更多表现了个体语言表达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口头诗学从过去对民间的、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的描述,观照到当下书面文学理论无法覆盖的缺环,值得加以认真审视和关注。
传统总是默认以时间顺序排列,较远的传统比诸较近的传统有更特别的分量。传统也有地域性,某一传统“理应”属于某一地域范畴。一般来说,“传统”可以定义为一种历时性规范,如信仰、习俗、伦理、技术等。在讨论过去岁月的生活方式、文化遗产,展开文化比较和文明对话,以及说服异见者时,传统是最有力的论据之一。同时,传统又极为脆弱,现代性是其最大的破坏者。但吊诡的是,现代性作为破坏传统的力量,以“破旧立新”为特征,却也形成了理性传统。如此,传统还能打破传统,传统何为?
传统既然可以打破传统,就提示我们对传统的理解需要使用不同限定词,比如美术传统、婚姻传统、文学传统等。在口头文学领域,就成为“口头传统”。但另一方面,传统打破传统的发生,如果仅仅是定语之间的争执,传统本身就失去了存在意义。当我们高呼“保护传统”,我们是否清楚明白保护的是什么,如何去保护。因此,虽然传统如此常用,对其的理解却始终未能透彻。
口头传统的时间相关性
至少从公元前500年人们思考“荷马问题”开始,口头传统就进入研究视野,并从帕里与洛德的口头程式理论研究开始进入学术视野,建构起程式、主题/典型场景、故事范型/类型的理论框架。
现代文学理论的底色是对书面作品各要素的分析和关系研究。口头程式理论中使用的一些概念,尽管往往前缀多重定语以与书面文学理论名词相区分,最后更像是书面文学理论的特殊案例和补充。这带给口头形态文学研究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产生了基于文献版本逻辑建立的“时间”研究观念,比如从口头史诗唱词中推断故事中人物的“实际”生卒年、事件的实际发生时间等。
“口头传统”作为“传统”的一种,也带有对“传统”的一般认知偏向,即推崇其传承之久远,仿佛只有古老才能证明这一传统的价值。或者说,如果“传统”不与“古老”和“悠久”搭配,“传统”一词就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其实“口头传统”并不需要用时间的悠远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因为各种证据显示,在21世纪,“口头传统仍然是主要的传播方式”,“活态”才是它最大的特征。身处悠久历史文化中的人,会自觉地将时间更长的传统视为更重要、更合适、更经典者。尽管我们并不认为传统与时间之间存在正向对应关系,但口头传统确乎具有时间相关性。口头传统遵循“源头”“流传”这样带有流水隐喻的时间性,其中包含自足的时间和时间刻度系统。伽达默尔将“传统”界定为“流传的”物质遗产、精神记忆和行为习惯。洪汉鼎将其翻译为“历史流传物”,指向了两个属性:产生于“过去时”的历史属性,活态流传中的“共时”属性。
口头传统的研究者时常希望从“历法计时体系”,也就是通用计时方式,如公历、农历、佛历、回历、年号等来对口头传统内容的时间轴进行标注,试图将口头传统与“科学”对标,以“规范”口头传统研究。但多久的过去可以成为传统?有学者认为需历时三代。“代”的使用非确指,而是一种指代:每一代有多长时间并不受限制。从这一立场看,具体的时间长短就不那么重要了,口头传统是否真的传承了“千年”,并不是多数研究话题所需要的合法性证明。口头传统成为传统的关键,并不在于存续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传承过程中是否产生了“神圣性”。
这里所谈的“神圣性”无关宗教信仰,而是用来描述“往往以过去的形式出现”,以一种历史时间性的假象,来确立一种“本身没有‘原因’,它就是一切的原因”、称之为“传统”的理由。所以口头传统的时间线与历史学的时间线并不同,即便是当下的创作,也因为依附于被尊为传统的仪式、程式或主题,仍然被称作“口头传统”。
神圣化创作者是口头传统的一大特征。比如以《格萨尔》为代表的史诗说唱。灵感来源神秘的史诗说唱艺人会拥有更高的声望。这是在如今对传承人提倡重视和保护,进而逐渐消泯过去藏族艺术传统中“匿名性”的过程中,某种突如其来的逆转,足见创作者的神圣性是藏族口头传统极为强调的特征。藏族将神授现象运用到许多方面,除了史诗说唱,唐卡绘画、藏文创制等都有与神授相关的传说。
这种对创作者的尊崇并不是当代口头史诗所独有的。历史上最典型的就是强调“经”,这成为口头诗学和书面文学理论共享的通则。“圣者作、贤者述”的中国传统,与西方的注释传统,或称“圣典”“教义”传统也基本相同。口头传统神圣性的建构,有着与书面文本的经典化类似的过程,是以经验积累为基础的,这种经验就是“记忆”。经过“经验实践—惯习养成—范式选择—对象命名—团体认同—理念传播—经典形塑—教育孵化—仪式确认”的过程,口头传统就具有了某种神圣性。
口头传统的双向复述
当我们说尊重与保护传统,是希望能够保持一些被称为“传统”的部分不被改变,保持“原样”。这种对同一性的诉求在界定不明时很容易被理解为“原本”中心论。在书面文学传统中,源头经典是“原本”,回到原本是解释一切正当性的基础,“回到孔子”或者“回到苏格拉底”等回到原本的诉求总会在传统被威胁时适时出现。
在解释学的视野里,处于流传中的传统,“既是此一物,又是彼一物”。口头传统在亦此亦彼之间,沿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展开复述:向后回归源头和向前继续发展。向后回归源头,也是我们一般意义上对复述的认知,即对已有的、原本的“传统”忠实地进行模仿,追溯口头传统的“代代相传”。如今我们叙述口头传统时,常常会将自己局限于“少数族裔”“原住民”等视野,但其实所有具有世界意义的源头经典在传播之初,大多或长或短有一段口头传播的历史。
口头传统的讲述者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帮助我们认识这种对源头的复述。仍然以《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为例,不同类型的艺人都用各自的方式来确认“源头”。神授艺人从根本上确保了源头的合法性和对源头的还原度,虽然是代代相传的口头传统,但神授艺人的蓝本直接来自神或者史诗故事本身。漫长的转述和改写、创作历史在神授传统中被有意略过了,“原本”的权威得到了保证。同样,藏族史诗独有的圆光艺人和掘藏艺人也是如此,只是方式不同。闻知艺人是几乎所有史诗传承的主要方式,要求艺人记忆力强,善于模仿,善于阅读,博闻强记。闻知艺人依靠自己的记忆力来保证对于史诗“源头”的忠实。
除了人的因素,口头文学的许多特征也保证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内容能被最大程度地记忆并准确传递。在口头程式理论中,程式被识别为“任何重复出现”。“反复出现”的“片语”和反复出现的典型场景,“很好地解释了那些杰出的口头诗人何以能够表演成千上万的诗行,何以具有流畅的现场创作能力的问题”。尽量靠近“原本”的复述都不是“原本”,而是一种阐释。何况再高明的记忆天才也难以保证内容的原封不动,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内容一定会发生变化,有学者称之为“自身疏异化”。因此,对于口头传统的关注,单向追溯原本的道路并不完整,还需要关注前行的复述。
前行的复述通往另一个方向,在一代代传承复制过程中,经过层层解读,实现转化,最后的结果或者推动了传统的发展,或者改变了传统的样子。口头传统领域的“表演理论”就代表了这一方向。该理论认为口头诗歌文本是“表演中的创作”,“每一次表演都是一次创作”。若将这种复述的语境极端化,即用另一种自然语言来“复述”,能看到这一向度显著的特征。在同一种自然语言下的“复述”也同此理,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复述者”的作者身份与本土性
口头传统正是如此处于表面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口头传统也是传统,受到对“传统”偏见的束缚:人们认为有一个必须遵循的标准,传统离这个标准越近,越具有说服力。为了增强这种说服力,部分口头传统发展到了一种极致,即以神秘化的方式确保口头传统的神圣性和讲述者的权威性,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了口头传统的相关标准,也就是口头传统的实践者们所宣称的“恪守传统”。另一方面,口头传统又不像书面文学那样有一个被认定的标准本或权威本作为规范“文本”,无法设定参数来比对各种版本之间是否有差异,有怎样的差异,是否尊重了“原本”。这样一来口头传统自然处于一个有意无意都会盈缩增减的动态状态,看上去似乎不如书面文本那样有规可循,但最后一定会遵循“万变不离其宗”的观念,也就是所谓的“在程度之内变异”。至于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可以认定是对“宗”的推崇和追随。中国古代“丸之走盘”的比喻,被引申为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万变不离其宗”的特征。显然,在我们理解口头传统时,多少也受到这种古典思维的影响。
“万变”给予了在“宗”的羽翼下充分解读和变化的权力。“变”的实施者都在“宗”的语境下成长,也在“宗”的语境下理解“宗”,他们的思维范式在“宗”内,所以不离其“宗”是一种逻辑上必然的结果。不过“宗”形成并完善于过去某个时间点,所有的“变”都与它有时间距离,只是距离长短不同,这一点在过去常被忽视。由于具有时间距离,即便是处于同一传统的前理解结构下,复述者所处的历史时间点与原本已经不同,有了新的时代理解和要求,形成了新的传统。复述者复述的是一个处于过去相对完整、封闭语境中的原本,但是将这一原本拿到了复述者所处的当下语境中来讲述。原本的生命力和意义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才显现出来,两种历史语境得以结合,成为伽达默尔所命名的“效果历史”。
在过去的套路中,都是以原本的“宗”为中心的,区别只在于现代的研究视角除了尊重“传统”,增加了对复述者视域的关注,在复述原本的过程中对原本有所发展。伟大的依然是“原本”,也就是那个“宗”,优秀的复述者也只是“复述”者,他以承载者的身份搬运了“宗”。源头创立和后世流传都需要各时期的复述者不断地讲述。他们的角色比创立者还重要,担任了经典的鉴定者、记诵者、解释者、传承者等多种角色。在该传统传承过程中遭遇内外危机时,还要担任改革者、协调者的角色,力挽狂澜。实际上,他们才是真正的作者,或者说是传统的主人和实践者。我们习惯于评价一位史诗说唱艺人成就的标准是他能够讲述的史诗部数,比如江格尔奇朱乃能够讲述26部长诗,玛纳斯奇居素普·玛玛依一个人讲出的《玛纳斯》就整理出18部23万行。不过,我们在文学史建构中,很少用作品数量来衡量作家的成就。由此可见,在研究视野中,虽然也在注重史诗的创作过程,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史诗说唱艺人还没有被真正当作“作者”来对待。
毋庸置疑,口头传统具有空间特征,并在近年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越发得到关注。地区差别对口头传统最大的影响是语言,不同的语言可以被称为“方言”。空间给生活在其中的主体提供了一种思维界限,以“特殊的方言性叙事”为特征。这种“方言性叙事”既包括同一种自然语言在同一地区经过历时性发展产生的变化,也包括不同空间里同一种或多种自然语言下的语言差别。
这种本土性的命名和归属其实也容易陷入悖论。地理边界在这个意义上成为进行判断我与他者、正常与荒诞的唯一且科学的标准。当我们谈到传统,尤其是口头传统时,需要建立一种立体的观念,除了纵向的传统观念以外,还需要关注横向的传统。纵向的传统“来自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宗教共同体以及被大众接受的传统”;横向的传统是“由这个时代与这个时代的人们施加给我们的”。横向的传统其实有时更加重要,但总是被忽视,所以“在‘我们是什么’与‘我们认为我们是什么’之间存在鸿沟”。
从18世纪、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虽然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许多少数民族(原住民)文化渐次被外部世界发现,但那是一个人类学西方中心主义的时期,对待西方以外的文化传统主要是以“猎奇”为出发点的,这些文化被当作野蛮落后但充满神秘风情的文化表征介绍给发达世界。从20世纪上半叶之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人口流动的频繁,文化传统以朝向一种彼此平等的“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面目重新呈现于大众媒体和互联网。此时再看传统的本土性,就带上了复杂的色彩:在被他者的视线“平等”对待并借助全球化路径被广而告之的同时,本身却又会在文化保护的意识下,表现出比过去强得多的排他性的逆全球化特征。如何走出纵向流传的“舒适区”,在横向的流通中继续流传?这是对口头传统提出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