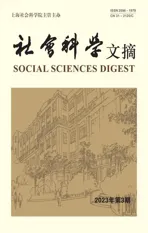世俗时代的精神图景
2023-09-23杜维明查尔斯泰勒邱楚媛
文/杜维明 查尔斯·泰勒 译/邱楚媛
思想界的新变化:对精神性的回归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近年来我发现,在思想界,甚至在专业哲学研究的圈子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变化——它涉及对精神性的重要性的认识。我自身的经验是存在局限的,但我观察到,即使是德里达,在他晚年也回归到犹太教的精神性传统中去谈论宽恕的议题。普特南在他退休之前,也开设了一系列课程来讲述四位极具精神性关注的思想家:迈蒙尼德、罗森茨维格、马丁·布伯和列维纳斯。这一切都表明,理查德·罗蒂阐述的那种解构主义只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甚至可能不是最有说服力的。你的作品《世俗时代》也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论点,即世俗时代应当以某种方式结束,尽管人们可能不接受你关于“超越”的重要性再度出现的观点。
查尔斯·泰勒(以下简称“泰勒”):是的,我认为变化已经出现。那些曾经排斥精神性的人,有许多已经转变了。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变化。我想很多以前对精神性不屑一顾的人已经意识到,如果你排除了对精神性的思考和谈论,你就排除了人类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排除了人类生活中很多好的和坏的东西的根源,从而导致对人类生活的理解残缺不全。当你从但丁的《神曲》和巴赫的《圣歌》等作品所呈现的西方传统来思考时,显然其中有一些被精神性传统所滋养的极其重要的东西。我认为一些哲学家开始对强硬的世俗主义失去了耐心,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在寻找一条精神性的道路,但至少他们开始担心我们对人类的理解正在日益变得狭隘。对这些精神性的内容,有的人会说是精神信仰,还有人会说是终极关怀。尽管他们会有不同的解释,但都认为精神性以某种方式探索和揭示了人类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杜:当我第一次接触到你关于自我的根源和本真性的研究时,我就觉得其中有很强的精神性的成分。现在我想提出一个个人问题。作为职业哲学家,大多数人都会把他们的个人信念与其哲学工作明确区分开来。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对儒家传统怀有认同,所以所谓“完全无利害关系的立场”对我已经不适用了。你的情况是怎样呢?
泰勒:我认为我们提出的哲学论点必须是在原则上可以说服任何人的。所以如果我提出的论证是基于“上帝存在”这一前提,那就不是一个哲学论证,因为我无法从其他人、从另一个立场开启我的论证。而我们必须和所有人交流,即使我们不能说服所有人。这就是我在哲学上对这种情况的看法。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持一种立场,他就会有某种直觉;而另一个人持另一种立场,他就会有另一种直觉。在某种程度上,“完全的敞明”在哲学中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你应当让人们知道你来自哪里,你的直觉的来源是什么。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处理的这些哲学或人类的问题其实是解释的问题。谁能最大程度地理解文本、理解人类的生活和历史以及其他事项呢?当你有一个观点而我有另一个观点时,我对你说:“你的观点还不错,只是太狭隘了。我有一个想法,我认为可以涵盖你的。”类似这样的争论循环往复。所以我得努力说服你,其依据是历史上发生过这类事情,而你就是这么解释的。尽管如此,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是和我的整个生活密不可分。所以让我们坦诚相待,我来自这个传统,你来自那个传统。我很钦佩也很尊重你的工作,每个人都知道你思想的根源,但你并没有提出在原则上不能说服每个人的论点,你也没有说这就是一种好的存在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好的操作方式。
杜:我们可以从更哲学的角度来描述它,比如,用伽达默尔关于前理解或偏见的观点来描述。但我在最近三四年产生一个想法,即我试图在私人(private)和个人(personal)之间进行区分。你追随约翰·密尔的传统,因此你主张必须培养一种隐私意识,这在政治哲学中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当我说这是我的“私”(private)事时,意味着我不想和任何人分享。但是“个人的”(personal)这个词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当我说“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时,可能意味着这是主观的、私密的,但也很可能意味着我对这个观点持有生存论上的认同。在后一种意义上,正因为是个人的问题,我才有不同的看法想与你探讨,所以它不仅是可问责的、公开透明的,而且还可以被证伪。这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重要讨论,比如迈克尔·波兰尼的个人知识概念。唐君毅曾指出:“作为哲学家,我们真应该对我们所读的书、所做的事产生一种敬畏感、一种尊重感。”现在看来,这话很有道理。但当时他受到一些分析哲学家的攻诘,他们说:“这个人还不够哲学。”在他们看来,如果你说“我有一种敬畏感”,那就意味着你在谈论宗教,而不是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果一个哲学家说他在做宗教研究,那无异于“死亡之吻”。那意味着他没有论据,也没有推理的能力。因此,我常常感觉到,完全表明自己的价值立场有时是不可能的。当我说:“我是一个儒家。”他们说:“既然如此,那你对儒家思想的讨论是有偏见的。因为你对它有偏好。”.
泰勒:我想他们没有看到的是,理性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实是阐明新的愿景。换言之,这很像托马斯·库恩关于范式转换的观点。在科学上,如果你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研究证据,是不会有任何进展的。只有当人们产生新范式的想法时,才能以新的方式使证据之间形成相关性,然后它们开始结合到一起。所以,得到这些洞见是非常重要的。你是出于对儒学的热爱才获得关于儒家思想的洞见,如果你不爱它,你就不会获得这些洞见。要想使富有创造力的人为讨论作出贡献,我们就必须允许对讨论对象有偏好的人参与其中,否则讨论将无法产生新意。我觉得这种排斥情感偏好的观点就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已经事先提出,我们不需要再去作进一步的创造,我们只需要对它们进行严格的检验就可以知晓一切。这就是那种老式的实证主义观点。
杜:但这种观点还是非常强大,无处不在。即使是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倪德卫先生,也曾对我坦言:“我正在摆脱哲学。我想做一些与以往不同的事情。”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他是儒家传统尤其是儒家美德伦理最好的诠释者之一。他说:“我想做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比如,我想去考证孔子所钟爱的周朝是在某一年份完成了对殷商的征服。”我说:“为什么?这并不是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他说:“我从事哲学工作已经很久了。我提出的任何观点都会有反对观点,以及更多的不同观点。我现在做的研究确定性如此之强,以至于没有其他人能够提出反驳。”
因此,我越来越意识到,不仅是在哲学或者宗教学领域,甚至在史学以及科学领域,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按照库恩的说法,如果科学界是这个样子的,那为什么还会有哥本哈根学派?为什么会有尼尔斯·玻尔?为什么要认定这个问题很重要,那个问题却不重要?这不仅是知识社会学的问题。在科学探究的结构中,也有个人因素的参与。如果你不热爱它,你怎么能成为一流的科学家?
泰勒:的确如此,我想我们都完全赞同这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不接受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实。我想这是因为旧实证主义的根基很牢。对许多人来说,它就是理性的代名词,人们的思考不能偏离它。如果你要求他们跳出那个框架,会让他们非常不舒服。还有一点就是,当你观察他们时,你知道他们对某些具体的事物确实有所偏爱。他们偏爱某些原则,在潜意识中这样去做。
杜:你刚才提到理性的偏离,但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涉及理性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在韦伯的概念中,人有工具理性,但是也存在关于理性的限度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在很多领域中,理性要么是不相关的,要么并不重要,比如常识性的内容。我不知道你对理性的限度问题有何看法?
泰勒: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关于理性的自觉意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某些主题中你永远无法做到完全正确,而在其他主题中可以做到。你对一个修辞家或演说家的要求,并不会像要求数学家那样精确无误。这是主题的差异所致。因此,当你谈论常识时,你谈论的是聚合了很多原因的事情,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无法一一列举这些原因。比如我们坐在这里一起谈论“证明”,但你所说的“证明”是什么意思?你必须给出一个有人怀疑它的背景,这是其一;你还必须对不同的问题有自觉的认识,这是其二;其三就是我刚才说的,推理的过程中经常需要有人引入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可以使我们真正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事物,它可能会变成拓展我们视野的最好方式,所以这也是理性的一部分。因此,你不能把理性简单看作一种通过正确的演绎就可以做出推理、避免产生矛盾、接受明显成立的事实的能力,尽管许多人想将理性限制在推理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真的将理性限制于此,那么我们根本不会想到任何有趣的事情,那样就不会有进步了。我们将不会有牛顿,也不会有伽利略,这就是对理性进行如此狭隘理解的后果。
超越欧洲中心主义
杜:接下来我们谈一谈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贝拉表达过一个观点,西方(欧洲和北美)下一代真正杰出的哲学思想家需要对外部世界的知识有所了解,或者至少愿意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如果没有这种自觉意识,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哲学家、思想家。遗憾的是,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一些影响了哲学话语塑造的最重要人物都变得非常狭隘,或者至少流露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福柯实际上就是其中之一。德里达甚至可以说是傲慢的,他说过“不存在中国哲学”或类似的话。在中国也有一个挑衅性的争论,即:“有没有中国哲.学,还是只是哲学来到了中国?”当然,哈贝马斯也属于这个群体。我认为你的研究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也许因为你是加拿大人,我不确定。
泰勒:我想确实是这样。我来自魁北克,成长于双语的环境,能看到这两种模式。很多人认定这个世界就像他们的语言所描绘的那样,而对于语境之外的事物,他们的理解是混乱不清的。但我认为,我们应当意识到人们之间必须互相解释,所以我养成了这个习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存在不同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当你觉得人们在胡说八道的时候,那只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一些东西。因此,你最好学会他们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学习其他思维方式的语言对我的工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杜:我认为美国对待多元文化主义的态度不同于加拿大的做法,后者一定是你的哲学理念最重要的灵感来源之一。比如在多伦多,人们很早就刻意把多元文化作为值得庆祝的事情。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推广不是无意间取得的,而是通过斗争得来的。其中存在着竞争和对抗,你几乎必须要热衷并赢得对抗才能被接受。否则,你就不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而你作为哲学家,罗伯特·贝拉作为思想家,都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换言之,我认为一种多元主义的思潮正在兴起。
我察觉到,当你谈到中世纪时期上帝的重要性时,基本上只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神论立场。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在中国,这种立场甚至不存在被拒绝的可能性,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有关一神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利玛窦是一个伟大的融通主义者。他花了13年的时间学习汉语,使自己看上去几乎像一个儒家文人。他也使一些杰出的士大夫学者成为基督徒,但后来他遇到了麻烦,因为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不接受他允许中国人进行祖先崇拜或者保留祖先崇拜的做法。而当教廷认定耶稣会士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国皇帝就生气了。这就是“中国礼仪之争”。然而,利玛窦在当时的确想转变中国人的信仰。这激起了我的思考——利玛窦的策略是什么?我认为他的策略是解构他那个时代的儒家思想,即理学或新儒学。为了使它失去合法性,利玛窦认为,必须回到源头,必须回到孔子,甚至是孔子之前。因为“天”的观念在利玛窦时代的中国已经转换为一种非常不同的话语。理学话语下“天”的最终来源不是早期儒家的人格化的天,而是我们称之为“理”或“理则”的基本原则。所以他试图通过回到理学观念的源头来解构当时的儒学。如果你想修正你的观念,你会不会认为以上帝为中心的超越只是进入世俗时代的一个版本?是否还存在其他版本?
泰勒:是的,我对此深有所感。我愿意这样去表述:有很多关于人类生活的深刻见解,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分散在迥然相异的观点之中,其中包括无神论的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过去我们不曾提出的东西。我们需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我们的共识。而要理解这个问题,我认为,要从“爱”的角度来了解这些不同的立场。在探寻另一个立场时,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人们为什么爱它。不要只罗列出干枯如尘的神学思想或儒家思想是如何说明它们的,我想深入了解人们为何对此感到兴致盎然,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因为把握了这一点而变得丰富起来。它可能会改变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方式,即使不能,它也会使我们对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宏大畛域产生更好的理解。我想让我们回到自身的信念中去,那是我们被人类的精神性召唤去做的事情。当然,自我反省或自我批评也是它的成果的一部分,但真正伟大的是共融。换句话说,通过彼此相互学习的活动,人们可以发展出一种友谊。他们因此深深地尊重对方,并产生了一种联系。如果真的能形成这种通往共融的交流,那么所有因为互不理解而造成的问题都会消失。如同你介绍的儒家思想那样,有各种信念者实际上都可以与他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