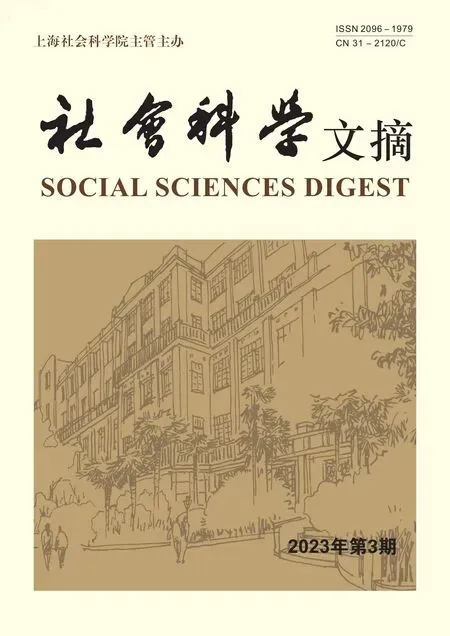东京审判的不容否定性
——兼及日本的争议缘起与学界评价
2023-09-23程兆奇
文/程兆奇
2006年,日本出版了一本名为《东京审判是捏造》(以下简称《捏造》)的书。《捏造》第一章第一节“今天为什么要研究东京审判”之下有两个小标题,一是“日本人自信心丧失的根本原因是东京审判的精神创伤”,二是“克服东京审判应是日本一切政策中最优先的政策”。日本以东京审判为主题的著作中,约有半数如同《捏造》,“研究”东京审判就是为了否定东京审判。本来,在一个“多元社会”,这一类来自右翼的否定在意料之中,不必随之起舞;但近年日本政治人物打破禁忌,从幕后走到台前,公然和右翼唱起一个调子,却很值得我们注意。如2013年,安倍晋三以首相身份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重要场合明确表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又如,2017年,稻田朋美在防相任上撰文纪念右翼代表性学者渡部升一,文中也呼吁要“克服东京审判史观”。局外人也许很难理解,对于东京审判这样一个去今已久的历史事件,日本政要为什么屡屡甘冒内外批判的风险发表反对言论?换言之,东京审判带给日本的究竟是什么?
在东京审判的多重意义中,有两点最为重要:第一是与纽伦堡审判共同开创了人类社会追究发动侵略战争元凶的先例;第二是对日本近代对外扩张是侵略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定性。前者对战后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刑事审判的司法实践至今仍有重要影响;后者对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秩序以及日本战后的政治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日本有关历史问题的所有争论中,东京审判是关键核心。也因此,与南京大屠杀等时起时伏的具体历史事件的争论不同,否定东京审判的主张从东京审判开庭之际日本辩方质疑管辖权起,便从未间断;这也是东京审判时日本政府曾在幕后操盘及东京审判后长时间搜集材料、组织研究等的主要原因。
东京审判的盖棺论定不仅关系到日本的侵略史,而且关系到战后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形塑。对日本来说,无论是想要恢复历史上的所谓“荣光”,还是试图要从“和平国家”(非核、专守防卫等)转为所谓“正常国家”,否定东京审判都是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东京审判并没有走入历史,对它的讨论不仅是学术界的事,而且与现实的国际政治密切相关。
日本围绕东京审判的争论
围绕东京审判的争论起于开庭之际,争论涉及法理、证据、程序等许多方面,核心是管辖权之争,尤其是伦敦会议为战后国际军事审判确定的“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的所谓“事后法”问题成为争论焦点。针对以清濑一郎为代表的日本辩方不断纠缠,首席检察官季南、英国检察官柯明斯-卡尔等检察官团队以相关史实结合国际法权威著作和近代以来国际法、国际条约中有关发动战争和战争犯罪的规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但检方的回应未能阻止辩方的节外生枝,反而激发了辩方阻挠审判的企图。有鉴于此,为了避免审判无限期拖延,庭长韦伯宣布对辩方关于法庭合法性的质疑“全部驳回”,以后判决书重申法庭合法性的源泉就是“盟国最高统帅”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和莫斯科会议的授权。这一点从审判时的辩方到今天的日本右翼,始终认为是不可接受的。
法庭进入庭审之后,检方提出的几乎所有主张与所有被告的罪责都受到了日本辩方的反驳,这是东京审判之所以旷日持久、大大超出预期的主要原因。当时检辩双方的攻防虽在法庭之内激烈进行,但并没有燃烧到法庭之外。原因与东京审判时日本处于百废待兴的战败初期、被告的命运难以成为关注焦点有关,更与追究战争责任——包括日本独有的所谓“战败责任”——的浓厚氛围有关。当时普遍认为,被告特别是东条英机,本来就对日本的灾难难辞其咎。对东京审判的否定声浪是后来随着冷战局面的形成、日本经济的复苏,特别是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到来而逐渐升高的。
与今天否定性舆论呈现压倒之势不同,早期日本舆论对东京审判给予了高度礼赞。学界中如横田喜三郎等的极高评价为人熟知。《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所著《东京审判》(八卷,另有特辑《东条讯问录》一卷),是迄今为止对东京审判过程最为详尽的记录,并和审判同步出版。该书第一卷在前言称,“东京审判是对我们过去罪过的鞭笞”,不正视过去,“新日本国就不可能出发”。作为日本影响力最大的媒体,《朝日新闻》的这一见解也是当时日本主流看法的写照。收录有起诉书和开庭最初数日庭审记录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判记录》在宣判之前的1948年9月出版,笹森顺造(后为自民党众参两院会长)为此所写的序言这样说:
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公判记录是人类历史全面创新的伟大文献。由野蛮向着文明、虚伪向着真实、不义向着正义、偏颇向着公正、隶从向着自由、报复向着祝福、侮辱向着爱敬、斗争向着和平、分裂向着协同,可以期待它是与把人类社会导向更高的幸福的文化生活相称的一个大宪章。
笹森顺造在日本的政治谱系中不是左派,他对东京审判给予的极高评价,可以表明当时肯定东京审判的认识为社会主流。
另一方面,否定东京审判的声浪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后才逐渐高涨,但日本辩方并未因盟军总部的出版管制而自我收敛,与东京审判几乎同步,他们努力向法庭之外传布自己的主张。重光葵的辩护律师高柳贤三在东京审判宣判的当月,以英、日两种文字出版了《远东审判和国际法》,高柳强调,侵略罪(反和平罪)“在国际法上是不存在的”。
高柳的著作得以出版主要是有“学术”的外衣,但辩方主张的暗流其时已经开始涌动。有感于此,1950年4月21日,季南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其中谈到因“帕尔法官的反对意见被不当地强调,极易招致误解……导致误认诉讼全体的结论”,因此“衷心希望阁下能理解”“出版各法官的意见和包括检辩双方的开头陈述的决定”。季南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因为二战后冷战局面的形成,使日本社会对东京审判的热情迅速冷却。与此同时,否定东京审判的议论开始蔓延。帕尔的“少数意见书”早在审判结束前已为辩方所知,1952年4月28日日本解除占领的当日,田中正明即以《日本无罪论——真理的审判》之名摘要出版,当年《全译日本无罪论》也在日本出版。以后帕尔的主张几乎为所有日本否定派著作所援用。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日本重新跻身于发达国家,要求恢复日本历史的“名誉”、重现父祖辈往昔“荣光”的情绪日益抬头,对他们来说,否定东京审判的重要性也日益突显。除了重弹辩方的旧调,日本右翼开始反攻倒算,试图“清算”东京审判对日本社会造成的所谓“灾难”。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与日本政界弥漫的否定声浪相比,日本学术界主流对东京审判的评价并没有随之发生颠倒性的翻转。
日本学术界对东京审判的正面评价
东京审判的学术研究起步很早,早在审判当年的11月,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即成立了“审判研究会”。研究会编辑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研究》于1947年4月出版了第一辑。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从法的角度展开,核心是管辖权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一方面,当时检方在没有创法这点上的立场非常明确,另一方面,季南在开庭陈述中谈到国际法时的表述(日文版庭审记录用了较暧昧的汉字“嚆矢”),与“不是创造新的法律原则”的态度显示出了微妙的不同。无独有偶,日本学界的基本倾向虽是认为东京审判突破了国际法,《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研究》的发刊词却也十分巧合地用了汉字“嚆矢”。这个虽两可但正向的词语的使用开风气之先,与法庭之内辩护方强调违反罪行法定主义截然不同。在这一点上,各方的纠结,是因为无论辩护律师,还是法官检察官,更不用说法学学者,都是在法律没有追溯力为原则的近代法学教育传统中成长起来的。
因此,我觉得日本学术界最有价值的认识,即在于并未拘泥于“罪行法定”在国内法中“天经地义”的地位,而在“罪行法定”在国际法上并未形成普遍共识的同时,仍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国际犯罪尤其是最重要的战争犯罪是不能因此而免于追究罪行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研究》发刊词说:东京审判“这一尝试作为建设持久和平基础的世界新秩序的契机,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天回过头来看,日本法学家在第一时间的立场,最能体现战后痛定思痛的反思态度。当时日本法学界在“事后法”上的看法与东京审判的辩方没有太大差别,但对于审判却给予了高度评价。之所以如此,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主流法学界对日本军队犯有应受惩罚的罪行有充分的认识。
今天的日本舆论和一般观感与东京审判时对比确实已出现翻转性的变化。然而,日本学界的整体,尤其是长期深耕东京审判的严肃学者,并没有为20世纪90年代后整体右转的日本社会风气所裹挟,他们对东京审判的基本评价固然不像横田喜三郎等老辈学者那样给予那么高的评价,但在主要问题上看法的方向并未改变。比如,1996年日本学界在神奈川县召开了纪念东京审判50周年研讨会,就“分权的国际社会构造”、“形成途中的国际法”、“国联从头起就是从限制战争、禁止战争的方向开始”、日本执政者的认识“完全脱离时代潮流”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认为:一是作为“反和平罪”的前提的战争违法观,在“十五年战争”爆发时已确立;二是基于“反和平罪”的审判得到了战后国际社会压倒多数国家的明确承认或默认;三是以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包括“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的纽伦堡原则的决议,相关的法典化工作也在进行;四是作为战后的国际法的规范意识,“反和平罪”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作为规范意识已难以加以正面否定;五是批判“反和平罪”的主要论据罪行法定主义,作为国际法的原则当时并未确立。
日本学术界和我们所处环境不同,自然对东京审判观察的视角和评价也不同。我觉得他们的看法还是有相当的正面性。这不仅是因为今天日本社会已很难看到与东京审判检方和多数派法官一致的主张,而且是因为日本主流学界的主张与季南强调国际法的“黎明期”“渐进性”有异曲同工的一面(“嚆矢”的交汇是一个象征),可以从反向消解对东京审判违反“罪行法定主义”的质疑。许多日本学者在否定主张铺天盖地的逆风环境下,没有随波逐流,守住学术分际,已很不易,值得称赞。
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不容抹杀
有关东京审判对日本侵略性质的盖棺论定、对日本战犯罪有应得的惩罚、对国际法和国际刑事审判的司法实践发展的影响、对日本战后政治转型承前启后的作用,以及对审判得以在各国协调下实现等法律、政治、历史、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学术界已有充分论述。今天回顾日本东京审判争议的由来和现状,重点是想引出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检方主张,从同盟国的角度重温东京审判的初心和意义。
在东京审判开庭之际,对于辩方将提出管辖权的质疑,检方的心理准备是有的,但辩方全面出击,摆出不达推翻审判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还是出乎检方的意外。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清濑一郎等辩方律师在管辖权之争中来势汹汹的质疑,便不会出现检方大量地援引国际法、条约、协定甚至同盟国领导人讲话、国际法著作等作为审判根据的一幕,向哲濬检察官也不会在法庭上强调“我们没有制定新的法律”。
如果从发展的眼光看,检方在管辖权之争中的主张是有理的,也可以说是有力的。但管辖权之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转移了焦点。这不是说辩方号称获胜的自我加冕有其道理,而是说其使本来“不容置疑”“不言而喻”的严正性在条文辩论中多少被模糊了。对管辖权之争,检方表现为被动地“兵来将挡”,但检方早已精心准备的开庭陈述其实有着更为正大的理由。季南代表检方作的“开庭陈述”中反复强调被告的罪行使“文明面临了生死存亡”,如果不惩罚这样的罪行,“未来的战争不仅威胁文明,而且威胁一切生灵”。“免遭文明毁灭”当然具有最高的优先性,包括法的其他一切的位阶,都不能和它相提并论。在这一点上,纽伦堡审判的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在纽伦堡审判开庭陈述中,也慎重强调危害和平对于“文明世界”的巨大威胁。两大审判检察官在开庭陈述中的不约而同,不是个人的“英雄所见略同”,它代表了同盟国也可以说是爱好和平的“文明世界”的强烈而普遍的愿望和诉求。
东京审判首席检察官季南在开庭陈述中多次提到“人类”“文明”“和平”,重申审判是“拯救全世界免遭文明毁灭的斗争”。在开庭陈述之前,面对辩方对管辖权的质疑时,季南明确表示“维护和平”是东京审判的“根本的目的”。其实,在确定战后审判的讨论过程中,对遵守既有司法公正所可能面临的困难,同盟国早已有了充分认识,但最终没有采取更方便的就地处决或设立简易军事法庭的速审速决方式,反而是知难而上,采用国际法庭审判的慎重方式,这表明了同盟国(→联合国)不仅希望取信于当下而且希望垂范于后世的捍卫和平的坚定决心。最后,援引东京审判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话结束本文:“以我之见,东京审判像纽伦堡审判一样,应该被视为‘产生于这次世界大战中的最伟大事件’(借用杜鲁门总统的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