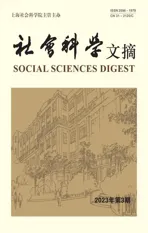风险应对力
——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视角
2023-09-23林展
文/林展
在一百多年的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大致产生了生产关系范式、现代化范式和中国中心观取向等研究范式。这些范式从不同角度增进了对清代经济的认识,也成为总结百年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核心线索。要继续推进清代经济史研究,需要继承和发扬以上范式的合理性,也需要超越其局限,形成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本文借用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这一概念,结合已有研究范式中对生产力指标的讨论,将生产力—风险应对力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清代经济史研究,以此弥补已有研究范式主要重视生产力因素的不足,并进一步说明使用这一分析框架来研究清代经济的可行性和价值。
风险应对力概念来自陈志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一书(以下简称《文明的逻辑》),在该书中,他指出已有研究对社会进步和文明变迁的评价,往往只有一把评估的尺子,即“生产率”,但这一把尺子并不够用,不足以全面认识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例如,由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自秦汉至明清均没有大的变化,如果只采用生产率这一把评价的尺子,那么就会得出结论,认为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难言有任何进步,这显然不合理。因此,他认为应该引入第二把尺子,即“风险应对力”。在该书中,他指出,由于人类社会一直受到各种天灾人祸等风险事件的威胁,因此,不管是早期从游牧采集转向定居农耕,还是后续文明化历程中迷信、各种仪式、礼节、婚姻、家庭、宗族、宗教的发明,以及市场、金融产品和国家体系的建立,都加强了人们的跨期合作,提高了人类在天灾人祸之下生存的能力,降低了暴力和冲突,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化。本文以之为借鉴,将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引入清代经济史研究之中。
之所以强调将生产力与风险应对力相结合来理解清代经济,是因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三个重要范式中,生产力都是核心线索。比如,以生产关系为主线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其重要的出发点是讨论那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性因素。而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化范式,是对生产关系范式下经济史研究过于偏重生产关系的纠正,随后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的范式。这一范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重视生产力,因此,其核心被称为“生产力转向”。中国中心观的研究取向,致力于打破现代化范式中隐含的西方中心论,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经济社会发展的线索,也推动了从实践出发的经济社会史研究。不过其所考察的核心指标,仍然是基于生产力标准的。
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的含义与衡量指标
(一)含义
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是指同时结合生产力和风险应对力两个指标来理解经济活动。生产力一般是指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其常用的衡量指标是生产率,即单位投入所对应的产出或产值。比如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单位劳动所获得的产量或产值。风险应对力,即应对风险的能力,反映经济活动的波动性,一般而言,波动性越小,风险应对的能力越强。风险应对力概念关注这一应对力的大小、来源和发挥作用的方式等。风险应对力所应对的风险,包括各种自然的、社会的风险,比如天灾、战乱等。
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是马科维兹在1952年发表的关于如何评估风险与回报的论文及其后续的相关研究。在该论文中,马科维兹主张明确认识到风险及其大小(通过方差来衡量),同时提出有效资产组合的概念,即“对既定的期望回报给出极小方差,对既定的方差给出极大期望回报”。马科维兹的均值—方差分析主要是针对金融资产定价,而陈志武的《文明的逻辑》一书则将其扩展到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研究。
(二)风险应对力的衡量指标
与生产力指标相比,风险应对力指标的构建要困难很多,以下基于风险应对力这一概念的内涵,尝试提出若干能够反映风险应对力的量化指标。
第一组指标是保险型作物和风险对冲
保险型作物是指,虽然并非主粮(比如水稻、小麦等)作物,其播种的面积可能不广,但因为其产量在较为极端的气候条件下,仍然能够有所收获,能够在关键时候帮助人们提供存活下来的最低数量的卡路里,其作用类似于现代金融产品中的保险。典型的保险型作物包括一些美洲作物,特别是红薯、玉米等。在正常年景,这些作物不需要发挥作用,一旦遇到影响生存的风险事件,则能够有效降低人们的生存风险。与此相类似,也可以提出另外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就是农户、村庄或不同地区种植的不同农作物,其产量波动的相关系数。具体而言,由于不同农作物对于气候条件的反应不同,旱灾的时候,有些农作物产量降低甚至绝收,但有些农作物还能有产量,那么这时候,农作物总产量的波动系数,即方差就会比较低。风险对冲,除了体现在农作物不同品种之间,也可以体现在不同的职业之间,比如农业和手工业、农业和商业,还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家庭成员之间,比如不同家庭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
第二组指标包括缓冲性库存与资产流动性
缓冲性库存是经济学中较为常用的概念,通常指用来平抑价格波动的商品。比如政府的石油储备,在石油价格较低时,增加储量,在石油价格太高时,将储备投入市场。与缓冲性库存相关的一个指标是流动性,即一项资产在不降低其市场价值的情况下,能够多快转换为现金。货币无疑是最具流动性的资产,而土地房屋等不动产缺乏流动性,绫罗绸缎、皮张等的流动性则居中。
第三组指标为化险性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之一。通常的人力资本可以称之为生产性人力资本,度量这些常规人力资本的指标包括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工作经验等。经济史研究中对于历史时期人力资本的考察主要是关注识字率、身高等指标。《文明的逻辑》一书指出,在一般的生产性人力资本之外,还存在“化险性人力资本”。前者有助于提高生产力,后者则有助于化解生活风险(包括消费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书中认为,大致从周初至晚清的时段,其间生产率基本没变,但由于儒家礼制的巩固等,风险应对力提升,因此消费风险下降,生活安全感改善;在此意义上,儒家礼制增强了中国社会的化险性人力资本。
第四组指标包括生存风险与生命安全
生命安全是比人均收入、人均消费更为基础的福利指标。但以往在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讨论中却很少涉及。近年来,这一指标也受到学者较多的关注。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已有学者对普通人的生命风险进行评估。
第五组指标是经济衰退率与波动率
经济衰退的频率越低、衰退的数值越小,表明一个经济体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以往长期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是增长率。Broadberry等学者则提出了衰退率指标。衰退率是经济出现负增长时增长的速度,或者说是衰退的速度。与衰退率类似,波动率也是反映经济活动风险程度的指标。波动率越高,表明不确定性的程度越高,波动率越低则反之。
以上介绍了五组用来衡量风险应对力的指标,显然不能够涵盖所有的指标,其他相关的指标还包括市场整合指数、利率等。
风险应对力与大分流问题
以下主要介绍在大分流问题下,引入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对于清代经济重新评价的可能性和可能产生的新认知。
第一,对内卷化的再认识
如何对农业生产率进行评估,是大分流讨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以往对清代农家经济生产率的评估,通常是估计亩产量、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很少估计亩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波动。这一特点反映到著名的内卷化争议之中,就是按照单位劳动日来计算劳动报酬,还是按照年来计算劳动报酬。如果从风险应对力的角度看,从年和家庭来计算生产率可能是更为合理的,因为这有助于将风险因素纳入其中。
第二,国家能力与小农家庭
国家能力研究中,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与同时期欧洲国家相比,清代中央财政收入增长较慢,人均税负低?马德斌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统治者与官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会带来委托代理问题,统治者为了避免地方官僚借机剥削百姓,只能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笔者认为还可以考虑另外一种原因,即农户经济活动本身的波动性,虽然清代的税率在国际比较中并不高,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农户一旦遇到歉收、绝收或者是因为生老病死需要大额开支,那么农户的收入流就会面临大的挑战。
第三,市场功能和大国优势
市场的发育与规模是大分流比较中的核心指标,也是斯密型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在生产力视角下,对市场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其发展规模,特别是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本身的表现,而很少分析市场对于人们应对风险的价值。最新的研究则表明,市场对更为广泛的福利指标也有重要的影响。比如陈硕和曹一鸣对大运河废除之后市场机会减少的讨论。与市场规模的讨论相类似,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特别是一些跨国比较中,强调清代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有数量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市场规模。如果引入风险应对力视角,至少还有两方面的因素需要纳入分析当中。首先,清代的大国优势也体现在其应对风险的能力上面。由于其广阔的疆域,在清代整个国土同时发生严重灾害的概率较低,通常是某个省或某几个省遭到灾害,没有遭到灾害的省或地区就可以提供协助,从而形成一个内部的保险市场。其次,由于规模太大,这带来治理上的挑战,对清代后续的转型也带来阻碍。
第四,对清代经济特征的重新评估
已有研究表明,清代经济落后的时间要早于彭慕兰和加州学派所认为的1800年左右。清代经济在大分流之前在生产力维度上已落后于欧洲,这是否就是清代经济的全部特征呢?如果引入反映风险应对力的指标,情况可能会有不同。以反映风险应对力的指标 “生命安全”为例,陈志武等学者发现,在1661—1898年之间,清代普通人的命案率大约在每年10万分之0.35至1.47之间。这大大低于同期欧洲或英格兰的水平。
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的价值
(一)促进对清代经济的全面理解
清代经济史的已有研究范式主要重视生产力指标,这可能导致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容易形成线性思维;二是容易将经济活动从社会中抽离,从而使社会经济史变为单纯的经济史,造成经济史的孤立化。与生产力指标不同,风险应对力更多讨论的是生产力指标之外的因素。比如在《文明的逻辑》一书中就讨论了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儒家文化、宗教等以往经济史很少关注的文化和非正式制度。
(二)推动经济史与生态史等学科的有效融合
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早已有相关学者对风险、不确定性等因素进行深入讨论,并指出将这些因素纳入经济史分析的重要意义。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一是灾害史和生态史的研究,比如夏明方很早即强调灾害这一类自然风险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和早期工业化的影响,以及荒政对于农业近代化、国家转型的影响,也致力于将不确定性带入历史。生态史研究对风险问题的重视和分析理路与本文所提出的风险应对力有共通之处,这为生态史与经济史的有效融合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二是历史气候变化的研究。比如方修琦等提出粮食安全分析框架,强调气候变化的均值和极值对于粮食丰歉的影响,进而影响人均粮食产量、个人粮食占有,从而可能引发饥荒、动乱、战争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风险应对力概念,但上述文献无疑是对现代化范式的重要反思。通过将风险应对力放到与生产力同等重要的位置,结合两者来对清代经济史进行研究,将有助于灾荒史、生态史、历史气候变化研究等强调风险因素的研究成果与经济史研究更为有效地结合起来。
(三)有效回应社会变迁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和局部战争的爆发,整个世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之中,如何有效应对风险、避免衰退与毁灭,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将风险应对力概念和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明确引入清代经济史研究之中,无疑是对现实社会重大变迁的回应,有助于学术共同体重视清代经济中的风险因素以及考察清代人是如何应对各种风险的。
结语
通过引入风险应对力这一新的分析视角,建立生产力—风险应对力这一分析框架,能够弥补已有研究范式过于重视生产力的不足,也是对当今社会大变革的一种有效回应。如果不考虑风险应对力这一维度,我们对清代经济的评价将是不全面的,或者说,可能遗漏清代经济的核心特征之一,也不利于从中国社会内部寻找清代经济发展的规律。当然,强调风险应对力,并非弱化生产力指标的价值,而是希望两个角度相互配合,促进对清代经济更为完整的认识。
笔者认为,生产力—风险应对力分析框架有机会带来新的范式变革:一方面,这一分析框架能够涵盖已有研究范式的主要理论,也能够指出其不足;另一方面,其借鉴了灾害史、生态史、历史气候变化、社会史和文化史等学科中的新探索,推动了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风险应对力转向”,有利于产生新的可操作的研究路径和解释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