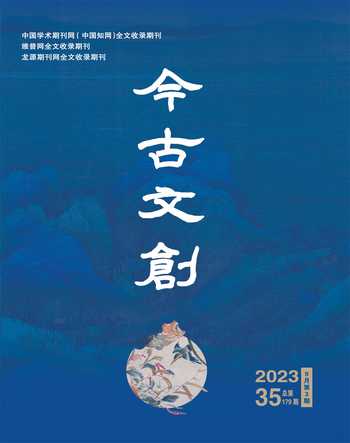动物城堡中的消解与颠覆
2023-09-19黄婉妍
【摘要】安吉拉·卡特的《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颇具空间特色,其中“城堡”是最引人注目的异托邦之一。作为“偏离异托邦”的城堡在《师先生的恋曲》《老虎新娘》中都发挥着消解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作用,都为人物的变身与生成提供了舞台,但前者以瓦解人兽之分和击碎背后的划分依据为主要目标,后者则致力于开拓远离文明规训的空间,它们都使城堡成为一个富有后现代性色彩的生成空间,为卡特的反逻各斯主义思想作下鲜明脚注。
【关键词】安吉拉·卡特;《师先生的恋曲》;《老虎新娘》;动物;异托邦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5-002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5.009
基金项目:2022年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一般项目)“异托邦视域下《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的空间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2SKY306)。
在童话的逻辑里,动物拟人化是常见的写作策略,虽然动物拟人化的策略能培养读者建立人与动物平等的理念,但需要注意的是,动物只有通过拟人化的手段才能发出声音进而被重视与理解,如果没有此种策略,两者依然无法和谐平等对话,由此可见,即使在拟人化策略的帮助下两者沟通有所进展,但人与动物之间的壁垒依然隐形地矗立着,在解构人类主流地位的同时仿佛又重新建立起人类中心主义的秩序。
福柯是最先吹响了关注空间的号角的发起人之一,其所提出的“异托邦”迥异于乌托邦的“牢固性、统一性和同质化”[1]13,它是“异质的、发散的,而不是同质的统一结合”[1]15,这种强调打破固定化和统一性的趋势呼应了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与解构特征,也是安吉拉·卡特所一直努力呈现的。若要进一步考察卡特作品的后现代主义色彩,除了聚焦于人物形象之上,空间也是不容忽视的考察因素之一。《师先生的恋曲》及《老虎新娘》均是卡特对《美女与野兽》的改写,在这两则改写中,两位高度人格化的野兽仍然无法与人类居住在同片区域内,而是选择离群索居,卡特的这一空间设置使得人与动物的间隔更为显著。城堡既像是动物为与人类保持距离而所打造的隔绝空间,同时也是动物主动驱逐人类及人类文明的偏离异托邦,卡特没有刻意构建起人与动物边界消解后的两者共处一隅的美丽新世界,而是让人类与动物的界限仿佛消解但却更为坚固。但在作为偏离异托邦的城堡里,人兽的界限消解及身份转换、人类中心主义的消散都有了可供实现的场域:在《师先生的恋曲》中,卡特打破了建立人兽之分的脆弱依据并借此消解了两者的界限;在《老虎新娘》中,卡特打则造出一片可供人类化身为动物,远离文明规训的天地。
一、《师先生的恋曲》:人兽差异的消解
在《师先生的恋曲》中,城堡位于主流空间(即人类村落)的边缘外,狮子居住在一间金碧辉煌的帕拉迪欧式建筑中,这建筑“仿佛躲在一棵古老丝柏的积雪厚裙后”[2]60,这处拟人的运用提示此地极为隐蔽,丝柏像是一道禁止他人靠近的屏障。卡特花了许多笔墨强调城堡的隔绝、孤独与特殊,如:“仿佛关上的门将里面一切都囚禁在冬季园墙内,与外在世界断绝。”[2]60城堡不沾半点人的气息,狮子并没有聘请用人、女仆,只有一只可爱的小猎犬忙前忙后招呼客人,这是因为“眼前总有人来往会太过苦涩地让他记得自己有多不同”[2]65。即使狮子的住所、衣着打扮、行为举止高度人化,也改变不了他爱吃冰冷食物的习惯及他是动物的这一现实。自柏拉图以来,人与动物之间便天然地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界限,这是“为了从虚构的差异中捕获‘人之本质的概念,从人为的划分中确立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3]58,这条“准则”在童话世界里也依然奏效,由始至终,无一例外都是动物在向人类世界靠近,就算努力如狮子,也依然很难彻底摆脱身上所残留先天的动物特征。
作为偏离异托邦的城堡为异常的个体搭建起了一片天地,这里容纳着不符合一般标准的特异存在。权力与知识合谋打造出了偏离异托邦,它们明确规定了主流与非主流、正常与不正常的界限,狮子作为非人非兽的存在,他无法被主流的人类世界所接纳,保持敬而远之的距离是他忘记自己有多么不同的做法,他将城堡打造成一处安身立命之所,然而城堡却只离人类村庄只有半公里的距离,这一微妙的地理距离既表现出狮子一方面渴望靠近,另一方面又时刻铭记差异存在的复杂心理。
狮子亲手打造的偏离异托邦时刻突显人兽之分的存在,但那些区别是否真实存在呢?卡特曾表示:“人和动物之间的任意划分掩盖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人其实也是一种动物,只是一种拥有特别复杂社会制度的动物。”[4]225卡特并没有刻意描写人兽之别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因为除了明显的外表之分,人类与狮子没有任何区别:“狮头,狮鬃,狮子的巨掌,他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以后腿人立,但身上却又穿着暗红缎子家居外套,拥有那栋可爱的房子和环绕此屋的低矮山峦。”[2]64一个“像”字便使人兽之分的唯一依据摇摇欲坠,这句比喻撕裂出一个混沌的身份空间,狮子像一头狮子本就是一句不符合逻辑与事实的比喻,若要使比喻成立,那比喻主体应该是人类而不是野兽,然而巧妙的是卡特在后面引入转折,一个“但”字却在提醒读者这个主体应是野兽。这句比喻使狮子陷入人兽难分的处境之间,虽然混沌不明,却给人兽提供了可以互相转化的契机。卡特不仅擅长消解秩序、瓦解规则,更擅长解構、溶解秩序背后的依据以此证明秩序规则的虚假与脆弱。卡特借助这一精妙的比喻打破人兽之别,利用喻体、本体之间的含混与矛盾表明人兽之别不是自然之别而是人为建构的分类与等级—— “如同种族、阶级、性别等概念,动物本性的概念亦是一种人类建构的产物。”[5]53
卡特设置这一保持微妙距离的偏离异托邦的目的不是强调人类与动物的区别与差异,而是借此空间说明人兽无异的可能性,此种可能性借助美女的行动得以具体展现。美女听完父亲地对狮子的描述后不禁恐惧,她前期对狮子的认知带有鲜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印记,她觉得狮子很奇怪,“那令人困惑的不同模样几乎令她无法忍受,那存在使她呼吸困难。”[2]65即使狮子并没有对美女做出任何出格的行为,美女依然会出于对动物的恐惧而备感不安,她的恐惧具有双重性:“恐惧既来源于人类文明对于野兽错误的神话建构,亦来源于人类物种对于陌生物种的好奇。”[5]56
自古希腊起,传统的动物认识便囿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影响,人类占据于优等之位审视位动物,习惯性从否定和差异的角度定义何为动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则以语言、理性等为标尺划分出人兽的区分界限,而笛卡尔则完全否定掉了动物的所有能动性,他所提出“动物机器”概念将动物彻底物化与他者化,使人类为主、动物为客的两分思维更为严重。人兽之分本就源自二元对立思维下的机械划分,动物总是与负面恶劣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它们被人类以否定性的语言定义着,“从来不是通过一种清晰的实质性界定与动物形成对立”[6]16,以至于人类面对动物的时候往往只看到了由否定和差异组成的界限,而“人与动物之间不应只是看到界限,而更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相互存在的关系。”[7]84美女在与狮子的相处过程中,美女虽然逐渐放下了对动物的恐惧,意识到狮子的可爱,但她无法忽视横亘在两者之间的人兽之别。当得知狮子奄奄一息时美女选择立即动身,待她再次抵达城堡后,她才发现狮子的眼睛也有眼皮,就像人的眼睛一样,而她从来都没有发现这一点,“是因为她只顾着在那双眼睛里看自己的倒影”[2]72。直至此处美女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才得以消解,美女从狮子身上找到了人与动物本应被发现的联系,而不再执着于两者的差异,她跳出了传统固化的人兽划分沼泽,提供了人与动物和谐平等相处的可能性。美女主动提出留下来的请求,这一举动表示美女不再畏懼人兽之分,而是心甘情愿地投入爱河之中,她用眼泪洗去了狮子的毛发,用爱消解了人兽之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城堡这个充满可能的异托邦空间里,人与动物都有了逃逸逻各斯的可能。
二、《老虎新娘》:逃离规训的颠覆
虽然在《老虎新娘》中野兽依然被当作“异类”对待,但故事却开始颠覆了人类与动物的主客体地位,人类面对动物时更多的是恐惧与害怕,人类的权威在动物的威严下逐渐瓦解,同时也破除了像《青蛙王子》《美女与野兽》中的动物变形逻辑——使犯错之人变成动物是一种惩戒——其仍在承认人类高于动物的人类中心主义。因此,在故事中卡特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将这种被动之举扭转成了主动选择,如《老虎新娘》中的少女自愿选择变身动物。
待被父亲输掉的少女来到城堡后,老虎三番五次要求用物质来换取观看少女赤身裸体的机会,少女明确表示拒绝,她不明白老虎为何如此执着于“一位小姐从未被男人看过的肌肤”[2]92,恨不得自己和别的小伙子打过滚以此撕裂所谓的贞洁标签。随后,小厮邀请少女前去和老虎骑马,当他们骑到河边时,小厮提出了老虎的最后一个要求——“如果你不愿让他看见你脱光衣服——那么,你就必须准备看见我主人赤裸的模样。”[2]96少女看出了老虎害怕被拒绝的忧虑,便点头答应。当老虎脱下衣服以最原本面目出现在少女眼前时,少女感到自己胸口撕裂,好像出现了一道伤口,她向老虎表示不会伤害他之后也解开了外套。
少女脱下衣服后羞涩与忧惧交杂:“而我的动作笨拙,脸有些红,因为没有任何男人曾见过我赤身裸体,而我是个骄傲的女孩……此外我也有些忧惧,怕他面前这个纤弱的小小人类样品本身或许不够堂皇,不足以满足他对我们的期望。”[2]97在此处少女用的是“我们”这一字眼,如果结合少女的心理活动,可以将“我们”理解为全体人类。少女事后想起那日与狮子的互相凝视:“相较于我原先准备给的东西,野兽要的只是一件小事,但人类赤身裸体是不自然的,从我们以无花果遮掩私处开始便是如此。他的要求令人厌恶。”[2]99此处就更为直接地揭露少女的矛盾,既然一开始可以接受和老虎发生关系的话,并认为老虎想要的“只是一件小事”的话,那为什么对赤身裸体抱有如此如此剧烈的抗拒之情?再者,为何人类赤身裸体就是不自然的行为?自亚当、夏娃吃下智慧果开始拥有羞耻意识之时,便是人类与动物建立划分界限的开端,在文化和历史的层层加码之下,原始自然的赤身裸体行为已被贴上“不文明”和“不自然”的标签,颇具否定色彩的裸体便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与动物的划分标准之一。德里达曾在《我所是的动物》做出如下思考:“没有动物会想着为自己穿衣。衣服对人来说是专有的,乃是人的一种‘专有特性(propres)。穿衣本身是与人所专有的所有其他形象不可分的。”[8]115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的影响下,拥有羞耻意识的人类习惯于用服饰遮蔽身体,而被认为没有羞耻意识的动物则经常赤裸登场;顺此逻辑,人类总是位于观看者的一方,而动物是人类凝视的对象。老虎所提出的要求颠覆了少女思维固化中的人兽地位之分,主客体的互换对少女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侮辱。
与狮子的城堡有意无意地与人类村庄保持半公里不同,老虎的宫殿可以说是远离人烟。如果说从少女抵达宫殿到与老虎互看裸体之前,宫殿只是起到了地理意义上的隔绝的作用(即划分人与动物的居住区域),仍发挥着偏离异托邦中的分离功能,那么在完成彼此的凝视之后,宫殿则变成了一个逃离主流规训,释放异质力量的场所。在人类中心主义为规律运转的世界里,人被确定为至高无上的主体,一切行动都要确保人类利益,还需“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知世界”[9],人类的一切及其所制定、创造的全部都被奉为圭臬。
在对望之前,老虎也如狮子一样,在外表上努力地向人类形象靠拢,然而却显得极为怪异和不自然:“那张脸确实很美,但五官太端正对称,少了些人味;那面具的左半与右半仿佛镜子对映般一模一样,太过完美,显得诡异。”[2]80而在互相注视之后,老虎彻底抛弃了人类的装束,尽情肆意地裸露着动物的身躯,房间弥漫着毛皮和尿液的味道也丝毫不在意,和初登场时的形象形成巨大反差。如果说老虎前期的行为都是为了获得“人类”这一特定的社会成员身份,是他认可、靠近人类文明的肯定表达,那么与少女凝视之后的回归本性则是一种对理性、教育及文明的戏谑与不屑。而少女也在双向凝视后有了新的体验,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自由”[2]97,在镜子她看到了父亲欲望满足后的笑容和收拾好的行李,她意识到了人类世界的虚伪与假意,她毫不迟疑地选择化身动物,这是她与人类文明的诀别:“他每舔一下便扯去一片皮肤,舔了又舔,人世生活的所有皮肤随之而去,剩下一层新生柔润的光亮兽毛。”[2]101少女以赤裸的身躯解构衣不蔽体的文明羞耻,以动物的形象解放自我欲望,以生成的身份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少女让变身为动物不再是一种惩罚,而成为一种逃离虚伪、追求真实的自由选择。少女与老虎都在凝视的往返中以逃逸的姿态破除掉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枷锁,城堡为两者开辟了一处可供远离文明约束的异质空间。
三、结语
《师先生的恋曲》《老虎新娘》中的城堡虽都发挥着偏离异托邦的功能,都在消解着人类中心主義,但却发挥着不一样的作用:在《师先生的恋曲》中,狮子的城堡小心翼翼地与人类村庄保持互不侵犯的礼貌距离,将人兽界限化为了具体实在,在肯定的角度上承认了“异”的存在,美女真心的接纳消解了人兽的固有之别,让城堡变成了真实存在的乌托邦。而《老虎新娘》则用反向逻辑书写了另一种可能,老虎的宫殿则像是一片肆无忌惮的天地,它居于远离人烟的郊区,在否定的角度上呼应了“异”的偏离,少女在与老虎的周旋中脱掉了人类文明的大衣,选择变成动物,老虎的宫殿为其提供了远离文明规训的奇迹之地。
城堡是卡特魔法世界中最为独特的异托邦之一,卡特借助这片空间呈现人与动物身份流动、生成的可能性,借助动物与女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及双向互动探讨了人类中心主义何以破解的可能。城堡的书写为卡特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提供了有迹可循的线索。
参考文献:
[1]邹敏敏.“异托邦”理论的建构——福柯的空间美学思想研究[D].深圳大学,2017.
[2]安吉拉·卡特.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M].严韵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汪民安等.文化研究关键词(修订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4]Cater A.Shaking a Leg:Collected Journalism and Writings[M].New York:Random House,2013.
[5]SEIRA Y.向弱势的写作——安吉拉·卡特的“动物—文明”叙事[D].华东师范大学,2021.
[6]王馨曼,王凤才.终止“人类学机制”的生命本体论——阿甘本对人与动物关系的形而上学——政治哲学解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1(06).
[7]雅克·德里达,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明天会怎样:雅克·德里达与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对话录[M].苏旭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8]雅克·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M].夏可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9]曾繁仁.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与生态美学的兴起[J].文学评论,2012,(02):107-112.
作者简介:
黄婉妍,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西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