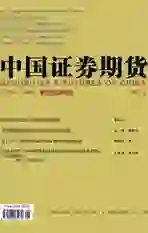多层次传递型内幕交易责任认定的实证考察与理论反思
2023-09-19陈岱松徐嘉豪
陈岱松 徐嘉豪
摘 要:信息传递与互联网技术的耦合带来传递型内幕交易中传播链条的延长,造成现行推定规则在追究各信息受领主体责任时的局限性,也导致了法律责任在交易端与泄露端间的严重不匹配。应当认识到,泄密人与受密人责任是成立内幕交易责任的两个方面,现行推定规则实则是在泄密人责任成立的基础上对受密人责任的推定。将泄密人违法性具体化为从泄密中获益,受密人交易行为的违法性具体化为对受密人违法的认知,方能揭示内幕交易以获益为核心的违法性本质。身份关系所蕴含的人际利益是信息传递的原动力,在坚持一次推定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信息传递过程中各主体间的身份关系,以信息获取便利性与利益一致性为实质审查标准,可以将形式上处于不同传播层级的主体实质认定为同一层级知情人,从而在确保推定事实效力的基础上对内幕交易责任主体实现精准覆盖。
关键词:多级传递;推定规则;身份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媒介给信息传播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进入网络空间后,人们获取、传递信息的方式由原来的点对点转变为面到面的爆炸式增长。作为证券市场公平交易的基础,证券信息的传播也呈现上述特点。无论是上市公司正式披露的年报,还是来源不明的各种小道消息,通过报纸、电视、人与人的口口相传甚至是网络短视频,都极易在大范围内形成影响,这就给内幕交易执法带来了新的挑战。据统计,2022年全年做出的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件共涉及99名当事人,其中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直接从事内幕交易的共处罚29人次,占比为3053%;基于联络接触从事内幕交易的共处罚60人次,占比为6316%。①基于联络接触的泄密型内幕交易已经成为内幕交易违法的主要形态。在执法广泛采用推定方式认定泄密型内幕交易责任的情况下,面对内幕信息多链条传递趋势,如何认定各传播链上内幕交易主体的责任日益成为执法的难点。
二、推定规则的局限导致内幕交易责任认定的窘境
在缺乏直接定案证据的情况下,推定作为一种以间接证据定案的方式有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现行内幕交易执法基本以“一次推定”案件为主,而当内幕信息发生多层次传递,势必面临“多次推定”能否成立的问题,需要从推定方式本身寻求理论与现实依据。
(一)以推定认定内幕交易责任的法理基础
传递型内幕交易案件具有隐蔽性强、传播能力广的特点。从证据距离来看,是否知悉内幕信息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有关证据完全处于交易行为人控制之下,导致在举证能力上监管机关往往缺乏直接证据证明相关人员知悉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此时若执意恪守“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监管机关证明客观上难以证明的事项,则有违实质平等原则。为了避免内幕交易因缺乏直接证据而无法定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内幕交易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证券行政处罚案件证据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座谈会纪要》)共同确立了内幕交易推定规则:一是基于特殊身份的推定,《证券法》第74条规定的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有密切关系的人,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基本吻合;二是基于联络接触的推定,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与内幕信息知情人或知晓该内幕信息的人联络、接触,其证券交易活动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内幕交易司法解释》在认定“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时亦采用相同的推定逻辑。具体来说,监管机关应当证明的基础事实需满足以下两点:一是相关主体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密切关系或联络接触;二是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基本/高度吻合。在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的吻合度上,具有密切身份关系的人之间传递内幕信息的可能性较单纯的联络接触人之间而言更大,故而区分基本吻合与高度吻合的证明标准。基于推定事实的可推翻性质,《内幕交易司法解释》第4条又赋予当事人以交易具有正当理由和正当信息来源推翻前述推定的依据。
适用推定规则是综合内幕交易案件中的证据距离、各方举证能力后对执法公正与效率的妥协,推定规则适用的前提、基础事实、推翻推定事实的救济途径在现行规则之下均已具备。虽然现行内幕交易推定的规则存在法律位阶较低的问题,但已然形成完备的逻辑,且无法理上的障碍。
(二)“二次推定”规则的适用局限性
适用推定规则在现行内幕交易执法中多以内幕信息一次传递为限。本文统计了2020—2022年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做出的297件内幕交易行政处罚决定,其中传递型内幕交易案件207件,内幕信息仅发生一层传递的为169件,占传递型案件的816%。而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传递的便利度极高,内幕信息完全可以链条式地发生多层次传递,除了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处直接获得内幕信息的受密人外,还会形成第二、第三等多个受密人。这些受密人完全可以利用现行推定规则以一次推定为原则的局限,达成由第二、第三受密人进行交易并一同分享内幕交易获利的共谋协议,以此来规避现行证券执法的覆盖范围。近三年内幕交易行政处罚中存在信息多层传递的案件仅有38件,占传递型案件的184%,这也间接表明了证监部门在处理此类案件上的力不从心。在缺乏泄密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推定规则将产生明显的局限性。推定所依据的基础事实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若以推定事实再行推定另一个事实,则缺乏推定规则适用的前提条件,所形成的二次推定事实在真实性上也已大打折扣。若一次推定事實真实性可达80%,二次推定则已降低至64%,更勿论信息传递链条更长的内幕交易案件了。
现有内幕交易行政处罚案件中,采用二次推定的案例数量极少,且多未作详细论证。在“韩锋内幕交易案”中,马某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赵某有通信联络。韩锋与马某关系密切,操纵其配偶林某账户买入浙大网新股票获利。参见浙江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19〕1号。浙江证监局认定韩锋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且无合理解释,认定韩锋构成内幕交易。本案中马某系第一受密人,韩锋为从马某处获得内幕信息的第二受密人,当马某知悉内幕信息已系推定事实,以此为基础再行推定韩锋知悉内幕信息,已属二次推定。如果说韩锋案的认定实属牵强,那么在“王智元内幕交易案”中,适用二次推定尚有合理之处。本案中俞某是内幕信息知情人俞某强之子,两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共同生活。王智元与俞某是同学关系,王智元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买入“佐力药业”的行为与内幕信息高度吻合,买入时点也与王智元与俞某的通话时点非常接近,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18号。证监会认定王智元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形式上本案依然存在推定俞某知悉内幕信息,并以此为基础二次推定王智元内幕交易成立的逻辑,但鉴于俞某与俞某强的密切关系,俞某具备知悉内幕信息的高度便利性,故在此基础上作二次推定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二次推定散见于证监部门的执法实践中,未有一般化的标准可供借鉴,处罚决定书也基本不对为何采用二次推定作专门论证。
(三)过度依赖推定规则导致内幕交易泄密端与交易端责任失衡
推定规则除了在内幕信息二次以上传递的主体中适用困难外,还造成了对泄密人的追责困境。《证券法》第53条明确将“泄露内幕信息”作为内幕交易违法形态之一,理论上传递型内幕交易中必然存在泄密人与受密人两类主体,证监会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也常通过“认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受密人与知情人存在联络接触——受密人交易行为异常”的逻辑来推定受密人责任的成立。在《座谈会纪要》中,行为人与知情人的密切关系或联络接触是内幕交易成立的基础事实之一,而这样的规定实则已经暗含了“知情人泄露内幕信息”这个前提。但同时推定成立内幕交易又不以认定知情人泄露内幕信息为前提,导致选择性执法现象突出。近三年做出的207件传递型内幕交易处罚案件中,处罚泄密人的仅有34件,占164%,意味着作为内幕交易“信息源”的广大泄密群体未受到法律的制裁。
知情人泄露内幕信息同样面临取證困难,在现行推定规则之下,当受密人内幕交易已然成为推定事实,则无法在此基础上推定泄密人责任成立,否则会陷入二次推定的泥潭。故而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对泄密人的追责十分困难,不利于打击内幕交易的源头,也造成了法律责任在交易端与泄露端间的严重不匹配。
因此,有必要从理论角度阐述内幕交易何以禁止,以及泄露型内幕交易中,泄密人与受密人的违法源于何处,以此为日后的执法提供理论指导。
三、传递型内幕交易中各方责任成立的前提
从逻辑必然性与责任配置公平性出发,传递型内幕交易案件一定存在泄露人泄露内幕信息和受密人利用信息进行交易这两个环节,确立泄密人责任与受密人责任的成立标准,方能实现对传递型内幕交易的全面评价和公正执法。在内幕交易规制理论上,存在美国信义关系理论与欧盟市场平等论之争,前者强调信义关系对内幕交易主体限制的作用,并以传统信义义务理论为基础,及作为拓展的信息传递理论和盗用理论将内幕交易主体从公司内部人等传统信义关系人间,扩展至从信义义务人处受领信息之人和对信息源负有信义义务之人;后者则认为任何人不当使用任何对证券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均会对证券市场诚信及投资者信心造成损害,强调以拥有内幕信息作为认定行为人构成内幕交易主体的唯一要素,而不论其与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特定关系或通过某种途径获取内幕信息。无论采用何种理论,对内幕交易的有效规制须回归到执法实践,知悉内幕信息作为成立内幕交易的要件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尤其是当信息的传递方式趋于隐蔽化,确保执法的可操作性是完善内幕交易规制理论的基础。
(一)身份关系—推定规则区分于认定模式的核心要素
根据《座谈会纪要》,成立内幕交易有认定模式和推定模式,前者是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直接交易;后者则为与内幕信息知情人联络接触或关系密切之人,交易活动异常且无合理解释的,推定成立内幕交易。如果仅从文义解释来看,在认定模式下只要具备特定身份关系的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交易内幕信息标的公司股票的,即构成内幕交易;而推定模式下除了特定身份关系或联络接触情形外仍需具备交易行为异常要件。但从证监会的执法实践来看,交易行为异常并非只是推定模式下的考量要素。部分地方证监局在认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直接交易案件时,也将交易行为异常作为认定依据。例如,在“朱荣明内幕交易案”中,内幕信息知情人毛某雯的母亲袁菊芳在知悉内幕信息后又将其泄露给同事朱荣明。根据《座谈会纪要》,朱荣明作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只要存在交易活动即可成立内幕交易,但浙江证监局依然指出朱荣明交易时间与内幕信息发展高度吻合、交易方式与交易习惯不同的异常交易现象,以此认定成立内幕交易。究其原因,一是交易行为异常乃证监部门发现所有内幕交易行为的起点。自上市公司公布重大事件起,证监部门的大数据系统会自动筛查过往一定时期内的异常交易行为,锁定异常交易下单人、开户人、资金来源与去处。与此同时确定内幕信息敏感期、知情人,并对比下单人、开户人、资金方是否为法定知情人及其近亲属,或是否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联络接触,一旦符合条件则存在内幕交易嫌疑。参见浙江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12号。二是即使具备法定知情人身份也未必知悉内幕信息。《证券法》第51条规定的八类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获取信息便利度上有明显不同,与发行人董监高、控股股东、实控人等对公司业务具有控制力或影响力的主体相比,其他因特定职务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获取内幕信息的概率大大降低,此时交易行为异常因素可以提高内幕交易认定结果的证明效力。如此看来,推定模式与认定模式的区分要素在于信息发生了传递,推定模式下的交易者乃与知情人有联络接触或存在密切关系的“二手方”。
本文从2020—2022年做出207件传递型的内幕交易案件中统计出232对“知情—受密人”关系。其中,知情人与受密人为好友、同学、老乡等熟人关系和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关系的各有69对,占比均为297%。知情人与受密人为同一单位同事和存在商业合作、业务联系关系的各有39对,占比均为168%。知情人与受密人仅仅存在单纯的联络接触情形,而无特殊身份关系的只有16对,占比为69%。内幕交易熟人作案的特点十分突出。即使《座谈会纪要》区分了密切关系人和联络接触人,但特殊的身份关系与内幕交易活动间具有事实上的惯常性,能否对此类身份主体进行类型化规制?此等身份关系与内幕交易责任各方成立的理论间是否具备一致性?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受密人责任源于泄密人责任的成立
与合法证券交易不同,内幕交易行为人利用了内幕信息所蕴含的重要经济价值,故仅仅受领内幕信息不必然产生禁止交易义务,知悉自身据以交易的信息为内幕信息则是受密人责任成立的前提。成立受密人责任的本质在于探讨知情人禁止交易的义务何以随着信息的传递而传递至受密人。在美国Dirks案中,泄密人向监管机关举报公司舞弊未果后,又将该信息泄露给了分析师Dirks,Dirks建议其客户卖出公司股票。因泄密人向他人告知公司舞弊行为并不违法,Dirks建议他人买卖股票不构成内幕交易。该案将内幕交易主体扩张至从传统信义关系人处受领内幕信息的外部人,揭示了受密人行为的违法性来源。该案确立的信息传递理论认为受密人承担“披露否则戒绝交易”义务的前提在于以下两点:①泄密人泄露信息违背了对股东的受信义务;②受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泄密人违反义务的行为发生。具体来说,当泄密人违反保密义务泄露内幕信息,而受密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信息来源的违法性时,便可认定其知悉内幕信息并承担戒绝交易的义务。知悉作为一种主观状态很难通过客观证据直接证明,美国信息传递理论将证明受密人知悉内幕信息转化为证明受密人对泄密人违法行为的明知,使监管机关的证明对象由受密人的主观心理转向泄密人违法的客观事实。此时受密人的受领信息渠道、与泄密人间的身份关系等均可作为不法性判断的重要因素。泄密人违法则是受密人责任成立的前提,否则除非受密人属于《证券法》第51条规定的法定知情人,法律不应令他对合法渠道获得的信息承担禁止交易义务。除了知道或应当知道泄密人行为违法会引发对受密人的保密期待外,信息受领人的保密承诺亦会引发禁止交易的义务。
若无论传递链条长短和如何获取信息,单纯以从内幕信息知情人处获悉信息即认定为受密人,则该标准下受密人范围过于宽泛。信息传递理论通过对受密人主观状态的限制,实际上限缩了受密人责任的范围,重点打击通过合谋实行内幕交易的行为,避免了偶然性信息受领者承担内幕交易责任的风险。内幕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失真的可能性逐渐加剧,传播链条越后端的主体所享有的信息优势越小,其承担的市场风险也就越大。例如,受密人仅从公交车、菜市场等途径无意获得信息,即使该信息事实上符合内幕信息未公开性与重大性要件,从受密人角度,一是其并无对道听途说信息作严格审查的义务,二是受密人根据偶然性获得、来源不明的信息交易实则是一种自担风险的市场投机行为。证券法允许、正视和保护合法投机行为,因其能敏锐地发现值得投资的企业,促进证券市场真实价格形成。同时,该理论也能降低经常从事接收、分析各类市场信息的市场分析师、基金经理、财经记者等的法律风险。这些主体通过收集、辨别、加工、再推薦客户买入卖出证券,有助于促进市场真实价格的形成,增强市场的有效性。若无对主观状态的限制,前述专业主体就必须对所处理信息是否为重大未公开信息进行详细审核,在增加工作成本的同时,也可能因无法实现有效审核而承担法律责任。
(三)泄密人责任成立的前提:从泄密行为中获益
传递型内幕交易中的违法性源头在于泄密人的违法性。Dirks案指出:违反保密义务泄露内幕信息并不一定违法,泄密人是否违反信义义务的关键不在于泄露行为本身,而取决于透露的目的,具体来说就是判断泄密人是否直接或间接地从泄露内幕信息中获益。Dirks vSEC,463 US 646,662(1983)内幕交易违法性于形式上体现为利用内幕信息交易,而既为交易行为,其实质目的则是从交易中获得不法收益。无获益目的的驱使,行为人即缺乏内幕交易的动机。虽然不排除存在无获利目的的单纯泄密行为,但此种事项不具有普遍性,法律对此类“非理性”的边缘人群并无单独创设内幕交易制度来规范的必要性,故而不以获益为目的的泄密不在内幕交易规制范围之内。
在认定泄密人的获益要件时,除了物质利益较容易辨别外,各种形式的精神利益是否应当包含在内?个人利益的范围应如何认定?在Obus案中,法院认定内幕信息泄露人与受密人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情感、经济联系,可作为认定泄密人违反受信义务的基础,Obus,693 F3d at 287从而实现了以特定人际关系来判断是否违反受信义务的较为简易的证明模式。相对于追究交易端责任,在我国为数不多的追究泄露人责任的案件中,监管机关也有通过人际关系来认定泄密人责任的模式。例如,在“肖家守内幕交易案”中,证监会认定肖家守无泄密的主观故意,但其作为重组收购的核心负责人,应当对重大重组信息在法律上负有高度谨慎的保密义务。但肖家守在重组过程中不够谨慎以致泄露相关内幕信息给配偶朱莉丽,属于重大过失,应予处罚。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2〕24号。本案中肖家守泄露内幕信息的对象为其配偶朱莉丽,属于共同生活且关系密切之人。又如,在“冯振民、吴春永内幕交易案”中,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经理吴春永在电话中向宏达股份总会计师包维春打听宏达股份股票是否能买,包维春说买了风险不大。证监会认定包维春对吴春永打听、刺探、印证内幕信息未保持足够谨慎,属于过失泄露内幕信息行为。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3〕14号。包维春虽未明确泄露内幕信息,但吴春永作为投资经理,对内部人包维春的回复会高度敏感,且二人在业务上可能发生经济往来。在这两个案件中,在认定泄露人的主观过失时,泄露人与内幕交易行为人间均有固定的情感或经济联系,监管机关虽然没在处罚理由中明确提出此类关系对认定泄露人责任的作用,但也在无形中与美国Obus案所确立的规则相一致。在无直接证据证明泄露人从信息泄露中获益的情况下,以特定的人际关系来认定泄露人的获益要件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尤其在中国注重人际利益的社会环境下,通过维持特定的情感联系可能转化为未来的、长期的经济利益。执法实践中传递型内幕交易也往往发生在具有特殊身份关系的人员之间,近三年的传递型内幕交易案件中,传递人间为好友关系、配偶子女等近亲属关系、单位同事、业务合作关系的占全部信息传递人的931%,证监部门仅对69%的传递人未认定明确的身份关系。将身份关系作为责任认定要素既可倒逼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应有的谨慎,从源头上防止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也可将对信息传递过程的取证转化为对身份关系的证明,可有效缓解现行执法中仅有通话记录而无从确定通话内容,导致无法确认泄密事实发生的窘境。
以泄密人获益作为违法性来源,并将身份关系作为证明获益的核心要素,不仅揭示了内幕交易以不当获益为目的的违法性本质,而且能与证明受密人违法相辅相成。资本市场上难有“无缘无故的爱”,内幕交易活动中的利益交换必然以存在某些合意为基础,代表着一方对另一方行为某种程度上的知悉。一旦泄密人与受密人间存在物质利益输送或某种特定的人际关系,则往往意味着受密人对泄密人违法性知悉的高度可能性。若这种利益交换并不明显,则需由执法机关寻找足以证明受密人知悉状态的证据。
四、多层次传递型内幕交易认定的修正路径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具有更快、更广泛且更离散的特征,即使内幕信息知情人也无法完全控制内幕信息传递的速度及范围。但是内幕信息的多层次传递并不应当降低对受密人认知要件和泄密人获益要件的证明要求,而是可以通过身份关系使证明事项客观化。确立这一原则的目的在于精确把握内幕交易的违法性本质,避免打击范围的盲目扩大。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将满足违法性要件的交易主体纳入追责范围,避免行为人通过多层次传递来规避内幕交易法律,同时又能平衡泄密端与交易端的责任,是未来执法的重点。
(一)通过身份关系缩短传播链条
“二次推定”缺乏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证据链条明显单薄,在证明力上具有更大的或然性,若贸然采用极易对无辜群体的合法权益造成侵犯。在近三年的传递型内幕交易处罚案件中,存在内幕信息多级传递情节的案件有38个,其中仅有18个案件适用了二次推定。在上述案件中,证监部门均未掌握直接证据证明内幕信息发生了二次传递,仅以传递人间具备特殊身份关系即认定构成共同内幕交易。例如,“秦嗣新、秦奋内幕交易案”中,秦嗣新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与知情人徐某有公开交流,同期将大额资金转入儿子秦奋账户并大量买入“鑫茂科技”。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25号。证监会实际上默认了秦奋与秦嗣新间存在内幕信息传递的事实。又如,“朱广瑜、张蓓蓓内幕交易案”中,朱广瑜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与知情人李某勇、李某1、李某2有通话,同期朱广瑜配偶张蓓蓓交易鲁商置业股票。参见山东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6号。山东证监局亦未对朱广瑜与张蓓蓓间的信息传递事实进行论证,而是径直认定内幕交易成立。据统计,在这18个案件中共涉及19对“知情—受密人”,其中为父母子女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的各有3对,配偶关系的有11对,1对为共同居住、工作的疑似情人关系,1对为近亲属兼公司财务合作关系。可见在执法实践中,信息传递人间的近亲属关系、共同居住事实、资金往来因素是成立二次推定的关键所在。
将推定限制在一次以内是为了防止在推定事实的基础上再行推定,导致削弱二次推定事实的证明力。具体到内幕交易执法中,由于不同受密人处于不同传播层级之上的事实,导致传播方式、内容、时间等因素均带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这会严重削弱信息传递事实的证明效力。但是如果能确保推定事实的证明效力,采用多次推定亦未尝不可。将推定规则限制在一次推定并不意味着只追究信息单次传递下的内幕交易双方责任,而是可以突破形式上的传递层级限制,从实质上去探究传播链上各主体的关系。身份关系背后所蕴含的人际利益,是传递型内幕交易各方行为的原始动力。当形式上不同层级的受密人间因具备某种特殊的身份关系,导致内幕信息在这些主体间的传递具有高度因果联系时,应当将这些主体视为同一层级受密人,也就能实现在维持一次推定的基础上将传播链条后位的其他主体囊括进来。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内幕信息虽然形式上发生了传递,但当这种传递发生在《证券法》第51条列举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内,因这类群体本身就具备获取内幕信息的便利条件,可以从实质上认定为同一层级的知情人,直接依据《证券法》第50条做出处罚。
第二,当内幕信息传递超出法定知情人范围时,应当关注身份关系对缩短信息传递链条的作用。受密人与知情人存在长期共同生活、密切资金往来、近亲属关系往往意味着具备获取内幕信息的便利途径和个人利益关系,容易成为知情人从事内幕交易的掩护,故而可将此类受密人作为“准知情人”,与知情人列于同一传播层级。身份关系对缩短传播链条的作用在“成艳娴、顾慧佳、顾鎔内幕交易案”中尤为明显,成艳娴与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叶某菁关系密切。顾慧佳、顾鎔则与成艳娴系十多年好友,三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有多次联络接触,顾慧佳、顾鎔的证券交易账户行为明显异常,证监会认定三人构成共同内幕交易。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67号。形式上内幕信息从叶某菁传递至成艳娴,再由成艳娴分别传递给顾慧佳和顾鎔,发生了两次二级传递,但基于各主体间多年好友的密切关系,证监会实质上将成艳娴、顾慧佳、顾鎔三人间的信息传递过程淡化了,认定三人系同一层级受密人,进而成立共同内幕交易。将此类密切关系人认定为同一层级传递人的原因在于知情人与特定关系人员间的利益高度一致性,在知情人员向特定关系人泄露内幕信息的情况下,特定关系人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获利,实际上同知情人员自己获利并无本质的区别。See Salman vUnited States,580 US(2016)但是对密切关系人的认定应当持严格限制的立场,不宜仅凭亲属、朋友、同学等关系就认定为同一级传播人。建议将允许推定为同一级传递人的范围限定为:①配偶、子女、父母;②有长期共同居住关系的人;③有长期密切资金往来的人。实质审查标准则为该类群体间是否具备利益一致性和信息获取渠道便利性两大特征。
第三,对于以窃取、骗取、套取等积极的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的家属,此种实质性认定应当更为严格,理由在于法定知情人的家属对自身的地位和由此产生的义务应当有清晰的了解,对从家庭成员处无意听得的信息应当保持高度谨慎,而非法獲取人的家属在意识上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应要求其对家庭成员的非法获取行为持同样的高度谨慎。因此不得单以家庭成员关系就认定各方责任,而是要结合其他直接的证据证明内幕信息确实发生了传递。除此以外,考量受密人与信息源头、泄密人间的关系,内幕信息传递的介质能否固定、留痕以及涉案人对内幕信息的认知等也可作为认定同层级传递人的重要依据。
不得不承认的是,即使通过身份关系将传播链条缩短,也难以避免遗漏一些更为隐蔽的内幕交易行为。传递型内幕交易执法不仅有赖于法律规则的明确,也需要侦查技术的进步。在现有的侦查技术下,一些传播链条长、手段极其隐蔽的内幕交易难以被发现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但是通过身份关系的思路仍可以将部分有预谋的内幕交易窝案纳入打击范围。况且,内幕信息会在多层级传递中逐渐失真,越在传播链条后端的受密人,其获得及时而准确的内幕信息的概率就越小,能据之交易并获利的可能性也就越低,此时受密人的交易与证券投机行为越发接近,交易行为的不法性也就随之消解了。
(二)从共同违法视角下追究泄露型内幕交易各方责任
受密人责任源于泄密人行为的不法性,而判断泄密人合法与否的关键在于其是否从泄密中获取个人利益,受密人与泄密人的责任是成立泄露型内幕交易的两个方面,泄密人与受密人也呈现普遍的共同违法特征,而现行法律对成立行政共同违法的要件尚无明确规定。
上文已明确了泄密人与受密人责任的成立要件,并提出通过身份关系将特定内幕交易主体锁定在同一传播层级的执法思路,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受密人与泄密人作为共同内幕交易加以处罚。认定共同内幕交易可以从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及有责性三个阶段递进式展开认定。具体执法思路是当行为人具备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时,原则上可以推定构成行政处罚,此时满足该当性的行为若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则该行为具备违法性,但尚不涉及责任认定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进入有责性判断,根据行为人是否具备行政责任能力、主观状态的因素分别确定处罚额度。上文已述,对受密人追责以主观故意为前提,但是直接证明主观故意非常困难,实践中将泄密人违法性具体化为获益要件,受密人对泄密人违法的认知则与证明泄密人获益相辅相成。而泄密人是否获益并不以故意泄密为前提,这也是在肖家守案中证监会对过失泄密人肖家守予以处罚的原因,此时泄密人与受密人是否存在内幕交易的共同故意并非成立共同违法所考量的内容,只要泄密人与受密人在客观行为上具有关联,如在内幕信息敏感期联络接触的事实,且存在着某种利益互动,如直接的物质利益交换或足以产生固定情感联系的身份关系,即可认定双方成立共同内幕交易。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泄密人的主观状态、共同内幕交易的具体数额来分别认定各自的责任。
对于交易方责任的认定实践中已经形成成熟的执法经验,本文不作讨论。在对泄密人追责方面,主观上责任成立不以故意为限,可以拓展至过失泄密。在违法所得的认定上,则应当坚持在对其故意的审查基础上,将泄密人因故意泄露内幕信息所导致的受密人内幕交易违法所得作为泄密人的违法所得。如果泄密人对于二传、三传乃至之后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并无主观故意,则不宜将后者内幕交易的违法所得计入泄露人违法所得之内。
(三)以类型化思维完善内幕交易抗辩事由
根据抗辩事由是否可以独立地阻却违法,可以将其分为独立抗辩事由与非独立抗辩事由。独立抗辩事由包括《内幕交易司法解释》第4条规定的上市公司收购、预定交易计划、依据公开信息交易和其他正当交易行为;非独立抗辩事由则是指当事人提出的法定理由之外的抗辩理由。有学者整理了2004—2020年证监部门做出的382份内幕交易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当事人提出的主要抗辩事由进行了归纳,其中非独立抗辩事由主要包括6种:独立分析判断;违法情节轻微,分别为获利较少或亏损与社会危害性小;依据公开信息交易;符合以往交易习惯;法律认识错误;纯属巧合或偶然,共占全部抗辩事由的79%。可见《内幕交易司法解释》所规定的独立抗辩事由远不足以涵盖实践中当事人的抗辩理由范围。但实践中当事人的抗辩能被证监部门采纳的寥寥无几,行为人若想排除行为的违法性,应当完全切断知悉内幕信息与交易行为的联系,即证明即使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会进行相同交易。
推定规则平衡了证监部门在内幕交易是否成立事项上的举证弱势,但当推定事实成立后,举证能力强弱态势已然平衡,此时不宜无差别地对当事人反驳推定事实苛以过高的证明标准。可以参照《座谈会纪要》对密切关系人与联络接触人交易异常行为吻合度相区分的规则,当事人的内幕交易抗辩亦可以身份作为区分。对于密切关系人之间成立的内幕交易,当事人若具备获取内幕信息的高度便利性和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其提出的申辩理由应达到优势证明标准,即当事人应当证明内幕交易不成立的可能性大于成立的可能性,方能推翻监管机关的推定事实。而对于因无特定身份关系下联络接触而推定成立的内幕交易,当事人的申辩理由达到产生合理怀疑的程度,即可推翻内幕交易推定。总之,应当尽快根据主体条件的差异,设立不同标准的推定规则,让越易获取内幕信息的人承担更加严格的抗辩证明标准。
五、结语
在多层次传递型内幕交易责任认定中,應当充分意识到泄露人责任与受密人责任是内幕交易成立的两个必要方面。监管机关要在明晰各行为主体违法性来源的基础之上,关注各行为人的身份特征、信息获取渠道、联络接触情况等关键性证据,充分发挥推定规则在现有执法技术条件下的作用,必要时可以突破形式上传递层级的限制展开积极执法。同时,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推定事实不可避免地会与自然事实产生一定程度的偏差,这是执法在公平与效率间权衡的结果。为此,完善内幕交易中的各项抗辩事由,赋予行为人对推定事实进行反驳的权利亦是未来执法应当关注的重点之一,有必要在日后的理论与实践中展开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李浩证据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黄江东,施蕾证券法治新图景:新《证券法》下的监管与处罚[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2
[3]高振翔传递型内幕交易中推定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从苏嘉鸿案谈起[J]证券法苑,2019,27(2):231-253
[4]REINIER KThe legal theory of insider trading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in Klaus J,Hopt and Eddy Wymeersch eds European Insider Dealing[M]London:Butterworths,1991
[5]曹理新《证券法》下内幕交易认定的理念转换与制度重构——以光大证券“乌龙指”案为对象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1):78-84
[6]韩轶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犯罪主体认定的“辩审冲突”问题研究[J]法商研究,2023,40(1):130-143
[7]赵姗姗法益视角下证券内幕交易罪主体范围的规范构造[J]政治与法律,2018(10):43-56
[8]GEORGE W,ROBERT PFinancial Services Law[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9]万国华,杨海静论反欺诈原则在证券法中的确立——对诚实信用作为证券法基本原则的反思[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19-129
[10]STEPHEN BRegulating Insider Trading in the Post-Fiduciary Duty Era:Equal Access or Property Right Research Handbook on Insider Trading[M]Edward Elgar,2013
[11]缪因知人际利益关系论下的内幕信息泄露责任研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38(3):129-140
[12]吕成龙内幕交易的“源头规制”:动因、经验与路径[J]证券市场导报,2020(9):60-69
[13]缪因知反欺诈论下的内幕交易类型重构:原理反思与实证检验[J]法学家,2021(1):125-141,195
[14]熊樟林共同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与处断规则——兼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7条之检讨[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33(3):151-158
[15]陳晨证券市场多层次传递型内幕交易犯罪认定难点研析及理论辨正[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7,32(6):56-67
[16]齐萌,刘博内幕交易抗辩事由:实证分析与法律规制[J]财经法学,2022(2):130-145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Responsibility Determination of Multilevel Transmission Type Insider Trading
CHEN Daisong XU Jiahao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50,China)
Abstract:The coupling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Internet technology brings about the extension of the transmission chain in insider trading,resulting i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presumption rules in holding the subjects of information recipients liable,and also leading to a serious mismatch between the legal liability at the trading end and the leaking endIt should be recognized that the liability of the leaker and the recipient are two aspects of the liability for insider trading,and the current presumption rule is actually a presumption of the liability of the recipient on the basis of the liability of the leakerThe current presumption rule is in fact a presumption of insider trading liability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aker's liabilityBy concretizing the illegality of the leaker to benefit from the leak and the illegality of the recipient's trading behavior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recipient's illegality,the nature of insider trading illegality with benefit as the core can be revealedThe interpersonal interests contained in the identity relationship are the driving force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By analyzing the identity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u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resumption,and by taking the convenience of information access and consistency of interests as the substantive examination standard,the subjects formally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issemination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same level of knowledge,thus ensu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esump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sider tradingIn this way,the insider trading liability can be precisely covered based on the presumption of fact
Key words:Multi-Level Transmission;Inference Rules;Identity Relations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