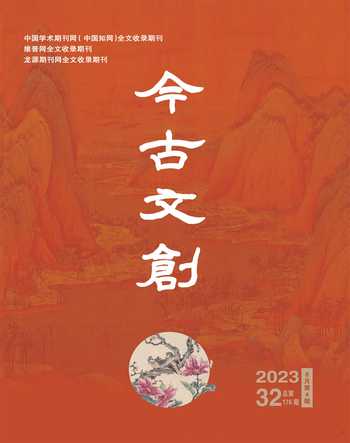晚明才女文化中的女性定位
2023-09-19刘雅婷
【摘要】晚明是才女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才女群体相继涌现,然才女之间却也有着不同的定位。她们或占据一定的生存优势,成为主体意识的建构者、社会生活的参与者、世俗命运的偏爱者;或处于相对被动的境地,充当家族利益的联结者和生活实际的顺势者。通过研究才女文化中的女性定位这一问题,可窥见晚明社会下女性的文化生存空间。
【关键词】晚明;才女;才女文化;女性定位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2-007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2.021
才女是女性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又因为“才”的存在而显示出相对独立的意味。狭义上说的才女单指有才华的女性,她们拥有一定量的文化知识和艺术才能,可以顺畅阅读,有创作能力并有一定作品问世,甚至能参与知识群体的文化交流[1]。至于广义上的才女,它的评判标准则涵盖多个方面,才、德、色兼备的女性才可被称之为才女。个体性才华、良好的德行、姣好的容貌成为才女群体和一般女性群体的边界所在。晚明是才女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才女群体相继涌现,更新了晚明以前才女零星产生的状态。然而任何一个群体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内部难免会存在一定的分化。冠之以才女之名的女性群体间也有着不同的定位,她们的人生际遇不尽相同,对自我、对生活、对命运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态度。就现有资料来看,晚明的才女们或占据一定的生存优势,成为了主体意识的建构者、社会生活的参与者、世俗命运的偏爱者;或处于相对被动的境地,充当了家族利益的联结者和生活实际的顺势者。本文拟对这几类才女加以论述,进而揭示晚明时期女性群像之一隅,以增加对古代女性及其所处社会的了解。
一、主体意识的建构者
封建社会制度下女性无需自立自强担当大任,遵守三从四德攀附于男子即可。但在晚明才女群体中却出现了一大批职业女性,她们自我意识浓厚,对个人命运有着强烈的关注,对社会发展也有着更为深刻的体察,凭借自身爱好或者才能而有所营生,在复杂的男权社会中积极争取立足之地,闺塾师便是当中的代表。
明代图书的坊刻与出版活动兴盛,明中叶以后图书的阅读群体不断扩大,家族内有才识的女性不断产生,女性教育需求大大提高,职业女塾师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这些闺塾师基本都出自有着女性学问传统的文人家庭,在家道中落的境地下,她们通过教授上流社会中的女孩儒家经典、诗歌绘画等艺术而谋生。作为出版过作品的诗人或得到承认的画家,这些女性在因其名声而获得塾师的工作之前,实际上就已经是职业艺术家了[2]135。像是文俶出身于苏州的一个著名画家家庭,而后自己承袭家学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画家,很多女性都愿意找她担任塾师。黄媛介则更为典型,她出身于秀水黄氏家族的一个旁支,接受了较好的文化熏陶,才名远扬。“髫龄即娴翰墨,好吟咏,工书画。楷书仿《黄庭经》,画似吴仲圭,而简远过之。其诗初从选体入,后师杜少陵,潇洒高洁,绝去闺阁畦径”[3]45。丈夫杨世功没有足够的能力养家糊口,她便通过教书、出售诗画字来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因其作品风格独特,当时许多名士都曾为她题跋作傳。后声名日显,受邀到北京为高官之女担任塾师。
像黄媛介这般闺塾师的存在其实是对儒家社会性别体系的冲击,女性的自我谋生威胁了旧有的“三从”基础,女性的声望违背了安静和隐居的理想女性形象,闺塾师身体的流动性和越出自己闺阁界限的能力颠覆了女性生存空间封闭性的理想[2]135。但女性凭借自身突出的文学艺术才能安身立命,实现经济独立和精神追求,不将大大小小的生存需求寄托于他人身上,可谓是独立人格的体现,这种践行女性主体意识的行为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二、社会生活的参与者
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加之自身接触的文化知识更新了才女们的思想,开阔了她们的眼界,使得她们并不愿像传统闺秀般困于内宅方寸之地。她们渴望跨出封闭的地界,同男性一般自由探寻其他领域。良好的出身加之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使得才女相较普通女性有着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用。适时诸多女性社交团体应运而生,像是沈宜修主持的家居式诗社,将夫妻双方家族内的女性集结起来,组织聚会、出游、交换诗作;商景兰主持的交际式社团则运转在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内,成员并不局限于族内的亲属,除社内女性的文学创作外还为其他女性的作品书写序跋;还有公众性的女性结社,社交范围从相对私人的领域扩展到公共领域,女性的诗人身份得到了公开承认,其作品内容不仅涉及情感生活,还有对家国大事的思考和评论。
还有些才女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是通过和其丈夫社会角色相倒置这一途径实现的,被其父称“身有八男,不易一女”[3]34的王端淑和丈夫丁圣肇便是如此。在文人圈中,王端淑成为了丈夫的替代者,她以其丈夫的名义撰写了大量的诗歌、书信、挽歌、传记和墓志铭,还曾为丈夫代笔向南明朝廷上奏文,试图为他的父亲,一位死去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2]140。此外,女性虽囿于家内职责,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对公众事务和国家前程的关心。如顾若璞曾受科举课程的训练,日常便会与儿媳讨论国家政策问题;方孟式的丈夫死于1640年的抗清战役,而后她本人也选择了以身殉节;王端淑则通过作品公开表露自己忠明反清的政治立场,还为刘宗周、倪元璐、祁彪佳、父亲王思任等15位忠明官员书写传记……从中不难看出,这些才女有着不输男性的社会责任感。
三、世俗命运的偏爱者
人各有命,有些才女几近一生都是颠沛流离,有些才女却是世俗命运的偏爱者,即便不是一生都顺遂,也多在某个阶段获得了运气加持,于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占据了更多的生存优势。
邢慈静出身名门,是晚明文坛上誉重一时的才女。“母万爱慈静甚,必欲字贵人。年二十八,始适武定人大同知府马拯”[4]747。在讲究适龄婚嫁的封建社会,女性基本20岁之前都已出嫁,像邢慈静这般因父母爱女心切而大龄出嫁的是极少数。家族并未将她的婚姻作为利益工具,而是悉心寻觅良配,夫妻二人也确实恩爱情深,美满的婚姻使得女性今后的人生相对而言有了一定的保障。也正是因为出嫁颇晚,所以邢慈静有着较一般女性更为充足的闺阁时光,这就为其积淀深厚的文化素养创造了有利条件。才女名婉接受文教的途径主要是婚前的娘家学与婚后的夫家学这两类[5],邢慈静无疑是经受娘家学浸染的典型,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文学和艺术熏陶,当中又以其胞兄邢侗的影响最深。邢侗工书画,备崇王羲之,与米万钟、张瑞图、董其昌并称“晚明四大家”。在兄长的引领与指导下,邢慈静亦是书画俱佳,“善画白描大士,书法酷似其兄”[4]747。晚年寡居礼佛时她也是寄情于诗画,创作了诸多作品并遗世。至亲的培养与爱护让她拥有了可一辈子傍身的才能,无论何种境况都可使她于物质或精神层面留有退路,将生活的主动性掌握在手中。
晚明女性文学大家商景兰也值得一提,她出身于官宦之家,与丈夫祁彪佳的结合是门当户对,婚后夫妻二人亦是伉俪情深。商景兰所在家庭中男性亲属所取得的政治与文艺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她丈夫作为抗清名臣的殉难,提高了她作为节妇和祁家家长的威望,她作为诗人的盛名在清早期也得到了显扬[2]242。这就使得商景兰即使身为孀妇也依旧拥有显著的社交自由,可给公众领域造成不小的影响。加之她寿命绵长且子孙满堂,打破了明末女性才高福薄之说,连带着她以节妇身份彰显出的崇高道德也获得了高度肯定。相较于那些早亡的才女,商景兰可谓是相当幸运,通过充分利用家族男性亲属所创造、遗留的显性、隐性资源,有效巩固了她身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四、家族利益的联结者
女性接受良好的教育,进而知书达理,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能够培养出才女的家庭大多不是等闲之户。女子虽然无法带来科举及第的殊荣,但倾家族之力悉心教养出的女性,对于整个家族的发展也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女性具有良好的知识文化素养,在婚姻方面则可具备更强的竞争力。男女间的知识差距越小,婚后女性便可与丈夫更好地沟通交流。出于整个家庭或家族发展的考虑,上层家庭在选择新娘时会对女性的才华颇为关注,有才识的女性结亲的对象亦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知识分子。名门望族间的强强联合可促进阶层的上升或维持现有阶层的稳固,叶绍袁、沈宜修这对有金童玉女之称的夫妻便是当中代表。二人都于文学方面颇有造诣,且都出自吴江最显赫的家族之中。叶家自14世纪便繁荣昌盛于苏州城南吴江南部的太湖北岸,其主要派系都聚集于此。在叶绍袁之前,他的直系家族已连续四代都出了进士出身的官员[2]204;沈氏亦是人才济济,文学家和为官者不计其数,沈宜修之前的四辈中都有出进士,其伯父沈璟为著名的戏剧家,创立了吴江学派,门生众多。一个家族想要在地方社会中长久绵延下去,离不开依托于亲属关系和婚姻关系所形成的血缘纽带。所以叶、沈两人的婚姻不过是家族间长久结盟的手段之一,才华匹配的背后是利益权衡。
另一方面,有才识的女性本身就是家族实力的体现,她们的存在彰显了所在家族的教育理念与方法的正确性,是对其家族文化的肯定。且基于良好的學识,才女在下一代的教养上相对会得心应手些,在教育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起了家族文化的传递者。无论是未婚女还是出嫁女,她们在维护和强化书香门第的良好声望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对于显贵之家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隐形财富。才女的培养与塑造虽然摆脱了“但教男而不教女”的落后思想,但无法否认当中依旧有着很强的功利性。特别是晚明时期才女群体家族性特征日益显著,相当一部分才女难以以独立的个体身份生活。受家族所供养,便要为家族争取一定的利益,成为了既定的事实。
五、生活实际的顺势者
袁中道在《珂雪斋集》谈及其胞姐,“姊性端重,匿影藏声一一遵女戒。独好文,强记夙悟。大人每见而叹曰:惜哉不为男子”[6]431 !在他看来,“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略,使为男子,其取功名及文章事业,何遽出两兄下,而竟泯泯闺阁,实可叹”[6]432。其实他所感叹的莫不过“女性”这一社会身份带给他姐姐,抑或是众多与他姐姐类似女性的弊端。女性有才识固然值得夸赞,但在三从四德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认知下,遵女戒,相夫教子,侍奉姑婆,管理内宅家事……这些传统伦理中所认可的女性特质才是最应该肯定的,并以此建立起了服务于男尊女卑观念的空间管理秩序。所以袁中道最多只是感叹他姐姐的遭遇,言语中并未涉及到对男女不平等的抵触。他并没有因盛赞其姐而支持她将自身才华最大程度发挥,也就是说他认为女性对才的追求比之对德的遵循并非更有意义,女性接受这些因天生性别导致的不公平待遇无可厚非。之后更是以子嗣绵延、夫妻和睦这些绝对的男性视角来判定其姐人世福缘不浅:“伯修无子,子予子,而姊有三男矣。中郎有子,未见其冠婚及入校,而姊见幼男冠婚入校矣”[6]432。“今姊夫妇相庄无间言,诸子于于色养,岁时伏腊,儿女团圞,取酒脯凫鲤为欢笑”[6]433。这般对现实生活美满的定义却也恰恰印证了传统社会对于女性所施加的束缚,女性的幸福离不开婚姻与家庭,或者说是离不开男性,她们无法作为独立的个体生活,个人的价值追求显得无足轻重。
此外,在男性占据主导权的封建社会中,突出的才华对于女性来说有时并无锦上添花之效,反而有画蛇添足之嫌。男性会通过某些他们看来合情合理的论调来驯服身为弱势群体的女性,一些身心系于男性的女性亦会主动迎合,狭小的生存空间会使得部分才女自愿甘于平庸,选择成为一个更能被社会所认可的人。如王凤娴遵循节妇准则,认为妇道人家不应与诗文打交道,便将自己的大部分诗文付之一炬。沈宜修的婆母因担心沈氏多才,夫妻二人经常作诗互赏会影响叶绍袁科举备考,便禁止其写作。为免家庭失和影响丈夫科考,她不得不违心地放弃自身的文学爱好。黄宗羲之妻叶宝林“少通经史,有诗二帙”[3]54,在听闻越中闺秀以诗酒结社的事迹后却认为这是特别伤风败俗之举,而后“即取己稿焚之,不留只字”[3]54。上述才女,她们都是生活实际的顺势者。某些人确有才华却要自觉扼制,某些人接受了男权思想的驯化,不做不利于自身淑女、贤妇等形象塑造之事。即使她们当中有人心存不满与怨怼,也无多少人在意,加之自身缺乏足够的勇气去抗争,最终泯然于众人矣。
六、结语
才女群体的产生与壮大无疑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从中可反映出晚明社会的发展状况和女性的文化生存空间。基于生活环境和自我价值观念的不同,才女们的人生走向也不尽相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象,或主动,或被动,或处于二者之间。封建社会的女性如何在不占性别优势的情况下掌握一定的主动权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才女群体当中的部分女性对此作出了解答——有才便要善用,好运不可浪费,人格独立永远不是空谈。现今女性权利、地位、价值等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我们或许可从晚明才女文化中不同女性的定位中总结相关经验,找寻问题的突破点。
参考文献:
[1]柳素平.晚明非家庭知识女性的生存空间[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111.
[2](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3]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
[4](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刘俐.晚明才媛:邢慈静书艺渊源与风格取向[J].书法,2021,(06):167.
[6](明)袁中道著,钱伯城点校.珂雪斋集(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
刘雅婷,女,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专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