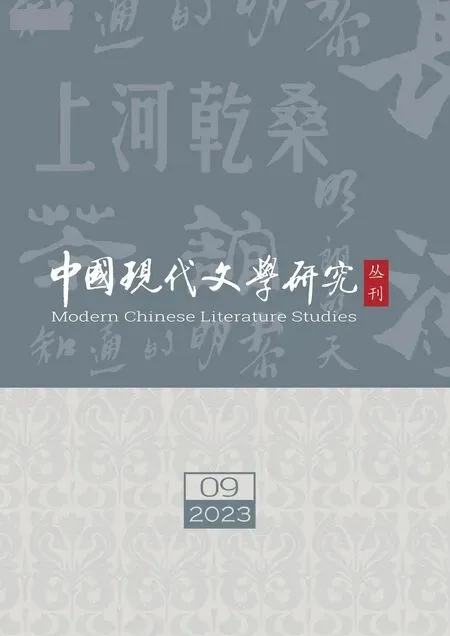《祝福》中的时空结构与自然伦理问题※
2023-09-14刘红英
刘红英
内容提要:《祝福》是中国现代经典小说之一,学界对该作品的研究已经很多。但作为经典,它依然拥有可以深入探讨的空间。在当代环境问题成为世界热点问题时,鲁迅进化论思想庶几被挑战。本文通过凸显“贺家墺”在小说整体结构中的意义,进而发现《祝福》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问题上展现了整个历史与宇宙的时空体系。在这个繁杂而有序的时空体系中,自然伦理问题是个值得深入研析的课题。它对进一步理解鲁迅的自然观、科学观、宗教观、历史观以及鲁迅思想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都有所助益。
《祝福》是中国现代经典小说之一,学界对该作品的研究已经很多。近年来,随着伦理学、民俗学、叙事学等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兴起,该小说也因其主题的不确定性、人物形象的多义性、情节结构的交叉复沓、空间场景的魅惑性等特征,从而获得了更加多样化的解读。同时,有的研究偏离鲁迅思想与鲁迅精神愈来愈远。事实上,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自成体系、自我独立,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以“某一点”而“非此即彼”。本文在充分考虑该小说所揭示的宗教意识、故乡叙事、“彷徨”心境、启蒙反思等问题的同时,通过凸显“贺家墺”在小说整体结构中的意义,进而分析在《祝福》中鲁迅所表达的自然观、科学观、宗教观与历史观。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偏重《祝福》中宗教伦理问题的时候,这些研究是否忽略了其中的自然伦理问题以及鲁迅思想的整体性?诚如诸多研究者注意到祥林嫂对“灵魂”“地狱”的询问,但“贺家墺”这一空间场景与“鲁镇”以及“地狱”等空间想象又有怎样的关系?如果祥林嫂的“死亡”令后来研究者追问不已,那么,阿毛的“死亡”是否也有不可忽略的隐义?并且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在当代环境恶化,生态伦理被热议的全球背景中,《祝福》中的自然伦理应作何分析?它对中国现代社会及文化转型的历史意义与当下价值是否构成冲突?事实上,在《祝福》中诸多具体可见的现实事端与各种氤氲弥漫的超现实想象背后,拥有鲁迅对自然、社会、历史、宗教、人性等诸多因素的思考,并且构建了一套将这些交叉的矛盾着的诸因素连接起来的严密的时空体系。在这套体系中,既呈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在宇宙空间中的共时关系,同时显示从原始自然到人类历史的进化。进而言之,小说既蕴含人类历史时间的推进与某个时段的断裂以及断裂之后的连续,又将这一切包孕在宇宙空间之下。因此,对《祝福》以及其中所揭示的鲁迅思想的研究,“当俟宇宙发生学(Kosmogenie)言之”1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按照恩格斯对自然伦理的揭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98页。。
一 贺家墺:一个“狼吃孩子”的山村与鲁迅进化论思想的必然选择
鲁迅思想的重心在“立人”,《祝福》中对鲁四老爷、四婶、柳妈以及其他诸多人物的刻画与对“我”的内心活动的描绘,无不显示鲁迅对国民精神的深思与关切。目前对《祝福》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重祥林嫂对“灵魂”的追问与小说中的宗教伦理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祝福》中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宗教信仰思考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祝福》中,“贺家墺”是这种关系的隐喻,它是小说故事时间的起点,也是鲁迅思考“鲁镇”与“地狱”等一系列事件以及“立人”问题的逻辑原点。若忽略这一原点,对《祝福》的阐释与对鲁迅思想的理解,都可能是偏颇的。《祝福》中有一段话,鲁迅不厌其烦、一字不改地重复了两次,即:
“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墺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他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1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15~17、13页。
这段话首先以重复的形式强调了阿毛“听话”,却遭到如此悲惨的结局。其次,它引起了听者/看客的两次不同反应。这段话中阿毛这一人物设置与“贺家墺”这一空间场景所隐含的意义,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开端”或起因。小说写到“肯嫁进深山野墺里去的女人少”2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15~17、13页。,“深山野墺”意味着人类生存环境的险恶。在鲁迅笔下这组关系呈现了“动物世界”的凶残与恶劣。在“贺家墺”与“鲁镇”之间,“鲁镇”可能才是比较安全的去处。当然,“鲁镇”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及礼教文化的隐喻,是《祝福》重点描述并批判的对象。但在小说故事时间的初始,“贺家墺”的设定是对“鲁镇”的反衬,也预示“鲁镇”作为历史前进中的“城镇”存在的必然缘由。鲁迅在《人之历史》中写道:“论人类从出,为物至卑,曰原生动物。”3鲁迅:《人之历史》,《鲁迅全集》第1卷,第17、14页。然而,在自然界,“时有强物,灭其耎弱,沮其长成,故强之种日昌,而弱之种日耗;时代既久,宜者遂留,而天择即行其中,使生物臻于极适”4鲁迅:《人之历史》,《鲁迅全集》第1卷,第17、14页。。众所周知,鲁迅在留学日本之前,学修自然科学。这对他后来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理性批判思维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在当代环境问题成为世界危机的时候,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庶几被挑战。但如果着重思考“贺家墺”与阿毛在《祝福》中的作用,并结合鲁迅创作的历史语境,就不难理解鲁迅对进化论思想的价值选择。
古今许多文人学者往往崇尚“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自然境界,钦佩“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格。在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陶渊明诗歌与散文成为后世多数文人的精神依托。然而,鲁迅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评价没有那么乐观,或者说鲁迅并不相信在陶渊明及其诗歌中能找到精神寄托。他说:“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第538页。在《故乡》中,鲁迅也曾通过对少年闰土“月下刺猹”的描写,勾绘了一幅美丽自然与纯真人性和谐交融的美丽图景。许多研究将《故乡》与《祝福》相提并论,因为它们同样书写故乡,描写故乡的“自然与人”,同样反映鲁迅对“故乡”情感上的疏离,从而表现现代人特有的生命体验——故乡是“永远回不去”的。然而,从自然伦理的角度来思考《故乡》与《祝福》,两篇小说则截然不同。《故乡》中“月下刺猹”的英雄少年,在《祝福》中变成了被狼“挖空了五脏”的阿毛。当然,闰土已为少年,阿毛尚在童年,但这个区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孩子的形象,揭示了从《故乡》到《祝福》,鲁迅的自然观与生命观的变化。如果说鲁迅在《祝福》中以“地狱”想象来思考人的精神依托,但他设定了一个前提,即人在满足基本生存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形而上思考的可能。
在人与自然之间,是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的关系。这是“五四”时期一代知识分子在特定文化历史时空中的文化选择。正如王富仁所说,“不论是文化,还是民族和人,都是在其特定的时空结构中显示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离开特定的时空结构,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就将是模糊的、游移的、不确定的。与此同时,一个思想家将他面对的各种不同的事物纳入到怎样的时空结构中来感受、来理解,不但决定了在他的思想中周围世界的性质和作用,同时也决定了他的思想本身的性质和作用”2王富仁:《时间·空间·人(一)——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郭沫若的《女神》中展现了特定历史时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是特定的中国现代学人对“蛮荒自然或天然自然”的理解与体验,是一种主体精神的表达与诉求,也是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必然逻辑,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了一个‘西方世界’,发现了一个新的空间,它们的整个宇宙观才逐渐发生了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变化”3王富仁:《时间·空间·人(一)——鲁迅哲学思想刍议之一章》,《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期。。在这个新的空间中,“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既体验空间给人带来的陌生感,又体验时间带来的断裂感。当然,就文艺现代性而言,对“民心淳朴”的回望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困境。当代作家北村在《我的自然生活》中“记述了自己远离城市回到乡下生活的经历”,然而,他“对中国文化中‘人融于自然’的观点表示怀疑”,因为“自然的含义中首先包括的是植物和动物,而人是文化的、疏离的甚至是遮蔽的”。1转引自贺绍俊:《“自然写作”,也是先锋写作——从〈草原〉2022年度“自然写作”说起》,《文学报》2023年2月21日。当代作家的自然写作与鲁迅、郭沫若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更为清晰地表述了他们与古代知识分子“天人合一”自然观的不同。贺绍俊认为这是作为现代人所践行的责任意识。《祝福》中阿毛的命运与“贺家墺”这一空间场景的描绘意味着鲁迅对古人所持有的自然观与天命观的否定,他以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隔断了在前行无路时陷入乌托邦想象的退路。这既体现出鲁迅在特定时空背景下选择进化论思想的缘由,也表现了鲁迅思想中特有的生命力与强者精神。
二 鲁镇:鲁四老爷的“书房”与鲁迅对社会自然的现实批判
“鲁镇”是《祝福》中另一重要的空间场景,是中国封建社会与文化的缩影,凝缩了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从建构到衰亡的历史演变。它象征人类从蛮荒自然向社会文明的过渡。在对“鲁镇”文化图景的描绘与展现中,鲁迅凭借对生活与社会敏锐的感受力与对文化悖论的认知,在对故乡人与事的“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情感背后,呈现出“鲁镇”存在的合理性,它毕竟是人类文明由野蛮时代向前的跨越,只不过在晚清之际这种文化走到了它的极限。《祝福》中“鲁四老爷”的“书房”便是这种“极限”文化的具体表征。书房“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一堆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2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6页。。书房的陈设象征这种文化的衰败。“朱拓”的“寿”字,血腥般地呈现出衰朽腐烂的状态与令人触目惊心的哀痛。小说中一再写到“鲁四”与“老爷”并称,是对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讽刺与否定。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人们,一个个行尸走肉。他们麻木、愚昧而迷信。叙事者“我”对祥林嫂“既哀又恨”,不仅体现在对其外貌和肖像的形容上,而且在描述其勤快劳作、勇于反抗等性格特征时,无论如何说,绝不是一种赞扬,而是充满讥讽与挖苦语气的。因为祥林嫂的“劳作”与“反抗”也恰恰是封建“礼教”文化驯养的结果。
如果说原始的“天然自然”是荒芜与野蛮的,人类历史同样呈现出它的暴力与血腥。“祥林嫂,你放着吧!”1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17页。司空见惯的日常对话,背后掩盖的是命令与被命令的等级关系,它隐含着“这历史没有年代……满本都写着‘吃人’”2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47页。。鲁迅对以鲁镇为象征的封建礼教及其文化的批判,始终以“人”作为中心与重心。“立人”是鲁迅毕生追求的命题,他提倡“剖物质而张灵敏,任个人而排众数”3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7、58、57页。的个性精神。然而,这种对“个人”“个性”的提倡,它与欧美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个人”“个性”的具体内涵不同。在20世纪初期,中国处于被侵略、被侮辱的民族危机中,鲁迅的“立人”思想始终与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联系在一起。他提倡“立人”,是为了“立国”,因为国家富强的“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7、58、57页。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是鲁迅一代学人,对古代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责任精神的继承。但他又与中国古人的“天下”观与民族观不同,鲁迅思想中始终有一个大写的“人”的自我理念。在国家和个人之间,他认为国家建设须有个人精神与自我意识作为基础。鲁迅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黑格尔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他对个人启蒙与国家关怀的思考,背后都暗含着进化论意义上的历史时间观念。所以,在肯定个性精神的同时,他顾及现代中国民族建设的时代性与特殊性。他在1925年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5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32页。鲁迅所虑不仅具有现实针对性,而且富有极强的预见性。在个人与国家之间,他始终主张建立的是“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立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6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7、58、57页。换言之,唯有以“立人”为前提,中国方可跻身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立人”与“立国”的两重维度使鲁迅思想融汇了西方启蒙主义精神传统中“个性”观与源于民族发展精神基础上的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思想。王得后指出:“鲁迅文学以他的‘立人’思想为根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这是他的‘立人’思想的第三块基石。”1王得后:《鲁迅研究笔记》,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61页。
不过,鲁迅基于“立人”思想对封建礼教与等级制度的批判,也有其特定文化传统与历史现实背景。《祝福》中对鲁四老爷的“书房”进行特写,放大其没落的状貌,并强调鲁四老爷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但是,他“大骂新党”,“并非借题骂我”2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5页。……事实上,“我”所否定的也是“讲理学的老监生”所象征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腐朽文化,而不是全部中国古典文化。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道:“昔者帝轩辕氏之戡蚩尤而定居于华土也,典章文物,于以权舆,有苗裔之繁衍于兹,则更改张皇,益臻美大。其蠢蠢于四方者,胥蕞尔小蛮夷耳,厥种之所创成,无一足为中国法,是故化成发达,咸出于己而无取乎人。”3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45页。简言之,鲁迅对中国远古的“礼乐”文化是肯定的。事实上,“礼”,是“人与人各种和平的交往方式以及这些交往方式所必须遵循的规范和原则,是人与人建立超自我整体联系的方式”4王富仁著,宫立、李怡编:《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上),《王富仁学术文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1、33页。。“从皇帝到孔子,是中国由原始性的自然存在状态向社会化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国家化、政治化而具体实现的。”5王富仁著,宫立、李怡编:《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上),《王富仁学术文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1、33页。历史、文化、国家建设都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包括断裂与延续。中国历史在发展到晚清之际,其文化已经不足以与现代世界接轨。鲁迅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6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25页。颇为反讽的是,“四叔”与“四书”同音,鲁迅是否有此意,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毋庸置疑的是,鲁迅是在全球的、世界的、宇宙自然的,以及“全部历史”的时空视域中,以“立人”为重心来思考中国问题的。他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三 地狱:祥林嫂的灵魂之问与鲁迅对人的内在自然的超越性探求
“地狱”想象是《祝福》中第三个重要的空间场景,也是最具“魔力”色彩的空间构建。因其超越外在客观自然,关注的是人的精神救赎与灵魂出路的问题,成为当代研究者比较热衷的话题。但是,从自然伦理的维度上看,人在经历原始自然与社会自然之后,必然回到人类自身(人的内在自然)来思考生命的本质。《祝福》中弥散着“五四”落潮期的感伤与迷茫。祥林嫂与闰土、杨二嫂,甚至子君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并没有直接受困于经济的窘困。不过,值得强调的是,祥林嫂的疑虑正是“我”在深思也是反思的问题,即超越物质的现实层面,甚至越过启蒙的文化层面,人的内在心灵与精神当如何安置?从叙事手法上来讲,祥林嫂是作者设置的“自我”影像。
“她”(祥林嫂)既是“他者”,也是“自我”(叙事者“我”),是“我”借祥林嫂发问来思考关于死亡、地狱与灵魂问题的。小说写道: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2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7页。
如果说“我”与祥林嫂之间,在整个故事的叙述中是叙述与被叙述、审视与被审视的关系。实际上祥林嫂的声音仍然是“我”的声音,是“我”与自己的对话。按照谢林对“主体与客体”的阐释,他说:“主体最初是一个纯粹的、没有在当前出现于自己面前的主体——当它想要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它就成为自己的客体……”3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页。简言之,当“主体”思考“自我”的时候,他将自己对象化。对象化的“自我”实际上是更加理性而清醒地回到自我。小说中“我”“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1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7页。,如此精辟的类比意味着“我”成为那个“被审视”的对象,实际上是“我”对自己的质问。但如果认为这是鲁迅在否定启蒙并进而思考中国文化中缺失宗教的问题,则有所偏颇。鲁迅所思考的依然“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以唤起国民的精神与灵魂来。
鲁迅并不相信“鬼神”,他说:“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3鲁迅:《致李秉中》,《鲁迅全集·书信(1927—1933)》第12卷,第260页。然而“不信鬼神”的表述,并不等于鲁迅否定宗教的作用。他谈到过“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4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第8卷,第29、30页。。鲁迅所肯定的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它不仅指具有规范性的既成体系的宗教信仰,而且包括具有宗教作用的各种风俗。《祝福》中祥林嫂所相信的正是风俗的“力量”。但很明显,鲁迅对祥林嫂的“信仰”是不屑与否定的。如果说胡适指出过:“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5胡适:《名教》,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鲁迅则认为不在于中国是否有宗教,而是需要分辨清楚“正信”与“迷信”的区别。他说:“设有人,谓中国人之所崇拜者,不在无形而在实体,不在一宰而在百昌,斯其信崇,即为迷妄,则敢问无形一主,何以独为正神?但宗教由来,本向上之民所自建,纵对象有多一虚实之别,而足充人心向上之需要则同然。”6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第8卷,第29、30页。简言之,“正信”是给人向上向善的“力量”的,否则,它就是“迷信”。即使是那些既成体系的宗教传统,如果不能给人“向上向善”力量,它也是一种“迷信”。比如,某一些圣徒会一边“高声欢呼,颂赞上帝”,一边却“手执利剑,以图报复异教,刑罚万民”。7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冯丽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在谈到中国的伦理与风俗时,伏尔泰认为:“中国人在伦理方面总是高于其他民族,但其他科学进步不大。毫无疑问,大自然赋予中国人以正直、明智的精神,但没有赋予他们以精神的力量。”1伏尔泰:《风俗论》(下册),梁守铿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4页。这种“精神的力量”,与鲁迅所谈及的意义大体一致。事实上,无论宗教还是风俗,当它不能给人以“精神的力量”时,便是“迷信”。
“做祭祀”“放鞭炮”是《祝福》中象征宗教与信仰的两个重要意象,这是典型的具有宗教意味的民间风俗。小说写道:“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2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5、21页。小说首尾都写到“鞭炮”,开头“是送灶的爆竹”,有“幽微的火药香”;结尾写“爆竹声连绵不断”,使“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人们以无限的幸福”。3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5、21页。这种描写消解了“祝福”的美意,同样显露出讽刺甚至挖苦意味。在《电的利弊》中,鲁迅说道:“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4鲁迅:《电的利弊》,《鲁迅全集》第5卷,第18页。在《祝福》中,所有这些宗教般的神秘叙事,其背后是鲁迅对宗教、科学以及生命意义的深入思考。这种思考既包含在形而上层面对人的精神与生命意识的探求,也蕴含在进化论维度上对人作为动物的进化,还有呈现在社会关系中人同时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两难困境。如此,祥林嫂的“死亡”至少拥有三重意义。首先,在自然生命的意义上,“死亡”是人作为动物的最自然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祥林嫂的“死”与其儿子阿毛的“死”,都是在“物竞天择”中自然生命的结束。然而,人类社会的进化毕竟不同于自然界,即“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此为祥林嫂“死亡”所具有的第二层意义,即人是具有精神生命与人伦意识的。阿毛死于“蛮荒的自然”(被狼吃),而祥林嫂死于封建文化的“吃人”。而由于两者之间是母子关系,他们先后“死亡”可能就存在某种因果联系。不仅如此,祥林嫂之“死”还具有第三层意义,即“死后”的问题。鲁迅临终前依然这样认为:“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研究,忘记了。”1黄大卫选编:《鲁迅散文》,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关于“死后”,鲁迅不像但丁在《神曲》中对“地狱”进行详尽而逼真的描绘与展现,而是以简笔进行素描,借祥林嫂之口发问。在充满魅惑性的超现实叙事背后,鲁迅所秉持的仍然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正因为如此清醒的理性审视,小说中“我”只能将自己悬置为一个“孤独者”——“抉心自食”“自啮其身”2鲁迅:《墓碣文》,《鲁迅全集》第2卷,第207页。。祥林嫂在大年三十夜“死掉”了,而“我”在“祝福”声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3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21、6、182页。。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麻木就是“死亡”。叙事者将“我”融入整个“醉醺醺”的“祝福”中,是对“自我”的客体化。这说明“我”是清醒的,同时是孤独的、悲凉的。然而,《祝福》在各种讽刺的、否定的、悲剧性的声音之外,始终还有一个清晰的声音,“无论如何,我决计明天要走了”4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21、6、182页。。“向前走”始终是鲁迅在“明知前面是坟”却仍然匆匆向前的姿势,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绝望者的精神选择,而“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5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21、6、182页。。整体来看,《祝福》展现出的是一部自然史与人类史相互交织的历史,它具体表现为从“贺家墺”所隐喻的天然自然,到“鲁镇”所象征的社会自然,最后到“死亡”所意味着的人的生命自然的有限性终结。但最有意味的是,“地狱”想象使生命在终结处又展开了无限延宕的可能,这不仅体现出鲁迅对彼岸世界的形而上思考与超越性诉求,而且这种构思使这部小说具有了“史诗”般的艺术魅力。6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