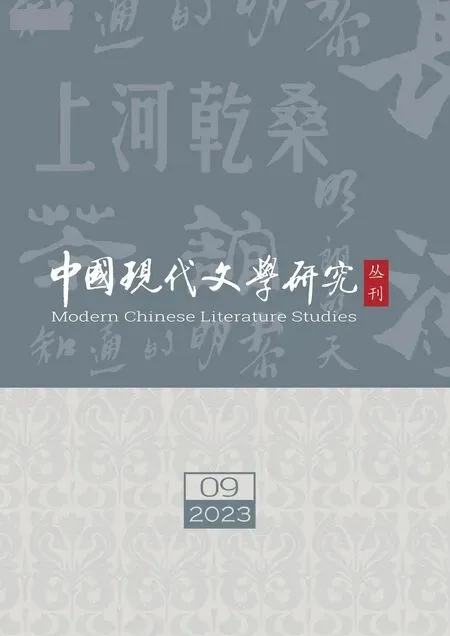革命认同与思想启蒙※
——论苏区新诗的革命叙事、大众化书写及其历史经验
2023-12-20周晓平
周晓平
内容提要:作为左翼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新诗,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经历了自身的洗礼与蜕变。一方面,诗歌的创作内容与之前出现了极大的不同,革命叙事与思想启蒙成为时代的潮流;另一方面,诗歌的形式继续在白话文基础上朝着大众化、自由化、通俗化的方向前进。苏区新诗的艰难探索是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历史阶段。
“五四”时期,伴随新文学运动的到来,白话文在文学中的呈现,使中国诗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胡适“实践效果大于实际效果”的新诗“尝试”,到郭沫若《女神》诗集的诞生,再到湖畔派小诗、“带着脚镣跳舞”的新月派、象征派,以至于七月派、九叶诗人的诗歌运动,等等,中国新诗的发展经历了艰难的探索。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一环,即左翼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新诗,在艰难的革命历程中经历了自身的洗礼与蜕变。无论编撰的文学史,还是在文人学者、诗歌研究者的诗评与诗集编撰的书写中,苏区新诗在不经意间失却了应有的重视。这样一个在重要的战争年代出现的新诗,人们不应当也不应该忽略它的真实存在,何况这是发生在具有不平凡革命战争年代并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与价值建构的新诗。
一 问题的提出:苏区新诗的滥觞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力量遭到惨重的削弱。为了积蓄力量,重振旗鼓,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从城市转向了农村,从而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广袤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1931年秋,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之后,中央苏区不断发展壮大,红军和地方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特别重视苏区文化建设,重视工农思想。所属的各级文化、宣传部门和各种文艺团体中,知识分子也逐渐增多了。正如瞿秋白所指出:“普洛文艺要是自由的文艺,因为调动新的力量到这种文艺的队伍里来的,并非贪欲和声望,而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对劳动者的同情。”1《瞿秋白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62页。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爱好文艺抑或本来就是从事文艺工作的。他们一面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一面拿起笔来从事革命文艺创作。真是能文能武。如戏剧家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著名作家成仿吾以及青年学生石联星、彭舜华等,大都是从上海的“左联”投奔到中央苏区的。同时,苏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艺大军有成效的战斗,以及苏区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也给了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以很大的鼓舞。他们写散文、编剧本,有的创作新诗。瞿秋白到苏区担任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兼管艺术局的工作后,除了领导苏区的戏剧运动外,对于诗歌创作也十分重视与关心,并且身体力行地创作了一系列的新诗。他特别强调新诗或歌词的创作应努力做到大众化,指出:“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曲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就能流传。”2参见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50年6月18日。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倡诗歌的大众化,更为主要的是在创作实践上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榜样。
事实上,十年内战时期,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分割成两个阵地:一是苏区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革命文艺部队;二是国统区内以鲁迅为首的由左翼作家组成的革命文艺部队。这两支文艺队伍看似不同,但他们的共同的革命理想与目标是一致的,即对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正如傅钟回忆:“党中央和上海的左联,曾经不断输送文艺干部和青年学生到根据地和红军部队里。尤其是左联派代表到根据地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更加强了这一工作。”1转引自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85、189~190、183页。茅盾就曾在左联《文学导报》上发表《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一文,热情地赞扬工农革命运动在苏区的蓬勃发展。苏区知识分子创作的诗篇题材广泛而新鲜,感情真挚、热烈而不空泛,既着眼于现实的斗争而又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它正确地反映了工农兵群众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使新诗开始走上了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左联在1931年发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指出:“江西苏维埃区域的革命工农和红军空前的革命力量,打败了国民党三十万大军的三次围攻,组织了工农兵的政权——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面对这一新的大好革命形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定要以新的阵营,以最大的努力,负起革命所提出的巨大而迫切的要求”。号召革命文艺工作者应该“在文学的领域内,宣传苏维埃革命与组织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斗争”,并要求“作家必须抓取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民众生活,红军及工农群众的英勇的战斗的伟大的题材”。2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苏区文学研究室编著:《江西苏区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6、108页。1933年,在苏区的报纸杂志上就出现了许多新诗,通过诗的形式来抒发革命的感情。同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农兵的歌唱,又激励着他们投入革命的创作生活,这样新诗就以战斗的姿态出现了。
二 “五四”新诗的拓展与苏区诗歌的革命叙事
(一)“五四”新诗的拓展
苏区的新诗创作,一方面继承了五四运动以后新诗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又较之“五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新诗创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主要基于两方面逻辑。一是创作者参加了实际的革命斗争,具有深厚的革命情感;二是新诗的内容反映了工农兵群众的思想,新诗成为革命斗争的一种工具和斗争的尖锐武器。丁玲说:“我们要从各方面发动使用笔,用各种形式,那些最被人欢迎的诗歌、图画、故事等等去打进全中国人民的心的阵地,夺取他们,来站在一个阵线上,一条争取民族解放的战线上。革命的健儿们!拿起你的枪,也要拿起你那一支笔!”1转引自汪木兰、邓家琪编:《苏区文艺运动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页。然而,应该看到“五四”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新诗运动,都未能做到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因为从“五四”时期到大革命时期,新诗运动的主要参加者虽然向往革命,讴歌革命,但大都是出于对革命未来的想象。而苏区新诗的作者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进入根据地的革命知识分子。这种结合虽是初步的,但为以后新诗运动的继续发展,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其中,瞿秋白的《赤潮曲》最为突出:
赤潮澎湃,
红霞飞动,
惊醒了工农,
中国工农举起了红旗,
高声歌颂,苏维埃万岁!
猛攻,猛攻,捶碎帝国主义国民党,
奋勇,奋勇,为我们工农群众的解放。
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
同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
为解放而奋斗,看赤潮万丈涌。
该诗原系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1934年到苏区后,作了修改并谱了曲,作为战歌在群众中流传开了。它处处显示了诗人坚强的革命信念和豪迈的革命气概。瞿秋白是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卓有成效的革命斗争经验激励苏区人民勇敢地投入战斗。
在苏区的新诗中,还有不少是反映苏区军民的战时生活的诗,如《在列宁室》《青年士兵与快枪》《月夜行军》《开赴前线》《插秧曲》等。《青年士兵与快枪》是一首写得富有情趣、别具一格的抒情短诗,它抒发了红军战士十分珍爱手中武器的思想感情,赞美了红军战士高尚的革命情怀:
普通人的恋爱是姑娘,
我的恋爱是快枪。
她能杀敌冲锋,
不象姑娘们的娇模娇样,
我爱她,我爱她英勇的心肠。
我的灵魂交给她,
我的生命寄托在她的身旁,
夜间睡觉时把她靠近我的胸膛。
我爱她,我爱她生死不忘!1转引自张全之:《“苏区”与“上海”:中国左翼文学的双重面影》,《中央苏区文艺研究论集/中央苏区文艺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80~81页。
苏区的诗歌中占绝大部分是对革命的讴歌,充满着积极的、昂扬的革命情调,它积极地拓宽了“五四”新诗的创作内容。
(二) 苏区新诗革命文艺对左翼文学的影响
中共建立苏区革命根据地后,紧紧依靠革命文艺的力量,做好革命的舆论与宣传工作。中共掌握着革命的领导权,牢牢地把握着革命文艺的运动方向与话语权。从1931年秋到1932年春,左联一些负责工农文化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除了为上海工人夜校编写工人读本外,还曾为中央苏区编写工农教科书和其他通俗读物,这对于苏区群众的政治启蒙与文化的普及,是很有益的工作。正是由于苏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革命文艺部队与国统区内由左翼作家组成的革命文艺部队的相互呼应与配合,从而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使党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不断地巩固与壮大。他们利用战斗间隙对红军加强政治和军事的训练;还采用教唱和讲解歌词内容相结合的方式,如“国际歌”和“红军纪律歌”的教唱和讲解,既提高了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又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加强了部队的组织性与纪律性。苏区还进行了军中游戏、自编自唱的活动,大大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启发教育了群众,使之勇敢地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
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的时候,革命的反抗也没有停止过,并且越来越高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倡导与论争还掀起了高潮,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也形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潮流。“普罗(proletariat译音的缩写)诗派”也随之形成了。如果说1927年前只有郭沫若、蒋光慈等人创作革命诗歌的话,那么1927—1930年间作者队伍则大大扩展了。很多诗人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诗歌创作,一些革命诗歌社团、刊物纷纷出版和发表革命诗集与诗歌。创造社诗人郭沫若、段可情、黄药眠、龚冰庐、周灵均,太阳社诗人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殷夫等表现得更为激进。普罗诗派坚持诗歌的革命性原则,批判以诗为消遣的、吟风弄月的玩物,逃避严峻的现实的错误倾向,对其他诗派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也不能罔顾这么一个事实,当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带领群众打击一切反动力量的时候,一些左翼文学作家也在寻找自己的“朋友”和“敌人”。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的左翼文人也开始瞪大眼睛密切地寻找自己的“朋友”。他们发现的第一批“敌人”是从“五四”走来的“资产阶级”作家:鲁迅、周作人、叶绍钧及胡适、陈西滢等。他们感觉到,这些早已成名并占据着文坛要津的作家成为他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学启蒙的障碍。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对这些在他们看来代表封建势力(如将鲁迅称为“封建余孽”)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文人的批判,为革命文学铺路,从而建立文化和文学上的“根据地”。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左翼作家在1928年的批判性突围,还是没有分辨清楚真正的敌人和朋友,尤其是对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攻击,很快就显示出了片面性。为了纠正这一错误,1930年,在中央苏区力量的干预下,他们组成了新的战线——左联。它并非一般性的文学社团,而是一个“政党”式的组织,具有高度的政治色彩,并与苏区高层领导和苏联文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左联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文学活动,推动整个现代文学进入一个先锋色彩十分强烈的时期。在理论上,左联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全面而系统地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左翼诗歌成为时代的主流。它造成了一种学习革命诗歌与革命文艺论著的浓厚氛围,普遍提高了中国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作为革命文艺的苏区新诗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它产生于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之中,又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发展,它为工农兵群众所创造,又为其所利用,它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反动派的有力武器,它继承和发展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革命传统,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其中心内容。苏区新诗是世界无产阶级左翼文学的一部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艺家纷纷投奔革命苏区,为苏区的文艺传播、理论宣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 马克思文艺理论大众化与苏区新诗语言的通俗化
“五四”以后,新诗在形式和格律方面的创造焕然一新。许多革命诗人创造了多样的自由活泼的诗体。显然,这种诗体的大解放,使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然而,由于过分地从西洋诗歌中去找出路,而忽视了传统诗歌的优美、精练的优势,尤其,对人民口头创作的新鲜活泼、通俗易懂的特色缺乏相应的重视,使新诗欧化的现象十分明显。因此,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形式不足。正如瞿秋白所认为的,无产阶级文学是大众的文学。新诗白话应当变成民众的文艺。因此,瞿秋白认为,新诗首要的问题就是去“变”。怎样去变?这就需要“向群众去学习”,就是“怎样把新诗白话文艺变成民众的”问题。瞿秋白等人在中央苏区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理论,它要求文艺要以一种大众化的形式对党的革命政策进行宣传,从而达到大众化的效果。而新诗作为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革命体裁的实践者,实现了自身的大众化,成为革命宣传的工具。瞿秋白进一步认为,“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无产阶级大众文艺,应当向那些反动的大众文艺宣战。可以造成新的群众的言语,站到群众的‘程度’上去,同着群众一道提高艺术的水平”1《瞿秋白文集》第1卷,第463~464页。。苏区的新诗既继承了“五四”以后新诗的自由活泼的表现形式,又基本上克服了欧化的倾向,使新诗在民族、大众化方面有了开拓式的发展。苏区新诗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一方面,苏区新诗中反映的是工农兵生活与革命斗争的内容;另一方面,苏区新诗语言是地道的群众语言。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新诗为了增强诗歌的宣传鼓动效果,特别注意学习和吸取苏区民间歌谣的长处,几乎摒弃了欧化的倾向,它风格朴实、明快而音节自然流畅,既可以读还可以唱,真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实质上,它为新诗朝着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具体而言,当革命文学提出之后,主张“到民间去”,“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1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时,诗人、文学家从“艺术之宫”走出来,如何用人民的语言去表现革命实际的问题便凸显出来了。革命的大众化文艺,如何“拿‘读出来可以听得懂’做标准”,“应当运用最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也就是“最广大的民众有听得懂的可能的白话”2宋阳(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创刊号,1932年6月10日。来写文章、作诗,去反映现实的革命斗争,表现革命的英雄,这就是一个非常实际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央苏区的新诗在大众化方面,尤其在运用最广大的民众能听得懂的白话口语进行作诗方面,是大踏步地向前跨进了一步,是卓有成绩的。苏区的新诗创作在初步实现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方面以及努力朝着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方面所积累的经验,显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四 苏区新诗的价值与经验
苏区新诗是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战斗号角,它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生长在翻身求解放的工农大众之中,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描绘了土地革命时期的时代风貌,体现了暴风骤雨的时代精神,塑造了富有阶级与时代特征的新的工农兵形象。但是,有人因为它太“土”而否定其审美价值,丁玲早就在《文艺在苏区》中说过:“这初初的蔓生的野花,自然还非常幼稚,然而却实实在在生长在大众中,并且有着辉煌的前途是无疑的。”3参见吴海、曾子鲁主编《江西文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53页。一个世纪过去了,穿过历史的隧道重新审视当时的诗歌,它虽不精美,但很崇高,始终奏响着时代的主旋律,跟随着革命大军,走向理想的彼岸,这种向上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发扬。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如毛泽东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鱼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陈毅的《反攻下汀州龙岩》《梅岭三章》《赣南游击词》;蔡会文的《好事近·渡桃江》等,描述了红军在开辟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中,进军神速、所向披靡的雄姿,“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表现了革命的大无畏精神。1转引自刘国清:《中央苏区文学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苏区的新诗创作所取得的成就,虽然不如苏区的歌谣创作和戏剧创作所取得的成就那样突出,但苏区的新诗创作以其鲜明的革命内容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在193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无疑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但是,苏区新诗的经验教训也是明显的。正是由于当时苏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之中,创作时间不充裕;兼之由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苏区的新诗作者通常都是为了及时配合某项政治任务而创作的,因此,有不少作品在题材提炼、艺术概括、语言的精练与含蓄等方面,都未能仔细琢磨和用心推敲,艺术上显得比较粗糙。由于当时诗歌的宣传观念,过分夸大诗歌的宣传作用,必然以取消它的形象性特征为代价。他们以为这些“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具有某种想当然的煽动性而引以自信与自豪,着重于诗歌为政治服务的表现功用,而忽视了诗歌自身的内在艺术的追求,以情感表现为归趋,其社会效应不在教育人们的直接行动,而是通过潜移默化去感染读者的心理、情感。也由于对宣传效应的过于倚重,诗的形象性受到消损,使之直接演绎图解政治,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有些作品并没有经过审美意识的过滤和艺术创作的醇化,就急于转化为革命口号或政治鼓动标语,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早期苏区新诗由于注重的是“白话”而不是“诗”,缺乏诗的审美感染力,结果导致了严重的“非诗化”倾向,失之于对诗美特性的轻视和忽略。因此,苏区的诗歌留给人们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沉重而深刻。革命诗歌的生命在于诗人的使命感和审美感的统一,但普罗诗人在强烈的使命感和审美感之间出现了裂痕和倾斜,诗美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而最终也伤害了诗歌本身。这就是苏区诗歌成败得失昭示的最根本的经验和教训。
苏区的诗歌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它荡涤着人们的心灵,具有崇高的革命情结。一方面,因为革命斗争与普及提高的需要,用白话创作的诗歌显得非常彻底;另一方面,一些革命领导人,因为他们深厚的古文修养而创作的旧体诗的出现,又对“五四”以来新诗与旧体诗的对立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这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也为多元共生的新诗发展打开了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