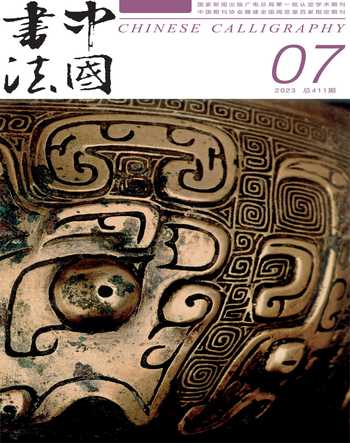张怀瓘书论中旨在“达节”的阴阳化生思想
2023-09-14王仲凯
王仲凯
关键词:张怀瓘 阴阳 达节
张怀瓘在《书断·评》中自言其书论“庶乎《周易》之体”。《周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道以阴阳含纳万有,孕育无穷变化于其中。这种阴阳化生的理念渗透于张怀瓘的书法理论之中,使其书道思想充满了莫测生机。其中就包含了崇变尚和、阴阳动态协调和旨在“达节”的书法创作理念。
崇变尚和
张怀瓘认为书法具有“随变所适”的特点,此为书法“达节”的基本条件。他在《书断·评》中认为书法因具有阴阳变化的丰富性“于刚柔消息,贵乎适宜,形象无常,不可典要,固难评矣。”难以依据某种一致的标准做出评价。《系辞下》言《易》:“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1]蔡渊解道:“典,常也。要,约也。其屡变无常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而已。”[2]这种“唯变所适”的思想在书法创作中就体现出了阴阳权宜之变的复杂性和不测性。张氏在《评书药石论》中讲:“圣人不凝滞于物,万法无定,殊途同归,神智无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着,至于无法,可谓得矣,何必锺、王、张、索,而是规模?”又引《系辞》曰:“物极则返,阴极则阳,必俟圣人以通其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如其所言,他主张书之为道当超拔于物象、法相之外,以无法为至法,穷则为变,如此方能得其阴阳化生的随机妙用。这也体现了张氏注重在书法创作中的性天之明畅,落笔才会具有“随变所适”的灵动变化性。
张怀瓘的书法理论还蕴含着阴阳和合的思想,为书法“达节”的必然要求。《系辞下》曰:“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3]《荀子·天论》曰:“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而成。”[4]万物化育,其中皆蕴含阴阳冲和之理,“和”为生生之理必然的体现。张怀瓘在《评书药石论》中有言:“惟题署及八分,则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萧散,恣其运动。”书法创作当呈现出一种活泼健康,充满生机意趣的精神风貌。同时他也提到“书能入流,含于和气,宛与理会,曲若天成”。可见书法之生机意趣正是合乎造化,得其天理的生发,其中蕴含一种天然和洽的风神韵致。“含识之物,皆欲骨肉相称,神貌洽然。”书道亦需得此骨肉相称之和,书写才会有“神貌洽然”之感。张怀瓘在《书断》中对欧阳询与虞世南的书法有这样的论断:“欧若猛将深入,时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选,罕有失辞。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他认为欧阳询之书“森森焉若武库矛戟”,筋骨外露而乏肉,虽刚劲然寡于润色,“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而虞世南的创作内涵筋骨而不显之于外,有使者之风。“外露筋骨”的呈现基于一种物我相对待的思维方式和与物“相刃相靡”的有为的待物方式。而“君子藏器”则是一种“含章可贞”的生命涵养,其所含摄的章美之道是生命内蕴的,本体光辉的显现,这一光辉“光而不耀”,含有一种寻常日用中的蕴藉之意,为“日用而不知”的冲和之生意,透显于书法即为阴阳和洽的“含于和气”之风貌。《周易正义》疏云:“性者天生之质,正而不邪;情者性之欲也,言若不能以性制情,使其情如性,则不能久行其正。”[5]故而唐君毅有言:“万物无永相矛盾冲突之理,而有由相通感以归中和之理。”[6]以性天中正冲和之意观照协合种种情态,即为书法创作中的“性其情”,可使书法之表现刚柔并济,兼相为力,化成合天气象。
动态协调
张怀瓘阴阳化生的观念还体现在其阴阳动态协调的创作思想中,这也是书法“达节”的题中之意。在张怀瓘书论中不乏对峻险惊奇之书风的赞叹。如其《书议》中所言:“观之者,似入庙见神,如窥谷无底。俯猛兽之牙爪,逼利剑之锋芒。”他在《文字论》与友人的交流中对自身书法创作也有夸张意味的描述:“或若擒虎豹,有强梁拏攫之形,执蛟螭,见蚴蟉盘旋之势。……气势生乎流便,精魄出于锋芒。观之欲其骇目惊心,肃然凛然,殊可畏也。”如此雄奇峻險的书法审美和唐代雄健昂扬、包纳万象的时代风貌是浑然相契的。
张怀瓘在《书断序》中讲书法“耀质含章,或柔或刚”。虞世南在《笔髓论》中讲到:“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秉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7]书法创作者秉承天地化育之心,不离道域而将创生之力与终成之力相挽接,其刚健之雄勇在坤道的凝聚之下得以放旷于笔墨,即有如“擒虎豹”“执蛟螭”般豪放之胸襟,兼具“入庙见神”“窥谷无底”的探赜之幽怀。正如其《书议》所言“岩谷相倾于峻险,山水各务于高深”,纵横天地而不失其所。《系辞下》有言:“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8]由乾而知险,以其通达见神变峻险惊奇;由坤而知阻,以其贞固得万类成其所是。此惟依于道心之生机方能体会其中的天地化育之理,一味任性使气,创作不出伟大而深沉的艺术作品,必于阴阳动静间得一协调,才能彰显雄奇峻险之伟傲又不失于疏狂,其中自然蕴含一种富于动势的平衡,表现为刚柔相济贯穿始终的生命张力与其中所涵摄的阴阳冲和之生意。
张怀瓘还提到:“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资运动于风神,颐浩然于润色”,刚柔相济,阴阳相生,书法作品才会焕发出充沛的生命力,呈现出无穷丰富之美感。这也反映出道心之用在书法创作的动态协调之中蕴涵无穷的生发力和创造力的特点。
旨在“达节”
张怀瓘书法理论中“达节”的观念为其书法阴阳化生思想的根本指向,也是其书道崇变尚和与重视阴阳动态协调的根本愿旨之所在。张氏评张芝书法“又创为今草,天纵尤异,率意超旷,无惜是非。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于造化,至于蛟龙骇兽奔腾拏攫之势,心手随变,窈冥而不知其所如,是谓达节也已。”《周易正义》疏有言:“以物得开通谓之道,以微妙不测谓之神,以应机变化谓之易”[9]可见易道之理中蕴含着微妙不测发乎道心的神变之用,此中生发无不与自然天道微妙之生机相应契,如此方有张氏所谓“天纵尤异”“心手随变”的“达节”之功,体现了书道发乎性天之机以成其阴阳之变的思想。其用则如庄子所谓庖丁解牛,合于天而应于事,无所不中,可谓达节。正如张氏所言:“其(张芝)章草《金人铭》可谓精熟至极,其草书《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合于自然,可谓变化至极。”书法创作达节的意义正在于落笔每每恰到好处,合于自然之理,犹若造化生成。他对锺张与王羲之还有“动无虚发”“百发百中”之评,皆为心手随变,而能每每挥毫恰如其分的达节之意。《周易正义》解“一阴一阳之谓道”,疏曰:“故在阴之时,而不见为阴之功;在阳之时,而不见为阳之力,自然而有阴阳,自然无所营为,此则道之谓也。”“故至乎「神无方,而《易》无体」,自然无为之道,可显见矣。”[10]此言《周易》阴阳化生的中道之理发之于道心自然之用,而非出于刻意营求的有为之为。张氏在《评书药石论》中言书道则曰:“为书之妙,不必凭文按本,专在应变,无方皆能,遇事从宜,决之于度内者也。”,由以上可见唯有发乎性天之明“自然”之理,以决之于度内之“衷”,不失其微妙之致,临事从宜,才能发用“殆同机神”,而有阴阳化生的达节之功。书道与易理于此一也。
此外,对阴阳偏执的化解乃是书法“达节”的根本保证。张怀瓘在《评书药石论》中提到当时书法风尚出现的一些问题:“从宋、齐以后,陵夷至于梁、陈,执刚者失之于上,处卑者惑之于下,肥钝之弊,于斯为甚。贞观之际,崛然又兴,亦至于今,则脂肉棱角,世俗相沿,千载书之季叶,亦可谓浇漓之极。”这种阴阳失衡的“脂肉棱角”之病,究其根源,一是创作者为“世俗相沿”之书法形貌所束缚,主体自身的精神性不得彰显,故而生机不能全然展现;二是创作者为对自身的认知所困,出现所谓“执刚者失之于上,处卑者惑之于下”的障碍。其弊病皆在于执于一偏,滞其生机,不能通源达变。张怀瓘言:“书亦须用圆转,顺其天理”就是说书写应回归于天地化育之道心,用笔圆转自如舒展得开,不滞其生机,有活泼泼的生命气象寓于其中,其创作才能不失自然之理,而成达节之用。这就需要书法创作者以天人相合之大我与天道之运化相契会,不为小我之妄执所拘,不为相状所蔽,才能书写合乎天道而不陷入于“脂肉棱角”之类的阴阳偏执之病。张怀瓘无所偏执的书道思想还体现在对书法文质关系的理解中。在《六体书论》中他提出“质者如经,文者如纬”。观其《书断》对王僧虔和庾肩吾分别有“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评价。可见文质两端作为阴阳的表现亦不可偏废,而当有“耀质含章”的整全之态。故而他提出这样的书评原则:“固不可文质先后而求之,盖一以贯之,求其合天下之达道也。”其中“一以贯之”的书评理念正是道心发用的体现,其中就寄托了张怀瓘书法理论旨在“达节”以合乎阴阳化生之道的书道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