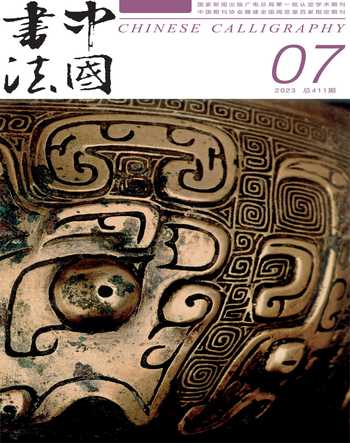“行人”与南书北渐
2023-09-14王吉凯
王吉凯
关键词:行人 书风 融合 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因其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了军事、地域上的对立,后之论书者亦多以“南北不相通习”来否定南北之间的书法交流。然从南北朝时期的“行人”现象来看,其交流互动可谓频繁,这种现象同样可反映到书法艺术方面,其中又以南朝对北朝书风影响最为明显。本文以南北朝时期“行人”为线索,围绕“行人”以不同视野、不同角度来剖析南北朝时期的南书北渐现象。
南北朝时期的"行人"互动
所谓“行人”指古代外交官的一种称谓,是代表本国同他国进行沟通交流的使者。黄宝实《中国历代行人考》称:“古之所谓行人,即今之外交官。居则摈相应对,出则朝觐聘会。”[1]阮元作“南北二论”所提出的基本观点是依据地域来划分的,其所谓“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羲、献诸迹,皆为南朝秘藏,北朝世族岂得摩习!”[2]在阮元看来,南北书法之所以可分为两派,是因为南北世族之间不相通习,流行于南朝的王系新体被作为秘藏,无法传入北朝,故南朝之帖与北朝之碑判若江河。
然以南北朝之间的行人现象来看,南北之间交流互动之频繁程度远非阮元所谓之“南北世族不相通习”。据郑钦仁等编著《魏晋南北朝史》载南北朝时期行人情况:“前后交聘见于记载的有八十次,双方互派遣使者姓名可考者也有一百一十六次。”[3]劉永涛《行人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一文载南北朝姓名可考者行人一百一十九次。[4]笔者据黄宝实《中国历代行人考》整理出南朝出使北朝行人凡九十次,北朝出使南朝行人亦有八十八次,且南北双方出使行人多是主动派遣,以南朝刘宋为例,仅《北史》所载“宋人来聘”和“使于宋”字样就各有二十七次之多。
行人作为使者出使别国,故南北双方对行人之选择极其重视,《二十四史札记》云:“南北通好,尝籍使命增国之光,必妙选行人,择其容止可观,文学优赡者以充聘使……其邻国接待聘使,亦必选有才行者充之。”[6]因行人肩负使命,代表国家形象,其言行举止必合乎礼节,所以行人必“妙选”,出使国选文学优赡者,而接待国亦必选有才行者,故行人必博学通识。阮元《南北书派论》以南北两派皆出于锺繇、卫瓘,北派由崔悦、卢谌、高遵等传至欧、褚,其称:“北朝望族质朴,不尚风流,拘守旧法,罕肯通变。”[7]在阮元看来北朝望族“拘守旧法,罕肯通变”,加之“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这也正是造成南北两派书风判若江河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以南北朝行人的选拔标准来看,北朝所派遣出使南朝之行人却恰是在北方名门望族中选拔,其中尤以崔、卢、李、郑等望族为显。黄宝实《中国历代行人考》所谓:“南北朝行人之选,既重门第,兼尚风华,浸暇遂为甲族世业,寒素之士,罕得与焉。要而言之,清河博陵之崔,太原之王,范阳之卢,赵郡之李,荥阳之郑,杜陵之杜,北地之望也。”[8]北朝行人在崔、卢、李、郑等名门望族中演为行人世家。崔氏一门行人有崔长谦、崔劼、崔子侃、崔瞻、崔儦、崔彦穆等,卢氏一门有卢玄、卢度世、卢昶、卢元明、卢思道等,李氏则李骞、李同轨、李浑、李湛等,郑氏有郑羲、郑伯猷、郑道邕等,四门之行人竟多达三十余人。南北朝时期双方行人往来最早见于史料是南朝刘宋武帝永初二年(四二一),南朝派遣行人沈范、索季孙出使北魏,[9]南朝刘宋时期派遣行人出使北魏达三十五次,北魏派遣行人出使南朝亦有二十八次,足可见当时南北双方行人往来之密切。
“行人”与南书北渐
南北朝之行人因“妙选”之故皆出名门望族,同样作为接待国接待行人之“主客”的铨选标准亦与行人相似,故无论出使国之“行人”还是接待国之“主客”,必是身份显赫、博学通识之人,其中不乏善书者。据《北史·李谐传》载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五三七)曾派遣李谐、卢元明、李业兴出使梁朝,梁武帝则使朱异为主客接待,“梁武帝使朱异觇客,异言谐、元明之美。谐等见,及出,梁武帝目送之,谓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此等何处来?﹂谓异曰﹁过卿所谈。﹂是时邺下言风流者以谐及陇西李神儁、范阳卢元明、北海王元景、弘农杨遵彦、清河崔瞻为首,初通梁国,妙简行人……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10]其中南朝主客朱异即有书名,《述书赋》称:“彦和连环,迅不可及。如过雨之奔簷霤,飞燎之赫原隰。”[11]《书小史》称其“尤善草书”,北朝行人在与南朝主客的交往过程中,以诗文唱和为常态,其中记述文字,睹其笔迹也必在情理之中,这也无意中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南书北渐。
刘永涛《行人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一文在谈及北朝崔、卢、李、郑四门行人时亦称:“四门行人著述有集者有之,博学多才、涉猎群书者有之,通晓经传、谙熟文史者有之,才藻富瞻、能文善写者有之,无文藻者甚少。”[12]《北史·列传》载“魏初重崔、卢之书。”[13]况魏初之时崔、卢世家通婚,以卢玄为例,其于北魏太武帝延和二年(四三三)兼散骑常侍出使南朝刘宋,卢玄父卢邈、祖父卢偃、曾祖卢谌皆有书名,《北史·卢玄传》载:“谌父志法锺繇书,子孙传业,累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14]其祖父卢偃“博学善隶书,有名于世”[15],其父卢邈“善草迹”,可以想见卢玄亦当受家学熏陶。而崔浩即为卢玄之表兄,卢玄虽无书名,若考虑其家学渊源和崔、卢两家之联姻,于书一艺也必然通晓一二。在崔、卢、李、郑四门行人中,虽无史料记载有以书名世者,但以上述四门尤其是崔、卢世家在北朝的社会声望和文化地位来看,书史虽不载其名,但也必为善书者。上述崔、卢、李、郑四门行人出使南朝并没有直接材料表明和南朝有关于书法艺术的互动,但依然可以从其他行人中看出端倪。
北朝书家蒋少游与李彪曾于太和十五年(四九一)被孝文帝派遣出使南齐,蒋少游在阮元《南北书派论》中被列为北朝书家,《魏书·蒋少游传》:“蒋少游,乐安昌博人也,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吟咏之际,时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而名犹在镇,后被召为中书写书生。”[16]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少游敏慧机巧,工画,善行草书。”[17]蒋少游与李彪此次出使南齐似有各自任务,李彪论丧服,而蒋少游则是艺术交流,这一点从《南史》中可以看出,《南史·崔祖思传》载:“永明九年(四九一)魏使李道固及蒋少游至,崔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来必令摹写宫掖﹂,未可令反,上不从,少游果图画而归。”[18]蒋少游出使南齐“摹写宫掖”,崔祖思建议齐武帝萧赜阻止蒋少游,而齐武帝却令蒋少游果图画而归,可以看出当时南北双方在艺术上是存在互动的。
关于蒋少游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称其“善行草书”,这在史料对北朝书家的记载中是不曾出现过的,《北史》称魏初重崔、卢之书,但多称其“善草隶”或“草书”,而绝少“行草书”,如崔宏“尤善草隶、行狎特尽精巧”,崔浩“体势及先人,而巧妙不如”,崔衡“学浩书,颇亦类焉”;卢鲁元“善正隶书”,卢伯源“习家法”;江式“篆体尤工”,江顺和“亦工篆书”等。[19]其二,蒋少游与李彪出使南齐的接待主客刘绘亦善书,《南齐书·刘绘传》称其“聪警有文意,善隶书。”[20]庾肩吾《书品》列刘绘为“中之下”,《书小史》称其:“官至司马,从事中郎,撰能书人名一卷,尝自云﹁善飞白书﹂,言论之际,颇好矜知。”[21]可以看出,刘绘当时在南齐亦有书名,而蒋少游出使南齐时,齐武帝萧赜使刘绘为主客接对,加之二者皆善书且以书名显,在交谈过程中谈及书法艺术或蒋少游“果图画而归”中含有南朝书画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此外,北魏时期慕容白曜攻占刘宋三齐之地,将原属南朝的能工巧匠迁入平城,“平齐民”“青州民”和相当一部分投奔北朝的南朝书家也为南书北渐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上述蒋少游即属“平齐民”之列,除蒋少游外,尚有刘芳、李思穆、王世弼、庾道、夏侯道迁等俱是由南朝入北魏之善书者,《魏书·刘芳传》:“慕容白曜商讨青齐,芳北徒为平齐民……芳常为诸僧拥写经论,笔迹称善。”[22]刘芳子刘懋亦有书名,“芳从子懋,字仲华。祖泰之,父承伯,仕于刘彧,并有名为。懋聪敏好学,博综经史,善草隶书,多识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员外郎,迁尚书外兵郎中,加轻车将军。”[23]《魏书·李宝传》载:“思穆字叔仁,父抗。自凉州渡江左,仕刘骏,历晋寿、安东、东莱三郡太守。思穆有度量,善谈论、工草隶,为当时所,太和十七年(四九三)携家累自汉中归国,除步兵校尉。”[24]《魏书·王世弼传》:“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刘裕灭姚泓,其祖父从裕南迁。世弼身长七尺八寸,魁岸有壮气,善草隶书,好爱典坟。仕萧鸾,以军勋至游击将军,为军主,助戍寿春遂与叔业同谋归城。景明初,除冠军将军、南徐州刺史。”[25]《魏书·夏侯道迁传》称夏侯道迁“ 历览书史, 闲习尺牍札翰”,[26]庾道与夏侯道迁一起迁入北魏,《魏书·江悦之传》称:“时有颍川庾道者,亦与道迁俱入国,虽不参谋,亦为奇士,历览史传,善草隶书。”[27]由南入北之善书者史籍所载甚多,其中不乏南朝皇室,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隋统一南北。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首先《魏书》所谓之“隶”即为今之楷书,宋王应麟《玉海·小学》云:“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至欧阳《集古录》误以八分为隶书。自是凡汉石刻皆目为汉隶,东魏大觉寺碑题额曰隶书,盖今楷字也。”[28]又明张绅《法书通释》亦云:“古无真书之称,后人谓之正书、楷书者,盖即隶书也。”[29]因此,《魏书》所载由南朝入北士人之“隶”即为当时南朝所流行之王系新体,他们将这种流行于南朝的楷书书风带入北朝并结合北朝楷书雄浑朴厚的特质,并最终促成北朝洛阳体书风的形成。再次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谓之蒋少游“善行草书”和《魏书·夏侯道迁传》所谓之夏侯道迁“习尺牍札翰”,此二者当为同一种书体,结合二人俱有南朝背景和蒋少游之行人身份来看,二者所习当是南朝所流行的王系新体。
至于南朝书风北渐的实物,则可以从一九九六年出土于山西大同石家寨村的司马金龙墓中找到佐证,墓中有一件漆画屏风,上有题记,书体为楷书,按墓主司马金龙之卒年,屏风题记当在太和八年(四八四)之前。从屏风题记来看,则与南朝《明昙墓志》《萧融及太妃王慕韶墓志》书风相类,虽仍存少许隶意,但在笔画使转处可以看出其笔意节奏鲜明。“此屏风的绘画风格,与传世著名的顾恺之《女史箴图卷》有不少共通之处……因此,这件屏风,很可能是东晋制作的,或是司马楚之在亡命之际所带的晋见礼之一,或是落入北人之手的姬辰车载而入的东西之一。”[30]考墓主司马金龙之父司马楚之,楚之父司马荣期为东晋益州刺史,司马楚之十七岁时归顺北魏,而此屏风则极有可能是司马楚之归顺北朝时所带之物,继而又传至司马金龙。又《北史·崔暹传》载:“梁、魏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唯寄求佛经。梁武帝闻之,缮写,以幡花宝盖赞呗送至馆焉。”[31]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南朝书风已渐入北朝,只是当时在北魏初重崔、卢之书的笼罩下并未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至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才得以凸显
行人影响下的北朝新体
南北朝行人出使短则一两月,长则数年,而且行人之间往往也仰慕文采而建立深厚的友谊,即使复命还朝也多保持书札往还,其中亦不乏善书者。如南朝行人庾信、徐陵皆曾出使北朝,且二人俱有书名,《九品书人论》称庾信“行及草品中之中”,《书小史》称其“善行书”。[32]张怀瓘《书断》则称徐陵“善正书”。徐陵于梁武帝太清二年(五四八)出使东魏,直至北齐天保六年(五五五)乃还,曾在北朝滞留七年之久。徐陵在北朝滞留期间,与北朝文士魏收、裴让之、杨愔、李昶等多有交往,其中李昶与徐陵又多书信往来,李昶在写给徐陵的书信中自称:“弱龄有意,颇爱雕虫,岁月三余,无忘肄业,户牖之间,时安笔砚。”[33]李昶虽无书名,但其自称“弱龄有意,颇爱雕虫,户牖之间,时安笔砚”,可以看出其亦暇弄笔翰,且与徐陵又多书信往还。
此外,从南北朝时期的诸多碑版中亦可窥见南北书风之相似处,晚清碑学书家康有为、曾熙、叶昌炽等人也多以此来驳阮氏南北分派之说。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對比了诸多南北朝碑版,然其书风之相似处尽显,故其称:“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余考之,北碑中若《郑文公》之神韵,《灵庙碑阴》、《晖福寺》之高简,《石门铭》之疏逸,《刁遵》《高湛》《法生》《刘懿》《敬显儁》《龙藏寺》之虚和婉丽,何尝与南碑有异?南碑所传绝少,然《始兴王碑》戈戟森然,出锋布势,为率更所出,何尝与《张猛龙》、《杨大眼》笔法有异哉!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碑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也。”[34]曾熙在《书画题跋》中亦称:“自仪征阮氏创分南北书派,海内学者多沿其说,熙窃以为惑矣……盖南北碑志《二爨》与《中岳灵庙》同体,以刚胜;《李洪演造像》与《曹娥》同韵,以柔胜;梁《程虔神道》与《崔敬邕志》同取掠空之势;南帖中《黄庭内景经》与《石门铭》同擅纵击之长,安见南北书派判若江河?”[35]南北朝碑版之中,有南北与北碑风格绝类者,如二爨之于《嵩高灵庙碑》;亦有集南北之长者,如近世出土之《霍扬碑》。
沙孟海在《中國书法史图录上册分期概说》中称:“北碑结体大致可分为﹁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两个类型……《张猛龙碑》《根法师》、龙门各造像是前者的代表,《吊比干文》《泰山金刚经》《唐邕写经颂》是后者的代表。”[36]就整体风格来说,“平画宽结”类多为平城体书风,而“斜画紧结”类则为洛阳体,而孝文帝汉化改革,北魏都城由平城迁至洛阳,书风亦为之一变,洛阳体“斜画紧结”类风格的形成则正是南北书风融合的产物。刘涛在谈及孝文帝汉化改革所带来的书风影响时称:“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以后,北方的南士获得重用,他们带来的南朝书风也就据有指导地位,于是﹁斜画紧结﹂的今体楷书成为铭石书的正体而迅速普及,江南盛行的﹁草隶﹂书法也风靡北方,这些南士成为北魏新书风的主导者。”[37]王玉池《王献之〈廿九日帖〉与“北碑”等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北碑中存在体势特征与王献之《廿九日帖》极为相似的字例,并认为这种现象“应与北魏统一北方和刘宋建国后,南方诸朝和北魏联系日多以及魏孝文帝主张汉化有关。”[38]就北魏时期孝文帝汉化改革迁都洛阳后的书风转变来说,北方南士所带来的南朝新风显然对洛阳体“斜画紧结”风格的形成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将“王褒入关”为南书北渐之开端,其称:“南派入北,惟有王褒。”[39]然从北魏时期的洛阳体书风来看,南书北渐的时间当更早于王褒入关。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称:“洛阳体的出现,表明北魏楷书受到南朝新风的影响,走上了弃旧图新之路,过去的书论家把﹁王褒入关﹂事件作为﹁南风北渐﹂的开端,实际上北魏后期书法已经与南朝接轨,洛阳体就是证据。”[40]加之《北史》所载“宋人来聘”“使于宋”字样甚多,当时南北交往日多也是不争的事实,而南北之交往则必有赖于行人,行人往来于南北之间,则同样加速了南北书风的融合。徐利明在《中国书法风格史》中提到:“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至北朝末,南朝必有众多的士大夫书家及其书法作品以各种途径对北朝的书法产生积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了北朝书法加速变革,向南朝二王类型的新体演化。”[41]如果说北朝平城时期“平画宽结”的北碑风格与南碑“二爨”等书风相似是共同延续曹魏隶楷之变,那么,孝文帝汉化改革后的洛阳体“斜画紧结”北碑风格则无疑是继承了南朝所流行的王系新体书风。从立于北魏正光元年(五二〇)的《司马昞墓志》可以看出,其在笔法上已与永明五年(四八七)的南朝齐《刘岱墓志》无异,笔画线条上较之北魏早期大刀阔斧的直折形式相比,《司马昞墓志》中已具备提按鲜明的弧线笔画,且在转折处已见笔法痕迹,较之北魏其他刀斧痕迹已大有不同,可以窥见受到南朝王系新体的影响。正如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所谓:“在北朝晚期,刻石书法的笔势、笔法也与南朝的二王书风趋近,渐渐归于统一。”
北朝晚期的诸多碑刻书法已较之早期大有不同,具体表现在笔画上细腻柔和且书写性加强,整体风格也由粗犷向妍美转变,这种风格类型也无疑向南朝二王书风靠拢。在整个南书北渐过程中,行人善书者的南北往来显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结语
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政权对峙,无论在社会习俗、文学艺术等领域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书法艺术亦是如此。阮元南北书派论专以法帖属南而碑版属北,然从传世南北朝诸碑来看,其书风相似者甚夥,加之南朝禁碑,故南朝碑版相对北朝之墓志、摩崖、造像、题记等相对较少,阮氏所谓南北分派之说在碑版、墨迹层出不穷的近世可谓失察。考之于史,南北朝行人多为当时书家之后或本身即为善书者,行人往来于南北,亦有助于当时南北书风之传播,故行人在南书北渐的过程中有着极为特殊的作用。“行人”的作用,在书法研究视野日益开阔的今天是不能被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