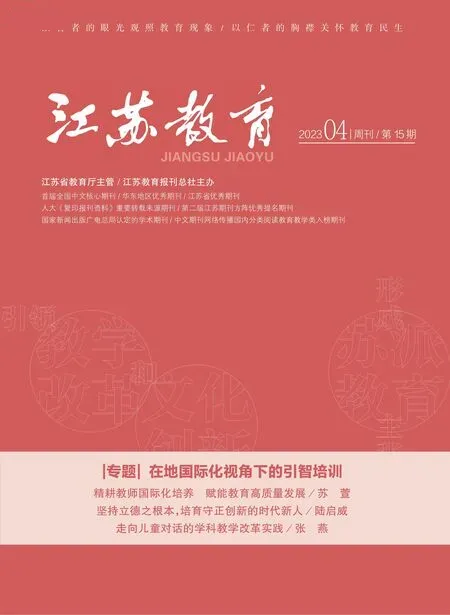教师之美:崇高性的建构与艰难性的实践
2023-09-14吕林海
吕林海
一所学校的美丽,深层地彰显于学校中的教师之美。这样的美,并不一定是一种形象意义上的“美观”,而更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美好”。这种“美好”,形塑了教师作为师者的真正“范”之蕴意,即谓“美范”。如果再深一步,我们可以说,教师“因美而范”,即教师只有具备了“美好”,才可称为“师者之范”。“美好”,构成了教师成为“师者之范”的充分条件。即使在此确认了“美范”的价值存在,我们仍然需要再向前进一步,去更深入地理解“教师之美”究竟意味着什么。唯有如此,“范”的实践建构才会更具方向。
通过对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第一实验小学“美范教师”校本实践的深入研习,笔者试图深入这所学校的背后,努力把握和解决如下核心问题:“教师之美”的“美”所指称的是什么?这个所指称的东西,它源自何处?而对这两个问题的探析,就引出了本文试图辨析的两个方面内容,即“崇高性的建构”和“艰难性的实践”。笔者认为,也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的深度持守和不懈追求,江苏省宿豫区第一实验小学才在教师发展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不断收获教师成长的幸福。
一、崇高性的建构:美是一种教师的“道德自我”之形塑
当我们讨论“教师之美”这个话题时,首先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即何以称为“美”。这涉及看待“教师之美”两种不同的视角。第一种视角是“客体性视角”。这种视角下的教师,是一个被审视的对象,即他(她)是一个被审视的客体。此时的“美”,是这个“客体教师”所拥有的属性。当我们说,这个教师是“美”的教师时,其实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把这个教师的“美”看作这个教师客体所拥有的特质,这是一种客观的特质。而作为观者的我们,就认为“美此时此刻正属于这个教师”。这里的“美”有一种命定的特点,即它“恰好就附着在了这个教师身上”,这个教师恰好在天性处符合了自然界(一种更广意义上的自然界)所圈定的美的属性定位。
然而,这种客观性视角下的美,是一种凝固的美,甚或是一种窄化的美。它的固化性和狭窄性的根本在于,“人之美”和“物之美”是不同的,其差异深层地体现在美的时间性上。具体而言,教师之美是“人之美”,这种美是一种时间性的产物。很难说,此时此刻的这个教师是美的,这种美即使被“叫出”,也很苍白。这个教师,即使此时此刻是“美”的,但这种“美”也必定是一种时间累积后的综合而复杂的涌现,它是这个教师深层人性与精神的积淀性展现。更确切地说,教师之美的时间性,深深地扎根在教师之美的精神性之中,而精神是不断生成的,它无法被瞬时化和片刻化,它是时间性地经历和淬炼后的产物。与之相反,物体之美是“物之美”,这种美是一种非时间性的产物,是一种可以在瞬时被“喊叫出来的美”。这种“此时此刻”被“观者”感知到、“喊叫出”的美,是一种物的形象所激活起的观者的某种精神上的激动之情,是观者瞬时间赋予此物的一种意义。
之所以说“物之美”是一种观者在片刻赋予此物的意义,是因为物无精神性且无情感性,而“美”其实就是一种精神意义和情感意义,它可以被赋予无精神的物。正所谓,“此情此景顿生情愫”,而“那时那景却全无感觉”。某个物、某个景,此时此刻或许让人心生惆怅,抑或充满豪情,但那时那刻却让人觉得索然无味,抑或处之淡然。
“美”对于物而言,是一种被赋予的状态,并且是一种“片刻性地被赋予”。与“物之美”的“可被赋予性”相反,人有精神、有情感,“人之美”其实就是人的精神、人的情感,这种美不需要从外部被赋予,而是一种“内在地”“自我建构、自我赋予和自我生成”。如果“人之美”还需要再从外部被他人赋予,就会出现两种美——内生的美和外赋的美,此时便会产生一个矛盾性的追问,即哪一种“美”更真实,抑或更本真。很显然,只有主体自身才能“更真地”拥有这种对美的意义把握,主体内生的美才是更美的“美”与更真的“美”。由此可见,“教师之美”是“人之美”,对“教师之美”的把握需要返回教师的主体自身,需要从“主体性视角”来进行内观或内视。
从主体性视角来对“美”加以内在的自我审视,这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思想贡献。他超越了源自鲍姆斯通的传统美学视角,将“美”从客观的属性转向了主观的精神。在康德看来,回到主体的“自我精神建构”和“深层人性反思”,才能真正地理解“美的真谛”[1]6。那么,“教师之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精神建构”呢?
“教师之美”其实有两个基本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优美”,这是一种教师的欢乐之美、喜悦之美、机智之美,它使人感到这个教师容易“亲近”。第二个层次是“崇高”,这是一种教师的严肃之美、博大之美、深情之美,它让人对这位教师心生“景仰”。“优美”是一种德性,“崇高”则是更高的德性。正如康德所说的,“崇高感感动人,而优美感则迷醉人”“优美使人欢愉,崇高使人敬畏”。“优美的教师”是美的,他(她)也能对某个学生表现出同情和善良,对某个情境表现出宽容和接纳,但这种同情、善良、宽容与接纳或许只是出于一种偶然的、个别的、可变的、情境的触发与意念,它所体现的“道德感”并没有深层地形塑于教师的精神深处,这种德性只是一种“被采用的德行”;只有把这里的“某个”“某些”上升到“普遍”“全体”的意义,此时的“道德感”才会是一种崇高之美,这样的教师才会被一种“人性的完满性”所充溢,他(她)此时充满着“博大而高贵的感情”,成为崇高的教师,并获得众人极高的敬重。可是,“崇高”的终极境界显然是无法达到的。这是因为,“对普遍的接纳”“对全体的宽容”是一种最深层的人性善良,是一种“真正的德行”和“根植于人性普遍原则之上的德行”。但对那种终极意义上的人性美,无法根除的人性自私永远是一道深嵌的屏障,终极的崇高之美永远需要教师在不断克服这种“自私的屏障”的过程中去不断逼近,它是人性修行的永恒目标。
由此可见,“教师之美”就是每个教师对内心深处一种普遍善良的人性美之深层感知、深层接纳和深度践行,就是每个教师不断克服自我的局限、迈向崇高的道德自我之形塑旅程。正如康德所说,“每个人的真正德行只能植根于原则之上,这些原则越是普遍,则它们就越崇高、越高贵”[1]14。笔者认为,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第一实验小学对于“美范教师”的内涵理解,正是超越了一种对“优美”的表层把握,而走向了一种对教师“崇高”的深深追求。
二、艰难性的实践:美生成于教师的“痛苦的教育实践”
明晰了“教师之美”的“崇高性”的内涵,自然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即这样的“美”如何生成。“生成问题”的解决,才会促使教师走向更加自觉的自我完善。
教师之美,是一种崇高性的建构,是一种精神的不断自我修炼,这唯有通过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的“身体实践和精神反思的互构机制”才可不断生成。但什么样的实践才是形塑“教师之美”的关键特质呢?这不禁又让我们回到康德对于“美的崇高性”的深刻见地上来了。在康德看来,“崇高之美”是一种真正的人性之美,由它而生成的行动“都要把这种美作为其普遍的基础,——这便是真诚,它和轻薄的寻欢作乐、和心性轻佻的反复无常是无缘的”;这种美“很接近于沉痛,就其实建立在那种畏惧感之上而言,那是一种甜美而高尚的感情”。
可以看出,“崇高之美”是人的一种因畏惧而痛苦,进而又“甜美且高尚的生命情感状态”。每个人都有自利的心态,一旦某种行动超越了自利,对这个人而言,这种行动就需要付出某种牺牲、某种代价、某种利益,在人的本性中,这是一种“深层的危险和逼迫”。但一个人一旦超越了这种源自自利本性的自保之困境,走出了这种“暂时的畏惧和痛苦”,他(她)就会感受到一种更大的完满,一种与更普遍的人性原则的深层相遇和拥抱,从而达至更高的道德生命境界。康德由此深刻地指出,“那种畏惧感是一个受束缚的灵魂,当其怀有一种伟大的意图但又看到他所必须要加以克服的种种危险以及自己眼前的艰辛而又巨大的自我克服的胜利时,所会感受到的;这样,由原则而产生的真正的德行其本身就有着某些东西,看来是与一种忧郁的心灵状态相一致的”[1]17。
“忧郁的心态”正是一个教师走向“崇高心灵”的必经之路,因为他(她)正在经历一种“艰难性的实践”,这也是一种“让他倍感忧郁和痛苦的实践”。其实,痛苦的实践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道德实践,它逼迫着主体在忧郁的情感中领悟着精神成长的深层密码。正如德国思想家、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所说,“在所有身体感受中,唯痛苦像一条可以通航且永不干涸的河流,将人类带向大海。无论人们在何处耽迷,快乐都不过是一条死胡同”[2]。结合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第一实验小学教师们的成长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教师而言,当他(她)被专家听课和指导之时,他(她)必然感到一种对自我原初经验的超越,这逼迫着他(她)克服自我、突破舒适圈,在畏惧中体会一种“新的意义生成”;当一位教师在“痛苦的”阅读中,不断收获、不断成长之时,必定也是他(她)不断克服自我的局限、走向更加丰满而理想的自我之时。如果更深地解析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第一实验小学教师的成长密码,可以看到,无论是“美阅课堂”,还是“向美而阅”,教师“崇高之美”的建构都历经了“痛苦的否定性”,而后生成“至美的肯定性”。此时,教师所“肯定的”,是他(她)对“永恒而普遍的教育人性原则”的深切认同、深层体悟和深刻践行。在对“否定性”的不断经历中,一名教师才能更深地走入“肯定性的奥秘”之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教育之美”。这或许就是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第一实验小学教师所不断经历的成长旅程,但这段旅程是一种“痛而后美”的心路历程。
对于教师而言,痛苦的教育实践生成于一种“他者的出现”。他者,或是听课的专家,或是带教的师父,或是实践领域中的任何一个相关联的他人。他者带来了一种“否定性的经验”,这种经验“在我们身边发生了,我们碰见了它,遭遇了它,被它推翻,被它改变……,其本质是痛楚”[3]。在痛楚中,教师产生了一种更加深刻的认识,一种更加新的意识状态。而教师的教育实践一旦去拒绝痛苦,它就走向了一种“被物化的生命样态”,而唯有“被他者触动之感”[4],才能使教师的生命鲜活起来,才会免于被囚禁于同质化的地狱之中的精神困境。
对于教师的成长而言,那是一条“苦路”,一条精神成长的痛苦之路。但唯有通过痛苦,精神才能获得新的洞见,获得更高形式的知识和意识。痛苦动摇了教师惯常的意义认知,强迫精神进行彻底的视角转换,“让一切在全新的光芒下现相”。经由痛苦而战胜痛苦,这就是教师精神成长的痛苦辩证法。
痛苦是一道裂隙,那是“全然他者”得以进来的地方,“教师之美”在此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