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一天有一天的温柔:72岁奶奶开民宿还“债”
2023-09-14柴柴
柴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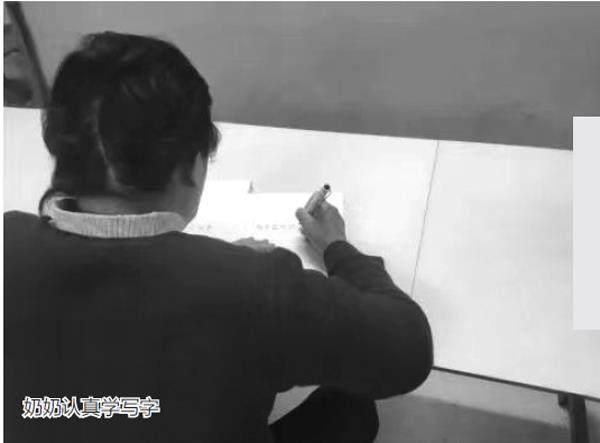

2017年,刘玉得知,72岁的奶奶执意要开一家民宿。家里人都不理解,奶奶却有充分的理由:还钱,之前借子女的20万,一定要还完。
奶奶要开民宿,挣钱还给子女
2017年,刘玉还在读大学,随父母回河南老家探亲。她听到爸爸跟妈妈商量:“这次回去,还有一件事嘞,玉玉她奶突然要开个旅店,咱到了得劝劝她。”
刘玉惊讶不已,忙插话问:“奶奶都七十多了,怎么突然要开旅店?”
爸爸答:“唉,庄稼人,估计忙一辈子了,闲不下来。就是她现在身体也不好,早就不是以前推车卖馄饨、上山摘柿子的年纪了。”
妈妈面露难色:“可咱妈那脾气,不同意她能听?就像玉玉她爷,现在干不动砌砖的活了,不还天天跑出去跟着人家当小工。”
刘玉仍在思考奶奶这次怪异想法的缘由,又问:“会不会是因为没人在家陪她?”毕竟父母都在西安,姑姑一家都在郑州,如果爷爷早出晚归,奶奶活像个孤寡老人。但父母也说不上来,商量着:“还是不要开了,岁数大了,操劳不过来。”
刘玉听说姑姑同样不支持,毕竟,老人到了这个岁数,在家休养,才更能保证身体健康。等他们到了奶奶家,刘玉见奶奶正穿着一件自己以前扔掉不要的T恤,被她改成了居家汗衫,并在里侧胸口位置缝上了两层布,奶奶说:“这下里头就不用穿内衣了,不勒,看着也不难看。”
奶奶一向如此,拾拾补补,如果谁要给她买件新衣服,那比登天还难,更要落一通埋怨。
刘玉仔细看她,她的头发剪得很短,显得干练无比,但花白的颜色掩饰不住,还有那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窝,无一不在展露这位老人饱经过的风霜。
奶奶开始和刘玉谈论着那些平日里的家长里短,不忘慈祥地笑。当刘玉询问起计划开旅店的事时,老人突然认真起来了,蹙起眉头,眼睛里闪出了波光,反复强调说:“这不叫旅店,叫民宿。”
这的确是一种时兴的叫法,她那倔强的模样,像刻意地接轨在时代的浪潮中。
刘玉问奶奶:“奶,你不认字,从哪里学的这个时髦的词?”奶奶一下舒开眉头,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智能手机,并说:“在手机上瞅嘞!”
确实,之所以叫民宿,是因为奶奶并不是要找个店面来开,而是改造自己现在闲置出来的自建房——那是1993年她和爺爷亲手盖起来的普通民宅,花了足足2000块,拢共四个房间,当中一个小院。
后来几经改造,往上垒了两层,配着红锈色的铁门,看着像拼接的积木。刘玉和表弟小时候都住过那里,后来又随父母去了别处生活。
那时候这里还是彻头彻尾的农村,正前方就是黄河水,附近是一垄一垄的农田,往城市走有很远的距离。奶奶开始也是农民,以种田为生,滚滚黄河带来的灾害不断,收成极不稳定,老人过得苦而辛酸,后来干脆去了城里务工。
二三十年过去了,这里摇身一变成了环境优美的市郊,政府在邻近黄河的地方修建出了大型公园,还在附近建设了文博城会展中心,用以每年举办在此地的某个知名博会。
奶奶把她思考的计划娓娓道来:“现在来咱附近旅游的人不少,能赚不少钱嘞。”
刘玉表示认同,也敬佩不已,她已经72岁高龄了,能想到那么多东西,无疑是对岁岁增长的年龄不屈的抗争,更是对于那层农妇和文盲身份的挑战。
刘玉说:“奶,你很像肯德基那个老爷爷,他是六十多岁才开始卖炸鸡的,后来风靡全球。不对,你比他还厉害,你都七十多了。”
“肯德基,知道。还有麦当劳,卖外国冰糕。”奶奶骄傲地笑笑。
刘玉问她:“奶奶,那你为什么那么想要赚钱?”“我想着赶紧还钱,早早还完。”奶奶说。刘玉不由得恍然一惊。
奶奶所谓的“还钱”,其实不是还给外人,而是还给刘玉父母一家和姑姑一家,两者拢共二十万元,欠了有些年了。这件事得从奶奶58岁那年说起。
那时候,刘玉父母要在外地城市买房,而姑姑家要在姑父那边新盖房子,四下用钱之际,奶奶把她和爷爷的积蓄拿了出来,合计十多万,给两家各分去了一半。为了减轻两家彼时的生活压力,她还宣告这笔钱不用还了,她和爷爷能自己赚钱养老。
两家都没客气,拿走应了急,但是心里面肯定想着宽裕了还回去。等陆陆续续有了积累,开口要还,奶奶断然拒绝了。她是个要强的人,始终认为自己应该为子女付出那些,不求回报。
为了赚钱养老,奶奶找了门生意,支起了一个三轮车,在附近的学校门前卖鸡汤馄饨,五块钱一碗。除此以外,她还在闲余之际,独自前往西北的山里摘野生的柿子,在家里晾成柿饼,再七八块钱一斤卖出去,虽然只能卖个几百块钱,但她乐此不疲。
爷爷也很听她的,每月出去干活,将千把块钱工资悉数上交给奶奶保管。那十年,他们攒下了十万块钱。只是到奶奶接近七十岁的时候,她的身体出现了一些毛病。自建房中没有暖气,犹如冰窖,关节更是难受,去了好几次医院治疗,开过一段时间的空调,都不受用。家人试图把奶奶和爷爷接到自己的家里照顾,可被老人拒绝了。
奶奶打算买一套带暖气的舒服房子来住。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后,在自建房的附近,奶奶相中了一套二手商品房,里面带市政供给的暖气,价格便宜,30万左右就可以买一套。
她积攒下的钱肯定是不够的,卖家也有些急等用钱。所以奶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想到了找子女借笔钱。
她宣告,钱她一定会还的,而且会尽快还。刘玉的父母和姑姑姑父其实都没放在心上,他们欣然出了剩下的20万元,并商议由姑姑亲自陪着奶奶去买,以免遭人哄骗。
年过七十的奶奶,就这样在暮年买下了她人生中第一套带暖气的楼房,写的是她的名字。夫妻俩搬去了新楼房住,自建的旧房子有时候租出去,有时候就空置着。
克服重重困难,民宿渐入正轨
72岁的奶奶从不认为自己还不上那笔钱,她担心的只是还钱的速度。因为她也愈发做不了推车卖小吃的活了,攒了两年才还了一万多。
尤其在刘玉和弟弟逐渐长大,上学用钱的时候,在刘玉父母姑姑都渐渐老去的时候,老太太决定,还是得早点把这笔钱还上。于是,她有了开民宿的想法。
劉玉看出来,奶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心里早就算过了细账。虽然家里不支持,但奶奶的人生一直是她自己掌握的,没有人能够真正阻拦。
果然,她和父母回城后,奶奶和爷爷就自顾自忙活起来了。奶奶找来两家装修队,画了图纸,无非是刮刮腻子,给卫生间铺上瓷砖,换些旧窗户,门口捯饬捯饬。两位老人完成了大部分装修:自己动手粉刷了屋子的墙壁和天花板,工人们只负责抹水泥、铺砖。
刘玉难以相信这是爷爷奶奶能办成的事,为此爷爷腰痛了许久。同时,奶奶为了省钱,自己去弹了棉花做被芯,还在市场上截了大卷的白布来缝被套。她起早贪黑,缝了接近一个月,眼睛更花了。但是,最困难的事情在于“开”。
姑姑为此专门回了一趟老家,给奶奶的民宿买了台二手电脑和摄像头,联好网,用以操作公安局要求的入住备案。然后,给奶奶的手机上注册好民宿APP,成了正儿八经的商家。
但姑姑的工作不是一劳永逸的。奶奶不认识几个字,一是不能和询问的顾客打字聊天,二是不能给人家打字录入公安局的备案系统。爷爷认识的字倒是比奶奶多不少,不过没有什么用,他也不会拼音。
姑姑打算教两个老人认字,刚教两天,就放弃了。老人家到了七十多的岁数,又普通话不标准,实在难以学会这些东西。奶奶的民宿虽然在姑姑的帮助下开起来了,但其实是个半烂不烂的摊子。
一筹莫展之际,爷爷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奶奶买的楼房对面租住了一对可怜的母子,孩子叫徐旭,正读初中,母亲在服装厂里做缝纫工,单亲家庭,相依为命。爷爷叫那个孩子过来,和他商量着能不能每天下学后,去不远处的自建房里待一会儿,帮奶奶打字录入电脑系统,会给报酬,也能管一顿晚饭。
徐旭的母亲贪图晚间加班的一点工钱,平时都是叫孩子自己在家煮点东西吃,或是等到十点钟以后,她回到家了再做给孩子吃。她也知道对面的老人绝非什么坏人,便欣然接受了爷爷的邀请。
自此,徐旭下学后,带着作业,去奶奶开的民宿里帮忙,在那边吃奶奶做的饭,不是什么大餐,常常是老人包的饺子、包子、馄饨,偶尔能吃点鸡肉和猪肉炖冬瓜。虽然简单,孩子却说比自己母亲做的好吃一百倍。他会帮奶奶录入白天或晚上入住的旅客的姓名,当然常常要麻烦客人重新配合一下,但没办法,再简单的事奶奶也得用一种很难很烦琐的方式才能完成。
当然,徐旭后来还承担了其他任务,一是帮助奶奶网购一些东西,比如说一次性用品、凳子、水杯,也教会了奶奶取快递,无论是驿站还是快递柜,这也是后来奶奶不再托刘玉网购的原因;第二件事是,有空的时候帮奶奶在APP上和顾客聊天,但是只能是晚上,这很不方便,也常常和顾客有来无往,惹得对方一通不快。总之,来住的客人少得可怜,难以赚到什么钱。
奶奶希望姑姑能在外地登录她的账号进行客服操作,应对问询的意向顾客,毕竟姑姑在家算是个家庭主妇,空闲时间不少。姑姑开始也应允了。但是实际帮忙的时候,姑姑常常颠三倒四,错过一些重要消息,颇有敷衍的意思。
奶奶大为不满,又重新要回了账号,由自己、爷爷和徐旭一起来操作。只是他们三个都不太懂,经常闹出啼笑皆非的问题。
有一回,刘玉接到奶奶的电话,奶奶说:“玉,奶想着电话跟客人说,刚叫娃把电话号码发给那个人了,他咋非说没收到?”刘玉仔细一研究,原来是商家直接发出自己的号码,对方收到时会有四个数字被盖上*号(app机制)。可解释过后,奶奶还是听不太懂。
奶奶见网上找顾客那么困难,打算把精力从网上转移到现实生活中。像许多年前火车站附近的旅店老板一样,她去会展中心和公园附近招徕住客。她不认识字,但是叫徐旭帮她写了份广告的字样出来,然后自己依葫芦画瓢,誊抄到纸片上。
说是纸片,其实都是刘玉从前上学时候剩下来的演草纸,奶奶搜集起来没舍得扔,就用刀子截成纸片,用来制作广告。她每次抄一百多份,上面标明了地点、价格、电话,还有名字。
一开始叫“黄河之家”民宿,然后叫“黄河的家”民宿,最后叫“天鹅之家”民宿。
奶奶虽然不认识字,起过的三个名字却别有一番诗意。她每天要带着自己写好的卡片,走三公里到公园和文博城发广告,光路上就得半个多小时。然后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在那里转上四五个小时。她像往日里卖馄饨那样招呼行人,又有别于卖馄饨那样简单。
继续折腾之路,此生活在热爱里
奶奶从不骗人,会简要概述民宿的条件,她很自信,认为不管什么人都愿意来她的民宿里住——这是失败的判断,有钱的不会来,太年轻的不会来,只有那些打算凑合一晚的人会来。
刘玉放假时跟着奶奶去发过几次广告,那也是她毕生难忘的体验。只见奶奶手握一沓广告纸片,剩下的装兜里,一旦见着背着包、推着行李箱的人就冲到跟前,递上去纸片。
奶奶递完广告,往往不等回答,就帮忙拿起对方的东西:“重吧?”然后准备好随时带人去“天鹅之家”。这套动作行云流水,和她干别的活一般麻利。
如果有人愿意跟她走,她会带着对方,不自觉地脚步飞奔起来,早已忘记自己腿脚的病痛。但大部分人并不客气,生怕她沾上自己,忙说:“不用不用不用。”有的甚至根本不说话,立马躲得远远的。
除了来往行人对于广告的冷眼相对、恶语相向,很多人会将奶奶辛苦写的纸片随手丢掉。可奶奶从不抱怨,从不詈骂,而是走过去,弯腰拾起来散在地上的“天鹅之家”,用手掸掉尘土,再次握到自己的手里,像个宝贝似的。
她从不为此叹气,而是说:“抄着累嘞,拾回来还能用。”在奶奶的万般努力下,“天鹅之家”民宿渐渐步入了正轨,确实要比她原先赚钱要多,当然,操劳也更多。
奶奶的身体大不比从前了,叫她难受的还是打字录入系统这样的小事。因为原先帮忙的徐旭突然要离开了,他母亲想去别的地方打工,要带他去别处念书。虽然徐旭的母亲也对这里恋恋不舍,但是为了多赚些钱,她觉得这点牺牲不算什么。
奶奶当然也不舍得,但当时她心里更难过的是自己的民宿以后如何打字登记,这是个大麻烦,为此她彻夜难眠。
为了解决困扰奶奶的难题,爷爷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叫徐旭帮忙把那台旧电脑改为了手写输入法,并且告诉奶奶,比着身份证上的字来“画”就行了,比着“画”,点击一模一样的字。
“画”,这真是个极简单但是足够有效的浪漫办法,奶奶甚至不用学,稍加练习几次就会了,和用树杈在沙地上划拉一样。
到这时,刘玉才意识到,可能只有老年人才能想到适合老年人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个角度上说,可能只有像爷爷和奶奶这样平日里无话可说却又相濡以沫的伴侣,才知道对方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徐旭临走时,奶奶给了他不少东西,柿饼、自己腌的咸菜,还有一个小红包。
没了帮手,奶奶继续靠自己经营着那家民宿。接近夏天的时候,迎来了某个展会的举办。奶奶趁此徘徊在文博城附近,再次发着她的小卡片。仍是她一笔一画在昏黄的灯下,用演草纸写好的。
电话里,刘玉听她说生意好了不少,那些天一晚上能赚大几百,这对于老人来说几乎是没有过的体验。很快,她就一家又还了一万。
好景不长,在文博会结束后,尤其夏季结束,秋冬住店的客人越来越少。奶奶的生意再次一落千丈。刘玉安慰她说:“就和坐火车似的,都有淡季旺季。”奶奶还是眼巴巴地守着,孜孜不倦地去发广告纸片。
只是,奶奶的生意没能熬到下一年的旺季,因为她身体更加不好了,老的自建房里仍然阴冷,她待的时间一久,总会难受,为此又去了几次医院。
终于,“天鹅之家”民宿开了不足一年后,还是倒闭了,也许这就是生活的真相。
只是奶奶想,还是要做别的事情赚钱,她要还钱。恍惚间,刘玉感觉她不仅像肯德基老爷爷,也很像堂·吉诃德。
往后,奶奶既没有馄饨的摊,也没有民宿的店,她开始把柿饼生意做大做强。以前她去摘,现在摘不动了,就去收别人的,一筐一筐地买,托朋友的兒子帮忙运回家,她再晾成柿饼来卖,赚中间四五块的差价。
爷爷身体还硬朗,继续干着小工的活。他们固执地每攒够一万块钱,就一张张在床头铺平整,坐在那儿好一阵清点。
奶奶数完,爷爷再数一遍。清点好,用塑料皮筋扎起来,装在黑色小包里,再手把手还给两家的子女。父亲和姑姑无奈地笑着收下,根本阻拦不了。
疫情肆虐期间,外地生活也并不顺遂,刘玉的姑姑决定回老家做点小生意。做什么呢?她思来想去,最后打算利用奶奶的自建房,曾经的“天鹅之家”民宿,做一个附近学校学生的托班。很多父母没有时间及时接送孩子,可以托管在这,管吃管写作业。
托班很快开张,生意还不错,孩子们很多,姑姑忙不过来的时候,常叫奶奶去帮忙做饭,按月给她1500块工钱。
现在,刘玉的奶奶还有12万没有还清,但她会再次蹙起眉来,十分认真地说:“俺做饭挣钱,还是能把欠你们的钱还清。”
编辑/邵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