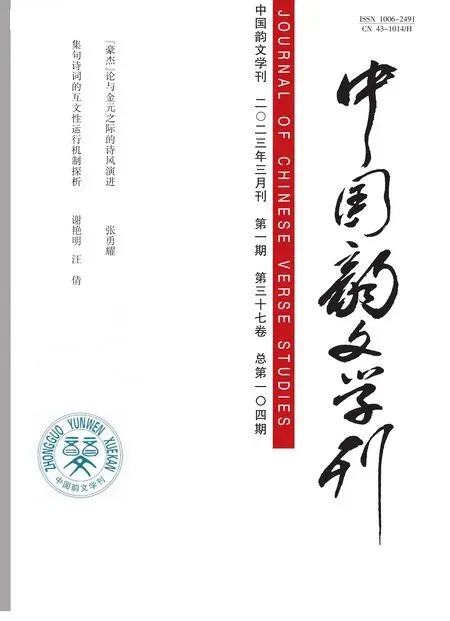论唐宋词的戏剧意味
2023-09-10陈晓清
陈晓清
(岭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将“诗”、“词”与“曲”相提并论之最著名者,当属王国维那段话:“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P1)王国维以进化论的视角观照中国文学,从而画出了一幅文学进化、承递之缩略图。近现代词学研究者,多习惯于把“诗”与“词”并举,以诗学的评价标准评判“词”之得失与异同,从思维习惯上来说,属于从前往后看。若能反向思维,从后往前看,即以“曲”为独立视角来看“词”,以“曲”的评价标准来看“词”,会有不一样的发现。不少学者也曾在忠于文本赏析的同时,读到“词”中的戏剧意味,如夏承焘赏析辛弃疾《西江月·遣兴》词时写道:“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画。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2](P147)幺书仪更是从戏曲的起源、发展来考证:“今存敦煌卷子中《云谣集杂曲子》内有《凤归云》二首。由于这《凤归云》在敦煌卷子中同时有舞谱存在,所以,可以断定,《凤归云》一定是一个歌舞表演。”[3](P41)可见,词有戏曲的雏形,有类似戏曲的文本,且兼具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可算得上符合近代戏剧之意义了。
俄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曾提出“叙事诗歌”“抒情诗歌”“戏剧诗歌”的概念。当论及人类文学发展历史的时候,他描绘了一条从叙事诗歌到抒情诗歌,最后到戏剧诗歌的发展脉络。“戏剧诗歌”,又简称“剧诗”,在别林斯基眼中是诗歌的最高形态。有别于客观记录自然发生的事的叙事诗,不同于主观的表现诗人本人内在的抒情诗,“戏剧是叙事的客观性和抒情的主观性这两种相反的因素的调和”[4](P13)。孙康宜在《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中写道:“通俗曲词的模式却是千变万化:有叙事体,有戏剧体,当然也有抒情体。”[5](P28)可见,西方所定义的抒情诗歌、叙事诗歌、戏剧诗歌在唐宋词里面齐齐亮相。陶文鹏《论唐宋词的戏剧性》一文,从袁可嘉先生关于新诗戏剧化的观点出发,分析词的戏剧性表现,对唐宋词的艺术作出新的阐释。林顺夫阐释姜夔《浣溪沙·著酒行行满袂风》时使用了“戏剧张力”一词。王晓骊在《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一书当中曾专门撰写一章《词与戏曲》详尽论述词与戏曲之关系。戏剧大都具有动作、表演、角色、冲突、假定性情节、代言等要素,而类似的戏剧元素也一直存在于词的文本当中,只需要我们以戏剧之视角去发现。以下拟详论之。
一 劝酒词的当代戏剧先锋意味
词产生于酒席歌筵之间,在筵席上担当起劝酒的功能。欧阳炯《花间集序》写道:“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6](P1)以绮艳的文字给我们描述了词的佐酒之欢的情境。至宋代,自上而下的游宴享乐之风进一步推动了词的发展。宋代祝酒行令之风盛行,而词在其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如曹冠的《霜天晓角》:“浦溆凝烟,谁家女采莲。手捻荷花微笑,传雅令、侑清欢。 擘叶劝金船。香风袭绮筵。最后殷勤一瓣,分付与、酒中仙。”[7](P1170)这首词描绘了酒席上女子唱词劝酒的场景。我们看到有一定的动作,甚至相应的道具配合,而且女子作为劝酒人,还担任着主持整个酒席、掌握节奏、调节气氛的作用,不是仅仅唱词那么简单。词人题下自注云:“荷花令用欧阳公故事,歌《霜天晓角》词,擘荷花,遍分席上,各人一片,最后者饮。”[7](第四卷,P1170)可见,歌妓演唱曲子词一边劝酒,一边配合相应的动作。另如毛滂《剔银灯》词自注云:“同公素赋,侑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劝酒。”[7](第二卷,P871)又如《事林广记》癸集卷十二记载了四首酒令词《浪淘沙令》《调笑令》《花酒令》等。其中《卜算子令》就完整地记录了相应的动作:“先取花一枝,然后行令,唱其词,逐句指点。举动稍误,即行罚酒,后词准此。”[7](第十卷,P503)全文是这样的:
我有一枝花,(指自身,复指花。)斟我些儿酒。(指自令斟酒。)唯愿花心似我心,(指花,指自身头。)岁岁长相守。(放下花枝,叉手。) 满满泛金杯,(指酒盏。)重把花来嗅。(把花以鼻嗅。)不愿花枝在我旁,(把花向下座人。)付与他人手。(把花付于下座接去。)[7](第十卷,P503)
在喧腾欢闹的酒筵歌席间,歌妓且歌且舞,优美的词与动人的歌舞相结合,成为调节筵席气氛、带动与席者情绪的佐欢之具。与歌舞结合,且演且唱的劝酒词就很有戏剧雏形了。若按当代戏剧分类,可算是独幕的歌舞剧。只是与我们现在所习见的台上台下观演的戏剧很不一样。不过,中国古代戏台三面开放,观演之间的交流一向比较自由。而且,当代戏剧也有打破第四堵墙的呼声,董健、马俊山说道:“当代,有些导演为了打破‘第四堵墙’的局限,把演区扩展到了观众席,让演员走下舞台,与观众握手、拥抱、交谈,或者设法把一些观众纳入演出,使之成为另类戏剧角色,更是典型的直接参与。”[8](P244)打破演员与观众之间的演与观的对立关系,加强观众对戏剧的直接参与,这是当代戏剧的突破。从这个角度来看“劝酒词”,它具有当代戏剧的先锋意味。酒筵歌席是其演出之剧场,歌舞者与观众之间有更多的互动,甚至观众被纳入演出,成为戏剧的一个部分。
从当代戏剧先锋表演的角度重新审视劝酒词,如早期劝酒词有刘禹锡《纥那曲》:“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同郎一回顾,听唱纥那声。”[9](P59)又有:“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9](P60)从词中,我们可以看到酒宴的情境,杨柳、竹枝、纥那,唱完一曲又一曲,兴乐无穷;同调不同词,唱完此曲再来一曲,边唱边祝酒,在歌声中,宾主尽欢。在这样的劝酒词当中,记叙了酒令唱曲的真实场景,其间的戏剧场景如在眼前。黄庭坚的劝酒词《定风波》:“上客休辞酒浅深,素儿歌里细听沉。粉面不须歌扇掩,闲静,一声一字总关心。 花外黄鹂能密语。休诉。有花能得几时斟。画作远山临碧水。明媚。梦为蝴蝶去登临。”[7](第二卷,P59)此词则更如一出戏剧,有人物、场景、声音,可演可感,具体形象。冯延巳有一词《薄命女》:“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9](P685)语言通俗自然,一歌女且歌且拜的形象,活灵活现,颇具戏剧性。而在她的祝词当中,塑造了她真心痴情的一面。全词纯以代言形式,通过人物的言语展现人物的性格。代言体,有言语、有动作、有歌唱,且人物性格在行动中呈现,这些就具有了构成戏剧的基本条件。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宴乐观剧”传统,士人的宴席陈设之处,就是歌妓乐舞表演之地。这就使得戏剧表演没有当代壁垒分明的台上台下的公共剧场模式。在唐宋时代的宴饮场所,观众与演员的距离相当近,表演者与观众的关系非常密切。日本河竹登志夫在《戏剧概论》一书中,引入了能量传播与耗散的理论。这是当代戏剧理论的一个重要收获。“场”论为透视观众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如“观众是剧场内产生‘场’的力,即在向着舞台集中的‘矢量’的作用下,形成舞台与观众之间产生感情交流的‘戏剧的场’”[10](P129)。从演员与观众之互动来看、劝酒词是最具东方戏剧美学特点的戏剧词。它使观众扩大了空间视觉范围,取得了进一步将观众导入规定性情境的良好戏剧效果。表演过程当中,演员与观众之间,观众与观众之间都有密切的交流。日本河竹登志夫则把这种交流称为“垂直表演”。因为“演出者的形体进出于观众席中,他们的官能活动,包括台词的节奏与旋律,都一并垂直地射向观众,使观众陶醉、兴奋”[10](P153)。我们设想劝酒词表演的形式、场所及其社交功能,都可以说是一种“垂直表演”。歌女置身于观众(与宴者)中间,歌女的劝酒活动,包括劝酒的节奏与旋律,都一并垂直地射向观众,使观众陶醉、兴奋,一饮再饮,醺然忘忧。
表演者(歌女)与观众、观众与观众之间,相互感应,形成了某种情感与心理上的共振——这就形成一个共同的“场”,“在‘场’的不断传递与反馈的过程中,构成一种共同的心理时空,并成为戏剧艺术产生的一种最基本的动力源”[11](P176)。劝酒词作为演唱文本,则成为一个催化的媒介,推动表演者与观众共同创造戏剧。这就是劝酒词在酒宴筵席上发挥的戏剧性效果。
二 唐宋词的戏剧类别
著名的戏曲家李渔论词带有戏曲家的眼光和见地,他的《窥词管见》写道:“词内人我之分,切宜界得清楚。首尾一气之调易作,或全述己意,或全代人言,此犹戏场上一人独唱之曲,无烦顾此虑彼。常有前半幅言人,后半幅言我,或上数句皆述己意,而收煞一二语,忽作人言。甚至有数句之中,互相问答,彼此较筹,亦至数番者。此犹戏场上生旦净丑数人迭唱之曲,抹去生旦净丑字面,止以曲文示人,谁能辨其孰张孰李,词有难于曲者,此类是也。”[12](P557)李渔在这里是将曲的文本统称为“词”,把词的类别分为“一人独唱之曲”和“数人迭唱之曲”,并且指出词中“常有人我难分之弊”。以此视角来点检、辨析词作,亦可旁证词之演进为“曲”的基本事实。如:
(一)一人独唱之曲
在词学研究领域的话语体系,有“男子作闺音”一说,尽管此说论讼纷纭,但学者一般认为,意即男性词人在词作中以代言体的形式来写出女性口吻的词,以供歌妓演唱。如无名氏所作《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9](P861)
此词以一个女子的言语来展现情节、塑造性格。除了首句,其他六句皆是女子追忆当初她的丈夫发下的誓言。与汉代民歌《上邪》极相似,都是用自然界中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来比喻其情之坚贞。言语之间,男子当时信誓旦旦的形貌如在眼前,而今天却要休妻了。女子则以排比式的比喻给予最强烈的回击,最后一句 “要休我,除非三更出太阳!”将女子的怒与强悍生动真切地展现出来。此词不足50字,两人感情之过去与现在,突遭情变的波折,以及信誓旦旦的男子的虚伪,一往情深的女子之不容分说的霸道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通篇词读来,颇有戏剧感。戏剧性包含多方面要求,如偶然性、突变性、传奇性、震撼性等等,但主要指戏剧冲突。“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这是戏剧文学和戏剧艺术的神圣法典。这首词的戏剧冲突可谓激烈,要休与不要休,壁垒分明。枕前誓愿,已成过去,如今是“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的对立。连用六个比喻,都是自然界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气势连贯,表达天崩地裂般的决绝。戏剧冲突,可谓激越。
又如无名氏《抛球乐》:
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姊分明道,莫将真心过与他。子细思量着,淡薄知闻解好么。[9](P819)
此词也是一女子独白的口吻,唱出心声。从她的话语当中,展示了她的遭遇和心理活动,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恋爱故事。第一句,就告诉我们这番恋爱的结局,以失败告终。三、四句则回忆当初,用倒叙的方法,追述故事之初:二人刚认识的时候,姐姐就曾明白地告诫,不要对他付与真心。第四、五句,则写她经过这次失败的恋爱后的醒悟。全词纯以一人口吻,而整个恋爱的过程、结局,交代得清清楚楚,而女子的纯真、深情,与男子的薄幸,以及姐妹情深,相劝的冷静理智,都塑造得鲜明生动。沈家庄评道:“此类妓女之命运,后来在关汉卿杂剧《救风尘》中宋引章身上得到更富典型性的生动、全面反映。由此可探得中国古代妓女文学在题材、形象塑造方面某些承继和影响之消息。”[13](P242)又如韦庄《思帝乡》写一女子之独白:“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9](P167)决绝而直白,奔放之势如黄河不可收,戏剧意味十足。
亦有男子的口吻,如周邦彦《虞美人》:“灯前欲去仍留恋,肠断朱扉远。未须红雨洗香腮,待得蔷薇花谢、便归来。 舞腰歌板闲时按,一任旁人看。金炉应见旧残煤,莫使恩情容易、似寒灰。”[7](第二卷,P706)全篇除了首两句,其余六句皆为男子话语。临别前男子对女子倾诉衷肠,有告慰、叮咛、理解和期许。宋代无名氏《失调名》“你自平生行短,不公正、欺物瞒心”[7](第十卷,P304),纯是一人口吻的唱词。宋代无名氏所作《御街行·霜风渐紧寒侵被》以对白来写,写法新颖、别致,作者设计了一个情节,游子托雁传情,这一长句“塔儿南畔城儿里,第三个、桥儿外。濒河西岸小红楼,门外梧桐雕砌”[7](第十卷,P804),看似絮絮叨叨,实是殷勤。这段词非常口语化,俞平伯评其 “以长句作具体详细的描写,小说散文之意,且开金元曲子风气”。[14](P161)俞平伯敏锐地读到此词之戏剧意味的开创性。
这些词作善于用人物自身的语言塑造人物、展开情节。词中人物形象通过自己的语言和行动来展现自己的性格特征,具有鲜明的戏剧性。
(二)数人迭唱之曲
敦煌民间词当中有不少对答体,此类作品便是后来元杂剧对唱或对白的滥觞。如《云谣集》杂曲子当中的《凤归云》二首:
幸而今日,得睹娇娥。眉如初月,目引横波。素胸未消残雪,透轻罗。□□□□□,朱含碎玉,云髻婆娑。 东邻有女,相料实难过。罗衣掩袂,行步逶迤。逢人问语羞无力,态娇多。锦衣公子见,垂鞭立马,肠断知么。
儿家本是,累代簪缨。父兄皆是,佐国良臣。幼年生于闺阁,洞房深。训习礼仪足,三从四德,针指分明。 聘得良人,为国远长征。争名定难,未有归程。徒劳公子肝肠断,谩生心。妾身如松柏,守志强过,鲁女坚贞。[9](P802)
两首词有三种叙事人称,第一首的上阕以“公子”口吻自述,叙述他对东邻女子的爱慕之情,下阕是第三人称叙述故事始末,第二首又换成了女子的口吻,是这位女子的婉拒之辞和自明心志的叙述。故事情节与《陌上桑》相似,读此词,犹如生旦在场上轮番对唱,兼有旁白叙述。
又如《南歌子》二首:
斜影朱帘立,情事共谁亲。分明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谁绾,甚人踏破裙。 蝉鬓因何乱,金钗为甚分。红妆垂泪忆何君,分明殿前实说,莫沉吟。
自从君去后,无心恋别人。梦中面上指痕新。罗带同心自绾,被狲儿踏破裙。 蝉鬓朱帘乱,金钗旧股分。红妆垂泪哭郎君,妾是南山松柏,无心恋别人。[9](P926)
这组词像是男女对唱,第一首以丈夫的口吻,因丈夫疑心妻子移情别恋,问妻子;第二首则以妻子的口吻来一一对答,回答丈夫的疑问,誓言忠贞。在一问一答的对话中,隐含着一定的情节,不乏具体的细节描绘,“指痕新”“罗带同心绾”“踏破裙”“蝉鬓乱”“金钗分”“红妆垂泪”等,让一个“自君适东,无心为容”的痴情女子形象活脱脱出现在眼前。这种叙述手法表现的效果,俨然戏剧人物在表演。故事情节、具体细节与人物心理活动悉数呈现给观众。
唐宋词中还有人与喜鹊的对话,如无名氏《蝶恋花·叵耐灵鹊多谩语》。这首词更具有鲜明的戏剧特点,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没有任何语言交代,而完全是在人物角色对话中交代事情缘由。且设置了矛盾冲突,一个被锁在金笼,一个想飞向青云里,少妇之恼的心理活动,在喜鹊的话语中被披露出来,颇有戏剧性。
以上几首词都由人物的“对话”构成,词作的文字笔墨集中在主要人物的身上,专注于表现主要人物的命运。没有过多的关于地点、状态、人物的叙事式描绘,人物用自己的语言表现自己的心理症候及特征。在以上文本当中,人与人的对话、人与自身的对话、人与动物的对话、人与社会的对话,多种声音竞相鸣放,都具有对话的平等性,颇具有戏剧的特点。
三 唐宋词的“剧诗”形态
关于抒情诗、叙事诗与戏剧诗的区别,一直是西方文艺理论学者辨析的焦点。叙事诗是作者写出文本表述客观的自然发生的事,而戏剧则是剧作家写出文本让演员表演故事。叙事诗与戏剧诗的关键区别在于一个重“事”的展现,一个重“人”的塑造。罗伯特·斯科利斯和罗伯特·凯洛格在《叙事文学的特性》中写道:“叙事性的文学作品,应该有故事和讲故事的人,二者缺一不可。戏剧文学中有故事,但没有讲故事的人,演出时由剧中角色直接进行表演。”[15](P103)而浦安迪论道:“抒情诗直接描绘静态的人生本质,但较少涉及时间演变的过程。戏剧关注的是人生矛盾,通过场面冲突和角色诉怀——即英文所谓的舞台‘表现’(presentation)或‘体现’(representation)——来表达人生的本质。”[16](P6)可见,要区分叙事诗与戏剧诗歌,关键在于如何“表现”。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构成“戏剧”的几个必要条件是:故事情节有一定长度;媒介是语言;表达方式是摹仿、代言。幺书仪在《戏曲》中归纳任半塘关于中国戏曲成熟时代的“唐代说”观点,写道:“凡属‘代言、问答、演故事’的文体形式,即可以称为具有了构成戏剧的基本条件。”[3](P10)而王国维则认为:“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1](P32)可见,戏剧诗,即“剧诗”的关键词在于代言、对话、人物及戏剧冲突。幺书仪论戏曲的发展时说道:“直到宋代,流传至今的南曲戏文才跨越了叙事代言混合,而以叙事为主的诸宫调,成为以代言为主而时有叙事间杂其间的‘代言体’文学样式,至此,它就具备了王国维所规定的所有的因素。”[3](P12)也就是说,“代言体”文学样式,有戏剧的所有元素,具备“剧诗”的形态。而唐宋词从《花间集》开启的源远流长的“男子作闺音”的文学传统,就是这种“剧诗”形态最鲜活的例子。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沈家庄曾在其硕士论文《清真词艺术论》章节中,详论周邦彦《清真词》的戏剧性特征。他说:“周邦彦生活在北宋末叶,杂剧盛行,表演诸宫调故事内容丰富,傀儡戏也演出完整的故事情节。勾栏、瓦子遍布汴城街巷,说书人更是活跃在茶坊酒肆。多方面的艺术熏染,又善于学习、汲取当时新兴艺术种类的成果,因而词人的长调表现出浓郁的戏剧性、故事性结构特色。”接下又结合别林斯基有关戏剧理论,以周邦彦的《兰陵王》《瑞龙吟》为例,论证清真词长调的戏剧性模式:“……让抒情和叙事与场面的配合有多侧面感和立体时间空间感,并且使自己成为在这些场面中活动的人物,让读者观察,给人一种类似戏剧性情节安排的结构模式。我们说它们具有戏剧性结构,是因为这些词不但表现为‘叙事诗和抒情诗之间的调和’这一特点,像戏剧一样‘把业已发生的事件表演成为仿佛现在正在读者或观众的眼前发生似的’[4](P69),而且它具有作者(主体)构思戏剧情节的两个特点。一,词中情节的发展与词人不是隔绝的,恰巧相反,是从他那里引发出来,又回复到他那里去。二,词人在这里的‘出场’,就像别林斯基所说的‘跟他在抒情诗中的出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他已经不是感觉着、并观察着凝聚在自身之内的内心世界,他已经不是诗人自己,而变成了那个由他自己的活动所组成的客观的、现实的世界中被观察的对象了;他被划分成许多部分,变成了根据其作用和反作用而构成戏剧的那许多人物的总和’[4](P69)。故这类作品具有故事性、戏剧性的特点而显出作品包孕宏深、气象浑穆、感情与形象容量阔大的充实感。”接下来,沈家庄又具体以《清真词》开篇第一首《瑞龙吟》为例,指出“词第一段极像今天电影文学剧本的开头:‘路·梅树·桃花·静寂的小巷院落·燕子飞进一户人家。’这个场面,正是从主体(词人)引发出来,而且词人作为被观察对象正徐徐步入镜头。第二段是往事的追想。把十年前的场景表现得像在眼前发生的一样。一段和二段的平列,再现了两个空间,表现了两个年代,在这两个场面中间词人都是作为戏剧人物成员而出现……词人始终是作为情节中活动的人物让读者观察……最后,词中情节展现只身单骑的词人,在黄昏的雨帘中,缓缓移过芳草池塘的剪影。结尾的画面是:无灯的暗夜;衰寂的院落;风卷着柳絮掀起竹帘,发出撞击门框的单调声响……全词组织得俨然一幕小戏”[17](P55)。
以北宋第一词人柳永为例,他写有大量代言体的词作。戏剧文学是代言体而不是旁叙体。如果从词的戏剧性、表演性来思考,词的创作相当于剧本,它以代言体的形式来创作。柳永的词作当中,一部分是以男子口吻,为男子代言,如《秋夜月》:“当初聚散。便唤作、无由再逢伊面。近日来、不期而会重欢宴。向尊前、闲暇里,敛着眉儿长叹。惹起旧愁无限。 盈盈泪眼。漫向我耳边,作万般幽怨。奈你自家心下,有事难见。待信真个,恁别无萦绊。不免收心,共伊长远。”[18](P375)此为男子代言,倾诉心声,从回忆起,当年分别后,再也没有机会见面;而这次却在宴会上不期而遇。以男子视角写女子形态。读者通过人物眼睛看世界,看这段恋情,通过台词认识人物的性格特点。又如柳永《红窗听·如削肌肤红玉莹》《长寿乐·尤红殢翠》这两首词皆以代言体的形式摹写生活,从男性视角切入,写出了在筵席上相遇、相识、相爱的才子佳人故事。
而柳永创作了更多的词是为女子代言,男性作者代入女性角色,为故事的叙述设置一个女性叙述者,娓娓道来。如柳永《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18](P52)
这首词以代言体的形式,用一个女子口吻在春日思念恋人,诉衷肠。全词纯以白描手法,通过人物语言来交代“暖酥消,腻云亸”的细节,体现女子的痴情。下阕则用直白的方式说出心里话,其语言贴切身份,体现出市民性。黄胜江评道:“在柳词中不少作品都传达出一种丰富的戏剧性情态,或通过人物声口形成对比,或行为产生冲突的不和谐,或心理的矛盾,或制造情节的悬念给人以期待……此词(《定风波》)以一女子的口吻写闺怨,犹如一段代言体的唱词,对那‘薄情’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情溢于言表……这样反反复复、层层道来,尽显小女子声口,颇有生活意趣,戏剧性盎然。”[19](P116-P117)柳永的《定风波》具有明显的民歌风味,带有市民意识,语言通俗,口吻自然,女性角色的性格在女性角色的语言当中自然呈现。
柳永的词,如《迷仙引·才过笄年》《锦堂春·坠髻慵梳》《迎春乐·近来憔悴人惊怪》《滞人娇·当日相逢》等等,可以说写出了中国古典女性的独特气韵:那羞涩、高雅中的妩媚,单纯、自然中的窈窕均令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读这些代言词,读者的阅读体验会产生仿佛是在看当代青春偶像剧的感觉:男主角都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才华出众、情深义重;女主角都温柔体贴、哀婉多情、对男主角一往情深……对于词人柳永来说,他就是在虚构一个个才子佳人的充满戏剧意味的美好故事。以柳永为代表的唐宋词中这类“代言体”作品,大多为歌女量身定做,在词中也是纯以女性的口吻凸显个性。从戏剧的表演角度来看,似乎词人在创作之初就已经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女性角色,词人自己则如同导演或编剧,更多是从动作、情节来展示古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社会人生。
综言之,以柳永为代表的男性词人在写女性代言词时,有意识、有目的地强化用文辞去展示女性形象的各个性格侧面——这样的词作,自然地呈现女性角色的动作性及戏剧冲突,及其可展演的场面特质,并依靠女性角色的语言来实现人物性格的刻画、心理的揭示、故事情节的展开以至人物活动的环境铺衍。这类词作,具有浓烈的戏剧化的表现效果而符合“剧诗”形态的标准。
结语
中国戏曲,包含音乐、歌唱、舞蹈、表演、说白等五种技艺,从类别来看,可归入歌舞剧,即用歌舞演故事的戏剧。与之相较,词的本名“曲子词”,原本就包含“词”和音乐“曲子”二者相加的戏剧意味。它是歌,也是剧本,有对话,有情景,展现一个特定场景;又有舞蹈,以歌、舞演一故事。词短小,更多像独幕剧。而联章组词,已经类似“曲”的体式(如《九张机》《踏摇娘》《商调蝶恋花·莺莺传》等)。词的篇幅短小,而作者善于提取事件中富有戏剧性的因素,通过悬念的设置来达到出人意表的戏剧效果,单纯的情节也能处理得具有冲突和波澜。这是因为叙事词中主体意旨的表达,主要通过具象的描述,与戏剧的角色再现方法近似。别林斯基说:“戏剧因素理所当然地应该渗入到叙事因素中去,并且会提高艺术作品的价值。”[4](P23)词通过规定情境中人物的语言、动作、体态,让人物作表演式的自我展示,在情节中包含情韵。受体通过角色的说话、举止、行事对其作相对独立、自由的审美感知,从而达到言少意多、意在言外的艺术效果。戏剧靠声色与活力打动受体。那些极具戏剧意味的词作也往往将人物、情节、场景等描述得有声有色、灵动鲜活,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睹其景。在唐宋词当中,我们能读到偏重于情节结构营造,一意追求纡徐曲折的传奇剧;也能读到淡化情节、简化性格,突出一个观念、一种氛围,或一层领悟的理念剧;还能读到以刻画人物性格或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为构思原点的心理剧。
历代词论著作当中,也多有论及词与戏剧之关系,如清代刘体仁论“词中戏语”云:“词中如‘玉佩丁东’,如‘一钩残月带三星’,子瞻所谓‘恐它姬厮赖,以取娱一时可也’。乃子瞻赠崔廿四,全首如离合诗,才人戏剧,兴复不浅。”[20](P619)清代张德瀛《词征》亦有论道:“杨补之《玉抱肚》词云:‘这眉头强展依前锁。这泪珠强收依前堕。’此类实为曲家导源,在词则乖风雅矣。”[21](P4086)宋代孔仲平《谈苑》卷五引黄庭坚语:“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诨,方是出场。”[22](P695)此为黄庭坚“以剧论诗”之明证。而黄庭坚所创作的词被后人称为“蒜酪体”,恰恰是因为其词作“酷似曲”。黄庭坚这种独特的词风与诗歌传统的审美风格迥然不同,而开后代曲风之先路。故沈家庄指出词之一体“顺乎历史文化发展逻辑而成为介乎传统的诗与杂剧之间的一种具有桥梁和中介作用的文体”[23](P380)。这个论断实际上已经明确定义了唐宋词中的戏剧性的真实存在,词的这一文学功能呈现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精神交流和对话活动,是人的觉醒在唐宋词中的体现,且在文学史发展链上与元代戏曲叙事文学接轨。因此,我们今后深入研究唐宋词的戏剧问题,更要把唐宋词置于文体发展史上,看到其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