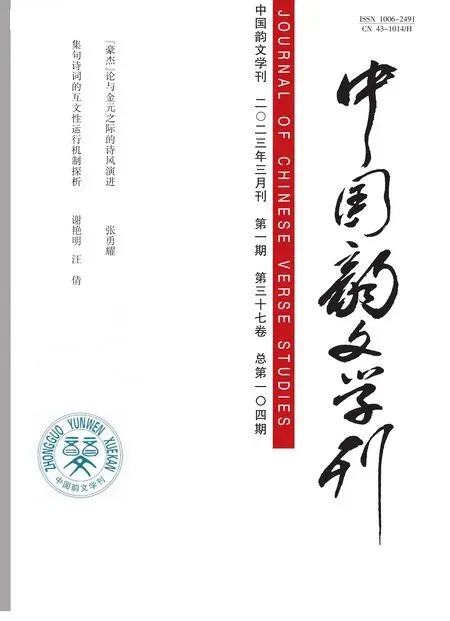归与不归之间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与“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之对比分析
2023-09-10成敏
成 敏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涉外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1)
一 引言
“文章憎命达”,中国诗人刘长卿(约709—780)与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都是命途多舛,借助文字来抚平心灵的创伤。刘长卿是唐朝杰出的诗人,他出身贫寒,屡试不中,直到四十多岁才考取功名,却又因为性格耿直,触怒权贵,被一贬再贬,背井离乡,四处漂泊。弗罗斯特虽然在文学方面成就斐然,曾四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但“年幼时父母相继去世,患病的妹妹也死在医院里,中年时妻子患病去世,年老时儿子自杀身亡”[1](P51)。死亡如同挥之不去的幽灵,笼罩着他的人生,他自己内心也时常涌动着自杀的冲动。二人 “同是天涯沦落人”,在命运的暴风骤雨之下,投向文学的怀抱寻求慰藉,用简单质朴的语言,浇心中之块垒。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以下简称《逢》)是刘长卿的作品,全诗四句,短小精悍: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2](P127)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风雪夜在树林停留》)(以下简称“Stopping”)系弗罗斯特的作品,正文内容如下(1)下文注出的本诗的相关译文均为本文作者自译。[3](P142-143):
Whose woods these are I think I know.(我想我知道这是谁的树林,)
His house is in the village,though;(他的小屋就在村里。)
He will not see me stopping here(他不会见我驻足在此,)
To watch his woods fill up with snow.(看他林中飘雪的美景。)
My little horse must think it queer(我的小马定觉奇怪,)
To stop without a farmhouse near(在无房无舍处停下。)
Between the woods and frozen lake(在树林和冰湖之间,)
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一年中最黑的夜晚。)
He gives his harness bells a shake(它摇了摇身上的铃铛,)
To ask if there is some mistake.(问我是不是弄错了。)
The only other sound’s the sweep(此外只听到)
Of easy wind and downy flake.(轻风和雪片簌簌声。)
The woods are lovely,dark and deep,(树林可爱,漆黑又深邃,)
But I have promises to keep,(但是我有诺言要遵守,)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还要走几英里才能安眠,)
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还要走几英里才能安眠。)
“人类思维逻辑是相近的。”[4](P54)人之为人,不论中西,有些情感与表达方式是共通的。两首诗在意象方面,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处。都是通过优美的语言,作用于人们的视觉和听觉,让事物在头脑中留下更加鲜活的痕迹,凸显出日常生活的质感,激发出人们的种种想象与遐思,启发头脑,感荡心灵。不同之处在两诗的结尾,《逢》为“风雪夜归人”,强调“归”;而“Stopping”则一再重复“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还要走几英里才能安眠)”,强调“走”,重心迥异的背后,是中西之间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
二 相似之处
“诗歌有以下特点:由节奏和声音造成的音乐效果,精确鲜明的意象,以及由词的内涵意义和典故所暗示的多层次的解释。”[5](P4)两首诗的相似之处在于,都让读者听到悦耳的歌,欣赏到美丽的画,激发起耐人寻味的思索。
(一) 和谐一体之音
“音乐与诗歌自古就有着极亲密的联系。”[6](P78)在音律上,两首诗都格律严谨,朗朗上口。
《逢》借助语音的呼应来加强语义关联、从而使全诗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如第一行的‘山’‘远’(shan,yuan),第二行的‘天寒’(tianhan)和第三行的‘门’‘闻’(men,wen)等都用的是半谐韵”[4](P53)。发音整齐而不失变化,语义和谐而不失发展。虽说“汉字尽是单音,在声的轻重上见出的节奏不鲜明。而英文音轻重分明,音步整齐,节奏很容易在轻重相见上见出,不须借韵脚的呼应”[7](P37-38),但是,作为一首英文诗,“Stopping”却既不乏轻重相间的节奏,又注意到了韵脚的呼应。全诗由四个诗节组成,轻重搭配井然有序,基本每行都是“抑扬格四音步”[4](P53)。每一节的四行中,第一、二、四行的最后一个单词押韵,形成韵脚。如第一节中,“know”,“though”和“snow”的/ʊ /音齐整,押成尾韵;第三行末的“here”虽似异类,实为造势,且看第二节中同样落于第一、二、四行的韵脚“queer”,“near”与“year”,所压的/ә/韵与“here”的/ә/音一脉相承,遥相呼应。同样的,在第二节中标新立异的“lake”的/ei/音又引出第三节的韵脚:“shake”,“mistake”以及“flake”;第三节第三行的“sweep”又为第三节的韵脚“deep”“keep”“sleep”“sleep”打下了铺垫;第四节末尾一/i∶/到底,收尾。如此,全诗韵式为:aaba-bbcd-ccdc-dddd,同中有变,变中有垫,浑然一体,一气呵成,既整齐有序,又活泼有趣。
(二) 风雪跋涉之形
就直观的形象而言,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与美关系最密切的感官是视觉和听觉。”[8](P69)在视觉与听觉的传达上,如在对象的选择、颜色的描绘、对听觉的诠释等方面,两首诗都独具匠心,让人感觉如见其景,如闻其声。
“美国学者阿恩海姆认为,语言是视觉思维(visual thinking)的‘辅助媒介’,即语言是人们描述视觉思维的工具。”[9](P135)目之所及,在视觉对象的选择上,《逢》选取日暮、苍山、寒天、风雪、柴门、吠犬等事物进行描绘,而“Stopping”刻画的是漆黑的夜晚、幽暗的树林、飘舞的雪花、村中的小屋、好奇的小马等事物,两者都是羁旅之见,夜幕之下,有山巍巍,有雪飘飘,有屋隐隐,有小动物点缀。在色彩的呈现上,都是黑白勾勒,见出素描的淡雅之感,而不是水彩的绚丽多姿;都是在漆黑的夜晚,飘着白色的雪花。《逢》特地点出“苍山”“白屋”,“白屋”不仅指房子简陋,一穷二白,而且是因为雪染而白;“Stopping”则写道“The darkest evening of the year”(一年中最黑的夜晚),白也好,黑也罢,都构成清冷苍凉、朴素悠远的风雪跋涉图。在听觉的诠释上,《逢》有“柴门闻犬吠”一句,以犬吠之声衬四下之安静;“Stopping”则有“He gives his harness bells a shake”(它摇了摇身上的铃铛)及“The only other sound’s the sweep/Of easy wind and downy flake”(此外只听到/轻风和雪片簌簌声)这样的句子,万籁俱寂,独显马摇铃铛声、轻柔的风声和雪片簌簌之声,更衬出周围的静,所以,两诗都有“鸟鸣山更幽”之妙。
(三) 耐人寻味之思
就目的而言,两首诗都是借景抒情,言有尽而意无穷,引读者咀嚼回味。透过两首诗的优美景致与和谐之音,又别有洞天,人们的情感、思想之门被打开,只是《逢》更重情思,而“Stopping”更偏哲思;不管是情思还是哲思,都投射出余味无穷的创造之美。
1.袅袅情思
就《逢》而言,只见一边是青山层峦叠嶂,旅人辛苦跋涉,急于投宿;一边是简陋的茅舍,在寒冬中更显清冷贫穷。夜黑,雪白,黑白交错;“苍山”远,“白屋”近,远近结合;“苍山”“白屋”静止不动,而“犬”在“吠”、“人”在“归”,动静交织。“意象思维使诗歌的句法由意象来主导,这样,诗人的情感和思想便可以通过‘意象叠加’和意象的自由组合获得神秘的意趣,显示出深邃的象征内容和无限的情感内涵。”[6](P85)透过诗中的黑白、远近、动静等意象的组合,可以想象,柴门之外,是饥寒交迫心慌慌的艰难跋涉;柴门之内,是热饭暖炕的欢声笑语。正因为有前面萧瑟苍凉的“暮”“远”“寒”“贫”做铺垫,后面的“归”才熠熠生辉,温暖的人间烟火气扑面而来,如龙之点睛,如夜之明灯,让人眼前一亮,心头骤暖,噬风饮雪之苦一扫而光。目前学界对所“归”为自己之家或他人之家尚存争议,若为自己之家,则流露的是中国人绵延千年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依恋之情溢于言表;若为他人之家,则投射的是中华民族,尤其是普通老百姓那份“进门即是客”的古道热肠,感激之意跃于纸上。“事实上,意象思维与诗人追求生命的感悟有关,对于诗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再现自然物象和风俗场景,而是要表达出内心的感悟和生命的意识。”[6](P85)不管所“归”是不是自己之家,温暖之底色始终未变。所绘之景与所表之情和谐一致,使景平添内涵与意义,不致流于空洞浅薄,而抹上几分含蓄与隽永之美;使情具有了形式与附着,不至流为空穴来风,正所谓“景物需经感情融注,以得其生命;感情需有情感附丽,以成其形象”[10](P41)。至于叩门之问、答门之声、进门之嘘寒问暖等一并省略,留给想象去填补。“想象力在形象思维过程中具有巨大的作用,它能使艺术家从自然和现实提供的素材中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的世界。”[11](P210)不管是温良醇厚的情感,还是想象空间的预留,都让作品情思悠悠,余音袅袅,其味无穷。
2.悠悠哲思
“Stopping”貌似简单,风雪之夜,作者在某个树林停留,沉醉于寂静之中可爱的大自然,但却感觉到未完成的使命的召唤,不得不离开此景,继续赶路。短短四节,惜字如金,末尾却连说两遍“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还要走几英里才能安眠),这一奢侈的重复似乎是在暗示:此中有深意。
“马”本是自然中之动物,却因为主人在没有农舍处停下而感到奇怪,这是自然之物染上了社会色彩;而人本是社会的一员,却在雪夜的树林,即大自然的怀抱流连忘返,由此可以见出自然与人之间的互通、互换,圆融一体。如果将雪花飘飘的“woods”(树林)看成自然的原生状态,看成平静心灵的安放之地——所有烦恼烟消云散的理想之所,那么“我”停留在树林感受到的就是天人合一、美丽和谐、共生共荣的美好境界;而冒雪前行的“miles to go”(还要走几英里)则让人联想到人生之路,艰难,漫长,却不得不走;“sleep”(安眠)指历经辛苦之后的长眠,暗指死亡。所以这句话就充满树林中的安逸与树林外的责任的对抗,提醒自己,人生短暂,不要沉迷美景而忘了社会责任,赶路要紧。
但是,神秘、深邃的树林“在让人感到独具魅力的同时也可能是危险、残忍的”[12](P32)。就空间而言,当时所处之地是“Between the woods and frozen lake”(在树林和冰湖之间),“frozen”(冰)让人看到冰冻、静止、死气沉沉,给人以苍白、凄清之感;就时间而言,是“evening”(夜晚),根据荣格对原型意象的分析,有关于水的循环的象征“通常分为四个主要的阶段,一年中的四季即一天中的四个时间段(早晨、中午、晚间、深夜),水循环的四个方面(雨水、泉水、河流、海洋或雪),生命的四个阶段(青年,成年,老年,死亡)”。[13](P160)在“Stopping”中,对应的时间是晚间,但“我”还在前行,所以可能延续至深夜,再加上水循环中对应的“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生命的第四个阶段:死亡。简而言之,“‘日出’所喻指的是出世、创造、启蒙;而日落则喻指死亡”[14](P267),那么夜幕之下、冰湖之畔的树林就成了死亡的象征,相应地,诗歌最后两句话的含义也就变了,指向了要战胜死亡,完成未了之事。
“在日常生活中,对意义的追求因太含糊或太复杂而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或摒弃。但是,它存在于每个人、每代人的灵魂之中。”[15](P38)到底“woods”是理想之地,还是死亡之所,这种不确定性在读者心里激发起强烈的好奇心,为其留下广阔的自由解读空间,从而推进理解的深度。眼前所见只是雪夜的树林,而心中所想可以阡陌纵横,气象万千。通过毫不起眼的日常生活点滴,捕捉到人类思想与情感中转瞬即逝的美,并洞察出更深邃、更具启发性的含义,这是文字的丰富,也是思维的神奇。
3.思之美
就语言本身而言,不管是《逢》的袅袅情思,还是“Stopping”的悠悠哲思,都让人看到语言的弹性和收放自如之美。“究其本质,语言就是多功能的,以致连最简单的语言所传达的意思都不止一种。”[16](P30)语言文字的丰富性本身就为多样化的解读敞开了大门。“中文可以一音多义,多义字较多,多义字多了就容易造成一种模糊感,就是表义模糊。它一字多用,字义就容易宽泛、笼统。不过它既然笼统的话,它也同时就可以简洁。它既然简洁,就容易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就有综合能力。”[17](P126)所以就有《逢》中“归”的模糊之美,以及惜墨如金的字里行间所留给读者的无穷的想象空间。而英文“具有精密的语法,性、数、格之类一应俱全,主、谓、宾、定、状、名、动、形、数、量、代、副、介等,词性界定,毫无苟且;句法严密,词序井然。故具有极强的逻辑形式因素,其逻辑暗示诱导力亦极强”[17](P138)。所以“Stopping”不像《逢》一样,需要读者借助想象去填补各种景物画面的细节,但是却诱导读者对树林、诺言、旅途等景物所内含的意味及其所勾勒出来的逻辑真理孜孜以求。
就思维的舒展与享受而言,Frost曾说:“现在我正说着一样东西,但当我说那个时,可能我还说着更多。”[18](P23)诗歌的意义也依赖于这些“更多”——纸上的字映入眼帘,在脑海中盘旋,不停地启发读者去琢磨其中所蕴含的层层叠叠的含义,这种“思想的漫游”[19](P1460)所带来的,除了隐晦之乐,更有创造之乐。这种创造空间的保留是熠熠生辉的,因为“我们共同希望的就是某种形式的复活,这希望虽然渺茫却从未停息过”[20](P1329)。于读者而言,可以拥有更加酣畅淋漓的阅读,在“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自由中,在对意义的追寻与捕捉中,在各种想法的引发与碰撞中,思维的细胞变得活跃,头脑的生活变得丰富,从而享受到思想的翱翔、精神的滋养与审美的愉悦;于作者而言,其一成不变的文字因读者的不同和阐释的差异而得以常读常新,生机勃勃,实现某种程度的“复活”,甚至是青春永驻。思想的交锋带来的,不仅是作品内涵的不断深化,更是作者本身自我认识的拓展与自我价值的实现。
就人性而言,“每个人都反对他人的偏见,而偏好自己所献身的真理”[21](P70)。别人的想法只被视为偏见;只有经由自己的头脑苦苦琢磨出的东西,才被去除偏见的外衣,戴上真理的桂冠,大摇大摆登堂入室。所以,作者不宜把读者灌得太满太实,留出思考的空间更能讨喜。不确定性与未知能激发人们无限的好奇与探索之心,“凡是引起我们的欣羡和激发我们的情绪的都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我们对事物的无知”[8](P126)。不确定性带来的无限可能,最能拨动读者的心弦,在其心中唤起难能可贵的认同感,以及久久不能消散的回响。
三 相异之处
诗的最后,《逢》以一句“风雪夜归人”收尾,指向“归”;而“Stopping”则一再重复“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强调安眠之前还有路途遥遥,指向“不归”。同途殊归,其由而何?中西方有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氛围,“决定了他们对生命美感的理解有所不同,而且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价值规范”[6](P97)。中西之间不同的文化价值规范大体在于:中尚集体,西重个人;中偏感性,西重理性;中好统一,西重对立。
(一)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中国人眷恋家庭,富有集体主义精神;西方人个人主义思想比较突出,所以在“Stopping”一诗中频见“I”(“我”),而在《逢》则不见提“我”。
在《逢》中,“我”之存在清晰可感,而无一处提及。中国人信奉集体主义,而集体主义强调人的依赖性——与景物、与动物、与他人之间的依赖性;对中诗而言,有景有境则有情有人,无须标榜。如“‘日暮苍山’所写的景是日暮天寒、苍山飘雪,景中不含任何感情,然加上‘远’字,就包含了感情”[22](P53)。一个“远”字,让一个孤独凄清、惶恐不安的旅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又如“犬吠”,“犬吠是个意象,隐意是有主人”[22](P53),既有犬,则有主,即人也;再如“风雪夜归人”,风雪之夜,柴门一开,温馨一片,展示出来自他人的物质与精神的支持的重要性,展示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虽无“我”字“人”字之出,然层层关系之中,处处可见“我”和他人之踪影。“为文若河流入中国,或隐或现,或绝或续,而渊深长。今人恐句不属,字字挨粘,无文胆。”[23](P7)人、对话等,虽隐而出,使全诗言简而意远,此乃“文胆”之所在,若刻画得太满太实,反失其空灵悠远之美。
“Stopping”中六处提到“我”,其中五次以主格“I”出现,一次以宾格“me”出现,“我”之存在赫然在目。弗罗斯特本人也曾强调:“因为背景,有些人称我为自然诗人,但我不是。在我的诗歌中总是存在别的东西;所谓‘别的东西’指的是在自然的背景之下,总是包含人的存在;……我相信我们把人摆在最重要的位置。”[24](P207)在诗中,彼时彼地,黑色的树林茫茫无边,白色的雪花漫天飘飞,整个世界非黑即白。眼前所见,单一,重复;心中所感,凄冷,孤独;在这一片寂寥之中,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形只影单的存在。但是,任凭风雪肆虐,职责仍在心头,仍要继续前行,所以在末尾一再重复“And miles to go before I sleep”(还要走几英里才能安眠)。个人主义强调自我实现,这种责任与担当的背后又何尝不是写着对个体自身的重要性及能力的自信呢?
(二) 感性与理性
“世界本质上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他们属于伴随结构的真实内容,即主体、客体和媒介。”[25](P449)面对大致相同的主体——雪夜的树林,因为媒介的不同——刘长卿与弗罗斯特所代表的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呈现出的客体——树林所具有的内涵意义也截然不同。“中国一个主要的传统话语规则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与西方以‘逻各斯’为中心的哲学文化信仰有明显的异质性。”[26](P181)所以《逢》引发的是漫天情思,用想象去填补风雪夜归之后的寒门温馨;而“Stopping”则是引发绵绵哲思,用智慧去追寻剩下的几英里到底指向何方。
中国文学“将重点放在天伦之乐,吊古伤怀、颂祝主人、亲朋赠答、感时忧国等伦理情感的抒发上”[11](P258),表面看,《逢》表达的是风雪之夜艰难跋涉、终得一隅之安的欣喜;事实上,是一个历经坎坷的封建文人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层思考,表达风吹浪打之后“不如归去”的隐逸与解脱之心。作为一个盛唐末季的诗人,作者的孤愤、无奈是可以触摸到的。不管是表面还是内在,这首诗都让人看到“情”的暗流涌动,这是风吹浪打之下生命之流的绵绵涌动,“正是情的存在,才有宇宙,才有大千世界无穷循环的存在”。[27](P14)
与中文的图画性相比,英文更多的是“强调了人的智力运行轨迹”[27](P6),这种智力运行轨迹在“Stopping”中清晰可辨。在诗中,“woods”究竟是宠辱皆忘的诗意空间,还是扼杀一切的死亡之所呢?整首诗究竟指不要沉迷美景而忘了社会责任,还是指要战胜死亡、完成未了之事呢?这种抽象性与模糊性恰恰是世界的本质与真相的体现,因为世界原本如此,难以捉摸,难下定论,人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本身。Pope在其AnEssayonCriticism中,给“wit”(智慧)下了一个有名的定义:“真正的智慧是装扮得恰到好处的大自然,一直是人们心之所想却从未好好表达过的。”[16](P15)智慧是无形的,在某些情况下,文字对事实的亦步亦趋也许只会造成真理与价值的渐行渐远,所以不如留几分空灵,让读者结合既往的生活经验,去凝炼出文字之中闪耀着的智慧。智慧如同大自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外部的装点不过是画蛇添足,言语的框定不过是词不达意,既如此,不如让智慧之光闪耀在人们的心中,让其流连于人们头脑的空间,焕发原始的生命力,而只在纸上留下可见可感可以付诸笔墨的物理的事实。在从有形走向无形的过程中,已知与未知、风景与哲思、作者与读者不断接触、交流、共舞,实现思想的生成,达成彼此的默契。通过对诗中所运用的暗喻与象征手法的捕捉与领会,树林、诺言、旅途等散乱之物汇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并得以神形兼备,和谐而不失隽永。寻常的物体、惬意的自然、表面的简单都是欺骗性的,潜藏着的是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冷静思考,对生命主体的深刻认识。
(三) 统一与对立
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农耕文化,使中华民族倾向于在一个地方安居乐业,有很深的家国情怀,和为贵的思想深入人心。在中国人眼中,“虽然事物都是由不同性质的对立因素(阴阳)构成的,‘阴阳’是指世界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如上与下、天与地、动与静、升与降等等,但阴阳双方又是互相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28](P30)这种对立双方的互相依存在《逢》中清晰可辨:人与自然是水乳交融的,人类的“白屋”就在大自然的“苍山”之中;人与动物是和谐统一的,“犬吠”之声让跋涉之人欣喜地感到人烟将近,让屋里之人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寂寥冬夜迎来外面世界的几许繁华与热闹,而如果是家中之人,则更添几分忐忑不安之心终于落地的安然;自我与他人是互相支持的,一个“归”字尽显相见之暖,迎面而来的是柴门之内的嘘寒问暖、热汤热饭、其乐融融;动与静、奋斗与安逸是相辅相成的,夜幕降临便静静地安歇,暂时的安逸并不排斥白日继续赶路、继续奋斗,而且“静”是为了更好地“动”,二者互相转化……在这种令人舒适的和谐统一之中,大体可以见出中国哲学“是一种安宁、快乐的人生哲学” 。[17](P63)
西方游牧业比较发达,生活方式灵活机动,在面对各种环境之下的形形色色的大自然时,人们的探险精神与征服欲被激发出来,这就使得西方人“过于强调事物的两种不同性质之间的对立与斗争”[28](P30)。所以,在“Stopping”中,看到的是风雪之夜的坚执前行,因为人与自然的对立——自然的美景令人沉醉,然而人类社会的责任在召唤;因为动与静、奋斗与安逸的对立——似乎只要停下来,静下来,就是安逸,就否定了奋斗之心;因为自我与他人、人与动物的对立——“我”选择在没有农舍之处停下,而随行的小马也并不能理解“我”为何在没有农舍之处停下,因为别人的房舍并不属于“我”,别人也很难理解“我”,所以不管是出于一份“莫愁前路无知己”的豪情,还是出于一份“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苍凉,“我”都只有继续前行。这也让人看到西方文化的特点,“它不是为了美,主要是为了强有力”[17](P40),雪夜的跋涉彰显出的,是人类的坚韧与决心。
四 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与“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在音、形、思等方面都存在异曲同工之处,这说明整个人类,无论中西,在对生命美感的理解与把握上存在共通之处;而中西方彼此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所以在两首诗的末尾处,《逢》与“Stopping”分别指向的是“归”与“不归”,这就可以追溯到两首诗背后的文化差异——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对世界的感知相对感性,善于发现事物的不同性质之间的统一,所以有“归”的圆融与喜悦;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对世界的感知相对理性,强调事物的不同性质之间的对立,所以有“不归”的傲世与坚韧。两诗所投射出的中西文化的相同之处是沟通的基础,不同之处意味着双方还需要更多的交流。“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29](P556)东方西方,各有所长。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不是一座孤岛,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在披荆斩棘、奋勇前行的同时,多一份对他人的理解与信任,多一份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在殚精竭虑、运筹帷幄的同时,保留几分天真,保留几分“难得糊涂”的圆融与洒脱;在风雪之夜稍作休息之后再出发,在天亮之后再继续追求剩下的几英里(miles),怀着人间烟火的温暖,去追求鸿鹄之志的高远,为全人类而不仅仅是为自己创造出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岂不比孤胆英雄夜以继日的风雨兼程更添几分豁达与崇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的:“世界命运掌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30](P60)中西之间只有尊重多元共生,才能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