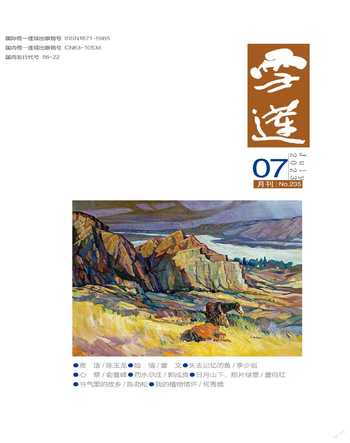失去记忆的鱼
2023-09-06李少岩
一
小区大门往右,约一公里处,有一座林深静幽的城区公园。闲暇时,我喜欢去那里走走。要说,人是一种习惯性的动物,兜兜转转,往去来回,时间久了,我信以为,公园成了我心里的某种寄托,或者说,我已成为公园的部分内容。
同住小区的老张,隔三岔五邀我去公园遛弯。他住小区南段13栋,我住2栋靠近小区大门,我们之间隔了一段不远的距离。每次出门前,老张会事先给我发微信:大门等我,就过来。如果能去,我简单地回复他:好。便利索地下楼,站在路口抽烟等他。不到一支烟的工夫,一个敦厚、魁梧的身影,从远处甬道里优哉游哉地晃过来。时不时地,老张会给我兜里塞两包烟,嘟囔地说,随礼得的,家里也没人抽,给你。
一路上,我们很自然地聊些俗世生活,泛泛而谈,是那种浮皮潦草的层面,因为我们彼此心知肚明,世间那些囫囵事儿,有许多不可言说的隐喻。老张从事城市规划工作,与他结识多年来,天南海北地聊,他从不涉及工作和家庭,只晓得他妻子在银行工作,女儿在西安读大学。私下里,他聊得最多的是钓鱼那门经儿,什么水域用什么鱼竿?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什么鱼用什么饵料?他说得五迷三道,有板有眼,而我能记住的,寥寥无几。我能理解,老张作为一位理工男,平素也就好这一口。老张反驳道,我没有你的文字天赋,在办公室里,你发在报上的文章还是要拜读的。我当然明白老张口中的拜读只是谦辞,权当调剂,一笑了之。有几回,老张也曾奉劝我,老李,你别老是坐在屋里,有时间出来活动一下,下次跟我一起去钓鱼,你有兴趣吗?这期间,老张的确打过几次电话,说要开车来接我。我婉言谢绝了。
我拒绝老张的邀请,倒不是我有多无趣。而是我认为,每个人该有自己独享空间,他的世界我不去介入,我的场域也不必外人涉足。人与人之间最熨帖的相处方式,就是在心里保有些许隐秘性。一如这园里诸多草木之间,它们相安相知,向阳而生。
进入树影婆娑的园区小径,满眼葱茏的原生植物。松木、杉木、樟树、冬青、桐树、柏树,合欢、山樱、杜鹃,以及许多叫不上名的树种,这些草木挤挤挨挨、以亘古不变的信念,托举一种致力向上的精神意向。风一摇,枝叶间掀起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树们似在絮叨云雨风月,又似在述说彼此的寂寥。我不禁要想,置身这么密集的空间,如同城市摩肩接踵的钢筋丛林,不知这些草木有何感想?老张告诉我,这里原来就是一片繁茂的林子,二十世纪末,城市开始大规模扩建,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器,似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奔涌而来。开始施工之前,有相关技术人员实地踏勘,一眼相中了这片林子。经过一番缜密、细致的考量,几经周折,林子被幸运地保留了下来,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
尔后,城市的建设者分别从东门、南门、北门依次深入。三条大道往林中延伸,然后分岔成许多小径,这些蛛丝一般张开的路网,犹如人体内的毛细血管,使林子有了愈发丰富的肌理。这些年,林中每条路我都悉数走过。每条路有不同的景观,每道景观都是不可复制的版本,像极了个体生命的不同境遇。
走过一条狭长的柏杨林道,在一个人工湖边,我与老张停住了脚步。湖水茵茵,清明澄澈。一群花色各异的锦鲤潜在水中,它们时而左、时而右在湖中尽情地游动,那阵势,似在饰演一场水上芭蕾,又似一众无所事事者在闲庭信步。在临湖台階上,一个小女孩在母亲的指导下,正在往水里抛撒鱼料,那些粒状的鱼料,成抛物线均匀撒在水面,溅起沙沙的音律。刹那间,鱼儿们乱作一团,它们争先恐后地抢食鱼料,原本风平浪静的水面,顿时掀起一波富有节奏的水花。女孩兴奋地跳了起来,不时发出喔喔地欢叫。那会儿,女孩的欢笑声犹如快乐的音符,在山水交融的空间里渗透、漫溢。天地间,俨然一幅意趣横生的水墨丹青。
老张静默无声地走过来,朝湖水睨了一眼,他若有所思地说,人要是像鱼一样快乐地活着,多好啊。老张的表情凝滞而深邃,继而,他陷入一阵沉默,脸上浮现一抹不可名状的落寞。老张突兀的话语,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意味。换做平时,老张总是一副豁达、开朗的状态,此刻,经由他口中道出来的怅然,令我感到莫名的惊诧。
水汽漫漶,云淡风轻。间或一阵山雀清脆的啁啾声,隔着一汪清水,从远处的丛林里逸过来,灵动,旷远,漾在水波潋滟的湖面上,起起伏伏,宛如一曲撩拨心门的天籁之音。这时,女孩手中的鱼料已经抛撒完了,年轻母亲拽着女孩转身离去。远远地,女孩一步三回头,一脸意犹未尽的依恋。年轻母亲安慰着女孩,说,妞妞,我们明天再来哦。
我就想,妞妞一定会来的,她广阔的世界里有无限可能。
不绝如缕的蝉鸣声,如水一样漫过林间,时近时远,萦绕耳际。
一时间,母女俩的背影消失在林荫中。一湖绿水又恢复了起初的静态,鱼们失意地在水中巡游、迂回。不一会儿,它们像接受了某种指令与召唤一般,列为一个层次分明的纵队,在水中周而复始地回旋。我暗自思忖,鱼们是在找寻投料的女孩,还是它们心中另有隐情?忽而又想,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在女孩仓促离开之际,还来不及梳理心绪,鱼的大脑早已忘记了心中的失意,忘记了那些曾经果腹的饵料。
那一刻,我看到时间的影子汇入湖中,鱼的世界里,光影浮动。
二
进入秋天,来自远山的风儿,一阵一阵捎来飕飕的凉意。我感觉时光如白驹过隙,一粥一饭,一汤一菜的日子太不经过,许多还来不及料理的事物,似一场风掠过城市丛林,不着痕迹。恰如园内那一汪湖水,水面之上,貌似一派岁月静好,殊不知,水面之下,暗流涌动,掩藏许多不为人知的内涵。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跟老张会面交流,一星半点儿信息也没有,我心里难免有些空落。给他发了一个握手的微信图像,一连几周,也不见他回复。便想,大概是在户外钓鱼吧,山高路远,荒郊野外的,手机自然没有信号;又想,人这一生,在世间中沉浮,谁没有冗务缠身的时候?一个周末午后,阳光温煦,我在书房打字累了,点燃一支烟,随手翻一下手机,仍然没有老张的信息。我随即关了电脑,一个人悻悻地朝公园走去。
我选择从南门进入林间,源于一种旷日持久的习惯。每次来到这片熟悉的水域,一群锦鲤会如约出现在眼前。我不由揣摩,这是原来那一群锦鲤?又或是另一伙不熟之客?每次来到湖边,它们总会适时赶来,似在与我共赴一场灵犀相通的约会。令人遗憾的是,我没能遇见母女俩,这让我无端生出一些郁闷。遂想,这苍茫人世间,兴许真有一种宿命的因子在空中浮游,看似难以触摸的介质,无所循行,却又无处不在。这个世界太深远了,来去匆匆,即便栖居同一座城市,不期而遇的概率能有几何?
这样想着,我也会停下脚步,在湖边长椅上静坐一会。我的目光不由地滑向湖面,水波浩渺,空灵而静雅,目之所及,一抹跃入眼帘的幽蓝。在湖之中,一前一后,两艘脚踏游船舒缓地朝湖心划去,木浆拍打水面的啪啪声起起落落,一时间,空寂的湖面陡生几许活力。
一行白鹭贴着水面滑过,眨眼间,箭一般射向远山的空茫之中。
在我凝目远眺之时,耳畔传来汪汪的犬吠声。不远处,一条长椅上坐着一位衣着考究的老人,身旁拴着一条拉布拉多。老人在平静地观察湖面,他似在思索什么?那狗并不安分,看到水中的鱼儿嬉戏闹腾,不时地狂吠几声。狗的视力局促有限,而在面对动态事物时,却有着极其灵敏的嗅觉和听觉。此刻,老人与狗,如同定格湖边的静物,岿然不动。这让我想到安东尼的雕塑艺术,在他四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始终在探索人体与空间的关系,他始终认为,孤独是天地间独有的一种感觉,是造物主赋予生命一种纯粹的存在。
观澜安东尼的雕塑艺术,有一种灵魂之门瞬间洞开的领悟。你不难发现,他的作品完全脱离传统艺术的表现方式,或躺,或坐,或悬空,或兀立大山,或面朝大海,在不同的时间,会有不同的阐释。有那么一会儿,我对湖边老人与狗有了兴趣。我走过去试图与他搭讪。须臾间,我放弃了这种贸然的行动。许多时候,不打扰,彼此保有一种距离,就是对别人应有的尊重。
在万象丛生的生活圈,你能遇上某个人、摊上某件事,冥冥中自有对应和安排。
有一段时间,我来湖边兜圈,总会遇见那位老人独坐长椅上,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系在他身边的那条拉布拉多,不时警觉地瞄我几眼,眼神里夹带几份戒备,几份对老人的依恋。老人目光从容地打量我,眼神里富含几丝慈祥,他语气平和地对我说,坐一会吗?那一刻,我脑海里几乎没有犹豫,便应允了。一阵聊下来,老人告诉我,他是一位退休的国企职员,老伴前两年离世了,他有一个女儿在国外工作。女儿挺孝顺的,也曾接他在那边呆过一段时间,在异域空间里,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他感觉日子过得寡淡无味,如坐针毡,索性又回来了。老人说,没事就来湖边看看鱼,像鱼一样快乐地活着。
老人沉浸在一种冥思的状态,他那份专注的样子,似一位满腹经纶的僧侣,正在禅坐入定。很长时间里,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的意愿,用静默面对湖水,高天流云。某种意义上,似一种形而上的契合,殊途同归。事实上,这样的静默相处不止一两回。起初我们能够畅聊一些时事话题,然而聊一会儿,便遁入在沉思默想中,直到暮色四合,众鸟归隐,我们才互道珍重,各自散开。
有一阵子,我在湖边没有看到那位老人,内心萌生些许的隐忧,一丝不祥的意念在心间时断时续地弥漫。好在,这一切担忧是多余的。时隔不久,某个黄昏再次相遇老人时,我问及他的近况,他说前些天忽然降温,身体染了风寒,一个人在家调理了一些日子。随后,老人兴奋地给我看视频,是他女儿从大洋彼岸发过来的,手机画面里,小外孙在自家草坪里玩球,一脸淘气的样子。老人说小外孙叫彼特,今年已经6岁,在女儿引导下,能用含糊不清的母语叫外公。老人聊起稚气十足的小外孙,他老迈的脸颊,显现一抹绝无仅有的笑意。
立时,我想到亲情这个词汇,这种根植于血脉的情感元素,每个人有不同的诠释、不同解读方式。这如同我们饱览群书,一万读者心中,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的形象。
老人不经意地问起我的职业,我一时语塞,因为我实在不愿透露,我每次与他聊天,是在为自己搜集写作素材。我说我是教书的。诚然,相较于写作,教书这份职业似乎更加稳妥,事实是,我也曾有过短暂的教书生涯。我忽然发现,现实生活总是多维的呈现,仅仅浮于生活的某个表象,这样的写作方式是蹩脚的,在时间的长河面前,这些所谓的文字堆积,如一潭死水,毫无意义。
面對澄清的湖面,老人眼神是笃定的,一如湖水,波澜不惊。
三
窗外,一场一场恣意挥洒的冬雨,让我领略了漫天席卷的寒凉。那天,我在书房看书,是梭罗的《瓦尔登湖》,读到冰天雪湖,恍然间,有一股来自遥远的湖风穿越时空,呼呼啦啦地朝我扑面而来。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噤。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堪称经典的不朽之作,每一次打开,我能从中汲取绵延不绝的能量,在浑然不觉中遁入澄明之境。
萧索的冬日,很容易叫人趋于混沌中。那个午后,我沉浸在书中某个章节,搁在桌上的手机响起一串铃声。我瞅了一眼,原来是老张发来的微信。这份突如其来的信息,令我心里顿生几许怨艾:老张,你这家伙潜水也太深了,四五个月不出来冒个水泡。遂想,暂且不急于打开,也不回复信息,让你体会等待的滋味。
不一会儿,一个陌生电话打过来,我轻摁了免提键,是一位女孩低沉的声音,她颇为拘谨地问,你是李叔吗?我不解地问,我是……你是哪位?电话那头传来微弱的啜泣声。我一阵纳闷,心想,这是唱得哪一曲?电话那头稍作停顿后,似在极力调整自己的情绪,她局促不安地说,我是老张的女儿,我爸昨晚已经去世了。
我脑袋一阵炸裂,有一种陡然而生的眩晕。我问道: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女孩停止了哭泣,她解释道,李叔,我爸昨晚11点钟在医院去世了。
放下电话,我脑屏似在不断地刷新。人生一世,总会有许多事儿,让我们猝不及防。回想那天在公园,老张面对湖中畅游的锦鲤,他那种异乎寻常的表现——我难以想象,一个人需要多么强大的自控力,才能让自己的心灵平静如水?生命中没有经历过悲欣交集的长夜,哪有大彻大悟的终极拷问?良久,我从悲恸中回过神来,连忙打开老张的微信,是老张妻子用他手机发来的讣告。至于信息内容是什么,这已经不重要了。
一个生命在悄无声息中陨落了,犹如划过夜空的流星,冷艳、独孤,忽闪而过。
令人心悸的殡仪馆,在铅灰色的天空衬托下,隐隐地凸显着肃穆的气息。哀乐声声,烟尘袅袅,一场庄严的追悼会正在如期进行。主持人用极尽缓释的语速总结概述了老张的生平,言辞里释放着浓浓的哀思。之后,老张女儿出来致答谢词,细数父亲生前对自己的疼爱有加,几度哽咽,声泪俱下,父女之情从她浅显的文字里流淌开来。
追悼会散场时,老张妻子叫住了我,希望我能停留一会儿,她低声说,李老师,你是老张生前好友,他有一样东西要我交给你。我不禁愣住了,我与老张只是君子之交,清淡如水,能有何物交还?正在惊愕之时,老张的女儿走过来,她双手将一本褐色笔记本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原来是老张的一本剪报本。这些年,他竟然将我发在报上的作品收集在一起。老张女儿对我说,李叔,我爸清醒时曾经交代,一定要把它交给你。
我忽覺眼角湿热,内心颇感一份意外与沉重。我缄默地合上笔记本。那一刻,我不知该说些什么?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物事,语言难以触及内核。通常,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像鱼一样快乐地活着,而在骨感的现实中,我们能够像鱼一样快乐吗?老张犹如汹涌人潮中的一滴水,如今,这一滴水已经回归大湖,应该是他蓄意所要寻找的归宿吧。
又是一个日暮时分,夕色染红了远方的天际。从小区出发,循着那条熟悉的路径,我又来到城区公园那片水域。时值隆冬,行人稀少,我百无聊赖地环湖一圈。自始至终,我没有遇见那位老人和他的拉布拉多。这一次,我心里没有太多失落。我就想,待到明年春暖花开时,他一定会来的。即便,他以后不会再来,那也是人生中无法回避的常态。
我坐在那条长椅上,放目四野,湖面岑寂,远山空濛;几只山雀在林中叽叽喳喳,似在商议什么?我听不懂它们的语言,但我知道,它们应该是快乐的。生命中的每一次相聚,弥足珍惜。我将目光投向湖中,那些花色各异的锦鲤已然不见踪影。想起老张曾经说过的话:一入冬季,鱼们大多躲进深水处,和人一样开始猫冬了。
我在想,这个漫长的冬季,躲在深水处的鱼们,会有老张所说的快乐吗?
答案有些模棱两可,似有若无。显然,鱼的世界里,隐匿太多人类未知的密码。或许老张从获知病灶的那一刻起,他已经通透了。想来,一个内心通透的人,大约已经遁入物我两忘的境地吧。生命中所有的体认需要时间。我像一尾失去记忆的鱼,漂在川流不息的人海中,一个人简单、深情地活着。
【作者简介】李少岩,原名李绍岩。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怀化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海外文摘》《雪莲》《散文百家》《中国校园文学》《中国铁路文艺》《安徽文学》等四十多家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