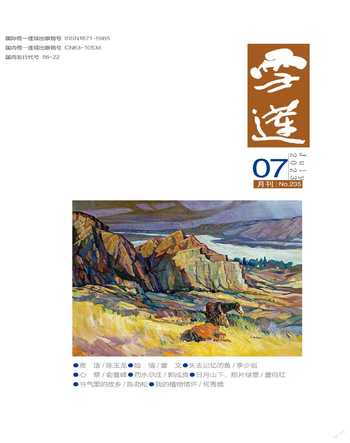恍惚人间
2023-09-06刘群华
土 箕
没有谁会用心关注土箕。我没有。但父亲是个例外。
父亲对土箕的热爱,与对刀和锄头的热爱一样具有浩荡而苍茫的思想。父亲心里,土箕像故乡的一朵云,从农家的屋檐下掠过,留下一片片斑斓的竹影。我心中,是篾匠剖竹织了土箕之后,故乡的一半山峦钻入土箕,另一半河流,在霞光的映照下,戴上了玫瑰般的冠旒。
在故乡,土箕显得苍古、凝重、华灿、庄严,好像超越了人的气度和智慧。
土箕占据了父亲的肩头。由一条扁担挑着,在淅沥的细雨里,在红叶或白雪中,在缀满露珠与鸟鸣的天穹下,土箕摇晃着深情或忧伤的生活。故乡的阳光,依然浑圆和饱满。在土箕之下的山涧、溪流,摇曳着幽蓝的兰花和雾霭。也许,父亲的肩膀太蛮荒厚重了,悒郁、痛苦甚至悲怆的印痕,让我平实朴拙的文字,无法寻找到淡淡的心痛。
土箕在父亲的肩头蹀躞迈步,并且仰头嗥叫。这时的土箕盛满了土豆、红薯、白菜、萝卜,沉甸甸的担子让土箕的嗓子里似乎有铜质的颤音,哀婉得有些抒情。我坐在土坪上,门朝流水,背靠高山,只要抬起頭来,就能望见山顶的层林、云岫和若隐若现的悬崖,只要低下头去,父亲上坡的脚步就像汗水上闪动的光,美丽、诡异、神秘。但从父亲的喘息中,又想象到他的胸膛里有只雪豹在出没,在游荡的血液中有种高雅高古的韵致。上坡的土箕仿佛拖曳着父亲的身子,对我而言,足够震撼了。毋庸讳言,父亲挑土箕的记忆,通过一圈圈转动的胶片,定格在我的心里。
在一处隐秘的山路上,此地荒草丛生,茅草花如雪飞扬,还有青翠的松树,枝柯虬曲,遮天蔽日。那里有我家的几亩水田,父亲必须把家粪挑进田里,用以肥沃新莳的稻禾。这时的父亲,忽明忽暗地行走于山路上,大只大只的蝴蝶扑进土箕。画面仿佛一个纤尘不染的童话。而山路之下,故乡的牛羊、灶烟、草垛、庙宇,或卧或立,或聚或散,也都汹涌至父亲的土箕。
父亲拥有土箕,土箕也拥有父亲,人和物之间的心灵是相通的。在故乡的天蓝和水蓝之下,土箕里盛满的冰蓝、墨蓝、宝石蓝、纯粹的蓝,都是作物的蓝。在这些蓝里,竹篾的光线射向波浪氤氲起的绯红或桔黄里,那么缈幻、神秘、空茫而无知无觉。在我的眼中,土箕围绕着父亲的灵魂,绽放着花朵,是对一个家庭。这是一种朝圣的方式,父亲在土箕里磕着长头,寻找内心的神灵。当傍晚来临,父亲的土箕衬托出流泻的晚霞,白色的、黄色的、紫色的、橙色的、黑色的云,宛若柔美、怡静、纯朴而圣洁的花,静静地开在村庄里。
土箕横亘于肩头或手里,与父亲的时光一同流逝。它也有腐蚀破败的时候,这时,它便沉沦于一炷篝火,照亮清晰或模糊的月光。父亲走进了土箕的光亮中,天上的云朵和尘埃,地下的青草和沙砾,都被空旷的宁静所笼罩。我的身边横卧着一具土箕的骨架,但不知这对土箕在父亲的肩膀上匍匐了多久。
应该把它烧了!我有点憎恨。
父亲说,留下吧,这是你祖父挑的土箕。
对于祖父的土箕为什么父亲一直保存,好像是一种未消逝的声音在牵引着父亲的思念。我坐在一棵干枯的树墩上,看着土箕指向遥远的远方,呈现出一种旷世的绝望与孤独。其实,于我而言,这对土箕的骨架已经不是竹篾,而是一种精神的存在。
有一年,父亲的另一对土箕也老了,如迷乱神奇的黑洞,这对土箕之所以老得快,是因为它挑了一个冬天的泥石。父亲望着坍落的泥石,拖出了新的土箕,可是泥石的磨砺让它的躯体很快烟消云散了。这堆空旷荒寒的泥石,父亲以坚忍的目光打量着它的傲岸和挑衅,用土箕把轰然落地的泥石装进又倒出,肩膀上的老茧更深沉了,从父亲所在的角度望过去,能看清从时间深处破尘而出的一种忧郁和苍凉。
宿命如此,好像任何人没有逃脱。土箕隐喻了人的悲伤和迷茫,还传递了思想的遮蔽或掩盖。我望着清空的泥石和残破的土箕,月光清冷洁净,荒草静默死寂,峡谷间升腾、缠绵、缭绕的我试图穿越土箕的荒原和沼泽,缓缓地落在父亲的怀里。
父亲爱一双土箕,胜过爱我。我傻傻地认为。
怎么可能呢?土箕哪有我珍贵啊。我又否认了。
在土箕面前,它的步幅,父亲的精神,被零乱的风飘摇了。
住在溪上
幽幽溪流,环绕山峰对峙、万籁岑寂的村庄。飘逸于山巅之上的云岫,深邃迷离。溪流的恬静、安谧、悠闲,仿佛一丛乳白的花卉,倾倒在浅草清冷而灼烈的阴暗里。
在溪之岸,蒲公英娇小的种子,通过风伸长的脖颈,朝着山谷沉落的方向摇曳。几只水鸟,羽毛夐古,比决绝的蓝天还要嶙峋、寂寥。在青翠消逝之前或消逝之后,没有谁知道,溪流会留下什么谶言和神话。我站在起伏不平的村庄,发现溪水流经的土地上,有许多灰白的浅浅的水痕。那是洪水退却的暗疾,包蕴了故乡的惆怅与忧伤。
父亲对这条溪流徜徉了好多年,从他小时候开始,溪流一直带着潮湿的翅膀,向前飞翔。溪流是村庄唯一澄澈的活水,圣洁地润泽着两岸的动物和植物,在它梦幻般的语言里,给干燥皲裂的土地输送了生机与活力。父亲身边的吊脚楼、灰棚、废墟、鸡鸭、牛羊、荒原,不断有溪流美丽的身影。
一根长长的塑胶管,跨过了土丘和浅沟,把溪水清澈地引入了我家简陋的厨房。初时,溪水进厨的状态是恍惚而诡谲的,像个刚进门的媳妇,局促不安。父亲把溪水接进了厨房,溪水从此脱离了灵动的水草、蝌蚪、漱石枕流以及鱼儿们,在阳光下挣扎、迷乱、茫然,好像不肯屈服于这种莫名而来的宿命。
父亲对故乡的溪流有过颇深的阴影。那是一年的夏天,乌云倏然地聚集,风一阵紧似一阵,大雨如倾倒的一筐石砾砸上了稻禾、野草、泥土、树木、青藤。父亲表面很镇定,但内心早已慌乱。洪水的来势盖过了往年,漫过溪堤,在石头和蓬蒿上滚过,把白色花穗的芦苇、沿河的水田,吞噬得千疮百孔,满面疮痍。
溪流之上,潮湿的水汽氤氲而升。山风不减,呼啸着掠过嵯峨的崖头。深居的树木,木讷地矗立,在凶狠的雨水中,如鬼魅般披头散发。父亲大喝一声,就带领着我们全家撤出了沿溪的吊脚楼。我从密植的雨布中看去,吊脚楼已在风雨中摇晃,瓦檐掀空,门前的石砌也被洪水冲跨了。
这一次的溪流,没有了往日的温柔,脾气瞬间暴躁不堪。父亲站在雨中,孱弱的背影,像一片无家可归的落叶,随风飘摇。一颗颗硕大的泪珠沿着两颊滚落,触及了我的柔软。我好像看到一个男人强大的身躯,已经悬挂在荒山悬壁之巅,濒临坍塌了。好在雨水倏地骤减,浑浊的浪花像一只鸟一样从荒丘间飞了下去,留下几声凄清的鸣叫,给寥廓的村庄,平添了几分劫后重生的喜悦。
溪流是一个村庄的记忆,也是父亲内心深处漂泊的歌谣。我想一条溪流的命运跟一个人的命运一样,总会在冥冥之中注定。我走进故乡的溪流时,浩荡的风,在旷野中强劲地升腾,像一阵森林的绿涛,不断向高处攀援、跳跃,最后涌动出千万条灿烂的光线。阳光的恢弘,土地的厚重,像是父亲沉久的喟叹,在故乡面前繁茂壮美。
有一个夜晚,溪流呈现出它可爱的一面。父亲对着这些自然界中的精灵,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沉迷于这个夜晚,将目光投向了朦胧的山谷,想穿透山谷间的幽蓝和深邃。可是前方虚渺,能隐约望见溪流飘逸的身子,着一身白纱,欲语还休。还有不少的灯光,穿梭在幽静也罢,喧嚣也罢,朦朦胧胧的炊烟里。
住在溪上,除了茫茫水草之外,溪流的宏厚和喜悦,像是故乡的一曲长调,从父亲的喉咙里迸发,迷离了山间的野兽和飞禽。父亲不是孤独的。我想,我也不是孤独的。在大地蓦然的眼神里,一切都不是孤独的。
故乡的溪流,是不朽的流云。父親仰望天穹,碧蓝如洗,山风的微拂,像是述说一种绝世的葱郁和空旷。
嚼 春
有一种葱翠、清新、自然的韵味,还有一种高山峡谷间云雾缭绕的湿润,由浅入深地慢慢浓郁,这大概是茶的感觉了。
在故乡,我看到茶是绿在心里的。
故乡的茶,要嚼,细细地嚼,耐着性子嚼。这种藏匿于一片绿的茶叶,会嚼出雅致、柔软、清香。
记得少年时,我在茶亭喝茶。那时年少,对茶不堪了解,更不要提能嚼出茶的精神内核呢。
临近谷雨,我家忙着筹备春耕的种子和农药化肥。可我们住得偏远,交通不便,离集市的来回路程有三四十里,得到这些东西太辛苦了。母亲听鸡叫三遍,忙翻身下床去烧火煮饭,天朦朦亮时出门。紧赶慢赶,到集市已是中午。而返回时,母亲则挑担肥料上坡下岭,身上全被汗水浸湿了。双腿也累得抽筋打颤。
这时,便渴望一壶茶。但山沟沟人烟稀少,哪有茶呢?而沟谷里的泉水,有经验的老人说喝不得生水,一喝准保肚子痛。我跟母亲挑肥料,身子走得出了汗,口舌早已经干燥生烟了。这时,倏地一抬头,只见岭上的茶亭如一树妖艳欲滴的杨梅,在我的眼前晃,诱惑得我直吞口水。
上了茶亭,就有茶喝!母亲鼓励我。
雷公岭茶亭四面开阔,立于峰腰,坪上有茶园,枝叶繁茂如盖。谷底的风徐徐翻来,凉风习习。那时茶亭里住了户人家,廊上竖了只大木桶,木盖子上摆了一只大海碗,赶路的人歇了脚,舀一碗春茶浇得全身舒畅,脚板心都轻松、透爽。
茶亭系方圆几里的绅士们集资修建。近百年来,当年的头人早已作古。现在来打理的人是一名孤寡婆子,包吃穿。孤寡婆子手脚勤快,茶亭被收拾得窗明几净。偶尔过路的人少,还能混到一口热饭。而庄上的猎户踏春上山,几天几夜蹲在绿意浓密的茶亭,品着新摘的谷雨茶,死守野猪、麂子等猎物,这时,春天的情怀轻快、兴奋。
这种逢河架桥、见山开路、十里一亭的风俗,让晓餐夜宿的人十分方便。雷公岭茶亭不管是春天忙于耕种,还是白雪封山时的清闲,都有人准备了让过路人过宿的被子、餐具、粮油、红茶,并隔段时间来人打理。过路的人吃了用了,只记得在门板上写:某某沟某某人用了某某东西,在厨柜留下了几块钱,或说下次再还。来打理的人就自然明白、会意,会拿钱增补好。
茶亭里的茶,似乎是春天的一海碗绿。但是嚼来,又不完全是茶。
我放下担子,在茶亭里喝茶,沐浴着凉风,不管喝的是一叶一尖的红茶,还是喝的两叶一尖的绿茶,它们熬煮的浓汤,皆散发出清清的香气来。
其实,口渴之人喝茶,喝得粗莽、匆忙。
故乡还有另一种喝茶的说法。他们说喝口茶,就意味着放手放脚休息片刻。这种场景在故乡极易碰到。几个干活的人累了,说喝口茶。便凑到一块,相互敬杆烟,说起南京的城隍北京的土地,古往今来的正野之史,或者乡间小道的流言。我倘若在旁,则沉醉于故事的起伏和生动,而讲的人口沫横飞,手舞足蹈。如果放在城里,桌上有一杯热春茶,这位就是说书的智者,多了几分艺术的氛围和精彩。
与福建人喝茶,对比故乡人喝茶,少了一袋干咸鱼。福建人喝春茶,眼前有一方木雕的四方盘子,还有几个精致的紫陶杯,然后冲一大壶水,哗哗煮了,趁热灌。而茶具旁放了一些干虾和咸鱼,细细捏住一只放在嘴里嚼,拌和着茶,嚼出了大海的味道。在我的咀嚼声里,海水波涛汹涌,礁屿坚硬嶙峋。
这样喝茶,可以嚼出福建人出海时的辛酸和坚韧。
是的,茶是有灵气的。故乡的青峰耸峙,深沟云壑,也造就了茶叶繁衍出不同的茶水。
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故乡的茶里有一种不再是单纯的春茶水了,是一种糊糊,既有茶的春气,也有杂食的清香。这种叫擂茶,既解渴,又能填饱肚子,是出行劳动的必带品。
那时候的人,生活条件极差,春天摘几筐茶叶晒干拌一些玉米地瓜之类的杂粮,用擂盂捣碎如泥,再晒干备用,有时喝一碗擂茶便顶一餐正食。当然,擂茶也有精细的佳品,生活条件好的家庭用花生、芝麻等混合绿茶捣碎,自然这种擂茶的味道不一样了。这样的擂茶是有亲戚来时才拿出的,母亲给客人冲水泡一碗,结果客人一饮而尽,意犹未尽,用手指把碗里沾的擂茶归拢,像水洗的一样干净。
这些年,一到春天,出了新茶便每家每户捣擂茶。母亲捣得最多,她踮着脚在谷雨前把嫩尖摘好,然后把花生和芝麻炒熟炒香,一并倒在擂钵里捣碎坛藏。母亲的擂茶大陶罐是一个家幸福的场景、温馨的时光。
每年的春天,母亲的擂茶做好了,就给我寄一些。母亲说:“让外面的朋友尝尝。”我笑:“他们吃海鲜开洋车,会吃这个?”母亲听了很难过,还是妻子善解人意,说:“妈,他们吃惯了好的,眼巴巴盼望着故乡的土特产呢。”母亲听了,在电话那头骂我:“还是和小时候一样顽皮。”我听了,幸福地笑,心想有妈真好啊!
母亲的擂茶跟我走南闯北,他们吃了没有一个不拍案叫好的。
现在,春天又来了,故乡一垅一垅的茶园又绿了。我似乎看到母亲背着一个楠竹扁篓,轻轻地,如蝴蝶一般从一丛飞到另一丛。我还远远地看到故乡的院子里,母亲在一只偌大的擂盂里,用一根坚硬的捣杵,做着擂茶。
有一天,我和朋友喝茶,我有几分炫耀地说:“这是我妈摘的春茶!”他听了淡淡一笑,无所谓地一饮,却发觉口感清纯,这茶确实与众不同。朋友脱口而出:“这茶要嚼。”
嚼?我这么多年没有嚼过茶。我疑惑地把茶嚼了嚼,那些尖芽散出的嫩叶,开出了一个鹅黄泛绿的春天!在故乡的每一片茶叶里,都会嚼出父亲的苦涩,也会嚼出母亲的清凉。
我听了,决定第二天去看看故乡的茶。
故乡的茶是一幅绿色的画卷,逶迤的山峰与茶树紧紧地对峙,溪水和野花点缀其中,一只兔子的狡黠让一座山灵动了。与我相近的几尾竹子,还像少女一样着一袭绿纱裙,摇曳出浪漫而有朝气的涟漪!
我再一次摘下一片鲜茶放进嘴里咀嚼,叶儿在我的舌尖唇齿间翻滚,青青的、轻轻的浓郁,如我轻快的脚步,如我豁然开朗的胸襟。
【作者简介】刘群华,笔名刘阳河,作品散见《星星》《散文百家》《湖南文学》《山东文学》《延河》《扬子江》《草原》《鸭绿江》《滇池》等刊,偶尔被《意林》《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刊转载,并入编多省市模拟高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