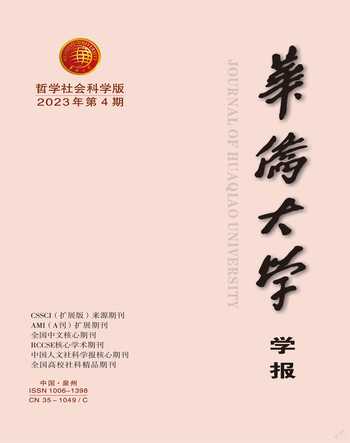资本·技术·生活: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三重逻辑
2023-09-06赫曦滢
资本·技术·生活:国外马克思主义
城市批判理论的三重逻辑○赫曦滢
摘要: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是对既有城市认识论进行批判性质疑与审视的方法,通过阐明城市景观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历史—地理辩证关系,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症候的叙事变革。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作为显性问题域得到系统性阐释的半个世纪中,可以提炼出三重彼此联系的研究逻辑,涵盖了该领域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一,通过分析资本逻辑对资本主义城市中生产或消费的干预,在生产与再生产的生发机制中探寻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关联;其二,通过梳理技术逻辑对全球城市的改造,在城市金融化、城市企业化、城市信息化三维维度中探寻城市何以更新资本主义的存续方式;其三,通过生活逻辑对生命政治城市的缔造,寻求城市主体性的衍生逻辑,从日常生活与城市相互依存的动态关系中探寻城市何以使资本主义生活化。这三重逻辑延续了“批判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展现城市转型与重构的多样性、普遍关联性,对自觉更新马克思主义的叙事范式具有指导价值。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生命政治
作者简介:赫曦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E-mail:he-xi-ying@163.com; 吉林 长春 1300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空间正义重塑研究”(18CZX004)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23)04-0005-09
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的一个分支,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双重推动下其研究的理论旨趣和现实维度正在不断发生“变异”。伴随着世界—城市假说、城市—新自由主义共同体、星球城市化、全球城市主义等新思潮的兴起,城市表现出天使与恶魔的双重面孔。它既是创新的源泉,又是剥削的重地,一直徘徊于希望与绝望、繁荣与凋敝、正义与不公的经历之间。城市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之一,不断以创新的方式塑造自我,以应对经济危机以及社会的需求与变革。这使得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成为既具备理论面向的哲学慎思,又具有实践面向的现实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演变与发展在很长时间中被认为是经济线性发展的结果,这种历史主义观点在批判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个流派中均占有一定地位。而实际上,城市发展是错综复杂的时空分层过程,不同的发展道路、生活方式与历史当下性都会对其走向产生影响。反之,城市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向也施加影响,构筑了城市—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当代样态,这种结构是历史、地理、社会、文化和经济相互作用的杂陈与并置。本文仅为城市批判理论及其话语逻辑提供一条分析理论,希望有助于拓展城市研究的视野。立足城市秩序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之间的历史—地理辩证关系,以“城市景观是资本主义加速生产、交换和消费的重要载体,对空间的组织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分工及实现积累的特殊方式”为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的三重维度重新规划资本主义城市分析的总体框架,在梳理当代城市属性与功能变革的同时,勾勒当代资本主义的展开逻辑。一方面,这一研究将资本主义的理解拓展到生存世界的全部领域,不再停滞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为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走出狭隘的规范性领域,向技术性、生命性领域拓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一研究通过揭示城市发展逻辑的时代性变化,为反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局限性,进而提出超越传统的话语模式提供了基本前提。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三重维度
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模式,以空间为切入点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引领了西方左翼思潮从时间决定论向空间分析法的重要转向。城市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是空间理论的核心话题。为何资本主义与城市发展变得如此密不可分?这源自资本主义的本性使然。资本主义究其本质乃是一个稳定性极差的经济体系,在每次大的社会动荡之后必然要经历去嵌入与再嵌入经济社会过程。为此,在大衰退和大萧条后,资本主义都会将自身重新融入社会关系中,从而重塑其主流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这为我们思考后疫情时代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提供了重要思路,也是本研究的现实价值所在。当今时代,城市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改造的驱动器,它会将社会和生活本身的包容表现作为关键要素,归于资本主义复苏与重塑的过程,以此来支撑资本主义的再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发展逻辑与叙事变革,必然要将其与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与现实需要进行勾连,在城市—资本主义共同体的认识论下描绘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未来。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多次危机,在知识层面引发了学者对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世界运行机制的研究兴趣。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次贷危机和新冠疫情,被所有专家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重大全球性危机。学者们不仅开始重新探讨资本主义及其内部矛盾等经典话题,而且讨论其结构转型、不同运转模式,以及不断修复自身的方式。但在研究中,不同學者在视角切入、具体方法与理论选择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分歧,使得最终呈现出的研究框架与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并使得研究高度碎片化和零星化。故很难在相对平面化的统一维度中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进行分类与总结,在谱系学层面难以把握其“总问题”“总特点”“总趋势”。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让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回归不同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机制中,重启对其城市—资本主义共同体的基本论域及逻辑线索审视,清晰地把握该理论的学术演进历程与发展趋势,进而超越其理论局限性。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强调认识的实践场所性,以及对于社会空间重构下不断改变的背景、条件和中介环境的批判性反思。相对于预设主体和客体的刚性分离,批判性和反思性研究方法更加强调主客体依托社会空间联系的相互构建、关联和持续转型。基于此,从城市批判的动态分析框架来看,主要有三种相互交织的逻辑,打牢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地基。
第一,从资本逻辑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城市。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最初的理论框架是通过“理解城市景观到瓦解资本逻辑”,将阅读城市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症候的切入点,从学理上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纳入资本主义运动轨迹,进而阐释城市化如何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换言之,就是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扩张的内在机理进行批判性分析。这一逻辑的诞生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和“新左派”的兴起交相辉映,并与福特—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性危机相叠加。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资本主义城市的解读铸就了这一决定性转折点。列斐伏尔超越了劳动力与资本的对立,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解放的潜力;卡斯特展示了当代城市作为管理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场所,是如何协调生产、消费和交换领域之间的关系,为随之而来的对城市管理的批判性反思奠定基础;哈维对金融和土地租赁作为城市增长和社会空间转型的引擎问题加以理论化,预言了新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发展的金融化。至此,马克思主义已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源泉,资本主义也不再被单纯地理解为一种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榨取劳动力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而是充满内在矛盾的社会秩序。
第二,从技术逻辑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城市。自20世纪90年代初到次贷危机前的这段时间,高度科技化、信息化给城市带来巨大发展契机,“技术赋能与重塑发展模式”成为城市研究的总问题。第三次科技革命几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层面都在施加影响,并推动了全球化进程。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和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等人不但将城市批判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在科技和全球化互衍的维度上引发了新思考。技术逻辑更加关注技术对人类整体经验的重塑能力反思,如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及它在全球内如何被统筹安排。同时,高新技术被当作型塑社会的多元化力量而被重新“挖掘”,它超越了狭义的经济要素,肢解了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成为塑造城市生活方式的能动性“成分”。基于此,技术逻辑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重要线索。
第三,从生活逻辑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城市。自次贷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社会面临彻底重构。全球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导致新一轮世界范围的危机应激反应与社会重组,在认识论、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上重新强调了城市批判理论发展的可能条件。在新冠疫情不断蔓延当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投资需求不足而导致的“长期停滞”时代将要到来。资本主义价值链条的重心从之前的社会变成生活本身,城市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城市发展生命化与生活化”成为全新议题。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最早提出了生物权力和生命政治的基本理念,重塑了城市治理的解读范式。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探讨了大都市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场所,是诸众的骨骼与血液。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将生产理解为生活的主观性和关系形式,而非商品与服务的生产。这些对人类生活的重新理解,都预示着资本主义将整个生活商品化的倾向,工作场所和私人生活的分野变得模糊不清,以生活为中心的剥削与自我剥削新模式正在成长。资本主义城市社会在经历疫情与金融危机的双重冲击之后,正在达到一种“新常态”。正如拉杰·帕特尔(Raj Patel)预言的那样,“城市是活着的政治”,无论是地理抑或社会层面,资本主义以生活为视野的建设宗旨将打造资本主义生活化发展模式,以增强城市抵御风险的能力,形成稳定与持久的发展动力,正在成为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新的理论增长点。
二资本主义城市与资本逻辑
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代指一系列以不同方式提供对城市生活一般性理解的观点与阐释,这些理解超越了偶然与局部的层面,专注于城市发展的本质特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西方左翼思潮中盛行的空間转向,为重塑城市批判的维度提供了切入点。在激进地理学和新城市社会学的交汇处,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试图重新梳理“城市知识的谱系”,开拓了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布展的内在机制批判性分析。在重新研究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批判性思考后,出现了两种城市批判理论倾向。一种倾向是探讨“资本—城市”异化关系,沿着资本城市化、空间的生产逻辑展开探讨;另一种倾向是以后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为基础,尤其是以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思想为线索,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挖掘由资本逻辑引发的“城市意识形态””变革。
列斐伏尔作为对“资本—城市”异化关系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对资本主义城市进行了颇具哲学意味的概括。列斐伏尔与本雅明一样,对城市批判具有辩证的理解。这种理论自觉来自于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同时借鉴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尼采(Nietzsche)的反历史决定论哲学。他凭借一己之力将马克思主义从对时间的沉迷中解放出来,坚持认为哲学具有空间维度,建构了充满希望的空间哲学。列斐伏尔认为城市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相遇的场所,二者的结合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换言之,使用价值与物理环境、人和原材料相关;交换价值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着眼于商品的价值。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城市的发展,城市中空间的转换日益商品化,资本逻辑主宰了城市发展的方向。艾拉·卡茨尼尔逊(Ira Katznelson)告诉我们,列斐伏尔探讨“城市—资本”异化关系的出发点是对理论建构和经验建构的城市和城市主义的分离。如果说19世纪催生了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城市模式,那么20世纪则孕育了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城市模式。资本城市化使与生产性资本相关的资本循环日益占据城市发展的主导地位。资本逻辑内在的空间均质化效应使得城市实践矮化为单向度的商品生产,进而篆刻上了价值规律的标识,原本多元化的城市主义被强制性“描绘”和选择性“删除”。资本城市化使城市发展路线图沿着资本剥削的轴线布展,资本主义多元化被“单一叙事”所蒙蔽,城市的异质性与多样性被压制,之前拓扑型与立体化城市,被资本逻辑主宰下的平面化“零向量”所取代。
卡斯特强调了把资本主义城市的商品化空间视为城市实践的关键决定因素,关注作为生产和消费手段的城市。他认为“城市问题的本质就是集体消费问题,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是生产力再生产问题的延伸”。集体消费是维系资本空间不断再生产的重要手段,这一过程同样受到资本逻辑的辖制。只有从这个角度看,城市主义才构成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是新型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方式,全球城市在本质上成为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卡斯特宣称城市问题正在成为政治、日常生活和传媒的关键要素,由此建构了“城市意识形态”的学说。他强调了城市在建构社会本体论方面的理论与政治意义,认为城市表达着在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国家角色。这一研究理路体现了早期法国城市研究的显著特点,即往往把城市的意识形态结构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以此嫁接起资本逻辑与意识形态研究的桥梁。集体消费同时受制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制度与社会经济关系,扮演着资本积累的触发者和资本生产的落实者双重角色。这也使其具有了特殊功能,即集体消费是城市冲破空间衰落周期律得以不断重生的出发点,进而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地理霸权的工具。
哈维在总结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资本—城市”异化关系已经被内化于资本主义体系之中,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剥夺性积累”过程。这意味着对资本逻辑的反抗必然会展现出双重性质,即针对资本剥削的斗争与围绕意识形态的斗争。对资本逻辑的研究不但是要在当代两种斗争形式之间确立有机联系,而且要理解引发两种不同形式斗争的根源存在何种关联。为了论证资本剥削具有空间性,哈维重新编织了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融入经济危机形成的分析中。经济危机的起点是资本的过度积累,本来应该不断贬值的货币和堆积如山的商品,通过城市的地理扩张和资本的乾坤挪移被重新激活,被新的空间所吸收,由此“空间修复”成为解决危机的临时方法。但是资本的机动性决定了它所创造的地理景观注定是不稳定和矛盾的,也必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场景,围绕劳动过程和不同阶级的斗争不可避免。两种斗争在根源上都是资本逻辑的必然产物,这一逻辑通过寻求剩余价值,实现盈利性目的。“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是永不停息的,由此也必然给社会、政治和环境带来灭顶之灾。
要言之,资本逻辑所营建的城市景观和城市意识形态斗争所展现出的双重反思,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检视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机制,并以此为基点探讨了城市与资本主义的共衍关系。作为从资本循环之空间叙事出发的城市批判维度,要揭示的正是资本城市化对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宰制,其根本目的是要说明在资本逻辑的调控下,城市空间生产已经突破了物的层面,获得了经济社会性质,这使得城市权利逐渐弥散并最终被非法褫夺。由此,清晰地认识资本逻辑对工业城市的掠夺,就牵住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牛鼻子”,找到了破除资本城市空间霸权的突破口。
三全球城市与技术逻辑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资本主义的组织逻辑中,一种新的发展方式迅速蔓延。为了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致敬,卡斯特把它称为“信息主义精神”,并高呼网络社会正在崛起。高新技术、全球化与城市化互嵌发展的态势不断增强,使得全球城市化从梦想变为现实。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所说:“虽然全球化无疑会影响乡村地区,全球经济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却主要集中于城市……同时,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本身也通过提供全球化所依赖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以及从密集的城市生活中不断涌现的观念和创新,来创造和推动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驱动中的全新社会,一些关键词不断涌现,如相互依存、时空压缩、融合、竞争、分裂、连接性等。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的重要特点是从工业产品生产走向技术和知识主宰的空间生产,进而实现全球城市化。全球城市社会的无情扩张和以不同霸权势力共存为特征的多中心构型,使其历史性的兴起了三股推动资本主义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力量,即城市金融化、城市企业化和城市信息化。资本主义不仅建立在金融行为的迅速增长之上,同时也建立在城市企业化以及高新技术加持之上。金融、企业和技术的结合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中主导城市发展的核心力量。这三大驱动力直接塑造了全球的城市面貌,并引领人类走入发展的新纪元。
信息化和数字化引领下的全球金融化现象在城市社会扩展,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关注的第一个核心问题。第一位提出资本主义存续不仅仅是生产方式,而是一种规则和积累模式的理论家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并开启了另类马克思主义的言说之路。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基于利润追求和財富积累的经济演变过程,城市在市场经济和相关文明的形成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一观点对于当代人理解金融化和全球城市化产生了强烈影响。特别是彼得·泰勒(Peter Taylor)汲取了灵感,认为当代全球城市作为商业服务的聚集区,对资本主义垄断力量的再生产起到核心推动作用。城市已经成为金融衍生工具,信息化和数字化给城市带来进一步的“内爆—外爆”,城市肌理被不断绷紧。沿着这一思路,阿瑞吉借鉴了布罗代尔和伊纽曼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关于世界体系的论述,指出城市与资本主义的互动关系是建立在金融霸权基础上的,城市是凝聚金融机构的“粘合剂”。城市金融化现象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加以观察,其一,城市金融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作为一种资本积累策略取代了生产性投资成为全球城市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其二,城市金融化现象直接引发了城市企业化发展趋向,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全球企业缔造了“创新环境”,并产生了空间协同观念;其三,城市金融化引领了城市信息化进程,在线平台、智能手机、人工智能和其他“网络化数字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加速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了城市生活。
城市企业化如何利用城市环境中的技术逻辑,使城市在全球化初期便融入地方—全球的动态关系中,并深入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关系中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关注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新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国际劳动分工的变革,塑造了“流动的空间”。这一“创新环境”是“一套特定的生产和消费关系,依托于某种社会组织运行,该组织以创新为工作目标,力图架构新知识、产出新产品、塑造新流程”。这样的环境具有互动性特质,可以依赖网络信息技术勾连不同的地理区域,并且产生空间协同效应。迈克尔·施托维尔(Michael Storper)、阿什·阿明(Ash Amin)以及奈吉尔·斯里夫特(Nigel Thrift)在描述全球城市的特殊性时所提到的“集聚经济”“非交易型依存关系”和“新马歇尔式节点”都表达了这一关切,即探讨技术逻辑对城市企业化的影响,解析全球化时代跨国大公司的生存机制。萨森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认为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化的发展使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塑造了一批具有复合型功能的全球城市。这些城市身为全球资本主义企业和国际管理场所具有整合资源和发号施令的功能,使得城市与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城市企业化倾向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副产品,城市的职能延伸到了管理全球经济、发展金融业和提供先进服务等领域,成为跨国企业必争的战略场所。
在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技术逻辑如何根植于各种城市环境,并形成无所不在的社会动力,进而构建全球城市—技术范式的紧密联系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关注的第三个核心问题。城市信息化基于信息技术的知识和知识对象的辩证关系而存在,全球城市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社会”,而非劳动密集型社会。知识而不是物质生产是城市发展的关键,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表现为符号化、“非物质”以及信息商品和认知式、交往式、合作式劳动。信息化和数字化社会处理的内容是话语性知识,城市发展的动力直接来源于知识信息生产、传播和使用,这是资本主义进入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独有特征。新技术和城市共同营建了知识世界的共同生产,人类主体和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以及包含着它们的有形空间无缝连接成一体。如罗杰·罗伯斯(Roger Burrows)所言:“构成城市结构的东西已经变了,不再仅仅是关乎场所经由流动进行的复杂调停所带来的突显特征;现在,软件和编码不仅是社会联系和互动的中介,而且日益成为构成因素”。信息和数字技术开启了参与、对话以及获取知识的新空间,也重塑了城市生活本身并产生新的知识,创造价值和意义。
综上,知识和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服务于金融和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成为促进剩余价值剥削、减少可变和不变资本的策略,更新了资本主义的存续方式。由此,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沿着“一体两翼”的构型展开,以信息化和数字化为“一体”,以金融化和企业化为“两翼”,勾勒了技术逻辑主导下的城市发展路径。数字化也直接导致了城市角色的转变,城市不再是存在冲突主体之间调停的场所,也非政府支出分配与再分配的平台,更不再是通过过度积累实现剩余价值的平台。技术逻辑通过在城市居民生活中植入信息资本主义的内在机制而扩大其影响范围,生命政治控制體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将城市居民变为被剥削的劳动者,对生命本身的宰制与调控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生命政治城市之旅正式拉开大幕。
四生命政治城市与生活逻辑
以城市为中心并在生命形而上学的抽象空间内依次展开的资本空间叙事,以及信息化和数字化带来的全球城市化效应,使得信息技术成为权力结构中被收编和异化的主题。最初,信息和数字仅仅是一种符码化载体,扮演着工具性角色。但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等技术革新,数据成为了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同时作为权力的符号学隐喻被不断挖掘,将城市发展引向了生命政治阶段。日常生活已经转化为剥削和革新的场所,如果我们不能走向一种逆熵式城市生活,不与异化的日常生活决裂,那么城市只会加剧经济、生态和政治危机。生命政治城市言说的核心问题是主体性在城市生活中的的生成逻辑,主要沿着城市的权力结构和生命政治生产两条主脉延伸,表达了日常生活是城市、权力以及主体性相互依存动态关系的核心。
从城市的权力结构出发探讨生命政治城市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第一条脉络。福柯将生命政治学的核心关切定位于在人类构建的权力关系中如何面对人之主体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全球城市化的重要衍生品。主体性与权力之间包含着深刻的悖论:一方面,主体被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所压抑与征服;另一方面,权力使主体获得新生,并由此“成其所是”。权力、主体和城市三个关键概念并非彼此隔绝,而是连缀成一个完整的知识谱系。权力无处不在,成为主体无法遁逃的背景。主体被权力关系包裹纠缠,亦被权力关系所规划与塑造。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在城市成为生产权力的治理技术开始的。“城市空间权力化”是贯穿福柯生命政治城市研究的核心线索,而日常生活则是引发这一权力运行机制的触发点。福柯城市空间权力化分析同时在经验和理论两个层次上加以表达:第一个层次包含对历史上特定的权力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如何形成的细致审查。在《另类空间》中福柯认为,20世纪是空间的纪元,我们时代的种种困境都与空间有关。由此,引出了资本主义城市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任何权力运行之基础的重要论断。第二个层面的分析超越了历史特殊性,构建了有普世意义的权力模型,进而形成了完备的权力理论。他确认了现代权力形式包含“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两种类型,两种权力在城市层面表现为生命政治学的双重维度“规训身体”和“调节人口”,生命权力的作用目标经由身体转变为人口。鉴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刻画福柯生命政治城市的基本特征,即城市中蕴含着贯穿于整个社会的权力关系网络,这些权力关系直接作用于生活本身,引发对于人之生命的掌控与治理,并通过城市策略与更大规模的国家战略而相互作用。最终,生活本身被彻底吸纳进城市发展机制中,使“活着”本身就具有政治性,并深深植根于先在性的权力结构中。福柯对于生命政治城市的探讨开创了城市研究的新视野,使城市具备某种生命管理职能,得以渗透到生活中的任意角落。
从生命政治生产出发探讨资本主义城市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第二条脉络。生命政治生产是与传统商品生产相对应的概念,劳动者因为协作关系的不断增强而摆脱资本的辖制具备了自主生产的能力,产出知识、语言、符码、信息和感受等,生产过程同时也是劳动者主体性价值增值的过程。当下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已经超越了工作场所的限制,渗透到整个城市。城市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场所,也是主体性觉醒的必要前提。生命政治城市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本体论机器”,通过隶属与激活关系不停地产生新的主体性。全新的主体性贯穿于城市的“血液洪流”中,使得城市被完全嵌入生命政治的循环里。生产的基础依赖于对人工共同性的取用,生产的结果又再度回流到城市中,并重构城市发展的逻辑。城市俨然成为生产生命的加工厂,将生活本身纳入城市体系中。伴随着生命政治生产霸权的出现,生命生产的空间和城市空间开始重合,这一进程又与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相叠加,把身体商品化推向了极致。生命被数字编码所吞噬,数字和信息不仅仅是创造价值的中介,其本身就是价值创造。信息化和数字化变革了劳动关系和资本积累模式,使生命政治生产成为消费性与非物质性的符号生产。借用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的“社会化”概念以及阿甘本和维尔诺关于生活形式的唯物主义本体论理论,生命政治城市与信息化进程、生活形式之间相互结合,造就了以生活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
概言之,以主体性分析为核心叙事的生命政治城市,意味着物性生命的承认与首肯。这里的生命聚焦于作为物性实在和实在物性相统一的人之存在,生命政治的本质就是对人之主体性的承认与捍卫。城市在生命政治缔造的过程中承担着支配生命和生产生命的双重责任,日常生活成为塑造生命的直接途径。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看来,我们需要像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倡导的“次政治”和“生活政治”所表达的那样,赋予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个体以权力,让他们掌握自身命运,共同缔造新的生活制度,以应对经济崩溃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将城市生活重新政治化,以塑造生活的“美丽新世界”。
结语
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不同维度出发,我们提出了几条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研究逻辑,大体阐明了当代城市叙事的基本方向。资本逻辑、技术逻辑和生活逻辑构成了城市批判的“三脉”,建构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的主体框架,回答了“资本—城市存在何种异化关系”“城市何以通过技术与知识更新存续”“城市如何使资本主义生活化”等一系列重要的学理问题。基于此,一条资本主义城市社会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线索在城市文明的空间语境变迁中清晰可见。城市社会的传统思维在全球化和数字化语境中被彻底颠覆,城市批判理论不但提炼出资本、技术和生活逻辑在具体地缘景观中必然遭遇的结构性悖论,而且凸显了参与城市建设的主体在复杂的权力博弈与城市生态中重塑城市生活与寻求城市解放的可能性。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开拓了都市化的批判进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分析框架,揭露了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隐藏的扩张逻辑与霸权逻辑,拓展了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维度,具有理论的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国外马克思主义城市批判理论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着用城市批判取代整体历史过程把握,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宏观问题完全归结为城市问题的片面化理解误区。用城市批判的单一维度替代社会问题的总体分析使其具有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也很难找到超越资本城市化的发展出路。
The Triple Logic and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Marxist Urban Criticism Theory
HE Xi-ying
Abstract: The Marxist theory of urban criticism in foreign countries is a method to critically question and examine the existing urban epistemology, and to promote the narr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ymptom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by clarifying the history-geography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landscap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logic. In the half century of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Marxist urban criticism theory as an explicit problem abroad, three interrelated research logic can be extracted, covering the core issues of research in this field. Firstly, by analyzing the intervention of capital logic in production or consumption in capitalist c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es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the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Secondly, through combing the technological logic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ities, the paper explores how cities can renew the survival mode of capitalism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urban financialization, urban enterprization and urban informatization. Thirdly, through observing the life logic of life politics city,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erivative logic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explores why the cities make capitalist life from the dynamic and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daily life and urban development. The triple logic continues the basic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critical theory”, shows the diversity and universal relevance of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which has guiding value for consciously renewing the narrative paradigm of Marxist urban critical theory.
Keywords: foreign Marxism; urban criticism theory; life politics
【責任编辑:龚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