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金流量表的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测度研究
2023-09-06田龙鹏李珊
田龙鹏 李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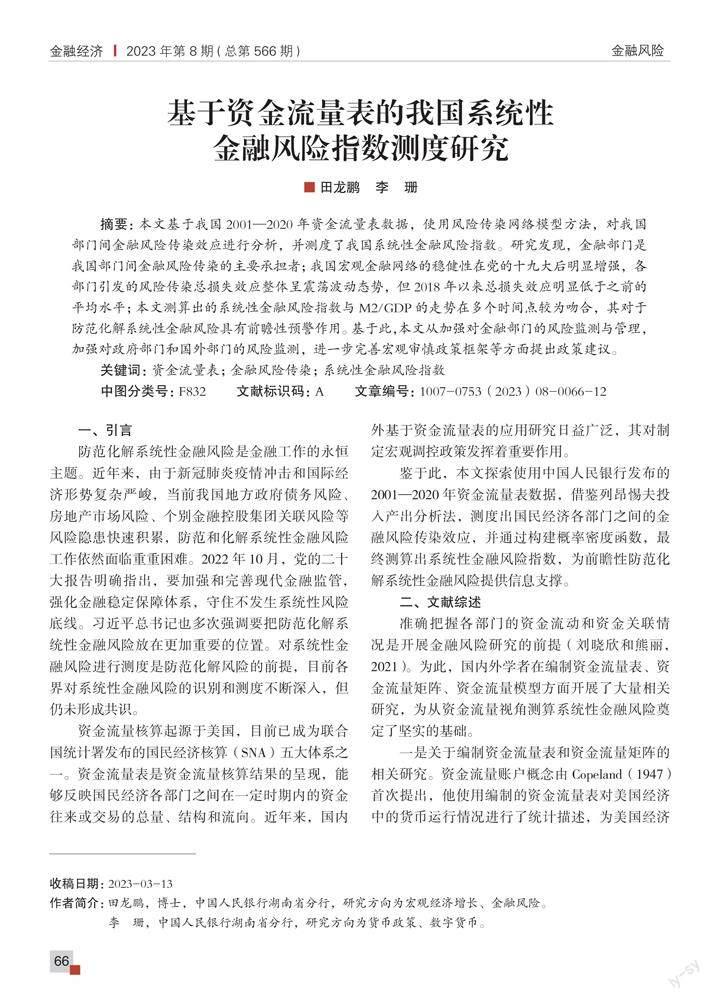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2001—2020年资金流量表数据,使用风险传染网络模型方法,对我国部门间金融风险传染效应进行分析,并测度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研究发现,金融部门是我国部门间金融风险传染的主要承担者;我国宏观金融网络的稳健性在党的十九大后明显增强,各部门引发的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整体呈震荡波动态势,但2018年以来总损失效应明显低于之前的平均水平;本文测算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与M2/GDP的走势在多个时间点较为吻合,其对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前瞻性预警作用。基于此,本文从加强对金融部门的风险监测与管理,加强对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的风险监测,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资金流量表;金融风险传染;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53(2023)08-0066-12
一、引言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近年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个别金融控股集团关联风险等风险隐患快速积累,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工作依然面临重重困难。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测度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前提,目前各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和测度不断深入,但仍未形成共识。
资金流量核算起源于美国,目前已成为联合国统计署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SNA)五大体系之一。资金流量表是资金流量核算结果的呈现,能够反映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在一定时期内的资金往来或交易的总量、结构和流向。近年来,国内外基于资金流量表的应用研究日益广泛,其对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
鉴于此,本文探索使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01—2020年资金流量表数据,借鉴列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法,测度出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金融风险传染效应,并通过构建概率密度函数,最终测算出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为前瞻性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提供信息支撑。
二、文献综述
准确把握各部门的资金流动和资金关联情况是开展金融风险研究的前提(刘晓欣和熊丽,2021)。为此,国内外学者在编制资金流量表、资金流量矩阵、资金流量模型方面开展了大量相关研究,为从资金流量视角测算系统性金融风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关于编制资金流量表和资金流量矩阵的相关研究。资金流量账户概念由Copeland(1947)首次提出,他使用编制的资金流量表对美国经济中的货币运行情况进行了统计描述,为美国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之后,资金流量核算及账户编制方法在世界各国迅速推广并不断完善。Roe和Stone(1971)编制了基于投入产出的U-V型资金流量表,建立了资金供需均衡模型,分析了资金关联效果。Tsujimura 和Mizoshita(2003)介绍了使用资金流量账户数据编制资产负债流量矩阵的方法(简称ALM),并利用ALM的列昂惕夫逆矩阵来评价日本的货币政策。我國学者也在编制资金流量表和资金流量矩阵方面进行了系列探索。王洋和柳欣(2008)从企业的现金流量表出发,通过加总形成了包含居民、企业、政府和银行四大经济主体的宏观资金流量表。李宝瑜和张帅(2009)先是编制了我国2000年和2005年的“部门×交易”及“交易×部门”资金流量矩阵表,然后基于设定的模型,编制了“部门×部门”矩阵表,解决了常规统计中无法获得部门间金融资金流量数据的问题。马克卫和李宝瑜(2015)将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划分为投入产出表、国民收入流量表、金融资金流量表;先分别建立三个模型,然后将其链接起来,形成一个反映国民经济所有环节乘数关系的模型系统;利用2012年的SAM数据,举例说明其在实际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还有部分学者研究和编制了国际资金流量表和矩阵(石田定夫,1993;王涛,2015;张南,2016;李宝瑜,2017)。
二是关于资金流量模型的相关研究。基于资金流量表和资金流量矩阵编制方法和数据,学界进一步探索出了几大类资金流量核算分析范式下的相关模型。第一类是仅将资金流量表作为数据来源。李扬和殷剑峰(2007)基于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从收入分配和部门储蓄倾向等两个方面对居民、企业和政府等国内三个部门的储蓄率进行了比较分析。肖文和周明海(2001)、潘文轩(2018)、杨巨和方恬(2020)、张车伟等(2020)则分别基于不同年份的资金流量表研究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演变趋势。易纲(2020)运用资金流量表数据,对过去十几年来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并从资源配置和风险承担角度测度了金融资产风险承担者的分布。第二类是符合资金流量核算原则的存流量一致性模型(Stock-Flow Consistent Model,以下简称SFC模型)。该模型的主要特征包括:存量与流量核算的一致性、各部门的行为决策相互影响和关联、历史时间、过程理性、货币和金融对实体经济运行的重要性(Godley和Lavoie,2007;Caverzasi,2013;柳欣等,2013)。张云等(2018)将SFC模型与DSGE模型进行比较后认为,SFC模型在货币、信贷、财富、生产和分配方面提供了一体化的处理方法,能够更好地分析现实经济体系中的货币政策、金融化、杠杆和收入分配等问题。温博慧等(2015)结合SFC模型和未定权益分析法,从宏观审慎中宏微观与时间截面两组维度的角度,研究了资产价格波动冲击下中国银行体系的网络抗毁性。王博和宋玉峰(2020)基于SFC模型视角,构建了一个“气候变化—政策响应—经济增长—金融稳定”的传导路径,研究了气候变化的转型风险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第三类是借鉴投入产出分析法开展的研究。胡秋阳(2010)设计并编制了中国投入产出式资金流量表,借鉴投入产出分析模型构建了资金关联模型,考察了部门之间、项目之间、金融交易与实物交易之间通过金融交易形成的资金关联结构和乘数效果。张云等(2018)基于中国投入产出式宏观资金流量表和资金关联模型,定量分析了发生在政府部门的局部债务违约,经由国民经济各账户之间的资金关联发生扩散和波及,从而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资金筹措和资金运用产生的结构性影响。
三是基于资金流量表开展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的相关研究。国内外学者对如何准确地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对金融系统整体风险的测度,对特殊金融机构风险的测度以及对金融风险传染效应的测度(Brownlees和Engle,2017;方意等,2019;Gandy和Veraart,2017),而基于资金流量表开展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研究大多从金融网络与风险传染效应着手。金融网络与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取决于负面冲击的大小:在小于临界值的负面冲击下,金融网络使金融体系更具韧性;在大于临界值的负面冲击下,金融网络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和不稳定的来源(Acemoglu等,2015)。宫小琳和卞江(2010)较早使用2007年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账户)数据,建立了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金融关联网络模型,揭示了负面经济冲击在部门层面循环传导的轨迹,量化了各部门在各传染轮次中的损失量,为应对系统性金融風险提供了较早的实证支持。张南(2013)将中国的资金流量表调整为矩阵式资金流量表,分析了部门间资产与负债的基本特征,进而应用列昂惕夫逆矩阵建立了部门间金融风险的波及效应模型并展开乘数分析,给出了各项金融交易风险波及的排序,解析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中国金融整体的最终波及效应。刘晓欣和张艺鹏(2019)首次构建出2000—2017年“部门×金融工具×部门”的三维投入产出式资金流量表,研究发现因不同工具转化为债权而引发的债务扩张推动了经济脱实向虚,加剧了金融风险。高慧颖等(2022)使用2017—2020年我国资金存量表测算了各部门间风险传染效应,并借鉴Silva等(2014)的方法进一步测算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
综上所述,从资金流量视角测算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方法充分考虑了部门间资金流动情况及部门间风险传染特征,在测算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现有文献侧重于比较不同部门在风险传染中的地位或作用,较少进一步构建指数反映整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状况;另一方面,疫情以来我国宏观杠杆率呈现阶段性上升趋势,但现有研究较少使用资金流量数据对疫情以来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变化进行测度。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较多比较各部门在风险传染中的作用,本文在Silva等(2014)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的测算方法,本文测算方法更加符合经济实际,科学性更强,是对现有基于资金流量方法进行系统性风险测算研究的有益补充。二是在数据使用方面,现有研究基于资金存量表测算了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但由于我国资金存量表仅公布了2017年以来的数据,且测算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存量风险,无法体现一段时期内风险的动态变化,本文使用2001—2020年的资金流量表数据,测算出较长时期内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变化,并通过与其他风险测算方法得出结果的相互印证,更好地证明本文测算方法的有效性。
三、基于资金流量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测度方法
现有公布的资金流量表为“部门×工具”形式,而基于投入产出法,需使用“部门×部门”形式的资金流量矩阵(即为“从谁到谁”矩阵,以下简称WTW矩阵)。因此,借鉴张南(2013)的方法,首先基于现有资金流量表数据,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推定出部门之间的资金交易数据。其次,编制出WTW矩阵后,列出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部门间金融风险传染效应测算方法。最后,构建基于五部门风险传染网络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
(一)WTW矩阵编制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资金流量表中的行表示各机构部门,包括住户部门(HH)、非金融企业部门(NFC)、广义政府部门(GG)、金融部门(FI)和国外部门(RoW)五个部门。列表示各交易项目(金融工具),包括通货、存款(表1中合并为通货与存款)、贷款、债券、股票等十七个大项三十四个小项金融工具(2020年资金流量简表如表1所示)。在各部门内部根据资金投向和资金来源分别列出了运用和来源。资金流量表的编制遵循复式记账原则对任一金融工具,各部门资金运用之和等于资金来源之和,最终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资金运用之和等于资金来源之和;但对单一部门而言,由于可能存在净金融投资,故其资金运用之和不一定等于资金来源之和。本文借鉴国际标准的资金流量表中的做法,将资金运用称为资产,资金来源称为负债①。
要编制资金流量WTW矩阵,需知道每一项金融工具的部门间资金流动情况。由于数据源限制,本文借鉴张南(2013)的做法,使用推定方式估算单一金融工具的部门间资金流动情况。总体原则是假定各部门对资金来源方的某一单一金融工具按照相同的比率筹资,称为负债比例系数,负债比例系数=部门持有某类金融负债/某类金融负债合计;金融资产的运用方按照该系数将资金投向至各部门,资产运用方部门运用该类金融资产额=负债比例系数×该部门持有的同类金融资产。
具体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某一金融工具,仅一个部门持有负债,多个部门持有资产,此时部门之间的资金流动关系简单直接,对该单一金融工具而言,WTW矩阵如表2所示,行方向为各部门的资金运用,列方向表示各部门的资金来源。
第二种情况是对某一金融工具,多个部门持有负债,同时多个部门持有资产。如对于表1中的股票,企业部门发行的股票金额(负债)为12 333亿元,而股票项目的负债总额为23 415亿元,则企业部门发行股票的负债比例为0.53(12 333/23 415)。从资金运用看,持有股票资产的部门分别为住户、企业、政府、金融及国外部门,所以各部门持有的企业发行的股票资产等于该部门持有的所有股票资产乘以企业发行股票的负债比例0.53,比如,住户部门共持有股票资产3 319亿元,则其中持有企业发行的股票资产为1 748.2亿元(3 319×0.53)。同理,可分别计算得出各部门持有的金融部门、国外部门发行的股票份额(见表3)。由此得到每一项金融工具的WTW矩阵表,然后将各项金融工具的WTW矩阵表进行加总,即可得到所有金融工具的WTW矩阵表。
(二)部门间金融风险传染效应的测度方法
Leontief(1936)首次提出了投入产出分析法,该方法主要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研究行业间、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关系。由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各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具有较多类似之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鉴该方法开展部门间金融风险分析(张南,2013;张云等,2018;刘磊和张晓晶,2020),并取得了较好的分析效果。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编制的WTW矩阵,借鉴投入产出法来测度部门间的金融风险传染效应。
1.构建部门间风险传染矩阵
WTW矩阵是构建风险传染矩阵的基础,矩阵中的部门类似于投入产出分析表中的行业,金融工具类似于投入产出表中的商品。投入产出表中,各行业的总产出等于总投入,为使得五部门的风险传染矩阵遵循这一原则,本文在WTW矩阵表中增加了两行两列,兩行为净资产与列和,两列为净负债与行和,行与列分别对应投入产出表中的总产出与总投入。但是由于各部门的资产合计与负债合计通常不相等,为满足平衡关系,借鉴张南(2013)的做法,在不改变原WTW矩阵数据关系的前提下,本文定义行和与列和为单一部门的资产合计(Ai)与负债合计(Di)两者中的较大值。五部门风险传染矩阵如表4所示。
2.测算部门间风险传染效应
(三)构建基于五部门风险传染网络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
四、金融风险传染效应及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测度
(一)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时间窗口为2001—2020年,主要是因为我国2001年加入WTO,2001年前后国内与国外部门之间的资金流动状况存在明显区别,为保持纵向数据变动的分析可比性,故选取这一时期为研究对象。文中资金流量表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网,WTW矩阵为作者借鉴相关方法推定得出。同时,本文借鉴Silva等(2014)的做法,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资产波动的方差以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的波动衡量;企业部门资产波动的方差以WIND全A指数(除金融、石油、石化)的波动衡量;金融部门资产波动的方差以WIND金融行业指数(仅含上市金融企业)的波动衡量;国外部门资产波动的方差以标准普尔500指数的波动衡量。原始数据均来源于WIND数据库。
(二)金融风险直接传染效应
根据五部门WTW矩阵及上文风险传染效应计算方法,本文计算得出了2001—2020年各部门遭受1单位风险冲击后对其他部门造成的直接风险传染效应,如图1所示。
从图1可知,住户部门遭受1单位资产损失后,风险除自身承担外,主要直接由金融部门承担,原因是住户部门的主要融资渠道是金融部门发放的贷款。2001年以来,金融部门平均承担的风险损失比例达37.1%,其中,在2007年、2016—2018年承担的损失比例为50%以上。企业部门遭受1单位资产损失后,风险主要由金融部门承担,平均承担比例高达79.3%,由于企业部门也可能进行海外融资,国外部门的平均承担比例也达到了14.3%。同时,企业除贷款融资外,还可能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进行融资,故住户、企业、政府部门均承担一定比例的资产损失。政府部门遭受1单位损失后,风险也主要由金融部门承担,平均承担比例达58.4%。2020年,金融部门承担的损失比例高达96.1%,可能的原因是突发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实体部门经营困难,造成金融机构面临的潜在风险显著增加。金融部门遭受1单位损失后,住户部门平均承担损失比例最高(36.3%),其次是企业部门(26.6%),金融部门自身平均承担风险损失比例为19.2%,这是因为金融机构的存款资产主要来源于住户部门和企业部门。国外部门遭受1单位资产损失后,风险损失主要由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承担,平均风险承担比例分别为62.7%和28.1%,主要原因是在目前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政策下,金融部门、企业部门与国外部门的联系较其他部门更为密切。
(三)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
根据理论分析,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等于前n次风险传染效应之和加各部门期初损失,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图中每一条线表示各部门遭受1单位初始冲击后,经过部门间传染最终导致的整个经济体风险传染的总损失量。以2020年住户部门数据为例,住户部门遭受1单位风险冲击后,经过部门间风险传染,最终将导致住户、企业、政府、金融及国外部门资产分别损失1.54、0.26、0.06、1.27和0.02个单位,合计资产损失为3.15个单位(或3.15倍)。
1.各部门引发的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整体呈震荡波动态势
从图2中可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各部门遭受1单位初始风险冲击后引发的金融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有一定下降趋势,最低降至2008年的19.76倍③;随后,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国内各部门间资产负债关联网络遭受较大冲击,我国宏观金融网络的脆弱性有所上升,故遭受1单位初始风险冲击后导致的最终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也明显上升,至2017年总损失效应高达39.11倍。2018、2019年我国金融网络稳健性明显增强,1单位初始风险冲击导致的总损失效应分别降至17.34倍和19.52倍。这主要是因为自2017年末起,我国将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三大攻坚战首位。在此基调下,中国人民银行等监管部门陆续出台系列监管措施,遏制各种影子银行业务、资管业务野蛮生长,并取得了实效。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出台了系列刺激政策,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导致我国宏观金融网络的脆弱性有所上升,故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提高至24.31倍,但仍远低于2017年以前的较高水平。这反映出我国宏观金融网络的稳健性在党的十九大以后得到明显增强。
2.住户部门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最低,国外部门和企业部门最高
横向比较各部门遭受冲击后导致的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可知,住户部门的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最低,平均为3.19倍,2008年最低仅1.47倍。之后随着我国房价不断上涨,住户部门杠杆率逐渐提升,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也在波动中逐渐提高,2017年达到最高水平至5.25倍。国外部门的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最高,平均达到6.96倍,可能的原因是国外部门主要通过企业部门及金融部门与国内部门联系,而这两部门与国内其他部门的联系又较为密切,故来自国外部门的风险溢出效应能够较快地在国内各部门间传染,造成较大的风险传染效应,这一测算结果与宫晓琳(2012)的结论也较为接近。企业部门造成的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仅次于国外部门,平均水平达6.68倍,2018年之后,企业部门的资产金融化趋势得到明显遏制,故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明显减弱。政府部门和金融部门造成的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水平较为接近,平均水平分别为5.10倍和5.66倍。近年来,政府部门债务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2016年以来,政府部门造成的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已接近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债务上升对金融网络稳健性的影响值得关注。
(四)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测算
理论分析指出,存在一个初始风险冲击规模,使得经过n轮部门间风险传染后,部门的总资产损失至零。上文已经计算出各部门遭遇1单位初始冲击后的总损失效应倍数,使用各部门实际资产除以该总损失效应倍数,即可计算得出使得各部门总资产损失至零的初始冲击规模,然后可得出各部门金融稳定边界值SFi。结合各部门Ω④,代入式(8),可计算得出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SRIN)。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为检验本文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测度结果的合理性,选取现有研究常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衡量指标M2/GDP(马勇和陈雨露,2017),将其与本文测算结果进行比较。从图3中可以看出,M2/ GDP的增速在两次高点均与SRIN指数高点较为吻合,反映出本文测算结果的合理性。從SRIN指数变化来看,2001年以来,我国在大部分时点系统性金融风险较低,2006—2010年处于第一阶段相对高点,这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时点基本一致,且SRIN指数在2006年即有明显上升趋势,反映出基于资金流量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方法对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前瞻性预警作用。2013—2016年,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再次上升至高点,这一时期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规模明显攀升,可能是系统性风险上升的主要诱因。同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国M2/GDP增速出现阶段性上升,但系统性金融风险并未随之攀升,可能反映出我国的金融网络更加稳健,风险抵御能力较前两次债务上升期间进一步增强⑤。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风险传染网络模型方法,测度了我国部门间的金融风险传染效应和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研究发现:第一,金融部门承担了部门间风险传染的主要损失,即各部门遭受风险冲击后,经过部门间风险传染,最终金融部门承担主要损失。第二,从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的时序变化看,我国部门间风险传染的总损失效应在2018年以后明显下降,说明宏观金融网络更加稳健。第三,本文测算得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与M2/GDP走势在多个时点较为吻合,且具有一定先行趋势,反映出该方法测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具有一定合理性,值得进一步推广运用。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加强对金融部门的风险监测与管理。金融部门是我国宏观金融网络中最主要的风险承担者,要进一步加强对金融部门的风险监测,尤其是加强各部门与金融部门间资金流动频繁、规模较大等异常情形的监测,综合使用各类风险缓释工具,及时补充金融机构核心资本,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
二是加强对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的风险监测。从风险传染总损失效应看,国外部门遭受风险冲击带来的总损失效应最高,应充分关注各类外部冲击对我国金融风险的外溢效应,并及时适度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进行逆周期调节;政府部门遭受风险冲击带来的总损失效应近年上升最快,应通过债务偿还、展期、重组等方式化解存量债务,遏制增量债务,通过时间换空间等方式逐步缓释债务风险。
三是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进一步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监管部门应发布更加详细、频度更高、体现部门间金融交易的资金流量数据⑥,探索使用基于资金流量表数据的方法来监测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逐步扩大宏观审慎管理覆盖领域,更好地防范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的跨市场、跨部门传染。
注释:
① 严格来讲,资产与负债是存量概念,表示某一时期末的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结果;而资金流量表为某一时期内的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是流量概念。但二者本质均为资金运用与来源,为便于读者理解与行文,在流量表中借鉴资产与负债概念,分别对应资金运用和来源。
② 从经济实际出发,五部门面临的冲击可能是正向冲击,如利率下降、货币政策宽松等;也可能是负向冲击,如货币政策紧缩、美联储加息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本文认为,就理论上而言,五部门面临正向冲击和负向冲击的概率是相同的,且冲击规模越大,其发生的概率越低,而这一变动特征较为符合正态分布,故本文假设五部门冲击的概率密度函数服从正态分布。
③ 该倍数是五部门同时遭受1单位初始冲击后导致的总风险损失效应之和,属于极端情况。此处主要在于分析五部门资产负债关联网络的整体稳健性。
④ 由于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08年7月1日起才有数据,故2001—2007年国债收益率波动以2008—2020年波动平均值代替。
⑤ 由于用以测算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的基础数据是WTW矩阵,而这部分数据为推算得出,可能影响指数测算结果。
⑥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公布的是“部门×交易项目”形式的资金流量表,但本文测算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需使用“部门×部门”形式的资金流量表,而目前文中“部门×部门”形式的资金流量表是作者借鉴张南(2013)方法基础上推算得到的,这可能使得测算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异,故本文建议监管部门发布更加详细的资金流量数据。
参考文献:
[1] 刘晓欣,熊丽.资金流量存量核算与金融风险的文献综述-基于虚拟经济的视角[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1(03):3-21.
[2] COPELAND M A. Tracing Money Flows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7, 37 (02):31-49.
[3] ROE A R, R STONE. The Financial Interdependence of the Economy 1957-1966[M], Department of Applie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71.
[4] TSUJIMURA K. MIZOSHITA M. Asset-Liability-Matrix Analysis Derived from the Flow-of-Funds Accounts: The Bank of Japan's Quantitative Monetary Policy Examined[J].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2003(01):51-67.
[5] 王洋,柳欣.资金流量核算的新方法[J].统计与决策,2008(03):9-12.
[6] 李宝瑜,张帅.我国部门间金融资金流量表的编制与分析[J].统计研究,2009(12):3-10.
[7] 马克卫,李宝瑜.SAM乘数效应链接模型设计与应用研究[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2015(09):135-148.
[8] 石田定夫.日本经济の资金循环[N].东洋经济新报社,1993.
[9] 王涛.国际资金流量表的编制與模型应用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15.
[10] 张南.国际资金循环统计的研究与实践—与李文商榷[J].统计研究,2016(12):106-112.
[11]李宝瑜.国际资金流量表若干问题讨论[J].统计研究,2017(04):26-35.
[12]李扬,殷剑峰.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基于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经济研究,2007(06):14-26.
[13]肖文,周明海.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因素—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的比较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1(03):69-76.
[14]潘文轩.税收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J].财政研究,2018(11):84-95.
[15]杨巨,方恬.中国资本收入主体分配格局的演变与原因研究[J].教学与研究,2020(06):61-73.
[16]张车伟,赵文,李冰冰.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及减税降费的影响—基于七部门资金流量表的测算与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20(06):16-28.
[17]易纲.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J].经济研究,2020(03):4-17.
[18] GODLEY W, LAVOIE M. Monetary Economics: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redit,Money, Income,Production and Wealth[M]. Palgrave Macmillan.
[19] CAVERZASI E. The Missing Macro Link[C].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13.
[20]柳欣,吕元祥,赵雷.宏观经济学的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3(12):15-23.
[21]张云,李宝伟,苗春,等.后凯恩斯存量流量一致模型原理与方法—兼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较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01):154-178.
[22]温博慧,李向前,袁铭.存量流量一致框架下中国银行体系网络抗毁性研究——基于资产价格波动冲击[J].财贸经济,2015(09):46-60.
[23]王博,宋玉锋.气候变化的转型风险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基于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视角[J].经济学动态,2020(11):84-99.
[24]胡秋阳.投入产出式资金流量表和资金关联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03):133-146.
[25]张云,程远,胡秋阳.政府债务违约对中国宏观资金流转的数量影响分析——基于投入产出式宏观资金流量方法[J].财贸研究,2018(03):1-10.
[26] BROWNLEES C, ENGLE R F. SRISK: A Conditional Capital Shortfall Measure of Systemic Risk[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7,30(01):48-79.
[27]方意,韩业,荆中博.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度量研究——基于中国信托公司逐笔业务的数据视角[J]. 国际金融研究,2019(01):57-66.
[28]GANDY A, VERAART M. A Bayesian Methodology for Systemic Risk Assessment in Financial Networks[J]. Management Science, 2017,63(12):4 428-4 446.
[29]ACEMOGLU D, OZDAGLAR A, SALEHI A Z. Systemic Risk and Stability in Financial Network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105(02):564-608.
[30]宮小琳,卞江.中国宏观金融中的国民经济部门间传染机制[J]. 经济研究,2010(07):79-90.
[31]张南.矩阵式资金流量表与风险波及测算[J].统计研究,2013(06):67-77.
[32]刘晓欣,张艺鹏.中国经济“脱实向虚”倾向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产业关联的视角[J]. 上海经济研究,2019(02):33-45.
[33] 高慧颖,田龙鹏,周潮. 金融稳定边界与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测度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22(11):1-18.
[34]SILVA N,RIBEIRO N,ANTUNES A I. Towards a systemic risk indicator based on contingent claim analysis[M]//A Flow-of-Funds Perspective on the Financial Crisis Volume II, 2014: 263-285.
[35] LEONTIEF W W.Quantitative Input and Output Relations in the Economic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1936,18(03):105-125.
[36] 刘磊,张晓晶.中国宏观金融网络与风险:基于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20(12):27-49.
[37]方意,和文佳,荆中博.中国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风险溢出研究[J]. 世界经济,2021(08):3-26.
[38]宫晓琳.未定权益分析方法与中国宏观金融风险的测度分析[J].经济研究,2012(03):76-87.
[39]马勇,陈雨露.金融杠杆、杠杆波动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2017(06):31-45.
(责任编辑:唐诗柔)
Measurement of Systemic Financial Risk Index in China Based
on Flow of Funds Accounts
Tian Longpeng, Li Shan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hunan provincial branch )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sectoral financial risk contagion effects in China using the risk contagion network model based on the flow of funds accounts data from 2001 to 2020. The systemic financial risk index for China is measured.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financial sector is the main bearer of inter-sectoral financial risk contagion in China; The robustness of China's macro financial network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after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total loss effect of risk contagion triggered by various sectors shows an overall volatile trend, but the total loss effect since 2018 has been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previous average level; The systemic financial risk index calculated in this paper is relatively consistent with the M2/GDP ratio at multiple time points, and it has a forward-looking early warning effect on preventing and defusing systemic financial risks. Based on thi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strengthening risk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enhancing risk monitoring of government and foreign sectors, further improving the macro-prudential policy framework.
Keywords: Flow of funds accounts; Financial risk contagion; Systemic financial risk ind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