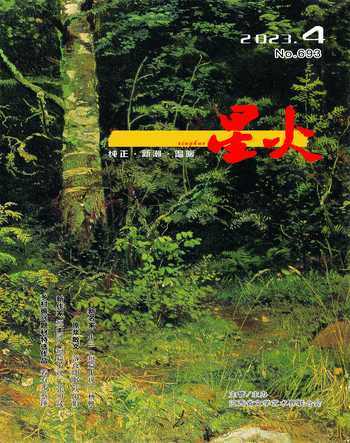天堂
2023-09-05从林
从林,北京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有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发表于《啄木鸟》《青年文学》《星火》《天津文学》《山西文学》《延河》《创作》《芙蓉》《特区文学》《厦门文学》《都市》《鸭绿江》《地火》《阳光》《佛山文艺》《北京晚报》等报刊。著有长篇小说《天堂之约》。
一
多久没下楼了,她自己也记不清了。老人久久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忽明忽暗的夜晚,心中一阵悲凉,眼泪扑簌簌往下掉。窗外杳无声息。从晚上七点一直到现在,已经大半夜了,老人就这么坐着,一动不动。窗外刮起了风,风声飒飒,窗帘像一面旗帜掀了起来,抖落一片尘土,满屋弥漫着呛鼻的土腥味。
好像有六七年没扫房了,这么长时间没扫房,窗帘能没有尘土吗?也不能说绝对没扫过,儿子每年春节前,都过来忙活忙活,擦擦玻璃,蜻蜓点水似的用鸡毛掸子扫扫这儿,掸掸那儿,像例行公事。儿媳妇要把窗帘卸下洗洗,老人总说不用不用,还不脏呢。儿媳妇也就借坡下驴,得过且过了。可能本来就是客气客气,怎么能当真呢。其实老人是心疼他们,现在年轻人不容易,工作压力大,上了一天班,還是多歇歇吧。儿子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错了。儿子是孝顺儿子。儿子几次让她搬到自己家去住,把这边筒子楼的房子租出去,房租多少在其次,主要是方便照顾她,省得两头儿跑。可老人始终不松口。截长补短地过去小住可以,永久搬过去常住,老人不愿意。那边的房子条件很好,一百多平米,三室两厅两卫,老人过去可以单独住一间,一人用一个卫生间,自由得很,方便得很。可老人觉得再怎么着,也没自己的家方便。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好。
吃饭的时候,老人接了个电话。妈,是我,燕子,您好吗?闺女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的电话。闺女移民已经好多年了,拿了绿卡,成了家,有了儿子,买了房子和汽车,工作稳定,收入不菲。最重要的,丈夫是和她一起去加拿大留学的同学,恋爱多年,知根知底,都是北京人,这让老人最放心。女人能有个爱她的男人比什么都重要。闺女说她儿子已经上大学了,是加拿大一所不错的大学,学海洋生物,这个专业在加拿大是热门,毕业后很容易找到工作。闺女还说她丈夫很忙,经常出差,美国、南美、日本,到处跑,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多,有时候也觉得挺无聊的。不过也没什么,男人不为事业奔忙,整天守着老婆孩子能有什么出息,到时候把钱拿回家就行了。闺女出国后,变得越来越实际了。以前是很有理想的,大学学的国际政治,整天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秋瑾是她心中的偶像,总想着改变世间的不平等,做点儿惊天动地的大事。那时,老人总开导她,让她实际一点儿,别那么异想天开。现在不用开导,闺女真的现实了,而且现实得很,把钱拿回家就行了。唉,也没什么不对的。难道没钱好吗?闺女告诉老人,他们正在筹备,等儿子大学一毕业就辞掉工作,开公司,自己当老板。老人一直倾听,不发表意见。远隔重洋,万里之遥,不了解情况,搭不上茬儿。其实这都不重要,闺女无聊,老人孤独,一个宣泄,一个倾听,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儿子闺女都是在筒子楼长大的,也都是从筒子楼出去的,十多平米的房子住四口人,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老人自己都说不清。老伴儿走得早,下中班骑车回家,被一辆飞驰而过的水泥罐车撞到了天空。孩子是老人自己带大的,像一只老母鸡,呵护着两只吱吱叫的小油鸡。如今小油鸡大了,出息了,飞了,老母鸡却老了,走不动了。身上的羽毛掉得不成样子,光秃秃的,灰暗无光。
老人费力地从窗前站起,一手拄着拐棍,一手用力撑着小方凳。那把油漆斑驳的小方凳,吱吱呀呀,痛苦地呻吟着。坐久了,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一点儿撑不住劲,好半天才有知觉,一点儿一点儿,自下而上,从腿到腰,重新梳理一遍筋骨,零零散散的,才算排列组合就位。
老人转身举拐杖,拉窗帘,怎么拉都拉不上,窗帘的环是金属的,窗帘的杆也是金属的,已经锈蚀,如同多年不用的锈迹斑斑的枪栓,再费力也拉不上。卡壳了。拉不上就不拉了,多大个事啊,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太太,不拉帘就不拉帘了,不拉帘又能怎么着。老人蹭到桌子旁,拐棍把水泥地面戳得嘚嘚响。天一凉,腿脚更不得劲了。桌上,是刚才没吃完的半碗剩饭,烫饭,就是上顿吃剩的菜和饭,倒到锅里,兑水一热。昨天儿子他们三口子来了,儿子炒了几个菜,平时老人自己没那么讲究,熬半锅粥,煮碗面条就对付一顿。饭早就凉了,像荤油一样凝在碗里,看不出个层次,一片菜叶挂在碗边的一根筷子上,另一根筷子四脚八叉地躺在桌上。儿子昨天来,又跟她谈起让她搬过去住,儿子的口气已经有了埋怨的意思。儿子说,您这不是折腾我吗?我来一趟,开车都得一个多小时,要赶上堵车,小半天就过去了。您就不心疼心疼我?儿媳妇在一旁搭腔,哪儿有跟妈这么说话的,妈是喜欢静,一个人习惯了,我们辛苦点儿,常来就是了。儿子白了儿媳妇一眼。老人明白儿媳妇的心思,谁小两口过得好好的,愿意平白掺个糟老太太。什么忙都帮不上,除了吃就是睡,睡醒接着吃。孙子上高中了,早不用人看了。孙子小的时候,老人还没退休,没看上,孙子是上幼儿园长大的。平时也奶奶奶奶地叫着,可总感觉没那么亲近,面子事儿。都是老人主动打电话嘘寒问暖,臭小子没有一次问候奶奶,除了跟父母一起来,自己就没来过。有时候,老人觉得伤心,细想,也没什么伤心的,不是自己带大的,能有那么深的感情吗?再正常不过了。
二
老人在儿子家住过一段。住了一个多月。五年前,老人做了一次大手术,在手术台上整整躺了六个小时。她是害怕做手术的,从年轻到老从没做过手术,动刀动剪,太恐怖了。可不做不行了。老人的腰弯得像个大虾米,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医院查出好几种毛病: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腰椎畸形错位。上半段没好地方了,医生说,您要是再不做,就站不起来了。这句话把老人吓坏了。她信。别说以后,现在都快站不起来了。儿子在手术告知单上签了字,她就被推进了手术室。从手术室出来,麻药药效还没过,迷迷糊糊地听医生向儿子介绍手术情况。她只听清一句话,她的腰上安了十个金属锔子。伤筋动骨一百天,何况老人做了这样一个大手术。康复是个漫长的过程。康复需要护理,需要耐心,需要一天二十四小时精神和肉体的呵护。那种情况老人当然要到儿子家康复。于情于理都得这样。无可厚非。儿子基本做到了。儿子上班,不可能二十四小时伺候老人,但儿子雇了个保姆,等于儿子出钱保证老人身边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伺候。下了班儿子过来看望,儿媳妇站在旁边,时常带点儿这样那样的好吃的。然后,就回客厅看电视去了。每天如此,像履行一种严格的程序。后来,连老人都觉得别扭了,说你们忙你们的,不用惦念我,这不是着急的事儿,得慢慢养。后来,儿子有时候加班或应酬,回家就很晚。儿子回来晚的时候,儿媳妇就很少过来或根本不过来。儿媳妇在另一间屋子辅导孙子做作业。这个时候,老人最别扭,像客居他乡,寄人篱下。一个多月后,能翻身了,慢慢可以坐起来了,老人说什么也不待了。回家自己康复。儿子急了,说您这是干吗呀,一个人回去我能放心吗?老人说,有什么不放心的,你们白天上班不也是我和保姆在家吗。让保姆跟我回去,你们该忙忙去,我什么事都没有,放心吧。
儿子用车把老人送回家,老人自己的家。
后来,老人康复后,也到儿子家小住过几次,三两天,十天半个月,都是儿子一再要求的。儿子的态度老人倒不是太在意,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深了浅了的,还能怎么着。就是儿媳妇不咸不淡,不冷不热,不阴不阳的,让老人很难接受。老人就不愿意去。
自己的家是天堂啊!
老人的房子是老房子,大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建的,五层高,筒子楼,当时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从一层到五层,从五层到一层,老人在每一个台阶留下多少足迹,她自己也记不清了,如同指尖在自己身上每一片皮肤划过,再熟悉不过了。她能感觉到它们的温度和律动。楼道里的灯鬼火般忽明忽暗,甚至有时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老人丝毫不觉陌生和恐惧,轻车熟路,如履平地,上下自如。
一切都过去了。
手术的效果好吗?好像还可以吧。老人想直起腰扔掉拐杖,行走如前。但似乎不能太理想化,太异想天开,太脱离实际,手术本身是有风险的,腰椎手术,就更有风险。没听别人说吗,手术后不瘫痪,能站起来就算成功。就像炒股票,不赔就是赚。这是什么逻辑啊?就是这个逻辑。老人应该觉得万幸,她的两个同事,跟她一样的毛病,手术后,一个刀口始终愈合不上,反复感染;一个真的动不了了,瘫在床上了。几个月后老人可以下地走路了,因为疼她还是蜷着身子,弓着腰,跟以前一样,像个大虾米。儿子说,您怎么还这样啊,直起腰来。老人说,我直了。儿子说,直了怎么还这样呀?最后,老人还是弓着身子走路,准确地说是蹭步。手术后,还是原来的状态。复查时,老人问给她做手术的大夫怎么回事。大夫看了片子后说,从手术的角度看,没问题,是康复期间锻炼不够。
也许吧。谁知道呢。
年龄大了,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病情稳定,不发展就行了。老人安慰自己,手术还是起作用的,要是不做,没准儿真像医生说的,連路都走不了了,瘫在床上了。
三
手术后,老人总共下了两次楼,都是儿子带她到医院复查。她拄着拐杖,儿子在一旁搀着她。从五层往下走,一步一步地蹭,有人上来,有人下去,正赶上早晨上班上学,大人孩子的,络绎不绝,楼梯拥堵程度不亚于地铁上下班高峰时的景象。人家倒是没说什么,还让老人别着急,可人都堵在楼梯口,上上不来,下下不去。儿子着急,一着急背起老人就往下走,到了楼下,放下老人,儿子一下蹲在地上,脸煞白,大口大口喘气。医院有电梯,但等候时间出奇地长,比等公交车时间还漫长。儿子借了个轮椅,推着老人,楼下楼上的,始终满头大汗。再加上排队拍片、排队化验、排队交费、排队取药,回到家还要上楼,老人觉得这个过程的痛苦远远大于病痛的痛苦。她甚至对上下楼有了恐惧感。
老人本来寄希望于手术后一个人可以下楼,但根本不行。做不到。不仅如此,腿的情况还越来越糟,挪步都困难,还谈什么下楼。医生说,膝关节严重退行性病变,唯一的办法是做膝关节置换手术,但风险很大,不能保证成功。经过腰的痛苦,老人早就打消了再做手术的念头。
不受那罪了。
自己下楼,对老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了。
但老人的心中是存有希望的,人是靠希望支撑的,有了希望生活才会有奔头。老人每天都被一种轰轰隆隆的声音唤醒,她并不觉得吵闹,反而像听悦耳动听的音乐。她马上从床上坐起来,寻着声音,拄着拐棍十分费力地挪到窗前,扒着窗台向外张望。常常在窗前一坐就几个小时,不觉得饿,不觉得渴。窗外是个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推土机欢快地叫着,永远不知疲倦似的。柴油机鼓着腮帮子,突突地喷着浓烟,味道厚重,把老人的眼泪都熏了出来。老人全然不觉。老人的脸上隐约漾着笑纹。其实,老人什么也看不到,是对门的李婶告诉她推土机在忙活,挖了一个大坑,挖出的土有小山那么高。还搭了一个架子,在楼的旁边,和老人住的楼一样高。老人坐在窗前,只看得见楼前的一条小路,小路笔直笔直的,水泥砖块铺就,两旁长着一般高的修剪整齐的小松树。老人熟悉这条小路。腰腿好的时候,老人经常沿着小路一直走下去,路的尽头是一条小溪,小溪清澈见底,鱼儿自由地游动,无拘无束的样子。岸边有几棵垂柳,懒懒地悠闲地飘荡着。夜晚,赶上天儿好的时候,月亮和星星倒映在水中,偶尔吹过一阵微风,搅动起一片耀眼的银子。年轻时,老人和老伴儿常到此遛弯儿,吃过晚饭,走着走着就到了小溪边。后来,有了闺女,带着闺女一起遛。再后来,儿子出生了,带着儿子闺女一起遛。再后来,渐渐地,儿子闺女长大了,不跟他们遛了,他们又自己遛。自从老伴儿走了以后,老人所有美好的记忆都定格在那个飘着垂柳游着小鱼的小溪边。
现在老人走不到小溪边了。
四
单位决定在筒子楼建电梯让老人兴奋得一宿没睡着觉。电梯是好东西,直上直下,不用爬楼梯,坐在里面,眨眼工夫就到楼下,眨眼工夫又上来了。不久,楼下就有动静了,汽车卸货的声音,咣当咣当的,推土机推土的声音,轰隆轰隆的。老人的心随着这些声音跳动,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同时也日益着急,盼望电梯早日建成。
老人把筒子楼建电梯的事在电话里跟闺女说了,闺女也非常高兴,闺女说,这下您可以下楼了。老人说,是啊,有盼头儿了。儿子从楼下上来,问,这乱乱哄哄的干什么呢?老人说,安电梯啊,电梯安好了,我就可以坐电梯下楼了,多方便呀!儿子说,你们单位总算办了件好事。老人说,可别这么说,单位挺好的,特别对我们老人,一直都挺关心的。安电梯的事坚定了老人不去儿子家住的决心。老人想,安了电梯,就如同安了翅膀,我就可以自己飞到楼下,不用麻烦别人了。
老人坐在窗前,享受着期待的快乐。
儿子时不时来,买来米面蔬菜肉蛋,老人自己挪着蹭着鼓捣点饭,还算将就。岁数大了,吃点儿就够,觉也睡不了多少,坐在窗前听楼下的热闹,是老人消磨时光最好的方式。
那天,老人正坐在窗前,忽然听到楼下的动静比往常大,很嘈杂,不光是推土机的轰鸣声。一会儿,老人听出来了,是吵架的声音,很多人在喊,一声比一声高。吵闹声就来源于施工现场那边。机器的轰鸣声停了,吵闹声陡然放大了数倍。
“你们他妈瞎折腾什么呢?把路都堵上啦!”
“没看见前边路口的牌子吗?施工绕行,这边过不去了。”
“凭他妈什么过不去,几天没回来,家都回不去了,没门儿!”
“那没办法,我也不能把这坑填上啊。”
吵闹声、叫骂声、金属器械碰撞声、人体接触扭打声、脚步摩擦地面声,交响乐一般,合成一团。
打架事件没影响施工进度,第二天楼下照常轰隆隆地响,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忙碌着。老人听着楼下的喧嚣声,脸上又荡出了笑容。还和往常一样,老人除了吃饭睡觉,整天坐在窗前,倾听这让她心情愉悦的音乐。老人觉得这就是动听的音乐。老人经常沉浸在美妙的想象中。拄着拐棍,挪到电梯门前,应该不会太远。据对门新婚的小两口说,电梯间在楼道的中间位置,也就三四米的样子。摁一下摁钮,等一会儿电梯停住,开门,进去,关门,眨眼工夫就到楼下了。赶上天儿好的时候,坐在楼下晒太阳,她不能往远处去,在楼下过过风也是很美的一件事。老人心疼儿子。老人想儿子以后再带她到医院看病,就不用背她上下楼了,累得气喘吁吁,脸煞白,不是个正色儿。儿子也是五十岁的人了,鬓角的头发全白了,以前头发密密麻麻的,现在头顶日渐稀疏,已经见亮光了。想到这,老人的心里一阵酸楚,不好受。
儿子日子过得也不容易。三十多岁才结婚。过去也没少谈女朋友,怎么都不合适,晃荡晃荡就三十多了。也是该着,人的命。儿媳妇比他小九岁,长得也漂亮,白白净净,小巧玲珑,是个南方姑娘,湖南的。以前在北京打工,在儿子的公司当保洁,儿子是个主管,一来二去就跟儿子腻上了。儿子晚上经常加班,她给儿子买饭沏茶,有时还自己做点儿小菜端到儿子办公室,菜的味道很好,让儿子很受用。儿子就觉得南方姑娘真温柔,真贤惠,心真细,手真巧,比北京姑娘好,北京姑娘大大咧咧,说话也不温柔,还不会做饭。后来,儿子把加班当成一件美好的事情,而不是负担,还从家拿过一床被子,加完班就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了。白白净净、小巧玲珑的湖南姑娘,下了班也不着急回宿舍,弄了饭菜和儿子一起吃,有时两人还喝点儿小酒。湖南姑娘白白净净的脸盘笑吟吟的,秀色可餐,湖南姑娘灵巧的小手做出的菜可口下饭,儿子的心情很好,胃也很舒服。
一天晚上,在儿子的办公室,吃完饭,湖南姑娘没有像小懒猫似的依偎在儿子身边蹭来蹭去,而是一本正经地坐到对面办公桌的转椅上,垂着头,一声不吭。儿子觉得奇怪,问怎么啦?湖南姑娘说,没怎么,就是觉得有点儿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儿子问。
“恶心。”
“恶心?”
“还困。”
“是不是病啦?”
“浑身没劲。”
“感冒了吧?让我摸摸发烧吗?”
“不是呀!”
“那怎么回事啊?明天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不去!”
“为什么呀,身体不舒服就要去医院,有病赶紧治,别耽误了。小病不治,病严重了就麻烦了。听话,明早我替你请个假,我拉你去医院。”
“哎呀,不去就不去。”
“你到底怎么回事?”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什么真傻假傻?什么意思?”
小巧玲珑的湖南姑娘不说话了,水汪汪的大眼睛溢出了眼泪,吧嗒吧嗒落在衣襟上。
儿子站了起来,疑惑地看着她。
她也用泪眼看着儿子,可怜巴巴的。
儿子突然从那泪眼婆娑的闪光中发现了什么。这时湖南姑娘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豆腐块大小,递到儿子眼前。
什么呀?儿子瞪大眼睛问。
医生说都快三个月了。
儿子明白了。
五
儿子把比他小九岁的湖南姑娘娶回了家。娶湖南姑娘绝不是儿子的本意,打死他也没想让这样一个女人做自己的老婆。他挑来挑去不就是选一个可心的女人做老婆吗?他心目中理想的女人一定要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是他事业的有力支持者和得力的参谋助手,要聪明、贤惠、温柔、漂亮。而今,湖南姑娘初中毕业,根本算不上有相当的文化知识;还算聪明,但聪明得不是地方;开始的贤惠、温柔,像一缕青烟,结婚后就飘散了,无影无踪了,而湘妹子的泼辣,儿子却充分领教了;似乎只剩下漂亮了,但前面的条件都不具备了,视觉感官也就渐渐麻木了。
儿子不是一开始就束手就擒的。儿子争取了一下,但很快就败下阵来。湖南姑娘软硬兼施,儿子就没办法了。湖南姑娘说,我一个姑娘家,还没结婚就怀了别人的孩子,今后还怎么做人啊?儿子小心翼翼地说,要不,要不把孩子做了?你说什么?你们男人心真狠,那可是你的亲骨肉啊!湖南姑娘几乎尖叫起来。儿子想无论如何不能把孩子生下来,生下来算怎么回事啊。你没结婚我也没结婚,没结婚就养个孩子,我的脸也没处放了。儿子后来想到的对策是破财免灾,自己酿的苦果只有自己吞下。他以为这招灵验,不就是想要点儿钱吗?我给。儿子递给湖南姑娘一张银联卡,说,上面有五万块钱,你把孩子做掉,拿着钱回家吧,够你几年的工资。儿子满以为事情就此了结,心想今后可得把持住,管住自己的下半身。瞧男人这点儿出息吧。湖南姑娘没出声,抬眼看了儿子一眼,接过银行卡,翻过来调过去地看。儿子明白她的意思,儿子说,没设密码,你随时可以取。
公司的一个女保洁工辞职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走一个再招一个就是了。新来的保洁工是个中年妇女,快五十岁了。儿子力推中年妇女,说中年妇女踏实,对工作认真,有责任感。
五个月后,一天晚上,儿子下班回家,进地下车库取车,打开车门发动车,发现车旁站着一个胖子,女的,头上严严实实地包着粉色围巾,鼓鼓囊囊地穿一件紫色羽绒服。儿子担心车拐弯碰着她,按喇叭让她躲开,她却站着不动。什么意思?儿子下车走近前,嘿,没看见车吗?躲开!那个女胖子还是不动。儿子急了,上前拉她。她挣脱开,仍站在原地。遇到碰瓷的了?見鬼了。儿子还要拉她,她把头上的围巾打开,露出了半个脸,红彤彤的,像个大苹果。尽管光线昏暗,儿子一眼就看清了,湖南姑娘直勾勾地盯着他,目光幽幽的。
“你,你没回老家?”
“回了,今天又回来了。”
“为什么?”
“我妈说,谁的孩子你生给谁,我不给你养着。”
结婚后,湖南姑娘就当了全职太太。可并不尽全职太太的职责,不看孩子,不归置屋子,不做饭。孩子小的时候,保姆看,三岁后送幼儿园。保姆一直没辞,家务活全包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老人对儿子的婚姻无可奈何。自己都顾不得命了,还管得了别人?
老人还是每天坐在窗前,听楼下那动听的音乐,音乐的声音越喧嚣,老人的心里越激动,像年轻时刚参加工作时,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老人记得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是十六块钱,学徒工的工资,一块钱一张,整十六张,嘎崩新。她揣着嘎崩新的工资,下了班没回家,直接坐上无轨电车,奔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当时那是北京最大的百货商场。她给母亲买了一条棉线围巾,厚厚实实,围在母亲脖子上,连脸都盖住了,很暖和的样子。母亲头上是一条用了好多年的头巾,她上小学的时候,就见母亲围着。围巾的本色是红色,后来变色变薄,粉不粉白不白,薄得透亮,围在头上一点儿不挡寒。可母亲一直舍不得扔,哪有钱换新的呀。她给父亲买了两瓶酒,正宗的牛栏山二锅头。父亲没别的爱好,就喜欢喝两口,可那个年代吃饭都成问题,哪儿有钱喝酒啊。实在馋得受不了了,偷着打二两散酒,八分钱一两的白薯烧,苦,涩,呛,辣,咽下一口嗓子像被开水燎了一下,可父亲已经很满足了。那天晚饭后,父亲满面红光,很满足的样子,平时话本来不多,这会儿成了话痨。聊他当兵时候的事儿,聊他技术多么多么好,技术员工程师都不如他,还吼了两嗓子,唱了几句京剧花脸。她给自己也买了一件东西,灯芯绒棉鞋。现在脚上的棉鞋,底儿已经磨透了,露了一个窟窿,雨雪顺着窟窿钻进鞋里,脚凉丝丝的;鞋面也磨薄了,右脚大脚趾顶出了鞋帮。姑娘家家的总得顾个脸面吧。剩下的钱,打月票,换饭票。那时的钱真经花啊!
除了在窗口听音乐,老人偶尔接闺女打的越洋电话。闺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丈夫啊,儿子啊,连工作谈得都不多。女人一结婚,脑子里的东西,慢慢地全都挤出去了,最后只剩下丈夫、儿子。有那么一句话,男人的世界是世界,女人的世界是男人。还是有些道理的。可最近一段时期,闺女的电话突然没了。往常一周怎么着也得打一两次。有时,老人实在忍不住,就问儿子,你姐姐没什么事吧?儿子说,能有什么事啊?她洋房住着,洋车开着,洋餐吃着,洋钱花着,比您享福,别瞎操心了您。可老人还是不放心。这么多年,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
还有一件闹心的事儿。楼下的音乐不响了。不响了有两种情况:一是完工了,电梯可以使用了;二是停工了,工程搁置了。老人后来听说是后一种情况。本来整栋楼的住户都同意安装电梯,在协议上都签了字。这是好事,没有理由不同意。可住在一层的顾景云突然从国外回来了。她长期在国外,陪儿子读书,房子就交给侄子住,侄子觉得安电梯也是好事,就在协议上签了字。顾景云这次回来是想把房子卖掉,她坚决反对在楼里安装电梯,理由是电梯紧邻她家卫生间,噪音巨大,影响房子的价钱。顾景云说,我是房主,其他人签字无效。工程就停了下来。
单位的领导说,这栋楼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电梯就安不成。
老人是看着顾景云长大的,她小的时候,老人抱着她到街上玩,给她买雪糕吃,带她到小溪边看鱼,那时的小溪比现在水面大,有好多漂亮的鱼在水里游,现在早就没鱼了。老人把电话打到顾景云家。
“小云啊。”
“谁啊?”
“我是你楼上的大妈。”
“哦,您什么事?”
“你还好吗?儿子上学不错吧?”
“您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闺女,大妈想跟你说说那电梯的事,我这不争气的腿,跟瘫子差不多了,早就下不了楼了,要是能修个电梯,我挪着步还能到楼下过过风……”
“您能不能下楼跟我没关系,您该找谁找谁去。我住一层用不着电梯,所以我也用不着安电梯。再说了,您干吗那么死心眼,住儿子家不就得了嘛!真是的。”
迎面杵过来一根顶门杠,老人被噎了个倒仰,身子晃了一下,电话从手中滑落,眼泪掉了下来。
屋子很静,外面更静,四周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也真奇怪,施工停止后,机器的轰鸣声没了,别的声音也没了,连自行车的铃声都没了。以后的日子,都是这么静。老人就在这静谧中坐着,一动不动地坐着。坐了几天,老人觉得实在太压抑了,想给闺女打电话聊聊。老人从未主动给闺女打过电话,一来怕花钱,国际长途一分钟就多少钱出去了,哗哗地流水,打不起;二来闺女隔三差五就把电话打过来,唠叨个没完,根本就用不着给她打。电话通了,铃声响了半天,没人接。不对呀,正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家里不可能没人啊。闺女跟老人说过,她那儿离北京有上万公里,在地球的另一面,有时差,北京是白天,她那儿就是晚上,她那儿晚上,北京就是白天。天黑睡觉前,老人又把电话拨过去,铃声执拗地响着,还是没人接。怎么白天也没人啊?
老人睁开眼,天大亮。几天来,惦记闺女一直睡不好,总是快天亮才迷迷糊糊睡着,醒来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
老人拿起床边小桌儿上的电话,拨通了儿子的手机。铃声响了两声挂断了,老人又拨过去,又挂断了,再拨过去,还是挂断了。这一个个都怎么回事啊?老人继续拨,这回通了。
“妈您到底干吗呀,我正在开会呢!”近乎吼叫。
“你姐姐她……”
“她离婚啦!”
“啊,离婚啦?什么时候离的?”
“早离啦!”啪地电话挂上了。
老人在床上坐着,一直坐着,坐了多长时间,她自己也不知道。后来老人觉得肚子饿了。昨晚熬了半锅粥没喝完,热热喝了吧。老人摸过床边的拐棍,撑着往起站,撑了两撑没起来,第三次站起来了。往前迈步,腿不像是自己身上的东西,一点儿劲吃不上,绵软无力。左腿迈出,右腿正要跟上,戳在地上的拐棍一打滑,人就被扔了出去,重重摔在地上,拐棍像一支飞镖将屋脚的一盆花打碎—一盆老人养了十几年的君子兰。老人忽然看见了老伴儿。老伴儿笑呵呵地向她走来,问你在这儿干吗呢?快起来弄饭,吃完了咱俩遛弯儿去,今儿天气多好啊!老人冲老伴儿说,你拉我一把,我這就给你热粥去。老人扬手,等老伴儿拉她,扬了半天,老伴儿也不理她。老人急了,你干吗呢,快点啊!
四周出奇地静。外面阳光真好,天蓝得瘆人,纤尘不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