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像鸟飞往她的山
2023-09-05小小程静之
小小 程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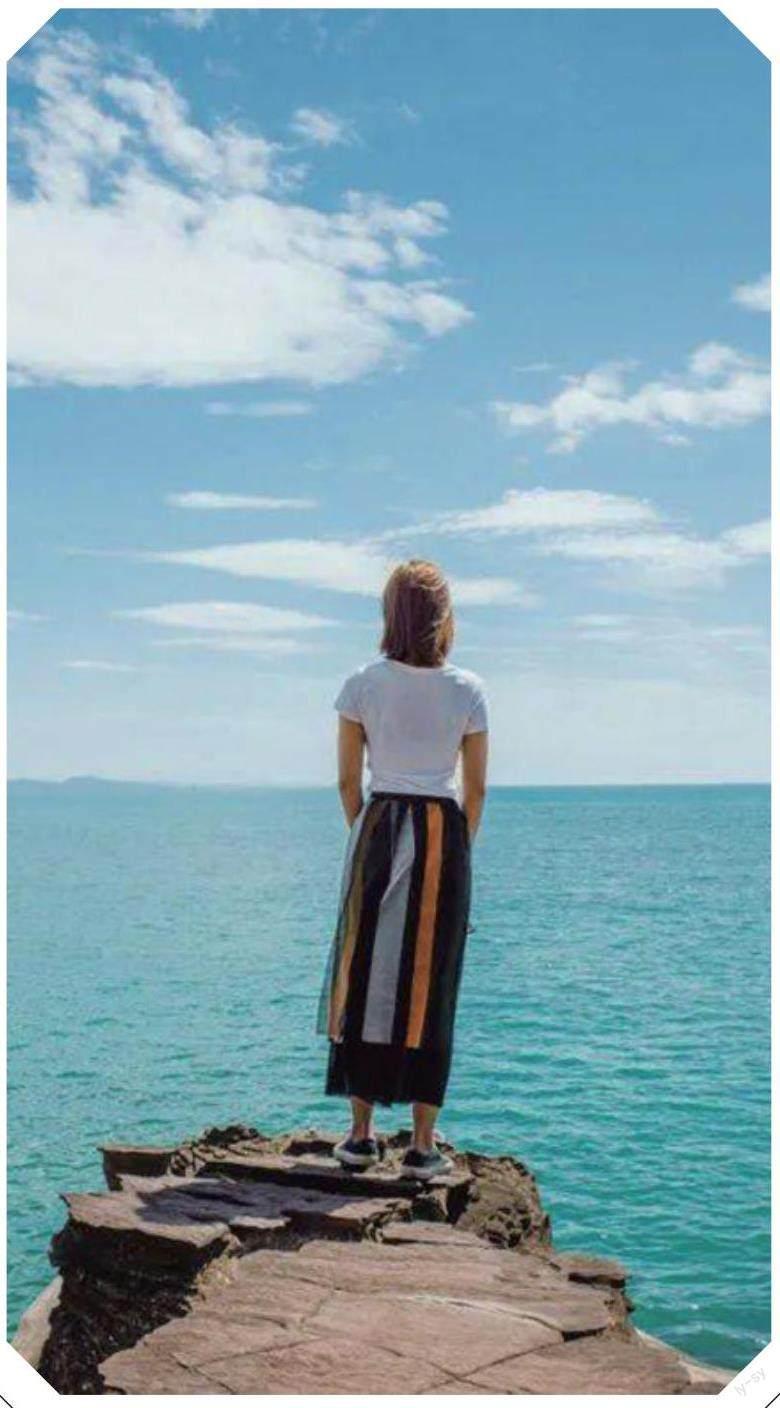
记忆
在继母来之前,我的记忆是很破碎的。
我最早的记忆是在河北老家。那时候,父亲和生母还没有离婚,他们经常打架。我在老家上过几天学,有一次放学回家,我爸坐在门口等我,问我在学校里学什么了,我打开田字格的本子给他看,上面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我”。
父亲和生母离婚时,我也不懂那意味着什么,只是之后我再也没去过姥姥家,爷爷奶奶又过世得早,家里就剩下我和我爸两个人,他只好带我出去打工。到了北京,我们住的地方在丰台区西道口,是正对着铁路的一排平房,我爸租了其中特别小的一间,里面就有一张炕、一个灶台、一口烧饭的大锅,还有一个箱柜。
小时候,我爸其实挺疼我的,过生日的时候,他会买2块钱的炸鸡排给我吃。我爸对我的爱其实是粗糙的、沉默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挺快乐、自在的,我跟我爸在一起,有吃有喝,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也不觉得自己在吃苦。
后来,继母就来了,开始跟我爸搭伙过日子。继母真的给我带来太多摧残,不仅是身体上的,更主要是精神上的。比如有一次,学校要收学杂费,她拖了很長时间不给我。老师让我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罚站,说什么时候把钱交上,什么时候停止罚站。那种感觉像被拉出去示众,对自尊心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我还是班里的课代表,觉得太丢人了,我不理解继母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心想,大家不是都喜欢好学生吗,所以我就认真学习。我经常拿奖状回家,没想到继母直接把奖状烧了,还让我把灰烬扫干净。我的自信就这样一点点被磨掉了。
在学校,我也交不到好朋友,因为打工子弟流动性特别强,同学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今天来了,明天走了。在我的概念里,友情是短暂的,伙伴是会突然消失的。
我的成绩一直是数一数二的,老师也说我是个好苗子,但父亲从来没有因此夸过我,上到初一他就让我出去打工赚钱。他身边人家的孩子都是这样的。那时候,我深陷在继母制造的痛苦里,一心想着只要不在家里待着,怎么着都行。就这样,我离开了学校。
孑然一身
我打的第一份工是在山西一家饭店当服务员。父亲把我送到木樨园客运站,买好了票,让我自己坐客车到太原,到了那边会有人在车站接我。上大巴车前,他偷偷塞给我200块钱,让我照顾好自己。
第一次离开父亲和家,想到新环境,我没有害怕,反而很激动。在饭店,我的工作是给顾客点单、端菜,站在包间门口等顾客叫,还要给客人推销酒和饮料,然后收集瓶盖儿来拿提成。
做服务员虽然是一项集体工作,但我还是没办法跟同事交朋友。交朋友的前提是认识自己,我从学生突然转变为打工者,没有经历逐渐社会化的过程,经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怎么跟别人交流。那种感觉就像一头没睡醒的小牛,突然被丢到地里,和大牛一起拉犁,小牛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机械地模仿。在饭店里,我仿佛是一个空心人。
那几年,我总是干不满一年就换一份工作,做过电话销售,装过暖气片,在网吧当过收银员,还被骗去过传销组织。为了生存,我必须努力挣钱。
走上社会,我感觉自己已经孑然一身。2009年父亲去世后,我更是完全没有支点了。那天,我突然接到亲戚的电话,亲戚说“你爸快不行了,快去医院看看”。我这才知道,我爸出了车祸,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没希望了。我在拔管之前见到他,他的身体是热的,手也是温的,但已经没有意识了。那时临近中秋,前几天我爸还给我打电话,问我中秋要不要回家,我说:“不回,我回去干吗?”我只是在赌气。不承想,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声音。
父亲走了之后,我被动地完成了亲情的切割,最后一丝家庭联系完全断掉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托住我。其实当时我完全不理解“死亡”,父亲的死好像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还是该上班就上班。直到这些年,之前没有处理好的情绪,会时不时冒出来,比如听到某首音乐、看到某个东西,我会突然想到父亲。
重生
自卑对我来说是一种阻力,也是一种推动力。
2011年,我成年了,开始在北京一家快递公司当客服。那时候,我没有特别清晰的自我认知,但对当下的生活有了具体的感知。我每天负责处理客户投诉,所做的工作都是工具性的,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被看见的“人”。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摆脱这种机械和麻木。
在一次投诉中,我认识了一位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在网上聊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对我说:“你挺聪明的,人生不应该止步于此,你应该去参加成人考试,继续接受教育。”
在网络上了解了自考以后,我很快选定了北京大学的心理学专业——一方面觉得自己有些自卑,另一方面想通过学心理学更加了解自己。上班的时候,我把考试用书放在手边,边看书边工作。下班后,我回到月租200元的木板隔断房,房间非常小,连张桌子都没有,我就坐在床上学习。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可以那么专注,完全沉浸在备考状态里,所有能量都汇聚在书上的字里行间。
第一次考试,我报了4个科目,都高分通过了。从专科到本科,加起来一共30多个科目,我考了大概4年时间,终于在2015年拿到了北京大学的学历证书。我好像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重生。
关系
早早进入社会,相当于我跑在了很多同龄人的前面,但也失去了很多东西。
对我来说,一个很难的事情是把自己的情感交付给他人。我不是一个轻易对别人交心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不会永远待在我身边的,可能很快就走了。所以,我会跟朋友真心相处,但也可以接受一个人随时断联。
当然,我的男朋友一直在我身边。我跟他是在自考的学习群里认识的,那会儿他20岁出头。通过接触,我知道他的父母也离婚了,他是在姥姥姥爷身边长大的。后来,我们合租一起备考,彼此引导,日久生情就在一起了。
在相处上,我最初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在感情上,我比较贪婪,非常需要他在身边;我常因一些小事和他闹别扭,就像孩子用吵闹引起他人关注一样。有时候,我会因为不安全感闹脾气,且很容易吃醋。我知道这是一种不健康的亲密关系,所以一直在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好在他有耐心,也比较包容,最主要的一点是,他真的打心底里重视我、肯定我。没有他的支持,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2016年,我跟男朋友准备换工作,就离开北京来了深圳。选择深圳的原因很简单,我听说深圳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裙子——我觉得自己很矮,不适合穿裤子,适合穿裙子。
在深圳,我顺利找到一份金融工作,一个月工资过万。刚开始,我很有干劲,干了一年,跟男朋友在深圳买了一套小房子,拼命工作还房贷,但越干越迷茫。我感觉到,虽然从机械的工作里走了出来,但在企业里,个人是那么渺小无力,我的投入与幸福回报比特别低,我深陷于很多当代年轻人共有的因意义感缺失而产生的迷茫中。
这时,一个朋友跟我提到,香港理工大学的设计专业很不错,跟我之前做过的产品经理的工作密切相关,建议我去试一试。我其实挺擅长读书,所以就想,不如把我的优势发挥出来,换一个赛道,继续读书,看看在学术领域能不能有所建树。我再次有了往上走的目标,决定去申请香港理工大学——一方面可以摆脱学历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想体验校园生活,弥补我没有怎么上过学的遗憾。
2018年,一个温暖的冬日早晨,我醒来后打开手机,第一眼就看到香港理工大学发来的录取通知。我趴在床上高兴地笑了。
蜕变
现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我们跟人的沟通有两种,一种是工具性的,一种是意义性的。在工作中,我很容易被当成螺丝钉,但学校是一个剥离了利害关系的地方,我跟同学和老师能够平等地相处。在相处的过程中,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真正地得到了认可和尊重。
我的角色变了,身边人的角色也变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开始进入我的生命。我认识了一个俄罗斯女孩,在中国人的审美里,她肯定算胖的,但她爱穿短裙,总是特别自信。有一次,我们俩在草坪上坐着,看到有人在弹吉他,她就和着吉他唱了一首《喀秋莎》,身边人都为她鼓掌。在学校的广场上,我还看到跳舞团里有一个女孩跟我差不多高,站在身材修长的女孩们中间,她跳得不算好但是非常自然。我恍然大悟:身材不完美的人也可以很舒适、很自信地展示自己。
这样一群人虽然不完美,但活得那么阳光、那么有勇气,所谓“缺点”也丝毫不妨碍身边的人喜欢他们。这带给我一种很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我开始慢慢地把自己打开。
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2020年申请读博士的时候,竞争非常激烈,申请者大都来自国内外顶尖的学校。我向一位老师提出申请,但他的研究方向跟我的不匹配,面试完之后,我就觉得没戏了。可是有一天中午,我突然收到另一位教授的邮件,对方表示愿意当我的导师,如果我同意,就在当天下午4点前回复邮件。当时,我完全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在相关领域是全球有名的教授,只是考虑到能继续上学,我就同意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看了我的简历,知道我工作了十几年,没怎么上过学,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后才来到香港理工大学的。教授凭着这些经历直接选中了我。他说,他尊重像我一样努力的人。他还说,之前他也有一段边打工边求学的经历,知道那样很辛苦,所以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我感觉自己真的被看到了。在那之前,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做成什么事情,也沒有取得什么成就。但他让我意识到,原来成就不一定要用考了多少分、挣了多少钱去衡量,我经历的所有痛苦、克服的所有困难,都是我的成就。
我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过去,发现它们并不是人生的污点,而是我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正是那些我想摆脱的生命底色,让我成为我。
我学会跟自卑相处、和解,活得越来越轻盈。当然也有放不下的,比如父亲的死亡、母爱的缺失,但我觉得复杂的情绪体验是人生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我不是一个自怜自哀的人,也不会拖着很重的东西前行,否则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