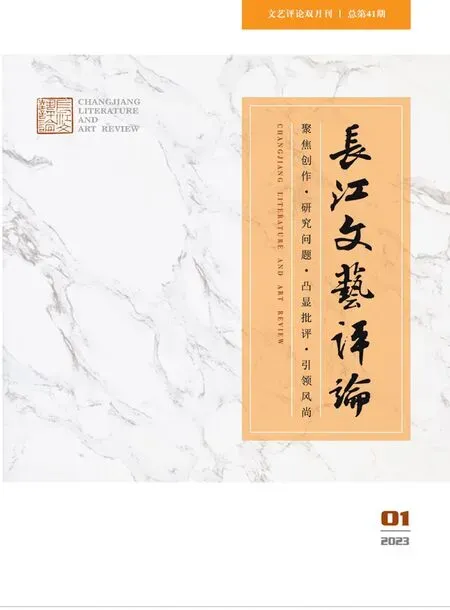古远清学术研究的前沿性
——以《古远清选集》为例
2023-09-01江少川
◆江少川
古远清一生出版了44种专著、29种编著,总共七十多种,学术历程半个多世纪,却极少出版论文选集。现在我们见到的论文选集有两本:一本是2002年马来西亚爝火出版社出版的《古远清自选集》,另一本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古远清选集》。前一本在海外出版,而且时间较早,国内不容易看到。后一本2016年在国内出版,时间上比第一本晚十多年,是唯一一本在国内出版的最有代表性的选集。花城版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由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这部选集虽未标明“自选”,其实是由作者自己选定的,为名副其实的自选集。选集分三辑:即华文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囊括了他研究华文文学的三大板块,收论文15篇。选集书名为《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古远清选集》,可见作者本人对前沿性何等看重。而书名中的前沿性,概括了古远清学术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古远清的著作超过千万字,这部选集只有26万字,可谓古远清华文文学研究成果的高度浓缩精华版,它是一个窗口,从中可以窥探到他的学术思想、研究特色,审美追求与学术个性,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也。
所谓前沿性,我以为对它的理解应该是多向的,一是研究方向的前沿,包括学科方向,研究重点或研究类别等;二是某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热点、焦点或敏感话题;三是某些领域存在的学术问题,或有分岐、有争议,或处边缘、未定论、未被研究的问题等也可纳入。
一、学科研究方向的新拓展
学科研究的新视点、新动向、新拓展从来是学术研究的前沿。古远清从踏入文坛,研究文学以来一直秉承这样的理念,在学术研究方向上特别关注前沿问题。他最早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以研究鲁迅与当代诗学为主攻方向。尤其关注当代诗歌研究,而且把目标锁定在当时诗歌研究的前沿,即诗歌批评。这里的诗歌批评重点不在于研究诗人及其诗歌作品,主要是研究诗评论家与有关诗歌理论。当代文坛,显然是研究诗人诗歌的多,而研究诗评论、诗评论家者少。古远清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写的《中国当代诗论50家》《诗歌分类学》《诗歌修辞学》以及稍后出版的《留得枯荷听雨声——诗词的魅力》等,构成他早期研究新诗的系列成果。《中国当代诗论50家》出版后,立即获得文坛好评,被称为是一件有开创意义的工作,拓宽了诗歌评论的新领域,为意味深长的全景式俯瞰。樊星在《诗论的拓荒之作》一文中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阅读、整理了200多种当代诗论著作的基础上,中肯地评述了52位诗论家在中国当代诗论研究中的独特成绩,并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见解。因此,这是一部堪称研究当代中国诗歌和诗论的必读书”[1]。古远清从研究新诗拓展到研究台港朦胧诗,出版了《台港朦胧诗赏析》《海峡两岸朦胧诗品赏》等四本书,以研究台港朦胧诗为契机,又萌生出向新的研究领域拓展的想法。他说:“从1989年开始,我又开辟了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台港文学”,“我只能从我熟悉的台港现代诗研究做起。先有《台港朦胧诗赏析》,后有《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问世”[2]。这一次的学科新拓展,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学术研究转型,这一大步改变了他学术研究的大方向,使他成为台港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与大家。
进入台港文学研究领域,古远清从来不会原地踏步,他总是在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力求独辟新径。就国内而言,有学者主编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史等多种,他却专注于台港文学理论批评,出版的有关台港的文学批评史、类文学史著作有9部之多。晚年又重写台湾文学批评史,补充更新大量新内容,完成四卷的精装本《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在研究台港文学的同时,他还把研究的范围扩展到澳门文学。如果把跨世纪前后二十年看作他的中期研究,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及以后就是他学术研究的晚期。2003年古远清在吉隆坡接受《南洋商报》记者的访谈,就萌生出拓展研究新方向的想法。紧接着从2004年起,他连续三年编选《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到2013年又开始编撰《世界华文文学年鉴》,从而开始了研究世界华文文学的新征程。到2016年出版《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古远清选集》,正坐实了他又一次拓展学科研究方向的心愿。这本选集的三辑中,他将华文文学研究放在第一辑,而这一辑的首篇论文就是《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前沿理论问题》,并就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进行了探讨。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存在一系列学术难点,需要进一步厘清和探讨。这篇文章是他企图构建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的发轫之作、构架蓝图。他在此文中非常肯定地指出:“2002年成立有‘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这个学会的成立,标志着华文文学已由过去的课题性研究,转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这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和弘扬中华文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也不能片面理解为名称的简化,因为这种命名提升了过去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品位。”[3]同时在文中他还初步概括出这个新学科“全球性、本土性、延缓性与交融性”的学术特征。选集出版以后第五年,古远清独自撰写的专著《世界华文文学概论》问世,这也是学界第一本由个人撰写的世界华文文学类文学史的重磅之作。
古远清学术研究的创新意识早在八十年代就已萌生,1988年他出版了42万字的《文艺新学科手册》,收录有145门文艺学和美学方面的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分支学科。那时,学科创新的种子就已经深埋在他心底,或许开始形成一种意识。新世纪以来,他在研究台港文学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把目光盯住了世界华文文学,编选出版了3本年度《世界华语文学作品选》,从第二个十年起,他同时开始了《世界华文文学年鉴》的编写,《世界华文文学新学科论文选》的编选,终于在2021年出版《世界华文文学概论》,为构建这一新学科贡献出自己毕生的心血。他对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具有鲜明的学科意识,同时初步概括出新学科的本质特征。《世界华文文学概论》的出版,可以看作建设这门新学科的碑石之作。
二、台湾文学争论中的铁笔
台湾文学史的撰写是新世纪以来两岸学者高度关注的学术问题,“在台湾学研究中,有一些政治敏感的问题,是许多学人回避的,但是,古远清却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学术坚持。”[4]选集中涉及文学史的论文有5篇,占此著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见分量之重。古远清曾经多次卷入台湾文学的论争,也受到过质疑与非议,对此我们应当分清是非曲直,给予科学的评价。在台湾文学的争论中,他就是一名骁将,一支铁笔,在大是大非、文化立场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以下从三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台湾文学的属性之争。
关于台湾文学的属性,这是两岸台湾文学史撰写绕不开的前沿问题。首先,他在《新世纪两岸对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以“反攻”大陆学者写的〈台湾文学史〉为例》论文中谈到台湾陈芳明、钟肇政、林瑞明这三位属于指标性人物。对台湾文坛的“双陈大战”之争,即陈映真与陈芳明关于台湾文学史之争,古远清的立场泾渭分明:他认为“‘双陈’争论的主要不是台湾文学史如何编写、如何分期这一类的纯学术问题,而是争论台湾到底属何种社会性质,台湾应朝统一方向还是走‘台独’路线这类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5]。
钟肇政在《台湾文学十讲》中给台湾文学下定义时,公然提出:“台湾文学就是台湾的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的一支,也不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6]古远清指出这本书台独意识浓厚,在两岸争夺台湾文学解释权方面具有典型意义。
而林瑞明提出“台湾文学应当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来书写”,“台湾已有将近百年独立于中国”,“独树一帜的台湾文学,既非日本文学,更非中国文学”,古远清撕开这位台湾文学教授的掩护术,道出他“对台湾文学的诠释隐含了一个权威‘台湾学者’身份,其代表的是‘台湾文学的主权在台湾’的立场”。[7]
从以上论争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在两岸文坛勇斗“文学台独”的骁将身姿。在这次争论中,古远清也曾遭到“文学台独”文人的攻击与谩骂,但他毫不退缩,像一个斗士捍卫着台湾学术研究的疆域。
第二,关于作家创作自由。
在《名不副实的〈世界华文新文学史〉——兼评台北有关此书的争论》一文中,对台湾成功大学教授马森出版的三卷本《世界华文新文学史》,古远清不仅指出这本史的一些硬伤:如作家的生平、出生年月、担任职务等方向的出错,还指出结构篇幅安排的失衡与不合理等问题。如马森在其文学史中说:“足见非共产党员不可能写作,而想写作的人也非要事先入党不可,这正是共产党控制作家的厉害处。”[8]对此,古远清严正驳斥道:“表现在叙述大陆的创作环境时,总不会忘记直接宣传台湾如何创作自由而共产党如何粗暴不懂文学不讲人性,一直扼杀创作自由”,“众所周知,在大陆有许多像笔者那样的非共产党员作家在写作”[9]。还特别点出有的省、市作协主席就是非党人士,原中国作协主席巴金也不是中共党员。以中国作家最权威的创作机构的领导为铁证进行反驳,极有说服力。
第三,如何评价皇民文学。
如何评价皇民文学,是写台湾文学史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考验史家或学者的试金石。日据时期的皇民文学,是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开展的皇民化运动的的产物,为日本军国主义唱赞歌,美化日本天皇。而台湾作家钟肇政竟然借《台湾文学十讲》提出宽容看待皇民文学,认为在日本人的高压统治下,作家写一些违心之论情有可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能用苛刻的眼光看待,公然为“皇民文学”叫屈减压。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写了一本《华语圈文学史》,他在此著中讲到皇民文学说:“所谓皇民文学就是以协助战争为主旨,……是将六百万台湾人民所共有的战争体验,加以论说化的产物。”“所谓的皇民文学,是就其对于非日本人而等同于日本人,却对新的日据时期的民众又抱有优越感的台湾人的观念与情感而言的。”[10]尽管藤井省三在书中对皇民文学的表述比较暧昧与隐晦(此书已在国内翻译出版),古远清仍然以其火眼金睛,一眼看出这位日本人的右翼立场,他在《研究华语文学的歧路——评“华语圈文学史”》一文中尖锐指出:“出自日本右翼立场的藤井省三,过分夸大,甚至可以说无限拔高皇民文学即汉奸文学对台湾人民产生的所谓‘为台湾公众所共有’的恶果,这并不是严谨的学者所应采取的科学态度。”[11]
他在文中笔锋犀利:“所谓皇民文学,通俗来讲就是汉奸文学。”“这个在台湾历史上没有地位的日本法西斯国策文学,之所以在台湾沉渣泛起,是因为为皇民文学翻案可拟抹杀民族大义,这正与当下台湾汹澎湃的‘台独’思潮相吻合。”[12]这一段批判文字尖锐犀利、力透纸背,揭露出这类文人别有用心的反动本质。
三、对台港作家身份辨析之洞见
华文文学领域中,有些作家的身份定位与评价比较复杂。古远清认为:“作家定位问题或曰归属,牵涉到国族认同和文学分类体系。”[13]所以对这个领域中有些身世经历复杂的作家,虽然都是华人,其身份定位也是值得探讨的前沿问题。
先谈他对台湾作家的身份定位。同是华人作家,就中国而言,有大陆、台港澳的作家,中国以外有海外华文或华人、华裔作家等。如张爱玲,生于上海,18岁去香港上大学,后因战争原因返回上海,1952年再度去港,写下长篇《秧歌》与《赤地之恋》。新中国成立,她没有跟随国民党去台湾,而是从香港去了美国。可是台湾的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中居然把张爱玲写进去了,用很大篇幅把张爱玲的影响写进书中,并说最完整的张爱玲还是只有在台湾可以看见。台湾“文建会”居然把张爱玲的《半生缘》列为三十部台湾文学经典。对此,古远清在《王洞爆料所涉及的夏志清的评价问题》一文中指出:陈芳明是“用偷梁换柱的方式巧妙地把张爱玲写进去,这很值得质疑”,这里的“偷梁换柱”,是指一位作家对某地影响大就可以定位为此地的作家吗?此即偷梁换柱、偷换概念也。古远清认为张爱玲“是原汁原味的上海作家,也许勉强可以称她为香港作家,但绝不可以将其强行绑架为台湾作家”[14]。这是非常准确而公允的定位与评价。
又如夏志清,他是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他早年从大陆赴美国留学。旅居美国后加入美国籍,自然是美国人。但对这类学者的身份也有个定位问题,以便研究他的地域归属与学术成就。他1946年赴美留学时还未踏进文坛,更不用说有学术成果。所以首先排除他是当代大陆作家的可能,可以将其归为海外华人作家。他赴美以后的著作大部分在台湾出版,而且经常频繁参加台湾的重要文学活动,一度是台湾两大报的海外发言人,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亲台倾向。古远清在《王洞爆料所涉及的夏志清的评价问题》一文中列出6条论据,特别是他积极热心投身台湾文学活动,俨然是台湾文坛的掌门人。“他身在海外,心系台湾,将其定位为台湾作家或台湾评论家更为恰当”[15]。
古远清对以上两位作家的辩析,是从他们离开祖国母体以后的文化立场与倾向、他们的文学活动实践进行辨析得出的结论。有理有据,实事求是,令人信服。
再看古远清对香港特殊作家群的定位评价。在论文《外流作家,从逃亡港澳到定居珠海》中,他谈道:“对台港澳文坛存在的偷渡作家群这一创作现象,学术界一直无人问津也不便问津,更谈不上系统性与权威性的批评话语实践,这不仅与研究环境有关,而且与研究对象的隐私有一定的关系。”[16]论文首先肯定香港有个“偷渡作家群”,并且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引用习仲勋的讲话:“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17]正是对偷渡作家的这种定性,成为研究这这波作家群的理论依据。基于这种观念,研究偷渡作家的经历与其对香港文学的贡献也就顺理成章,有据可依了。
文中提到的有代表性的香港作家,一是倪匡,被称为偷渡作家群的先行者,古远清高度评价他的创作增添了香港文学的新品种,以仅次于武侠小说的科幻小说创作成就独树一帜,开创了境外文学科幻小说之先河。“偷渡作家遵循一要温饱,二要发展的信条,将人的生存作为第一要素的生存实践。”[18]倪匡到香港后为了谋生什么都写,武侠、科幻、奇情、侦探、推理、文艺,由于他的创作成就,1987年当选为“香港作家协会”创会会长。
另一位是寒山碧,他在其自传中就坦率地写到自己三次偷渡的经过。他到香港后,勤奋写稿,有一次国民党驻港要员邀约他写文章,后来得知写文章出丛书原来是作为情报提供内部参考,所以此后那位要员邀请他参加台湾重要活动都被他婉拒了。古远清评价道:“按寒山碧的出生与经历,本该亲近国民党,拥护国民党,可是他对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十分失望,顿时感到不能不忠于自己的良知,不愿意背叛自己做人的原则,庆幸此生没有去做反共义士。”[19]古远清高度评价寒山碧的编缉工作与文学成就,赞赏他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坚守人文品格。
对香港偷渡作家群这样一个几乎无人敢碰的话题,古远清却知难而上,通过对他们在特殊历史岁月中曲折人生的考察梳理,理清了他们的前世今生,并依据他们的政治态度、文化立场与文学成就,为其正名并给予公允的评价,肯定了偷渡作家群在香港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对撰写香港文学史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四、古远清的学术个性
所谓文如其人,不仅是指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而言,同样适用于文学研究者。《古远清选集》中表现出的这种前沿性特征绝非偶然,这与他的学术个性密切相关。在学界,古远清被称为“另类的文学史家”“纯粹的学者”“一位独行侠”“文学界的劳动模范”“一位年长的青年学人”“把学问当成快乐事业的人”与“学术警察”,这些称谓视点不同,但都特别准确、形象。他是一个极有个性的学者、学术研究界的奇人。
首先是敏锐求新。敏锐,指一种眼光,思维能力。他善于发现问题,这是萌发学术研究的缘起,求新是指求变,不落俗套,另辟蹊径,发人之未发,发现学术研究的新问题。这是一种探索精神,一种学术的自觉性。他学术生涯中的几次研究转型,都源于这种敏锐求新的探索。
其次为执着坚守。古远清选定研究方向,寻找到某个课题,或遇到某些棘手的学术纷争,总是坚持已见,绝不动摇,咬定青山不放松,典型的一根筋精神。他卷入许多学术论争,从不畏惧,面对台湾文学史撰写的多轮论辩,在“余古之争”“双陈之争”中都是观点鲜明,哪怕对簿公堂也据理力争,一定要辨明是非,澄清事实。
第三是学术自信。自信是一种信念、底气与信心。古远清的学术自信一是来自于他深厚的学术功底与学术成就;二是来自于他对学术痴迷与乐此不疲的写作心态;三是来自于他的学术追求与锲而不舍的精神。他的文化自信,他的学术坚持,诚如一个访问者所说,表现了一种“文学研究的血性批评风格,这不能不令人仰慕”[20]。从《古远清选集》,我们看到了他学术研究的雄心豪情和从不服输的精神。古远清一生著作等身,成就卓著,与其自身的文化自信密不可分,这是一种极为可贵的学术品格。
注释:
[1]樊星:《澳门日报》,1993年11月11日。
[2]《古远清的文学世界》,香港文学报社2011年版,第13页。
[3][5][6][7][8][9][10][11][12][13][14][16][18][19]《古远清选集》,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169页,173页,176页,79页,79页,173页,93页,174页,53页,55页,246页,248页,249页。
[4][20]孙绍振:《推荐序·古远清的勇气和学术坚持》,《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第一册,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4页,4页。
[15]古远清:《台湾文学焦点话题》下册,台湾万卷楼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315页。
[17]参见《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